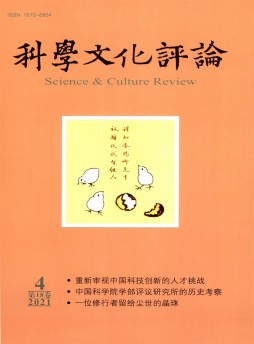科學文化哲學是其未來走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科學文化哲學是其未來走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提要】從科學哲學到科學文化哲學,是新世紀科學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從科學哲學到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從根本上改變科學哲學的狹隘定位,從而使其走出現有的困境,而且還將大大拓寬科學哲學的研究視野,從而為科學哲學的發展開辟頗為廣闊的前景。
【關鍵詞】科學/文化/哲學
【正文】
1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領域里,逐漸出現了不少新的亮點。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就是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
所謂科學文化哲學,大致可以看做為這樣一種學科或研究方向,即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從而對其進行哲學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學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依然是科學,只不過是它將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來研究,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做認識論的研究,因而它既區別于傳統的科學哲學,又區別于一般的文化哲學;其二,科學文化哲學研究依然是一種哲學研究,因而它比科學歷史學、科學社會學等元科學更加靠近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果說,我們將傳統的科學哲學理解為是一種狹義的科學哲學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廣義的科學哲學。更進一步說,科學文化哲學將是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深化和拓展。
2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有著深刻的理論背景。它是在20世紀末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重重困難的情勢下孕育和產生的,可以說是對科學哲學的一種重大突破與發展。
眾所周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在20世紀下半葉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即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然而,這兩次重大轉變不但沒有使西方科學哲學從根本上擺脫理論困境,反而使其大傷元氣,逐步從興盛走向衰落,甚至趨于解體。
那么,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徑可以使其解開癥結,從而擺脫現有的困境呢?筆者認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在于,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學科定位或框架過于狹隘,以致無法應對和解決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所固有的深層矛盾和問題。因此,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則是一條使科學哲學擺脫現有困境的重要途徑。
具體說來,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基本框架是認識論的和分析哲學的。它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其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學)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邏輯實證主義對“世界的邏輯構造”也許可以看做是所謂“正統的”科學哲學的最高成就。
然而,隨著20世紀60和70年代以來科學哲學經歷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顯然,邏輯實證主義者所研究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邏輯結構,歷史主義者所關注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歷史發展,而后現代主義者所強調的主題則是如何理解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
隨著科學哲學主題的重大轉變,人們不難發現,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實質上已經大大拓寬了。邏輯實證主義者把科學哲學看做是“經驗科學知識論”,也就是看做認識論的一個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歷史主義者不僅將研究“科學(知識)的邏輯”拓展到研究科學(知識)發展的合理性問題,從而大大拓寬了“經驗科學知識論”的研究,而且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等學科聯系在一起,使得科學哲學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于是,他們更多地關注科學發展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對科學的影響和作用,強調科學并不是價值中立的,它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可以說,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已經從認識論延伸到了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
至于后現代主義者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則更加寬泛了。他們所關注的焦點與其說是科學,倒不如說是“文化的整體”,特別是人文文化。他們反對將“科學的整體”從“文化的整體”中區分開來,強調在“文化的整體”中來理解科學,特別是以人文主義的視角來理解科學,用模糊主義的整體論來徹底模糊科學與藝術、政治乃至>宗教的區別。于是,他們不僅將科學消解于整個文化(特別是人文文化),而且還將科學哲學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學(特別是人文哲學)。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其癥結就在這里:
一方面,隨著科學哲學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和內容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仔細考察歷史主義科學哲學所研究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例如,科學與價值問題、科學進步問題和科學合理性問題等等,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所能應對和解決的范圍。它們所涉及的領域從根本上說不僅是認識論的,更是科學文化哲學的;而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方法當然不僅僅是分析的,更須是綜合的、辯證的。
另一方面,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被約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它的視野要比邏輯實證主義寬闊得多,但是,很明顯其基本定位還是認識論的,而不是科學文化哲學的。他們只是提出了科學與價值(文化)相關聯這個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對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許多情況下,歷史主義者們,例如,拉卡托斯、勞丹、夏皮爾等人往往回避各種復雜的文化因素去建構自己的科學進步模式或科學合理性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關注的依然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它與邏輯實證主義不同的是,邏輯實證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知識的邏輯,而歷史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發展變化的邏輯(例如“科學革命的結構”、“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進步模式”與“科學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說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的邏輯構造與實際的科學知識嚴重脫節的話,那么歷史主義的各種“結構”、“邏輯”和“模式”與實際的科學發展也有很大的距離。
后現代主義者似乎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及其癥結所在,于是,費耶阿本德不僅“反對方法”,而且還“告別理性”,宣告科學哲學行將終結。費耶阿本德觀點的合理因素在于:在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內,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費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無政府主義的認識論和非理性主義,關鍵還在于他并沒有超越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思維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論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則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學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應當干脆“告別理性”。羅蒂實際上也采用了與費耶阿本德相同的邏輯:在他那里,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線,那么,科學與其他文化就沒有任何區別;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沒有任何區別,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學(特別是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哲學)來消解并代替科學哲學。
由此可見,后現代主義并不是科學哲學的真正出路,后現代主義的后果只能導致科學哲學走向真正的終結。然而,隨著科學哲學的主題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確需要有一個重大轉變,那就是打破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使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從而從根本上解開使當代科學哲學陷入困境的癥結,推動科學哲學進一步向前發展。
3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使科學哲學走出現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還將大大拓寬科學哲學研究的視野,從而為科學哲學的發展開辟頗為廣闊的前景。
首先,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
事實上,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已經深深地觸及到科學價值論的內容。例如,庫恩解釋科學變化發展所使用的最關鍵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內容就是“價值”。在庫恩看來,每一個范式都帶有自身的價值標準,并且不同范式的價值標準是“不可通約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做出選擇,如同宗教皈依一樣,是“一種在不相容的共同體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選擇”,在這里并不存在一種可依據的客觀的合理的價值標準[3]。而勞丹為了克服庫恩的相對主義,寫了一本重要著作,書名就叫做“科學與價值”。為了避免價值問題的復雜性,勞丹做了特別的限定,強調他所討論的價值只涉及“認知價值”(即關于科學方法論的標準和規范)。盡管勞丹對庫恩的范式理論做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種比庫恩模式更漸進的科學發展動力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科學變化的連續性問題,但是,他對科學進步的解釋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終無法擺脫相對主義[4]。可以說,價值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的一大難題。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對價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應當對其做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說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側重點是對科學做認識論的研究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的側重點則應當轉向對科學做價值論的研究。
在科學文化哲學的視野里,科學價值論的研究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一方面,它將科學看做是一種具有豐富價值內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動,而不僅僅只看做是一種認識或認識活動;另一方面,它強調對價值的研究也應當是全方位的,而不應當僅僅局限于研究“認知價值”。總的說來,科學價值論大致包括以下兩大塊內容:一是研究價值對科學的影響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將科學放在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研究,從而揭示科學的動力、目的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這一塊內容與傳統的科學哲學有關,但其視野要比傳統的科學哲學廣闊得多。二是研究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價值,包括科學的技術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等等,從而揭示科學對于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對于人的生存、發展、自由和解放的意義和價值。這一塊內容顯然已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范疇,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之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代科學哲學在本質上是認識論的,而不是價值論的。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科學正在對人類社會產生著日益增長并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因而對科學價值論的研究其重要性就顯得越來越突出。杰羅姆·R·拉維茨指出:“現代自然科學活動已經改變我們的知識和關于我們對世界的控制,而在這個進程中,它也改變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諸多單靠自然科學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在他看來:“在當代,在關于對科學的理解方面最深層的問題是社會的,而不是認識論的。那些到達真理之類的較老的問題已經讓位于對科學的健康發展的關注和對其應用的控制的關注。”[5]盡管拉維茨的觀點似有可商榷之處,但它的確從一個角度(即從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影響這個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學價值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其次,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學各分支,從而使科學哲學具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正如前面所說的,傳統的科學哲學充其量只是對科學的認識論研究,而不是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盡管認識論也是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無疑哲學要比認識論廣闊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至少不是完備的科學哲學。由于科學哲學的定位過于狹隘,因此,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很難有恰當的學科歸屬。按照現行的做法,只能將認識論的部分劃歸于科學哲學,而將非認識論的部分分別劃歸到科學社會學、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倫理學、科學美學等元科學各分支,這樣一來,對科學的哲學研究事實上處于一種非常松散的狀態,有些研究(例如科學價值論的研究)甚至沒有一個恰當的元科學分支可以對應。顯然,這種局面不僅有礙于對科學做全方位的哲學研究,而且對于推進科學哲學的發展也是極為不利的。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而且有助于將滲透在元科學各分支當中的哲學思想挖掘出來并且整合起來,從而建構起更加完備的科學哲學,并使其朝著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邁進。
我們不妨以比較成熟的元科學分支即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歷史學為例,來探討一下整合元科學的哲學思想的可能性。
在筆者看來,科學社會學對科學的理解既是社會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將科學看做是一種社會體制,又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活動。于是,科學社會學的定位從一開始便帶有交叉的性質:一方面,它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因而毫無疑問屬于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一種特殊的文化活動,因而它與科學文化哲學密切相關。一般說來,科學社會學的實證研究部分基本上屬于社會學的范疇,而它的理論思辨部分則帶有很濃的科學文化哲學的色彩。事實上,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在理論層面上不僅是交叉的,而且還有許多重疊的地方。例如,默頓關于科學家的行為規范、科學的精神氣質等多項主題的研究,顯然是理論思辨的,而不是實證的,因而與其說屬于科學社會學范疇,倒不如說屬于科學文化哲學范疇。從更深層次上說,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兩者之間其深刻的關聯在于: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社會學研究,離不開對科學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離不開科學文化哲學;另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哲學研究,同樣也離不開科學社會學,因為科學文化活動在本質上是社會的。可以說,科學文化哲學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的理論基礎,而科學社會學又為科學文化哲學提供強有力的社會學的實證支持。
我們從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的深刻關聯中,不難看到整合元科學哲學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學社會學那里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有待我們去挖掘、整理、概括和總結。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學認識論研究(因為認識活動在本質上也是社會的)以外,科學社會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最重要的貢獻也許將在科學價值論這方面。例如,通過對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的研究(科學“內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內部來深刻地理解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通過對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科學“外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的外部來深刻地把握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和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從而更深層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離開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科學價值論將會變得非常空洞。
科學哲學同科學歷史學的關系似乎要比科學社會學更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強調,“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就科學編史學與科學哲學應該怎樣相互學習這個問題,拉卡托斯的觀點是:“(a)科學哲學提供規范方法論,歷史學家據此重建‘內部歷史’,并由此對客觀知識的增長做出合理的說明;(b)借助于(經規范地解釋的)歷史,可對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作出評價;(c)對歷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經驗的(社會—心理學的)‘外部歷史’加以補充”[6]。這個觀點無疑具有啟發性,但是,它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的關系,在本質上僅僅歸結為“規范的方法論”與“內部歷史”之間的關系(“外部歷史”僅僅是一種補充),未免太狹隘了。
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為科學文化哲學,而將科學史理解為科學文化發展史,包括科學本身的發展史(內部史)和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與其他文化的關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兩者之間的關系將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緊密得多。
事實上,許多科學歷史學家(特別是喬治·薩頓)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來理解和研究科學史的。只要打開薩頓所寫的科學史或科學史論著,我們就會感受到十分濃郁的文化氣息,體會到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有其自身的邏輯,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同哲學、藝術、宗教等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科學史不僅能夠為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研究提供重要的歷史學的線索,而且也將為整個科學文化哲學研究提供取之不盡的史料和素材。當然,科學歷史學與科學文化哲學之間的關系也絕對不是簡單的史料與理論之間的關系。應當看到,科學歷史學本身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例如,薩頓的科學史觀,包括他的新人文主義思想、科學與藝術相互關系的觀點等等實際上已經明顯屬于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了。可以說,科學歷史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貢獻將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認識論,也包括價值論、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科學社會學,還是科學歷史學,都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涵蓋面都非常寬,然而,傳統的科學哲學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種“內部的”科學哲學,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學哲學。這種狀況不僅導致科學哲學研究過于狹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學各分支處于比較松散的狀態。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到科學文化哲學,那么,后者也將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結果不僅將大大拓寬對科學的哲學研究,而且也將使元科學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有助于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真正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
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幾乎是整個元科學共同的使命。科學史學家薩頓說:“在舊人文主義者同科學家之間只有一座橋梁,那就是科學史,建造這座橋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來,科學史學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橋梁。科學哲學家瓦托夫斯基也認為,“科學哲學是科學和人文學之間的橋梁”。在他看來,“從哲學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科學的人文學理解,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
然而,盡管不少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離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離,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鴻溝依然很深。當然,導致兩種文化分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但是,應當看到,對于科學哲學來說,的確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別是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及其與此相關的狹隘的科學觀頗值得反思。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就體現了某種狹隘性。它不僅沒有設法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橋梁,反而在兩者之間劃了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表明科學與人文分別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叫做認識世界;另一個叫做體驗世界。新晨
毫無疑問,上述狹隘的科學觀與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遮蔽了人們的視野,使之看不到科學的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看不到科學與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聯系,而將其“看成為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做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8]這樣一來,關于科學的觀念就被大大狹隘化了。
顯然,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對于溝通兩種文化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將徹底打破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從根本上改變以往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從而有可能真正從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理解科學,理解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價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距離,深入考察和研究兩種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在兩者之間架起相互理解的橋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將真正肩負起元科學的共同使命,促進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融合。盡管有的科學哲學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學哲學成為溝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但事實上在傳統的科學哲學的框架里,幾乎很難實現,因為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范疇,因而不可能成為科學哲學的重要課題。然而,科學文化哲學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它將真正把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當做自己的重大課題,特別是通過揭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深刻關聯,來促進科學哲學與人文哲學、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從而推動整個人類文化的普遍繁榮和人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M].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序,2.
[2]江天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5.
[3]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M].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93.
[4]LLaudan.ScienceandValues[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64-66.
[5]JerorneRRavetz.ScientificKnowledgeandItsSocialProblems[M].NewBrunswick,1996.9,71.
[6]伊·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141.
[7]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51.
[8]M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7,58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