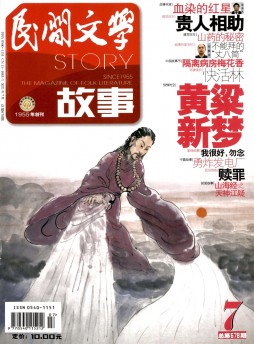民間文學法律保護模式構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間文學法律保護模式構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概述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這一概念,在我國的立法文件中最早見諸于199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該法第六條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雖然該法在此處用的是“作品”一詞,似乎和《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客體———作品一致,但筆者認為此處的“作品”實不能等同于一般意義上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因為若非如此的話,《著作權法》所稱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和國際上通用的“民間文學藝術表達”[2]一詞是同一含義。但《著作權法》并未對“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或作品)”作任何界定。筆者綜合了國際國內相關著述將之定義如下:所謂(中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或作品),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范圍內,有充分理由相信是由中國國民或某一民族集體創作的、世代相傳并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之基本組成部分的藝術表述。具體表現為民間傳說、民間詩歌、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服飾、民間建筑、和民間宗教儀式等等。[1](P49)
民族民間文學具有群體創作、口耳相傳、不斷變化、延續性長等特點,沒有形成固定下來的作品。因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一般意義上的“作品”相比,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或表達)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主體不同。作品的主體是著作權人,也就是創作作品的自然人或者依法享有著作權的法人或其他組織;而民族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或表達)是通過某個民族或某個地區幾代人的不斷模仿而進行的非個人的、連續的、緩慢的創作過程的產物,因此其主體身份不明確。第二,權利歸屬不同。作品的著作權歸著作權人(含自然人、法人與其他組織);而民族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或表達)因作者不是特定的個人,故其權利主體應為國家或某群體,具有群體性的特征。[2](P45)第三,客體范圍不同。著作權的客體一般只是智力成果,智力成果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必須依靠作品等載體形式才能為人們所感知;而民族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或表達)的客體除了智力成果這一無形表達之外,還包括客觀存在的具體之物,如民間建筑等有形表達,并且許多情況下是以無形與有形的有機結合而存在的。第四,保護期限不同。作品的保護期限是有限的,一般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亡后50年;但民族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或表達)因可以在傳承中不斷修改、補充,從而不斷完善和發展,仍處于不斷的演變之中,故其保護期限也應是無限的。早自我國《著作權法》問世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起,非洲、南美等地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由于具有豐富的民間文學藝術資源,首先提出了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主張,要求在國家及國際層面上建立一種特殊的保護機制,以對抗對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任何適當的利用,尤其對抗那些由境外人士實施的、利用民間文學藝術賺錢但卻不給予其發源地人民任何回報的利用。這些國家大多主張以知識產權的方式,或者更具體的說以著作權的方式對民間文學予以保護。而美國和歐洲等地的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因為自身文化底蘊不深厚,民族民間文化不發達,因此無法律保護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因為發達國家及其公民是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文化遺產的最大受益人,他們憑借手中掌握的現代技術,記錄甚至并依其好惡“改造”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形式,并最終借助各種化的大眾傳播媒體向公眾傳播以賺取大量的金錢和財富。所以發達國家極力反對以法律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其表面理由是:民族民間文藝表達屬于沒有特定權利主體的文化現象,并且超過了法律的一定保護期,故應被視為“公有領域”的東西,任何公民和組織均可以對其進行復制、表演、翻譯和改編,而無需征得他人的同意,更不必向他人支付使用費。因此那些自古以來就有的文化成果以及在傳統文化現象基礎上自然發展的民間文學藝術表達都將屬于共有資源,人人均可據自己所需取而用之。
由于我國在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方面存在立法的空白,使濫用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者有機可乘。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在疑惑,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作為一種歷史遺產,如果過分強調法律保護,這種資源是否會人為地被閑置,而不利于其傳承與發展?因此不積極主張進行相應的立法。筆者認為,不能坐等直至大量的傳統文化資源遭到破壞甚至滅絕,進而使受知識產權保護的創新失去了基礎,中斷了源泉,造成的損失已無法彌補時才感到痛心和后悔。何況,現代人以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為素材和源泉所創作的作品,尚且受到了國家法律的明文保護,并因此獲得了高額的經濟報酬。那么那些創造、傳承、發揚了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弱勢民眾、民族的創造性勞動又如何體現其價值呢?因此絕不能因噎廢食,而應該對我國浩如煙海的優秀民族民間文學藝術提供法律的、有力的、積極的保護。在選擇民族民間文學藝術法律保護的方式時,世界各國大多選擇了知識產權的保護模式,尤其是其中的著作權的保護模式。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二:其一,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與知識產權所保護的客體一樣,都屬于一種智力創造的成果。其二,知識產權制度已有幾百年的發展歷史,成為了一種全球通用的、較為成熟的法律制度,發展中國家希望借助知識產權制度而將保護民族民間文藝推向全球,藉此對抗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中的強勢地位。[3](P76)但是筆者認為,由發達國家極力推動而發展起來的知識產權制度,總體上是以保護創新為特征的。而民族民間文學藝術來源于傳統,是一種傳統的文化遺產資源,因此知識產權的固有理念不很適于對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
并且受知識產權制度中的著作權保護的“作品”,應該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已固定化的“成品”,而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具有延續性且仍處于不斷發展演變過程中,難以形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成品”。這表明《著作權法》因其固的的稟賦不能全面、有效的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上述種種沖突均傳遞出這樣一種訊息:即各發展中國家原先所設計的,單純仰仗知識產權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制度,因其先天的不足而難以發揮出制度設計者預期的功用,充其量也只是一種無奈的、過渡性的選擇,這就要求我們在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制度應有的作用的同時,將目光投向其他領域的制度。根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特征和國內外的相關經驗,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思路確立我國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法律機制:首先,應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資源,發揮知識產權制度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作用;其次,針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特征特別設立一些制度。即建立一種“知識產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特設法定權利”的綜合法律保護模式。
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保護
用知識產權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根本意義在于從法律上確認其是一種財產,有獨特價值,應該受到應有的保護。知識產權作為人們因智力勞動創造的成果所依法應享有的權利,包含有著作權、商標權和專利權等,其中的著作權和商標權都能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提供保護。
1、著作權法提供的保護。如前所述,與受《著作權法》明確保護的對象———作品相比,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確有許多特殊之處,但這并不能成為《著作權法》不能對它提供保護的理由。相反的是,在目前國家沒有專門立法規定的時候,我們更需要立足于現有的相關法律,盡可能利用已有的法律資源對之進行保護。由于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從總的方面說來也是一種智力創造的成果,與著作權的保護對象有許多類似之處。因此《著作權法》中的許多保護制度都可以用來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權利人和相關人。例如《著作權法》規定的著作權人享有的精神權利如署名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和著作權人所擁有的各項經濟權利,即復制權、演繹權、傳播權或表演權等均可用來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除此之外,與著作權有密切關系的鄰接權制度也應同時賦予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有關權利人。因此,應該在現有《著作權法》的框架內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力所能及的保護。在利用《著作權法》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提供保護的同時,應正視兩者間存在的差異,明確以下兩個問題:首先,《著作權法》中的權利主體一般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而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往往是特定區域、民族集體創作的結果,其具體作者身份不明、難以確定,因此屬于一種特殊的群體性權利,故權利人難以參照《著作權法》中的制度予以簡便的確認。按照修訂后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第15條第(4)款的規定,涉及作者不明的未出版作品時,如果有充分的依據認定作者為本聯盟某一成員國的國民,那么由何種主管機關代表作者在本聯盟所有成員國保護并行使其權利,將由各該國國內立法來確定。不烽國家的法律也往往授權具有管理職責的某一政府組織或者某一非官方組織、團體行使訴權,代表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群體主張民間文學藝術的智力成果權(如非洲的埃及、突尼斯等)。這一模式雖具有權力集中、方便管理等優點,但是更適合于民族單一且人口較少、領土面積較小的國家。而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十多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并且地廣人多、幅員遼闊,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也非常明顯,采取某一機構全權行使管理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保護職責的設想很不現實。因此,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以及《憲法》第119條的原則性規定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第38條的具體規定,在我國確立由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機關的相應職能部門(當地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和文化行政部門)為主的權利主體制度。授權上述主體在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這一群體性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依法主張權利。其次,著作權中的署名權是指權利人在作品上署名向世人宣告自己與特定作品間的關系的權利,其權利人一般為自然人或法人等,且具有確定性。而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因具有作者無法確定這一特殊性,故不能象一般文學作品一樣,由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來具體署名,但可籠統的用如“藏族史詩(《格薩爾》)”、“赫哲族民歌”或“景德鎮陶瓷”等字樣表明其歸屬。非權利人以某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為素材或源泉創作了新作品后應在作品中明確作“根據××××改編”的說明(如《烏蘇里船歌》一案判決的:注明“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
2、商標法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保護,應主要借鑒其中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制度。我國2001年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在第十三條(共兩款)和第四十一條第二款對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作了規定,商標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就相同或者類似商品申請注冊的商標是復制、摹仿或者翻譯他人未在中國注冊的馳名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不予注冊并禁止使用。第二款:就不相同或者不相類似商品申請注冊的商標是復制、摹仿或者翻譯他人已在中國注冊的馳名商標,誤導公眾,致使該馳名商標注冊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的,不予注冊并禁止使用。同時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二款還規定:馳名商標被他人搶先注冊后,若搶注人為善意時,馳名商標所有權人有權在該商標注冊后的五年內請求撤銷該注冊商標;若搶注人為惡意時,馳名商檔所有權人有權隨時請求撤銷該注冊商標。筆者認為,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和馳名商標一樣,都具有悠長的發展歷史,都能體現民族風格、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特質,都能提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都能給其合法權利人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因此,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商標法對馳名商標的上述特殊保護性規定,可以同樣適用于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保護。首先,當某一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如夜郎、侗族大歌等)被他人搶先進行商標注冊時,商標管理機關有權對該注冊申請予以駁回,不予注冊。其次,若搶先注冊成功后,權利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內(搶注人為善意時)或隨時(搶注人為惡意時)向有關機關提出異議,請求撤銷該注冊。
三、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保護
廣義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西方被稱作“經濟憲法”或是“自由企業的大憲章”[4](P312),是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基本法律。其立法精神為:禁止食人而肥或者搭便車;禁止不正當地投機取巧或者巧取豪奪;維護公平、誠實信用等商業倫理”[5](P2-5)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第1款規定:“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該條規定是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礎與靈魂,學界將這條規定稱為“一般條款”(所謂一般條款,是指能支配整部法律,在法律規定的具體事實構成不敷適用的所有地方,都能適用的條款[6](P36)),一般條款既是兜底規范又是競合規范。作為兜底規范,一般條款具有補充漏洞的作用;作為競合規范,一般條款與其他具體規范在適用時是并行不悖的,[6](P37)共同發揮著維護市場競爭機制有序、良性發展的作用。因此,采有一般條款制度既能保證法律的穩定,又能克服制定法固有的封閉、僵硬的局限性,使法律能夠靈活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規制各種新出現的不法行為。一般條款要求市場活動參與人不得為獲取不正當的利益而違反公認的商業道德。
而公認的商業道德,是市場經濟中為了克服市場缺陷,市場主體對市場所具有的共同的道德體悟和認識。[7](P77)它要求市場活動參與人在商業活動中不得從事極端的不合乎經濟倫理的行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文化的多樣性問題逐漸引起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的文明古國,在重視對民間文學藝術表達保護的同時,也要駕駛對民間文學藝術的發掘,在法律的框架下,使民間文化遺產成為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從而盤活文化遺產,弘揚我們的民族文化。盤活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應以“以效保護、合理利用”為原則,變消極保護為積極保護,將之進行合理的商業化開發。這一方面可以將我國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推向全世界,使世人都認識并折服于它們的絢麗多姿,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它們的商業價值為其自身保護提供足夠的資金。在商業化過程中就必須充分貫徹公認的商業道德。對于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市場化的過程中出現的諸如假冒抄襲現象、虛假標注作品來源和未以適當方式注明該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形式所出自的居民團體或地理位置等不正當行為,應盡量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精神和一般條款規定,進行強有力的打擊和制裁。但是,由于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與知識產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對象間畢竟存在一定差異,僅僅利用知識產權制度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其保護確實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還需要針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特殊性,建立相應的配套特設法定權利制度共同發揮作用,以期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提供周全的法律保護。
四、特設法定權利對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保護
特設法定權利這種保護模式將賦予權利人某些禁止權與受益權,從而使其可依法禁止其他人針對受保護的傳統文化資源實施某些行為(如對傳統文化資源的非法使用和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歧視與歪曲),或者在實施相關行為前以某種方式征得許可或同意。當其他人因利用受保護的資源取得收益時,權利人有權按照一定比例或方式獲得利益。利用禁止權保護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其效力范圍體現為: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合法權利人,一旦發現他人未經許可使用其擁的傳統文化資源,有權向有關機關申請類似于商標法上的“臨時禁令”和“即發侵權”的制止權[8](P161)。除此之外,權利人還有權禁止他人對其擁有的民族民間文學藝術進行歪曲、篡改和割裂的行為。最后,合法權利人還有權向司法、行政機關提起依法判令不法行為人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請求。這就可以防止并懲治商業社會中的“有心人”利用其掌握的現代科技,配以自己的片面理解和好惡隨意“改造”和“渲染”其他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的傳統文化資源的行為。在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保護機制中建立受益權制度,實質是期望通過轉移利益的制度,實現通過保護傳統以鼓勵創新的目的。促使擁有大量五彩斑斕的優秀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尚不發達國家,將對本國的傳統文化遺產的不致消滅的消極保護,變為保存與可持續利用并重的積極保護。
這樣的話,一方面在全人類共同走向現代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與傳統的多樣性;另一方面積極挖掘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在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特有的作用和價值,使其服務于現代社會與現代文明。具體操作上,可以參照1992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2001年底簽訂的《糧食與農業植物遺傳資源條約》的規定,賦予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提供者以利益共享權,即如果他人以某一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為素材或源泉創作了作品,受到了法律的保護,并因所汲取的資源而產生的作品商業化后獲得了高額經濟收入之后,受方應從其因利用該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而帶來的經濟利益中,提取出一部分給提供方。[1](P50)通過這樣的利益分享機制,既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加強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傳統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能力建設過程中獲得一定的資金來源,又可以為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作出貢獻。
五、結語
優美動人的歌舞,瑯瑯上口的歌謠,精美絕侖的服飾,精湛無比的工藝,風格迥異的地方戲,多彩多姿的民風民俗。這些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文化,既是我們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文化財富,也是我們發展先進文化的精神資源與民族根基;既是國家和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我們與世界各國交流的橋梁。但無可否認的事實卻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文化的沖擊等,我國民族民間文化的保護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亟需得到應有的保護。盡管從文化欣賞的角度來說,民間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從文化特性與保護的層面上看,民間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國的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當然只能由中國自己來保護,這民民族民間文化的民族性決定的。令人欣喜的是,在當前許多國家呼喚早日出臺國際性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總體框架的大背景下,我國也順應形勢,加緊了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的制定。目前,文化部已經起草了《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草稿),并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由此可見,我國民族民間文化(當然也包括了本文所關注的民族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法律保護體系的構建和完善應是指日可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