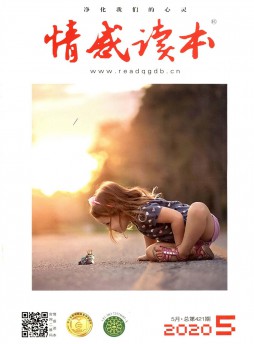情感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情感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當前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已取得話語霸權的“社會性別”,實際上已經遭受了理論上和實踐中的雙重困厄。一方面,作為社會性別理論基礎的“二元論”已經廣泛受到質疑;另一方面,中國目前城市化背景下出現的性別狀況使得社會性別理論無以言對。把情感引入到女性主義理論,是建構多元的、具有生產性和創造力的情感空間的一種嘗試。情感政治,也是社會變革和改變權力布局的一種力量。
關鍵詞:
社會性別;情感轉向;情感政治;女性主義
自1980年代引入中國的“社會性別”理論,到今天已經形成了話語和文化霸權,社會性別的主流化也成為政府和聯合國推行的目標。2014年10月23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審議了中國加入消歧公約后的執行狀況,11月上旬,消歧委員會了通過此次審議得出的中國結論性意見。意見中重要的一條就是關于婦女歧視的定義問題,聯合國消歧委員會呼吁中國政府和締約國,“采取一種綜合性的定義,以保證婦女免受生活中一切直接和間接的歧視”①。但在中國當下語境中,社會性別概念被多重利用及其不確定性,實際上已經對如何定義性別歧視形成干擾。而且社會性別的矛頭所指,有意或無意地減弱了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批評,把深層的社會矛盾簡化成一場“男人和女人”的戰爭。如何拓展女性主義理論,使之更具有生產性和創造力,在當下,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變成一個非常迫切的需要。以西方而言,自18世紀以來形成的工具理性和科學主義的獨霸局面,使得科學變成了另外一種宗教,情感被扔進了廢棄的角落。但是,當人類在經歷了進化論、線性發展觀、工具理性導致的戰爭殺戮,對自然的無限開掘引起的環境惡化,以及極端的兩極分化和第三世界的普遍貧窮之后,人們不得不反過來重新審視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情感紐帶,以及情感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女性主義,也應該重新拾起情感這個作為人類本源的武器。
一、對社會性別概念的反思
社會性別的概念最初源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以自由主義理念為指導的這一女性主義流派,從18世紀開始發展之初,就內化了西方文化中二元對立的原則,把理性和情感對立起來,認 為一個人由于擁有了理性才能被賦予政治及其他的權利和榮譽。二元對立思維在西方的起源,要追溯到柏拉圖的理念論。在中世紀基督教統治時期,理念論的至高地位被上帝取代,與之對立的便是肉身的人。自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在哲學假設的框架內發展了笛卡爾的懷疑論,形成關于心靈在原則上與身體相分離的形而上學。理性被看作是物質的本源,是對現實的普遍性的理解,而感性則被貶低至次文化的地位。阿莉森•賈格爾在《女權主義政治與人的本質》中指出自由主義的最初觀點就是:“假設人類個體在本質上是獨立于需要和利益的,這些需要和利益如果沒有處在其他個體的需要和利益的對立面,就是和其他個體的需要和利益相分離。”[1]自由主義把經濟看作第一位,強調競爭、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在理性主義的支配下,自由主義理論家假設所有的個體都是趨向利己主義的,這可為現代男性的行為提供一個近似合理的解釋,但是很明顯,這種模式不很符合女性的行為。人類的社會組織需要一些必要的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犧牲性的勞動來維系。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關于人的本質的回答是認同于男性標準的,即認為人的存在本質上是理性的存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同傳統觀點,忽視了人的生物性和情感在人的存在中起到的本質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也否認形而上學的二元論,認為人類世界和非人類之間有“內在的聯系”,人有自然的欲求,更有感情的需求,強調人的本質生物性的方面。而自由主義政治唯我論假設人類在本質上是孤立的,它與我們所習慣的社會的生物狀態這一事實是相矛盾的。
社會性別二元對立的劃分方式,把生理的和社會的性別區分開,成為了“酷兒理論”的基礎,給予“同性戀”“雙性戀”以理論上的支持。對于同性戀或者說LGBT群體是社會性別的建構還是天生的,當前在各個學科和領域都沒有定論。朱迪斯•巴特勒甚至令人信服地論證了生理性別也是一種文化建構[2]。那么,是不是也必須承認,在某種程度上社會性別概念建構了同性戀的文化認知?當LGBT群體以一種反文化建構的激進姿態出現時,是不是早已陷入了社會性別建構的窠臼?在當前背景下,社會性別又被挾裹進新自由主義的漩渦當中。正如柏棣指出的,社會性別理論,作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認識論結果,是源自白人中產階層的。而今天,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社會性別也逐步主流化,并且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合謀[3]。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場主義拜物教閹割平等的價值,在以抽象的競爭和效率為幌子下,放棄對一個社會內部和全球范圍內形成的巨大的貧富差別、在自由貿易的名號下實行的對落后地區的掠奪性開發和貿易等現實進行批判性分析,從而掩蓋了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4]1980年代以來,國家在政策上向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學界引介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也主要是來自歐美。社會性別的理論,在作為一個有效的分析范疇所具有的洞見之后,反而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消費主義達成了共謀,使得女性主義運動“去解放化”了。中國的社會性別理論和議題,逐漸對中國出現的實際問題無力言說和解決。出現這種理論困厄的原因,首先是因為1980年代社會性別概念的引入,正好替代了被質疑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解放理論。在20年的時間里,這個本是認識論的概念,逐漸取得了本體論的地位。“社會性別不僅是理論的出發點,而且本身就是理論。”[3]社會性別又被政治話語所借重,例如“建立先進的社會性別文化”“性別和諧”“社會性別主流化”等,在研究領域和實際生活領域都取得了話語霸權地位。于是“社會性別”使得本應是百家爭鳴、多元的女權/女性主義理論空間逐漸轄域化。
社會性別由于概念上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有重蹈性別本質主義的危險,社會性別的概念被顛覆利用,與消費社會及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達成一致,強調“女人味”。并且由于其對革命時期“去性化”的批評,而取得了話語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社會性別某些流派提出的“中性思想”和“雌雄同體”,往往會導致“絕對性平等”,就是認為女人要和男人一樣,忽視了由于生理差異和長期的社會文化差異造成的女性真實的生活狀況,當下語境實際對于下層女性是不利的,不利于針對她們的一系列暫時性保護措施的實施。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社會性別概念都干擾和使得歧視概念難以界定,使得歧視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往往以“形式平等”的方式隱蔽起來。社會性別概念忽視了造成歧視的深層的社會體制和文化結構。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具體的社會勞動中,因為女性生理和道德等因素的共同限制,會引發勞動分工的差異,但是這種分工并不帶有等級化的特征。可是,在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生產體制中,勞動分工出現等級化,家務勞動是無償的。恩格斯曾預言,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她們投入社會生產、家務勞動只占其極少的工夫時才能實現。但是今天,我們恰恰看到的是這種情況,一方面女性加入職業勞動的大軍,另一方面,她們還是要家庭、事業兩肩挑。從理論上講,在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下,女性是無法達到真正的解放的,即使男性也加入到家務勞動中來,也同樣無法平衡這種矛盾。如何才能改變女性受壓迫的狀況?這是女性主義要回答的一個終極問題,如果一直復制二元對立,那么在充滿了等級的社會結構中,總有一部分被壓迫的男人和女人存在。所以,從本源來說,女性受壓迫源于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那就是文化中的等級秩序無所不在。所以,從理論上來講,要改變女性的受壓迫的狀況,就要構建一種無等級、無界限的政治哲學和詩性的生存空間。
二、情感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建構
(一)情感的轉向1980年以來,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和意識形態在國際政治中的淡化,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歐美左派學術及其人文學者,將其關懷投向社會平等、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上來。在“文化轉向”的影響下,被邊緣化了20多年后的“情感”,重新回到了人文社科研究的中心。在此之前,已經有一部分法國歷史學家開始轉向研究“社會想象的歷史”。這是針對社會學過分強調經驗調查和量化而提出來的,因為社會學研究者往往忽視了情感的價值和作用,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在女性主義研究領域,也許談論“情感的轉向”為時過早,但已經出現了很多的研究成果。澳大利亞女性主義學者謝麗爾•赫克斯在《身份認同、情感和女性主義集體行動》一文中,以澳大利亞北昆士蘭地區的女性運動為案例,探討情感與女性主義運動之間的關系。謝麗爾指出,以往的社會運動理論往往認為個人是否參與社會運動,是在權衡利益得失之后才作出的決定。新的社會運動理論對于集體行動動因的研究,已經不再只是強調理性、策略和組織,而是更把分析重點放在集體行動中的意義、身份認同和文化生產上[5]。在《漂移的感受: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和情感政治》一文中,卡莉•哈密頓指出巴斯克人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情感的共同體”[6]。在一篇以秘魯為案例分析的文章中,作者探討了在后殖民主義的政治文化語境下,情感在南美女性主義運動中起到的作用[7]。指出在女性主義運動中,“情感提供了思想意識、身份認同及行動的動力”[8]。以上的這些研究成果,多是從某一地區的層面,從口述史、性別研究或者人類學的角度切入,開始建構情感與女性主義的理論。
社會學領域關于情感方面的理論研究成果,也可以給我們提供借鑒。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的喬納森•特納,從事情感社會學的研究已經有幾十年。他在《人類情感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人類先于聲音語言而自然學會了情感語言[9](P12)。人類能夠非常容易地•12•林存秀:情感與女性主義理論的拓展體驗到大約一百種復雜的情感。他指出,文化和社會結構是情感發生的條件,而且,情感反過來會影響社會文化結構。為了說明情感在改變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作用,他把社會結構分為3個層面,即人際互動的微觀層面、社區和單位的“中觀層面”,以及國家的宏觀層面。個體的情感是在某種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產生的,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產生了強烈的正面或者是負面情感。正面情感是維系社會紐帶的有力黏合劑,負面的情感卻能摧毀文化和社會結構。人類在日常生活中面對面的交往,依靠的是一套象征的符號體系。情感正是通過象征系統,在3個層面中發生作用。微觀層面的符號,可以上升為中觀和宏觀的符號,對中觀和宏觀世界的改變產生潛在的影響,反之亦然[9](P150)。特納的理論分析了情感與社會變動的關系,看到了情感在空間生產中的作用。如果說是牛頓力學的發現,引發了理性至上的思潮,那么,現代物理學的發展,也引發了人文學科領域對空間的重新認識。空間一般被看作是凝固化、轄域化的,隨著引力波的發現,我們看到了空間的多維性甚至時間的可變性。社會空間是在社會生產關系普遍性的脈絡里產生的,并且不斷創造出新的空間。正如列斐伏爾(Henri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里面所說的:“我們所面對的并不是一個,而是許多社會空間……在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沒有任何空間消失”[10]。空間是在歷史發展中產生的,并隨著歷史的演變而重新結構和轉化,而日常生活與大眾媒體就是情感政治空間生產的場所。
(二)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政治早在1930年代,因為報紙的傳播,“公眾”這個現代具有一定民主性質的概念就已經形成。在《公眾的形成———1930年代中國的情感與媒體炒作》一文中,作者通過考察1935~1936年轟動一時的女刺客施劍翹案,研究了性別和情感如何促進“公眾同情”這樣一個集體身份的形成[11]。我們也可以認為,由女刺客激發的公眾同情,調動起一個高度女性化群體情感的空間,而且,這個空間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成為一種道德、政治和司法的力量。在公眾的輿論下,施劍翹獲得特赦,她的成功之處在于她極大調動了公眾的情感。當下,由于網絡的發展,這種空間政治的力量愈發明顯。2015年1月15日,記者周哲在“澎湃新聞”中了一篇題為《女權主義者集體發聲:批判周國平意味真正性別革命的到來》的新聞稿。這是針對1月12日周國平在微博上發的一個言論而對幾位女性主義學者的采訪。這則新聞以后,迅速在微博和朋友圈中傳播開來。周國平的言論受到一致的指責和評判,他很快刪除了微博。周刪除的微博內容為:“男人有一千個野心,自以為負有高于自然的許多復雜使命。女人只有一個野心,骨子里總把愛和生兒育女視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個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論她在癡情地戀愛、在愉快地操持家務、在全神貫注地哺育嬰兒,都無往而不美。”針對周國平的言論,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宋少鵬說:“周國平的倒塌是一次男性重振男性氣質的(失敗)嘗試。”女權活動家、女聲網主編呂頻認為:“網絡團結了女性,讓她們不再容易被忽悠。”并且指出:“如果沒有互聯網,許多知名人士的真實想法可能不會那么容易暴露,女性也不那么容易集結起來分享彼此的觀點,這個事件是一個典型的‘網絡女權主義’”[12]。通過跟貼和微博網絡交流互動,針對周國平言論在公共層面的討論,發出了女性共同的聲音。這種集體的行動,是網絡媒體時代的想象共同體形成和日常生活情感政治的一個典型案例。周國平的言論也提醒我們,情感女性主義中的“情感”,絕不能被理解為一種本質主義的“情感”,把女性等同于“愛”“犧牲”“生育”“感性”,并且一廂情愿地定義女性的“美”,這便是男性文化建構起來的在文學作品中比比皆是的“圣母”“貞女”形象。“周國平們”的言論,代表了當下社會“女人味”的回歸,這種“女性意識”恰恰也是從社會性別概念中次生出來的,開始和反“”話語合流,之后又和文化保守主義達成一致。這看似是對女性的“褒揚”,實則是對女性的文化歧視,仍然把女性定義為“第二性”。圍繞這一言論的討論和評判,打破了帶有性別等級偏見的男性制造的“鏡像”,使之變成了一個“哈哈鏡”。這一次集體行動形成的“共同體”,是流動的和異質性的,主體的身份也是流動的、多元的,這就形成了列斐伏爾所說的多重空間的交叉。在網絡社會中,情感和文化認同會促成一種集體的默契行動。
三、情感理論的傳統資源
女性主義理論可以從中國古代思想中找到淵源,并且進行對比研究。從“儒”“道”兩家來探討其與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已經頗為多見。例如探討儒家“仁”的思想與女性主義理論中的“關懷理論”之間的關系②,或者是討論道家理論對于二元對立的克服等等。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最推崇平等思想的當屬墨家。在平等的基礎上,墨家學派提出其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兼愛”。墨子認為,天下之亂,皆源自人們不能相愛,如果人們都能夠以己推人,不易他物為非,以愛己之心愛他人,則天下大治。《墨子•兼愛中第十五》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暑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13]。
本來,歷史上任何時代,愈是能反映社會下層利益的學說,其空想的成分就愈多。但在一個觀念上把人分成等級的社會中,“兼愛”與之是不相容的。由于墨家思想反貴族化的明顯特征和代表下層利益,歷代的統治者并不提倡墨學。但墨子這種“兼愛”思想,代表了春秋戰國時期下層人們的愿望,因而受到了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底層人群的歡迎,并使其在民間流傳。而一種被邊緣化和處于“次文化”地位的女性文化,可以從墨家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理論資源。明代出現了“情”文化的上揚,知識分子試圖構建一個情感空間,來對抗理學和專制權力。在陽明學說激勵下,經過王學左派發展,以反對理學教條對“情”的禁錮為內核的“主情”文化思潮隨之發生,李贄和文學領域的湯顯祖、袁宏道即是其典型代表。李贄高倡“童心說”,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演繹杜麗娘因情而生,為情而死。在對理學觀念糾偏中,“主情”文化思潮極大地提高了“情”的哲學地位。馮夢龍更是進行了“情教”的建構。晚清到五四前的大眾娛樂市場上延續了“情”的空間建構,只不過主體不再是精英知識分子,而是生活在城市空間的普羅大眾。建構女性主義的情感理論,是試圖突破社會性別理論的話語霸權局面,批評兩元論和理性至上,開創多元的女性主義理論的一種嘗試。這不僅僅是一種學術理論建構,更是一種存在方式,要建構一個“情感共同體”。這是一種可能的生活空間,指向那些無形的、作為文化和精神而存在著的生活可能性。這是一種詩意政治的想象和建構,正是因為想象,才給予未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情感共同體的建構,反映了處于“他者”地位的人們的愿望和利益。“他者”的對抗,也會造成權力的消弭和翻轉。這種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政治,也許會改變現存權力關系的布局。
作者:林存秀 單位:山東女子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