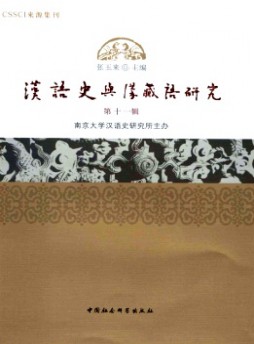漢語特點對漢語文學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漢語特點對漢語文學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作家所做的工作無非就是“研究”和運用語言。追本溯源地來看,一種文學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其所使用的語言。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曾經指出:“每一種語言都有它鮮明的特點。所以,一種文學的內在形式限制———和可能性從來不會和另一種文學完全相同。用一種語言的形式和質料形成的文字,總帶著模子的色彩和線條。”①可以說,正是語言,在不同的文學之間劃出了清晰的界限。自然,本身極具特色的漢語在這方面的影響也相當深遠,它潛移默化地從諸多方面的影響了漢語文學特色的形成。漢語的精神,從本質上說,不是西方那種執著于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滿感受和體驗的精神。漢語的思維,帶一種具象思維成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漢語是一種藝術性的民族語言,漢語思維具有藝術氣質。這種藝術氣質投射在文學上,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美輪美奐的中國文學。
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古典詩詞受漢語特色的影響最深,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樣式之一。它千百年來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著為數眾多的愛好者和學習者,成為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園地中一束光彩奪目的奇葩。本文試圖從中國古典詩詞入手,運用語言學相關知識,從藝術成因角度探討漢語特征對漢語文學的一些影響。文字的象形與內涵的詩意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書面的形式記錄傳承的,因而記錄時所使用的符號即文字對于文學尤其是書面文學特色的形成影響至深。作為最基本的組成材料,漢字在潛移默化中以自己的特點影響了漢語文學的特色。就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漢字不同于印歐語系的符號系統,它是一種表意性的象形文字。一般認為,認字的最早生成方式有象形、形聲、指事、會意四種。但若仔細觀察則不難發現,無論哪種方式都包含了外指的“物相”和內指的“意向”兩個因素,象形都是其基礎。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指出:“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可見,指事是在象形的基礎上加標記來實現的;“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武信是也”。可見,會意是在原有的象形基礎上逐步深化,通過形象的復合來揭示人們的思維和聯想的;“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②。可見,形聲是在象形符號的基礎上增加聲符來擴大文字再生產的,即使是音譯外來詞,人們往往也喜歡為這些表音字加上音符,如“目宿”加“艸”成為“苜蓿”,“師子”加“犭”成為“獅子”,“皮離”加“王”成為“玻璃”等等。
顯然,漢字是中國人習慣以直覺形象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致思途徑的產物。在印歐語當中,假若你從未見過某一單詞,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望其興嘆。而在漢語中,結果則很可能是另一種情況。比如你可能不認識“獾”字,但透過左邊簡化后的形旁“犭”和右邊的“”你總會猜到這該是一種讀音近似“”的動物的名字吧。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漢字外形與內涵關系就是這么緊密。因而,可以說,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感于外而發于內”的心理意向,一種客體與主體的相互交融,一種經過概括化、模式化了的“共相”。漢字的這種構成體現了主體對于客體的感覺、體驗與選擇,頗具詩的意味和審美的意味,因而也更適宜于抒情寫意,從而促進了中國詩詞藝術的興旺發達。日本學者兒島獻者在他的《中國文學史綱》中指出:“中國文字以象形為基礎,而指事會意形聲皆有一部分之象形,象形與圖畫,只有精粗之異耳。試觀郭璞《江賦》,通篇文字于紙上。再觀司馬相如之《上林賦》,篇中敘山者崇峨崔嵬嶄巖崎嶇等等,皆冠以山,敘魚鳥者亦如此,皆冠以魚鳥之偏旁,山與魚鳥皆象形也;故一篇文字全體生動,善寫高山絕峰,峻極于天之雄勢,易使人想見鳥飛天魚躍淵之活境,皆于文字構造有圖畫性質之所致。”③可是,漢字在不斷地演化過程中,流失了許多感性的東西,導致圖畫性和意象性不斷減弱。現代人欣賞到的用簡化漢字記錄的中國古典詩詞已較它們初被記錄下來時遜色得多。但由于長期的、歷史的文化心理積淀,漢字的這種“詩性”的特征在詩詞哲學過程中往往從潛意識的深層彌漫開來,在不知不覺中給人以詩的含蓄,韻的渾融,氣的煙蘊。比如“暮”與“晚”,意義相同,韻味大不一樣,觀其原因,還是和“暮”字的形義、淵源有關,“暮”的原字即“莫”,而“莫”的初始寫法則為“”,即日落草莽之中,因而“暮”比“晚”更能體現出雄渾蒼茫之象。如“可堪孤館避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秦觀《踏莎行》),“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處”(李清照《永遇樂》)。
正因為漢字是這樣一種脫胎于圖畫的文字,是基于主體對于客體的直感的、形象的、整體的把握,而不是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樣建立在理性的分析和規定之上,因而漢語詞匯的意義往往是渾然而模糊的,具有獨特的“觀物取象”的功能。它往往是一種整體象征,所突出的并不是客體的確切屬性,而多半是主體“心理形象”。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希臘的“月亮”(men)指的是月亮度量“時間”的功能意義,而拉丁語的“月亮”(Luna,Luc-na)則是指月亮的“亮度”。我們可以加上漢語的“月”比較一下,“月”顯然是取月亮在常態下的“形狀”的,比起“時間”和“亮度”來,“形狀”顯然直觀,卻少有思維的規定性、單一性、明晰性。“月”中似乎什么都包括了,然而又都沒有說清。至于后來的詩詞作品中,又把“月”稱作“玉鉤”(“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李賀《七夕》)、“桂魄”(“桂魄初升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王維《秋夜曲》)、“寒蟾”(“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樓半開壁斜白”———李賀《夢天》)、“銀蟾”(“暮蟬聲盡落斜陽,銀蟾影掛瀟湘”———毛文錫《臨江仙》)、“清輝”(“多情別,清輝無東,暫圓常缺”———王微《憶秦娥》)、“嬋娟”(“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調歌頭》)等,就更加感覺化,富于整體象征,也更加模糊朦朧如夢境幻境了。這樣的文字,缺乏科學語言所要求的透明度,但卻更加適合表現詩詞中文學性藝術性的意象。漢字自產生之日起,就為漢語文學準備了相當富于詩意內涵的基本的材料,為中國文學尤其是古典詩詞提供了相當適宜的生長土壤。音節的特點與形式的構建中國古典詩詞表象的特點是形式整齊,同時,這也是藝術形式的特色之一。它的引人入勝處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擅長帶著腳鐐跳舞,四言、五言、五絕、七絕、五律、七律的種種要求及品目繁多的詞牌規定,已經注定中國古典詩詞是嚴守紀律的一族。它們看上去井然有序,讀起來瑯瑯上口,頗具形式之美,音樂之美,表現出很強的藝術性。而這一切的成因,都與漢語音節的特點密不可分。
不同于印歐語以音系作為基本的語言感知單位,漢語的基本感知單位是音節。音節由聲母和韻母構成,聲調則把它們緊緊包裹住,因此,漢語的音節非常整齊,切分明確,在書面上則有一個個方塊漢字與之相對應。漢語的這個特點不僅使漢語能在形式上作十分整齊的排列,而且為漢語文學中的對仗、對偶等手法的運用與工整的形式安排提供了一個十分難得的基礎。中國古典詩詞便充分利用了這一基礎,對仗、對偶在篇章中比比皆是,有時甚至成為一種要求,如律詩要求頷聯、頸聯中的上下兩句相對,一些詞牌中作出了關于對仗的規定等,而且在長久的寫作中,詩人們還摸索出借對(即利用一字多義的現象以構成對仗。一個字有甲、乙、丙等多種意義,在詩中用的是甲義,但借用它的乙義或丙義與另一字相對。例如杜甫《曲江》: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流水對(即一聯中的兩句字面是對仗的,意思卻是相承的。例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等特殊對仗法,增強了藝術審美效果,頗值得玩味。如果說音節的組合為中國古典詩詞(尤其是詩)的格律樹立了基本梁柱的話,那么音節的聲調變化則使梁柱成為“雕梁畫柱”,前者奠定了節奏的基礎,后者以平仄的變化配合造成音調的和諧。在漢語里,每一個單音節的字都有一個聲調,來反映音節高低升降的變化。聲調最早發見于南朝的齊梁之間,有下上去入四種,其中上去入三種聲調統為仄聲,與前面的平聲相對。在此之后,文人們在詩詞創作中開始利用漢語四聲的特點,有意造成聲韻上的平仄相間變化,讀起來抑揚頓挫,天然具有一種音樂美。
讓我們以劉禹錫的《酬爾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和陸游的《鷓鴣天》為例,來看這種音韻上的平仄變化造成的音樂美感。劉詩如下:巴山蜀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詩中字的平仄為: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陸詞如下: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瀣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貪嘯傲,看蓑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詞中用學的平仄為: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相反,一篇作品即使意境再美,如果在音律上發生非和諧現象,審美意識與情趣將大受損害。且看下面語音的趨同性例子:屋北鹿獨宿(全仄)溪西雞齊啼(全平)中國古典詩詞一方面將其聲律模式建立在漢語單音節和四聲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在漢語單音節聲韻配合的特點上建立起具體作品的音律形象④,以獨具一格的音響審美效果傳達作品豐富的思想感情,大大強化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在古代韻書里,凡韻腹和韻尾相同的字,就歸為一個韻,《廣韻》中有二百零六韻,古代韻母系統之復雜可見一斑。韻的數目如此繁多,每個韻訓都為詩人潛心揣摩,不同的韻部產生了不同的情緒效果。宋人把《廣韻》中的二百零六韻分成十六撮: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每一攝對古典詩詞作者來說,都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感情體驗,這種體驗往往是下意識的,但確是區分得非常明確的,請看下面的四首詩詞: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花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重重發,朝夕催人自白頭。———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韻腳:州、由、愁、頭,押流攝尤韻。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鬃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陸游:《訴衷情》韻腳:侯、州、裘、秋、流、洲,押流攝尤韻。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柳宗元:《登柳州城寄漳汀封連四州》韻腳:荒、茫、墻、腸、鄉,押宕攝陽韻。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活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韻腳:茫、量、忘、涼、霜、鄉、窗、妝、行、岡,押宕攝陽韻。四首詩詞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中都有悲愁的成份,但前兩者是憂愁凄愴的味道更濃一些,后兩者則在悲傷中流露出一絲陽剛之美,之所以如此,和韻的選擇關系密切。不同的韻有不同的美學價值,這可能和韻母的音色有關。韻腳就如樂曲的主音,主音決定了一首曲子的調性。漢民族的詩歌,不僅在于意象、氣韻,還在于音樂感。所以劉勰說:“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于字句,氣力窮于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⑤氣力的強弱、剛柔就在于和諧與押韻。正因為漢語言在語言單位組合方面具有美的極大潛力,歷代詩詞作者無不醉心于語言的編排與操練,留下了大量具有語言形式美感的文學作品。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無一不看重形式之美。可以說,正是由于古人在創作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執拗與毅力,才使語言形式上的切磋成了中國古代最大的競技保留項目。啟功先生曾引張裕釗與吳汝綸論學手札說:“昔諸子謂退之用盡一生精力,全在聲響上著式夫,匪獨退之,自六經諸子,史漢以至唐宋諸大家,無不皆然。”⑥
經過眾多文人許多年的努力,漢語文學的形式已經被造得十分精美。由于語言發展的連續性,古人作詩填詞時“用破一生心”營造出的許多美妙形式,仍有一部分保留在現代漢語里,繼續發揮著作用,特別是在習慣語和成語當中,這種例子更是常見。這使人們在不經意間便領略到了那種形式之美,如“折戟沉沙”、“落花流水”等詞匯本身,給予我們的即是一種享受。更有甚者,這種重視形式的傳統已經形成了一種無竟識,因而在中國,即使是在店鋪茶館的外面,也常常看到“對聯”高懸,如“和氣遠招十一利,公平廣進四方財”,“坐片刻不分你我,喝一碗各奔東西”,不能不說這種無意識影響到了文學家的創作。可以說,漢語音節的特點及在此基礎形成的聲調及韻的劃分,賦予了漢語文學與眾不同的魅力。語法的特點與潛力的開掘這里讓我們先來比較一下李白的《靜夜思》與其英文翻譯:原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譯文:Sobrightagleamonthefootofmybed———CouldtherehavebeenafrostalreadyLiftingmyselftolookIfounditwasmoonlightSinkingbackagainIthoughtofhome不難發現,在譯文中,原文里未加確定的時態和人稱都被一一落實,詩中本來可以想象補充的空白蕩然無存。同時found、thought等詞的使用把本來連續的動作變為終止性的行為,原詩幽遠的意境也消失貽盡,從而也便失去了中國文學那種特有的模糊之美。這不僅是《靜夜思》一首詩在翻譯時面臨的尷尬,而且是絕大多數中國古典詩詞在譯成印歐語時所面臨的問題。在這里,最高明的翻譯家也難以再現原作之美。
這種情況的出現,和漢語語法的特點關系密切。漢語是一種分析語,具有極端的分析性,這使得詞語的組合十分方便,不受形態的約束,沒有印歐語那種復雜的形態變化,不像后者那樣在數、格、時態、語態和詞性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漢語的組合主要靠語義和語序,詞和詞之間沒有絕對的排斥性,只要語義上合乎邏輯事理,就可以搭配。所以,漢語的組織往往是語義和語言藝術方面的考慮大于句法的考慮。這種組合關系常常能夠容忍許多從邏輯上看是非常奇怪的組合。在這種寬式語言中,作家就如同在大海中游蕩,自由地表現自己,隨心所欲,暢所欲言。請看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前三句,是晚秋游子感情的自然流露,無一動詞,全是雙音節名詞有節奏的鋪排,流暢自如。再看李白《贈汪倫》:“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歌聲怎么“踏”?英語中恐怕非得用“With”來介紹“歌聲”,漢語沒有格的限制,“踏”和“歌聲”通過意義自然連接,不牽強附會,解釋成“在歌聲中踏行”,就是踏著歌聲!這是語言和感覺融為一體的徹悟,歡快、喜悅、節奏、歌聲聚在一起。李白還有“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的妙語,“半落青天外”、“中分白鷺洲”和“踏歌聲”用法相同,是詩人、語言、景物的自然融合。柳宗元《江雪》中的“獨釣寒江雪”,正是漢語賜給詩人的想象境地。對于說英語的人來說,必得用“in”引入處所格“雪”,對于漢語來說,把“寒江雪”當處所還是對象,可以自由想象。
很多學者都認為,漢語語詞組合自由,使漢語免除了許多規矩,與意象組合無關的成分都可以省去,因此漢語的表達往往言簡意賅,辭約義豐。由于漢語的單詞蘊藏了豐富的語文感受,因此將這些基本粒子排列組合起來,就成為一組組生動可感的具象。中國的文學語言大師們在采用這種具象思維的語言時,也大都用具象的手法來捕捉事物的形態,描繪心中的感受,這往往能觸發每個經過中國文化熏陶的讀者內心深處的共鳴。當一個個語詞的具象被詩人藝術地精心安排在一起的時候,它們內涵的豐富聯想和民族情感就組成了連續的有機的畫面,未著一個動詞,而動作自在其中;未用一字抒情,而心境溢于言表,因而發散出強烈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將一首中國詩譯成英語,要作許多處理,要增加許多元素(如動詞的變化,單復數,冠詞等等),但在我們的閱讀過程中,并非都要這樣,反而倒是以不作這種處理為佳,詩的印象仍舊完整無缺,而作了那些處理,詩卻會受損。中國古典詩詞所用的文言,由于超脫了呆板分析性的文法語法而獲得更完全的表達,如唐代陸龜蒙有這樣一首七律:平波落月吟閑景,暗幌浮煙思起人。清露曉重花謝半,遠風微動蕙抽新。
城荒上處樵童小,石蘚分來宿鷺馴。晴寺野尋同去好,古碑苔字細書勻。該詩也可以倒過來讀:勻書細字苔碑古,好去同尋野寺晴。馴鷺宿來分蘚石,小童樵處上荒城。新抽蕙動微風遠,半謝花重曉露清。人起思煙浮幌暗,景閑吟月落波平。讀者絲毫不覺得語法有何不自然,西文要同樣做,卻根本不行。原因就在于西文無法使一個字母同時兼有兩三種文法用途,而不需要字面上的變化。西文的細分限指特指的要求,使它無法可似中國文言這般自由。中國古典詩詞文法語法上的自由,意味著其欲利用語字的多元性來保持美感印象的完全。試看杜審言詩句:“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⑦如果像下面譯詩中那樣加入一些連接元素,譯成:Cloudsandmistsmoveouttotheseaofdawn.Plumsandwillowsacrosstheriverbloominspring.或者解說為:“云霞從海上映出一片曙光,梅柳渡過江帶來一派春意”。這兩種方式顯然都歪曲了原詩的美感印象的層次和姿態。文言是沒有時態變化的。沒有時態變化就是不要把詩中的經驗限指在一特定的時空———或者應該說,在中國詩人、詞人的意識中,要表達的經驗是恒常的,所以,不應把它狹限于某一特定的時空里。印歐語系中的“現在、過去、將來”的時態變化就是特定的時空。漢語文言中的動詞類字眼,可以使我們更接近于渾然不分主客的存在現象本身,存在現象是不限于特定的時空的。詞法上的寬泛同時也造成了詞的“多元性”,如在“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黑”中,“白”“黑”二字既可理解為動詞,又可理解為形容詞,因其兼具活動及狀態兩種不可分的情況。同樣,“青山橫北郭”的“橫”字既是動詞亦是前置詞。詞的“多元性”在翻譯上會造成很大的困難,由于詞性的限制,譯者必須作出種種處理決定,而限制了原詩的多面延展性,直接破壞了原詩的美感活動的程序和印象。
總之,漢語是輕形態而重功能的語言,這使它在詞法與句法上都沒有許多限制,進入這種語言框架中的現實不需要經過多方面的界定,因而現實本身也就不必清晰地多方面呈現自己的特征,所以說,漢語更適合作為藝術文學的載體。王力先生曾經說過:“西洋語言是法治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⑧所謂“法治”,便是講規律,講邏輯,講嚴謹,講精確;所謂“人治”,便是講直覺,講感悟,講意會,講傳神。“人治”的特點增強了漢語言的人文精神,提高了言語主體在言語實踐中的自由度,為主體意識的自由馳騁,為言語意象的自由組合,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地,從而創造出別具一格的中國文學。這個結論應該說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