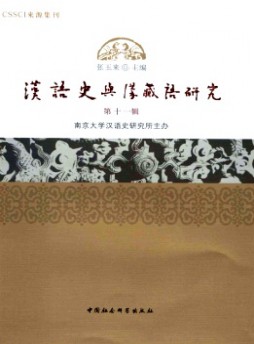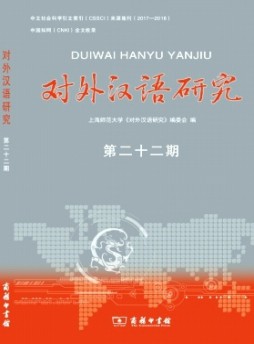漢語(yǔ)文學(xué)語(yǔ)詞的藝術(shù)化組合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漢語(yǔ)文學(xué)語(yǔ)詞的藝術(shù)化組合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漢語(yǔ)是一種充滿詩(shī)性資質(zhì)和審美表現(xiàn)性的語(yǔ)言,它的組合主要是依靠詞序排列和虛詞的應(yīng)用,詞本身的形態(tài)則大多不變。如“我愛(ài)他”,換成“他愛(ài)我”,語(yǔ)義便翻轉(zhuǎn)了,而語(yǔ)義的變化只靠“他”和“我”的位置顛倒;如果加上一個(gè)虛詞“也”,就可使兩個(gè)句子的意思統(tǒng)一起來(lái),成為一件事情的兩個(gè)方面,即“我愛(ài)他,他也愛(ài)我”,這就由兩個(gè)單句構(gòu)成了一個(gè)復(fù)句。可見(jiàn),語(yǔ)序在漢語(yǔ)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雖然語(yǔ)言受線性序列的限制,一個(gè)語(yǔ)詞不得不排列在另一個(gè)語(yǔ)詞的后面,但它們之間可以前后移動(dòng)、相互置換,在形式上具有可逆性。“漢語(yǔ)言單位的彈性表現(xiàn)在功能上就是它的變性,亦即詞義功能的發(fā)散性。漢語(yǔ)一個(gè)個(gè)詞像一個(gè)個(gè)具有多面功能的螺絲釘,可以左轉(zhuǎn)右轉(zhuǎn),以達(dá)意為主。只要語(yǔ)義上配搭,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連在一起,不受形態(tài)成分的約束。”[1]正是漢語(yǔ)的這種隨意性和彈性,決定了語(yǔ)詞組合的多向性。“一個(gè)語(yǔ)詞序列,可以順向建構(gòu),也可以逆向拼合,還可以以腹為頭雙向合成。”“語(yǔ)句可以無(wú)限延伸,語(yǔ)序可以隨意調(diào)整,語(yǔ)鏈還可以自由地切分。”[2]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作家充分利用漢語(yǔ)語(yǔ)句結(jié)構(gòu)之靈活多變的特性,通過(guò)語(yǔ)詞藝術(shù)化的組構(gòu),成功地表現(xiàn)著審美意象和藝術(shù)境界,傳遞著美的信息。漢語(yǔ)文學(xué)文本中的語(yǔ)詞組構(gòu)策略是多種多樣、千差萬(wàn)別的,僅從下面五個(gè)方面便能看出漢文學(xué)語(yǔ)言建構(gòu)的特點(diǎn):
一、運(yùn)用表象義豐富的詞,復(fù)蘇語(yǔ)言與感知覺(jué)表象的潛在聯(lián)系
語(yǔ)言是由語(yǔ)詞構(gòu)成的,語(yǔ)詞的核心是詞義,詞義的核心是概念,概念總是抽象一般的。所以,語(yǔ)言這種抽象化、概念化的符號(hào)更適合于表現(xiàn)抽象的思想。盡管如此,語(yǔ)言仍與人的感知覺(ju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它既有普通一般的一面,又有具體特殊的一面,因?yàn)檎Z(yǔ)詞是從若干個(gè)別事物中提取出來(lái)的,語(yǔ)詞與表象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比如“房屋”這個(gè)詞,它雖然指的是許許多多房子的抽象,但它又始終是與個(gè)別的房子聯(lián)系在一起的。每一個(gè)人在理解這個(gè)詞的時(shí)候,在把握共義的前提下,又都各有不同。城市人與農(nóng)村人的理解不一樣,大人與小孩的理解不一樣,古人與今人的理解不一樣,中國(guó)人與美國(guó)人的理解不一樣,因?yàn)樗麄兝斫膺@個(gè)詞所依據(jù)的生活經(jīng)驗(yàn)不一樣。這就說(shuō)明,“房屋”雖然是一個(gè)共義性的符號(hào),但它并沒(méi)有完全割斷與個(gè)別事物的聯(lián)系,在向人們顯示它抽象普遍的一面的同時(shí),它也向人們顯示出其具象特殊的一面。由此可以推見(jiàn),語(yǔ)詞的意義準(zhǔn)確地說(shuō)應(yīng)分為意義和涵義兩部分,意義與抽象認(rèn)知有關(guān),是普遍的、分析的,而涵義跟感覺(jué)有關(guān),跟過(guò)去的經(jīng)驗(yàn)、文化背景有關(guān)。意義可以傳授,涵義只能靠語(yǔ)境、語(yǔ)感去領(lǐng)悟。現(xiàn)代語(yǔ)義學(xué)對(duì)語(yǔ)言意義的劃分愈趨精細(xì),英國(guó)語(yǔ)言學(xué)家利奇就把語(yǔ)義分為七類:理性義、內(nèi)涵義、社會(huì)義、情感義、反映義、搭配義、主題義。[3]這說(shuō)明語(yǔ)詞語(yǔ)音層面下面的語(yǔ)義呈現(xiàn)出一團(tuán)“意義星云”,以理性義為中心,周?chē)鷱浡T多模糊不清的邊緣義。詞義的多向性與彈性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留下了廣闊的空間。文學(xué)是用生動(dòng)鮮明的藝術(shù)形象反映社會(huì)生活、表達(dá)主體情感的,形象性是文學(xué)的根本特性。這一特性決定了在文學(xué)語(yǔ)體中,比較重要的是語(yǔ)詞的表象義、情感義、社會(huì)文化義等,這些邊緣義間互相聯(lián)系,且都以“聯(lián)想意義”來(lái)概括,能引發(fā)巨大的表現(xiàn)潛力和暗示力。表象義是詞的所指對(duì)象在我們腦中引起的感知覺(jué)表象,通過(guò)表象可產(chǎn)生聯(lián)想,喚起相應(yīng)的審美情感。因而表象義在文學(xué)語(yǔ)言中獲得了極其重要的地位。作家傾向于選擇表象義豐富的詞,以使意象得以形象地符號(hào)化。例如,“枯藤”、“老樹(shù)”、“昏鴉”、“小橋”、“流水”、“古道”、“西風(fēng)”等都是表象義凸現(xiàn)、鮮明的名詞,這些詞能引發(fā)人們對(duì)所指客觀事物的聯(lián)想,能在頭腦中建立起相應(yīng)的感性的畫(huà)面。以這些詞作為語(yǔ)言材料,經(jīng)過(guò)詩(shī)人精心地組合建構(gòu),便形成了一首形象生動(dòng)、意蘊(yùn)雋永的“秋”的千古絕唱:“枯藤老樹(sh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fēng)瘦馬。夕陽(yáng)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yuǎn)《天凈沙•秋思》)普遍一般性的語(yǔ)詞,經(jīng)過(guò)詩(shī)人的具體化組合,使之指向了具體、特殊的事物,喚起人們的感官具象反應(yīng)。詩(shī)中每三個(gè)語(yǔ)詞為一組,分別構(gòu)成三幅看似獨(dú)立的圖景,但其中都蘊(yùn)含著一個(gè)悲涼的主題。各個(gè)語(yǔ)詞所標(biāo)志的事物的狀態(tài),由近及遠(yuǎn),由靜及動(dòng),由次及主,由外到內(nèi)地分層推進(jìn)、立體延伸;景色的描寫(xiě)與心理的襯托相得益彰,每一個(gè)自然景物中都滲透了蕭條秋色里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悲涼。
二、利用詞義聚合的不同特性,造成有意味的文學(xué)話語(yǔ)
漢語(yǔ)是世界上詞匯最豐富的語(yǔ)言之一,在《漢語(yǔ)大詞典》中就收集了37萬(wàn)多條(只包括一般語(yǔ)詞)。同一事物常有許多不同的說(shuō)法或名稱,例如,“死”歷來(lái)被認(rèn)為是不吉利的事情,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盡可能用委婉的說(shuō)法來(lái)表示:“仙逝”、“謝世”、“永別”、“長(zhǎng)眠”、“歸西”、“作古”等等,有多達(dá)幾十種說(shuō)法。這些語(yǔ)音形式不同而意義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詞,就是一般所說(shuō)的同義詞。在文學(xué)作品中,作家巧用語(yǔ)言系統(tǒng)中的同義詞不僅避免了用詞的重復(fù),為句子帶來(lái)錯(cuò)綜變化之妙,而且能通過(guò)運(yùn)用同中有異的同義詞,傳達(dá)出不同的情感色彩和風(fēng)格色彩。如《紅樓夢(mèng)》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ài)情悲劇為中心,描寫(xiě)了賈府衰亡的過(guò)程,全書(shū)貫穿著悲和愁。為了表達(dá)各種場(chǎng)合、各類人物、不同程度、不同內(nèi)涵的“悲”和“愁”,作者運(yùn)用的兩組同義詞共達(dá)36個(gè)。其中表示因悲而痛的有:“悲痛、悲慟、悲切、悲凄、悲戚、悲哀、悲”;表示因傷而悲的有:“傷感、傷心、悲感、悲傷、傷悲”;表示凄苦的有:“凄楚、凄惻”。愁有感于形而慮的“煩慮、憂慮、愁煩、憂愁、憂”;有動(dòng)于心而悶的“愁悶、憂悶、納悶、氣悶、煩悶、悶”;有心緒不展的“悒郁、憂郁、抑郁”;有心境不暢的“懣憤、懊惱、煩惱、苦惱”。筆之所至,無(wú)所不及。于賈府,則愈顯出封建社會(huì)搖搖欲墜之態(tài);于寶黛,則更見(jiàn)其愁腸固結(jié),如泣如訴。[4]在語(yǔ)詞的意義聚合中還有一種現(xiàn)象值得注意,這就是語(yǔ)詞的多義性,即通常所說(shuō)的一詞多義現(xiàn)象。例如,“蠟燭”一詞的實(shí)體詞匯意義是“蠟制的照明物”。以這一實(shí)體詞義為基礎(chǔ),又生發(fā)出了極為豐富的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國(guó)俗語(yǔ)義。以燃成灰燼始干的燭淚喻深深的情思和雖死不悔的決心和信念;根據(jù)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品質(zhì),“蠟燭”一詞用來(lái)泛指“樂(lè)做奉獻(xiàn)的人”,特指“教師”;由于搖搖曳曳的燭光易被風(fēng)吹滅,又有了“風(fēng)燭”比“殘年”的用法;中國(guó)過(guò)去在婚禮中,在新房?jī)?nèi)以點(diǎn)紅蠟燭表示喜慶,并于紅燭之上加上龍鳳彩飾,以增添吉祥熱鬧的氣氛,是為“花燭”。“花燭”遂指代“新婚”,“洞房花燭夜”即為“新婚之夜”;而在“他是蠟燭,不點(diǎn)不亮”這句話中,“蠟燭”一詞具有貶義,泛指“不自覺(jué)、有傻氣的人”。可見(jiàn),“蠟燭”一詞具有豐富的象征義、比喻義,修辭上有褒有貶,既表現(xiàn)纏綿之情,歡樂(lè)之感,也表現(xiàn)悲涼之意。這種種豐富的涵義都是在“蠟燭”一詞的實(shí)體詞義的基礎(chǔ)上所增添的民族文化蘊(yùn)含,是通過(guò)對(duì)蠟燭實(shí)體的特點(diǎn)的聯(lián)想而產(chǎn)生的。一詞多義現(xiàn)象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在于它使語(yǔ)言非常經(jīng)濟(jì),一個(gè)詞包含幾個(gè)意義,可以大大減少語(yǔ)言符號(hào)的數(shù)目,使用者能從詞匯所具有的涵義的匯集中,獲得無(wú)比豐富的意義,并可以根據(jù)上下文選擇出一個(gè)與表達(dá)目的最為吻合、恰當(dāng)?shù)暮x。消極的一面在于易使話語(yǔ)產(chǎn)生歧義現(xiàn)象。正因?yàn)槿绱耍瑢?duì)于一詞多義,人們?cè)诳茖W(xué)語(yǔ)言和文學(xué)語(yǔ)言中采取兩種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在科學(xué)語(yǔ)言中,不允許存在含混不清的表達(dá),要力求消除語(yǔ)言的多義現(xiàn)象,使語(yǔ)詞的能指與所指一一對(duì)應(yīng)。而文學(xué)要用語(yǔ)言表達(dá)出作者罕見(jiàn)的、新穎的、獨(dú)特的、原初的審美感受與體驗(yàn),意義明確單一的語(yǔ)詞是難以傳達(dá)出如此豐富復(fù)雜的審美體驗(yàn),因此,文學(xué)語(yǔ)言就要提倡和保留語(yǔ)詞的多義,并通過(guò)各種手段造成一詞多義現(xiàn)象。正如法國(guó)釋義學(xué)派創(chuàng)始人保羅•利科所說(shuō):“詩(shī)歌是這樣一種語(yǔ)言手段,其目的在于保護(hù)我們的語(yǔ)詞的一詞多義,而不在于篩去或消除它,在于保留歧義,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語(yǔ)言不再是通過(guò)它們的相互作用,構(gòu)建單獨(dú)一種意義系統(tǒng),而是同時(shí)構(gòu)建好幾種意義系統(tǒng)。從這里就導(dǎo)出同一首詩(shī)的幾種釋讀的可能性。”[5]文學(xué)語(yǔ)言恰是善于運(yùn)用語(yǔ)詞多義性的語(yǔ)言,利用同一語(yǔ)詞具有的多種意義,拓展了文學(xué)作品的容量和內(nèi)涵,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李商隱《無(wú)題》“相見(jiàn)時(shí)難別亦難”);“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明天。”(杜紫微《別詩(shī)》)這兩首詩(shī)中都以垂淚的蠟燭象征苦戀者那黯然銷(xiāo)魂的離別之恨和幽然神傷的思念之情。而在“還主動(dòng)和我們打招呼,蠟燭!”(陸文夫《井》)中的“蠟燭”一詞則是貶斥性的罵語(yǔ),意思是“什么東西,那么不自量!”正是由于文學(xué)語(yǔ)言具有多義性的特點(diǎn),因而才能夠包容眾多的情感體驗(yàn)、生活經(jīng)驗(yàn)和哲理意蘊(yùn),收到言有盡而意無(wú)窮的藝術(shù)表達(dá)效果。
三、創(chuàng)造語(yǔ)詞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偏離效應(yīng)”,使一般化語(yǔ)詞生發(fā)出獨(dú)特的表意功能
在日常語(yǔ)言中,語(yǔ)言符號(hào)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guān)系是固定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即使一詞多義,也是可以確定的,這就是語(yǔ)詞的常態(tài)意義。這些常態(tài)意義的表現(xiàn)性畢竟是有限的,因?yàn)樗艿秸Z(yǔ)法規(guī)則和造句習(xí)慣的制約,語(yǔ)言表達(dá)難以脫離概念化的邏輯軌道。相對(duì)于理性邏輯,藝術(shù)形象中的生活與情感則是變異了的。前蘇聯(lián)心理學(xué)家列昂節(jié)夫在給維戈茨基的《藝術(shù)心理學(xué)》作序時(shí)深刻指出:“情感、情緒和激情是藝術(shù)作品內(nèi)容的組成部分,但它們?cè)谧髌分惺墙?jīng)過(guò)改造的。就像藝術(shù)手法造成作品材料的變形一樣,藝術(shù)手法也造成情感的變形。”[6]這就告訴我們藝術(shù)作品中的情感是個(gè)人情感的改造與升華,要成功地傳達(dá)這種變異的情感,就要有與之相適應(yīng)的藝術(shù)形式與手法,就要在日常語(yǔ)體的基礎(chǔ)上轉(zhuǎn)換生成審美語(yǔ)體,其轉(zhuǎn)換生成的基本規(guī)律是:“只有違反標(biāo)準(zhǔn)語(yǔ)言的常規(guī)并且是有系統(tǒng)地進(jìn)行違反,人們才有可能用語(yǔ)言寫(xiě)出詩(shī)來(lái)。”[7]在實(shí)際語(yǔ)境中,詞義又是變化多端的。當(dāng)詞義的變化超出語(yǔ)詞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確定聯(lián)系時(shí),能指與所指間的恒定關(guān)系就會(huì)破裂,偏離也就隨之產(chǎn)生。偏離的另一層意思便是指在詞的用法、搭配及語(yǔ)法功能等方面違背常規(guī)的用法。語(yǔ)詞的偏離在兩個(gè)方面造成獨(dú)特的表意效應(yīng):首先,通過(guò)言語(yǔ)的偏離及超常搭配,打破其常態(tài),使語(yǔ)詞不再指向共相、一般的意義,而是指向獨(dú)特、個(gè)別的意義,語(yǔ)詞的具體特殊的一面就突出出來(lái)了。如“花”這個(gè)詞,雖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yǔ)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輯的《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修訂本)中,對(duì)它的解釋多達(dá)19項(xiàng),其中包括“花”的一些比喻義、象征義,但是,這些解釋里“花”依然是共相意義上的“花”,能指與所指還是能夠確定的。在文學(xué)作品中,采用偏離的方法及語(yǔ)詞的超常搭配,“花”便指向各種特殊的事物和意義,“花”的意義和用法是變化萬(wàn)千、無(wú)法窮盡的。詩(shī)人張先的佳句“云破月來(lái)花弄影”被視為千古絕唱。“花”本來(lái)是不能“弄影”的,但恰是用了一個(gè)擬人化的“弄”字,而境界全出。這是詩(shī)人把自己的心情投射到花上,使花人格化的結(jié)果。在月光下徘徊、起舞、顧影、傷愁的既是花也是人,是二者的巧妙融合,是物化了的詩(shī)人的審美感受。沒(méi)有“弄”字這一超常搭配的語(yǔ)詞,則花歸花,人歸人,詩(shī)人的心境無(wú)法窺見(jiàn),花的出現(xiàn)也失去了意義。顯然,這一佳句中的“花”,不可能是共相意義上的花,而是殊相意義上的,即詩(shī)人獨(dú)特情感體驗(yàn)中的花。其次,語(yǔ)詞的偏離能恢復(fù)語(yǔ)言感性鮮活的表現(xiàn)力,并打破讀者心中固有的接受定勢(shì)。語(yǔ)詞的常態(tài)意義由于經(jīng)常使用,已變得機(jī)械化、一般化了,既失去了它與感性經(jīng)驗(yàn)的聯(lián)系,又使人在接受過(guò)程中感覺(jué)不到其生動(dòng)鮮活的一面。文學(xué)語(yǔ)言通過(guò)言語(yǔ)的偏離和打破其成規(guī)與常態(tài)的“變異”,能夠使人們產(chǎn)生新異感,并有助于打破那種非藝術(shù)接受機(jī)制的慣性運(yùn)動(dòng),產(chǎn)生出藝術(shù)語(yǔ)體所需要的言語(yǔ)接受圖式。譬如,我國(guó)古典詩(shī)詞中對(duì)“愁”的描寫(xiě),總是用具體生動(dòng)的感性形象來(lái)表達(dá)這種抽象的、飄忽不定的情感:“問(wèn)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愁有長(zhǎng)度;“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dòng)許多愁。”———愁有重量;“自在飛花輕似夢(mèng),無(wú)邊絲雨細(xì)如愁。”———愁有形狀;“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duì)愁眠。”———愁能相對(duì)而望;“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言還慵。”———愁有酒味,能醉人;“菡萏香銷(xiāo)翠葉殘,西風(fēng)愁起綠波間。”———愁有動(dòng)作,能陡然立起。這里,詩(shī)人將難言的愁思,別出心裁地用文字凝鑄成一個(gè)個(gè)鮮明生動(dòng)的意象,令讀者在曲折玩味中覓得詩(shī)詞的真諦。這些詩(shī)句中對(duì)于語(yǔ)言常態(tài)的偏離和“變異”的表達(dá),迫使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到語(yǔ)言本身,而不是它以外的別的東西。新異、獨(dú)特的語(yǔ)詞搭配,使我們感受它時(shí)已無(wú)法重復(fù)原來(lái)的感知路徑,無(wú)法襲用原來(lái)的接受模式和套路,只有憑借豐富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悉心地去體味、感悟。這就打破了我們心中原有的接受定勢(shì),從麻木不仁的狀態(tài)中驚醒起來(lái),使思維恢復(fù)生機(jī)與活力。顛倒詞序,在語(yǔ)言方面設(shè)置一些“謬誤”和“悖理”的現(xiàn)象,在詩(shī)、詞、曲、賦中常能見(jiàn)到。如南朝江淹的《別賦》中有一段這樣寫(xiě)道:“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全賦論及各種離情別緒縈繞心頭,牽腸攪肚,使人痛苦萬(wàn)分。但言“心折骨驚”,論理上是不通的:人的心靈怎能折斷,無(wú)感知的骨頭又怎會(huì)產(chǎn)生驚懼之感呢?顯然,這是作者對(duì)正常詞序的有意顛倒,旨在強(qiáng)調(diào)離愁使人的心靈如同猝然折斷破碎,這種愁怨竟然使無(wú)知的骨頭都為之震驚,那么其痛苦程度不就可想而知了嗎?若按正常詞序“心驚骨折”,則失之泛泛。為了使言語(yǔ)表達(dá)簡(jiǎn)練形象、生動(dòng)活潑,在特定的語(yǔ)言環(huán)境中臨時(shí)改變?cè)~性,在文學(xué)作品里運(yùn)用得也很普遍。如“雨絲斜打在玻璃窗和水泥窗臺(tái)上,濺起的迷茫將窗外的世界涂染成一幅朦朦朧朧的圖畫(huà)。”(張建文、高立林《為了國(guó)家利益》)把形容詞“迷茫”活用為名詞,表示顏色,形象生動(dòng),給讀者以想象的空間。
四、“碎片化”的語(yǔ)詞組合,拓展文本內(nèi)在的藝術(shù)張力
文學(xué)文本的話語(yǔ)結(jié)構(gòu)從本質(zhì)上說(shuō)是作家在觀照生活時(shí)審美情感秩序的外化。就是說(shuō),一定的審美情感模式必然會(huì)產(chǎn)生與其對(duì)應(yīng)的話語(yǔ)結(jié)構(gòu)。正如杜夫海納所說(shuō):“藝術(shù)的語(yǔ)言并不真正是語(yǔ)言,它不斷地發(fā)明自己的句法。它是自然的,因?yàn)樗鼘?duì)自身說(shuō)來(lái)就是它自己的必然性,一個(gè)存在的必然性的表現(xiàn)。”[8]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要以自己活躍的審美情感去超越以理性思維為基礎(chǔ)的語(yǔ)法規(guī)則,同時(shí)就需要建構(gòu)出能滿足非理性思維的要求,能充分反映作家審美情感和創(chuàng)作個(gè)性的新的語(yǔ)法規(guī)則,美國(guó)語(yǔ)言學(xué)家喬姆斯基(NoamChomsky)的轉(zhuǎn)換生成語(yǔ)法充分滿足了這些要求。喬姆斯基認(rèn)為,語(yǔ)言可按其規(guī)則進(jìn)行不同形式的排列組合而產(chǎn)生出不同的語(yǔ)句和語(yǔ)義,而且趨向無(wú)窮。這一語(yǔ)法理論是以既有的語(yǔ)法規(guī)則為前提,強(qiáng)調(diào)語(yǔ)言運(yùn)用的變化性、創(chuàng)造性,它允許對(duì)舊有的語(yǔ)法進(jìn)行破壞、改革,以便通過(guò)語(yǔ)言形式的重組來(lái)生成新的語(yǔ)義。這種轉(zhuǎn)換生成法是符合文學(xué)語(yǔ)言組構(gòu)規(guī)律的。作家如果遵循現(xiàn)象之間的因果必然律,按照常規(guī)語(yǔ)法去反映現(xiàn)實(shí)、組構(gòu)文本,就會(huì)把生活中許多偶然的、個(gè)別的、無(wú)法按照因果關(guān)系去解釋的意象與思緒篩選掉、遺漏掉,使文本的面目變得蒼白虛假。為了突破舊有的話語(yǔ)結(jié)構(gòu)模式,一些作家在結(jié)構(gòu)作品時(shí)不僅選擇了片斷拼接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而且大膽采用“碎片化”的語(yǔ)詞組合方式,以使那些無(wú)法貫穿于因果關(guān)系鏈上的大量偶然的、個(gè)別的意象都被拼接黏合而納入文本世界之中,形成散點(diǎn)透視的效應(yīng),使意象之間的范圍、距離、深度增大,拓展了文本內(nèi)在的藝術(shù)張力,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象與再創(chuàng)造的空間。如巴金在《春天里的秋天》中這樣寫(xiě)道:沒(méi)有父母的少女,酗酒病狂的兄弟,純潔的初戀,信托的心,白首的約,不辭的別,月夜的驟雨,深刻的心的創(chuàng)痛,無(wú)愛(ài)的婚姻,丈夫的欺騙與犯罪,自殺與名譽(yù),社會(huì)的誤解,兄弟的責(zé)難和仇視,孀婦的生活,永久的秘密,異邦的漂泊,沉溺,兄弟的病耗,返鄉(xiāng),兄弟的死,終身的遺恨。這段是在敘述一部電影的情節(jié),它是由18個(gè)偏正詞組并列拼接而成,其中有的詞組內(nèi)還含有并列著的多個(gè)信息。每個(gè)詞組都是一個(gè)獨(dú)立的意象,多項(xiàng)詞組聚合成動(dòng)態(tài)的意象群,各項(xiàng)之間看似沒(méi)有必然的聯(lián)系,顯得零亂雜多。但卻在廣闊的時(shí)空中延展出一幅幅流動(dòng)的畫(huà)面,形成了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在貌似零亂無(wú)序的語(yǔ)詞搭配中,傳遞著豐富的信息和各種復(fù)雜的情感。
五、營(yíng)造各種特定的語(yǔ)境,使語(yǔ)詞獲得具體、特殊的涵義
由于文學(xué)語(yǔ)言的運(yùn)用總是在一定的語(yǔ)境中進(jìn)行的,并受特定語(yǔ)境的影響與制約,因而,文學(xué)文本中的語(yǔ)詞不僅具有它本身的詞典意義,而且還包含一種由特定語(yǔ)境所形成的涵義,“詞既是能指的又是表現(xiàn)的。說(shuō)它是能指的,是指它含有一種客觀意義,這種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于它的外部,要求運(yùn)用理解力;說(shuō)它是表現(xiàn)的,是指它本身含有一種內(nèi)在意義,這種意義超出了理解力所把握的客觀意義。詞是符號(hào),又不只是符號(hào):詞陳述,同時(shí)又顯示,而它顯示的與它陳述的并不一樣。”[9]這種內(nèi)在意義(涵義)之所以與意義不同,就因?yàn)樗怯缮町a(chǎn)生的,它所反映的是對(duì)象與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是個(gè)人對(duì)于語(yǔ)詞內(nèi)容的一種主觀體驗(yàn),即人們通常所說(shuō)的“言外之意”,它潛藏在符碼形式的深層。所謂語(yǔ)境是指使用語(yǔ)言時(shí)所處的實(shí)際環(huán)境,即指言語(yǔ)行為發(fā)生時(shí)的具體情境。語(yǔ)境在范圍上有大與小之分,在形態(tài)上則有顯與隱之別。小語(yǔ)境指書(shū)面語(yǔ)的上下文或口語(yǔ)的前后語(yǔ)所形成的言語(yǔ)環(huán)境。大語(yǔ)境是指語(yǔ)言表達(dá)時(shí)的具體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小語(yǔ)境是易被人們注意的顯語(yǔ)境,而由言語(yǔ)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聯(lián)系所構(gòu)筑的大語(yǔ)境,是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的隱語(yǔ)境。由于文學(xué)語(yǔ)言的運(yùn)用總是在一定的語(yǔ)境中進(jìn)行的,并受特定語(yǔ)境的影響與制約,因而,文學(xué)文本中的語(yǔ)詞不僅具有它本身的詞典意義,而且還包含一種由特定語(yǔ)境所形成的涵義。同樣一個(gè)陳述事實(shí)(語(yǔ)言),在不同的陳述情況(語(yǔ)境)里,便會(huì)具有大相徑庭的功能效應(yīng)。正是在具體的語(yǔ)境中,普通語(yǔ)詞才能生發(fā)出具體的、特定的意義。如“老爺”一詞是普通的舊式稱謂,雖然顯示著封建等級(jí)關(guān)系,卻沒(méi)有豐富、深刻的涵義。但是,在魯迅小說(shuō)《故鄉(xiāng)》的特定語(yǔ)境中,“老爺”一詞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味。童年時(shí),“我”與潤(rùn)土是親密無(wú)間、無(wú)所顧忌的伙伴。時(shí)隔30年,潤(rùn)土見(jiàn)到我卻恭敬地稱我為“老爺”,這生分、隔膜的稱呼,不僅表現(xiàn)出潤(rùn)土對(duì)“我”的尊敬,而且折射出了他那自卑、麻木的心態(tài),包含著既歡喜又悲涼的情感,顯示著人與人之間無(wú)法突破的隔膜。在此,語(yǔ)詞不止訴說(shuō)著自身,它說(shuō)出了遠(yuǎn)比自身豐富得多、深刻得多的涵義。可見(jiàn),在具體文學(xué)語(yǔ)境下,一句普通的話語(yǔ)可生發(fā)出無(wú)比豐富的涵義,令人品味不盡。這正如美國(guó)著名的藝術(shù)心理學(xué)家魯?shù)婪?#8226;阿恩海姆指出的:“事實(shí)上,語(yǔ)詞在不同的前后關(guān)聯(lián)、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個(gè)人或不同的社會(huì)群體中,都具有不同的內(nèi)涵。”[10]由語(yǔ)言的上下文關(guān)系構(gòu)筑的小語(yǔ)境,容易被人注意和引起重視,而言語(yǔ)與社會(huì)生活的聯(lián)系(文化背景、社會(huì)規(guī)范和習(xí)俗等)造就的大語(yǔ)境,常被人所忽略,其實(shí),恰是這些隱而不見(jiàn)的社會(huì)文化因素,是形成文學(xué)語(yǔ)言深層涵義的根本原因。如杜甫的《孤雁》:“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shuí)憐一片影,相失萬(wàn)重云?望盡似猶足,哀多如更聞。野鴉無(wú)意緒,鳴噪自紛紛。”該詩(shī)描寫(xiě)了一只離群的孤雁不飲不啄,一直苦苦地追尋著失散的伙伴,甚至產(chǎn)生出那群雁總在眼前晃動(dòng)的幻覺(jué);但這幻覺(jué)畢竟不是真實(shí)的情景。在它周?chē)傍Q噪”著的并不是昔日的伙伴,而是一群可惡的“野鴉”,這只孤雁因此而愈加焦躁不安。表面看來(lái),正如題目所表明的是一首描寫(xiě)孤雁的詩(shī),實(shí)際上它是詩(shī)人的“自寫(xiě)照”,即借用孤雁這一動(dòng)物形象抒發(fā)對(duì)知己的思念之情和對(duì)因戰(zhàn)亂帶來(lái)的人與人之間那種不信任現(xiàn)象的詛咒。詩(shī)中借孤雁這一象征體所傳達(dá)出的象征意義(內(nèi)涵意義)是非常豐富、深刻的。而要正確認(rèn)識(shí)和把握詩(shī)句中內(nèi)蘊(yùn)的涵義,則要聯(lián)系大語(yǔ)境,即詩(shī)人所處時(shí)代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來(lái)理解。語(yǔ)境賦予語(yǔ)言以個(gè)性化涵義和生命的活力。正是在一定語(yǔ)境的規(guī)定和限制之下,抽象概括的語(yǔ)言符號(hào)才變得具體、生動(dòng)、形象、豐富,從而轉(zhuǎn)化成情味無(wú)窮的藝術(shù)符號(hào),作家運(yùn)用這樣的藝術(shù)符號(hào),才能創(chuàng)造出內(nèi)涵豐富、詩(shī)味雋永的藝術(shù)形象。所以,在文學(xué)作品里,詞語(yǔ)的意義是從作品的整個(gè)話語(yǔ)系統(tǒng)(大語(yǔ)境)中獲得的。因此,一些詞語(yǔ)不僅具有表意功能,而且具有傳遞審美情感的表現(xiàn)功能,單純的語(yǔ)言符號(hào)已轉(zhuǎn)化成藝術(shù)審美符號(hào)。文學(xué)語(yǔ)言與作品中的具體情境緊密相連,文學(xué)語(yǔ)言正是在語(yǔ)與境這種唇齒相依的文本結(jié)構(gòu)中獲得了它的審美性。總之,文學(xué)作品中使用的語(yǔ)言并非是語(yǔ)言學(xué)中的語(yǔ)言,而是超越了普通語(yǔ)言規(guī)范的變異的語(yǔ)言,是作家心靈創(chuàng)造和審美組構(gòu)的結(jié)果。在陌生化的語(yǔ)言形式中蘊(yùn)含著豐富的審美信息和情感內(nèi)蘊(yùn),它能成功地呈現(xiàn)出作家心中獨(dú)特的審美意象和個(gè)性化的生命體驗(yàn)。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shí),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為什么說(shuō)“文學(xué)是語(yǔ)言的藝術(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