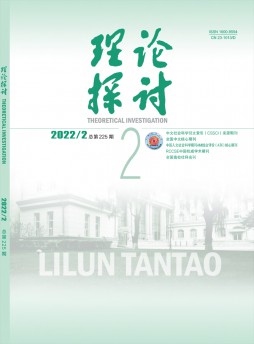探討文學(xué)史的寫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探討文學(xué)史的寫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nèi)容提要:文學(xué)史寫作,應(yīng)該不再是對前輩學(xué)者的人云亦云,而應(yīng)有新的視角、新的思維,新的思考;應(yīng)該不再是材料的機(jī)械陳述,而應(yīng)將研究對象視為一個(gè)有機(jī)的整體;應(yīng)能從感性的材料中不斷升華為理性的概括。木齋《宋詞體演變史》以“詞體”建構(gòu)宋詞史,開辟了詞學(xué)研究的新天地,書中隨處可見作者深刻的思想,可稱“有思想的學(xué)問”;木齋此作是對通行觀點(diǎn)的“顛覆”。
關(guān)鍵詞:詞史寫作木齋顛覆
文學(xué)史該怎么寫,有沒有或該不該有固定統(tǒng)一的模式?羅宗強(qiáng)先生《文學(xué)史編寫問題隨想》一文認(rèn)為:“文學(xué)史誰愛怎么寫就怎么寫!只要它的編寫者是嚴(yán)肅的,學(xué)風(fēng)是嚴(yán)謹(jǐn)?shù)木涂梢浴!睆?qiáng)調(diào)不必追求一種模式,應(yīng)有“學(xué)術(shù)個(gè)性”。[2]先生所論極是。詞史已有不同的寫法:1、通代詞史,如劉毓盤的《詞史》、胡云翼的《中國詞史大綱》、許宗元的《中國詞史》、黃拔荊的《中國詞史》等,以作家為綱,作品為目,按時(shí)代先后順序敘述;2、斷代詞史,如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近代部分(實(shí)際上即是唐宋詞史)、楊海明的《唐宋詞史》、張仲謀的《明詞史》、嚴(yán)迪昌的《清詞史》等;3、按流派構(gòu)建的詞史,如劉揚(yáng)忠的《唐宋詞流派史》等;4、類別詞史,如楊海明的《唐宋詞風(fēng)格論》(專論唐宋詞風(fēng)格演變史)、鄧紅梅的《女性詞史》等;5、史論結(jié)合的詞史,如劉尊明的《唐五代詞史論稿》、王兆鵬的《唐宋詞史論》等,還可以寫詞調(diào)演進(jìn)史、詞人生活史、詞人心態(tài)史、愛情詞史、山水詞史等。
一部詞史,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名家名作史,木齋先生《宋詞體演變史》以“詞體”建構(gòu)宋詞史。作者《前言》自述道:“這是一次欲以詞體演變史來勾勒唐宋詞演變歷程的嘗試。之所以要嘗試以詞體史來勾勒詞史,是有感于一般的文學(xué)史、詞史寫作,容易陳列眾所熟知的材料,成為時(shí)代背景、詞人生平、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特色的機(jī)械陳列,因而會(huì)缺乏深度和新意;而論文的寫作,雖然具有深度和新意,卻不能構(gòu)成一個(gè)有機(jī)的聯(lián)系,或說是一個(gè)體系,只能解決有關(guān)研究領(lǐng)域的某些局部問題。而局部問題研究的缺陷,不僅僅是一個(gè)簡單的研究范圍大小的問題——由于研究者著眼于所研究問題的局部性,在大文學(xué)史觀缺席的情況下,往往會(huì)使研究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能從整體和宏觀的視角給予微觀的把握。”[3]因此,作者嘗試以寫作論文的方式來寫作詞體史,即具體的每一章節(jié),都由一篇或者數(shù)篇論文來組成,以進(jìn)行局部問題的深入探索,同時(shí),又以文學(xué)史的規(guī)模和思路,來規(guī)范每一個(gè)局部問題(即每篇論文)的命題和內(nèi)涵,從而將詞體的個(gè)案研究與宋詞史的總體走向有機(jī)地聯(lián)系起來。作者對“詞體”做了明確界說,本書所論“詞體”,并非指區(qū)別于“詩”的廣義“詞體”,而是專指狹義的“詞體”:“‘狹義的詞體’,是指那些在詞史流變中呈現(xiàn)自己獨(dú)特的范式和風(fēng)格,自辟蹊徑,卓然名家,并且被其他詞家效法的詞人詞作。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獨(dú)特性,即迥然而異于他人之詞;二是影響性,即其樣式和風(fēng)格獨(dú)到而又具有相當(dāng)?shù)乃囆g(shù)水準(zhǔn),從而產(chǎn)生詞史影響,引起他人仿效。”(P1)該書的研究視角,落在宋代眾多詞體中那些更具有劃時(shí)代意義的詞體上,它們堪稱是“詞體中的詞體”:從宋初體、柳永體、晏歐體、張先體、東坡體、小晏體、少游體、山谷體、方回體、美成體,到易安體、稼軒體、白石體、夢窗體,共計(jì)十四體。以十四位詞人為中心視角,并視為一個(gè)有機(jī)的整體,來勾勒宋詞體的演變路線圖。與傳統(tǒng)的宋代詞史相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宋詞體演變史》,也可以說是一部精煉的詞史,忽略宋詞在演變歷程中的那些非本質(zhì)的細(xì)節(jié),從而達(dá)到凸顯宋詞演變歷程的效果。
傳統(tǒng)的詞史,與傳統(tǒng)的中國文學(xué)史相似,更多地注重將每個(gè)時(shí)代的歷史背景、作家背景和作品狀態(tài)列示出來,而該書,更為強(qiáng)調(diào)研究每一種詞體在宋詞整個(gè)歷程中的特質(zhì)、地位和變革,研究諸多詞體之間縱向的位置和關(guān)系。重點(diǎn)突出,而不是面面俱到,又有史的線索,點(diǎn)、線、面三結(jié)合。不是進(jìn)行孤立、靜態(tài)的研究,而是將它們作為一個(gè)整體的、動(dòng)態(tài)的“史”來加以詮釋。如此,更能合理把握詞史本質(zhì)和內(nèi)在演變規(guī)律。這種獨(dú)特的框架結(jié)構(gòu),有別于通行的詞史著述模式,開辟了詞學(xué)研究的新天地,堪稱詞史的新建構(gòu)、新突破,是一部既嚴(yán)肅又有個(gè)性的詞史著作。
全書章節(jié)安排合理,如每章都有一節(jié)“概說”,各章結(jié)構(gòu)大體相同,又有差異。每一章節(jié)皆有新意,獨(dú)立出來,都是一篇優(yōu)秀論文。作者從抒情內(nèi)容、題材的選擇與處理、人物形象的描繪、表現(xiàn)手法、語言風(fēng)格、章法、意象等方面對“詞體”做了綜合考察,從不同角度挖掘詞體的內(nèi)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使人們對宋詞史有了全面、立體的認(rèn)識(shí)。換一種新的視角審視詞史,確有不少欣喜的發(fā)現(xiàn)。全書格局宏大,角度新穎,獨(dú)辟蹊徑,自成體系。作者有強(qiáng)烈的史意識(shí),注重動(dòng)態(tài)地把握詞史流變,又注重宏觀綜合概括,以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為基礎(chǔ),加上嚴(yán)密的邏輯論證,得出的結(jié)論自然既新穎,又準(zhǔn)確。
此著新見迭出,精彩之處不勝枚舉,許多論斷都給讀者以啟發(fā),此僅舉其要者。如宏觀概括詞史演進(jìn)規(guī)律,極為精辟:“在詞體的社會(huì)階層屬性上,是一個(gè)下移的過程,即由宮廷之詞,而分流為歌妓詞和士大夫詞,最后定格為詞人之詞;而從詞體的藝術(shù)屬性上,則是一個(gè)不斷雅化的過程,最后,到南宋姜吳時(shí)代達(dá)到了雅化的極致。”(P3)“東坡體之所以達(dá)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還不僅僅是由于有了張先體、晏歐體的奠基以及范仲淹之后整個(gè)士大夫階層的群體覺醒,更由于東坡首先實(shí)現(xiàn)了由應(yīng)社、應(yīng)歌的應(yīng)對他者的寫作方式,成功轉(zhuǎn)型為非應(yīng)的自我抒懷,從而將張先、晏歐的詞體士大夫群體意識(shí)表達(dá),轉(zhuǎn)型為士大夫精英的個(gè)性化表達(dá)。”(P3)論“小晏體”時(shí),聯(lián)系到整個(gè)文學(xué)史:“小晏體表面雖為醇酒婦人,實(shí)則卻是小山人生觀念的一種表現(xiàn)。可以說,陶淵明隱于田園,阮籍隱于醉酒,林逋隱于西湖山水和梅花,東坡歸隱于內(nèi)心世界,而晏小山則隱于小晏體中的歌兒舞女、醇酒夢境。這將是明清以來悲涼之霧遍布華林的主流思潮。從這個(gè)角度來說,小晏體與東坡體又有異曲同工之妙,殊途同歸之實(shí)”(P140)作者重點(diǎn)論述“美成體”現(xiàn)象與詩歌領(lǐng)域中的江西詩派現(xiàn)象之間的關(guān)系,極富理論深度:“美成體所開辟的新天地,若是不求全面的話,概言之,首先是一種法度精神,其次是詞體的進(jìn)一步向士大夫文化的轉(zhuǎn)型,再次是一種末世情懷,是一種悲哀的、灰暗的人生色調(diào)。而這些精神,雖然應(yīng)該說是當(dāng)時(shí)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多種因素的合成,但就最為直接的影響而言,筆者認(rèn)為,美成體的創(chuàng)制,實(shí)際上是詩壇上盛行已久的江西詩派的詩學(xué)精神一脈相傳的結(jié)果。”(P184)
第二章中,作者論道:張先(990—1078)的生年比宋祁(998—1062)早八年,但宋祁卻仍在宋初體范疇之內(nèi),而張先卻代表了后一個(gè)時(shí)期的詞風(fēng)。其實(shí),年齡差距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重要的是兩個(gè)人實(shí)際的詞體特質(zhì)。張先雖比宋祁年長,但由于張先的生活,更為接近士大夫之間的群體生活,更早地使用了詞作為士大夫酬贈(zèng)往來的載體,從而具有開風(fēng)氣之先的歷史地位,而宋祁的詞風(fēng)仍然逗留在宋初的寫作習(xí)尚。更何況,張先比宋祁晚死十六年,他的寫作生命是長于宋祁的。(P37)這一論述,啟發(fā)我們反思文學(xué)史寫作中,作家先后秩序的排列完全以生卒年為依據(jù),是否合適?
第五章中,作者就劉熙載的張先“始創(chuàng)瘦硬之體”的觀點(diǎn)進(jìn)行發(fā)揮,詳盡分析了“瘦硬體”的內(nèi)涵,認(rèn)為張先詞改變了傳統(tǒng)詞的寫法,完成了由前人的女性虛擬想象寫作,而為士大夫生活情感真實(shí)寫作的轉(zhuǎn)型,實(shí)現(xiàn)了由含蓄而為“發(fā)越”的風(fēng)格轉(zhuǎn)換,顯示了詞的詩體屬性,實(shí)現(xiàn)了由描寫式向敘說式的詞體句式轉(zhuǎn)移,實(shí)現(xiàn)了場景由小巧而闊大的轉(zhuǎn)移。作者認(rèn)為,“張先體”的“瘦硬”是在尊重詞體“別是一家”內(nèi)在規(guī)律之下的“瘦硬”。如此對張先詞的解讀和評(píng)價(jià),是新穎又深刻的。
作者以“雅俗”構(gòu)建宋詞史,以取代傳統(tǒng)的“婉約”、“豪放”論。認(rèn)為蘇軾詞的本質(zhì)是對詞的雅化,美成詞是“以俗為雅”。作者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該摒棄前人的“婉約”、“豪放”的偏見與成見,而對“詞體”賦予新的認(rèn)識(shí)。這是對傳統(tǒng)觀念的修正和完善。
此著重視研究詞體的“原生態(tài)”與“衍生態(tài)”,啟發(fā)我們評(píng)價(jià)宋詞時(shí),不應(yīng)將虛擬情感與真實(shí)情感劃等號(hào),宋代許多詞作是“商業(yè)化”寫作,是虛擬情感,不是寫詞人自己。注重動(dòng)態(tài)分析,如將“東坡體”的形成歷程分為密州之前的“雛形期”,密州、徐州、湖州時(shí)期的“形成期”,黃州之作,則完成了由“應(yīng)體”向“非應(yīng)”的飛躍。注重淵源和影響探討,如第十章論“美成體”的“法度”,即追溯到江西詩派的“法度”;第十四章第一節(jié)論夢窗詞的接受歷程,實(shí)際上,是一部精煉的夢窗詞接受史。注重“關(guān)系”研究,探討各因素間的“交互”影響。注重比較研究,將詞體與詩體比較,尤重名家間比較,如晏殊與歐陽修比較,黃庭堅(jiān)與蘇軾比較,黃庭堅(jiān)與賀鑄比較。注重反思,如第十二章論“稼軒體”時(shí),首先對“豪放婉約論”進(jìn)行“批判”和反思。論證時(shí),不是四平八穩(wěn)、面面俱到,而是集中筆墨,論述主要特征,作者十分強(qiáng)調(diào)“本質(zhì)”,即抓住研究對象的本質(zhì)特征,而舍棄一些枝節(jié)問題。
該書旁征博引,有大量的量化分析作為對論點(diǎn)的支撐。如第六章中,作者提出“東坡體”發(fā)生了由“應(yīng)”向“非應(yīng)”的飛躍,將東坡倅杭時(shí)期、密徐時(shí)期和黃州時(shí)期的詞作,分別做了量化分析,在將倅杭時(shí)期的詞作逐首辨析之后,得出結(jié)論說:“清點(diǎn)東坡倅杭時(shí)期之作,共計(jì)有詞作五十一首,其中應(yīng)社詞作四十首,應(yīng)歌詞作五首,這一數(shù)據(jù),證據(jù)確鑿,說明東坡詞早期的寫作,基本是面對他者的應(yīng)體之作,只有六首不能確認(rèn)與他者的關(guān)系,但也各有其原因。”(P115)這樣,關(guān)于“東坡體”起于“應(yīng)”的觀點(diǎn),就有了強(qiáng)有力的證明。接著,對密徐和黃州不同時(shí)期的詞作一一量化統(tǒng)計(jì),得出明確結(jié)論:密徐時(shí)期“應(yīng)體”之作占據(jù)一大半(百分之五十五);黃州時(shí)期共計(jì)有詞作七十八首,應(yīng)體之作共計(jì)有三十五首,應(yīng)體之作第一次沒有達(dá)到百分之五十。這個(gè)數(shù)據(jù)表明,“東坡體”在數(shù)量上實(shí)現(xiàn)了由應(yīng)對他者的應(yīng)體之作,向面對自我、抒寫自我的“非應(yīng)”的飛躍。又如第九章中,作者對黃庭堅(jiān)“山谷體”八十一首題材進(jìn)行了量化分析,分成十五類,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定性分析。第十一章中,將《全宋詞》中四十七首易安詞分類,將“易安體”題材構(gòu)成、具體寫作對象和性別視角皆做了統(tǒng)計(jì)分析。靠數(shù)據(jù)說話,憑具體的事實(shí)立論,而不是主觀臆測,任意發(fā)揮。如此,自然得出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澄清了長期以來學(xué)界的模糊認(rèn)識(shí)。“定量”分析的基礎(chǔ)上,同時(shí)結(jié)合定性研究,對宋代各“詞體”重新進(jìn)行“定位”。這種治學(xué)方法,在學(xué)風(fēng)浮躁的當(dāng)下,尤其值得稱賞。
作者視野開闊,并不局限于就詞論詞,還重視宋詞的“文化”特性研究。如論證柳永詞的“近代文化”屬性,作者認(rèn)為,詞體產(chǎn)生于盛唐,而唐五代之際,還是典型的宮廷文化時(shí)代;柳詞所具有的市井歌伎俗詞的特征,則是唐宋之際由貴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轉(zhuǎn)型的產(chǎn)物,柳永不但寫作市井生活、市井情調(diào),而且寫作自己的真實(shí)情愛,并且是與妓女之間的泛愛,這就必然地溢出傳統(tǒng)士大夫文化的范圍,而擁有了近代文化的性質(zhì)。柳詞的慢詞長調(diào)、鋪敘寫法、以白話入詞等等寫作特色,其實(shí)都是這一屬性的具體表現(xiàn),也是近代文化這一屬性的必然結(jié)果。(P41)
作者善于由具體研究中提煉出理論,并進(jìn)行“命名”,如分析賀鑄《橫塘路》詞時(shí),作者論述到:文學(xué)寫作,可以大體分為背景式寫作和創(chuàng)作式寫作兩種方式,前者真實(shí)、生動(dòng)、具體,后者概括、凝練、空靈。就詞體而言,飛卿時(shí)代多為虛擬的創(chuàng)作,東坡體則多為具有具體背景的寫作,到黃庭堅(jiān)的山谷體,延續(xù)東坡體的具體場景,我們能從中讀到哪些作品寫于黔州,哪些寫于戎州,賀鑄的方回體,則具體背景的寫作方式日益淡化消隱,而創(chuàng)作式的寫作日益突出。(P182-183)作者提煉出“背景式”寫作和“創(chuàng)作式”寫作兩個(gè)概念,并結(jié)合詞史論述,觀點(diǎn)新穎,極有理論價(jià)值。作者對詞學(xué)史上的“命名”,進(jìn)行挖掘、梳理,還重新“命名”,如“應(yīng)體”與“非應(yīng)體”,又如“館閣體”的命名,并與“西昆體”對比,皆發(fā)前人所未發(fā)。
書中隨處可見作者深刻的思想,可稱“有思想的學(xué)問”,而不是為了學(xué)問而學(xué)問。由此,筆者聯(lián)想到時(shí)下對“乾嘉學(xué)派”的評(píng)價(jià)。“乾嘉學(xué)派”的主流是有思想,關(guān)心世道人心。當(dāng)下,有些學(xué)者沒有認(rèn)清“乾嘉學(xué)派”的真精神,誤將乾嘉學(xué)派“末流”當(dāng)作學(xué)術(shù)“主流”和“正宗”,以為天下之“學(xué)問”盡在“考據(jù)”的“乾嘉學(xué)派”,非此,皆不是“學(xué)問”,有思想是空談,宏觀研究是空疏,甚至對梁啟超、胡適那樣的大學(xué)者的學(xué)問也鄙視譏評(píng)。“學(xué)問”變成純粹的技能,變成去除思想內(nèi)核的材料編排,學(xué)者變成純粹的“工匠”,這樣的“學(xué)問”,意義究竟有多大?我們應(yīng)認(rèn)清“乾嘉學(xué)派”的真精神,提倡有思想的真學(xué)術(shù),糾正學(xué)問凸顯、思想淡出的傾向。須知,只有具備深刻的思想,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xué)術(shù)。學(xué)術(shù)與思想密不可分,“學(xué)術(shù)思想”連稱,無學(xué)術(shù)之思想,多是無根之游談,無思想之學(xué)術(shù),多是資料堆砌,意義不大。王元化先生所倡導(dǎo)的“有思想的學(xué)術(shù)”和“有學(xué)術(shù)的思想”,才是真學(xué)術(shù)。
作者思維敏捷,視野開闊,博學(xué)多識(shí),見解深刻。恪守學(xué)術(shù)的懷疑精神、求實(shí)精神和創(chuàng)新精神,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膽大心細(xì)。不迷信權(quán)威,不盲從“定論”,如對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李煜開始“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觀點(diǎn)的質(zhì)疑,這種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如拜倒在權(quán)威腳下,對權(quán)威的觀點(diǎn)從不敢懷疑,不敢說一個(gè)“不”字,學(xué)術(shù)事業(yè)是不可能前進(jìn)的。當(dāng)下,古代文學(xué)研究界最缺乏的就是這種勇氣和精神,不少論著只是注釋權(quán)威的觀點(diǎn),不敢有己見,以求穩(wěn)妥。筆者由此想到,學(xué)術(shù)要?jiǎng)?chuàng)新,要前進(jìn),必須有大膽懷疑精神,必須提倡和踐行五個(gè)“懷疑”,即“懷疑權(quán)威”、“懷疑傳統(tǒng)”、“懷疑定論”、“懷疑書本”、“懷疑前輩”。舍此,一個(gè)學(xué)者是不可能大有作為的。
作者長于求異思維,從“反面”看問題,從“沒問題”處看出問題,不少觀點(diǎn)皆人所未道,新人耳目,是對通行觀點(diǎn)的“顛覆”,結(jié)論未必“無懈可擊”,但確有新意,至少能引發(fā)人們的進(jìn)一步思考。在拜讀全書的過程中,作者的語言風(fēng)格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詞史研究,既是“史”的研究,強(qiáng)調(diào)史的客觀性、真實(shí)性,史的發(fā)展脈絡(luò),史的規(guī)律總結(jié),又是“文學(xué)”研究,強(qiáng)調(diào)審美性、感性,要求語言優(yōu)美流暢,有個(gè)性,詞是“純美”的文學(xué),研究它尤其需要優(yōu)美的語言。作者論文帶著激情,書中將客觀史實(shí)描述與主觀價(jià)值評(píng)判有效結(jié)合一起,較通常著作更具個(gè)性色彩,從中可見作者的風(fēng)采,行文亦獨(dú)具個(gè)性,清新靈動(dòng)、優(yōu)美流暢,富有氣勢和情味。這對某些“新八股”式艱澀板滯、干枯乏味的學(xué)術(shù)論著寫作語言模式,也是一種矯正。讀木齋先生著作本身,即得到一種高雅的審美享受。他的論文和著作一直受到大學(xué)生和古代文學(xué)研究者、愛好者的普遍歡迎,獨(dú)具個(gè)性的語言也是原因之一。學(xué)術(shù)界早已提出唐宋文學(xué)研究應(yīng)該“審美化”,因?yàn)樘扑卧娫~實(shí)在太美了。作者一貫將唐宋詩詞研究“審美化”,善于欣賞美、挖掘美,積極地研究美、傳播美、創(chuàng)造美,這是十分值得稱道的。
作者在《后記》中說:“學(xué)術(shù)既然是一個(gè)求索真理的過程,謬誤和階段性的認(rèn)知就會(huì)是一種正常現(xiàn)象,超越自我,甚至是不斷地超越自我,也是一種正常現(xiàn)象。一個(gè)個(gè)體生命的存在,也許終生都不能得出最后的絕對真理,但他只要是一種真實(shí)的、誠懇的、認(rèn)真的求索,哪怕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也會(huì)比那歷史教員式的照本宣科有意義。”(P328)作者不僅有挑戰(zhàn)權(quán)威、顛覆定論的勇氣,更可貴的是有挑戰(zhàn)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氣。辛勤耕耘,頻頻收獲,從《蘇東坡研究》到《唐宋詞流變》,再到《走出古典——唐宋詞體與宋詞的演進(jìn)》,每一本專著的問世,都是對自我的一次超越。現(xiàn)在,作者奉獻(xiàn)出一部厚重的詞學(xué)專著,這是自己學(xué)術(shù)生命的升華,也是完成又一次大的自我超越。此書是十年磨一劍的結(jié)果,其問世是水到渠成的。作者正處在學(xué)術(shù)生命的豐收期和收獲期,學(xué)界同仁和廣大讀者有理由相信,此書的面世,并不意味著結(jié)束,而是又一次開始。作者在寫作完成這本書稿之后,追本溯源,進(jìn)一步思考和研究了唐五代曲詞的發(fā)生史,暫定名為《唐五代曲詞發(fā)生史》,我們期待著更加精彩的專著早日問世。作者《后記》中另有一段議論意味深長:“我從來沒有一種專業(yè)的態(tài)度,而是抱著一種游戲的態(tài)度,一種玩的態(tài)度。對學(xué)術(shù),我也確實(shí)是抱著審美的態(tài)度。換言之,學(xué)術(shù)寫作,是一種人生存在方式,一種樂趣。每當(dāng)研究一個(gè)新的問題,寫作一篇新的論文,都能使我感受到一種創(chuàng)造生命的快樂。”(P328)筆者深有同感,以“玩”的態(tài)度做嚴(yán)肅的學(xué)問,享受做學(xué)問的樂趣,而不是將學(xué)問當(dāng)作追名逐利的工具。這是一種做學(xué)問的境界,也是一種人生境界。當(dāng)下學(xué)者,應(yīng)該追求這種境界。筆者凡俗,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綜上所述,筆者從木齋的《宋詞體演變史》的個(gè)案,探討了詞史的寫法,并進(jìn)一步擴(kuò)而廣之,反思文學(xué)史的寫法,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幾點(diǎn)初步的見解:1、文學(xué)史寫作,應(yīng)該不再是對前輩學(xué)者的人云亦云,而是應(yīng)該有新的視角、新的思維,新的思考;2、文學(xué)史寫作,應(yīng)該不再是材料的機(jī)械陳述,而是應(yīng)該將研究對象視為一個(gè)有機(jī)的整體;3、文學(xué)史寫作,應(yīng)該能從感性的材料中不斷升華為理性的概括,從而將似乎沒有規(guī)律的文學(xué)史現(xiàn)象,總結(jié)出某些規(guī)律性的理論,并將這些理論在文學(xué)史的實(shí)踐中加以驗(yàn)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