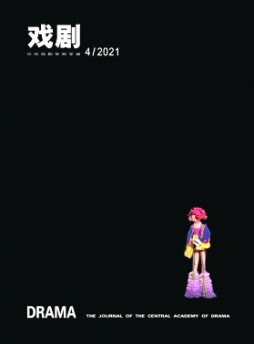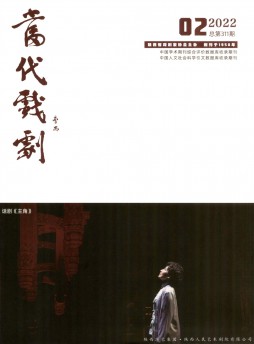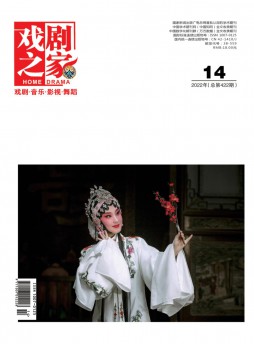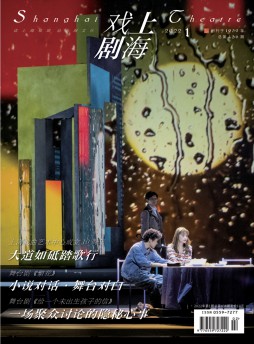戲劇視角下中西法律文化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戲劇視角下中西法律文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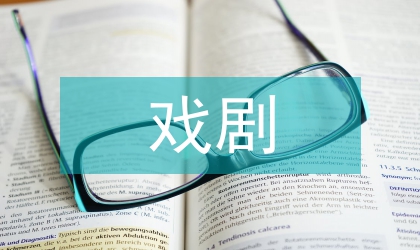
一、遵守法律與法律權威——從兩部戲劇說起
《鍘包勉》和《安蒂綱》這兩部情景類似、影響深遠但內核迥異的戲劇集中反映了“遵守法律”這個命題。通過分析這兩部戲劇所展現的法文化的差異,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方對于“遵守法律”這個命題的不同理解。本文將揭示,中國法以家庭倫理為主這個論斷雖然較為準確地勾畫了中國法的基本精神,但若將其與政治倫理作比較研究時,尤其是與西方對于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的關系相比較時,該論斷則有其局限性。在“遵守法律”與“法律的權威”上,中西文化展現了完全不同的特點。索福克勒斯在其創作的偉大戲劇《底比斯三部曲》⑤中塑造了悲劇英雄俄狄浦斯王,并且在最后一部《安蒂綱》中用大公主安蒂綱和新國王克雷之間的沖突,再次展現了無法逃脫的宿命這個悲劇性的主題⑥。安蒂綱與克雷的對抗,體現了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經典論題:在國家法之上存在著永恒不變的普遍正義⑦。在黑格爾哲學中,這一古希臘悲劇還反映了“城邦政權所體現的帶有精神方面普遍意義的倫理生活”和“家庭所體現的自然倫理生活”這兩種“最純粹的力量”之間的矛盾。自然法與國家制定法之間的對立,以及城邦倫理和家庭倫理之間的沖突,體現了古希臘哲人對法律本質的深刻思考。這兩種對立,實際上并沒有對錯正誤之分,克雷和安蒂綱的主張都有正當的理由,并且都是“絕對本質性的”主張。作為國王的克雷有義務維護城邦的安全,維護政治權力的權威和尊嚴。在義務和職責的約束下,克雷作為城邦的權威代表必須懲罰叛徒,以此保證城邦法令的權威和執行。另一方面,安蒂綱認為她有義務履行同樣神圣的且有自然血緣關系為支撐的家庭倫理責任,如果違背自然法的這一根本原則,城邦法的正義將無從談起。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明確聲稱這種對立和矛盾“是最高的倫理性的對立,從而也是最高的、悲劇性的對立”。家庭倫理與城邦倫理之間的沖突,情與法之間的沖突,以及戲劇中它們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凸顯了《安蒂綱》的悲劇因素。不僅安蒂綱本身是反抗世俗王權的悲劇英雄,國王克雷的行為和命運也呈現了另一種偉大的悲劇意義。他在維護城邦利益和政權合法性的時候,不得不嚴厲懲罰親人⑧。正如蘇力教授在評價這部戲劇時指出,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看,克雷代表的是“正在形成、尚不穩固但必將在社會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的城邦政治制度”,因此,克雷代表的是一種“變革的力量”。克雷必須挑戰已經長久確立的家族倫理體制和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克雷不僅是城邦秩序的維護者,他還是新制度的革新者以及舊秩序的反抗者。在班考夫斯基的代表作《合法生存——法中之情與情中之法》一書中,安蒂綱與克雷的悲劇在于他們都無視對方的世界“:他們都以法律的名義保護自己,但在各自堅持己見時卻丟失了人性”。他們都在自己認同的一套價值體系中與世隔離。克雷堅持城邦的規則,安蒂綱堅持神的法律,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法與情之間可能或者必然的沖突,他們只看到了規則,而忽略了偶發性、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的生活。“他們都希望生活是清晰可預知的,因此他們都忽視了情感的因素。”親情與國法之間的激烈沖突,在中國戲劇中也經常出現。被神化的包公形象,是中國最為著名的正義法官的代表⑨。民間關于包公鍘其侄包勉的故事,正好體現出在親情與國法發生沖突時,中國的戲劇家和老百姓所期望和接受的“理想情境”。《鍘包勉》一劇⑩,是描寫包公對于犯有貪污受賄罪的侄兒包勉,面對其情深義重的嫂嫂吳妙貞的說情,也毫不通融,依法處死包勉的故事。這一戲劇情節雖然正史無考,但是從相關史實與包公所立的《家訓》中可以看出包公秉公執法、不顧私情的一面。
二、以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的命題方法看兩部戲劇的差異
僅從戲劇本身看,包公和吳妙貞的沖突與克雷和安蒂綱的沖突非常相似。兩部戲劇都涉及國法與親情。然而細究起來,兩部戲劇凸顯了中西方對國法、人情問題思考的巨大差異。根據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代表人物哈特在其代表作《法律的概念》一書中創見性提出的內在視角和外在視角的劃分,戲劇中的人物持法律的內在視角,戲劇的創作者和我們這些閱讀者都屬于外在視角。持內在視角的人,他們的行動和他們對法律的看法有直接聯系,法律往往影響著他們的決策和行動,甚至直接是他們行動的理由。而對于持外在視角的人而言,法律與行動的理由之間并無如此緊密直接的聯系。第一,我們從法律的內在視角分析兩部戲劇中人物的行動和其行動的理由。《安蒂綱》中的克雷和安蒂綱根據不同的法律采取了不同的行為。《鍘包勉》中的包公和吳妙貞同樣也根據不同的規則而產生分歧。包公強調“王法條條,昭然在目,不可違抗”,而吳妙貞則痛斥包公“恩將仇報,忘恩負義,喪盡天良”。然而,西方戲劇中的安蒂綱與克雷最終沒有達成妥協,安蒂綱以死亡捍衛她心目中的神法,《鍘包勉》中的吳妙貞卻最終妥協于王法。實際上,戲劇中的吳妙貞從未質疑王法的正義性,她一開始痛斥包公的理由是包公作為執法者并沒有網開一面、高抬貴手、法外留情。在包公辯解之后,吳妙貞內心也“恨兒子包勉,不該貪贓枉法,按律治罪,理所應當”。吳妙貞最后不能接受的是“失去終身靠養”,因此想一死了之。而在包公承諾奉養吳妙貞之后,吳妙貞才終于“深明大義”,原諒了包公。在這兩部戲劇中,行為人對于國法與人情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安蒂綱》中,行為人直指國法與人情不可調和的沖突,用通融人情的神法質疑不通人情的國法,對國王所代表的國法尊嚴采取輕視、不接受、對抗和不妥協的態度。而《鍘包勉》中的行為人都是認同王法的權威性,僅僅是在執法官能否高抬貴手、瞞天過海地輕判罪犯上有分歧。在《鍘包勉》中,并沒有法律和正義的二元化的區分,法律是一元化,法律就是王法,而王法就是正義。第二,我們從法律的外在視角來看兩部戲劇所反映的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安蒂綱》的創作者和對其廣為流傳與分析的閱讀者,都發現了法律與正義的可分離性,也因此發展出了實證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之間長久的辯論:惡法亦法還是惡法非法?從神法到自然法,西方法律文化中始終保留著對超越于世俗國家規則的自然正義的敬畏。這種自然正義包含了對人性本身的寬容,對人之常情的理解和保護。因此,安蒂綱剛烈地追問:違背人情的法,算不算得上正義的法?而從戲劇情節本身的設計和后人的閱讀與傳播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這一質疑是“同情”而“贊賞”的。《鍘包勉》中的吳妙貞卻不同,她并未質疑法律的正義,而是質疑執法者本身的道德缺陷,即恩將仇報。王法對于她來說,雖然是不可違抗和質疑的,但是卻是可以“繞過”和“欺騙”的。戲劇的寫作者和后來的閱讀者,雖然同情吳妙貞的不幸,但更多的是對于包公這個執法者的“一邊倒”的贊賞,也就是對該劇中的包公不欺瞞王法、必須秉公執法這一點上的贊同。從法律的外在視角來看,西方的讀者更多地保持了對法律本身正義與否的審慎態度,而中國的讀者則更多傾向于對于王法本身就是正義這一點的強調。第三,從戲劇中的案件結果來看,司法者或裁判官的結局非常不同。《安蒂綱》中的克雷不僅僅是規則的制定者和維護者,他本身就是政權的最高統治者。然而,《安蒂綱》中的這位執政者雖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過錯,結局卻非常不幸。他為了維護城邦的利益和政權的穩固,做出合乎城邦利益的判決,卻最終受到命運的懲罰。安蒂綱死后,他自己的妻兒也隨之死去,戲劇作者以這個隱喻剝奪了克雷這個執法者享受人情溫暖的權利。戲劇作者在《安蒂綱》中所隱含的回答就是:法律與人情本身就不相容。《鍘包勉》中的包公不僅得到了吳妙貞的諒解,也得到了世代人的愛戴,成為中國的“司法之神”。在包公身上,人們雖然傳唱他的秉公斷案,傳唱他“法不容情”,卻通過他對吳妙貞承諾贍養,以及其他包公戲中他對于百姓的同情和愛護,對司法者寄予了一種“執法有情”的愿望。同情和保護弱者的司法官包公成為人們心中正義的象征、法律的代言人。而《安蒂綱》中的王者克雷卻是西方法律的代言人,孤獨、冷酷而無情。第四,安蒂綱將親情產生的權利和義務超越于實在法,將其歸于神法的范疇。而吳妙貞對于親情權利義務的理解,并沒有超越王法。《安蒂綱》中的家庭倫理與世俗法律之間二元對立,而《鍘包勉》中的家庭倫理卻隱藏在世俗法律的控制之下或范圍之內。前者強調超越于國家的親情,而后者則默認從屬于國家的家庭。安蒂綱表述的是超越的、永恒的親情權利和義務,吳妙貞承認的是世俗的、不超越王法的親情。根據西方對法律的劃分,法律分為國家的法、社會的法、自然法。安蒂綱將親情置于自然法的領域,而吳妙貞的親情屬于社會法中家庭法的部分。因此安蒂綱指出了國家法與外在的自然法的對立,而吳妙貞指出了國家法與內在的家庭法的沖突,兩者討論的是不同的沖突。第五,對于社會規范的調整,西方法律文化中產生了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的秩序”和哈特的“承認規則”這樣的理解。社會規范與國家法律不同,不是人們刻意建構的理性,不是人們行為的理由而是人們行為的結果,或者是人們對已經存在的規則的識別與認可。西方的社會規范也不同于自然法的規則,它不是恒久不變的真理或正義,而是同國家法一樣屬于世俗的、經驗的世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也有與西方類似的區分,例如法家學說偏重于國家法,老莊和墨家學說都談及自然法,而儒家強調的禮實際上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之上的身份等級制度,是社會規范中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僅以家族倫理為尺度的一種社會規范。因此,中國的禮治秩序強調的是個人對于家族的從屬,個人必須與其他人發生聯系,必須在家庭關系中尋找自己的坐標。當包公秉公執法的時候,他代表的是一個政府的官員對國家法的職責,參照的是國家法的坐標體系。而吳妙貞則試圖用家庭恩義關系來指責包公,說包公忘記了自己的家庭責任和家庭從屬關系,實際上是以儒家血緣身份制度和從屬關系來責備包公。值得注意的是,吳妙貞并未質疑包公所維護的法律,也就是說在國家法的層面,吳妙貞是認同包公的職責的。因此,在儒家法所調整的社會規范和法家法所調整的國家法發生沖突時,戲劇中的吳妙貞和包公都認同國家法的最終權威性。因此,《鍘包勉》中的吳妙貞雖然值得同情,但缺少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因素。《安蒂綱》中的兩位主人翁同樣是親屬關系,但安蒂綱自始至終都沒有控訴克雷本人不顧親情,她控訴的是克雷的法律違背了神法。在這個意義上,安蒂綱是以另一套規范來控訴國家法的不義,也因此具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因素。
三、結論
從以上五點對中西兩部戲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即與西方法觀念相比,中國法的基本精神是否表現在強調家庭倫理上?如果僅從以家庭倫理關系來調整社會規范的“禮”著手,或者僅從中國古代的家國式、君父式治理模式看,中國法的確強調家庭倫理,以血緣關系建立身份等級制度,并且將其他的社會關系容納于這樣一套家庭倫理的調整體系內,例如師生關系,君臣關系,都比擬為家庭內的父子關系。然而,如果將國家法這套參照系統也納入我們的視野,我們會發現,恰恰是在這兩套體系并存的時候,中國將社會法納入國家法,強調國法的最終權威,而西方則強調社會法與國家法的分離,強調神法或自然法的更高權威。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法的基本精神,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強調國家法、實證法的唯一和最高的權威。只不過儒家在尊重以君主為代表的國家法的最終權威時,用親情關系來弱化法律的機械與嚴苛,在“法不容情”時寄希望于執法者“法外開恩”,彌補由于嚴格執法而產生的法律不得民心的僵化局面。因此,與西方相比,中國法的特點不在于更強調家庭倫理,而在于特意將家庭倫理放置在政治倫理的調整范疇內,而西方則更強調這兩者之間的分離、對立與不可調和的沖突。另外,對于“為什么要遵守法律”這個問題,兩部戲劇也體現了中西法文化的差異。《安蒂綱》中的安蒂綱與克雷都遵守著各自認為正義的規則,安蒂綱面對克雷的懲罰,并未以“違抗法律才是正義”作為借口,而是提出更高的法來強調“遵守法律”的正義。因此安蒂綱和克雷都承認“遵守法律”的道德。只不過雙方對于“法律是什么”有不同的認識。對安蒂綱而言,惡法不值得遵守是因為惡法非法,只要她所認可的法律,就應當遵守。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要提出承認規則來闡明法律是什么。他無異于進一步解釋了亞里士多德的著名論題“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應當是制定良善的”的前半段。用哈特的承認規則來看安蒂綱的行為,我們能進一步提出疑問:“人們”對法律的識別與“安蒂綱”對法律的識別是一回事嗎?“安蒂綱”所識別和承認的法律才是法律嗎?在戲劇中,除了安蒂綱之外,雖然有人同情和理解她的行為,但人們更多的是承認、識別和遵守了克雷的法律。因此,安蒂綱反抗的實質是在識別和承認法律上產生出的問題,而并非僅僅是不遵守法律的問題。而《鍘包勉》中吳妙貞對于國法并不存在“識別”和“承認”的問題,更隱蔽的問題是對于“法律的遵守”的問題。吳妙貞希望包公能夠網開一面,因為包公位高權重,“可以”徇私枉法。如此一來,我們看到了吳妙貞的局限:在對國法這一最終權威的識別和承認上,她并不存在質疑;但即便認識到了這一最終“權威”,她仍然希望執法者包公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能夠繞過這一權威。也就是說,在吳妙貞這里,法律的權威性不是問題,但“是否遵守法律”在此語境內卻成了一個問題。《鍘包勉》廣為流傳、受人歌頌的是包公在巨大的人情壓力下仍然能夠秉公執法,嚴格遵守法律。但很可惜的是在其他的包公戲劇中,包公是否“遵守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他能否懲惡揚善獲得民心才是根本的問題。由此可見,“遵守法律”這一行為模式本身在西方的語境下就是正義,只不過存在國家法和自然法的分別。而在中國的語境下,“遵守法律”的結果決定了行為本身是否正義。包公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所稱頌的司法之神,在于他的裁判指向了人們所認可的懲惡揚善的結果,而非程序正義。
作者:何鵬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后流動站
- 上一篇:城管局工作謀劃范文
- 下一篇:唯物史觀視角的禮儀文化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