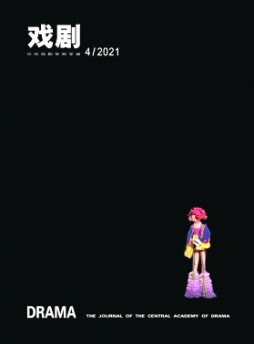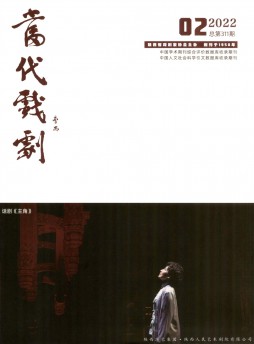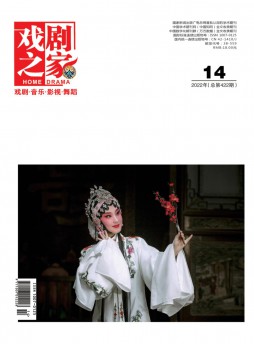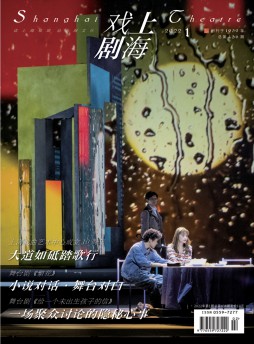戲劇創作作用下電影藝術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戲劇創作作用下電影藝術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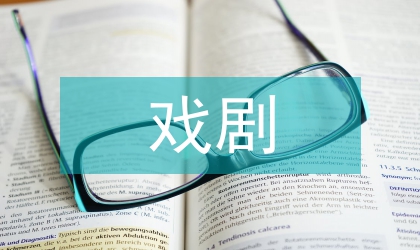
謝侯從事戲劇的年代,正是法國社會變革風起云涌、藝術觀念和創作手法劇烈變化的時期。和整個世界一樣,上世紀60年代的法國社會矛盾重重,沖突7戲劇的延展與升華頻繁發生,再加上各種社會思潮的泛濫,以及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反對“越戰”運動和中國的“”等事件的影響,終于在1968年爆發了著名的“五月風暴”。這場風暴在當代法國史上意義重大,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個人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在戲劇界,早在50年代上半期,布萊希特及其敘事戲劇理論與實踐就在巴黎,乃至全法國掀起了陣陣旋風,更是在貝爾納•道特、貝•索貝爾、讓-彼耶爾•萬桑等人不遺余力的推動之下,成為這一時期主宰法國劇壇的創作方法。與此同時,由30年代的法國人阿爾托創立的“殘酷戲劇”理論在美國戲劇團體“生活劇團”的推動下,終于受到其同胞的重視并被應用于實踐。于是,在其時的哲學思潮、社會運動,以及阿爾托和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法國戲劇發生了自“荒誕戲劇”以來最為重要的轉折與變化。謝侯此時投入戲劇,受其影響在所難免。于是,人們看到,在謝侯的戲劇創作中,無論是布萊希特的“敘事體戲劇”還是阿爾托的“殘酷戲劇”都極其鮮明地得到了體現與張揚。和多數戲劇家一樣,經歷過60年代的社會變革之后,謝侯對事物的認識,尤其是對社會和藝術的認識,都深受其影響,無論是其戲劇觀,還是戲劇創作都打上了這一時期的特殊印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其藝術的核心價值,并且一以貫之地在其創作中得到弘揚與升華。作為一名成長于上世紀50至60年代的青年戲劇家,謝侯自然而然地浸潤于其時得風氣之先的“敘事體戲劇”氛圍之中,更何況他周圍都是羅歇•普朗雄、阿里亞娜•姆努什金、讓-彼•凡桑、呂克•蓬迪、貝•索貝爾等這么一群躊躇滿志的布萊希特信徒。尤其是貝•索貝爾,因為曾經在柏林劇團有過近4年的實習經歷,更是被公認為法國最為正宗而堅定的布氏戲劇家。巧合的是,謝侯以專業的戲劇導演身份首次亮相,恰恰就在索貝爾擔任院長的熱奈維利耶劇院。
如今看來,在布萊希特敘事體戲劇理論與實踐的精髓之中,最為重要的一條便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看待戲劇及其與社會的關系,戲劇必須反映當下社會,發現矛盾并認清本質,促進觀眾思考,激發起其改變社會的熱情。受此影響,和普朗雄一樣,謝侯在對待前人的經典作品時,敢于為我所用,敢于施行必要的“手術”,以凸顯劇本對今人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意義。1966年,年僅22歲的謝侯第一次有機會作為專業導演登上國立劇院的舞臺亮相。為此,他選擇了19世紀劇作家歐仁•拉比什的劇本《盧爾希奈路事件》(1857)。拉比什乃是其時一位炙手可熱的“林蔭道戲劇”作家,名下有近180部作品,但多為千篇一律的輕喜劇,《盧》劇也不例外。謝侯當然無意搞笑,而是想通過“歷史化”手段對劇本進行大刀闊斧的改動,尤其是強化對人物的批評,來彰顯劇本對今人的借鑒意義。原劇表現兩位主人公在聽女仆讀報時,誤以為發生在盧爾希奈路上的兇殺案為自己酒后所為,不禁惶恐不已,于是鬧出了種種笑話。殊不知這是一張20年前舊報紙上刊登的消息,真相大白之后,一切恢復原樣。謝侯在執導時,為了揭示劇本的現實意義,不僅改動了臺詞與舞臺指示,甚至將一樁原本與實際毫無關聯的舊案改成了剛剛發生的真實命案,從而徹底改變了劇情,輕浮的鬧劇搖身變成一部沉重的“悲劇”。謝侯通過強化原作中的黑色幽默成分和突出人物的兇殘本性,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私、冷酷、欺騙與暴烈一面,其引起觀眾兩極的評價也在情理之中。
謝侯在擔任薩托維勒市劇院院長期間,在執導莫里哀喜劇《唐璜》時將這種古為今用的做法發揮到了極致。他將原作中通過主人公的言行反對其時宗教的內容以及相關的懺悔、寬宥、同情等主題擱置一旁,著力突出所謂的政治意義,亦即把唐璜塑造成一個“不滿路易十四政治統治、公然以生活放蕩、自由思想來表達其獨立的一個階層的代表”。[1](P.144)為此,他把一些自己認為毫無意思的場景(如“禮拜天先生”的那一場)大刀闊斧地刪除,卻在唐璜身邊增添了一幫落魄小貴族,以示這位敢于挑戰王權的“花花公子”并非孤軍奮戰。謝侯還在演出中讓6位衣衫襤褸的農夫當著觀眾的面操縱各種舞臺裝置,用以區分場景。農夫們操作完畢之后,并不退場,而是跳到一旁的草堆上酣睡,直到下次換景。此外,謝侯對唐璜這個人物的處理以及舞臺的設計也與其導演理念一致:破落公子穿上了當代反叛青年的黑色皮茄克;破敗的唐璜府邸之后矗立著一座漂亮的莊園,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仆人斯戛納瑞爾則為這位居無定所的落魄貴族費力地四處搬家……不同階層的對比、社會的不公乃至時代的變遷等由此得以凸顯。凡此種種,與十多年前受布萊希特鼓舞而大膽提出“舞臺寫作論”的普朗雄對《偽君子》一劇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①為了讓經典劇作能夠為今人服務,尤其是為了挖掘出其中的政治內涵,謝侯和普朗雄、索貝爾等人一樣可謂毫無顧忌,并且無所不用其極。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殘酷戲劇”理論從美國“出口轉內銷”,開始受到法國戲劇家們的重視。在阿爾托的影響下,戲劇家們的藝術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其創作方法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敘事體戲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戲劇的政治功能、教育作用的重視之上,那么“殘酷戲劇”的影響則更多地體現在對戲劇的拯救功能的認識、對文本的重新理解、對語言的革新以及對空間的重新發現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一些明顯的區別之外,“敘事體戲劇”與“殘酷戲劇”并非水火不容,相反,在某些方面還十分接近。因此,當這兩者同時作用于同一位戲劇家身上時,要想把它們截然區分開來不僅難以實現,而且也沒有意義。謝侯的后期創作、尤其是電影創作便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兩者的融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融合對其電影創作的影響甚至遠遠大于對其戲劇創作的影響。1972年,謝侯從意大利回到法國,應普朗雄之邀與其共同擔任里昂國立大眾劇院(TNP)的院長。在經歷了薩托維勒劇院的失敗和意大利導演喬治•斯特萊爾領導的米蘭小劇院的洗禮之后,謝侯的人生觀、戲劇觀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再像以往那樣對政治充滿期待,甚至對曾經努力實踐的大眾戲劇提出質疑,更加熱衷于表現死亡、殘酷等主題,其演出也越來越追求“壯觀”。與索貝爾相反,謝侯喜歡用“spectacle”一詞,該詞在法語中既指一般的戲劇、歌舞演出或任何一類表演,同時又有壯觀、宏大場面之義。當這些壯觀的場面用于表現人類的沮喪、絕望和死亡等主題時,其對觀眾的沖擊力量之大可想而知,而這種巨大的震撼力與沖擊力又正是阿爾托夢寐以求的。基于觀念上的這些變化,謝侯回國之后執導的第一部戲便是以死亡與恐懼為主題,并且不是個體的死亡、而是群體的殺戮。這部由法國當代劇作家讓•沃捷耶改編的英國人文主義時期劇作家克斯托弗•馬洛的戲名為《巴黎大屠殺》,表現的是發生在16世紀下半期法國由宗教紛爭引起的“圣巴托羅繆慘案”,場面的血腥遠遠超出了凡人的想象能力。為了強化“壯觀”效果,謝羅在兩堵墻夾擊著的舞臺中央注滿了水,“演出展示了死亡的種種手段:暴力、投毒、刺殺、扔出窗外、恐嚇……尸體不斷地倒在河里并順水流淌”。[2(]P.89)也許并非巧合,20年后其電影巔峰之作正是同一題材的《瑪戈王后》,其中的血腥程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謝侯早期戲劇的代表作是1973年執導的馬里沃的《爭執》,著名戲劇評論家貝爾納•道特認為此劇涵蓋了這位導演日后其他創作中的所有圖像與主題。
《爭執》原本是一出18世紀的老套喜劇,表現貴族青年男女的懵懂愛情,與《巴黎大屠殺》相比似乎毫無“壯觀”可言。然而,謝侯不僅對劇本動了“手術”,增加了整整45分鐘的序幕,還把馬里沃本人以及當代戲劇家弗朗索瓦•雷若有關教育以及兩性平等的文本“拼貼”了進去,為人物增加臺詞更是不在話下。然而,“壯觀”更多的表現在演員的安排及其表演方面,兩位負責小貴族教育的侍者變成了黑人不算,青年男女貴族初次見面之后竟然脫光了上身來做性別對比。整個演出堪稱美輪美奐,燈光、服裝、舞美無不令人驚艷,最為評論家們稱道的是兩堵“會說話”的高墻:“它們分割著空間、給出或堵上透視點……成為大自然演戲的場所”。[1](P.150)高墻之外,舞臺上還有噴水池、樹影等,無不都是參與整個演出的“會說話”的“物理語言”,實踐了阿爾托的理想。值得一提的是,其創作團隊里的中堅力量——舞臺設計師理查•佩杜齊還參與了謝侯的多部電影創作,保證了謝侯藝術風格上的一致。
二謝侯從小受到各門藝術的熏陶且多才多藝,因此,盡管他在戲劇,包括歌劇界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他內心的“電影沖動”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學生時代曾經在影院林立的拉丁區看過大量的電影,另一方面則由于許多同時從事戲劇與電影的大藝術家如英格瑪•伯格曼、魯奇諾•維斯康蒂等人一直都是其心中的偶像。早在上世紀70年代,謝侯就開始涉足電影,拍下了《蘭花的肌膚》(1975)和《朱迪•泰普沃》(1978)。后者雖然請出了著名影星西蒙娜•西涅萊,卻還是沒有取得多大票房價值。謝侯并不氣餒,在入主南泰杏樹劇院之后,還專門修建了一座電影院,表明了要在戲劇、歌劇和電影三方面同時發展的堅定決心。在擔任日常事務繁重的院長一職期間,他忙里偷閑,先后拍攝了包括《受傷的男人》在內的3部影片并獲得了觀眾好評,為其巔峰之作《瑪戈王后》打下了厚實基礎。在結束了杏樹劇院院長職務之后,謝侯的創作重點則轉向了電影。筆者以為,如果將謝侯的影片看作是其戲劇創作的延伸與發展,亦即將戲劇家謝侯與電影家謝侯結合在一起研究的話,那么我們對其電影便會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認識。表面上看,拍電影只是謝侯一種與生俱來的夢想,但從深層次看,拍電影又何嘗不是其戲劇家情懷在銀幕上的一種升華。用謝侯自己的話來說,拍電影是為了走出“過去的戲劇”,走進“另一種敘事”;[3]但另一方面,更是他出于對其時法國電影的不滿。在他看來,當時法國的電影大多“過于輕率”,不僅故事內容太簡單,而且拍攝過程十分倉促、粗制濫造。更為嚴重的則是,大多數導演往往缺乏社會責任感。因此,謝侯表示:“我要讓自己講述的故事更有擔當”。
其實,如前所述,這種社會責任感乃是謝侯這一代藝術家所特有的品質。為了拍攝《瑪戈王后》,謝侯整整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準備。他不僅把大仲馬的原著讀得滾瓜爛熟,同時還閱讀了大量德國小說家亨利希•曼的作品,而與之搭檔的腳本作者則花費了更長的時間。之所以如此,謝侯在接受索貝爾采訪時說道:“需要想象一種敘述,它是關于我們歷史的,但又令今人思考”。[4]作為一名深受布萊希特影響的藝術家,謝侯不僅在選擇戲劇劇目上重視其與現實的關系,如1983年排演日奈的《屏風》無疑與法國人心中至今仍揮之不去的阿爾及利亞情結相關,而且在電影題材選擇上也同樣追求“與某一現實相吻合或某種對當代的研究”。盡管他一再強調自己在執導電影或戲劇時決定因素更多是偶然,然而我們更加傾向于認為,這種偶然還是有著某種前提,即影片與其人生觀、藝術觀相一致。在談及《瑪戈王后》的意義時,謝侯認為:“必須深入研究圣巴托羅繆慘案,思考寬容、天主教、屠殺新教徒、與政治陰謀的結合、宗教信仰與純粹的權力斗爭之間的分界等意味著什么……”[4]眾所周知,近幾十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外來移民的涌入,法國社會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宗教、民族融合以及政治與權力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該部影片放映之后立即得到了法國社會熱烈而廣泛的反響。如果說謝侯的戲劇更多地受到布萊希特影響的話,那么他的電影其實更多打上了阿爾托的烙印。可以說,“殘酷戲劇”的觀念同樣深入進了電影家謝侯的骨髓。何謂“殘酷”?依照阿爾托的說法,“對精神而言,殘酷意味著嚴格、專注及鐵面無情的決心、絕對的、不可改變的意志”。[5](P.99)或者更明確地說,“是指生的欲望、宇宙的嚴峻及無法改變的必然性,是指吞沒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風,是指無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而沒有痛苦,生命就無法施展”。[5](P.101)這些話多少有些拗口,充滿哲理,其含義也是眾說紛紜。而實踐當中,要將這些抽象的“意志”、“必然性”或“生命旋風”變成具體可感的形象談何容易,多數人望文生義,直截了當地在舞臺上揮刀亂砍,搞得雞飛狗跳,甚至血腥不堪。當然,亂象的始作俑者還是阿爾托本人,因為一方面他強調殘酷不是“流血”、“受苦”,另一方面他又沒有予以排除,甚至自己也搞過一出類似的《血噴》。因此,在全世界的多數舞臺上,阿爾托式的演出大都逃脫不了歇斯底里、刀光劍影甚至血流滿地等名副其實的“殘酷”。當這種“殘酷”延伸到電影之后,駭人聽聞的畫面便如滔滔洪水向觀眾襲來。如果以殺人流血來衡量的話,《瑪戈王后》可謂無以復加地直喻著阿爾托的“殘酷”。影片的題材便是1572年夏天在巴黎發生的“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一夜之間約有3000人受害。在規模遠不如今日之大的巴黎市區竟然有如此多的人遇難,其慘烈程度可想而知。在謝侯之前,已經有過表現這一歷史事件或類似慘案的影片,一般都將之放在接近尾聲的高潮之處。然而,有著豐富戲劇經驗的謝侯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其置于開端的位置,很快進入高潮,以一系列的“壯觀”畫面再現了這段慘痛的歷史。與前人相比,謝侯營造的場面實在太血腥、大殘酷了:……不同的殺人方法,不同的兇手和死者的面孔,不同的追逐:宮廷侍衛們殺戮新教領袖們,安茹公爵、吉茲公爵追逐外省人,莫赫維追殺高利尼,高戈納斯追殺拉莫爾,查理第九掩護新教人士,瑪戈和夏洛蒂穿行于恐怖之中,這許多復雜的事件錯綜一處,構成了圣巴托羅繆壯觀的殘暴之夜。
[6]然而,謝侯還不甘心,在令人心驚肉跳的殺戮之后,又把倒在血泊中的遇害者剝得精光,遇難者被當作牲口一般堆上了板車,又像垃圾一般被扔進坑里……畫面之慘不忍睹,甚至連見多識廣的法國觀眾都難以忍受。當然,如果我們僅以血腥暴力來考察阿爾托對謝侯影響的話,恐怕不僅曲解了“殘酷戲劇”的精神,而且也是看輕了謝侯的理解力和藝術表現力。他曾經如此表述:“我想做這么一種寓意戲劇,其中表演所承載的思想能夠最終激發人們的情感”。[4]事實上,其電影與戲劇一樣,激發觀眾的思想與情感才是謝侯材于法國當今社會的題材,自然不可能都出現類似大屠殺的畫面。不過,雖然沒有揮刀殺人的情節,但類似于“精神的專注”、“不可改變的意志”,尤其是“痛苦”的場面卻比比皆是。如《受傷的男人》《被迫害妄想》《死亡詩篇》等,光從其片名中就可以看出“殘酷”的意味。《死亡詩篇》雖然是中文翻譯使然,但影片本身表現的正是主人公托馬的患病、治療和死亡的過程,乃是名副其實的一種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更進一步,還會發現謝侯電影所選取的題材大都是對傳統觀念的挑戰,不是表現同性戀就是死亡(《受傷的男人》《死亡詩篇》《愛我就搭火車》等),而直言不諱的鏡頭語言往往讓觀眾難以承受,但同時又激發出其強烈的情感。而這,正是阿爾托理想之體現。在謝侯的電影中,“殘酷戲劇”的觀念還體現在對文字以外的“物理語言”或“形而上”語言的重視。這種語言在戲劇舞臺上體現為音響、音色勝過文字概念本身,體現為舞臺設計、燈光、服裝等不再是簡單的陪襯,體現為演員的身體、舉手投足無不充滿意義,體現為舞臺空間中的場面調度等。電影的表達方式迥異于戲劇,這一切又都歸集于圖像與聲音組成的一個個鏡頭、一幅幅畫面之中,其中心則是演員的身體及其表演。所有這些特點,在謝侯的影片中均有相當生動鮮明的體現。人們尤其注意到,在《瑪戈王后》中,無論是畫面、音響還是演員的表演,謝侯都做到了極致。作為畫家之后,他對影片畫面的要求極其嚴格。有論者認為,這部影片中人們“可以看到近百個明顯借鑒于歐洲名畫的畫面”,其“基本質感、色彩、影響按照(古典)歐洲繪畫的特征構成”。[6]如此具有質感的畫面,配以匠心獨運的音樂,再加上依據歷史而重現的大量細節,包括人物服裝、宴會美食、殺人武器、森林狩獵以及民間舞蹈、宮廷禮儀等,都使得《瑪》集中而又鮮明地體現了謝侯獨特的電影風格。而這種風格貫穿了謝侯的全部影片,并成為謝侯的個性標志。在筆者看來,形成謝侯風格的最重要元素應該是其對演員及其形體的高度重視。眾所周知,謝侯是戲劇演員出身,有著大量的舞臺實踐,即使是以導演為主業之后,他還時常粉墨登場。科爾代斯的戲劇之所以能夠風靡一時,主要得益于他的杰出導演,但何嘗不同樣得益于其高超的表演?可以想見,這樣一位導演在拍攝電影時自然也會極其重視演員及其表演。事實上,謝侯不僅重視演員在拍攝現場的臨場發揮,更重視演員的排練。每次拍片都和排戲一樣,他必定會做精心準備,除了讓演員圍坐一起為之說戲之外,更要求演員進行大量的排練。
謝侯認為,導演多讓演員排練可以從他們身上挖掘出令人震驚的東西,從而使得電影重新找回其“驚人之力”。因此,謝侯影片中的演員表演畫面往往極具視覺沖擊力。除了《瑪戈王后》之外,《死亡詩篇》中兩位女護士為動手術之前的托馬剃除體毛的冗長鏡頭、《親密》中頻繁而又長時間出現的做愛鏡頭無不如此。謝侯對身體的高度重視在法國戲劇影視界十分有名,幾乎每一部影片中都有十分細膩的身體展示,其中的裸體畫面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也是使他成為頗具爭議的導演的重要因素之一。應該說,謝侯作為一位戲劇、歌劇和電影三棲導演藝術家,其作品數量并不算太多,然而質量大都上乘,為后人留下了不少優秀作品,乃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我們認為,謝侯之所以成為謝侯,乃是時代造就英雄的結果。謝侯成長于“二戰”之后,其時法國經歷了從戰爭廢墟中崛起、殖民地人民奮起解放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動蕩等過程,與此同時包括存在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等種種哲學社會思潮,還有以“荒誕戲劇”、“新浪潮”電影等為代表的現代藝術等,所有這一切都在強烈地沖擊著法國的戲劇與電影,沖擊著傳統的審美觀念與思維模式。謝侯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與藝術氛圍之中成長,深受布萊希特“敘事體戲劇”與阿爾托“殘酷戲劇”等觀念的熏陶,從而決定了兩者都在其藝術創作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早中期的戲劇與歌劇,還是后期的電影,都概莫能外。謝侯的藝術道路始于戲劇、終于歌劇①,后期則為電影。然而萬變不離其宗,戲劇才是其藝術核心價值的主體。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謝侯的電影藝術乃是其戲劇藝術的延伸與升華。要深刻地理解其電影,就得認真地研究其戲劇。
作者:宮寶榮單位:上海戲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