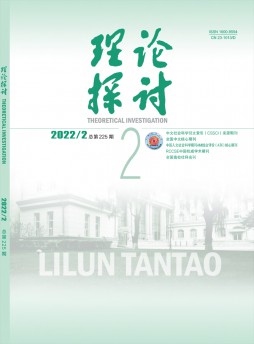探討圖書館學(xué)與傳播學(xué)的調(diào)和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探討圖書館學(xué)與傳播學(xué)的調(diào)和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人們通常將知識管理列為圖書館學(xué)領(lǐng)域,而將知識傳播列為傳播學(xué)領(lǐng)域,那么這樣看來,圖書館學(xué)與傳播學(xué)的融合怎么會產(chǎn)生呢?其實,圖書館學(xué)和傳播學(xué)之間的學(xué)科界限都有各自的特色,談到融合只不過是設(shè)想在圖書館學(xué)和傳播學(xué)的實踐領(lǐng)域建立起一套可以示范和研究的理論,因為它們共同面對的是“知識”這一概念領(lǐng)域。然而,知識又不是他們各自的全部,而且在圖書館學(xué)與傳播學(xué)的交集中,也不僅僅就只是知識這一項,知識之所以被獨立出來,或者說被作為關(guān)鍵詞凸顯出來,在于知識自身的本質(zhì)在這兩門學(xué)科領(lǐng)域的重要位置。雖然從標(biāo)題上看,圖書館學(xué)側(cè)重知識管理而傳播學(xué)側(cè)重知識傳播,但在實踐過程中,管理與傳播是相輔相成的,而且就是在各自的學(xué)科領(lǐng)域,管理與傳播的實踐也是日常發(fā)生的,并且發(fā)生的原理與機制具有相互的可借鑒性。尤其是當(dāng)下社會,更加促進(jìn)了融合的產(chǎn)生。作為兩門學(xué)科的融合,而不簡簡單單是工作實踐中的相互借鑒來說,學(xué)科與學(xué)科之間的共性和發(fā)展趨勢應(yīng)該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和具體的融合實踐證明。但是,這種融合并不代表兩門學(xué)科將會合并為一個學(xué)科,他們之間的差異和區(qū)別以及各自功用的不同還是十分明顯的。英國圖書館活動家麥克考文認(rèn)為圖書館員的職責(zé)不是改善用戶的個性和心靈,而是最大程度地擴大他們的選擇。韓繼章和吳晞也在論文中指出“讀者平等地享用圖書館服務(wù)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1]
而傳播學(xué)的融入正是要深入這種職業(yè)理性精神的探索,讓圖書館在網(wǎng)絡(luò)化時代,立足發(fā)展、開拓創(chuàng)新、繼續(xù)成為知識、文化和信息的中心。傳播學(xué)的奠基人施拉姆也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我們研究傳播時,我們也研究人,研究人與人的關(guān)系以及與他們所屬的集團(tuán)、組織和社會的關(guān)系;研究他們怎樣相互影響,受影響;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別人和受別人教;娛樂別人和受到娛樂。要了解人類傳播,我們必須了解人是怎樣相互建立起聯(lián)系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來到一起,試圖共享某種信息,他們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他們的生活經(jīng)驗不同,攜帶信息的標(biāo)志在他們看來很可能不同。經(jīng)驗愈是不同,他們理解的信息也很可能愈是不同。尊重多元和差異,學(xué)習(xí)寬容和實踐寬容是兩門學(xué)科的共同宗旨。
1知識概念以及相關(guān)關(guān)鍵詞
知識是管理和傳播的共同對象,也是管理和傳播賴以成立的基礎(chǔ)和材料。根據(jù)美國亞特蘭大Em-ory大學(xué)Goizuete商學(xué)院決策與信息分析系教授AmbitTiwana以達(dá)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魯薩克(Pru-sak)對知識的定義為基礎(chǔ),提出以下定義:“知識是結(jié)構(gòu)化的經(jīng)驗、價值、語境信息、專家見解和直覺的非固定混合體,它為評價和利用新經(jīng)驗與信息提供了環(huán)境和框架。它源于所知者的頭腦,并為之應(yīng)用。在組織中,知識不僅常常內(nèi)嵌在文件或存儲庫中,而且還存在于日常活動、流程和規(guī)范中。”[2]
從另一個角度看,知識一般被分為顯性知識、隱性知識和灰色知識,按照上文麥克考文的提法,圖書館能夠提供“內(nèi)嵌在文件或存儲庫”中的“完成態(tài)”的顯性知識;而對于“源于所知者的頭腦、并為之應(yīng)用”的“進(jìn)行態(tài)”知識,圖書館是無法提供這類服務(wù)的;灰色知識介于兩者之間,雖然有其獨特性,但如果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問題能夠解決,灰色知識的服務(wù)就可以水到渠成了。傳播的概念和技巧在這方面與圖書館學(xué)的交流說基本一致。從整體論角度講,知識雖然是結(jié)構(gòu)化的,但是也要隨著經(jīng)驗、價值、語境信息、專家見解和直覺的變化呈現(xiàn)出非固定性,無論是從知識的形態(tài),還是對知識的拓展和創(chuàng)新,都需要傳播以及傳播活動中的人的參與。如果將知識的結(jié)構(gòu)性比喻成芝諾圓圈的話,圓圈的邊界就是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起點,圓圈越大,邊界就會越長,所以學(xué)問越好的人,因為他的知識的結(jié)構(gòu)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和領(lǐng)域更加寬泛,不懂的東西隨著圓圈的擴大而增加,人也相應(yīng)地變得更加謙虛。不同的圓圈的交集,就是傳播的作用和產(chǎn)物,人們常常講的我有一個想法,你有一個想法,交流之后,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兩個新想法的故事,其實就是傳播的機制和效果。個人要想擴展其知識總量時,知識的發(fā)展是以圓圈的邊界為起點的,而傳播所產(chǎn)生的交集使交流的雙方知識拓展都呈現(xiàn)出跨越式的趨勢,這種知識的遷移容易激發(fā)創(chuàng)新性的想法和主張。
信息與知識是經(jīng)常一起提及的概念,有時候人們對信息和知識之間的界線并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就是簡單地認(rèn)為區(qū)別不大,可以互換。所以,當(dāng)圖書館改為信息中心時,圖書館知識海洋的比喻依然被人們提起,一些學(xué)者對圖書館提供的是知識服務(wù)還是信息服務(wù)也一直在糾纏不清之中。雖然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知識包含在信息之中,但從以上知識的定義中,知識明顯更加傾向于個體的、主觀的方面,也就是說如果經(jīng)驗、價值、語境信息、專家見解和直覺沒有記憶或存儲,以至于能夠隨時取用的時候,知識并不能被稱為知識,它沒有力量。而且結(jié)構(gòu)化的知識,能夠為分析、理解、應(yīng)用信息提供機制和模式。其實無論是知識也好、信息也好,在沒有被人們掌握和利用之前,都是靜止在世界之中。信息更加傾向于社會化狀態(tài),尤其是網(wǎng)絡(luò)化社會的發(fā)展,使人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動帶來的機會、挑戰(zhàn)與壓力,信息的流動過程,也可以簡單地定義為傳播,傳播和信息就如同硬幣的兩面。按照信息論的創(chuàng)立者香農(nóng)的理論,所謂信息,就是可以減少或消除“不確定性”的內(nèi)容,從信息流動的過程分析,一般來說信息可分為問題信息、途徑信息和地址信息,圖書館在這三個方面都提供著相應(yīng)的服務(wù)功能。一些專家認(rèn)為圖書館提供的不應(yīng)該是知識服務(wù),而應(yīng)該是信息服務(wù),針對這一點的討論集中在知識和信息那個更加準(zhǔn)確和個性化的問題,但是無論知識和信息,在主客觀的本體論層面上做研究和討論,明顯是紙上談兵。由于知識和信息正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起到與物質(zhì)和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以知識或者信息搜索為服務(wù)方向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正在顯示出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的誘惑,所以這些紙上談兵的引申含義有的是金錢誘惑下的難言之隱罷了。“信息或知識,當(dāng)它不再是作為工具和實現(xiàn)其他經(jīng)濟目標(biāo)的手段,而是作為一種資源的概念時,它對傳統(tǒng)物理空間體系和經(jīng)濟學(xué)體系同時構(gòu)成了一種系統(tǒng)的架構(gòu)。”[3]
知識與信息是圖書館最重要的物質(zhì)基礎(chǔ),圖書館一方面通過知識管理將無序狀態(tài)的知識與信息組織、協(xié)調(diào)到位,另一方面,以用戶為導(dǎo)向的讀者服務(wù)工作在新媒體的技術(shù)的壓力下,必須將傳統(tǒng)的讀者服務(wù)精神與傳播學(xué)的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才能在知識傳播的領(lǐng)域,得到更大的收獲和啟示。沒有最終的知識傳播效果,圖書館的知識管理功能就會有被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和新媒體技術(shù)取代的危險,而且目前這種恐慌性的不自信,已經(jīng)在圖書館的館員中有所蔓延,傳播學(xué)的融入是圖書館自身發(fā)展的新的起點和定位。
2圖書館學(xué)與傳播學(xué)的融合
一般來說,能夠構(gòu)成學(xué)科的三方面因素是學(xué)科的歷史、理論與實踐。歷史上看,圖書館與傳播學(xué)的關(guān)系十分具有戲劇性的場景:二戰(zhàn)期間的1942年,包括施拉姆、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等傳播學(xué)的前輩,每兩三天便聚集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長方形會議桌旁,研究并決定應(yīng)該向美國公眾傳播什么樣的信息,以鼓舞國內(nèi)的士氣。正如D•M•懷特所說:“大眾傳播研究1942年‘始于’國會圖書館”。事實上拉斯維爾的“5W”傳播模式正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研討班上提出來的。而如果在1943年,施拉姆接受衣阿華大學(xué)圖書館館長的位置的話,傳播學(xué)就有可能出自圖書館學(xué)和信息科學(xué)了[4]。
目前,中國大學(xué)中的圖書館系有的已經(jīng)和傳播學(xué)結(jié)合改名為信息傳媒學(xué)院了。北京大學(xué)信息管理系的周慶山也在給研究生上傳播學(xué)概論課程。美國圖書館學(xué)家J•H•謝拉將“交流說”寫在他的《圖書館學(xué)引論》中,并且明確了傳播和交流過程的要素和核心,這些都與傳播學(xué)的理論有相通的意旨,從這些年的圖書館專業(yè)期刊論文中,探討傳播學(xué)與圖書館學(xué)、情報學(xué)的關(guān)系,探討圖書館傳播效果等相關(guān)論文也大量增加。但要真正在理論上達(dá)到融合的目的,還需要中國圖書館學(xué)界和業(yè)界的實踐努力。張欣毅認(rèn)為“公共信息資源及其認(rèn)知機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體”等學(xué)科范式是圖書館學(xué)研究的新的方向和新的開始,當(dāng)然這個邏輯的起點在于他把傳統(tǒng)的圖書館學(xué)看作是“充其量只是一個‘機構(gòu)范式’,或言‘圖書館管理學(xué)’,它在研究對象的本體論尤其是人文本體論(社會價值本體論)建構(gòu)的‘先天缺失’,使其只能解釋、回答一些屬于‘形而下之器’層面的問題,遇到像‘人文本體論轉(zhuǎn)移’、‘社會價值觀重構(gòu)’、‘發(fā)展觀重構(gòu)’之類的‘形而上之道’層面的問題就顯得太過蒼白無力了。”[5]
由此看來,圖書館學(xué)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時代必須面臨學(xué)科深入和拓展的問題,當(dāng)前,不僅是圖書館學(xué)的學(xué)科拓展的問題,其他學(xué)科在知識密集和超文本的時代里,都面臨著多少同樣的問題,如果研究一下圖書館學(xué)科的引文情況,就會不難看出,究竟有多少學(xué)科是應(yīng)該圖書館學(xué)借鑒的,又有多少學(xué)科有與圖書館學(xué)交叉和共同發(fā)展的趨勢。其實如果追根溯源的話,許多融合的情況本來就在歷史過程中,已經(jīng)有過一定的體現(xiàn),變化是包含在學(xué)科發(fā)展自身中的,隨著時代和條件的變化,學(xué)科之間融合的趨勢是一種客觀的渴望,有些時候,囿于自身學(xué)科的地位和學(xué)者的面子,學(xué)科之間的關(guān)鍵詞和專業(yè)詞匯之間的通約性還沒有別發(fā)現(xiàn)而已。但是,各個學(xué)科的專業(yè)名詞和關(guān)鍵詞又有著學(xué)科的獨特性和獨占性,在通約的基礎(chǔ)上,只能是求大同、存小異,才更加有利于學(xué)科的健康發(fā)展和學(xué)術(shù)的正常交流。借鑒其他學(xué)科的知識體系,并不是實用主義,而是知識自身結(jié)構(gòu)的超文本現(xiàn)象的必然要求。
網(wǎng)絡(luò)傳播時代,對圖書館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沖擊,圖書館作為人類精神文明成果的收藏地的地位,從根本上得到了動搖,人們完全可以在家中上網(wǎng)來獲取信息和知識,圖書館“有藏?zé)o用”的尷尬局面很可能就會成為事實,許多圖書館為了生存,不得不出租閱覽室另作他用。從文獻(xiàn)收藏和情報利用到知識管理與知識傳播的進(jìn)步和轉(zhuǎn)換是圖書館生存發(fā)展的必然之路。目前,關(guān)于傳播學(xué)與圖書館學(xué)融合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還沒有全面展開,隨著國家圖書館政策的變化和人們自我提升、自我修養(yǎng)意識的加強,切實有效地將圖書館學(xué)與傳播學(xué)的理論和實踐融合,才能夠更好地指導(dǎo)圖書館未來的發(fā)展和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