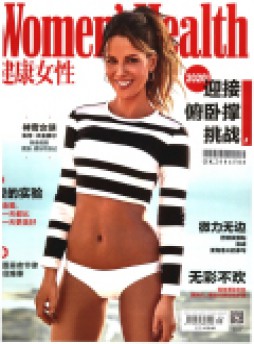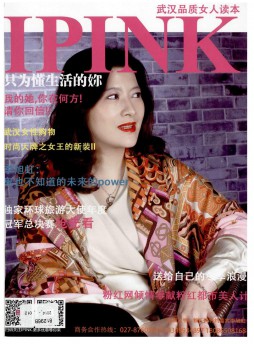女性作家詩詞創作的變化傾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女性作家詩詞創作的變化傾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作家雜志》2015年第四期
滿蒙八旗,浩浩蕩蕩,鐵騎入關,勢如破竹,最終踏平中原大地,建立起了遼闊的大清帝國。作為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在二百多年的漫長歲月中,清朝既為中華民族作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貢獻,也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屈辱不堪的辛酸歷史。目睹著它的滄桑巨變,從萬眾矚目的輝煌,到四面楚歌的悲愴,清代泰州女性作家的內心自然也是波瀾起伏,經歷了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從而使她們的詩詞創作呈現出不同時期的變化傾向。
一、風云變換中的凄涼苦吟
明清鼎革,滿清王朝為鞏固政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錮漢族思想,扼制漢族文化,漢族處于飽受歧視、深受壓迫的社會最底層,這引起了民族志士的強烈不滿。為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他們奔走呼號,體現出昂揚的反抗斗志,洋溢著濃厚的愛國熱情,但時代環境的冷酷,人生境遇的凄苦,卻讓他們的理想趨于幻滅,心靈飽受創傷。清朝前期涌現出了很多遺民作家,代表性的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他們記錄抗清斗爭,表達故國之思,抒發功業未就的悲憤,感嘆歲月蹉跎的無奈,風格沉雄悲壯,筆調哀婉凄清,體現出那個時期的創作主調。在當時的泰州文壇上,也活躍著這樣的遺民作家群體,代表性的作家有冒襄、鄧漢儀、黃仙裳等,受他們的影響,清朝前期泰州女性作家詩詞也呈現出這樣的主旋律。如女性遺民作家蔣葵和蔣蕙,她們遠離塵世,飄然歸隱,以決絕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故國之思、亡國之恨。蔣葵,字冰心,法名德日;蔣蕙,字玉潔,法名德月,暗寓不忘故國之意,以表冰清玉潔之心。兩姐妹,因遭家難,同入空門,伴一生古佛青燈,守一世晨鐘暮鼓,世事不聞,纖塵不染,坐化之時,僅留下了數冊詩詞,成就了佛門的一段千古佳話。翻開她們的詩詞佳作,詩學取向以韓孟為宗,風格凄清蒼涼,愁悶冷澀,充滿苦吟之聲。如蔣葵的《暮春苦雨即事》和蔣蕙的《秋夜聞蛩》,兩人皆取清寒蕭條之景,抒寂寥愁苦之情,這種愛禪喜靜的個性滲入其詩,深刻影響著詩風,帶有鮮明的遺民特色,體現出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對“人生無常,一切皆苦”的體認。
大家閨秀季嫻,字靜姎,號元衣女子,喜為詩,兼工長短句,著有《雨泉龕詩集》。女詞人偏愛寂靜、黃昏,喜好深夜、秋冬,詩集中有很多此類的作品,如《晚晴》《望遠》等,少暖色調,多冷色調,蕭瑟凄清,飽含深沉的滄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嘆之音,以助成清冷苦寒的詩歌意境。王睿,性情淡泊,志趣高雅,與吳嘉紀結為夫婦后,衣食不周,朝不謀夕,但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曾留下“大義歸夫子,饑寒死不怨”的蕩氣回腸之句。受丈夫影響,女詞人常借助詩詞抒發自己的悲憫情懷,如《清平樂•柳絲》,通過啼鶯、斜陽、飛絮、浮萍等意象,串聯起清貧生活的點滴,意境冷峭凄清,格調纏綿悲愴,這種風格與其抑郁苦悶的生活境遇、淡泊閑靜的個性才情是密不可分的。清朝前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宮婉蘭、徐幼芬、鄧繁禎等,大約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數并不是很多。因為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向來以男性為中心,女性處于被壓迫、被歧視的地位,封建宗法制度更是嚴酷異常,對女子進行文化奴役,道德鉗制,馴化其性情,愚化其思想,從而把“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奉為天經地義的信條,構筑起封建社會所謂的正統意識形態。這些陳規陋習扼殺人性,束縛才智,使得清朝前期的女性在創作道路上步履維艱,能留下些許足跡的只能寥寥數幾。
二、太平盛世里的性靈之音
清朝到了康熙時期,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帝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到了乾隆時期,大有建樹,成就輝煌,出現了康乾盛世的繁榮景象,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到嘉慶時期。這段時期國泰民安,文風昌盛,袁枚是當時最負盛名、最有影響的詩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他提倡“獨抒性靈”,認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在當時備受女性青睞。[1]于是東皋女詩人熊璉在《淡仙詞話》中也提出了與袁枚相似的見解:“詩本性情,如松間之風,石上之泉,觸之成聲,自然天籟”。[2]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清朝中期泰州女性詩詞作品不再表現悲苦失意的情懷,而是致力于藝術技巧的追求,傳達出很多自然清新的性靈之音。泰州陳氏家族中的才女陳傳姜,著有《得山樓詩稿》,其夫朱澤況,監生,工詩畫,她與丈夫經常談詩論畫,可謂志趣相投,琴瑟相諧。正是在這樣詩情和畫意的互相交融和滲透中,陳傳姜的詩詞創作才得到了不斷的豐富和發展。陳傳姜特別擅長寫景,不事雕琢,隨性而發,靈動清雅,自然閑適,正合于袁枚“性靈”之主張。如《中庭》,以女性特有的敏銳纖細,抓住“梧桐”這一具體意象,時而粗線勾勒,時而精雕細刻,可謂有聲有色,有動有靜,文筆優美,意境獨特,詩情畫意盡顯其中。她的題畫詩也是揮灑自如,很有特色,如《題清泉石上圖》等,作者善于選擇富有典型特征的景物進行具體描摹,從而創造出一種幽深寧靜的詩歌意境,體現出女性詩詞特有的體物入微、明凈流麗的清綺之美。清代中期,女性活動較宋明以來較為自由,一些家庭開明、思想解放的女性嘗試著走出閨閣,投入自然,這使得女性文學視野更加開闊,筆觸更加自由,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仲振宜、仲振宣姐妹曾隨父親仲鶴慶遠游至四川,她們飽覽壯麗山河,游歷名勝古跡,塵封的心靈猶如打開了一扇明窗,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命體驗,于是情感涌動,文采飛揚,寫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清新之作。為豐富閱歷,開闊眼界,趙箋霞曾隨丈夫仲振奎行至太行,一路的所見所聞,使她心生感悟,文思泉涌,于是真情實感自然流淌于筆端,讀之令人耳目一新,仲振奎稱贊道:“溫潤以澤,務使宮商應節、聲律和諧。”[3]清朝中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石學仙、洪湘蘭、仲蓮慶等,大約三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三左右,人數相對較多。因為這段時期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一些開明家庭開始讓女性識文斷字,從而使女性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更多的聯系。在這種濃厚氛圍的感染下,泰州眾多的女性詩詞作家開始大膽嘗試,沖破傳統思想束縛,擺脫正宗格調限制,以才運筆,直抒胸臆,可謂是信手拈來,渾然天成。
三、風雨飄搖時的現實寫照
清朝到了道光時期,國力開始衰落,到了咸豐時期,已是國庫空虛,危機四伏,內部爆發了太平天國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外部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長期停滯的中國封建社會陷入到了內憂外患之中,滿清王朝風雨飄搖,岌岌可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龔自珍、魏源等開風氣之先,開宗明義地直陳社會劇變給敏感士子造成的心靈震撼,闡述了“經世實學”興起的歷史必然性,他們的詩文見解精辟,文筆曲折,飽含著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蘊含著強烈的時代憂患意識。[4]在這種濃厚氛圍的感染下,清朝后期的泰州女性詩詞作家開始嘗試突破“小我情懷”,放眼現實社會,作品取向有所變化,悲苦凄涼的生存境遇、漂泊流離的亂世感受、苦難深重的社會人生成為了她們觀照的主體。李國梅,字芬子,興化人,李瀚女,解舉鼎妻,《重修揚州府志》載其著有《林下風清集》一卷,《然脂集》載其著有《芬子集》。她生活在清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心系蒼生,胸懷國事,其詩詞多涉及社會動蕩、政治黑暗、百姓疾苦,如《秋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戰亂場面和蕭條景象,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再如其《水退伐樹》,雖論古人之事,實抒今人之懷,暗喻本是同根一體,不應骨肉相殘,而應榮辱與共,同仇敵愾,體現了對國計民生的關注,對理想社會的渴求,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高佩華,字素香,葉雨樓妻,工詩,著有《芷衫吟草》,其中《巫山一段云》,作者并不單純專注于景色的細膩描繪,而是托物言情,寓情于景,通過景物描寫滲透主體精神,從而影射苦難深重的社會現實,寄托驅云見月的美好心愿。張蘭,字素香,泰縣人程紹安妻,守節撫孤,擅長詩詞,著有《馀生閣詩抄》。其中一首《讀李太白集》,著眼現實社會,關注民生疾苦,寫得酣暢淋漓而沉痛雋永;另一首《落葉》,筆鋒犀利,深刻尖銳,真實反映了社會動亂,黎民疾苦的社會現狀,尤其最后一句“倘遇桓司馬,金城恨愈多”,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造成這種社會狀況的內在根源,作為女性詩詞作家能夠具有這樣獨到深遠的眼光,針砭時弊,憂國憂民,實在難能可貴。清期后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朱均、任香尉、張粲等,大約二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二左右,人數不算太多。因為時局動蕩不安,社會危機四伏,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到處輾轉漂泊,顛簸流離。生存的困境帶來精神的痛苦,一些女性作家經常會對社會問題、性別角色、情感出路等進行尋根問底的深刻思考,于是不再簡單地停留在具體的生活表象,而是理性地將目光投入到社會現實,感受時代跳動的脈搏,從而形成對于社會時代的密切關注與深切憂患。但在這樣內外煎熬的生存境遇中,能夠超越自我,心系蒼生,憂國憂民的女性畢竟不多。
四、列強入侵后的愛國情懷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國家公然入侵,在中國瓜分勢力范圍,強占租界地,中國主權嚴重喪失,陷入極度屈辱的深淵。清政府懦弱無能,喪權辱國的行徑,激起了愛國志士的強烈憤慨,也點燃了愛國作家的創作熱情,以黃遵憲、康有為、譚嗣同等為代表的改良派紛紛口誅筆伐,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激烈的反帝情緒,形成了洶涌澎湃的愛國熱潮。作為中國改良主義運動的代表性作家,他們批判封建統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會的沒落,期待改革風雷的到來,呼喚個性思想的解放,他們的砰然一擊,驚醒了很多世人的沉夢,促使人們奮起還擊,絕地求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報效祖國,巾幗不讓須眉。泰州女性詩詞作家在強烈感召下,愛國熱情空前高漲,興化的劉韻琴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志向遠大,立志報國,從小仰慕古代女英雄,在《木蘭從軍》中慷慨激昂地寫道:“一朝戰罷回東閣,千古風高花木蘭。”愛國女俠秋瑾不幸慘遭清政府殺害,劉韻琴義憤填膺,不顧自身安危,毅然決然地寫下了著名的七律詩《吊秋瑾》,最后一句“恨煞東瀛初反棹,秋風秋雨送蘿蘭”,更是態度明朗,語氣堅定,鮮明地表達了對清朝政府黑暗統治的切齒憤恨,對革命烈士獻身精神的熱情謳歌,具有廣闊的社會歷史內容,富有豪邁的巾幗英雄氣概。劉韻琴一生都在實踐自己的崇高理想:“開啟民智,教育救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所處時代,能有如此表現,實在令人欽佩,讓人嘆服。
女性作家曹湘浦才情流溢,視野開闊,她飽含愛國熱情,體察百姓疾苦,以女性獨特的視角、特有的筆觸抒寫自己的悲憫情懷。翻開她的詩集《繡余吟草》,關注黎民生活之困頓,百姓勞作之辛苦的詩篇隨處可見,如《少婦愁》和《蠶婦吟》,字里行間浸透著對戰亂中百姓凄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對列強犯下滔天罪行的滿腔憤恨。還有一些女性作家的詩詞作品,一掃閨秀詩常見的纖弱低迷之風,洋溢著一種慷慨激昂,奮發向上的豪氣,讀之令人振奮。如錢荷玉的七律《登岳墩》,通過將民族英雄岳飛與賣國奸臣秦檜形象的對比,形成強烈反差,表達出自己鮮明的主體意識和獨到的思想領悟,由此可見她的腹笥之寬與眼力之遠。清朝末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陸椿長、陳佩章、韓佩芬等,大約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數相對最少。因為婦女解放運動,經過了艱苦的摸索和實踐,直到五四時期才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關注到婦女的生存狀況,以“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西方女權思想為武器大聲疾呼,堅信深受壓迫的中國女性一旦覺悟,必將成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但畢竟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5]在根深蒂固傳統觀念的統治下,在強大社會輿論的壓力下,能夠真正沖破世俗偏見,掙脫重重藩籬,以天下為己任、走在時代前列的女性畢竟是少數。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出泰州女性作家詩詞在清代的發展軌跡:從女性意識的最初覺醒,到勇敢地沖破傳統羈絆,掙脫宗法制度的統治;從思考女性的存在價值、主體意識,到追求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從局限于自我的性別意識,到帶有自覺色彩的國家“興亡意識”和社會“憂患意識”;從初具感性的愛國憂思情懷,到有了強烈的“參與意識”,并付諸理性實踐。[6]所以從清代泰州女性詩詞的發展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代女性艱難地尋找著自己角色定位的過程:探尋自我、思考自我、發現自我、彰顯自我,借助詩詞這種相對獨立的文學樣式,全方位地展示自我,從而使清代泰州女性詩詞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體現出女性自我精神風貌的完整性,為清代文學的發展增光添色,在泰州地方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沈輝 單位:泰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