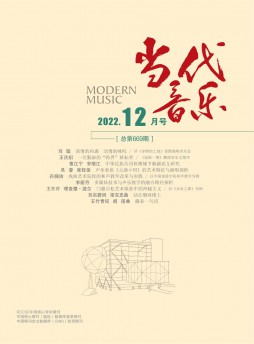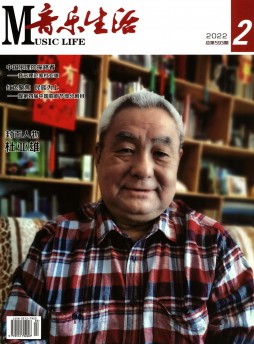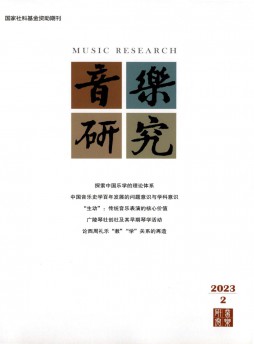音樂存在的困惑與解答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音樂存在的困惑與解答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在深受釋、道影響的蘇軾身上,詩歌、音樂與哲學都有豐富、深刻的體現。現存蘇軾琴詩展示出對音樂存在方式的高度關注。蘇軾在《琴詩》中質疑音樂的存在,由此提出“琴非雅聲”說,并在針對陶淵明“無弦琴”所作的翻案詩中直面消失的音樂,對樂器、音樂機制與音樂的關系作出客觀評價。面對稍縱即逝的音樂,蘇軾提倡音樂中的審美人格,用詩歌記錄、保存,使音樂在文化、審美的層面上得以傳承。
關鍵詞:蘇軾;琴詩;音樂哲學;存在
音樂、詩歌與哲學關系密切,產生哲理詩和音樂哲學①。其中,哲理詩在古典詩歌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而音樂哲學則罕有論及,這就使詩歌與音樂研究難以推進。②在深受釋、道影響的蘇軾身上,詩歌、音樂與哲學都有豐富、深刻的體現。他對音樂尤其是古琴有許多哲學思考,富含閃光片段。比如《東坡志林》卷四云:“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③雖是因論茶觸發,但如果不是經常思考此類問題,蘇軾也不會得到啟示。縱觀蘇軾的音樂哲思,主要集中在對古琴的探索,尤其對音樂的存在方式最感興趣,其中又包含著音樂存在的空間性和時間性等問題。學界的探究多以“樂道”、“琴道”或傳聲藝術為主①,重心不是落在“道”上,就是具體的“技”上,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本文從音樂哲學角度論述,通過探究蘇軾的琴詩與哲思,具體展現其音樂方面的困惑與解答,從而探索詩歌與音樂的研究新路。
一、《琴詩》對音樂存在的質疑
元豐四年(1081年)六月,蘇軾作《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此詩甚類佛偈,蘇軾《與彥正判官》明確說道:“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②,內容上又與佛經關系密切。《楞嚴經》卷四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③因此,一些學者認為此詩不是詩④,更多的學者則從此詩與佛禪關系的角度考量⑤,也有學者認為盡管是佛禪戲作,并不減損作為詩歌的魅力⑥。將佛禪因緣和合思想引入詩歌中并非蘇軾獨有。韋應物《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⑦又《贈李儋》:“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⑧宋長白評價云:“皆于楞嚴三昧有會心處;韋語顯,蘇語密。”⑨問題在于,蘇詩在韋應物詩歌的基礎上有什么新創造?當然,這種思想并非佛家獨有,儒家易學思想也有此類觀點。如蘇洵《仲兄字文甫說》對“風行水上,渙”之解釋瑏瑠,通過風與水相遇產生漣漪的自然現象,來表達對文章形成的看法,對蘇軾也有影響。但更讓人關心的是,蘇軾在此影響下,又在詩歌中給出了什么新哲思?目前學界在新哲思角度有所思考,如劉承華認為蘇軾詩歌體現出他對演奏之道的獨特領會:“當心與譜、手與弦的關系還需要你去處理時,即意味著你仍然在將演奏當作演奏,因而也就意味著你的心、譜、手、弦之間尚未達到高度的默契與統一。只有當你演奏時而又忘記你在演奏,才算達到真正的演奏境界,進入演奏之‘道’。”瑏瑡池澤滋子則認為蘇軾更關心精神的解脫之道:“雖然這首詩說的只是琴的聲音不但不在琴的樂器本身,也不在演奏者的指法,但是蘇軾在這首詩里,表現了要從樂器和指這些物體解脫出來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琴的真趣。”瑏瑢這些意見都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蘇軾的哲思,但沒有揭示出蘇軾的“音樂”哲思,而要探討這一點,就不得不跟詩歌聯系起來。事實上,只要把蘇詩跟韋應物詩歌一比較,就能看出蘇軾的關注點不在因緣和合上,而涉及音樂的空間存在問題。為更好地理解,不妨引用波蘭美學家羅曼•茵格爾頓(RomanIngarden,1893—1970)的音樂存在概念“純意向性對象”。于潤洋介紹說,茵格爾頓是通過現象學研究音樂的,茵格爾頓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音樂存在的問題,即音樂的本體問題:“而從它(指音樂作品———筆者注)產生的那一瞬間起,就以某種方式存在著,并且不依賴于是否有人演奏它。”①于潤洋對此有更為明晰的概括:“存在著兩種對象,一個是不依人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實在對象,另一個則是依附于人的意識的意向性對象。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是嚴格的、清晰的,二者不是同一的,不應相互混同。
藝術作品屬于后一個范疇,即意向性對象,而音樂作品就其本質、存在方式而言,則是一種更加純粹的意向性對象。”②正是在這一點上,音樂作品與文學作品發生聯系:“在他看來,音樂作品像文學作品一樣,是一種非實在的‘意向性客體’,或者說是意識性對象,它自身存在著一系列有待填充的未定點,而讀者通過自身的主觀體驗和理解填充了這些未定點,從而使音樂作品原來所提供的有限的想象世界具體化。在這個過程中聽者通過自己的一系列意向活動構造了一個完整的、被填充了的客體,從而揭示了音樂作為一種純粹的意向性客體,與其他藝術相比,它在人類的情感世界中所占據的獨特位置。”③但同時,它又跟文學作品不同:“在音樂作品中并不存在構成文學作品所特有的那些語言因素(概念、詞匯、句子等),因而也就不存在由這些因素構成的那些具體對象,諸如實物、事件、情節、人物等等,也就是說音樂作品中并不存在文學作品中那種‘意義層’。”④于潤洋指出,茵格爾頓發現文學作品有四個層次,即語音層、意義層、被表現的對象層和概要化方面層,而后兩層是需要讀者填充和具體化的,而“音樂作品(指沒有歌詞、劇情等因素參與的純器樂)的本體結構同諸如文學、繪畫、建筑等作品不同,它并不是多層的,而是單層性的。在音樂作品中并不存在文學作品中所具有的那些涉及意義、客體的層次”,而“音樂作品本體的性質就已決定了它自身并不存在于某一特定空間中,它本身就不是一件可以存放于空間中的實物”⑤,同時它又具有“超時間性”(內在時間結構),因而并不存在于實在的時空之中,而“以非實在的意向性對象的方式存在著”,它比文學作品更純粹,是“純意向性對象”。因此,欣賞者在感受過程中要“以更大量更強烈的意向活動去填充它,賦予它以更多的主觀意識以參與構成音樂作品這個意向性對象”⑥。盡管茵格爾頓認為音樂是“純意向性對象”的觀點頗受學者質疑,如李曉囡就將音樂也分為四層⑦,但通過其論述,對音樂的存在方式得出的結論本身卻很有啟發,尤其對我們理解蘇軾的《琴詩》之哲理內涵極有助益。蘇軾自然不會知道“意向性對象”之類的概念,但從他詩中可以發現,他否定琴聲在主客體上的存在,與茵格爾頓的觀點內涵很接近。蘇軾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闡發叢林禪僧人人皆知的因緣和合思想,更在于從根本上質疑琴聲的時空存在,從而才是真“問”紀老:“你們都以琴聲比喻佛法,如果琴聲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佛法如何存在?”蘇軾此問的真實意圖在此。若非出于對琴聲時空存在的質疑,蘇軾是無法如此深入地譬喻、發問的⑧。那么,蘇軾是如何表明音樂主客體方面的不存在呢?
二、“琴非雅聲”:音樂消逝的極端例證
蘇軾的“琴非雅聲”觀,歷來受到學界關注。其《雜書琴事十首•琴非雅聲》說:“世以琴為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①對這段話,眾說紛紜,即便是音樂史學者的解讀,分歧也很大。蔡仲德說:“后者更認為古之琴聲才是雅聲,今之琴聲則已淪為鄭衛,今之箏笛更等而下之。”②從蔡仲德的理解來看,是把文中的“琴”看作“今琴”,即當時的人認為他們彈的琴正是雅聲,而蘇軾認為古琴才是雅聲,時人所彈之琴跟古代的鄭衛之音類似。但這樣增字為訓并不可取。章華英則說:“這段話指出了琴曲與民間音樂的關系,是很有見地的。”③這又把“琴”理解為“古琴”,從而看出以古琴為載體的雅俗之變,其中便包含著“琴曲與民間音樂”的轉化。無論是哪一類理解,都包含著一個預設,即古琴之聲和今琴之聲、雅聲和俗聲是可比的,這跟蘇軾文中之意不符。從“琴正古之鄭、衛耳”來看,很容易誤導讀者往音聲比較的角度來理解,聯系上下文,會發現蘇軾這一論述實際上針對的并非音樂,而是樂器(類似于《琴詩》中的“弦”,即樂器的材質、形制等)和音樂機制(類似于《琴詩》中的“指”,指演奏技法等),回顧樂器、音樂機制的變遷、交融歷史,蘇軾感嘆雅俗、華夷之聲“莫能辨”。在蘇軾的觀念中,可以比較的是樂器和音樂機制,在它們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音樂比較,當它們本身融合、變化、無法區分后,音樂本身也就隨之不可分辨。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作《戴道士得四字代作》詩:“賴此三尺桐,中有山水意。自從夷夏亂,七絲久已棄。心知鹿鳴三,不及胡琴四。使君獨慕古,嗜好與眾異。共吊桓魋宮,一灑孟嘗淚。歸來鎖塵匣,獨對斷弦喟。”④此詩雖是代作,誠如紀昀“仍是自寫胸臆”⑤之說,主要還是表達蘇軾自己的看法。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云:“唐法曲雖失雅音,然本諸夏之聲,故歷朝行焉。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自爾夷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前輩嘗言,今世所謂琴者,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則皆胡風矣。而雅音替壞,不復存焉。”⑥這對蘇軾“琴非雅聲”觀的解釋基本正確。只是古人所關注和想要恢復的是雅聲、雅音,所以他們只說“雅音替壞,不復存”,仔細推想,那個隨著樂器、演奏等不斷變化而變化的俗聲、俗音,又何曾繼續存在呢?音樂和詩歌雖然都是時間藝術,但在時間的流變之中,演奏出來的音樂不斷消失,詩歌卻可以借助語言和文字保存下來。即便唐宋時期發明記錄琴音的減字譜,也無法完全同樣重現音樂。因此,并非同時演奏的音樂之間的比較,只能是在“意向性對象”中存在,也就是在人們的回憶、聯想中進行較主觀化的比較,如元祐三年(1088年)蘇軾在《范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中云:“朱弦初識孤桐韻。”自注:“時公方進新樂……舊樂,金石聲高而絲聲微,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⑦一旦時間跨度超過個體的經驗認知,那就只能用富含文化傳統的概念,如雅俗、華夷之類甄別。
蘇軾在元祐末年所作《見和西湖月下聽琴》中便云:“謖謖松下風,靄靄隴上云。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樽。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我有鳳鳴枝,背作蛇蚹紋。月明委靜照,心清得奇聞。當呼玉澗手,一洗羯鼓昏。請歌《南風》曲,猶作虞書渾。”自注:“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澗道人崔閑妙于雅聲,當呼使彈。”①首四句化自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②詩句,但在陶詩的基礎上,又增加“風聲”。與白云的高不可攀不同,“風聲”流動不已,變化無窮,“自其變者而觀之”,跟音樂一樣無法維持存在,無法持寄。這種消逝感更明確地體現在《十二琴銘•松風》中:“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于萬竅號怒而實無。其蕩枝蟠葉,霎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③在似有實無的風的作用下,聲音顯得更為飄渺,難以捕捉。那么,又怎么能夠分清松、風二者是誰在發聲?連聲音來源尚且存疑,又如何拿來比較?因此,在《見和西湖月下聽琴》接下來的幾句中,盡管蘇軾講到自己的古琴樂器和善作雅聲的演奏者,認為二者相遇,雅音可現,可以“一洗羯鼓昏”,但這更多地是一種文化價值寄托和對友人的情感認同,因為雅聲究竟是什么已不可知,無法比擬。這種極端的對音樂存在的體會,并非蘇軾獨有。北宋幾次作雅樂,最后都不能令人滿意,就是很好的證明④。在這種思辨風氣下,宋人也想出一些解決辦法。如《宋史•樂志》第九十五引蜀人房庶之說,其解決的辦法是“由今之器,寄古之聲”。他說:“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后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后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后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為正聲,而概謂夷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后世易以杯盂;簟席以為安,后世更以榻桉。使圣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桉,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⑤但最后還是沒有辦法區分雅樂和淫聲,只能以古代流傳下來的審美傾向和辨別標準來加以衡量。蘇軾的解決辦法則更加本質化,富有靈活性。
三、“無弦琴”翻案詩:正視無法持存的音樂
對于陶淵明的無弦琴,蔡仲德總結出對立的兩種理解:一是“有人甚至把它理解為弦聲與意趣對立,弦聲妨礙意趣,毀琴去弦才能得到意趣”(如楊發的《大音希聲賦》、宋祁的《無弦琴賦》等);二是以崔豹的《古今注》、蘇軾的《淵明無弦琴》為代表,“認為陶潛……意在強調超越音聲,追求弦外之意,把握音樂美之所在,而不在取消弦聲,否定弦聲”,這也是蔡仲德所贊同的⑥。為預防蘇軾遭到陶淵明般“不解音律”的責難,從而影響本論題的探究,故在展開之前,先就此問題略作說明。蘇軾確實不會彈琴,其《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其二云:“……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耳,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⑦由于烏臺詩案,蘇軾“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愿,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醖釀,便生出無窮事也”,朋友勸他學琴,蘇軾不愿勞心。可見,他對音樂的看法極為通透,同時也說明他不會彈琴。但不會彈琴(或者說不善于彈琴),并不意味著不懂琴①。其《東坡志林》卷五中便用琴學知識駁斥五臣注的荒謬:“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令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聲也。兩弦之間遠則有,故曰間遼。弦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②可見,蘇軾對古琴指法極其熟諳。不僅如此,他對古琴的妙處也有切身體會,在《雜書琴事•家藏雷琴》中云:“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為何等語也③?其岳不容指,而弦不,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于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岀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韻,此最不傳之妙。”④蘇軾所指即“納音”。劉承華云:“在龍池、鳳沼的對面即面板的內壁還各有一個隆起的‘島’,稱為‘納音’。‘納音’的形狀往往做成圓形盆狀(視池、沼的形狀而定),即周圍較寬較高,中間凹陷。這種形狀的納音功能,是為了避免聲音從龍池、鳳沼直接向外傳出,而迫使它在納音的周圍略作停留,繞路而出。這種繞路而出的出音方式,也使得古琴的聲音具有封閉、旋繞、內含、深蓄的效果。古琴出音的這一特點,蘇軾曾經在其《家藏雷琴》一文中指出過。”⑤正因為蘇軾對古琴極為熟悉,所以能對陶淵明無弦琴感同身受。在蘇軾之前,人們對陶淵明無弦琴以接受、傳承為主,如白居易、歐陽修等。歐陽修《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圣俞》其一云:“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弦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眾人喜隨時。其中茍有得,外物竟何為。寄謝伯牙子,何須鐘子期。”⑥對陶淵明無弦琴背后體現出來的人格特加贊美。蘇軾的一部分詩作也是如此。如《和陶貧士七首》其三云:“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
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⑦也偶爾通過陶淵明的無弦琴來委婉地勸誡彈者,如《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云:“白露下眾草,碧空卷微云。孤光為誰來,似為我與君。水天浮四座,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曲蘗醺。尚恨琴有弦,出魚亂湖紋。哀彈奏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⑧除此之外,蘇軾還對陶淵明的無弦琴作有翻案詩。在《張安道樂全堂》詩中說:“步兵飲酒中散琴,于此得全非至樂……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弦。”⑨《蘇軾全集校注》云:“張安道不僅無弦,更連琴也不具,似乎比陶更超然,臻于不憑借外物而至樂之境。”⑩如果說這還只是出于對長輩的尊敬,那么下面這首詩則說得更為直接。其《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嘆。無弦則無琴,何必勞撫玩。”瑏瑡又《淵明非達》云:“陶淵明作無弦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須弦上聲。’蘇子曰:‘淵眀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茍為不然,無琴可也,何獨弦乎?”①孔凡禮引葛勝仲《丹陽集》卷八《書淵明集后三首》其三“子瞻為徐州,誚淵明無弦不如無琴,后悔其言之失”之說,并云:“《文集》卷六十五《淵明無弦琴》以徐州之時說為妄。”②考《淵明無弦琴》其文,乃辯護陶淵明“知音”,并非對徐州“淵明非達”之說的反悔。葛勝仲之說無據。池澤滋子分析說:“蘇軾為何一方面稱美陶淵明是知音者,一方面又說‘淵明非達者’呢?這是因為蘇軾在淵明故意不修復斷弦的行為中,看出了淵明拘泥樂器形狀的心理。蘇軾認為,既然達到真的悟達,就是琴有弦也不會紊亂自己心中的平靜。所以沒有像陶淵明那樣,不修復斷弦,故意讓它處在不能演奏狀態。超脫于古琴的形狀,超脫演奏技藝,以平淡自然之心體味琴樂真趣,就是蘇軾所理想的至高悟達。”③此言得之。值得注意的是“無弦則無琴”一句。跟一般的翻案詩不同,蘇軾并沒有對同一對象,從不同的思路出發,得出不同的結論,而是依然順著陶淵明的無弦琴思路,只不過因為思考得更為深刻,所以得出不太一致的觀點。在蘇軾看來,沒有弦的琴不是琴,又何必稱作“無弦琴”,使其名實不符、混淆視聽?這就顯示出陶淵明跟蘇軾思想上的根本差異。如果說“陶淵明的‘無弦琴’深寓著老子‘有生于無’、‘大音希聲’和‘有無相生’的哲學本體論理念”,而“老子肯定‘無’,卻并不否定‘有’”,俗人卻并不能“洞見無弦琴背后的‘有’”的話④,那么蘇軾則把無弦琴背后的“有”摧毀,而代之以傾向于佛禪的空無思想了。這當然不是蘇軾思想的全部或主流,但通過其對音樂(尤其是雅樂)的存在方式的質疑和對無法持存的音樂的正視,都可以看出他在《琴詩》中問紀老的難題,其實也是他在心中一遍一遍思考、一遍一遍追問自己的難題。
四、《破琴詩》:音樂的審美留存
音樂產生的同時也在消逝,無法長久地持存,這一問題所象征的人生難題,在佛禪世界其實已經解決。《圓覺經》云:“受用世界及與身心,相在塵域,如器中鍠,聲出于外。”⑤這種“禪那”境界,超越動靜、止觀二障,如樂器雖在時空之中,樂聲卻已超越于時空之外,抵達彼岸,而并非消失。但這種解決的基礎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對以儒家思想為主的蘇軾來說,成效并不大。不過,只要換個角度,以審美目光來欣賞佛禪信仰,把僧徒奉行的宗教體驗當作審美境界,這種辦法則很有啟發意義。縱觀蘇軾的藝術人生,他對釋道的思想吸收,確實帶有審美實踐的性質。正如漢斯立克所說:“音樂藝術唯一的、永不磨滅的東西是音樂的美,亦即我們偉大的大師們所體現的,以及未來一切時代的真正的音樂創造者們將要培育的東西。”⑥在漢斯立克看來,音樂的美在于樂音運動。但在蘇軾眼里,音樂的美卻不僅僅如此,它更體現在人們的審美態度和對“琴意”的理解上,而對“琴意”的理解反映出來的其實是審美人格。元祐六年(1091年),蘇軾作有《破琴詩》。其敘云:“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淞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弦。予方嘆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弦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其詩云:“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弦,音節如佩玉。
新琴空高張,弦聲不附木。宛然七弦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弦曲。”①王文誥以為此詩別有深意,乃暗指劉摯,但我們的關注點主要放在蘇軾的音樂審美上。按照蘇軾追本溯源式的思考,“無弦”的不是琴,那么“十三弦”的也不是琴而是箏。果然,仲殊長老一彈,深通琴律的蘇軾就聽出“異聲”來。琴破可修,本來不是琴的箏,也能彈出“琴意”來嗎?在“通脫無所著”的仲殊長老看來,“秦箏是響泉”,不必執迷于“度數刑名”。受此夢啟發,蘇軾也注目于“琴意”,發現秦箏有時候也能彈出“音節如佩玉”的琴音,而沒有琴意的新琴彈奏出來的聲音,卻如箏聲②。房琯不辨于此,因而輕信沒有人格的董庭蘭,蘇軾說他“陋矣”,蘇轍《次韻子曕感舊一首》則表示“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③。這是琴學審美人格的唐宋之變,在唐代并不強調,但在歐陽修、梅堯臣等北宋人眼里卻異常重要,在蘇軾這里甚至成為抵抗音樂流逝的根本方式。唯有在音樂審美中注入這樣的主體人格,才能在音樂的消失中保持著不變的內核,再用文字記錄下來(“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傳之久遠。在思索音樂的存在方式中,與其說詩歌與音樂相遇,不如說是在哲學的思辨中共振。美國學者古斯塔夫•繆勒說:“文學的哲學應該表明:支配和區分著種族、時代和文化,并使它們可以為人理解的價值觀,是如何也指向它們的想象,并在文字藝術里得到體現。”④這種類似于“價值觀”的對音樂中審美人格的堅守與提倡,不僅能夠“指向它們的想象”,而且也能夠長久地在未來得到回響。
作者:關鵬飛
- 上一篇:音樂表現要素在欣賞課中的運用范文
- 下一篇:中美動畫音樂藝術特征比較探究范文
擴展閱讀
- 1音樂情緒在音樂賞析中的表現
- 2傳統音樂和民族音樂
- 3音樂欣賞
- 4現代音樂爭
- 5音樂欣賞
- 6西方音樂作品音樂學探究以及音樂技術分析
- 7音樂主題旋律
- 8音樂舞蹈
- 9音樂美學思想
- 10教會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