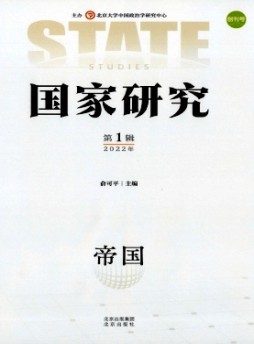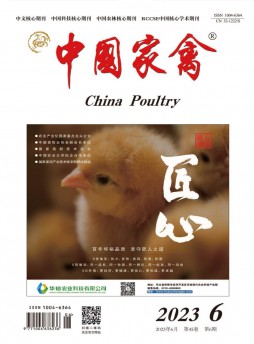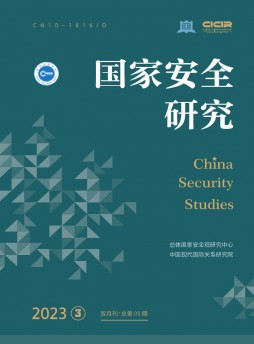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科學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從中央集權到地方分權的轉變
恩格斯非常明確地指出:“國家集權的實質并不意味著某個孤家寡人就是國家的中心,就像共和國中的總統那樣。就是說,別忘記這里主要的不是身居中央的個人,而是中央本身。”③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權力的集中有兩種,一種是官僚主義的集中制,另一種是自愿的集中制即民主集中制。這種自愿的集中制要求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實行集中。他明確指出:“真正民主意義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歷史上第一次造成的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是不僅使地方的特點,而且使地方的首創性、主動精神和達到總目標的各種不同的途徑、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順利地發展。”④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央與地方關系是對特定歷史時期政治局勢與社會背景的直接反映,是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晴雨表”和“度量尺”,是特定時期政治變遷、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歷史寫照。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關系各不相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時空條件下、不同的社會經濟生活以及由此決定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環境。從建國初期確立的蘇聯模式到如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法治國家的建設,此間經歷了許多曲折,與之相應,中央與地方關系亦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首先要結束自清末以來的國家分裂狀態,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使國家政權能從中央延伸至地方,對于以為首的黨中央來說,建立單一制的政治架構幾乎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全國統一”與“中央集權”成為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主調。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尊崇蘇聯為“老大哥”,以蘇聯為榜樣,效仿甚至是照搬了蘇聯的中央高度集權領導體制,逐漸形成和確立了中國特色的中央高度集權治理體制。在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中,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都有其合理性和科學性,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都應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慮。早在建國初期,黨中央對于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必要性就有了比較清晰和正確的認識。1951年,就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落后性與不平衡性,我們的工作便要采取分權的辦法來進行。一方面,我們要實行中央集權(凡是必須由中央集權的,都要集中到中央來),另一方面,也要分權于地方。因為只有經過這個步驟,才可以逐步地達到更好地集權的目的。”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中央與地方關系是一個充滿辯證法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⑤這把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高度集權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和條件逐漸消失,向地方分權成為中央與地方關系發展的總方向和總趨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央作為單一的調控中心無法統一協調日益繁多、層出不窮的社會事務,因此,必須不斷強化地方的作用,調動調控主體的創造性和能動性,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實現各項權力由中央向地方的分散和轉移,建立新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成為歷史的必然。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于改革中央高度集權體制,消除各項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1987年,鄧小平強調:“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內容。”中共十三大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確立擴大地方自主權的總原則是“凡是適宜下面辦的事情,都應由下面決定和執行。”⑥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改革的市場化趨向已明確,中央向地方下放權力的步伐加快,立法權也逐步下放到地方。1995年,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表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的講話指出:“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問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們國家大、人口多、情況復雜,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賦予地方必要權力,讓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靈活性,發揮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增強整個經濟的生機和活力”。
二、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
從理論上我國受到馬克思經典作家的影響,把計劃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從實踐上,我國受到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我國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自然成為合乎邏輯的選擇。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共產黨逐步擺脫這種觀念,形成新的認識。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副總編吉布尼時,首次對市場經濟從理論上作了闡述,他指出:“說市場經濟只限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十二大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思路。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新概念,不再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于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后來,又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⑦黨的十四大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這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實現的又一次重大突破。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表述不僅明確了未來全面改革的關鍵所在,更對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定調,表明黨對市場機制的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是市場與政府關系的一次重大理論突破。
三、從主體一元到主體多元的轉變
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構成了現代性的兩個維度,它們的結合掀開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大轉型,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邏輯,而且重塑了現代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關系,并最終演化出了法治政府、市場經濟、公民社會三元鼎立的現代國家治理結構。現代國家區別于傳統國家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其強大的權力滲透能力,“政治中心能夠領導、推動和批準在自己領土范圍內發生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根據自己制定的、靈活多變的命令管理整個國家。”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具有強大政治整合能力的現代國家的誕生。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絕對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控制機制的耦合,使國家權力空前膨脹,國家因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利維坦”和將權力觸角伸向社會生活各個角落全能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國家治理逐步告別非常規的運動式治理,轉入常規的制度化治理。政府職能的轉變,遵循的是與市場化改革相匹配的適應性調整的邏輯,因而歷次政府體制改革都有特定的經濟體制改革背景,計劃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逐漸讓位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國家中的每個公民也不再是完全依附于國家機器的零件,而成為具有獨立利益和自主意志的社會行為主體時,國家同他們的關系就不再是單純的命令服從關系,而是被注入了越來越多的平等契約的關系屬性。這就意味著國家再也無法直接通過發號施令,驅動社會組織和社會個體去實現國家的意志。現代社會是一個利益多元社會,國家治理不是政府一家“唱獨角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首先意味著在發揮政府治理主體作用的前提下,將政府的“他治”、市場主體的“自治”、社會組織的“互治”結合起來,進一步發揮市場主體和公民個體的治理職責,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共同實現良好的治理。
四、從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轉變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以各級黨組織和國家政權機構為核心,以各種群眾性組織為輔的組織形式,實現了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統一領導,初步形成全能主義國家治理結構。全能國家治理結構,抑制人類微觀個體在經濟活動中激發的活力,大鍋飯體制缺乏利益激勵機制,使社會成員缺乏生產積極性,整個社會在宏觀上幾乎陷入經濟的停滯,政治上搞“以階級斗爭為綱”,最終走向“”,整個國家付出沉重代價。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開始進入以促進經濟發展、保障效率優先為首要目標的重大轉型時期。國家逐步確立了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治理機制,強調了市場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自此,傳統的全能國家治理逐漸退,一種新形態的發展型國家治理逐漸形成。政府角色及其管理方式的現代轉型,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構的核心問題。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命題,并將國家“制度體系”建設提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可以辦的,應該由市場去辦;社會組織可以辦好的,交給社會組織去辦。只有市場和社會組織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才應插手,也就是要建成所謂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相對于無限政府、全能政府而言的,指政府的職能、權力、規模、行為都有一定限度,都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明確限制,需要公開接受社會監督與制約,并且有糾正其偏差的相應機制。有限政府強調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社會的自我管理,尊重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對自己不該管、管不了的不再干預,對自己應該管的進一步加強。有限政府有三個明顯的特點:(1)政府職能有限。我國屢次改革都以轉變職能為重點,正說明政府職能不是全能的、無限的,而是有限的。(2)政府權力有限。(3)政府規模有限。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政府的部分職能和權力也將逐步讓渡給社會,歸還給社會,政府規模理應逐漸縮小,“小政府,大社會”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趨勢。隨著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國家治理也會變得高效、廉價、務實。
五、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變
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是堅持“民本位”,還是“官本位”,即如何處理官與民的關系問題,決定著人心的向背,關系到執政集團的生死存亡。所謂“官本位”,就是以官為本,權力本位,它突出官權,忽視民權,以官為主,以民為仆,執政者按照本集團的價值觀念來評價、決定和操縱民眾的行為,而民眾只有服從的權利。“民本位”則是堅持執政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決不謀求個人或小集團的任何私利。“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的產物,中國自秦始皇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后,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等級森嚴的官僚政治體制,這種等級森嚴的官僚政治體制和絕對壟斷的權力就產生了并不斷強化著“官本位”意識。做官不僅可以光宗耀祖,聲名顯赫,而且“長期的官僚政治,給予了做官的人,準備做官的人,乃至從官場退出的人,以種種社會經濟的實利,或種種雖無明文確定,但卻十分實在的特權”。在中國封建社會,“民本位”始終是與“官本位”相伴而行的,此消彼長,但是“民本位”不僅沒有沖破“官本位”的藩籬,反而強化了“官本位”的地位。良好的國家治理,制度是關鍵,但治理者的素質也至關重要。改革開放后,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平等、公正等現代核心政治價值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位主義觀念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一文中,對官本位的傳統體制的特征、弊端、危害,作了極為深刻的剖析、揭露與批判。官本位其突出的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循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只有實現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變,才能真正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真正遏制腐敗的蔓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作者:吳德慧單位:許昌學院副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