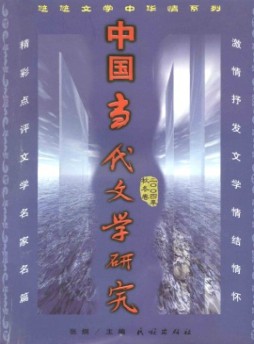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體驗(yàn)書寫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體驗(yàn)書寫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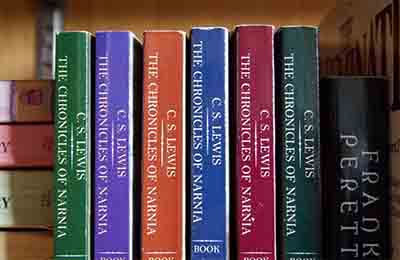
《長江學(xué)術(shù)雜志》2015年第七期
一、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和邊疆風(fēng)情:1949—1976年間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
聞捷的這種革命歷史敘事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比比皆是。碧野的散文《在香妃墓周圍》對照敘述了建國前維吾爾族人民的受壓迫和建國后的翻身得解放,尤其是維吾爾族婦女的翻身更受到熱烈歌頌。嚴(yán)辰的詩歌《織地毯歌》通過南疆和田維吾爾族織地毯工人在建國前和建國后的生活對比,歌頌了中國共產(chǎn)黨給邊疆人民帶來的翻天覆地的新變化。此外,還有嚴(yán)辰的詩歌《烙印——一個(gè)奴隸的傾訴》,張志民的詩歌《戈壁老漢》和《一條殘斷的鎖鏈》等都是寫新疆少數(shù)民族的奴隸翻身的,最終都要落實(shí)到:“誰撐起了奴隸們的腰桿?/親愛的共產(chǎn)黨和。”此類革命歷史敘述中,新疆少數(shù)民族無疑處于被解放、被拯救的弱者地位,他們能夠奉獻(xiàn)的只是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贊美和忠誠。建構(gòu)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文學(xué)策略之二就是高調(diào)宣揚(yáng)社會主義建設(shè)事業(yè)中的新人新事,新風(fēng)新貌,展示新政權(quán)領(lǐng)導(dǎo)下的美好新生活,從而贏得各族人民的想象性認(rèn)同。當(dāng)革命炮火的硝煙散去后,社會主義建設(shè)大潮風(fēng)起云涌,黨和政府乃至內(nèi)地的漢族人成為現(xiàn)代文明的推行者,成為現(xiàn)代性的傳播者,文明的火種傳播到新疆邊地。《復(fù)仇的火焰》中,沙爾拜就這樣對女友葉爾納描繪共產(chǎn)主義美妙遠(yuǎn)景:“啊!那時(shí)候多么好啊!/我們這兒建立起帳篷的市鎮(zhèn),/山溝里渦輪機(jī)隆隆地旋轉(zhuǎn),/每座帳篷都亮起電燈……//啊!那世界多么好啊!/共產(chǎn)主義就是人間的仙境;/哈薩克永遠(yuǎn)擺脫貧困和落后,/終日歌唱生命的青春!”當(dāng)然,必須明確的是,這美妙遠(yuǎn)景的提供者和實(shí)現(xiàn)者只能是黨和政府,因此真正需要認(rèn)同的是新的民族國家共同體。
還有艾青、碧野、郭小川等人也傾情于謳歌新疆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各條戰(zhàn)線上的沖天豪情,召喚著對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詩人艾青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最主要的就是歌頌新疆的軍墾戰(zhàn)士崇高的奉獻(xiàn)精神。他的詩歌《年輕的城》詠贊了農(nóng)墾城市石河子,詩人“透過這個(gè)城市/看見了新中國的成長”。碧野的長篇小說《陽光燦爛照天山》則展示了新疆兵團(tuán)屯墾邊疆、保衛(wèi)邊疆的昂揚(yáng)斗志。碧野的散文《雪路云程》、郭小川的詩歌《雪滿天山路》等都集中歌頌了天山公路的建設(shè)者。嚴(yán)辰的詩歌《金泉》歌頌了伊犁察布查爾草原的各族勞動者的辛勤奉獻(xiàn)和豐收喜悅;張志民的詩歌《哈薩克少女》、《墾區(qū)的夜》、《草原放映隊(duì)》等也是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新頌歌。這些頌歌營構(gòu)出一幅在黨和政府的領(lǐng)導(dǎo)下各族人民團(tuán)結(jié)奮進(jìn)、齊心協(xié)力、共同為美好新世界揮汗如雨、充滿歡歌笑語的動人圖景,似乎邊疆已經(jīng)脫胎換骨,再次中心化了。與革命歷史的新疆本土化、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新疆式推進(jìn)相比,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對絢麗多姿的邊疆風(fēng)情的描繪也是不遺余力。1963年上映的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之所以能夠在全國獲得極大的反響,那冰清玉潔的崇高雪山、明媚動人的高山草原、塔吉克族的民風(fēng)民情等就是重要因素。聞捷詩歌在1950年代能夠魅力四射,也與此有關(guān),用洪子誠先生的話說,“漢族敘述者對奇麗風(fēng)情和異族習(xí)俗的欣喜驚羨的視角,用柔和的牧歌筆調(diào)來處理頌歌的主題,對聚居于和碩草原、吐魯番盆地、博斯騰湖畔的少數(shù)民族勞動者的情感特征、表達(dá)方式的捕捉,是對讀者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像《天山牧歌》中那些優(yōu)美的抒情詩,無不呈現(xiàn)濃郁的新疆風(fēng)情,而長詩《復(fù)仇的火焰》對哈薩克族的游牧狩獵、婚俗民風(fēng)以及草原高山的奇麗風(fēng)景的展示也極具邊疆特色。當(dāng)然,更多的是像郭小川、嚴(yán)辰、李瑛、張志民等詩人,短期到訪新疆,被當(dāng)?shù)貪庥舻倪吔L(fēng)情迷醉。不過,對于這個(gè)時(shí)代的作家而言,邊疆風(fēng)情的體驗(yàn)書寫也必須返歸到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上來。
如所周知,此階段的文學(xué)受到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嚴(yán)密規(guī)訓(xùn)和有效控制,呈現(xiàn)出高度一體化、標(biāo)準(zhǔn)化的特征,因此當(dāng)時(shí)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也難逃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tài)的天羅地網(wǎng),只能出現(xiàn)高度模式化、雷同化的弊病。但縱然如此,新疆這塊大地的特色畢竟是難以輕抹的,那大漠戈壁、雪山草原畢竟不同于中原地區(qū)的千里沃野、村莊如織,那眾多馬背上的游牧民族畢竟迥異于幾千年來沉湎于農(nóng)耕文明的漢族,自由放縱、輕靈豪邁、瀟灑飄逸的精神氣質(zhì)還是給許多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帶來更為獨(dú)特的東西。像聞捷的《天山牧歌》對愛情的吟誦在1950年代幾乎就是新疆式的最后絕唱。而郭小川、張志民、嚴(yán)辰、李瑛等人在新疆大地上行走吟唱時(shí),似乎多了一份大漠般的浩蕩、綠洲般的驚喜、雪山般的超然。而碧野的《天山景物記》這樣的散文只有新疆才能孕育出來,那高山雪蓮、蘑菇圈、果子溝等還只是外在表象,難得的是流淌全篇的那種新疆式的明麗、新鮮和自由。當(dāng)然,此階段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也存在著鮮明的局限。當(dāng)漢族作家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動員下,以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為獨(dú)一宗旨書寫新疆體驗(yàn)時(shí),他們就在無意中遮蔽了新疆各民族的主體性,從而使得更為豐富復(fù)雜、具有生命景深的精神文化因素?zé)o法凸顯。而且無論在革命歷史的新疆本土化、還是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新疆式推進(jìn)中,當(dāng)代作家都只是把新疆各民族人民視為被拯救、被解放、被啟蒙、被灌輸?shù)膶ο蟆@缏劷菰谠姼琛敦浝伤蛠泶禾臁分兄v述貨郎給維吾爾人民送來畫像,于是“每個(gè)家庭都升起不落的太陽,/含笑注視維吾爾人,/維吾爾人遵循他手指的方向,/去迎接金光燦爛的早晨。”此種抒情無疑遮蔽了民族和人的主體性。此外,為了建構(gòu)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當(dāng)代作家?guī)缀跤幸夂鲆曅陆嗝褡宓默F(xiàn)實(shí),先入為主地把民族意識、宗教意識視為負(fù)面因素,急于破之而后快。像在長詩《復(fù)仇的火焰》中,聞捷把利用民族身份、宗教認(rèn)同來煽動叛亂的頭人忽斯?jié)M、阿爾布滿金塑造為十惡不赦的反面形象,而巴哈爾最終幡然悔悟,讓階級身份認(rèn)同超越于民族身份、宗教文化,才尋找到了出路。此種新疆體驗(yàn)書寫,自然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理由,但其中潛藏的問題也昭然若揭,值得警惕。而且,對邊疆風(fēng)情的描繪中,當(dāng)代作家更是有可能抽空新疆各民族的主體性,把邊地生活風(fēng)景化,從而阻礙了個(gè)體生命和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真實(shí)交流。
二、民間溫情的追尋和精神高地的構(gòu)筑:1980年代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
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時(shí)代熱潮無遠(yuǎn)弗屆,新疆雖地處偏遠(yuǎn),亦被裹挾其中。王蒙、張賢亮、高建群、楊牧、周濤、章德益、唐棟、李斌奎、張承志等人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構(gòu)筑了迥然相異于此前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風(fēng)景。他們已經(jīng)不再汲汲于營構(gòu)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了,那種走馬觀花式、頌歌式、外在化、風(fēng)景化也被超越了。他們有的長期在新疆底層社會生活過、磨煉過,對新疆多民族的民間生活已經(jīng)別有領(lǐng)悟,因此能夠?qū)懗黾雀挥猩畹滋N(yùn)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xué)佳作來,如王蒙;有的短期在新疆游走,但內(nèi)在天性和新疆的獨(dú)特靈魂構(gòu)成一種隱秘的和諧震蕩,從而能夠把新疆體驗(yàn)提升到詩意、神性的高度,如張承志;有的曾經(jīng)長久定居成長于新疆,已經(jīng)把新疆當(dāng)作故鄉(xiāng)一樣對待,因而立志發(fā)掘出新疆內(nèi)在的精神資源,如楊牧、周濤、章德益等。執(zhí)著地沉入廣袤的民間社會,發(fā)掘支撐生命的溫情,構(gòu)造出溫暖樸實(shí)的新疆形象,是王蒙、張賢亮、高建群等人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的根本追求。王蒙因受政治運(yùn)動的逼迫不得不避居新疆,從1963年到1979年長達(dá)16年,新疆已然成為他的第二故鄉(xiāng)。他曾反復(fù)以銘感于心的語氣談及新疆,并從馬鞍形起伏的個(gè)人命運(yùn)中來審視新疆體驗(yàn),把這種個(gè)人體驗(yàn)和民族國家的宏大命運(yùn)奇妙地縫合在一起。對于王蒙而言,新疆多民族的底層生活給他最重要的體驗(yàn)就是積蓄在民間的生命溫情,就是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摧毀不了的綿綿不絕的生命力量。
這種生命溫情、生命力量不但使他個(gè)人獲得救贖,而且必然會在民族國家重啟現(xiàn)代性的浩大工程時(shí)發(fā)揮出驚天動地的力量。王蒙在“在伊犁”系列短篇小說最喜歡敘述的就是那一個(gè)個(gè)雖遭國家暴力的百般挑釁、個(gè)人命運(yùn)的無端戲弄,但依然對生活不屈不撓、對生命尚存希望的維吾爾族底層人民。像《哦,穆罕默德•阿麥德》中的阿麥德雖然生活處境艱窘,屢受迫害和嘲弄,但依然娶妻生子,待人和善,妻子逃跑后還想著到內(nèi)地去漫游。《淡灰色的眼珠》中,無論阿麗亞還是馬爾克木匠,都是用情真摯,用心生活之人。至于《虛掩的土屋小院》中的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之間的惺惺相惜更是溫暖感人。還有短篇小說《歌神》、《溫暖》、《最后的“陶”》等都是用心捕捉著新疆民間社會的絲絲縷縷的生命溫情,彰顯著新疆人民的人性亮色。中篇小說《雜色》中的曹千里就從維吾爾族人民那里領(lǐng)悟了一種幽默而積極地對待人生的超脫態(tài)度。王蒙有意淡化極左政治對新疆各族人民的暴虐和摧殘,更有意淡化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差異,也不愿意把新疆生活單純地詩意化、風(fēng)景化,而是從高度實(shí)用理性化的人性視野來審視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死哀樂、日常生活。這樣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的確展現(xiàn)出了一個(gè)落難的漢族知識分子眼中的真實(shí)新疆。至于張賢亮、高建群等人的新疆體驗(yàn)也與王蒙頗為同調(diào)。張賢亮新疆體驗(yàn)書寫的小說代表作《肖爾布拉克》志在發(fā)掘縫合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罅隙的民間社會的生命溫情。而高建群的中篇小說《遙遠(yuǎn)的白房子》和《伊犁馬》無論是敘述遙遠(yuǎn)的新疆歷史,還是關(guān)注當(dāng)時(shí)新疆漢族戍邊軍人和哈薩克族少女的愛情波折,都筆調(diào)哀婉,風(fēng)流蘊(yùn)藉;不過,《遙遠(yuǎn)的白房子》更偏向于展示新疆游牧民族的浪漫血性,《伊犁馬》則偏向于展示新疆人民的多情重義。
應(yīng)和著改革開放大時(shí)代的要求,彰顯新疆大地的生命雄風(fēng)和開拓精神,建構(gòu)新時(shí)代的精神高地,是此階段新疆的新邊塞詩歌和軍旅小說的共同追求。1980年代新邊塞詩歌的崛起是當(dāng)時(shí)詩壇的一大熱點(diǎn),楊牧、周濤、章德益等人的詩歌頗為關(guān)注新疆的崇高雪山、蒼茫戈壁、疾馳駿馬、翱翔雄鷹等,從中提煉出粗獷彪悍、高曠超邁的精神姿態(tài),傾向于崇高之美、力之美,是難得的帶有新疆特征的黃鐘大呂之聲。楊牧在詩歌《我驕傲,我有遼遠(yuǎn)的地平線——寫給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準(zhǔn)噶爾》中寫道:“荒野的路呵,曾經(jīng)奪走我太多的年華,/我慶幸:也終于奪走了閉塞和淺見;/大漠的風(fēng)呵,曾經(jīng)吞噬太多的美好,/我自慰:也吞噬了我的怯懦和哀怨。/于是我愛上了開放和坦蕩,/于是我愛上了通達(dá)和深遠(yuǎn);/于是我更愛準(zhǔn)噶爾人的發(fā)達(dá)的胸肌,/——每一團(tuán)肌肉都是一座隆起的峰巒!”而周濤的詩歌《天山南北》則詠唱道:“她用暴雪,激勵我登攀的勇氣,/她用狂風(fēng),吹動我生命的帆桅。//戈壁紅柳,告訴我堅(jiān)韌而不卑微,/雪山勁松,教育我堅(jiān)強(qiáng)而不獻(xiàn)媚,/綠洲白楊,啟示我團(tuán)結(jié)而不孤傲,/冰峰雪蓮,誘導(dǎo)我純潔而不自美……”相對于聞捷、艾青、郭小川等人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而言,新邊塞詩派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無疑更富有主體性,更富有新疆獨(dú)有的地域特色。不過,他們的抒情主體還是被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規(guī)定好的集體本位的主體,因此其詩歌更多的是較為粗疏的理性敘說,缺乏更為細(xì)膩、關(guān)乎個(gè)人精神和靈魂的獨(dú)到發(fā)現(xiàn)。當(dāng)他們書寫新疆多民族的生活時(shí),他們往往也會把異民族加以外在化、風(fēng)景化。與新邊塞詩派一樣,李斌奎、唐棟等人的新疆軍旅小說也重在弘揚(yáng)那種敢于挑戰(zhàn)困難、富有開拓精神的新疆式的生命體驗(yàn)。李斌奎的長篇小說《啊,昆侖山》就反映了長期駐守新疆昆侖山的當(dāng)代軍人的生活、愛情、理想及追求,揭示了當(dāng)代邊防軍人崇高的人生觀和價(jià)值觀。其中,戍邊戰(zhàn)士向西行、黃沙等人的獻(xiàn)身舉動筑起了新時(shí)代的精神高峰。至于唐棟的短篇小說《兵車行》更是謳歌了戍守喀喇昆侖山兵站的當(dāng)代軍人的犧牲精神和崇高形象。
不過,無論是王蒙、張賢亮等人尋找新疆民間底層社會的生命溫情,還是新疆邊塞詩派、軍旅小說構(gòu)筑改革開放時(shí)代的精神高地,他們對新疆體驗(yàn)的書寫都還是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和引導(dǎo)之下進(jìn)行的,是對改革開放的現(xiàn)代性工程的呼應(yīng)和回答。新疆多民族的民族身份認(rèn)同、宗教文化認(rèn)同等核心問題都沒有進(jìn)入其視野之內(nèi),因此真正富有主體性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還是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由此可知,張承志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的確是一個(gè)極具魅力的文學(xué)異數(shù)。張承志在新疆考察生活過一段時(shí)間,對新疆情有獨(dú)鐘,他的《輝煌的波馬》、《夏臺之戀》、《美麗瞬間》、《九座宮殿》、《晚潮》、《白泉》、《大坂》、《頂峰》等小說都與新疆體驗(yàn)有關(guān)。他寫新疆的回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并不避諱其民族身份認(rèn)同,也不刻意回避其宗教信仰。像《輝煌的波馬》中,回族人碎爺逃避宗教迫害,帶著兒子碎娃子和厄魯特蒙古人巴僧阿爸及其兒子阿迪亞和諧共處于天山腳下的波馬,他們的生命在天山的優(yōu)美之中顯得如此純凈、美麗。《九座宮殿》則把新疆回族人追尋宗教信仰的艱難苦旅寫得那么感人肺腑。張承志在尋找自身的民族身份認(rèn)同、宗教文化認(rèn)同時(shí),也激活了其他民族的身份認(rèn)同、宗教文化認(rèn)同,以其自身明晰的主體性激活了他人的主體性。
即使是寫新疆的自然風(fēng)景,張承志也迥異于其他當(dāng)代作家。在《大坂》中,他這樣描繪天山的冰川,“大坂上的那條冰川藍(lán)得醉人。那千萬年積成的冰層水平地疊砌著,一層微白,一層淺綠,一層蔚藍(lán)。在強(qiáng)烈的紫外線照射下,冰川幻變出神奇的色彩,使這荒涼恐怖的莽蒼大山陡添了一份難測的情感。”短篇小說《美麗瞬間》中,張承志這樣描繪天山的草原:“從清晨起就一直高高逡巡的那支圣潔的樂曲,此時(shí)暴雨般傾瀉下來。天山藍(lán)郁的陰坡繃直了松枝,錚錚地?fù)u曳著奏出節(jié)拍。迎著金黃的陽光,眩目的綠草地仍在流淌漫延,光彩照人地誘惑著激昂和英勇。海拉提的黃驃馬卷著一連串黃黃的煙球,冬不拉曲子震耳欲聾。不可思議的瘋狂節(jié)奏打著大地的胸膛,前方一字?jǐn)[開愈逼愈近的迷蒙河谷。扶搖的霧靄顫抖著,終于模糊了更遠(yuǎn)的視野。那姑娘臨別時(shí)的一聲高喊像一個(gè)擲向天空的銀鈴,疾走涌落的音樂立即吞沒了搶跑了她。”此外還有《凝固火焰》中對吐魯番火焰山的神奇描繪。這種景物和碧野的《天山景物記》中那種被徹底馴服、宣示著優(yōu)美與富足的風(fēng)景大相徑庭,即使和新邊塞詩派筆下的粗獷彪悍的新疆風(fēng)景也大不相同。這是張承志對新疆的內(nèi)在詩意和神性的獨(dú)到發(fā)現(xiàn)。如果把王蒙和張承志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略加比較,就可以看出,王蒙是從漢族的實(shí)用理性傳統(tǒng)來審視新疆多民族的世俗生活的,而張承志則傾向于從信仰的超越性角度來觀照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內(nèi)核。在張承志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中,新疆大地不再是簡單的邊疆風(fēng)情的提供者,新疆各族人民也不再是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的忠誠對象,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文明也不再是不證自明的價(jià)值導(dǎo)向;他在新疆大地、新疆各民族的信仰里發(fā)現(xiàn)的詩意和神性拒絕著膚淺的風(fēng)景化眼光,抗拒著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質(zhì)疑著現(xiàn)代性的價(jià)值譜系。這無疑將為更多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提供新的精神導(dǎo)向標(biāo)。
三、詩意化和本土化的頡頏:1990年代到新世紀(jì)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
1990年代,現(xiàn)代化大潮更為兇猛地席卷全國,世俗化、實(shí)用主義、消費(fèi)文化等風(fēng)氣彌漫整個(gè)社會的各個(gè)角落,使得原本就務(wù)實(shí)的中華民族更為務(wù)實(shí),精神的天空更為低矮,心魂的羽翼更為稀薄。到了新世紀(jì),這種狀況根本沒有得到改善,現(xiàn)代性的幸福允諾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都落空了,我們在物質(zhì)產(chǎn)品的相對豐裕中體驗(yàn)著理想與精神的雙重失落,再加上整個(gè)社會階層日益固化,貧富差距日益突出,制度性的貪污腐敗污染著整個(gè)社會的空氣,和日益惡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日益潰敗的大自然,使得人心普遍極度喧囂浮躁。在這種語境中,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再次出現(xiàn)根本性的變異。無論是1990年代就在文壇上了產(chǎn)生極大影響的散文家周濤、劉亮程和詩人沈葦,還是到了新世紀(jì)獲得極大關(guān)注的小說家紅柯、溫亞軍、董立勃和散文家李娟,他們的新疆地域意識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他們有意識地張揚(yáng)新疆大地的詩意以對抗全國的世俗化浪潮,有意識到新疆大地去尋找新的生命精神去療救內(nèi)地漢族精神萎靡的沉疴宿疾,他們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在詩意化和本土化的兩個(gè)方向上都做出實(shí)質(zhì)性的突破。作為80年代新邊塞詩人之一的周濤雖然已經(jīng)滋生出獨(dú)特的生命意識,但整體看來還是更傾向于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媾和,更多的是對現(xiàn)代性的引頸翹望;因而在他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中,新疆謀求的乃是內(nèi)地、中心的首肯。但從80年代末轉(zhuǎn)入散文創(chuàng)作開始,到了90年代,周濤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開始出現(xiàn)了質(zhì)的飛躍。他開始細(xì)致地描繪新疆大地上的自然萬物、人情物事,并從中升騰出主動疏離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生命意識。《紅嘴鴉及其結(jié)局》中,周濤描繪鞏乃斯草原被捕捉到的紅嘴鴉居然不甘心當(dāng)俘虜和玩物活活氣死的壯烈;《鞏乃斯的馬》渲染了鞏乃斯草原馬的俊美和自由天性;《猛禽》謳歌了鷹的強(qiáng)悍與悲壯。從這些新疆自然生命身上,周濤表達(dá)的乃是他那種崇尚自由、離世避俗、富有孤高之美的生命意識,承接了魯迅對懦弱、缺乏血性的國民性的批判精神。在《二十四片犁鏵》和《一個(gè)牧人的姿態(tài)和幾種方式》中,周濤更是表達(dá)了對農(nóng)耕文明的鄙視,對游牧文明的贊賞。在內(nèi)地世俗化浪潮的倒逼下,周濤對新疆獨(dú)特的文化精神越來越自覺、自信,他曾說:“新疆是亞洲中心的一半。新疆是古西域的核心。
新疆是藍(lán)眼睛的伊蘭人的故地,是浪漫華麗的突厥語的歸宿。新疆是處處天險(xiǎn)中的條條道路。新疆是語言隔膜中的無言神交。虛偽庸俗敬新疆而遠(yuǎn)之,豪爽真誠進(jìn)新疆而復(fù)活。這就是新疆本質(zhì)中的一部分。而它的全部,是無法概括的。”因此,當(dāng)他面對所謂的中心、內(nèi)地時(shí),他已經(jīng)不再甘居人下,不再害怕無理的嘲弄和否定了,他極自覺地為新疆辯護(hù),在激烈的二元對立中把新疆詩意化,“當(dāng)北京景山的一棵相傳是崇禎自掛的歪脖子小樹前游人如織時(shí),和田碩大無朋的核桃樹王正帝王般張開它蒼邁郁綠的傘蓋;當(dāng)病入膏肓的一群招搖扭擺的所謂歌星在屏幕上展覽丑態(tài)與病態(tài)時(shí),喀什的泥墻瓦舍之間、月夜清白之地卻飄蕩著河流一樣渾厚、柔和的真正歌聲;當(dāng)欺騙成為常識、敲詐成為公理、金錢成為準(zhǔn)則、叛賣成為創(chuàng)造,一切的價(jià)值沉淪在洶涌的潮流之中時(shí),真誠、樸素、人性這類事物的最后棲息地也只能在邊陲的某些角落了。人性的理解和笑容,真誠樸素的禮貌和友誼,稀有金屬一般在綠洲的田園里閃閃發(fā)光、震撼心靈。”至此,新疆作為邊陲,已經(jīng)不再因遠(yuǎn)離政治、經(jīng)濟(jì)中心而羞愧,而是意識到了自身的本質(zhì)力量,并轉(zhuǎn)而作為價(jià)值圭臬衡量著內(nèi)地、中心的欠缺與失落。周濤說:“邊陲是永恒的。它的土地,它的人,總是在時(shí)髦的漩渦之外提供某種不同的存在。那就是美。”周濤終于和張承志走上同一條道路,不過周濤是立足人文精神基礎(chǔ)上的新疆審美,張承志則是立足于民族宗教基礎(chǔ)上的信仰追尋。與周濤的詩意化新疆體驗(yàn)書寫如出一轍,詩人沈葦從遙遠(yuǎn)的江南水鄉(xiāng)來到新疆,無疑也在追尋新疆的詩意和神性。沈葦詩歌在90年代詩壇上曾產(chǎn)生較大反響,他扎根新疆大地,對存在、時(shí)間、死亡、愛、故鄉(xiāng)等核心主題做出了較為深入的思考,又讓這些主題染上濃郁的新疆氣息。他的短詩《一個(gè)地區(qū)》曾廣為稱頌,“中亞的太陽。玫瑰。火/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藍(lán)/那人傍依著夢:一個(gè)深不可測的地區(qū)/鳥,一只,兩只,三只,飛過午后的睡眠”。
該短詩寫出了新疆的熱烈、高潔、孤迥之美,堪稱新疆靈魂的簡潔素描。在沈葦?shù)男陆w驗(yàn)書寫中,那種供膚淺游客消費(fèi)的邊地風(fēng)景、民族風(fēng)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新疆大地的深及靈魂的孤獨(dú)詠嘆,是對新疆大地萬般風(fēng)物的神性的耐心搜集,就像他說的,“我突然厭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販子。”沈葦能夠讓生命和新疆大地融為一體,再從中升騰出最個(gè)體化、最具有新疆特色的精神姿態(tài)。劉亮程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到了20世紀(jì)末期突然成就了一個(gè)傳奇,他憑借散文集《一個(gè)人的村莊》被譽(yù)為“20世紀(jì)最后一位散文家”、“鄉(xiāng)村哲學(xué)家”。他在散文集里極具詩意地描繪了北疆戈壁灘邊沿一個(gè)名叫黃沙梁的小村莊的外貌和靈魂。他眾生平等地對待所有動物,充分體諒一頭驢的生存境遇和脾性,和老鼠共享豐收的喜悅,與狗共同守護(hù)著村莊的靜謐,分享墻腳下螞蟻的智慧;他又能夠聽到野花的大笑,體驗(yàn)一株樹的渴望,和野地上的麥子一起沉醉于秋天。他在《村東頭的人和村西頭的人》這樣描寫陽光:“住在村東頭的人,被早晨的第一縷陽光照醒。這是一天的頭一茬陽光,鮮嫩、潔凈,充滿生機(jī)。做早飯的女人,收拾農(nóng)具的男人,沐浴在一片曙光中,這頓鮮美的‘陽光早餐’不是哪個(gè)地方的人都能隨意享受。陽光對于人的喂養(yǎng)就像草對于牲畜。光線的質(zhì)量直接決定著人的內(nèi)心及前途的光亮程度。而當(dāng)陽光漫過一個(gè)房頂又一個(gè)房頂?shù)竭_(dá)村西頭,光線中已沾染了太多的煙塵、人聲和雞鳴狗叫,變?yōu)槭浪椎臇|西。”這等樸實(shí)流麗又蘊(yùn)含生命哲理的文字實(shí)在沁人心脾。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亮程沒有停留在鄉(xiāng)村瑣事碎物的展示上,他能夠上升到哲理高度來領(lǐng)悟諸多事物。新疆大地的遼闊深邃賦予了劉亮程散文一種內(nèi)在的精神質(zhì)感。緊隨劉亮程而來的是李娟。李娟的書寫阿勒泰的系列散文《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請放聲歌唱》在近幾年文壇上相繼噴薄而出,奪人眼球,再次延續(xù)了劉亮程的散文路子,對新疆大地上的人與事做出純凈樸素的優(yōu)雅展示。她的散文彌漫著新疆游牧民族式的樂天知命、天真好奇又豁達(dá)超然的氣質(zhì)。在90年代以來直至新世紀(jì)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中,紅柯無疑占據(jù)至關(guān)重要的地位。10余年的新疆生活徹底解放了紅柯的想象力,更換了他的生命意識,反過來脫胎換骨的紅柯也成為新疆大地的一個(gè)抒情孔道,他以龐大瑰麗的小說世界把新疆精神提升到了純粹詩意和神性的美好境界。紅柯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具有非常鮮明的文明批判和國民性批判意味。在散文《浪跡北疆》中,紅柯曾說:“彌漫在戈壁沙漠上的絕不是荒涼,而是沉靜!這是腑臟最健康的狀態(tài),浮躁和喧囂這類雜音是摒除在外的。……我在黃土高原的渭河谷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當(dāng)松散的黃土和狹窄的谷地讓人感到窒息時(shí),我來到一瀉千里的礫石灘,我觸摸到大地最堅(jiān)硬的骨頭。我用這些骨頭做大梁,給生命構(gòu)筑大地上最寬敞、最清靜的家園。”他還說:“居于沙漠的草原人其心靈與軀體是一致的,靈魂是虔敬的。而居于沃野的漢人卻那么浮躁狂妄散亂,心靈荒涼而干旱。”由此可見,紅柯憧憬新疆、書寫新疆,與他反思內(nèi)地漢族的農(nóng)耕文明的局限性有關(guān);對于他而言,新疆才是生命的彼岸,代表著一種極其人性化、詩意的生活方式。紅柯在文壇上首先產(chǎn)生極大反響的是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他要到新疆尋找的就是馬仲英所表現(xiàn)的那種血性剛烈的生命精神。他說:“我當(dāng)時(shí)想寫西北地區(qū)很血性的東西。明清以后,西北人向往漢唐雄風(fēng),而回民做得好。他們?nèi)松伲幸环N壯烈的東西。我們這個(gè)民族近代以后幾乎是退化了。我想把那種血性又恢復(fù)起來。……我在馬仲英身上就是要寫那種原始的、本身的東西。對生命瞬間輝煌的渴望。對死的平淡看待和對生的極端重視。新疆有中原文化沒有的剛烈,有從古到今的知識分子文化漠視的東西。”因此,他筆下的馬仲英年紀(jì)輕輕揭竿而起,在戰(zhàn)場上出生入死,勇猛異常,信奉著“有滋有味活幾天,比活一百年強(qiáng)”的生命哲學(xué),最終騎馬躍入黑海不知所終。此外,像中篇小說《復(fù)活的瑪納斯》中的解放軍退伍團(tuán)長、《金色的阿爾泰》中的解放軍營長,長篇小說《大河》中的土匪托海等,都是像馬仲英一樣血性剛烈之人,支撐起新疆大地的雄性風(fēng)景線,也映照著甚至批判著內(nèi)地漢族人普遍存在的國民性的萎靡和怯弱。
從90年代以來到新世紀(jì),周濤、沈葦、劉亮程、李娟、紅柯、溫亞軍對新疆體驗(yàn)的書寫無疑都是立足新疆本土的,重在發(fā)掘出新疆大地的主體性,但他們都和內(nèi)地的漢文化、國家主流意識倡導(dǎo)的現(xiàn)代性有意識地建立起一種相互映照的關(guān)系。因此,他們重在發(fā)掘新疆體驗(yàn)中的異質(zhì)性,如詩意、神性、血性、溫情等。但董立勃在新世紀(jì)贏得較大反響的系列長篇小說,如《白麥》、《白豆》、《米香》等,在描繪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的歷史與生活時(shí),卻走上了另一條本土化之路。他筆下的那些人物都是建國后到新疆開辟新生活的漢族人,漢族文化已經(jīng)把他們塑造成形了,到了新疆,新的地域風(fēng)情、民族文化、精神信仰等似乎已經(jīng)對他們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了,他們的命運(yùn)主要受政治體制、個(gè)人性情、自然欲望等的影響。像《米香》中的米香、宋蘭、許明、老謝等人,都是地道的漢族人,沒有信仰,崇拜權(quán)力,精明勢利,凡事只考慮個(gè)人私利,但也富有生命韌性。他們把漢族文化較為完整地移植到了新疆,建構(gòu)出了新的家園。因此董立勃的這些小說和畢飛宇的《玉米》、《玉秀》等小說在精神氣質(zhì)、敘事質(zhì)地上都非常相似。其實(shí),董立勃的這種新疆體驗(yàn)書寫的傾向早在陸天明的新疆題材長篇小說《桑拿高地的太陽》、《泥日》中就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了。像《桑那高地的太陽》中的上海知青謝平的拼搏和精神毀滅,老爺子的專制和冷酷,把極左時(shí)代的政治變態(tài)、漢族文化較為丑陋的一面展示得淋漓盡致。如果新疆的地域風(fēng)情、民族文化等沒有辦法給漢族文化輸入一種異質(zhì)性的活力因素,那么新疆體驗(yàn)書寫無疑就喪失了獨(dú)立稱謂的必要性。那樣,也許是好事,也許是壞事。
四、結(jié)語
整體梳理了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的歷史后,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存在較為鮮明的內(nèi)在邏輯脈絡(luò)。首先是從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積極迎合到對其有限疏離。新中國剛建立之初,聞捷、碧野、郭小川、艾青、李季、張志民、李瑛等詩人、小說家到新疆工作、體驗(yàn)生活,幾乎都是負(fù)有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崇高使命的,就是要通過文學(xué)想象既讓內(nèi)地民眾把新疆視為民族國家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要讓新疆當(dāng)?shù)孛癖娮杂X獲得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性認(rèn)同。因此他們筆下的新疆人的少數(shù)民族身份會被中華民族、階級解放等宏大語詞遮蔽起來。到了1980年代,王蒙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雖然沒有那么急迫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宣教使命感,但他是要在新疆各族人民民間生活的脈脈溫情中去尋找彌合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裂縫的強(qiáng)力膠水,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認(rèn)同依然是穩(wěn)定的。《雜色》中的曹千里不愿甘居邊疆,渴望再次躍馬奔騰,表達(dá)的無非就是作者試圖獲得國家權(quán)力承認(rèn)的身份焦慮感而已。至于新邊塞詩派、軍旅小說都是渴望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首肯和揄揚(yáng)的。但到了張承志之后,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忽然出現(xiàn)質(zhì)的變化,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有限疏離幾乎成了他們不約而同的立場選擇。張承志有意尋找新疆少數(shù)民族不同的民族身份認(rèn)同,拒絕“中華民族”等宏大詞語的粗疏空虛。“半個(gè)胡兒”的周濤、紅柯等人都超越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民族限制和宗教管控,志在展示新疆大地的不羈靈魂。其次,從對現(xiàn)代性的無比憧憬到對其適度拒斥。就像聞捷的長詩《復(fù)仇的火焰》中的哈薩克族戰(zhàn)士沙爾拜對草原上的現(xiàn)代機(jī)器文明的憧憬所表現(xiàn)的那樣,聞捷、郭小川、碧野等人不言自明地把新疆視為被現(xiàn)代文明遺忘的角落,如今隨著建國后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高潮掀起,未來的幸福美滿指日可待。王蒙等人為遭受極左政治運(yùn)動干擾的新疆現(xiàn)代化建設(shè)而扼腕嘆息,希望從民間社會中尋覓新的力量盡快重啟現(xiàn)代性的宏大工程。新邊塞詩派、軍旅小說等都試圖從新疆大地中尋覓剛烈的生命精神、開拓精神參與到現(xiàn)代化大潮中去。但張承志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卻質(zhì)疑了這種唯現(xiàn)代文明馬首是瞻的盲目趨勢,他筆下的人物逆潮流而動,顯示出了較明晰的反現(xiàn)代特質(zhì)。周濤對邊陲的發(fā)現(xiàn)、紅柯對邊疆精神的提倡,也是對張承志精神的延續(xù)。至于劉亮程、李娟等人那么專心致志地描繪被現(xiàn)代文明大潮遺忘的小村莊、阿爾泰邊地,而不是向往都市的中心、市場的繁華,本身就具有濃郁的反現(xiàn)代意味。再次,從對新疆的風(fēng)景化觀照到對其內(nèi)在主體性的發(fā)現(xiàn)。這是與前兩個(gè)脈絡(luò)構(gòu)成呼應(yīng)的。聞捷、郭小川、碧野、張志民等人對新疆體驗(yàn)的書寫大都停留在風(fēng)景化的粗淺層次上。他們被新疆大地奇異的自然美景、多姿多彩的民族風(fēng)情所陶醉,但因被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裹挾,尚未能發(fā)現(xiàn)新疆內(nèi)在的主體性。王蒙倒是一度能夠和新疆少數(shù)民族打成一片,但受制于高度實(shí)用理性化的本民族文化,他也只能發(fā)現(xiàn)本民族文化可以接受的新疆特質(zhì),而發(fā)現(xiàn)不了超越于本民族文化的新疆更獨(dú)特的生命精神。新邊塞詩派是較早書寫新疆內(nèi)在的主體性的,但這種主體性還是被制約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許可的范圍內(nèi)。直到張承志,新疆大地獨(dú)特的生命精神、多民族宗教文化的超越之維等等顯示內(nèi)在主體性的東西,才首次被當(dāng)代作家以極具詩意、叛逆的方式張揚(yáng)出來。張承志甚至認(rèn)為新疆這個(gè)名稱都暗示著中心對邊疆的傲慢,從而有可能否定其主體性。周濤、紅柯、沈葦、劉亮程等人都已經(jīng)擺脫了對新疆的風(fēng)景化觀照建立了對新疆的內(nèi)在主體性書寫的不同模式。理解了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這種內(nèi)在歷史與邏輯脈絡(luò),我們才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文學(xué)史價(jià)值乃至對當(dāng)前文化的建設(shè)意義。最關(guān)鍵的是,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為當(dāng)代文學(xué)乃至當(dāng)代中國社會輸送了迥異于內(nèi)地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異質(zhì)文化經(jīng)驗(yàn)。新疆體驗(yàn)書寫的文化意義和內(nèi)地不同的地域文學(xué)的文化意義迥然不同,因?yàn)橄駜?nèi)地的荊楚文化、湖湘文化、江南士風(fēng)、三秦文化乃至東北黑土地文化基本上都是漢族文化的地方性演繹。但新疆體驗(yàn)書寫處理的乃是多民族聚居的、自然風(fēng)物迥然相異、宗教信仰截然不同乃至生活方式都差距甚大的異質(zhì)文化經(jīng)驗(yàn)。而這種異質(zhì)文化經(jīng)驗(yàn)相對而言更具有自由品格,更多姿多彩,更富有血性和強(qiáng)悍的生命意志,因此恰恰能夠彌補(bǔ)內(nèi)地漢族文化的欠缺。正如紅柯在《文學(xué)的邊疆精神》所說的,“中國人最有血性最健康的時(shí)候總是彌漫著一種古樸的大地意識,亞洲那些大江大河,那些名貴的高原群山就是我們豪邁的肢體與血管,奔騰著卓越的想象與夢想。邊疆一直是我們古老文明的搖籃。中國文學(xué)有一種偉大的邊疆精神與傳統(tǒng)。這是近百年來我們所忽略的。我們總是把目光盯著所謂發(fā)達(dá)國家,卻忽略自己家園里的另一種高貴而美好的東西。”程光煒也曾指出:“歷史時(shí)間的鐘擺,也許終將在內(nèi)地社會形態(tài)高度成熟化、同質(zhì)化并日益喪失文學(xué)的新鮮性和持續(xù)發(fā)展動力后,而倒向新疆、西藏和內(nèi)蒙古等少數(shù)族裔文化和文學(xué)的坐標(biāo)上來。”的確,當(dāng)代作家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尤其是張承志、周濤、紅柯、沈葦、劉亮程等人的新疆體驗(yàn)書寫,復(fù)活的就是紅柯所說的大地意識,偉大的邊疆精神傳統(tǒng),亦是程光煒?biāo)f的少數(shù)族裔異質(zhì)文化。這種獨(dú)特的邊疆精神、異質(zhì)文化經(jīng)驗(yàn)對于當(dāng)代中國人的精神重建必將產(chǎn)生持續(xù)而重大的影響。
作者:汪樹東 單位:武漢大學(xué) 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