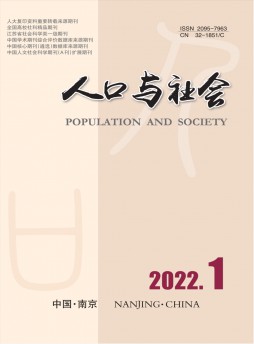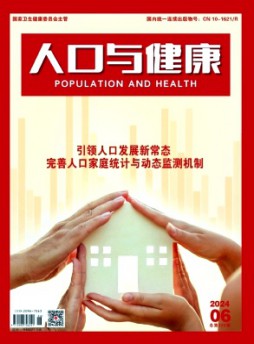人口年齡結構與城鎮居民消費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口年齡結構與城鎮居民消費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數據說明與統計描述
(一)數據說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ageneralsocialsurvey,縮寫為CGSS)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從2003年開始每年一次,調查范圍覆蓋了全國大多數省區,對于整個中國而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調查內容涉及個人及家庭的豐富信息,是不可多得的開放式微觀數據資料。本文采用的是CGSS第一期的數據資料,包含了2003、2005、2006和2008年的調查數據。在使用前對數據進行了以下篩選處理:(1)只保留四次調查都覆蓋的省份,共有27個省份(不含青海省、海南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港澳臺);(2)只針對城鎮家庭居民的數據資料進行研究;(3)將被訪問者的年齡限定在18—70歲之間。由于研究的主要變量是家庭的基本生活費支出,為了控制家庭規模的影響,必須把家庭支出換算成家庭人均值,考慮到所使用的數據情況,本文采用OECD平方根規模指數進行換算:將家庭基本生活費支出除以家庭人口規模的平方根即可得到家庭人均基本生活費支出,本文接下來的分析均以此指標來代替家庭消費支出。中國各地區間價格水平存在差異,同一消費水平在不同地區的實際購買力是不同的,如果不考慮價格的影響,則不能真實反映消費差距,因此,采用各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所有的消費指標進行了以2006年為基期的調整。經過數據的篩選和處理,包括去掉消費數據中1%最高和最低的異常值后,最終的樣本只保留了家庭收入和消費為正,并且被訪問者年齡以及其他關鍵變量均不缺失的15248個樣本。
(二)數據的基本統計描述表1報告了被調查的家庭的基本人口特征。從表1中可以發現,樣本中被訪問者的平均年齡在逐漸增加,由2003年的42.49歲增加到了2008年的44歲。教育年限①*也呈增加的趨勢,反映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城鎮居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鎮居民的家庭規模有縮小的趨勢,家庭的平均人口由3.32減少到了2008年的2.18,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城鎮居民生育意愿降低的現象,符合中國生育率降低的現實。表2提供了各調查年份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及消費差距的變動情況,從中可以發現,中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呈明顯的遞增趨勢,反映出中國城鎮居民分享到了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顯著地提高了消費水平。在表2中計算了多個常用的衡量差距的指標,如對數標準差、變異系數、基尼系數、泰爾指數等②**。各個衡量差距的指標變化規律是基本一致的,總體表現出上升的態勢(除了2006年有小幅下降),這說明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消費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從表1和表2提供的基本數據中,我們可以粗略地推斷:2003年到2008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口年齡結構呈老化的趨勢,而且消費差距也趨于擴大。若將所有觀測值的消費支出和年齡分布繪制出全樣本的年齡—消費曲線(如圖1),則會發現,消費支出近似呈現出“U”型分布,在18歲到26歲左右,居民消費支出處于最高位,此后逐漸下降;到了38歲左右又開始緩慢上升。消費支出的這種特征可能和中國特殊的人口政策有關,在樣本觀察期內,18—26歲的城鎮年輕居民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的主要支出都花在他們身上,他們處于消費曲線的高位不足為奇;26歲以后,多數年輕人都脫離了父母獨自生活,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收入并不足以支撐較高的消費,所以消費有下降的趨勢;38歲以后基本進入賺取更高收入的黃金時期,消費又緩慢的回升。然而,圖1的做法是將所有個體進行無差異對待,忽略了個體之間客觀存在的代際差異(不同年份出生在相同的年齡段,其消費水平是有差異的),這無疑遺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估計結果并不可靠。對此,本文接下來將運用組群分析方法來測度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變動及其來源的年齡效應與組群效應。
二、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分解
(一)組群分析方法在微觀調查中,對某一特定個體的終生進行固定追蹤是很難實現的,所以往往采用樣本輪換的做法,每一輪的調查樣本都會產生變動,這樣導致了無法獲得真正的面板數據。但是,如果按照某種屬性(如年齡、民族、職業等)將各期的調查樣本分成不同的組群(Cohort),在各個樣本期內,選擇各組群相關變量的均值,則可以構造出以組群為單位的面板數據,這種分析方法就叫組群分析方法(周紹杰,2009),根據組群來構造的面板數據稱為偽面板數據(PseudoPanleData)。偽面板數據允許各個調查期的樣本不同,其重點關注的是組群(如同一年代出生的人,職業相同的人)的統計特征,通過組群的各種統計量(均值、方差等)的發展變化,來揭示總體某一變量的分布特征。盡管偽面板數據不是真正的面板數據,但偽面板數據使用的是組群的統計量,減少了個體奇異值的干擾,從而降低了測量誤差,另一方面,由于不需要每個調查期追蹤固定的樣本,這使得樣本流失的問題不存在。雖然偽面板數據可以提供某一組群在某一年齡階段的經濟行為,但在實證分析中必須對組群間的系統性差異———即組群效應(CohortEffect)進行控制,否則組群效應將會混合到所估計的年齡曲線中,造成估計的偏誤。因此,在進行組群分析時,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在估計家庭消費支出的年齡曲線時把組群效應的影響控制住。控制組群效應的方法是把要分析的變量(在本文中為家庭的消費支出)分解為組群效應、年齡效應(AgeEffect)和年份效應(YearEffect)(Deaton,1997)。其中,組群效應反映了不同時代出生的群體,由于成長環境的差異等導致的代際的系統性差異(例如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群體,其消費行為和80年代出生的群體必然不同),年齡效應則反映了消費支出的生命周期特點。在實際計量分析過程中,各虛擬變量設定如下:組群虛擬變量以出生最早的組群作為參照組;年齡虛擬變量以最年輕的年齡組作為參照組;T-2個年代虛擬變量根據式(4)轉換。
(二)組群構造與消費支出的分解構造偽面板數據要根據觀測個體的出生年份來劃分組群,Deaton(1997)建議在構造偽面板數據時需要在組群個數和每個組群內樣本個數之間進行權衡,其原則是:組群內部差異盡可能小,而組群之間差異盡可能大。本文研究的樣本中,調查對象出生年份在1933—1990年之間,由于調查的年份只有四年,我們每10年定義一個出生組,得到6個組群。表3為“組群—年份”構成的偽面板數據在每個單元的樣本數。本文的樣本年齡分布在18—70歲之間,在四個年度的調查中,年齡最大的個體出生于1933年,在2003年為70歲,最年輕的個體出生于1990年,在2008年為18歲,共構造了58個組群(出生于1933—1990年),53個年齡組(18—70歲),在分解出三種效應(年齡、年份、組群)的過程中,共有57個組群虛擬變量、52個年齡虛擬變量以及轉化的2個年份的虛擬變量。圖2是各組群消費支出的年齡曲線,年輕組群的年齡—消費曲線位于左邊,年老組群的年齡—消費曲線位于右邊。年齡—消費曲線有兩個方面的特征:第一,除了最年老的組群(出生年份為1933—1941年),其余各組群的消費支出均表現為隨年齡增加而增長的趨勢。各組群的年齡—消費曲線并沒有呈現出“駝峰”形狀,而在對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中,如對美國(Attanasioetal.,1999)、英國(Attanasio&Browning,1995)、臺灣(Deaton&Paxson,2000)的研究結果均顯示年齡—消費曲線具有明顯的“駝峰”特征,中國的年齡—消費曲線具有其特殊模式。第二,在相同的年齡水平上,年輕組群的年齡—消費曲線全部位于年老組群的上方,這表明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提高了年輕一代的消費水平。另外,相鄰組群的年齡—消費曲線并未相連接,不同組群的消費支出分布在不同的年齡曲線上,因此,不能僅僅連接各個組群的年齡—消費曲線來形成一個總體的年齡—消費曲線,必須在控制組群間的差異的基礎上來估計一個總體的年齡—消費曲線。圖3繪制了年齡效應和組群效應。可以看到:第一,年齡效應幾乎保持著線性增長的態勢,只有在60歲以后的退休年齡才停止上升,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這與美國(Attanasioetal.,1999)和臺灣(Deaton&Paxson,2000)的“倒U”型特征也是迥異的。從平均意義來看,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年齡效應增長率約為5.96%。第二,組群效應曲線也基本呈線性增長的趨勢,組群效應的增長率約為3.33%,這一結果表明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給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帶來了更多的上升空間。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組群間的消費支出差異十分明顯,年輕組群的消費水平明顯高于年老組群,因此,在目前老齡化日趨嚴重的背景下,政府應該通過加快完善中國養老體制、進行收入的再分配調整,提高年老群體的財富水平,促進全社會的消費增長,提高居民的整體福利水平。
三、中國城鎮居民消費差距與消費差距變動的分解
(一)消費差距的分解為了便于對總體的消費差距進行分解,我們參照Deaton&Paxson(1994)、Ohtake&Satio(1998)及Caietal(2010)等人的做法,選取對數方差來衡量消費的差距。由圖4的年齡—消費差異曲線可以發現,幾乎在每個組群內,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差距都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大,這表明了消費支出存在著顯著的組內不平等。其中,Varlnyjk表示可以被分為j個組群和k個年齡組的總體人群的對數消費方差;chortm表示組群虛擬變量,當m=j時為1,否則為0;agen是年齡虛擬變量,當n=k時為1,否則為0;αm和βn則分別為我們要估計的消費差距的組群效應和年齡效應。圖5顯示了消費差距的年齡效應βn,從中可以看出,消費差距雖然隨年齡的變化而波動,但其基本趨勢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上升。這說明,在某一組群內(即出生在同一時代的個體內部),隨著年齡的增長,該組人的消費差距是逐漸擴大的,這暗示著同一時代出生的群體進入老年階段后消費差距會更大,那么在中國養老保險體系尚未完善的環境下,個人如何合理配置其有限的財富,平滑其一生的消費則是個體必須面臨的現實問題。表4是組群效應αm。結果顯示,各個組群的估計系數都為正數,而且統計上均顯著。由于我們的參照組是出生于1933—1941年之間的群體,全部為正的估計系數說明出生于1933—1941年之間的一代人,其消費差距是最小的,之后隨著出生年代的推移,組群效應也越來越大,從出生年代為1942—1951年的0.06增加到出生年代為1981—1990年的0.186,增加了兩倍有余。這個特征也容易理解:出生年代較早的一批人,其收入來源有限,接觸到的消費市場品種也較為單一,他們的消費差距必然不會太大;而出生年代較晚的一批人,收入來源的多樣化、消費品市場的極大豐富都為他們產生較大的消費差距提供了條件。這里,消費差距與消費支出的組群效應均表現出相同的規律,即組群效應隨著出生年代的推移而增大。根據前文的分析可得到中國城鎮居民年齡與消費支出的一般規律:年輕一代的消費水平要高于年老一代,年輕一代的消費差距也大于年老一代,在同一代人內部,隨著年齡的增長,消費差距是不斷擴大的。但僅根據這個規律我們并不能發現中國的老齡化進程是否對居民消費差距的變動產生了影響,本文接下來將對消費差距的變動進行分解,以考察人口老齡化在消費差距變動中的作用。
(二)消費差距變動的分解基于Ohtake&Satio(1998)、曲兆鵬和趙忠(2008)的方法,我們把中國城鎮居民消費差距從2003到2008年的變動進行分解,把消費差距的變動分解為“人口效應”(即老齡化效應)、“組間效應”和“組內效應”。具體做法如下:令sit為每個年齡的樣本在總樣本中的比重;σ2it為控制了出生組之后,每個年齡樣本的消費對數方差;Xit為每個年齡樣本的消費對數均值;i=18,19,…70;t為調查的年份。根據方差的定義和設定的上述變量,我們把消費對數方差變形,分解成三個部分。從表5中可以有如下發現:第一,消費差距的變動在各個時間區間內都為正,且變動量逐漸增加,這反映了在樣本區間內,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差距的確是擴大了,而且消費差距的擴大有惡化的趨勢。第二,出生組內的消費差距是總體消費差距變動的主要原因,其作用強度有增加的趨勢,而與組內效應相比,組間效應很小,這說明了中國城鎮居民在2003—2008年間消費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同一出生組內老年人和年輕人消費差距的拉大,這與圖5中控制了組群效應后消費差距隨著年齡增加而擴大的年齡—消費曲線相對應。第三,各個時期人口效應分解的結果都表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差距的影響都不容忽視,這一發現與曲兆鵬和趙忠(2008)不同,他們對中國農村的研究表明老齡化對不平等的影響非常微小。而本文的研究發現人口老齡化對城鎮居民消費差距存在著顯著的影響,而且影響作用有增強的趨勢,這暗示著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消費差距的影響在中國城鄉間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機制,值得更深入研究。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組群分析方法,利用CGSS2003—2008年調查數據,從微觀層面剖析了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人口年齡特征:(1)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年齡效應和組群效應均呈遞增趨勢,年齡效應的增長率高于組群效應的增長率。(2)消費差距的年齡效應雖有波動,但也呈增長趨勢,消費差距的組群效應則始終保持增長。(3)老齡化和組內效應對消費差距變動的貢獻明顯。前兩個特征意味著,中國城鎮居民年輕一代的消費水平要高于年老一代,年輕一代的消費差距也大于年老一代,在同一代人內部,消費差距隨著年紀的增長而擴大。后一特征則說明人口老齡化使社會面臨著更沉重的消費差距擴大壓力。對此,我們應當從以下幾方面來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并防止消費差距的過度擴大:第一,加快完善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醫療等方面,提高老年人的消費信心,釋放老年群體的消費能力。第二,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提升人力資本質量是提高消費水平的關鍵,而降低教育不平等是縮小組群內部消費差距的長效路徑。第三,必須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深保持足夠的重視,老齡化不僅不利于居民整體消費水平的提高,而且會擴大消費差距,造成社會福利的不平,中國政府應圍繞減緩老齡化、增加消費的生力軍等方面,審時度勢地調整相關政策,以達到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
作者:陳曉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