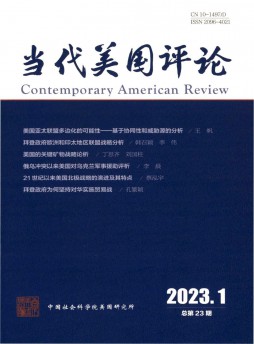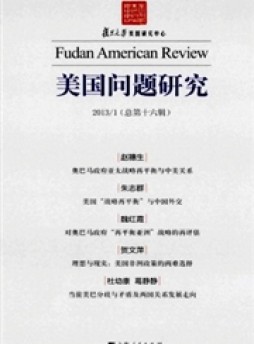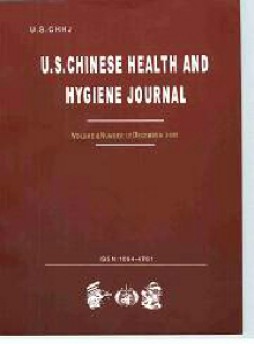美國(guó)收入分配政策稅收及社會(huì)保障政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美國(guó)收入分配政策稅收及社會(huì)保障政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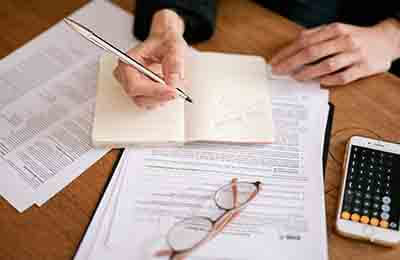
一、統(tǒng)競(jìng)選期間,布什許諾會(huì)通過(guò)制定“兒童減免”來(lái)推動(dòng)其“親家庭”式的稅收改革。最終,這一動(dòng)議作為對(duì)EITC的極大補(bǔ)充而被實(shí)施。分析表明,在支持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方面,增加EITC比提高最低工資更有效率。提高最低工資已經(jīng)擴(kuò)展到那些有配偶和子女需要撫養(yǎng)的工人,但他們并不一定來(lái)自低收入家庭;而且,提高最低工資對(duì)就業(yè)也存在負(fù)面影響,而EITC則更具有針對(duì)性。1990年的法案通過(guò)之后,EITC率對(duì)低收入納稅人的補(bǔ)償已經(jīng)超過(guò)了他們所繳納的收入稅或社會(huì)保障稅。在這之前,社會(huì)保障稅率為工資的15.3%,而EITC最多相當(dāng)于工資的15%。因此總的來(lái)看,這一里程碑式的變化很清楚地表明EITC已經(jīng)是一種支出額,而不是減稅。
1.克林頓時(shí)期。克林頓贊成提高最低工資標(biāo)準(zhǔn)以實(shí)現(xiàn)勞有所得,彌補(bǔ)過(guò)去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實(shí)際最低工資的下降。1995年克林頓總統(tǒng)提議提高最低工資標(biāo)準(zhǔn)(并沒有指明數(shù)額)。
全國(guó)最低小時(shí)工資于1996年10月1日從4.25美元提高到4.75美元,1997年9月1日提高到5.15美元。許多商業(yè)性稅收抵免被附在了最低工資法案的后面,并被正式稱為《1996年小企業(yè)就業(yè)保護(hù)法》。有關(guān)的證據(jù)表明1996年和1997年提高最低工資達(dá)到了支持者們所期望的效果:在不嚴(yán)重影響就業(yè)增長(zhǎng)的同時(shí),提高了低收入勞動(dòng)者的工資。最低工資的提高對(duì)處于收入分配末端的人群的影響并不小,他們的實(shí)際工資在經(jīng)歷了多年的衰退之后,隨著最低工資提高而增長(zhǎng)。
工作福利開發(fā)脫貧原則是克林頓政府社會(huì)福利政策的最大特點(diǎn)。克林頓曾說(shuō)“:我們將結(jié)束我們所知的福利”“,那些工作的人不應(yīng)該處于貧困狀態(tài)”“,能工作的任何人都不應(yīng)該永遠(yuǎn)依賴福利生存”。[2]1994年克林頓政府提出了一項(xiàng)福利改革法案,要求福利接受者在享受福利的同時(shí)立即參加培訓(xùn)或?qū)ふ夜ぷ鳈C(jī)會(huì),并對(duì)現(xiàn)金資助設(shè)定了兩年的時(shí)間限制,但是某些活動(dòng)可以不受此限制。兩年后,福利接受者被要求參加工作。
如果他們找不到工作,那么政府將提供一份有資助的工作。各州被賦予了更大的靈活性,但是福利仍然是政府的特定資助計(jì)劃,這表明所有有資格享受福利的人都有獲得資助的保證。1996年福利法案在經(jīng)濟(jì)擴(kuò)張最強(qiáng)勁的時(shí)期得到實(shí)施,成為美國(guó)歷史上最成功的服務(wù)于窮人的社會(huì)政策之一,明顯提高了單親母親家庭的勞動(dòng)參與率和家庭收入。克林頓政府還出臺(tái)了各種支持低收入貧困工作家庭的聯(lián)邦和州福利計(jì)劃,其中包括食品券、醫(yī)療補(bǔ)助計(jì)劃、兒童照料、兒童稅收抵免和勞動(dòng)所得稅抵免。另一個(gè)令1996年福利改革受歡迎的因素是工作資助體制。
大約從70年代開始,國(guó)會(huì)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計(jì)劃為有工作的家庭提供福利。初始的動(dòng)機(jī)和絕大多數(shù)計(jì)劃得到擴(kuò)張也許可以更多地歸因?yàn)閮H僅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而不是提供工作激勵(lì)的愿望。而克林頓政府要著手創(chuàng)建的是一個(gè)基于工作而不是基于依賴社會(huì)的新社會(huì)契約———通過(guò)獎(jiǎng)勵(lì)工作和要求工作來(lái)擴(kuò)大機(jī)會(huì),同時(shí)要求承擔(dān)責(zé)任作為回報(bào)的契約。克林頓政府想提供正確的激勵(lì)措施和價(jià)值:使每一份工作的薪酬都要高于福利,但同時(shí)要求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參加工作。工作是最有效率的,它為社會(huì)和反貧困政策提供了最經(jīng)得起考驗(yàn)的基礎(chǔ)。
看似難以解決的預(yù)算赤字問題讓位于大量的預(yù)算盈余,這使美國(guó)的財(cái)政狀況在90年代以出人意料的逆轉(zhuǎn)而聞名。克林頓總統(tǒng)想把加強(qiáng)社會(huì)保障作為第二屆任期的首要目標(biāo)之一,提出了指導(dǎo)社會(huì)保障改革的五項(xiàng)原則:
(1)21世紀(jì)加強(qiáng)和保護(hù)社會(huì)保障;
(2)維持普遍性和公平性;
(3)為人們提供可以依賴的受益金;
(4)為低收入和殘疾受益人保留經(jīng)濟(jì)保障;
(5)維持財(cái)政約束。
克林頓總統(tǒng)通過(guò)以下幾項(xiàng)行動(dòng)提供了出色的服務(wù):警示美國(guó)公眾人口老齡化必然會(huì)導(dǎo)致長(zhǎng)期的社會(huì)保障資金問題;在不提高工資稅稅率的情況下確立“首先挽救社會(huì)保障”的目標(biāo);提出股票投資在實(shí)現(xiàn)該目標(biāo)中的作用。克林頓政府通過(guò)保留預(yù)算盈余來(lái)幫助解決特定用途的應(yīng)支出項(xiàng)目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因?yàn)樾〔际舱ㄟ^(guò)了一個(gè)大規(guī)模的消費(fèi)導(dǎo)向型減稅計(jì)劃,在不到六個(gè)月的時(shí)間里就消耗了大部分盈余。從長(zhǎng)期財(cái)政不平衡的規(guī)模以及可被用以解決該問題的預(yù)算盈余的規(guī)模來(lái)看,美國(guó)人民失去了一個(gè)預(yù)籌未來(lái)退休金和聯(lián)邦醫(yī)療保險(xiǎn)受益金的大好機(jī)會(huì)。
2.小布什時(shí)期。
布什的第一個(gè)任期內(nèi),1981年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guò)的對(duì)稅率的大幅度削減再次上演,成為他的國(guó)內(nèi)政策的主導(dǎo)。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財(cái)政部大臣保羅·奧尼爾(PaulO’Neil)l指出,像他和美聯(lián)儲(chǔ)主席艾倫·格林斯潘那樣關(guān)心預(yù)算的人都在爭(zhēng)論中失敗了。格林斯潘指出如果不能保證解決債務(wù)目標(biāo),那么“減稅就是一種不負(fù)責(zé)任的財(cái)政政策”。2001年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與稅收減負(fù)調(diào)停法》減少了所有收入水平上的納稅人的平均稅率,邊際稅率下降幅度約為62%。位于中下收入階層的納稅人的最低稅率從15%下降到10%。很多位于該收入水平的工人們也發(fā)現(xiàn),他們每多掙一美元,他們的EITC也隨之下降21美分。一般來(lái)說(shuō),稅率的降低比其他的減稅方法更為有效,降低稅率能夠?yàn)橄嗤杖氲募{稅人帶來(lái)更為平等的待遇。與1981年的減稅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建議對(duì)低收入階層的減稅幅度要大大高于高收入階層。但是,從廣義預(yù)算的角度來(lái)看,在帶來(lái)更多再分配的問題上,減稅幾乎不太可能是累進(jìn)性的。
例如,設(shè)想削減社會(huì)保障稅,在減稅之后窮人的境況會(huì)更糟,因?yàn)樗麄冏罱K在政府支出上失去的好處要大于在減稅中得到的好處。削減福利的措施減少了再分配的凈值。2001年累進(jìn)性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之一是如何幫助那些位于收入底層的人,在2001年讓他們分享到收益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guò)支出。小布什總統(tǒng)建議把對(duì)納稅人的兒童抵免從5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但最終的議案規(guī)定這一抵免將分階段在收入位于10000美元以上的人身上實(shí)施,而不論他們是否納稅。預(yù)算將可償還的抵免部分(EITC和兒童抵免)看作是支出。簡(jiǎn)言之,2001年反對(duì)累進(jìn)性的分配戰(zhàn)爭(zhēng)無(wú)法僅在稅收體系之內(nèi)完成。有效稅率的下降對(duì)位于收入底層第30%等級(jí)之上的納稅人來(lái)說(shuō)是非常明顯的。在那之下,稅率已經(jīng)為負(fù)(考慮到EITC和兒童抵免),稅率的下降幅度略低。
近年來(lái)低收入階層稅收減負(fù)有了明顯增長(zhǎng),超過(guò)1/3的家庭現(xiàn)在不用支付凈收入稅。對(duì)于位于低收入水平部分的那一半人來(lái)說(shuō),產(chǎn)生影響最大的是兒童抵免。
2001年立法的兩個(gè)變化既緩解了也增強(qiáng)了高收入納稅者的法定收入稅率的降低。首先,2001年法案大大增加了受可選擇性最小稅收(AMT)支配的納稅人的數(shù)目。其次,2001年立法加強(qiáng)了高收入階層的稅率降低趨勢(shì)。減稅影響主要集中在最高的收入階層,這比包括里根在內(nèi)的以前的減稅措施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如果這一影響被計(jì)算在分配表之中,那么一半稅收減少都來(lái)自于最高收入階層。
2003年小布什政府開始對(duì)醫(yī)療保障體系進(jìn)行改革。當(dāng)年通過(guò)了一項(xiàng)法案,建立藥品保險(xiǎn)并將其納入醫(yī)療保險(xiǎn)體系之內(nèi)。這一法案在10年之內(nèi)的花費(fèi)預(yù)計(jì)將達(dá)到3950億美元,第二個(gè)10年的花費(fèi)接近10000億美元。根據(jù)這一法案的規(guī)定,從2007年開始,高收入者將不得不支付一項(xiàng)新的建立在收入基礎(chǔ)上的保險(xiǎn)費(fèi)。這意味著把很多高收入的老年人推向私人保險(xiǎn)市場(chǎng)。還有一個(gè)問題也同時(shí)出現(xiàn):身體健康的人會(huì)不會(huì)選擇不加入醫(yī)保體系?
更有爭(zhēng)議的是一個(gè)新的健康儲(chǔ)蓄賬戶(HSA),這個(gè)賬戶與醫(yī)保幾乎毫無(wú)關(guān)系。納稅人或雇員們被允許在賬戶中存入應(yīng)稅收入中的可扣除量。這些消費(fèi)者也可以購(gòu)買一項(xiàng)災(zāi)難性健康保險(xiǎn)。現(xiàn)在或?qū)?lái),賬戶中的錢都可以免稅提取出來(lái)以支付保險(xiǎn)范圍之外的其他健康費(fèi)用。
二、美國(guó)收入分配政策的效果分析
1.稅收政策的分配效應(yīng)分析。
在美國(guó),聯(lián)邦個(gè)人收入稅長(zhǎng)期以來(lái)被看作收入再分配的一種主要工具。學(xué)者在評(píng)估美國(guó)聯(lián)邦個(gè)人收入稅的再分配功能時(shí)認(rèn)為,即使考慮到聯(lián)邦收入稅法的變化對(duì)稅前收入所具有的誘導(dǎo)效應(yīng),1980~1990期間個(gè)人收入稅結(jié)構(gòu)在使稅后收入均等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愈益減弱;某一特定的稅法所產(chǎn)生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效應(yīng)受到稅前收入分配的影響,因而也受到實(shí)施該法律的年份的具體情況的影響。表1中的基尼系數(shù)表明自20世紀(jì)80年代早期以來(lái),聯(lián)邦個(gè)人收入稅結(jié)構(gòu)在使稅后收入均等化方面的效應(yīng)逐漸減弱。從1984年到1994年,稅前的基尼系數(shù)非常接近。1995年的稅前基尼系數(shù)有了顯著增加,這表明了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公認(rèn)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從表2可知聯(lián)邦個(gè)人稅收一直都具有再分配的效應(yīng),因?yàn)槎惡蠡嵯禂?shù)小于稅前基尼系數(shù)。但是,數(shù)據(jù)也表明自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以來(lái),這一效應(yīng)就在逐漸下降。這一效應(yīng)的下降主要是源于稅率的變化。同樣的稅收政策在不同的時(shí)點(diǎn)實(shí)施不會(huì)取得同樣的分配效果,因?yàn)闈撛诘亩惽笆杖敕峙鋾?huì)影響到稅收改革所能達(dá)到的再分配數(shù)量。換句話說(shuō),稅前收入分配本身的不均等性擴(kuò)大,是個(gè)人收入稅制的均等化效應(yīng)被削弱的一個(gè)主要原因。
社會(huì)保障與收入分配和經(jīng)濟(jì)保障息息相關(guān)。經(jīng)濟(jì)保障是我們的整體福利的一部分,它是個(gè)人確信自己對(duì)現(xiàn)在和將來(lái)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滿足的一種幸福感。獲得收入是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保障的關(guān)鍵。相反,沒有經(jīng)濟(jì)保障是指基本需要的缺乏,它表現(xiàn)為收入的不足與不確定性以及額外支出。造成沒有經(jīng)濟(jì)保障的主要原因來(lái)自家庭經(jīng)濟(jì)支柱人物的早逝、年老、疾病、失業(yè)、低于一般標(biāo)準(zhǔn)的工資收入、通貨膨脹、自然災(zāi)害和其他個(gè)人因素等等。社會(huì)保障項(xiàng)目為人們提供現(xiàn)金支付或服務(wù),以部分或全部地彌補(bǔ)由上述情況造成的收入損失。市場(chǎng)化、社會(huì)化社會(huì)保障發(fā)展的內(nèi)在傾向性導(dǎo)致美國(guó)社會(huì)保障項(xiàng)目呈現(xiàn)多層次的特點(diǎn)。
一些項(xiàng)目根據(jù)保險(xiǎn)政策來(lái)實(shí)施,要求收益人交納一定數(shù)額的“保險(xiǎn)金”,如老年人、幸存者和傷殘人保險(xiǎn)(OASDI)、失業(yè)保險(xiǎn)(UI)、醫(yī)療照顧(MEDICARE);另一些項(xiàng)目,則按照公共援助的方式來(lái)實(shí)施,以需求和收入檢驗(yàn)為基礎(chǔ),而且不要交納作為享受援助資格的“使用費(fèi)”,但要求受益人的收入水平在某一特定的數(shù)值之下,如撫養(yǎng)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補(bǔ)充保障收入(SSI)、醫(yī)療補(bǔ)助(MEDICAID)等等。結(jié)構(gòu)方面的另一種表現(xiàn)是收益形式。一些項(xiàng)目直接提供現(xiàn)金資助,如老年人、幸存者和傷殘人保險(xiǎn)(OASDI)、失業(yè)保險(xiǎn)(UI)、撫養(yǎng)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和補(bǔ)充保障收入(SSI)等等;而另一些項(xiàng)目則是在滿足一定要求的情況下直接提供實(shí)物性援助,如醫(yī)療補(bǔ)助、食品補(bǔ)助和住房補(bǔ)助等方面。以上各式各樣的社會(huì)保障項(xiàng)目在不同領(lǐng)域發(fā)揮了保障弱勢(shì)群體的功能。
失業(yè)、老年為重點(diǎn)到著力解決醫(yī)療保險(xiǎn)和醫(yī)療補(bǔ)助,以及以低收入年輕母親和撫養(yǎng)未成年子女為重點(diǎn)的家庭福利,從單純性救濟(jì)福利趨向工作福利。
社會(huì)保障政策的實(shí)施過(guò)程,實(shí)際上是對(duì)國(guó)民收入進(jìn)行再分配的過(guò)程,但是它不可能實(shí)現(xiàn)“收入均等化”,也不可能真正體現(xiàn)“全民福利”。美國(guó)社會(huì)保障的受惠是不平衡的,美國(guó)的社會(huì)保障制度是自由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國(guó)家的典型。
美國(guó)雖然實(shí)行對(duì)低收入和貧困家庭的福利補(bǔ)貼,同時(shí)又在稅收政策、退休政策等方面實(shí)行對(duì)高收入者有利的傾斜。據(jù)有關(guān)統(tǒng)計(jì)顯示,收入在10萬(wàn)美元以上的家庭占應(yīng)納稅家庭的3.9%,這些家庭在全部獲得補(bǔ)助家庭中所占的比例為4.6%;至于保健開支和保健賦稅優(yōu)惠的分配也是有利于10萬(wàn)美元以上收入家庭的,他們占美國(guó)家庭的3.9%,而賦稅優(yōu)惠則占4.3%,20萬(wàn)美元以上家庭占美國(guó)家庭的1.1%,賦稅優(yōu)惠則占3.8%。工人所得的福利金額是十分有限的,一般只占原工資的1/3左右;通過(guò)稅收得來(lái)的社會(huì)保險(xiǎn)基金,沒有全部用于居民的社會(huì)保險(xiǎn)開支。1948~1997年美國(guó)勞動(dòng)者實(shí)際收入(含名義工資加社會(huì)保障收入)的比重從9.4%增加到30.7%;同期剩余價(jià)值率從236.7%增加到280.9%;而勞動(dòng)者的實(shí)際收入占國(guó)民收入的比重則從29.7%減少到26.3%。事實(shí)上,社會(huì)保障制度只能調(diào)整豐裕階層、中產(chǎn)階層、低收入和貧困階層間的關(guān)系,緩和貧困現(xiàn)象,而不能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社會(huì)存在的貧困。
新自由主義主張?jiān)诮鉀Q貧困問題上發(fā)揮私人的作用。他們還認(rèn)為,美國(guó)社會(huì)福利正處于結(jié)構(gòu)性變化之中,公司方面已經(jīng)在家庭托兒、醫(yī)院管理、健康維持組織、兒童照顧和家庭照顧等領(lǐng)域進(jìn)行嘗試,這些預(yù)示著美國(guó)社會(huì)保障制度進(jìn)入了公司福利的新階段。
3.美國(guó)經(jīng)濟(jì)政策分配效應(yīng)分析。
分配是否公平并不是美國(guó)政府制定經(jīng)濟(jì)政策的考慮標(biāo)準(zhǔ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通貨膨脹、預(yù)算赤字和貿(mào)易逆差往往是他們考慮經(jīng)濟(jì)政策的出發(fā)點(diǎn)。影響美國(guó)稅收政策的首要因素是預(yù)算目標(biāo)而不是分配目標(biāo)。不過(guò),這些經(jīng)濟(jì)政策不可避免地會(huì)對(duì)社會(huì)分配格局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稅收政策、社會(huì)保障政策和社會(huì)福利政策是對(duì)收入分配最直接的影響因素。20世紀(jì)7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分配所發(fā)生的實(shí)際變化對(duì)人民生活的影響已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政府在這方面所采取的任何政策調(diào)節(jié)行動(dòng)。
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支出更多貨幣的辦法來(lái)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但一旦采用以貨幣資助窮人的辦法去追求公平,那么其政策的出發(fā)點(diǎn)就只剩下慷慨大方四個(gè)字了。而且,慷慨政策的運(yùn)用也決非易事。EITC是旨在幫助處于貧困線在崗工人的提案,是美國(guó)經(jīng)濟(jì)政策中少有的、能被稱為嚴(yán)格意義上的“收入分配政策”之一。它能夠增加低收入階層的工資,但對(duì)不從事工作的窮人卻毫不同情。收入分配問題只是在政府曾對(duì)其采取過(guò)認(rèn)真對(duì)策這一點(diǎn)上才可將其理解為政策問題。
特摩斯·斯密丁(TimothyM.Smeeding)通過(guò)實(shí)證分析得出結(jié)論:1979年至2002年在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國(guó)家中,美國(guó)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最高,而且美國(guó)政府政策與社會(huì)支出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是最小的。他進(jìn)一步指出這樣的區(qū)別不能解釋為人口統(tǒng)計(jì)方面的原因(如單親家庭、移民和老年化等),而應(yīng)該歸結(jié)為美國(guó)的制度以及缺乏為低收入工人家庭作出支出性努力。勞動(dòng)市場(chǎng)的制度安排,特別是集體談判、工資設(shè)定以及最低工資等對(duì)于決定國(guó)家間工資收入不均等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很明顯,工資分配上的區(qū)別對(duì)于家庭收入不平等有非常大的影響,因?yàn)楣べY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70%,工資不平等是由政府轉(zhuǎn)移支付政策所引起的。與其他發(fā)達(dá)國(guó)家相比,美國(guó)的再分配力度最小。大量非熟練工人的存在和安全網(wǎng)的不完備是導(dǎo)致這一結(jié)果的兩個(gè)重要原因。美國(guó)的社會(huì)價(jià)值觀和制度與其他國(guó)家不同,對(duì)市場(chǎng)體系也更為信仰。美國(guó)之所以有高于別國(guó)的不平等和貧困率,是因?yàn)槊绹?guó)選擇更多的不平等和貧困。
摘要:本文認(rèn)為,分配目標(biāo)并不是決定美國(guó)經(jīng)濟(jì)政策的首要因素,但這些經(jīng)濟(jì)政策不可避免地會(huì)對(duì)社會(huì)分配格局產(chǎn)生影響。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美國(guó)的稅收政策和社會(huì)保障政策對(duì)收入分配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從嚴(yán)格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收入分配問題只是在政府曾對(duì)其采取過(guò)認(rèn)真對(duì)策這一點(diǎn)上,才可將其理解為政策問題。
關(guān)鍵詞:收入分配;稅收政策;社會(huì)保障政策
參考文獻(xiàn):
[1]C.EugeneSteuerle.ContemporaryU.S.TaxPolicy[M].Washington,D.C.:TheUr-banInstitutionPress,2004:160.
[2]杰弗里·法蘭克爾,彼得·奧薩格.美國(guó)90年代的經(jīng)濟(jì)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