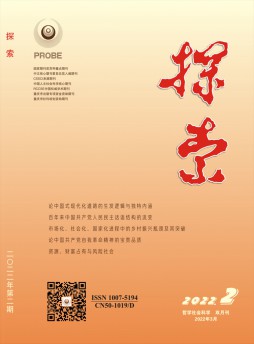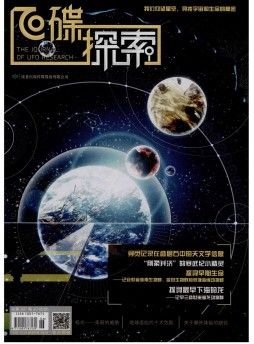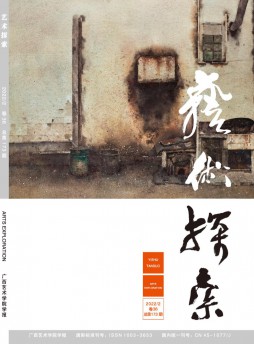探索餐飲業發展對農村經濟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探索餐飲業發展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西餐業的繁榮
19世紀50~60年代上海開設的西餐館主要是為了滿足外僑需要的,但也有少數華人去消費的,葛元熙曾描述:“外國菜館為西人宴會之所開設……華人間亦往食”[5](卷二)。民國時期上海外僑規模大,構成復雜。上海是近代中國外僑規模最大、最集中的城市,1891年有外僑4956人,1911年30292人,1930年增加到59285人[2](P317),1934年上海各區外僑總人數達到73504人。[1](P35)上海外僑來源國籍廣,1870-1930年僅公共租界的外國僑民就來自近40個國家[1](P28-29),1910-1930年法國租界的僑民是來自50個國家。[1](P32-33)外僑人數多、收入高和構成多元化是西餐業在上海發展的基礎,如意大利菜、荷蘭菜、日本菜館、法國菜館等都得以發展。1934年《上海指南》列出外國式的主要有大華飯店、華懋飯店、派利飯店、滄州飯店、匯中飯店、沙利文飯店、雪園、卡利飯店,這些飯店純粹外國式,是為滿足外僑需要的。民國時期西餐業的繁榮主要表現為中式西餐業的空前發展。所謂中國式西餐,即“雖然名謂西菜,除掉了幾道是依據歐美法烹飪以外,一大半都是脫胎于中國菜館里面。滋味的濃淡,饌肴的配合,都根據中國菜法燒的。”[9]中式西餐業主要受當時上海飲食崇洋消費觀念發展的影響,在外僑示范等因素影響下,19世紀70~80年代以吃西餐為時髦、為高貴的風氣在上海已經形成,那個時代的王廷鼎、王錫麒、姚覲元等日記均有記錄。1888年《申報》也曾報道,“山珍海錯非不鮮肥,而必欲以番菜為適口。”[10]而純粹外國式西餐所煮之菜,“類多生硬,與華人口味不甚相適”,為滿足華人崇洋飲食的需要,中式西餐業在上海快速發展起來。1880年開設的一品香是上海創辦最早、最著名的華人西餐館,此后華人西餐館紛紛開設,如普天香(1880年)、同香樓(1881年)、一家春(1883年)、海天春(1885年)、同然春(1887年)[11],到1899年四馬路西餐館林立,因許多西餐館都以“春”字為名,時人稱之為“無邊春色”。[12]清末隨著上海崇洋觀念在飲食領域的擴張,西餐業快速發展。[13]如孫寶聈出身名門世家,1898年日記內在外宴會記錄17次,其中15次為西餐。[14](P163-299)清末上海西餐業已形成一定規模,1901年《環球社圖畫日報》記載:“環福州路一帶之大餐館,多至數十家,局面之浩大,一品香、一枝香、旅泰等為最,而烹調精美,則一家春、嶺南樓可首屈一指焉,各省人士至滬者,往往不喜中國菜而喜大餐。故各大菜館之生意皆非常興盛,抑中抬西,亦吾人好尚變遷之一端也。”[15](P7)民國時期上海“風行請大餐”[16](P9),西餐業空前發展,1930年上海僅公共租界就有洋菜館155家[8](衛生,P18)。魯迅就常吃西餐,和朋友們也常選擇外國餐館聚會,如1928年9月13日應李志云及小峰之邀往皇宮西餐設晚餐,同座約卅人;再如1929年4月30日,朋友邀飲于大中華飯店,9月17日朋友為他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1932年9月15日到俄國飯店午餐,12月28日到日本飯館食河豚[17]。民國時期在飲食崇洋消費觀念的影響下,西式茶室、咖啡館、飲冰室等西式餐飲業也在上海發展起來,如1934年《上海指南》記錄:咖啡館都趨向“歐化”,清潔而精美,除外灘匯中,南京路沙利文,早上有咖啡市面,其余多在北四川路一帶,為中國人所開設,以女子為招待,自天潼路北,虬江路南,不下十余家,所售不限咖啡一項,亦有西菜、西點等。飲冰室也頗發達,所售有刨冰、汽水、冰淇淋、果子露、冷飲品等,著名的有南京路之冠生園、惠通、福祿壽,而滬西曹家渡一帶,又有幾家露天飲冰室,富紳豪客往往趨之。[4](P137-138)
(二)小型餐飲業以及餐飲業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
民國時期上海不僅規模比較大的飯店、酒店得以發展,而且為滿足低收入群體在外飲食需要或家庭對某些種類食品的需要,小飯館、臨時以及流動性飲食類商業快速發展起來,與之相適應與餐飲業相關的商業、工業在上海迅速發展起來。首先,小餐館、面館、大餅店等飲食類商業店鋪林立。上海是近代中國工商業發展的中心,低收入群體隊伍龐大,產業工人是民國時期低收入階層的主體,其他還包括人力車夫、碼頭工人等,1920年上海產業工人和交通運輸業工人總數已達30萬人,1937年超過100萬人。[18](101)這一群體為上海小餐館、臨時或流動性飲食商業發展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空間。1927上海市僅衛生局核發的飲食店執照就分為飯店、面館、點心店、茶館、粥店、茶食店、大餅店、糕團店、熱酒店、熟食店、冷食店等10多類,各類飲食店1220家,1930年增加到8387家。[8](衛生,P17)飲食店的繁榮不僅增加了政府稅收,提供就業崗位,還推動了相關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如促進了專業菜場和水果攤、水果店等的發展,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菜場就有18個、水果店及水果攤261家,1930年僅公共租界就有面包房96個[8](衛生,P18)。其次,餐飲業對機制面粉、汽水、啤酒等消費量的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相關工業的發展。在上海各類餐飲業、飲食類工商業和家庭對機制面粉等需求不斷擴大的推動下,飲食類工業快速發展。以面粉業為例,19世紀后期在面粉需求擴大的影響下,一批民族資本家于開始投資面粉業,到1932年上海有民族資本面粉廠14家,每年實需小麥14483000擔,每年生產面粉能力36936000包,實產面粉30055000包[8](工業,P21)。而食品類工業的發展又帶動了相關商業的發展。以制冰業為例,1934年有茂昌、新茂昌、上海、大華、永新、東方等15家制冰公司,每日出冰331噸。上海機制冰的銷路以粵菜館、冷食鋪、影戲院、兵營、住戶為主,消費者不直接向制冰公司購買,另由冰販從中販賣,由各冰販向制冰公司購入,再行銷售。這使一批專門販賣機制冰的商號興起,上海1933年販冰商號共有45家。[19](P33-35)再如上海居民對洋酒的喜愛促進了洋酒生產和洋酒商業的發展,1937年上海有著名外國商行兩家,專營洋酒進口,其他附帶兼營洋酒之洋行,統計不下十余家。[20](P14)
二、上海餐飲業發展對農村經濟變遷的影響
上海餐飲業發展對農村經濟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主要體現在種植業、農村家庭收入結構變化和養殖業的發展等方面。
(一)促進了上海市農村種植業結構的變化
民國時期上海人口規模超過三百萬,餐飲業、食品類工商業和家庭對糧食、蔬菜、水果等消費需求的變化,推動了上海市農村種植業結構發生巨變,突出表現為蔬果類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上海開埠前農村主要種植糧食和棉花等,開埠后為滿足城區居民對蔬菜、水果等需求,不少農田改種蔬菜、瓜果等。1901年海關報告記載:“中國人很快對外國水果和蔬菜有了愛好。一個頗有規模的、以供應市場為目的的菜園行業已經興起。這種形式正在廣泛地被采用,特別在上海近郊。”[2](P158)農作物種植結構的變化距離上海市愈近表現愈顯著,如為滿足西餐對洋蔥、土豆的需要,民國時期上海附近農村種植者越來越多,民國時期《真如志》記載:“有改植洋蔥頭者,為西餐之主要食物,銷售洋莊,獲利亦溥。”[21](卷三《實業志》,農業)“馬鈴薯,俗稱洋芋。近邑中植者,蓋自爪哇傳來,佐西餐之肉食,……吳淞江、蒲匯塘兩岸間,種植甚富。”[22](卷八,物產)民國時期上海市陸行等八區農作物產值中糧食已不占主導地位,有些區蔬菜產值已超過糧食(見表1)。1933年漕涇區蔬果類占農作物產值的51.3%,稻麥僅占農作物總產值的8.8%;再如真如區蔬果類占農作物產值的34.5%,稻麥占農作物總產值的14.9%;顓橋區蔬果類占農作物產值的19.4%,稻麥占農作物總產值的11%。從上海市陸行等八區各類農作物產值百分比可以看出,因上海餐飲業、飲食類工商業和居民對蔬菜水果需求的增加,農村種植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二)促進了上海市及鄰近省份養殖業的發展
首先,促進了家畜養殖業的發展。上海各類餐飲業和飲食類工商業以及家庭對豬、牛、羊等肉品消費需求的增加,推動了家畜養殖業的發展。以陸行八區為例,陸行區家畜等占總收入的22.4%,漕涇區占總收入的17.5%。對豬牛羊等肉品消費需求的增加,還促進了屠宰業的發展,1930年上海僅公共租界就有屠宰場6個。其次,促進了上海及其近鄰省份家禽養殖業的發展。20世紀20年代上海每年雞鴨所耗費達二百萬元以上,雞鴨行就有十九家,主要來自運河沿海之實應、高郵、邵伯,揚州長江沿岸之泰縣、口岸、靖江、如皋、南通、海門、崇明,浦江沿岸之川沙、南匯、奉賢,滬寧沿路之南京、常州、蘇州及安徽省境之蕪湖等地。[23](P16-17)再次促進了水產養殖業的發展。上海市對魚等水產品需求的增加,促進了上海市及鄰近省份水產養殖業的發展。上海居民以及大小餐館對水產類食品的需求量很大,如1933年上海市消費各種冰鮮魚類674495擔,價值6963379元。[24](P22)1934年6月上海市各種國產海味進口135.55擔,價值10867.38元,來自青島、威海衛、煙臺、江北等地。[25](PP11-12)最后促進了奶牛養殖業的發展。民國時期上海餅干廠、面包房、餐館以及家庭等對牛奶消費需求的增加推動了奶牛養殖業的發展。1929年上海已有奶牛養殖廠51家,其中開設時間在1年以上10年之內28家,10年以上20年之內12家,20年以上者11家。[26](P5)奶牛養殖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售奶業等發展,如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有牛乳房29個。[8](衛生,P18)
(三)促進了農民家庭收入結構的變化
民國時期上海餐飲業發展推動了面粉、汽水、啤酒、碾米等食品工業的發展,1932年上海碾米廠53家,釀造類工廠54家,榨油業工廠13家,罐頭食品業工廠38家[8](工業,P1-2)。大多數食品加工業的原料是農產品,不僅促進了農產品商品率的提升,而且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上海餐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了機會,也促進農村家庭收入結構發生變化。20世紀30年代初,家畜、家禽、水產副產物和副業已成為上海市陸行八區農家收入的支柱,殷行副業占農戶收入的43.5%,漕涇副業占農戶收入的40.7%(見表2)。總之,民國時期上海餐飲業的繁榮以及在其帶動下飲食類工商業的發展、居民消費觀念的變化等使上海對蔬菜水果、肉蛋奶等消費需求增加,促進了上海市以及鄰近省份農村經濟結構轉型,帶動了農村經濟變遷。
三、結論
餐飲業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能豐富和方便居民飲食生活,而且對拓寬就業渠道、增加稅收、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商業發展等均有重要影響。民國時期上海是遠東特大城市,餐飲業的空前發展對上海以及鄰近省份農村經濟變遷產生了深遠影響,是拉動上海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其影響下不僅居民消費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還形成了一條產業鏈,無數家庭靠其謀生,此外還產生了很多其他經濟社會影響,如對天津、漢口、杭州等其他城市餐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變遷都有重要影響,“上海好似近水樓臺,世界的新潮流,總比內地先受一刻兒,因此上海便成為內地企慕傾向的目標,凡是上海有一件什么較為新奇的事,內地總要尤而效之。”
作者:郭立珍單位:洛陽師范學院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