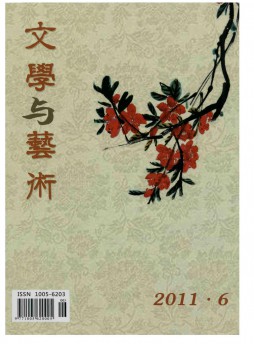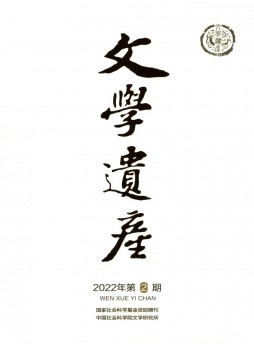《學衡》的文學翻譯與文化抉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學衡》的文學翻譯與文化抉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年第三期
《學衡》(CriticalReview)于1922年1月創刊于南京東南大學①。圍繞這一刊物,一個以梅光迪、吳宓、胡先骕、柳詒徵、湯用彤等為代表,以與五四新文化-文學陣營針鋒相對的價值立場為鮮明標識的學術文化群體“學衡派”得以形成。長期以來,在深受主流意識形態操控的現代文學界,這一群體因與陳獨秀、胡適、魯迅、茅盾等新文化運動主將論戰的身份,學術文化成就始終未獲得應有的評價。直至上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及后啟蒙時代的到來,學界才在反思中愈益注意到了“學衡派”在匡正五四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偏頗、守護傳統文化價值等方面的制衡作用,以樂黛云先生發表于1989年的《重估<學衡>———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1]為先導,對其在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學術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開始了重新審視。然而,研究者們大都關注“學衡派”在“昌明國粹”②方面的建樹,對其在西方文學譯介與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依然未有足夠的重視。曾被魯迅在雜文中譏為“假古董”的“學衡派”學者,并非抱殘守缺的舊派文人,而是大都具有西洋留學背景,接受了以哈佛大學為代表的美國名校系統的專業訓練的精英知識分子。其同人刊物《學衡》將“融化新知”與“昌明國粹”并重,雜志創刊號卷首插圖將孔子與蘇格拉底雙賢同列,即為象征。由于《學衡》的主要發起人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等均師從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歐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教授,梅光迪與吳宓先后獲得文學博士與碩士學位,胡先骕亦有深厚的中西文學素養,因此,文學譯介在《學衡》的西學譯介中占據著十分突出的位置。“學衡派”與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或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因而并非體現為對西學的接納與否,而在于擇取對象的差異背后迥異的文化立場。他們的文化抉擇,清晰地體現出“學衡派”同人與新文化-文學運動主將迥異的文化建設理想。在不再以魯迅之是非為是非、學術日益走向多元與民主的時代,有必要對《學衡》鮮明的翻譯特色與思想理路加以分析,以準確理解“學衡派”作為文化異端出現于上世紀20-30年代的獨特歷史價值。
一、以文化-文學進化論為對立面的古典趣味
“學衡派”西學譯介的首要特色,是高度重視西方文化與文學的源頭,即希臘羅馬時代的美學思想與文學成就的譯介,體現出鮮明的古典趣味。《學衡》關于希臘文化-文學的著譯多達17種(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吳宓的愛徒景昌極、郭斌龢先后翻譯的柏拉圖五大文藝對話錄,即《蘇格拉底自辨篇》(第3期)、《克利陀篇》(第5期)、《斐都篇》(第10期;第20期)、《筵話篇》(第43期;第48期)和《斐德羅篇》(第69期;第76期)。譯文前均有“譯序”或“引”,介紹蘇格拉底身世及各篇的寫作背景與特色。郭斌龢在《學衡》第77期還發表了《柏拉圖之埃提論》(Plato’sDoctrineofIdeas),對柏拉圖文藝思想的核心概念“埃提”(即“理式”)進行了專題介紹。在1933年7月出版的《學衡》最后一期上,郭斌龢又發表了導讀性質的《柏拉圖五大語錄導言》,吳宓在之前還加上了編者說明,景、郭二人合譯的《柏拉圖五大語錄》已經匯編成書,將由南京鐘山書局印行的書訊。可見,對柏拉圖文藝思想的翻譯、介紹與研究,幾乎貫穿于整個《學衡》雜志的歷史。五大語錄在《學衡》的連載以及隨后單行本的問世,亦開我國柏拉圖著作譯介之先河。此外,1923到1926年間,由向達、夏崇璞合譯,在《學衡》分期連載的《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亦開漢譯亞里士多德著作之先聲。其他如湯用彤翻譯的《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希臘之宗教》,吳宓翻譯的《希臘對于世界將來之價值》,胡稷咸翻譯的《希臘之哲學》,還有吳宓所著《希臘文學史》①等,均體現了《學衡》推介希臘文化的煌煌實績。對于作為希臘文學與后世歐洲文學橋梁的羅馬文學,《學衡》的譯介同樣走在了五四以來各文學刊物的最前列。錢堃新翻譯了羅馬最著名的散文家西塞羅關于人生老境的一篇作品,題為《西塞羅說老》(第15期)。吳宓又專門加上按語,介紹西塞羅的身世、羅馬文學的成就,以及該作的創作背景與風格。此外,吳宓還整理出向讀者系統推介西方文學經典的《西洋文學精要書目》多種,在第7與第10期上分別刊登了關于希臘與羅馬文學的書目。
“學衡派”對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重視絕非偶然。吳宓曾說,他“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約圣經》,宓看明(1)希臘哲學(2)基督教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業之原動力”,而在“兩希”文化中,“古希臘之哲理文章藝術等,為西洋文化之中堅,源流所溯,菁華所在。為吾國人研究西洋文化所首應注重者。”②這一追本溯源的意識直接來源于梅、吳二人的恩師、美國新人文主義思想大師歐文•白璧德。吳宓在日記中如此自陳與白璧德的關系:“蓋宓服膺白璧德師甚至,以為白師乃今世之蘇格拉底、孔子、耶穌、釋迦。我得遇白師,受其教誨,既于精神資所感發,復于學術窺其全真,此乃吾生最幸之遭遇。雖謂宓今略具價值,悉由白師所賜予者可也。嘗誦耶穌訓別門徒之言,謂汝等從吾之教,入世傳道,必受世人之凌踐荼毒,備罹慘痛。但當勇往直前,堅信不渝云云。白師生前,已身受世人之譏侮。宓從白師受學之日,已極為憤悒,而私心自誓,必當以耶穌所望于門徒者,躬行于吾身,以報本師,以殉真道。”如果說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更多接受的是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梅光迪、吳宓、胡先骕、湯用彤等人則是以白璧德為代表的美國新人文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人。吳宓甚至自稱為“華之白璧德”。新人文主義作為20世紀文化保守主義學說的代表,從歷史的角度看體現了人文知識分子對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以降西方功利主義和浪漫主義所帶來的道德淪喪和人性失落的理性反思。《學衡》第19期刊登了吳宓翻譯的白璧德哈佛同事、法國學者路易•馬西爾評述白璧德思想的長文《白璧德之人文主義》,吳宓在正文中又多處加上長長的按語,清晰勾勒了白璧德的思想精華及其發展輪廓。白璧德反對培根代表的“科學的自然主義”和盧梭代表的“感情的自然主義”,認為正是它們造成了近代以來重物質而輕內心、重放縱而輕節制的社會風習。這兩種傾向蔓延擴張,使得人類愈來愈失去自制,只知追求物欲而無暇顧及內心道德修養。此為尼采“超人”學說滋生的土壤,亦為一戰爆發之深層根源。所以他終身視盧梭為仇讎,主張以人性中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沖動之自我。正是由此意義上,白璧德推演出“今急宜返本溯源,直求之于古”的觀點:“蓋以彼希臘羅馬之大作者,皆能洞明規矩中節之道及人事之律,惟此等作者為能教導今世之人如何而節制個人主義及感情,而復歸于適當之中庸。故誦讀其書而取得其精神,為至不可緩也。”除“物質之律”而求“人事之律”,“使人精神上循規蹈矩,中節合度”,體現在思想行為上即為節制、理性:“夫惟人類能自拔于此,而上進于理智裁判及直覺之生活,乃有文明之進步可言。”體現于藝術中即為對形式與格律的重視:“白璧德斷曰:欲藝術之盡美盡善,僅有精湛之材料尚不足,而必需有既整齊且有變化之形式,以表達之而范圍之。”
除《白璧德之人文主義》外,《學衡》譯介白璧德的文章還有:《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胡先骕譯,第3期)、《現今西洋人文主義》(梅光迪,第8期)、《白璧德論民治與領袖》(吳宓譯,第32期)、《白璧德釋人文主義》(徐震堮譯,第34期)、《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吳宓譯,第38期)、《白璧德論今后詩之趨勢》(吳宓譯,第72期)和《白璧德論班達與法國思想》(張蔭麟譯,第74期)。20年代末,吳宓將《學衡》所刊白氏譯文匯集成冊,交梁實秋由新月書店以《白璧德與人文主義》為書名出版。美國新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還有保羅•E.穆爾(PaulElmerMore,1864-1937)和斯圖亞特•P.薛爾曼(StuartP.Sher-man,1881-1926)等人。《學衡》對他們的著作也有譯介。①在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學衡派”擁有了高度一致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體現出鮮明的古典傾向與清晰的文學史意識。在《學衡》第1期的《評提倡新文化者》中,梅光迪立場鮮明地批駁了陳獨秀的文化-文學進化觀:“文化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名家(如英國十九世紀散文及文學評論大家韓士立Hazlitt),多斥文學進化論為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且謂西洋近世文學,由古典派而變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變為寫實派,今則又由寫實派而變為印象、未來、新浪漫諸派。一若后派必優于前派,后派興而前派即絕跡者。然此稍讀西洋文學史,稍聞西洋名家諸論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國人童騃無知,顛倒是非如是乎?”他認為新文化運動者“趨時投機”,“于歐西文化,無廣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淺,所取尤謬,以彼等而輸進歐化,亦厚誣歐化爾。”所以他重視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愛默生、阿諾德等所代表的古典文學傳統,而反對以盧梭、雨果、司各特、華茲華斯、托爾斯泰、易卜生、蕭伯納等為代表的近代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在《論批評家之責任》(第3期)中,胡先骕為心目中博學的文學批評家開具了需要掌握的多種中西名著書單,西方作家即為包括荷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普魯塔克、西塞羅、但丁、莎士比亞、彌爾頓等在內的希臘羅馬以來近60位經典大師。吳宓亦在《論新文化運動》中指出:“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為上材,此當以西洋古今博學名高者之定論為準,不當依據一二市儈流氓之說,偏淺卑俗之論,盡反成例,自我作古也。然按之事實,則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之實驗主義者,則必謂墨獨優于諸子;其他有韻無韻之詩,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相關亦類此。”(第4期)綜上可知,“學衡派”對文化進化觀與文學革命論的否定,對西方近代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名目下諸多流派的蔑視等等,均直接源自白璧德崇古的美學思想,以及自身捍衛儒家道統的價值取向,在新文化-文學運動的大潮中固然不合時宜,被斥為“復古”、“反動”,言辭中確也有偏執和情緒化之處,但他們正本清源的價值立場,也使《學衡》以對希臘三哲,即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文藝學、哲學與倫理學思想的譯介,部分矯正了文化激進主義者在西學譯介上一味逐新的偏頗,體現出尊重傳統的自覺的文學史意識。
二、注重經典、強調理性的精英意識
除了希臘羅馬文化與文學之外,《學衡》對各時代、各國文學的選擇同樣體現出注重經典、強調理性與純正的藝術品位的精英意識,反對將文學降格為對大眾進行啟蒙與教化的工具,譯介國別涉及英、法、美、意大利等國,時間上則覆蓋了中世紀直至20世紀的歐洲文學。這一特色背后同樣貫穿了明確的新人文主義理念。從國別的角度看,英國文學所占份額最大。這與刊物主編吳宓的個人偏愛與知識背景有著直接的聯系。吳宓素愛英詩,在哈佛大學求學的第一年即選修了英文系J.L.洛斯教授的“英國浪漫詩人研究”課,研習過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拜倫、雪萊和濟慈的詩作。他于1930年在牛津大學訪學期間,亦曾遍訪拜倫、雪萊與司各特等先賢遺跡,寫下《歐游雜詩》五十余首。因此,《學衡》的英詩翻譯,極有特色。筆者有另文專述,此處不贅。留學期間的吳宓還在比較文學系克•霍華德•梅納迪博士“英國小說”課的影響下,特別推崇18世紀菲爾丁和19世紀薩克雷的作品。所以自《學衡》創刊伊始,他便致力于對薩克雷的《紐康氏家傳》(TheNewcomes)①的翻譯。在“譯者序”中,吳宓這樣解釋了翻譯動機: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文壇,薩克雷與狄更斯原是齊名的作家。但由于林紓翻譯的《孝女耐兒傳》(即《老古玩店》)、《賊史》(即《霧都孤兒》、《塊肉余生錄》(即《大衛•科波菲爾》)等的風行,國人知有狄更斯而不知有薩克雷。“而若論學問之淹博,文筆之雋雅,意境之高夐,工力之深到,則沙克雷且有一日之長,為狄更司所莫及。”(《學衡》第1期)吳宓還借用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與《石頭記》的風格差異比較了“二人之短長得失”,認為“狄更司多敘市井里巷卑鄙齷齪之事,痛快淋漓,若不勝其憤激者,薩克雷則專述豪門貴族奢侈淫蕩之情,隱微深曲,若不勝其感慨者。其于褒貶人物也,狄更司直而顯,揚善嫉惡,唯恐不及。其弊則書中之善人,幾同圣賢。而惡人皆如鬼魅。刻畫過度,反而失真。……薩克雷則不然,用筆婉而深,似褒實貶,半譏若諷。描畫人物,但詳其聲色狀貌之流于外者,而于微處偶露其真性情。明眼讀者,自能領悟,而沙氏則不自著評語。”由于善人有弱點、惡人有才具才更合乎常情,所以吳宓認為薩克雷的人物刻畫深度遠在狄更斯之上。他還從藝術水準的高度,得出狄更斯文風“時流于粗疏放縱”,而薩克雷則“沉著高華,修潔雅典,實遠勝之”的結論,認為《鈕可謨一家》是英國小說中唯一最像《石頭記》者,故在譯文的語言風格上亦效《石頭記》之白話,盡可能傳達原著風貌。從以上觀點可見,吳宓對翻譯作品的選擇更為側重藝術標準,顯示出知識貴族的精英趣味。“學衡派”重要成員、“白屋詩人”吳芳吉同樣強調衡量文學藝術作品價值優劣的標準“惟在文心之得喪”,可為參證。他定義“文心”為“集古今作家經驗之正法,以筑成悠遠之坦途,還供學者之行經者也”,指出時代變而“文心”不變,應把握“文學真諦所在”。此“文心”指的即是文學性。
②《學衡》分6期連載了小說的六章譯文。自第55期開始,吳宓翻譯的薩克雷小說代表作《名利場》也開始連載。可惜由于吳宓的教務、編務異常繁忙,兩部小說都未能譯完。193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伍光建根據美國赫次堡的節本翻譯的《名利場》,譯名為《浮華世家》。但吳宓實為該著最早的中國譯者,且其譯名也成為后來通用的譯名。③陳鈞是《學衡》法國文學的翻譯主力之一,先后推出了福祿特爾(即伏爾泰)的哲理小說《福祿特爾記阮訥與柯蘭事》(即《耶諾與高蘭》)、《坦白少年》(即《老實人》)和《查德熙傳》(即《查第格》)的譯文。后來,他又將譯文結集為《福祿特爾小說集》,列入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于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為18世紀法國啟蒙文學的泰斗,伏爾泰的哲理小說具有鮮明的理性特征。啟蒙運動本身即是以理性的名義審視與批判中世紀以來的宗教狂熱、政治專制與社會偏私的思想解放思潮。伏爾泰在美學思想上又偏好古典主義的理性原則,推崇維吉爾的史詩與拉辛的古典主義戲劇。吳宓在這部小說集的“譯序”中將伏爾泰作品的特色概括為“古學主義”,強調的正是古典主義美學趣味中與新人文主義相通的理性與節制。法國文學譯介中值得提到的,還有徐震堮翻譯的19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巨子圣佩韋關于“Classique”的一篇代表性論文,徐氏譯為《圣伯甫釋正宗》(第18期)。在“按語”中,吳宓不僅清晰交代了圣佩韋的生平著作,還說明了譯介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傾向古學派之作家”,“力言規矩格律及道德修養之要”。吳宓討論了Classique(英文為Classic)的名詞形式Classicism的中文譯名。他認為徐氏所譯的“正宗”因與中國所謂“古文正宗、駢體正宗”之意相合而較為合理。他還認為“Classicists”“行文最重簡潔明顯”,而非堆砌典故,所以“古典主義”這一譯名從字義上說并不準確,相較之下,還是“古學派”或“古學主義”更好。該文中,圣佩韋高度評價了希臘羅馬文化與文學的正宗地位,梳理了歐洲文學的主流傳統,提出了“整齊、智慧、中庸、理性”四者為“正宗”之“最要之義”的觀點。由于圣佩韋的文化與文學觀深刻影響了英國維多利亞詩人與學者馬修•阿諾德,而阿諾德又被視為白璧德的思想前驅之一①,因此,《學衡》擇取圣佩韋關于文學之取舍標準即“正宗”或“古學主義”的文章是相當自然的,與新人文主義尊重道德、崇尚理性、強調古典的取向完全一致。②意大利文學中,1921年,錢稻孫先生于但丁逝世600周年之際曾將用騷體譯出的《神曲》“地獄篇”前三曲,以《神曲一臠》為標題,發表于《小說月報》。1924年又出版了單行本,成為中國最早的《神曲》譯者。在第39期《學衡》上,錢稻孫先生取《神曲》這部夢幻體長詩的第一、第二曲本事,改編成中國雜劇,運用了“仙呂賞花時”、“仙呂點絳唇”、“混江龍”等曲牌形式,發表了《但丁夢雜劇》(第一出)。第41期上,吳宓又譯出美國著名的但丁學者查爾斯•霍爾•葛蘭堅教授(CharlesHallGrandgent)所撰《但丁神曲通論》的“導論”,對但丁的生平事跡、《神曲》的內容體制等進行全面介紹,對錢稻孫的翻譯加以呼應。第72期上,錢稻孫又用騷體譯出了但丁《神曲》“地獄篇”的曲一至五。可見,對《神曲》這部中世紀歐洲最偉大的作品,《學衡》的譯介同樣走在了最前沿。
綜上,如果我們與《新青年》、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五四以來主流的新文學刊物與社團的西學譯介加以對照,會發現它們與《學衡》的差異十分明顯。在中國近代以來面臨亡國滅種之危局的嚴峻形勢下,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通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中國廣為傳播。急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將中西之辨與古今、新舊之爭合為一體。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由是在進化的歷史觀中找到了建設新文學的合法性。陳獨秀在《青年雜志》一卷三號和四號連載了《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一文,提出西洋文學經歷了古典主義、理想主義、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幾種不同階段,而中國文學尚處于古典主義、理想主義階段,當前最需要的因而是19世紀科學昌盛之后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文學進化觀。因此,在1915-1921年間,以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周作人、茅盾等為翻譯主力的《新青年》的翻譯作品包括了屠格涅夫、契訶夫、莫泊桑、易卜生、顯克微支、安徒生、阿爾志跋綏夫和武者小路實篤等10余個國家的作家作品,前期側重于歐洲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后期則更注意俄國、日本及弱小民族文學。1922年,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就外國文學的翻譯選擇問題,亦有過一場論爭,背景即是有讀者給《小說月報》去信,提出了翻譯《浮士德》、《神曲》、《哈姆雷特》等“雖產生較早,而有永久之價值”的著作的建議。茅盾的答復則是:“翻譯《浮士德》等書,在我看來,也不是現在切要的事;因為個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紹給群眾,則應該審度事勢,分個緩急。”1922年8月1日,茅盾在《文學旬刊》(第45期)上借《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一文,再度表達了“要求文學來做詛咒反抗的工具……要求‘血與淚’的文學”的觀點。因此文學研究會的翻譯指向十分明確:即俄羅斯文學、“被損害的民族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與“為人生”的文學,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在新文化陣營中,文學翻譯與新文化-文學運動倡導文學革命、要求平民的、大眾的文學的目標是一致的,直接參與了傳播新思想的目標建設。而“學衡派”對這種趨時逐新的文學進化觀、對以文學作為迎合大眾、宣傳啟蒙之工具的傾向,對文學翻譯者對西方文學不求甚解、淺嘗輒止、缺乏系統性的做法不以為然。如胡先骕所說:“欲推翻知識階級,使之反變為愚騃。不惜將歷代俊秀之士所養成之高格文化,高格藝術,下降以就受教育,姿稟駑下之平民之視聽。”③他們自認真理在握、對中西文化更有發言權,以精神貴族自命而傲視群倫的姿態,自然遭到了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迎頭痛擊,如沈衛威所說:“由于其語境的錯位和文化背景的改變,使得他們反抗的話語和行為陷入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悲劇境地。面對新文化運動主帥人物的話語霸權,他們陷入了‘落伍’和‘保守’的困境。”
他們捍衛經典與文學性,尊崇文學傳統,反對功利主義的立場,顯然是有其合理性的。歷史地來看,新文化-文學陣營在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以矯枉必須過正的姿態反傳統,“開啟民智”、作為啟蒙工具的新文學確實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學衡派”不肯自降身段、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場與貴族姿態顯得不合時宜,但他們的翻譯擇取確實也起到了一個糾偏的作用。正如余英時在1989年9月香港中文大學25周年紀念演講中所說:“相對于任何文化傳統而言,在比較正常的狀態下,‘保守’和‘激進’都是在緊張之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例如在一個要求變革的時代,‘激進’往往成為主導的價值,但是‘保守’則對‘激進’發生一種制約作用,警告人不要為了逞一時之快而毀掉長期積累下來的一切文化業績。相反的,在一個要求安定的時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調,而‘激進’則發揮著推動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圖一時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創造生機。”這一關于保守與激進的辯證論述,同樣可用于歷史地看待“學衡派”的地位。樂黛云先生也認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三者往往在同一框架中運作,試圖從不同途徑解決同一問題,它們在同一層面上構成的張力和沖突正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契機。”所以,從此意義上說,在20世紀中國文化轉折的重要關頭,“學衡派”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路向與新文化-文學運動主將們的文化激進主義相互抗衡、制約與互補,在沖突、調整與張力中激發了文化-文學的正常發展,有助于矯正全盤西化、急功近利、民族虛無主義的傾向,參與推進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從世界范圍來看,新人文主義是西方的有識之士面對一戰的爆發,反思文明中片面的物質主義與科學主義傾向的自然產物。中國的“學衡派”對其的呼應,從歷史的角度看是有它的先見之明的。其文學譯介則彌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其他期刊與社團譯介西學的缺失,構成了中西文學交流史上無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作者:楊莉馨 王葦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