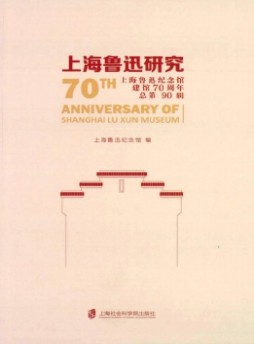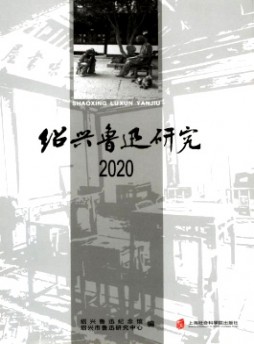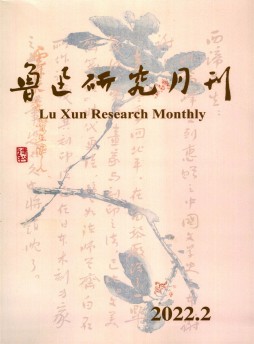魯迅作品中母性受難的意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魯迅作品中母性受難的意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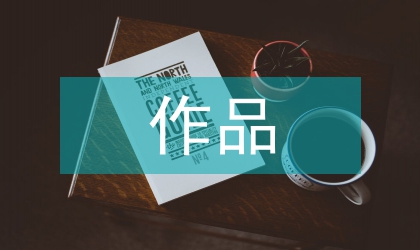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年第三期
魯迅在雜文《小雜感》中說:“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母親形象多次出現在魯迅作品中,除了《社戲》、《故鄉》和《在酒樓上》中的慈母,像《明天》中的單四嫂子,《孤獨者》中的祖母,《頹敗線的顫動》中的母親,尤其是《藥》中的兩位母親,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一些不識字的喪夫者、孤獨者、迷信者,或者“粗笨女人”。她們有的無名,有的無名無姓,是令讀者同情的苦難母親。不過,“同情”可能恰恰暴露了讀者“革命/啟蒙”視野下居高臨下的立場,以及一種二元對立式的思維方式,這種“現代(進步)的”或“人道主義式的”解讀忽略了本源層面上的“母性”存在,遮蔽了母性受難的困境及其批判性和救贖性。這在研究界對《藥》和《祝福》的解讀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一、被遺忘的“親子之愛”
以往對《藥》的主題理解大致經歷了從“革命”到“啟蒙”,從揭示革命者的悲哀、革命失敗的原因,到批判群眾愚昧、尋求現實改造的變化,在這兩種實質相似的視野下,小說中的另一條主線———“親子之愛”往往被遺忘和遮蔽了。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的解讀都聚焦于把“人血饅頭”當作“藥”這一“封建迷信”。所以這里的首要問題是怎么看“人血饅頭”。當讀者看到“用人血饅頭治病”(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已提及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犯人的血舐),馬上想到的是“迷信”和“愚昧”,何況這血又來自就義的革命者夏瑜,那么“愚昧”后面又要加上“麻木”和“殘忍”了。事實上,用鮮血治病在中國的民間就像“吃什么補什么”一樣,沒有科學依據,當然是一種“迷信”,但魯迅對這一類民間“迷信”并非簡單否定了事。在1905年發表的《破惡聲論》中,魯迅把當時的改良人士視為“迷信”的種種宗教、民間信仰、神話和神物等等,都看做是“人”的一種精神性(尤其是古民的“白心”和“神思”等想象力)的產物,是“不安物質之生活”的“人”的“形上需求”。
如有論者指出的,“魯迅既不是在‘近世文明’的立場上批判民間信仰,也不是作為傳統的維護者將民間信仰實體化、絕對化,他是在反思‘近世文明’的立場上看待民間宗教與迷信的,挖掘其精神氣質以作為反思‘近世文明’的思想資源”。在魯迅看來,關鍵問題不在于“迷信”的對與錯,而在于信者的態度是否真誠(是否真“信”)。像祥林嫂、阿Q、華老栓、華大媽、夏瑜的母親這樣的底層百姓,他們一輩子生活在“迷信”的傳統中,沒有機會領受一種“現代”的知識和觀念,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迷信”。但與那些追逐新潮價值、內心不信卻又信誓旦旦的“澆季士夫”相比,他們起碼是真的在“信”。迷信的世界就是他們的生活世界。而那些動輒指斥民眾的宗教信仰為“迷信”,而自己卻不知“正信”為何的人(多為受過教育的知識人)反而是“偽士”。魯迅最后的結論是:“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早期魯迅的這一宗教和迷信觀到后來并沒有根本變化。這提醒我們不要囿于“啟蒙”或“革命”視野,在科學(進步、覺醒)∕迷信(麻木、愚昧)這樣一些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去理解《藥》。二元對立化理解的表現之一就是忽略了《藥》中的“血”具有雙重性,即“革命者之血”和父親母親與兒子間的“血緣之血”。我們往往只注目于作為“藥”的“革命者之血”(“人血饅頭”),注目于革命者之血和不知革命為何物的民眾之間的錯位———“血”作為(啟蒙之)“藥”最終失效了,是革命者也是群眾的悲哀,而忽略了,這“血”也是真實的、身體及情感上的“血”———血緣之“血”。它是革命者夏瑜的身體之血,也是癆病患者華小栓的身體之血(癆病的癥狀之一是咯血),在血緣的意義上,它關聯起兩個母親、兩個兒子,體現的是“親子之愛”,即父愛和母愛(在小說的結尾,母愛又被特別凸顯)。
“親子之愛”說是朱自清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提出來的。他認為“親子之愛”是《藥》的正題旨,革命者的悲哀是小說的副題旨。后來我們先是將正、副顛倒,再后來就不再提“親子之愛”了。從內容看,“親子之愛”在小說中是貫穿性的存在。小說的第一部分寫老栓去刑場拿藥。無論是老栓去的路上“仿佛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的感受,還是拿到“藥”之后,“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仿佛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獲許多幸福。”都以老栓的行動和感受為中心。敘述人對老栓沒有諷刺。這里特別要注意的是,一是華老栓(和華大媽)并不知道被處決的是一位革命者(也就是說,以夏瑜的“血”做藥與他的革命者身份沒有關系);二是在敘述人的眼中,老栓與那些“古怪的”、“鬼似的”、“眼里閃出一種攫取的光”、“像被捏著脖子的鴨”一樣的看客(他們也出現在阿Q的行刑現場)有著明顯不同(這些看客恰恰是通過華老栓的視角呈現的)。第二部分寫小栓吃藥。“他(小栓)的旁邊,一面立著他的父親,一面立著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進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著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才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在這些描述中可以切實感受到父愛母愛的存在。這是一個充滿關懷的家庭場景,沒有諷刺性的話語出現。
小說第三部分的主角無疑是康大叔。他一出場就可看出與華家三口的不同(也與茶館中其他人不同)。康大叔對小栓漫不經心的“一瞥”(茶館內其他人也對小栓的咳嗽不以為意)與華大媽對“癆病”的敏感和對兒子的擔憂形成潛在的對照。從這里可以看到,同是群眾,老栓一家與康大叔不同,與牢頭紅眼睛阿義不同,與那些刑場的看客不同,也與茶館里的顧客(駝背、花白胡子、二十多歲的人)不同。后面這些“群眾”也許可以稱之為“愚昧”的。不過,小說的目的并不止于表現和批判“愚昧”。小說的第四部分最容易引起歧義。立足革命和啟蒙視野的解讀都被那一圈花環和那一只烏鴉所吸引,而忘了兩個悲哀的母親。如果置諸于“啟蒙”和“革命”的邏輯,那么花環和烏鴉就一定有象征的深意:“花環”意謂革命烈士沒有被所有的人遺忘,還有人紀念他們(因此革命仍然有希望);而烏鴉,大多數人認為它象征著“革命”。烏鴉飛去則否定了夏大媽的“顯靈說”,說明母親不理解兒子,不理解革命(當然也就不理解“花環”的意義)。上述理解將小說當做象征和寓言來讀(所謂“華夏”的命運),而忽略了小說的現實基礎,因此就會出現有論者指出的問題,即“過于關注作品中的象征符號,由于象征符號的多義性和象征符號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對作品象征內涵的把握很有可能成為研究者對象征符號的個人演繹”[7]。既然花環是作者魯迅自謂“不恤用了曲筆”“平添”上去的,它的涵義就未必有我們所說的那么確定。即使它象征著“希望”,那么這種“希望”也不僅僅指向“革命”,也指向對孤苦無援的夏大媽的安慰(同時它又讓另一個母親華大媽感到“不足和空虛”)。上述理解除了有將象征含義過于“落實”之嫌外,還隱含著將革命(啟蒙)與“親子之愛”對立的趨勢,認為母愛的蒙昧、自私對于革命者和革命是一種束縛和負擔。這無疑是受我們的“啟蒙/革命”視野所限。其實在中國民間,烏鴉既是只不吉利的鳥,也是一只“神鳥”,一只“孝鳥”。在魯迅故鄉紹興的目連戲中(它深深地影響了魯迅),它被稱作“慈烏”。日本研究者丸尾常喜就特別注意到在紹興目連戲《目連救母》中“烏鴉反哺”的情節。他把烏鴉看做“雖然背負著自身的不孝與母親的悲哀,但仍堅韌地走向前方的‘不孝的孝子’們的革命意志的象征”,所以小說寫的是“革命者的救民意志與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悲劇性隔絕”。
二、母性的批判
徑奔“血”的象征意義而去,而有意無意忽略了更基本的、血緣之“血”的存在,使得“親子之愛”要么被遺忘和遮蔽,要么被視為“蒙昧之愛”。那么這兩種“血”,或者說,“革命、啟蒙”與“親子之愛(迷信)”是什么關系?無論是朱自清的“正負題旨說”還是丸尾常喜的“革命者的救民意志與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隔絕”說,抑或是后來的“革命/啟蒙”立場下對民眾(包括兩個母親)之愚昧的批判性解讀,都沒有去追問這一問題。其實,正是小說第四部分中兩個母親的表現(稍后會論述),讓兩種“意志”、兩種主題、兩個價值世界產生了內在的關聯。這里僅僅用“親子之愛”或者“母愛”不足以概括兩個母親。因為她們的存在與其說是體現了某種母愛,不如說是凸顯了“母愛”在現實世界被剝奪的命運。但是,即使被剝奪了做母親的權力,那母性的聲音卻仍然綿綿不絕。這是一種本能,被動甚至愚昧,卻又是執著、包容的,這是處于受難中的“母性”。正是它,讓《祝福》中的“我”———一個現代知識者不安。與《藥》中兩個沉默寡言的母親不同,《祝福》中的母親祥林嫂以一連串的提問和反復“念叨”的方式令人側目。祥林嫂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被魯鎮的人們最終“棄在塵芥堆中的”的最底層的寡婦,卻出于信任,向“我”———一個“出門在外見識多”的讀書人一連提出了三個問題:人死后有沒有魂靈?有沒有地獄?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見面?如李歐梵所指出的,“她向‘我’提出的問題雖然是從迷信出發的,卻有一種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響,而且和‘我’的模棱的、空洞的回答形成驚人的對比,因為作為知識者的‘我’,本是更有可能去思索生死的意義的。”
這三個問題可謂是“迷信”對“啟蒙”的反問,它超出“科學”或者“啟蒙/革命”話語所能夠把握、闡釋的范疇,也是人道主義式的同情所不能回答的。不過“祥林嫂之問”是否就如研究者們所說,是關乎“生死意義之問”或者“信仰之問”,從中可看出祥林嫂的“覺悟”有多高,或者信仰有多深?從母性的角度看,祥林嫂更多是作為一個(喪子、喪偶的)母親和妻子在提問。這是她的切身之問(死后與家人能否見面),是憂心的母性在尋求安慰,所以祥林嫂是既希望其有,那樣與兒子就可以見面,又害怕其有,那樣身體會被鋸成兩半。不過從她急切的語氣可推測她希望其有。在這里母愛壓倒了恐懼。而“我”的落荒而逃應該理解為自以為掌握著這個世界的闡釋權的啟蒙的挫敗,可見“我”并非一個堅定的啟蒙者和無神論者,否則就應該直接給予否定的回答了。他沒有辦法拯救像祥林嫂這樣最底層的無助者,甚至連最后(也是最基本)的安慰都不能給予。啟蒙者在母性逼視的目光面前,在母性的受難面前無能為力,這是讓“我”長久處于“不安”當中的根本原因吧。
也正因為這種“不安”驅使‘我’去追述祥林嫂的生平。在其中,祥林嫂對兒子阿毛之死的“念叨”一再出現,驅之不去,糾纏著魯鎮的人們,以及敘述者和讀者。“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墺里沒有食吃……”。祥林嫂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復”訴說兒子被狼吃掉的經過,最終讓魯鎮的人們煩厭得頭痛。祥林嫂的“念叨”首先是一個母親對死于狼口的兒子的哀悼;其次,一再的重復表明她想(在自己和魯鎮人面前)繼續維持作為“母親(而非妻子)”的身份;第三,它也類似于宗教徒的“懺悔”和“告解”。不同的是,祥林嫂傾訴的對象不是上帝、神甫或菩薩之類,而是魯鎮的人們。她傾訴的方式不是私密,而是公開的,她希望通過這樣一種公開的告解方式尋求解脫。她就像自覺“有罪”的苦役犯,但她的“罪感”不是來源于信仰,而是出自母性的天性。和捐門檻一樣,一再的重復(告解)也是祥林嫂的贖罪方式。可是魯鎮沒有一個類似于神甫的告解對象,也不存在一個讓人在罪中復活的上帝。他們先是厭煩、唾棄了她的告解,又否定了她的捐門檻的贖罪方式。祥林嫂的無法求得救贖,鑒照出“我”所代表的啟蒙理性的缺失,魯四老爺所代表的儒家理學和家族制度的缺失,以及魯鎮的“祝福”儀式中神性的缺失。魯鎮的人們相信鬼神,注重家族祭祀的儀式,卻缺失最關鍵的實質———神性和救贖、愛與憐憫。先后失去丈夫和兒子的孤苦無依的母親,在“祝福”的時刻被魯鎮整個地排斥在外,在惶恐和絕望中死去,這是母性的受難,也是“人性”的受難。正是借助母性的受難,小說構筑了一個巨大的悖論和反諷———這大概是魯迅對中國文化最深層的揭示和批判了———中國的人間和地獄,皆不包容受苦者、絕望者,不能讓喪失的母性得到最終安慰。因此小說的標題“祝福”只能從反諷的意義上去理解。更意味深長的是,在這一母性的受難圖中,“我”與魯四老爺(及魯鎮的人們)扮演的角色并沒有什么本質差異。而當讀者亦認為祥林嫂“無知/愚昧”,不耐煩甚至取笑祥林嫂的一再“嘮叨”時,我們也與魯鎮的人們一樣,在祥林嫂的母性的“絕望”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或者當我們僅僅把祥林嫂視為一個“人吃人的世界”———所謂“夫權、族權、神權、政權”下的“犧牲品”,并予以同情時,我們也仍然遮蔽了祥林嫂之母性“受難”的尖銳批判意義。
三、母性的救贖
丸尾常喜說:“為了萬人之生而寧可一人赴死的夏瑜的意志,與為了小栓的生命而罄其所有的老栓的意志,本來可以作為共通的東西緊密地結合起來。可是,在這個舞臺上,二者卻決不相觸,各自散發著孤獨的光,一起為某種強暴之力所扼殺。”可是因為母性的存在,隔絕的二者有了交集。而《祝福》中母性的受難在揭示了“人吃人的世界”的真相———一個缺乏愛、憐憫與救贖的世界的同時,也把這個世界撕開了一個裂口,人吃人的循環因此有被打破的可能。這可以說,母性的受難既是對這個世界的批判,又是對它的救贖。因為在苦難的深處,“人性”總會與“神性”相通。不止一個研究者指出《藥》中夏瑜犧牲與耶穌受難之間的關聯:“耶穌也好,夏瑜也好,他們首先覺醒,甘愿犧牲,人格高尚,卻無法避免自身的犧牲也被誤解的悲劇命運”。。也有人注目其差異性,認為夏瑜作為革命者的犧牲中看不到神性。耶穌之血救贖了眾人,成為救贖眾生的靈藥,而夏瑜的血則沒有。《藥》中有一個“人子受難”的模式,但與《圣經》中的耶穌受難有本質區別:“夏瑜的犧牲沒有從任何意義上得到認可。作為人子一代的魯迅對自己在中國進行啟蒙革命的意義產生了徹底的質疑,并伴隨著深深的悲涼”。以上都是從夏瑜、耶穌犧牲與受難的結果而論。李歐梵則指出,“在這篇小說的象征性框架中,憐憫的舉動給犧牲的意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在受到肉體虐待時仍然給予憐憫,這種舉動顯然受到耶穌基督的啟發……然而,他與耶穌不同,他沒有上帝作為更高的權威,最終的意義問題不可能得自任何超驗的來源。這便是魯迅人道主義的最后悲劇。”
確實,如果只著眼于夏瑜與耶穌的犧牲,那么二者之間的差異明顯:兩人流血的目的不同,結果不同,尤其是夏瑜的犧牲中沒有救贖的希望(而耶穌經由犧牲后的“復活”成全了救贖)。這是“人”與“神”、“人性”與“神性”的區別。但是當我們的目光不受“啟蒙/革命”或“人道主義”框架的約束時,反而可能發現母性受難與耶穌受難之間的內在相通。在《藥》中,它集中地體現在小說的第四部分。這部分首先是通過華大媽的視野呈現,花環出現時兩個母親的視野開始融合。如果一開始兩個母親還是被一條區分死者身份的小路隔開的話,那么華大媽出于關心,跨過小路安慰夏大媽,就意味著她們之間因為兒子之死而打破界限。許多的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著說,“我們還是回去罷。”那老女人嘆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后“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如作者自謂,《藥》的這個結尾有些安特萊夫式的“陰冷”和“鬼氣”。
如前所述,不管花環和烏鴉是不是象征革命,它們對于悲哀的母性都是一種安慰。不過,《藥》的深刻之處恰恰在于,那“鐵鑄一般”的烏鴉最終違逆了夏大媽的意愿,沒有飛上夏瑜的墳頭,而是“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表明魯迅在這里并沒有以“母性”替代“革命”,“革命”依然在迷信的母親們的理解之外,也沒有以“革命”去否定“母性”,將二者對立起來,而是在“革命”與“母性”之間保持著一種張力。如果說小說寫的是“革命者的救民意志與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悲劇性隔絕”,那么兩個母親的共同悲哀就已經穿越了這一“隔絕”;如果我們不將兩個兒子作一種革命∕愚昧的價值上的對立,那么兩個母親的愛就不會因為兒子們身份(革命者、啟蒙者∕群眾、被啟蒙者)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相反,這種悲哀的愛泯滅了身份與價值之差,超越了革命∕群眾、覺醒∕愚昧的區分。兩個喪子的老母親帶著對兒子的哀悼相伴離開墳場,先覺的革命者(夏瑜)和愚昧的群眾(華小栓)的“死”因為兩個母親的“哀悼”(愛)而消泯了價值高低的區分,呈現為共同的人性。在母親們無言的、哀傷的“愛”中我們不是感受到某種母性的“神性”嗎?如此,那挫身而去的烏鴉將兩個母親的視野引向那“遠處的天空”,就不再是虛無,也不是那么“陰冷”,而是一個在母親們的理解之外,卻隱含著既是革命的,也是母性(愛)的希望與安慰的所在。可見,在《藥》中,“革命”與“母性”之間存在內在的緊張,卻并非對立。對于現實中的“母愛”,魯迅不是一般地肯定或否定。生活中的魯迅是一個孝子,魯迅的婚姻是遷就了慈愛的、作為家長的母親的意志,這使得魯迅對于母愛有著某種反思。在《<偽自由書>前記》里魯迅說:“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或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他在給趙其文的信中說:“感激,那不待言,無論從哪一方面說起來,大概總算是美德罷。但我總覺得這是束縛人的。譬如,我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忍不住,而我有一個母親,還有些愛我,愿我平安,我因為感激他的愛,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尋一點糊口的小生計,度灰色的生涯。因為感激別人,就不能不慰安別人,也往往犧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斗者更勇猛,更悲壯。但這種反抗,每容易蹉跌在‘愛’———感激也在內———里,所以那過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幾乎不能前進了。”
從這些話中可見魯迅對母愛的深思。魯迅的深刻和復雜之處在于他將母愛放在母性的受難中,放在與“革命(啟蒙)”/“迷信”、“現代”/“傳統”的張力中來描寫。如果說以往我們站在“革命(啟蒙)”或“現代(科學)”的立場遮蔽了母性,那么現在我們可以立足母性受難的立場返觀“革命(啟蒙)”與“現代(科學)”:《藥》與《祝福》中母性的受難,透露出一個比啟蒙、革命、現代更原初的價值和一個更深邃、更本源的世界的存在,而正因為有此一世界的支撐,革命者的犧牲才更顯其悲涼意味和悲憫性。“前現代”的母性世界看起來并不理解革命者犧牲的意義(即所謂“隔絕”),卻以自己愛的受難包容和安慰了革命者和革命,而在《祝福》中,帶給那被狼吞噬了的兒子的安慰的,也只有孤苦無依的母性的“念叨”。這就是母性的力量,一種弱者的“無力之力”。或者說,正因為其脆弱、無用(無效)、被動,才更凸顯其力量———通過受難與哀悼的方式。
這與耶穌自愿釘十字架而死所帶來的神性的“救贖”有著實質的相通:都源于“愛”的受難,都超越了種種界限與隔絕而通向“無限”,都是對“強暴之力”的批判,也都通過對“死”的最終安慰而呈現出某種救贖性和超越性,一種是宗教性的,一種是非宗教性的。這正是卡夫卡所說的,受難是這個世界上的積極因素的體現。結語:阿長的魂靈如木山英雄所說,寡婦形象、奴隸是魯迅構筑中國像的唯一基本實體,“民眾之悲慘與痛苦的紀念碑”。在魯迅那里,悲慘與痛苦的母親不僅讓人同情,同時也是批判與救贖的資源:她們首先構成對現實的否定和批判。其次,作為沉默和失聲的女性,她們無法解脫的“苦難”本身提出了對“革命”與“啟蒙”的反思與質疑。第三,無論是革命者夏瑜還是普通群眾小栓、阿毛,他們的“死”在母性的悲傷與哀悼中有了內在關聯。母性的悲傷、哀悼(“念叨”)亦成為兒子之“死”的終極安慰,“死”因此有了救贖的可能。而革命者的“血”(死)能否成為真正的“藥”,取決于我們能否把小栓(和阿毛)包括在死者之中,取決于我們能否理解母性受難的意義,否則就會像魯迅說的:“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最后想到的死者是《阿長與山海經》中的阿長。阿長與《藥》中的夏大媽、華大媽和祥林嫂一樣,無名無姓,也同樣迷信。青年守寡的阿長沒有做母親的機會,作為保姆充當了我母親的角色(我叫她“阿媽”),將母性完全轉移到我身上。不識字的阿長并不知道“三哼經(山海經)”是啥東西,但阿長的母性世界與《山海經》的世界———神話傳說、民間信仰(迷信)的世界———是同源的,因為她就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這個豐富、博大、神奇又不乏苦難的世界吸引了我,卻是我難以把握和言說,也無力改變的。所以我只能“祈禱”(這在魯迅的作品中可謂絕無僅有)“仁厚黑暗的地母”來安慰這個像地母一樣的女性。像魯迅這樣“無所信”的啟蒙者和革命者,也許只有通過寫作銘刻母性的受難與悲傷,銘刻對受難母性的虧欠和安慰,來尋求自我救贖。受難的母性因此成為魯迅文學之“罪”與救贖主題的源頭之一。
作者:盧建紅 單位:廣東財經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