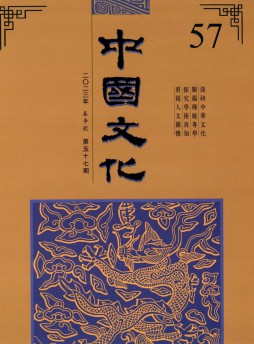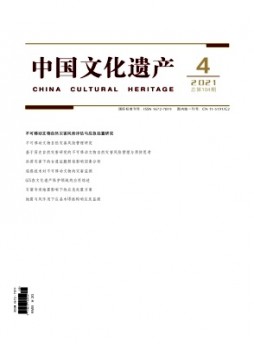中國文化語境下英語學習觀念轉變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文化語境下英語學習觀念轉變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濟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
[摘要]言語活動與情景語境直接相關,但根本上受文化語境限定。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借助語言來觀察、認識和表達復雜世界,并產生新的意義——實現語言向新的情景語境無限擴展的潛能。言語的意義在語境中才能得以發生和理解,語言作為意義的載體也適應語境,語言與文化語境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動態的。我國的英語學習是在當今中國文化語境中展開的,學習者所形成的學習觀念,扎根于當代中國文化語境;受其影響,普遍的英語學習反過來亦嵌入中國文化語境并促進其演變。中國文化語境下的英語學習應實現由語言工具論向文化論轉變,由語法知識向語言意義體系理解轉變,由單一課堂觀向復合課堂觀轉變。
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借助語言來觀察、認識和表達復雜世界,并產生新的意義——實現語言向新的情景語境無限擴展的潛能。言語的意義在語境中才能得以發生和理解,語言作為意義的載體也適應語境,語言與文化語境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動態的。學習者所形成的學習觀念,扎根于當代中國文化語境;受其影響,普遍的英語學習反過來亦嵌入中國文化語境并促進其演變。當下中國學生英語學習形成的學習觀念,扎根于當代中國文化語境,受到文化語境的根本約束,但英語語言又置于英美世界的文化語境中才能得到理解。那么,該如何處理英語學習和這兩種文化語境的矛盾關系?我們英語學習的觀念該發生怎樣的轉變?要擔負起在當代中國文化語境下英語學習的社會使命及文化責任,就要反思英語學習現狀所存在的問題,并加強引導以促進其向正確的方向轉變和發展。
一、英語學習的價值取向學習者的語言學習觀念
對其語言學習有深刻影響。當前,中國文化語境下的英語學習應從三方面進行分析:一是語言價值問題,為什么學習。分析英語學習者所追求的價值目標,這種價值選擇活動主要解決學習動機和預期目標問題。二是語言知識觀問題,學習什么。學習者是否具有正確的知識觀,英語學習是對工具性知識的學習還是對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學習者通過這種學習究竟能獲得哪些方面的提升。三是語言學習的方式方法和學習資源問題,如何學習、通過什么學習。這側重解決英語怎樣學的問題,關系到能否提高學習的有效性,以及語言學習能否成為一種自覺的、長久的、個性化的學習。在英語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對英語學習本身所包含的意義、重要性、價值進行評價和判斷,這是決定和影響英語學習者策略、行為的心理基礎。只有認識到學習本身所包含的價值,學習者才會有清晰的奮斗目標,愿意為之付出努力,并在遇到困難時保持堅定意志。英語學習者的價值觀,一方面表現為英語學習的價值追求,凝結為指向未來學習英語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判斷準則,成為英語學習者判斷英語學習有無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評價標準,這種判斷標準是應用于當下的。英語學習的個人價值取向是學習者的需求、愿望、目的和意志在英語學習中的集中體現。任何人的學習行為,總有一定的動機需求,離開了人的利益或興趣,學習活動則難以理解。人的需求和學習目的意味著對當下現實的不滿足,意味著要求超越現有,追求新的更美好的理想。學習者越能客觀、正確地把握學習動機,學習的目的越明確和可靠,學習本身就越具有真實性和可行性。個人在英語學習過程中自我價值的實現既表現為個體存在的意義,也表現為個體需求的滿足。在這一過程中,英語學習者的成功讓其體驗到實現個人價值的快樂,而失敗的經驗也會讓其因感受到巨大挫折而失去繼續學習英語的信心。
個人價值的實現過程,也是實現人的創造價值的過程。英語學習個體的創造價值問題,就是關于英語學習的意義問題。人的學習是基于社會、時代、文化、環境等背景的。特定的社會部門對人的要求是形成英語學習價值取向的因素,其中既有現代化的社會價值,也包含國際化的交流價值。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社會群體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個人價值永遠建立在生活的社會環境中。二語研究的學者們指出,在英語學習中,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對英語語言學習和交際的認識是不同的,提出“文化適應”和“社會文化”的理論假說,指出語言習得是學習者通過社會互動,將外在的語言形式內化為自己的思維,實現對語言的自我監控過程。總體而言,中國人和非英語國家但和英語語言屬于同一語系國家的人相比,英語學習的難易度、學習的進程等都會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這啟示我們中國英語學習者,如果不清楚中國文化語境的特點與影響,就會在英語學習的計劃、管理等方面估計不足,甚至無法做出正確的調節。中國文化語境是理解我們英語學習活動的基礎,脫離了文化語境的外語學習,不能進行知識整合以達到文化理解和文化創新的高度。在中國文化語境下思考英語學習的價值觀,可以使英語學習者的認識和實踐達到自覺,同時也可支配和調節英語的學習。布魯姆模式證明,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價值目標、方法策略是可控制的因素,當學習者有意愿學習而又懂得如何學習時,就可以取得理想的成績。英語學習的價值取向問題,不是英語學科存在和英語知識本身的問題,而是對英語學習者的意義問題,是以英語學習者為中心,通過實踐而實現的個人需求滿足、價值提升的問題。英語是已經價值化了的知識,英語學習者在英語學習中可以獲得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借助英語學習,學習者可以擴展其探索和創造的潛能,提升個人文化判斷能力和審美能力,實現個體的自身價值,也滿足社會的需求。
二、英語學習由語言工具論向語言文化論轉變
當代中國文化語境是一個特定的前提條件,對這一前提的認識狀況會對英語學習產生不同的影響。當代中國文化語境是生成英語學習觀的土壤,是對英語學習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重要因素。當前,語言學習被一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所引導,外語在中國一直被許多人理解為一種找工作、旅游、留學、經商等具有利益轉化潛能的工具,因而英語學習陷入一種“就語言教語言”、“就英語教英語”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語言工具論”誤區。工具論的外語學習觀使學習者在動機上直接體現為應對考試,拿到各種資質認證,因此他們只針對考試內容進行學習,這種學習動機使英語學習者產生偏見,導致學習者不能熟練運用英語。工具論的學習觀在學習方式上多采取聽講和背誦記憶,缺乏個性化的學習,沒有在根本上即語言理解和交流上做功。許多英語學習者只在課堂中聽英語教師講課,而英語教師總是忙于解釋語法、文章等,英語學習者淹沒在這種教學方式中,在課堂上保持沉默,只是在拾撿知識碎片,語言的刻板化非常明顯,學習的有效性較低。
刻板化的后果是導致許多學生在英語語言的理解力、共情力、判斷力和創造力上停頓不前。語言當作工具的結果是抹殺了語言的本質特征,將其擱置在一個外部的、局部的、淺層次的位置來看待。索緒爾指出,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即言語聲音為能指,概念為所指,無論是能指和所指的性質還是它們的關系性質都是不確定的,不存在天然的或內在的關系。[3]語言的使用不可以視為一個命名過程,而是要依賴于一個社會符號與意義的關系體系,這個體系就是文化語境。韓禮德認為,把語言當作社會行為來理解關系到對社會結構的理解,也關系到對語言的理解。他指出,“語言是現在這個樣子,原因就是它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并且行為意義的結構有助于我們洞察語言的社會基礎”[4]。語言不能僅僅是一種工具,英語學習并非簡單地復制或復讀語言,除了交際功能外,語言還具有強大的社會化力量,是影響人個性成長的重要因素。薩丕爾指出,語言會影響到人格特征。[5]語言學習是一種對文化的不斷接受和自我創造,并在學習過程中形成個人的世界觀。對此,洪堡特說道:“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人從自身中創造出語言,而通過同一種行為,他也把自己束縛在語言之中。每一種語言都在它所隸屬的民族周圍設下一道樊籬,一個人只有跨過另一種語言的樊籬進入其內,才有可能擺脫母語樊籬的約束。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說,學會一種外語就意味著在業已形成的世界觀領域里贏得一個新的立足點。”[6]語言工具論遮蔽了語言所具有的建構的功能。話語分析學者詹姆斯•保羅•吉指出,語言的建構功能無時無處不在,人們“可以用語言來使某種符號系統與某種知識和信仰形式在特定情境中建立相關或不相關、形成優勢或劣勢,也就是為一個符號系統或知識建立高于另一個符號系統或知識的優先權和威望。”
人們使用語言陳述時即在建構“事實”,這個事實是需要我們以判斷力去甄別的。當人們僅僅力圖理解一個現象,或者是進行譴責、合理化等不自覺的活動時,建構便產生了。“所有的語言,即使是做出簡單描述的語言,都是建構性的,會產生后果的……話語是走向行動、觀念和具體事件的毫不含糊的通道。”[8]若不基于一定的文化知識,對詞語意義建構的理解容易產生偏差,就不利于以英語進行的有目的的交往活動。因此,英語學習中要強化英語語言的文化意識。真正的英語人才要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所以文化學習的過程應該是從文化知識開始培養文化意識,達到對西方文化語境中人們如何用話語建構“事實”的深入理解,這也是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或科技方面的對話或批判的起點。這要求我們要調整英語學習的文化接受態度,克服過分偏重英語語言形式而忽略文化功能的弊病。英語教師應該找尋適當的教學方式方法引導學習者關注英語學習中的西方文化意識問題,注意語言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為了理解語言,我們就要研究社會結構是如何體現的:價值是如何傳遞的,角色是如何界定的以及行為模式是如何顯現的。”[9]課本教材、媒體文章等特定的語言言說方式能夠產生重大的意識形態后果,薩義德等后殖民主義批判學者對英美小說在形成帝國主義態度、參照系和生活經驗方面的分析給我們以重要啟示。[10]這一點我們因受工具主義學習觀的影響而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外語學習者在這方面的判斷力也普遍不足。工具可以被看作價值無涉的,而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是互體性的,一種語言就是一種文化,文化通過語言體現出來。把語言當作工具意味著遮蔽了語言具有的文化色彩。我們的英語學習具有促進學習者人文素質發展的意義,也具有對英美文化理解和對話的責任。在英語學習上,需要思考我們倡導什么,反對什么,怎樣與中國文化的學習形成合力,提升文化學習的境界,進而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英語學習也必須實現由工具論向文化論的轉變。
三、英語學習由語法知識向語言意義體系理解轉變
心理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是基因組中的內置物,語言學習者僅僅通過使用構成語法的各種生成性規則和轉換性規則就能創造性地構造出無窮的句子。這為眾多外語學習者出現的語言使用的高度刻板化所證否。“人類語言溝通中所謂的語法,指的是語言結構的約定俗成和語言結構的文化傳遞。”試圖僅通過語法知識就學會語言是不可能的。語言是社會的,是歷史的。英語語言的交際活動離不開文化,任何有意義的語言交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發生的。文化可以讓人更好地理解語言的含義,決定語言要表現的內容,因此是英語學習的基礎,也是解決英語學習問題的良好途徑。比如對生疏詞匯、復雜句式所形成的閱讀障礙,如果能憑借語境含義進行宏觀解讀,則能夠彌補語言語法含義的缺失。語言學家伯納德•科姆里指出,“人類語言仍保持這樣的狀態,即它們確實有句法,許多語言還確實有不能轉化為基本語義或語用關系的語法關系……我們認為只有結合語義角色和語用角色才能全面了解各種語法關系”。英語語言的理解不僅靠詞匯、語法本身,根本上要依賴一定的語言的文化符號體系。在外語文本閱讀教學中,應該充分認識到語言符號體系的重要性,有效地提高文本理解能力,讓英語學習進入意義體系層面,最終使學習者在判斷力、理解力上得到提升。一種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使用該語言的人們一直在這套符號系統中陳述知識和信仰。如最早在法語中產生的英文“elite”這個詞,指的是法國的特權階層,具有貶義屬性;后來被吸收進英語中,則成為一個褒義詞,指社會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并傳播到全世界,中文將它翻譯為“精英”。
如果我們理解法國大革命前后法國激進知識分子和英國保守的知識階層對大革命的不同態度,就能夠明白為什么會有這種語言變異。把語言作為符號體系來理解,也就是說理解一個概念必須把它放置那個符號意義系統中。薩丕爾指出,“符號表達了能量的濃縮,符號本身形式意義與它所代表的實際意義相比顯得微乎其微。在一張紙上隨手畫幾筆,可以起到簡單的裝飾作用,但同樣是幾筆,在某個社會里就會被解讀為‘謀殺’或‘上帝’”。任何書面或口語所表達的都會有“言不盡意”的感覺,伽達默爾對此解釋為,“存在著一種詞語的辯證法,它給每一個詞語都配備了一種內在的多重性范圍:每個詞語都像是從一個中心迸出并與整體相聯系,而只有通過這種關聯詞語才成其為詞語。每一個詞語都使它所附屬的語言整體發生共鳴,并作為它的基礎的世界觀整體顯現出來。因此每一個詞語作為當下發生的事件都在自身中帶著未說出來的成分,詞語則同這種未說出來的成分具有答復和暗示的關系。一切人類講話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為在講話中存在著意義的展開和解釋的無限性”。學習母語時,語言符號的意義體系不是通過知識形式來傳授,而是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通過交際行為獲得的。學習英語時,就要利用已掌握的語言文化來對英語語言符號作更深層的理解。英語學習需要從英語知識入手,沒有英語知識的系統學習,就沒有英語文化的完整體系。
英語知識的學習絕不是英語學習的終極目的,英語學習要通過對英語語言知識輸入和傳播的方式,使得英語學習圍繞英語知識形成一定的體系,培養英語文化意識,領悟英語語言內涵,了解英語國家文化氣質,將英語語言的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融匯為一種完整的意義符號系統,以幫助學習者洞察英語國家特定的社會語境。語言知識的輸入和傳播,是初級的,是英語學習的基礎,是整體英語學習的第一步。英語學習不能只偏重書面知識,英語教學也不能停留于句法、概念及語篇等知識,學習者要理解語言的符號意義,以此了解英語國家人們普遍具有的思維模式。四、英語學習由單一課堂觀向復合課堂觀轉變現代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科技變革為英語學習帶來了文化語境上的革命性變化,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廣泛地發生交互作用,何為學習以及如何學習也需要隨之調適。傳統的學習依賴于制度化的、組織化的課堂學習,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者不自覺地將教師看作知識權威,對知識權威的刻板化認識阻礙了學習者的質疑與探索精神。在單一課堂觀下,學習者過多地依賴于課本以及由教師提供的資源,顯然,這種語言學習資源觀是狹隘的。在互聯網科技普遍使用的條件下,很多知識和探索知識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在網絡世界中查詢、交流和檢驗,這使得教學由單向知識傳授向多維信息互動傳播轉變。利用互聯網社交工具也可以建立共同聯系的群體,促進相互學習。通過網絡,學習者可以利用其他國家的多媒體、原版書籍、英文報紙、雜志、歌曲等輔助手段來彌補單一課堂教學中英語文化語境的不足。就學習者而言,學習內容更加豐富,視野更加開闊,思維更加靈活。當下借助網絡能便利地實現翻轉課堂。
薩爾曼•可汗認為,互聯網帶來的教育革命意味著所有人都可借助互聯網獲得一流的教育,通向人的自主性終身學習之路。在這種科技語境下,對學習者而言,存在著由現實課堂和網絡世界交互作用的多重課堂,我們可以稱此種觀念為“復合課堂觀”。在復合課堂觀下,知識的權威不再是被制度和組織所塑造,權威不再是既定的,而是可變的,學習者將減少刻板化的權威認知,質疑精神和創新精神也因此能從自由的氛圍中生發出來。英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實現單一課堂觀向復合課堂觀的轉變,能更有意識地將語言文化學習與現代技術結合,提高英語學習的實效性。多媒體的創設語境優勢,為英語學習者提供了大量真實、生動的語言信息,多層次地呈現英語學習內容,使抽象的語言概念、語法學習與生動的語言語境相結合,促進了學習者思維的發散。學習者需要通過互聯網科技來關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英語學習狀況,樹立全球化英語學習與評價觀念,了解當代世界英語發展的動向。
在全球化時代,英語學習的環境和資源都發生了質的變化,要走向一個廣闊的復合課堂。在這個沒有邊界的大課堂上,當代中國的文化會與不同國家和地區中的英語使用者所帶有的文化價值與意義發生碰撞,學習者需要進行辨別取舍,其個性化的成長就是在對不同價值的辨別取舍中進行的。通過對不同國家和地區人們在英語語言學習上的對比,學習者能獲得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提高,進而能產生文化自覺意識,形成一個上升的良性循環。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發生了極大變化,這要求英語學習者要適應中國當前的文化語境,也要將英語學習放置于西方文化語境中來認識,認識到其語言所負載的文化價值與意義并做出鑒別。中國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和對話有賴于對英語語言及其社會結構的認識,即作為交流使用的英語語言環境和語境的認識。中國文化語境下的英語學習應實現由語言工具論向語言文化論的轉變,由語法知識學習向符號意義理解轉變,由單一課堂觀向復合課堂觀轉變。這種轉變會對跨文化交際的英語學習帶來更多積極的影響,中國的文化也會更具有開放性、多元化、包容性,這對中國的發展進步是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王建勤.第二語言習得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52.
[2]J.格林.喬姆斯基[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2—14.
[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00.
[4][9]韓禮德.語言與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57、61.
[5][14]愛德華•薩丕爾.薩丕爾論語言文化與人格[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337—349、332.
[6]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5—46.
[7]詹姆斯•保羅•吉.話語分析導論:理論與方法[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14.
[8]喬納森•波特,瑪格麗特•韋斯雷爾.話語和社會心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9.
[10]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M].北京:三聯書店,2016.2.
[11]諾姆•喬姆斯基.語言與心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168.
[12]邁克爾•托馬塞洛.人類溝通的起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332.
[13]伯納德•科姆里.語言共性和語言類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73.
[15]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585.
[16]薩爾曼•可汗.翻轉課堂的可汗學院:互聯時代的教育革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序言.
作者:陳了了
- 上一篇:農村幼兒園布局調整原則范文
- 下一篇:多元教學法在神經解剖教學的運用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