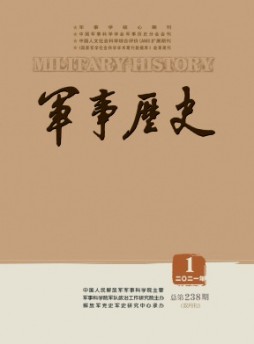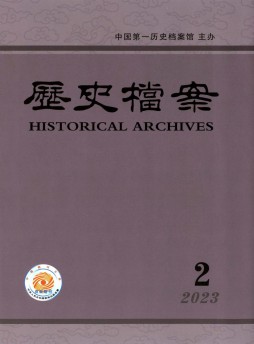歷史文學論文:英美文化的新歷史立場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歷史文學論文:英美文化的新歷史立場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邵胤王麗單位:云南經濟管理職業學院講師
新歷史主義對《黃色的墻紙》評論實踐
通過對古爾曼的《黃色的墻紙》進行分析,采用新歷史主義對該文章進行分析,在文章中為了使故事特征更為突出,在語言使用上比較瘋狂,依靠《黃色的墻紙》敘述人的判斷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在文章中雖沒有描述到她的瘋狂,也沒有提及任何關于她的病情,這個病的表征或許是歇斯底里的,或許是厭倦的。文章中描述了敘述者如何了解她自己的狀況,以及醫生給她的診斷,是神經質,還有些憂郁,或者是一種不嚴重的歇斯底里。
古爾曼發表這個文章的時間是1892年,她的目的是為了否定米切爾治愈她神經質或歇斯底里的努力,他的治療是讓她服從完全的休息,不能有任何工作或刺激。在《黃色的墻紙》中,無名的敘述者不斷秘密地寫作,同時裝作屈服于休息療法,而她的醫生丈夫約翰,則堅持不讓她接見客人,并保證充足的空氣和休息,放棄所有的體力的或智力的勞作。夫妻二人的沖突再現了古爾曼的這段經歷。那么,這是一段有趣的傳記式語境,實際上從這個語境中我們能夠看到在精神病領域對待婦女歇斯底里病癥主要方法上,故事直接參與,并表示了拒絕和不同意。但一種福柯式的分析將指點我們從傳記式語境中移開到文本獨立于作者的作用上,轉移到文本作為瘋狂話語的組成部分上。然而用新歷史主義的方法分析時,吉爾曼的疾病表征不會作為了解的對象,對引起病癥的社會原因較為重視,對檢驗這個病癥發揮作用的話語也重點地考慮。文章故事分析過程中,對一些問題比較重視,首先是在這個文章中小瘋狂和疾病的話語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其次是故事怎樣參與了對待瘋狂和疾病的“普遍經濟”。
在《黃色的墻紙》中敘述者的病情起到了怎樣的效果?文章中她的疾病癥狀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允許我們看到的是敘述者和她的醫生丈夫約翰發生的矛盾。她丈夫在處理很多事時都和她的思路不盡相同。她的愛好寫作,她對事物的懷疑和對世界的迷信,這些內容對于她的醫生丈夫看來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議,那么怪異。如她十分喜歡殖民時期“怪異”的大屋,更相信這是神奇的鬼屋,然而對于她的丈夫來說感覺不可理解,并且“公開地嘲笑所有不能感覺不能看到沒有實在形狀的任何談論”。這也顯示了他們倆的觀點迥然不同,這種觀點的區別使她的意識形態也受到影響,并對她的病情產生一定的影響,也許這種意識上的區別和差異與她的病情有較大內在聯系。
文章還將權力和權威作為故事的重要支撐,將權力相互爭斗,權威認證以一定的方式表現出來,更好地烘托主題。她的兄長也是一名醫生,并且是“高級別”的醫生,她丈夫和她兄長都認為她的病情沒什么真正的嚴重性,應該是輕微的神經抑郁造成的。但這種觀點對于敘述者來說顯然她是不同意的,在對她病癥的診斷方面,她只能根據自己的感受問一個人應該做些什么,而她沒有詳細了解病癥性質的權威,因為沒有權威使得她的觀點和意見只是小范圍的個人觀點。從這篇文章看來,這又是病人的意識被醫生的主觀壓倒,盡管她在治病過程中時常講述自己的困惑、懷疑等感覺,但仍然擺脫不了她是病人,她是醫生的研究對象的身份。從中可以看到權威能使一種控制狀況進入醫學治療實踐。病人的病情為醫學話語所決定,其中病人就成為了主體。醫生從醫學觀點出發認為寫作是她病癥的重要誘導原因,因此在治療時醫生反對她寫作,這使她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進行寫作,否則醫生會強烈反對,這也可使她得病。醫生警告她說寫作時思考可以誘發她的病癥加重,所以她承認她的情況總是使她感覺到糟糕。她也講述她對她丈夫約翰的診斷毫無道理而感到憤怒,并將這一切歸咎于她遭受的“神經質狀態”。她兄長和她丈夫對她的診斷被她接受,她處于反對他們理性的“不理智”狀態。因此,她接受了醫學話語為她決定的病態狀況,她是心理方面的不理智者,是行動方面的不正常者,是處理事情的瘋狂者,并且需要對她治療,需要將她糾正到重新回到醫學話語中所描述的理智和健康狀態。
以這種觀點看來,醫學話語完全施加給她,醫生依照醫學話語運用各種控制技術來對她進行治療,這種治療的主要方案就是監禁。因此,約翰按照這一原則,將妻子有意或無意地放置在屋子中。這一治療原則其實就是將她作為一個真正的病人,只能夠被醫生監禁,她也不得不臣服于監禁后的限制和觀察。《黃色的墻紙》產生了西方理性話語的人文主體,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創造人物,從而創作了她白己,在創作過程中,她雖然解放了自己,但也監禁了自己。在創作過程中,她能夠認識自己,也能夠認識文中人物的她自己,這就產生出矛盾的一面。作者是自由的,其自己也可以認為是自由的,但是這對自己了解的基礎上她卻屈從于被控制和被監禁,在她被監禁的同時她被解放了,在她靠自己的時候她卻是瘋狂的。在這種自由和監禁的矛盾中,在理智和瘋狂的博弈中,人的主體就此產生。自由只是靠某個地方、某種形式的監禁的存在才得到保證。要想體驗自由和理智,必須遏制瘋狂的發展,通過一定范圍的話語和意識形態決定和制約,主體才能真正地刻畫和塑造她自己的個性。只有通過抵抗權力,人的主體才能被遞呈到權力的手中。因為對新歷史學家而言,抵抗、自由、人文主義這些符號都是權力、權威和臣服的標志和蹤跡。
自我塑造在新歷史主義背景下的再現
威廉•福克納等作家的文本充滿了自我塑造,不再僅是英雄的頌歌,這種明顯的歷史意識釋放了個人歷史。福克納的小說發生在“南方”,嚴格意義上說,南方只是他的寫作方法,他經常把玩事實,把它們糅合、增刪、修改,賦予其完全不同于任何事實狀態的新貌,從而創造出一個具有獨特面貌的藝術世界,塑造了一個南方時代。回憶無論是對個人還是、體都成了南方社會身份的基本要素,集體回憶、討論、協商、分享甚至沖突以建立一個公認的過去。自我塑造是一種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識和話語,它作為一種物質實踐、特定的社會儀式和文化機構生產形式出現。沃爾夫筆下的《天使,望故鄉》主人公尤金在他這樣的家族生長、成長,他的價值、信仰和習俗也受到了當地人的影響,他對自己的第一次認識來源于和阿特茵小鎮的集體的認同,“聯邦之間那場內戰”實際上是尤金父母家常便飯式的爭吵的一個隱喻,尤金的困擾何嘗不是威廉•福克納等作家的困擾。當作家意識到時間的重復能帶來生活的差異性時,重復就有對時間的結構力量,作家也想通過“歷史回憶傳遞過去的知識”。
于是作者筆下的人物也不堪歷史時間的重負成為過去的一個回聲,成為過去再現時空的投影,但并不完全與前者相同。時間是每個人一生的宿敵,如福克納筆下的昆丁、班古、達爾等,沃倫筆下的杰克及他的父親,這些作者筆下的人物隨著時間迷失成為瘋子或白癡;福克納的金魚眼,斯諾普、沃爾夫的甘德太太、沃倫的威利先生、達利先生等這些人物可能是受現代工商業文明塑造,服從機械時間異化的人;而福克納的艾克、沃倫的馬斯敦等可能是勇于承認過去的罪惡,力圖斬斷與過去的聯系而獲得新生的人。
以上對新歷史主義的簡單介紹,然后用新歷史主義對吉爾曼的《黃色的墻紙》進行分析,并設想了在19世紀末期美國文學作品關于瘋狂的話語中吉爾曼的文章可能占據的位置,這種解讀的用處主要在于觀察在一種通過特定的文化或部署的話語中,文本如何作用。《黃色的墻紙》中敘述者作為病人與醫生之間的沖突,從新歷史主義者的角度對病人和醫學話語之間的矛盾進行觀察分析,分析與文中故事相關的社會實踐和相關話語,解析新歷史主義視角下的文學作品,因此,這種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使一個文學文本的意識形態作用變得清晰可見,通過歷史再現生產和塑造人物形象,繼而又生產和塑造了時代。
擴展閱讀
- 1歷史形象歷史題材
- 2歷史
- 3少先隊歷史
- 4憲政歷史
- 5東歐演變歷史
- 6歐洲擴張歷史思索
- 7文化歷史論文:古代的音樂文化歷史
- 8唯物史觀歷史命運
- 9音樂史料歷史
- 10鄉土歷史資源在歷史教學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