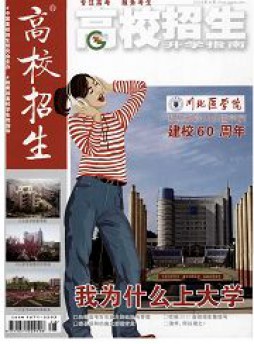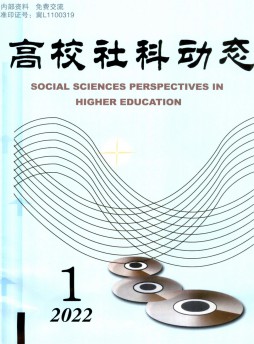高校行政化合法性制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高校行政化合法性制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1]當海德格爾借用荷爾德林這詩句時,他旨在表明正是陷入危險之中才使拯救成為可能。靠行政主義一路推動而來到全球化圖景中的中國大學已于21世紀的頭十年里進一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已使中國高等教育從“高等教育弱國”邁向了“高等教育大國”,[2]但文化上并沒取得與大國相匹配的地位,因為新中國大學恰是在行政主義的體制下發展的。當前國家居于頂層所做的最大制度設計是“去行政化”。本文基于組織社會學層面剖析“去行政化”改革對大學合法性復歸的意蘊。
一、知識品性與大學合法性的邏輯
(一)知識的品性布魯貝克認為,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學基礎有“認識論與政治論”[3]13兩種。認識論是對知識的探究,政治論是通過探究與傳播知識為國家服務。這一認識被大多數學者所認同。無疑,不管是認識論還是政治論,其邏輯起點都指向于“知識”,大學的立身之本就是知識探究和傳授,大學的價值取向必須指向或能夠保護大學的這一使命。如此,大學才具有合法性。易言之,知識探究與傳授是大學具有合法性的根本基礎。這就需要追問:大學存在所涉及的知識品性是什么?大學所涉及的知識是高深知識或是高深學問,這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常識性知識,它具有專門化、系統化與高深性的特質。這些特質決定了大學里從事知識探究人員的工作性質。對知識的探究、傳播與應用要求外部干預最小化。“為保證知識的準確性和正當性,學者的活動必須只服從于真理的標準,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壓力,如教會、國家或經濟利益的影響。”[3]42其實,如果單是從知識探究的角度出發,外界的干預應該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旦外界實施干預,就會影響大學對高深知識的探究,就會影響大學知識探究的目的,大學的知識探究只為真理而真理,大學是以真理至上的,因為“知識本身即為目的。”[4]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學的目的或目標就是自由性與智慧性地去探索知識真理,此外,便沒有其他目的或目標。所以,大學價值取向的一個最核心命題是:自由。正如學者指出[5]:知識的品性是自由———不管是社會知識還是自然知識,其意蘊都是自由,認識社會是為了自由,探索自然是為了自由,而探索知識的過程本身更需要自由。同樣,知識的傳授也離不開自由,因為自由不僅包含內容的自由還包含形式的自由,沒有自由的知識傳授就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的知識。大學只要具備了“自由”這個核心價值取向,大學也就具有了大學本應有的性格,即探索知識與傳授知識體現出來的“自足性、自反性、絕對性、無限性、批判性、藝術性和超俗性”,這就是大學的哲學性格,“中國的大學哲學性格應在‘自由與獨立’的前提下生成。”因為,“大學缺什么都不是特別重要,唯獨在缺了自由與獨立的時候,它絕不會再有哲學性格,從而它也就等于一無所有。”[6]可見,大學合法性的力量是自由與獨立探索高深知識的邏輯,它與外部社會控制之間博弈的結果決定著大學的合法性樣態。
(二)大學合法性的邏輯“知識的品性決定了大學的品性。大學品性即指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組織所呈現出來的品質和性狀。這是大學區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自我內在規定性,是大學得以正常運轉與永世傳承的組織基因。”[7]24作為社會組織的大學的合法性基礎在于知識賦予的“自由”。“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真理是達到自由的重要渠道。只有依賴自由的活動,才能產生真正的知識。”[8]如果大學不能保障知識探索與傳授的自由,以及探索與傳授自由的知識所必需的共同體自治,大學就不具有合法性。何謂大學合法性?組織社會學理論認為,“組織內權威結構的尊嚴性的確立就是其合法性。”[9]尊嚴性的確立是指其權威結構得到承認、支持與服從。這一合法性所指涉的不僅是一個社會組織的存在狀態,在更本質層面上,它還凸顯了組織的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社會認同是其外部合法性(下文簡稱“外”),自我認同是其內部合法性(下文簡稱“內”),一個社會組織的合法性是這兩者的統一。這是組織得以生存的邏輯基礎。借鑒組織社會學理論,“大學合法性就是外部社會和內部成員對大學組織存在的認同及接受狀態。”[7]21大學合法性也是內外合法性的統一。“內”是指組織成員對大學組織的承認和接受,即大學組織成員只要秉承和捍衛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這個合法性根基,就可獲得內部合法性,大學就會得到組織成員的認同接受,大學自身就會獲得發展與成功。“外”是指社會對大學組織的承認和接受,即大學秉承、踐行與堅守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的同時,可以印證大學外部的意識形態的價值正義性,就可獲得外部合法性。兩者關系是:“內”決定“外”,“外”不能決定“內”。“在大學發展中,內部合法性更重于外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決定著社會的支持與資源的獲取,內部合法性決定著組織成員的忠誠度,但是內部合法性的不足會使大學透支其外部合法性。”[7]37-38“內”高于并決定“外”的邏輯決定了知識與自由的關系即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這一權利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當性。“正當與自由兩者不能單獨構成權利。正當的要求只有通過自由的行為才能使某種權利成為權利事實。”[10]大學學術自由與自治這一權利之所以成為大學的權力,是它同時具備了正當性與自由性,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既是大學的價值規定,又是大學的實施規定。當然,大學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涵義雖然必須有自由的性格與行為,但并不意味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僅僅是能夠做應該做的事,而不被強迫去做不該做的事。”[11]學術自由還得遵循學術規律的要求,這不僅是學術自由的本體屬性,也暗合了一種基于學術自由正當性基礎之上的謀求學術自由“合法性”的過程,這為大學學術自由的制度與法律保障確立了思想與法理學依據。只有滿足了學術自由的正當性,大學才能真正發揮或釋放其功能。組織社會學研究認為,“內”才是其組織合法性的核心。“外”如果沒有“內”做保證,它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這樣的組織事實上是時刻都處于合法性危機之中的。而以此來審視當前中國大學的合法性邏輯,卻是“外”重于“內”,“外”決定“內”的顛倒邏輯。
二、中國大學的合法性危機
(一)大學合法性危機的產生大學內外合法性邏輯的顛倒產生于新中國時期“國家權力總體性地滲透和擴散到全社會各個組織”[12]的“總體性社會”模式中。在這個社會結構分化程度相當低的一體化社會,“國家對社會所有資源實行全面掌控,政治權力滲透于各個領域,整個社會生活的運作呈現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特征。”[13]如此社會結構里的大學,“沒有獨立的地位,大學是政府履行教育職能的實體組織,大學的教育活動被視為政府依據憲法規定行使教育權力的一部分。政治與學術合為一體,政府與大學之間沒有權力的分界,政府直接控制大學內部事務。”[14]“政府與大學之間仍然是一種行政模式化的縱向聯系或直線等級式的隸屬關系而非契約性的法制關系。”[15]這導致大學合法性邏輯是“外”決定著“內”,“外”壓制著“內”,“外”對“內”的干預達到最大化。殊不知,“政府干預大學止于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16]的有限性原則。大學自由探索知識的品性就此喪失,其合法性危機就此產生,難以“成為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最高文化機構、最高的精神象牙塔與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區。”[17]
(二)大學合法性危機的內涵大學合法性邏輯的顛倒導致外部強權知識體制源源不斷地輸入大學,大學的知識構成完全成了一種指向性很明確的設計和權力安排,知識在此已不是一種“先賦”的客觀事實,而是“人為”的通過權力將知識予以社會合法化建構,大學知識的“文化資本”就如同經濟資本的生產分配一樣,為權力擁有者及反映其意義的意識形態所操控。易言之,“知識不是中立、客觀的知識,也不是絕對的真理,而是意識形態滲透下的價值負載,是政府行政權力者精心構建的‘意義之網’和‘價值之網’”。[18]外部強權知識控制著大學內部知識生產,不僅使大學的知識來源無法獲得解釋,而且使大學內外都很難拿出一套符合世界一流大學發展規律的并具有足夠包容力和公共性的大學發展方案,“從而使從學術渠道對大學的發展變得異常艱難。”[19]47最終使大學自身存在的理由都將成為疑問。“外”決定“內”的顛倒合法性邏輯導致大學合法性危機具體變現為:行政主義話語、功利主義話語、科學技術主義話語作為強勢話語早已深入介入大學內部。“教育資源配置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門,從校長任免、經費撥付、項目審批,到學位授予權設定、專業課程設置、招生計劃名額等都由政府掌控。”[20]外部不尊重大學組織權威的尊嚴,大學內部對自身組織尊嚴的認同與接受性不足,導致大學內部的知識生產與外部權力媾和,與金錢等資源進行交換(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內部合法性不足會使大學透支其外部合法性),知識成了權力合法性的辯護,內部合法性反倒服務于外部合法性,當外部合法性要利用“知識”來為自己辯護時,知識本身的合法性也被消耗。進而導致大學知識生產的充分學術自由和按照各自學科高深知識發展的內在邏輯去進行自由探究的自治權力遭到破壞,大學內部合法性喪失了,其“知識生產越來越零碎、主觀,知識生產者們更關注的是直接的功利結果,不關心知識生產的完善性與一致性。”[21]這種顛倒了大學合法性的邏輯,違背了其自由探索的知識品性所產生的大學合法性危機是一種內在意義上的文化危機。
三、“去行政化”對大學合法性危機的拯救
(一)“去行政化”與大學內外合法性之間的關系如前所述,有了內部合法性對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這一合法性根基的秉承與堅守,大學組織尊嚴自然就得到了組織成員的認同并接受,認同與接受背后的合力就能推動大學有效發展,進而印證大學意識形態的價值正義性與正當性,如此,其外部合法性也就獲得了。而如何理順這一內外邏輯,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與世界一流大學中,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借此,“去行政化”的制度設計是對這個問題的審視與反思所作出的安排,既決定大學的內部合法性,又影響大學的外部合法性。因此,“去行政化”的價值基礎必須呈現出大學組織應有的品性和特質,從而與任何一個大學組織成員之于大學的個體理性或心理期盼相吻合,這就必然肯定了大學內部合法性高于外部合法性的位序。同時,這種呈現也能與社會期盼相一致,大學也就獲得了外部支持與承認,進而獲取更多的外部合法性。可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既是大學內部合法性的根基,也是外部合法性的源頭。大學內部合法性高于并決定著外部合法性。“去行政化”制度設計的本義必須圍繞這一邏輯關系來實施。
(二)“去行政化”是對合法性危機的制度外拯救“去行政化”的制度設計,的確給當代中國大學的內外合法性提出了最嚴肅的制度挑戰。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不管是對大學的過度行政還是當前的“去行政化”,都是在大學本身之外的制度設計,“去行政化”一方面證明中國政府對大學合法性危機有了清晰認識,一方面是對危機進行拯救的訴求,這一危機是在總體性社會里中國政府從大學外部造成的,這種訴求也只能是中國政府從大學外部居于權力主導下進行,這種制度設計本身的權能使這種大學發展的規則成為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權力事件”,而非“知識權力事件”。為此,“去行政化”對大學合法性危機的拯救首先是“制度外拯救”,在拯救中必須注意的是:制定外部制度的中國政府怎樣激勵大學主體實施既定的外部制度?而激勵大學主體實施既定外部制度的機制又是如何得到構建并落實的?顯然,單純的制度外部來源不能說明制度的實施機制和制度的效能。在切實的大學發展中,“一項制度是否能夠得到執行和執行的持續性,取決于這項制度的規范對象是否具有主動遵守這一制度的內在秉性,而不取決于制度制定者的主觀愿望。”[22]“外部制度設計的效度取決于外部制度是否與內部演展出來的制度互補。”[23]因為,“在中國,如果在政府對大學進行放權的同時沒有隨之進行強有力的制度變革和文化建設,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和辦學活力就不會自動增長。”[24]可見,中國政府須做到由外而內的制度設計與大學系統內部制度執行的有機銜接。
(三)“去行政化”對大學行政化管理的揚棄外部合法性不能決定內部合法性,政府對大學的宏觀監督不能演變為具體的操控與干預大學的知識生產。“知識有知識的規律,管理有管理的標準。知識追求自由,管理服從規范。因此,對知識的生產最好的管理就是讓它合乎知識的品性。所以,對于大學,最好是別問政府做了什么,而應該看它沒做什么。政府對大學最大的作用就是服務。”[7]156“國家絕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聯系起來,卻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他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利益服務,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發揮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遠非政府的近前部署所能預料的。”[25]因此,“去行政化”是在不完全拋棄行政制度中的科學合理管理成分與不簡單粗暴地視為對大學傳統管理的斷裂的同時,要形成政府、社會與大學之間的適度張力,并以法律的形式將這種張力固化以保證大學的適度自由,在尊重大學知識生產合法性管理范式的轉變式延伸基礎上,重建一種適合中國大學建設與發展的優先性制度管理體系,對大學管理以及學術的所有外來干預,都應限制在這些法律規定的范圍里。只有這樣,“去行政化”之路才可能獲取真正意義上的突破。前提就是中國政府自身在大學管理問題上不但要有自我開放、反省、批判、調整的能力,而且也要從大學外部全面創造能供“去行政化”的充足資源與完整條件。當然,“去行政化”的提出僅是一個從制度外拯救大學合法性危機的開端,這已流露出中國政府對大學發展目標的設計,已從制度安排上開始思考大學原有的管理。相信中國政府具有從目標到手段與方式的全面謀劃能力引發大學治理結構的深刻變化。通過自上而下與由外而內優先進行制度重構,以消除對作為知識生產者的大學的過度行政管制和邏輯困擾,促使大學直面真實的教育需求和市場競爭,從而內生出一種自由自主育人與知識生產的持續效應,努力“打造一種作為價值共同體與學術共生體的特色中國大學。”[19]54
(四)“去行政化”促使大學合法性的復歸“去行政化”指向的是對大學行政管理真理維度的尋覓,是新中國大學60多年本身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在中國政府由外到內引領大學對自身存在的邏輯正當性的反思與審視,是一個劃時代的政治權力事件。新中國以來,“在政府庇護與控制之下的中國大學缺乏對大學自身存在的邏輯正當性的哲學反思與精神審視。對自身合法性基礎的模糊認可與建立不僅使大學對自身存在的邏輯正當性理解不得要領,進而使發展緩慢艱難,而且加劇了它對政府的妥協與依賴。”[7]157如此,就連在最表層的功能上也導致大學喪失了一個社會組織生存所必須的不可替代性。大學與政府有關系,但不等于大學就要行政化。“去行政化”已釋放信號———引領全社會尊重大學,尊重大學學術自由,尊重大學對社會的引領職能,真正樹立大學在國家與民族中的最高文化精神機構的權威地位。內部合法性高于外部合法性的邏輯決定了大學不需要太多的外部行政化色彩,“去行政化”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尋覓大學自由生產知識的普遍真理性,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真正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即在政府社會認同與支持大學尊嚴下,進而從外部制度設計、經費保障等方面全面充分地為大學內部合法性服務,依法做到管辦分離,保障大學嚴絲合縫地社會化生存以及捍衛自身良性發展且充滿成熟理性價值關懷的一套結構功能規則體系。[26]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是簡單取消行政級別,而是規范行政權力,督促權力恪盡職責,恪守邊界,扭轉顛倒的大學合法性邏輯。同時,在學術領域建立一套獨立于行政權力之外的評價體系,讓學術按照自己的規律去運作。”[27]如是,“去行政化”才能真正成為還原大學對自由知識探索的品性與復歸大學合法性的制度設計。“去行政化”是一場持久戰,“教育變革是一場深刻的、更加持久的變革,最為重要的就是‘重塑’學校文化。否則變革就會膚淺和不持久。”[28]復歸大學合法性邏輯需要中國政府切實具體地搞清楚“什么是行政化管理模式,否則去行政化很難有實質意義”[29],需要中國政府進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去行政化”的劃時代意義不是單一的,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共同構建的。變革要時間,如果我們期望符合現代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國大學的運作體制能迅速地形成并在形成后不久即產生顯著效果,是不現實的。期待在中國政府對大學進行由外而內的制度拯救中,大學能有機會“構建一個可持續的機構。”[30]中國政府對此必須一貫地、持之以恒地、全面地予以投入與部署。“去行政化”一旦把握了大學合法性的內在展演邏輯,就能從根本上抓住重建大學合法性的根本路徑。大學一旦真正成為知識生產與學術自由的主體,并積極主動地而不是被動地“引領社會”,相信中國大學會發生變化,大學的創新意識與創新效果相信也會逐步得到培養并形成。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高校班級管理創新案例
- 2高校管理論文
- 3高校會計論文
- 4高校德育的特點
- 5高校大學生法制教育
- 6高校專業論文
- 7高校交通安全教育
- 8高校藝術設計教學論文
- 9高校匯報
- 10高校教育理論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