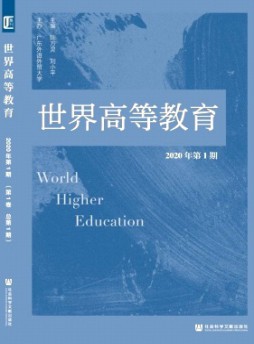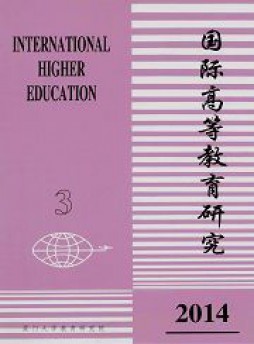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潘先生不僅始終立足本土,以開放的姿態(tài)、謙虛的態(tài)度,主動借鑒地引進適合中國國情的一切先進成果,他還身體力行,大力推廣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潘先生認為,國際化的題中之意還在于中國研究者參與世界高等教育事務的話語權(quán)。通過平等對話、溝通理解,不僅介紹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問題,而且探討世界高等教育的規(guī)律與趨勢。可見,走出去———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潘先生先后到過日本、菲律賓、泰國、英國、新加坡、尼泊爾、科威特、美國、俄羅斯、荷蘭、挪威、立陶宛等多個國家以及港澳臺地區(qū),將中國的高等教育成果積極向境外推廣,促進高等教育的學術(shù)交流。他特別注重在高等教育研究領域開展合作,并與人合作編了一些英文高等教育著作,如《Legislation:TheGuaranteeofDevelopmentofPrivateHigherEdu-cation》(《PrivateHigherEducationinAsiaandthePacific》,UNESCO,PROAPBamkok,1996)、《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StudyinChina》(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1997)、《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Past,PresentandProspect,Chance-TransformationinEducation》(Syd-ney:TheUniversityofSydneyPublishingHouse,2002)等。這些英文著作在溝通中外高等教育學術(shù)理解、推廣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方面發(fā)揮了積極的助力作用。此外,潘先生還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應積極參與國際高等教育課題研究,促進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交流和學術(shù)的普及。正是由于潘先生不斷踐行著其“走出去”的國際化理念,國外學者開始關注潘先生及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的許美德、美國的白杰瑞、挪威的阿里•謝沃。其中,挪威學者阿里•謝沃先生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創(chuàng)始人》(PanMaoyuan:AFoundingFatherofChineseHighEducationResearch)于2005年7月在挪威科技大學教育學院正式出版,該書集中介紹了潘懋元先生創(chuàng)建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建設歷程并展示了中國高等教育在21世紀的發(fā)展和研究趨勢。這對于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理念走向世界意義重大。2007年,國際權(quán)威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shù)據(jù)庫(SSCI)收錄的、在美國出版的國際著名學術(shù)刊物《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在第3期發(fā)表了潘懋元先生7篇學術(shù)論文。這7篇論文構(gòu)成一個專輯,題為“潘懋元和中國高等教育”,涵蓋了潘先生創(chuàng)建高等教育學科和各個時期關于中國高等教育問題最主要的學術(shù)思想。該專輯的內(nèi)容主要有“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學科芻議”“教育基本規(guī)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與實踐中的運用”“走向21世紀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轉(zhuǎn)變”“關于民辦高等教育體制的探討”“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之路”等。據(jù)悉,以專輯的形式在《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上出版?zhèn)€人系列論文還是史無前例的。潘先生系列論文的國際發(fā)表,表明了世界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高度認可,對進一步擴大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世界影響意義深遠。
二、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的特點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重要倡導者與踐行者,潘先生在“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如何實現(xiàn)”這一問題上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本土意識、廣闊的國際視閾以及高度的責任擔當,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國際化道路。
(一)強烈的本土意識,主動借鑒而非被動依附“如何引”是“引進來”的關鍵所在。在引進高等教育先進理論成果時,潘先生是“主動借鑒”地引進而非“被動依附”地引進。選擇借鑒與選擇依附,二者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借鑒是在立足本土的基礎上,以他國為鏡,對照自己,吸取有益的經(jīng)驗;而依附是不顧本國具體國情,對發(fā)達國家的先進成果照單全收、盲目套用現(xiàn)成模式。可見,借鑒的立足點是“本我”,而依附的立足點是“他者”。不少研究者不顧具體國情,迷失于“與國際化接軌”的口號,認為凡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方法就是正確的、科學的,自覺不自覺地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的研究理論,導致研究成果缺乏原創(chuàng)性與創(chuàng)新性,結(jié)果出現(xiàn)“越‘國際化’‘現(xiàn)代化’也越‘邊緣化’的情形”。潘先生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歷史、特色、國際地位以及未來的發(fā)展趨勢有客觀的認識與理性的評價,始終在立足本土的基礎上,秉承“有沒有借鑒之處”與“可不可以借鑒”的原則,實現(xiàn)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有沒有借鑒之處”解決的是國外研究成果先進與否的問題;而“可不可以借鑒”處理的是與具體國情適合與否的問題。任何國家的高等教育研究都受其文化傳統(tǒng)、歷史條件、價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其高等教育的理論成果在當時當?shù)鼗蛟S具有成功的解釋效力,但應用于別國別時則可能出現(xiàn)理論誤導實踐的情況。因此,“拿來主義”“生搬硬套”不可能是真正地“引進來”,只能是陷入“某國化”的被動依附與寄生局面。
(二)廣闊的國際視閾,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并重“從哪引”和“走向哪”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國際視閾的廣度,同時也影響著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發(fā)展深度。潘先生不僅從發(fā)達國家引進先進成果,更關注發(fā)展中國家,是“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并重”地“引進來”,同時也是“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并重”地“走出去”。從整體上講,發(fā)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無論在研究成果還是辦學實踐都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優(yōu)越感。美國著名學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就曾指出,美國高等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范例。換言之,美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模式與經(jīng)驗是最值得借鑒的。這種論斷難免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視閾產(chǎn)生誤導———盲目排斥對非美國或非發(fā)達國家的研究。但是,潘先生并不迷信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圣經(jīng)”,其研究視野沒有僅僅局限于發(fā)達國家,而是從一開始就關注、研究發(fā)展中國家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過程、成功經(jīng)驗以及失敗教訓。他充分打開國際化的研究視野,海納百川、博采眾長,不僅從發(fā)展中國家“引進”,主動學習借鑒,同時還“走向”發(fā)展中國家,將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而廣之、互通有無。可見,潘先生跳出了“發(fā)展中到發(fā)達”的單線學習借鑒,變?yōu)椤鞍l(fā)展中到發(fā)達”“發(fā)展中到發(fā)展中”的多線學習交流,由“單向引進”向“雙向交流”發(fā)展。
(三)高度的責任擔當,自信力與使命感兼具“走出去”的目的是讓世界了解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進展與成果,并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國學者應有的貢獻。“能否走出”以及“走出去的程度”與高等教育研究者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力與使命感密切相關。信心缺失,難以“走出去”,即使勉強“走出去”,也難以“走遠”。當“學科取向”的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遭遇“領域取向”的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時,部分研究者自覺本國高等教育理論成果“土氣”,缺乏“走出去”的信心與勇氣,不敢與國際高等教育研究同行一較高下,影響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國際化進程。潘先生不僅懷揣著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堅定信心,同時還秉承著將其推而廣之的使命意識,通過編著高等教育英文著作,在國際著名學術(shù)期刊上等形式,身體力行地積極“走出”,力圖突破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語言文化隔閡,擴大交流途徑,溝通學術(shù)理解,將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國學者更大的貢獻。種種踐行,體現(xiàn)了潘先生“大社會”的責任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分享不應局限于國內(nèi),而應走出國門,實現(xiàn)國內(nèi)外同行的互通與共享。
三、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的啟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愈加遭遇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雙重文化困境。如何正確處理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系是高等教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重要倡導者與踐行者,潘先生在“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如何實現(xiàn)”這一問題上,以強烈的本土意識、廣闊的研究視閾以及高度的責任擔當為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筆者認為,作為高等教育研究的后生晚輩,在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進程中,應注重提升文化自覺、拓展國際視閾以及樹立“走出”信心,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國學者更大的貢獻。無論是“主動借鑒地引進來”,還是“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并重地進出交流”,國際化的出發(fā)點與歸宿均在本土。為了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化進程,同時避免迷失于“與國際化接軌”的口號,高等教育研究者應注重提升文化自覺。因為只有理性認識本國高等教育研究的來龍去脈與演變趨勢,增強對本土文化的認可度與自豪感,才能擺脫心理依附,防范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畸形發(fā)展。其次,研究視野切勿狹隘。“從哪引”“走向哪”不應局限于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只有拓寬研究視野,挖掘高等教育研究的區(qū)域盲點,推陳出新,才能進一步豐富高等教育國際研究成果,充分實現(xiàn)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化。如浙江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受潘先生“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并重”思想的影響,長期關注非洲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不僅借鑒引進,發(fā)展自身,同時還積極走出,推廣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先進成果。筆者認為,限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浩如煙海的情況,不同研究機構(gòu)根據(jù)自身的條件發(fā)展自己的特色區(qū)域研究對豐富高等教育國際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整體上引進多,走出少,這種“交流逆差”挫傷了高等教育研究者“走出去”的信心與勇氣。但是,不邁出第一步就永遠無法走向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應樹立起“走出去”的信心與勇氣,以服務“大社會”的責任為使命,積極與國外學者進行交流切磋、互通有無,在吸收國外先進成果的同時,推介我國高等教育的成功經(jīng)驗,實現(xiàn)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國際交流與共享。
作者:吳薇馬杰單位: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