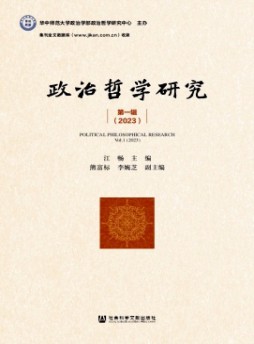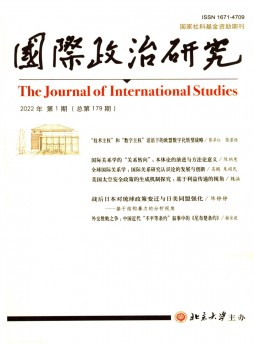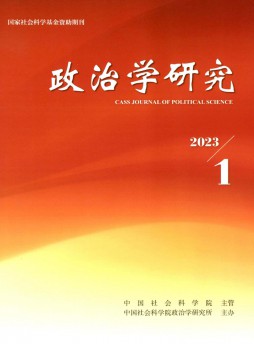政治生態下的“俠”文化剖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治生態下的“俠”文化剖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關于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俠”這一群體,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來自民間,將“俠”視為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漢,千古贊許;而另一種來自官方,將“俠”視為“以武犯禁”的社會蠹蟲,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這兩種對立性評價的表象背后,卻有著深層次的制度根源,即中國傳統社會的君主專制制度。民間對于“俠”的肯定性評價,是源于其在傳統既有的體制和秩序之下無法收獲公正時,對于體制之外的正義力量的期望和認可;而官方對于“俠”的否定性評價則是源于“俠”這種非官方的正義力量嚴重沖擊了專制政體下的統治秩序。
千百年來,“俠”被看做是替天行道的英雄人物,受到無數平民百姓的稱贊與傳誦,他們的英雄事跡永遠是百姓們街談巷議、津津樂道的不朽話題。但站在統治者的立場,韓非子卻給“俠”以完全不同的概念,稱其為“帶私劍”、“以武犯禁”之社會蠹蟲,建議君王將其斬盡殺絕。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似乎都采納了韓非子的這一建議,對“俠”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打擊。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在傳統的法律秩序之下,中國為何會產生“俠”這一文化現象,“俠”與“法”之間又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為什么長期以來,民間社會和官方體制會對“俠”有著如此不同的評價?“俠”文化又折射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怎樣的問題?這一切還得從“俠”這一概念入手。
一、“俠”之概念界定
有關“俠”這一群體的起源,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對于“俠”這一群體最早進行概念界定的是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文中將“游俠”與“私劍”并稱,而帶劍者的特征是“聚徙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2。這里,韓非子概括出了“俠”的兩個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有著高強的本領(以武);二是觸犯現行法律制度(犯禁)。但這其中并沒有對“俠”提出任何道德上的要求,似乎凡能夠以武力觸犯現行法律制度者———無論是替天行道之人還是鼠竊狗偷之輩———都可以歸入“俠”這一群體。直到后世的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才對“俠”這一概念做了較為系統的闡釋:“今游俠,其行為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至此,俠的基本特征也被較為系統地勾勒出來:一是信守然諾(即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俠”者,一定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而絕不會自食其言,半途而廢。如司馬遷筆下的大俠季布,“為氣任俠,有名于楚”(《史記·季布欒布列傳》),其信守然諾,重信重義,以致楚地諺語有云:“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而今日“一諾千金”的成語典故即是出自昔日的這位“俠”者。二是扶危濟困(即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可以說,這是“俠”最為重要的客觀特質,即憑借自身高超的本領和“雖萬千人吾往矣”的勇氣,不懼危難,不避艱險,舍己助人,抱打不平,救人于危難之間,解人于倒懸之急。正如司馬遷所言:“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史記·游俠列傳》),每個人都有遇到危難、束手無策的時候,這種情況即便如大舜、伊尹、姜太公、孔子這樣的仁者圣賢都不可幸免,何況是身處亂世的平民百姓?“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史記·游俠列傳》)。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俠”的身影通常是出現在弱者遭受不公或身陷困頓、走投無路、求助無門之時。三是不求回報(即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可以說,這是“俠”最為重要的主觀特質。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在西方國家也有類似于中國“俠”的群體,即“騎士”。他們也會到處游歷,助人解難和抱打不平,在客觀行為上酷似中國之“俠”。然而,騎士做這一切的終極目的卻是為獲取名譽和財富。而“俠”在舍己助人之后,卻是功成身退,不求回報。例如司馬遷筆下的大俠朱家,為搭救被漢高祖劉邦所通緝的要犯,亦同樣為“俠”者的季布,不惜以身犯險,挺身而出,四處奔走游說,終于救得季布的性命。然而,在獲救的季布被劉邦所賞識,當上了郎中、河東郡守等高官,飛黃騰達之時,朱家卻從此不與季布相見,羞于索取任何報答。因此,司馬遷形容朱家乃是“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史記·游俠列傳》)。信守然諾、扶危濟困和不求回報,司馬遷的這種闡釋相較于韓非子,對“俠”的高尚節操做了較為具體的要求:即“俠”不僅要擁有高強的本領,更要具備高尚的道德,因為離開了道德的規范,“俠”便會淪落成為胡作非為的“匪類”。因此,自司馬遷始,后世對于“俠”的界定便越來越強調其道德要素,從而使“俠”與另一個重要概念相關聯,那就是“義”。“義”乃是儒家最為推崇的概念之一,孔子曾說“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在孔子眼中,“義”既是君子的基本的人格,也是君子的崇高品格,并將“義”作為了君子與小人的基本分界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而后世的孟子,更是將“義”這一概念進一步升華,提出了“舍生取義”。據學者研究,自唐人李德裕始———其在《豪俠論》中說道:“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1]95。———“俠”與“義”這兩個概念便從此捆綁在了一起,“義”也成為了“俠”的價值體系當中最為核心的一環。因此,后世之俠,不論是現實社會中的真實存在,還是文人墨客筆下的虛構刻畫,都會嚴守義利正邪之分,正所謂“行俠仗義”。易中天先生說:“有了‘義’,也就有了‘俠’。俠就是義的實現。所謂‘行俠仗義’,就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行俠依仗的是義,實現的也是義,所以有俠肝者必有義膽。什么是俠?俠者使也,也就是見義勇為。也就是說,俠,就是使‘義務’(正義的擔當)變成‘義舉’(正義的行為)的精神,以及具有這種精神的人”[2]264。至此,我們似乎可以為傳統政治生態下的“俠”下一個完整的定義:“俠”即是有著高超的本領和高尚的人格,以個人的意志和力量來反抗社會黑暗,為此不惜挑戰社會既有的法律秩序以匡扶社會道義,并以此為己任的人!
二、“俠”與“法”的對立
從上述“俠”的特質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俠”與“法”似乎是一對矛盾體,其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與沖突(所謂“俠以武犯禁”)。我們不難發現:俠意識,是不承認有法律存在的,他們只會按個人的天理人情來行事,正所謂“替天行道”而非“替天執法”。也就是說,俠的心中只有道義,而無法律,他們當然也不會將法律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他們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乃是“義”。因此,我們常說“俠”乃是“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而至于這一“吼”和一“出手”是否會觸犯到現行法律秩序,卻不在俠客的考量范圍之內。于是,我們就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俠”要替天行道、抱打不平大多是要觸犯法律的。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水滸傳》中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魯提轄作為“俠”的一個典型,在面對社會的黑暗和不公之時,憑借自己的勇氣和俠義心腸,毫不遲疑地迎了上去。他為營救弱女子金翠蓮而三拳打死惡霸鎮關西是弘揚社會正氣的正義行為,但卻觸犯了當時的法律,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而被官府通緝捉拿,最終魯提轄為了躲避法律的追查,不得不委曲求全落發為僧。可見,對于“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的“俠義”行為,當時法律給出了否定性評價———魯提轄乃是大宋律法之下的“要犯”,必須予以嚴懲。然而,與法律給出的否定性評價相對應的是,千百年來,民間社會卻從沒有將魯提轄當作十惡不赦的“罪犯”來看待,而是將其視為伸張正義、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漢,對之稱贊有加。明代思想家李贄就曾在《水滸傳》“拳打鎮關西”這段文字之后,對魯提轄給出了“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薩、羅漢、佛”的高度評價[3]。“仁人、智人、勇人、圣人”乃是儒家理想人格,“神人”是道家的理想人格,“菩薩、羅漢、佛”是佛家的理想人格,因此,中國傳統三教“儒釋道”的最高稱謂,李贄都毫不吝惜地送給了魯提轄,足見其對魯提轄的推崇與贊賞。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像魯提轄這樣一個觸犯律法的戴罪之人,卻為何能夠得到民間社會的千古傳誦?在面對社會的黑暗與不公之時,我國傳統的民間社會為何沒有普遍理性地選擇運用“法律”的途徑來維護自身權益,而是去期待游走于法律之外,自掌生殺予奪的“俠”者?筆者認為,在“俠”與“法”這對看似矛盾的概念背后,在民間社會與官方秩序對“俠”這一現象做出的對立性評價的表象背后,有著更為深層次的制度根源。
三、民間社會頌揚“俠”之制度根源
眾所周知,法律乃是保障社會秩序、維護社會正義的核心力量。因此試想,一個社會如果有著一整套制定精良的法律體系,并能夠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那么,法律本身就足以建構良善的社會秩序,根本無需“俠”的存在,人們也不會在內心中渴望并呼喚“俠”的出現。然而,“良法善治”卻是要以一整套能使公權力受到制約并依法運行的政治制度為保障的,依現代政治學的視角來看,這便是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民主制度。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認為:為了終止伴隨自然狀態而在的混亂與無序,人們需要締結一項契約,并讓渡自己一定的權利而組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即國家,但人們在建立政權時仍然保留著他們在前政治階段的自然狀態中所擁有的權利。他指出,由人們構成的社會或由人們成立的立法機關的權力絕對不能超越公益的范圍,如果它專斷地不適當地處理人民的生命與財產,那么它就違反了社會契約的基本條件和它得以掌握權力所依憑的委托關系[4]59-60。因此,在現代民主政治(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民主共和制)之下,公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于人民,公“權力”也要時刻接受來自于人民“權利”的監督和制約。由此,公權力很難異化成為與人民相對立的“利維坦”,而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也不會偏離基本的正義軌道。然而,中國傳統封建社會實行的乃是君主專制制度,在這一政治邏輯中,公權力的合法性并非源自“民選”,而是所謂的“天授”———封建時代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即自稱“天子”,人民在官員的選任和升遷中,也不存在任何的話語權。因此,封建時代公“權力”也絕不會受到來自人民“權利”的制約,官員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只是單純的統治與被統治、管理與被管理———封建時代如“州牧”這樣的官職名稱,似乎更能精準地昭示中國傳統社會官員與人民之間的真實關系,即有如牧羊人和羊群之間的關系。孟德斯鳩曾經說過:“每個有權力的人都趨于濫用權力,而且還趨于把權力用至極限,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4]63。”因此,在失去了來自人民權利的制約之后,封建君主專制下的絕對權力很容易成為一匹脫韁的野馬,滋生出絕對腐敗,從而在立法與執法兩個層面完全背離“良法善治”的正常軌道。首先,從立法層面上看,封建時代可謂是“惡法”頻出。例如秦朝的苛法就公然規定:“誹謗者誅,偶語者棄市”(《史記·高祖本紀》),即敢于公然誹謗朝廷、詆毀皇帝的人,就會遭受滅族的懲罰,而對于那些即便沒有公然誹謗、只是私下議論朝廷之人,也會慘遭殺頭之禍。在這種情況下,“執法”實際上就是在“作惡”。所以“惡法”的存在使得統治者可以在“執行國家法律”的幌子下肆無忌憚的胡作非為,這就造成了社會正義的嚴重缺失,孔子就曾在泰山腳下無奈地感嘆“苛政猛于虎”(《禮記·檀弓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敢于對抗惡法的“俠”的出現,其形象就顯得格外光彩照人。正如前文所述,俠的心中是不承認有法律存在的(何況是惡法),在俠的心中只有道德與正義觀念;俠也不會用法律作為他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當然也不會理會統治者在作惡時是在執法還是在違法,只要路見不平,俠客們就會挺身而出、拔刀相助。這樣不畏強暴匡扶正義之人,自然而然就會受到民間的頌揚!其次,從執法層面上看,文明、公正的執法乃是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保障,而這又依賴于公權力的依法運行。在一個現代民主政體的社會中,公權力受到來自人民“權利”和公“權力”的雙重制約,因此其運行便會在法律規則的框架內,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在傳統中國這樣一個君主專制政體中,失去了人民“權利”和公“權力”的雙重制約,公權力的運行往往就會掙脫法律的枷鎖。于是,徇私枉法、濫用權力的情形就會時有發生。正如阿克頓爵士的名言:“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使人腐化。[5]”因此,在傳統中國,在公權力排除制約而逐步異化之后,底層百姓就不免會受到貪官污吏、土豪惡霸的欺壓而無法在既有體制內通過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七劍十三俠》第一回就稱貪官污吏、勢惡土豪、假仁假義等三種人為“王法治他不得”的“極惡之人”[1]9。因此,在既有的體制和秩序框架內,人民無法通過法律來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情形下,就必然會寄希望于體制之外力量來主持公道,伸張正義。而這一力量又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其一:足夠強大,可以對抗既有體制和官方秩序;其二:秉持正義,可以懲惡揚善,主持公道。而“俠”則恰恰滿足了這兩個條件。第一,“俠”的本領高強,因此力量足夠強大;第二,“俠”的心中有“義”,因此會匡扶正義。所以,易中天先生才會相對于流氓“惡霸”而言,將“俠”形象地稱之為“善霸”[2]249。明代漲潮曾言:“胸中有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能自掌正義,平天下之不平,那當然最好;至于無此本領的人,焉能不懷念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正因為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會正義的強烈愿望,才不會因為朝代的更替或社會形態的轉變而失去魅力”[1]9。所以,司馬遷認為,像漢代朱家、劇孟、郭解這樣的大俠,信守然諾,舍己助人,行俠仗義,扶危濟困,而且功成身退,不求回報,“雖然其行為不符合正統觀念(其行為雖不軌于正義),也常常觸犯王法(時扦當世之文罔),但個人品質無可挑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享有盛譽是名副其實(名不虛立),受人擁戴也是理所當然(士不虛附)”[2]252。所以,“要使法律成為社會正義的力量,不但法律本身必須公正,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執行必須超越種族、集團、黨派的利益。…否則,將給人以一種印象:法律只是某些人的掌中玩物,法律完全喪失了它的莊嚴”[6]20。如果法律在制定或執行層面就是不公正的,就會出現“有些執法者對侵犯人權的事麻木不仁,然而同時對忍無可忍條件下自行執法的事的反應卻出奇地靈敏和嚴厲,為了壟斷權力不惜做惡勢力的包庇者”[6]21這一現象。因此可以說,傳統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的公權力異化,以致法律在制定與執行層面出現的不公不義,乃是民間社會對“俠”這一群體贊頌之根源所在。
四、官方體制貶抑“俠”之制度根源
與民間社會對“俠”的贊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集團對于“俠”均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乃至必欲除之而后快。對“俠”的鎮壓始于何時已無從考察,但可以肯定不晚于韓非子時代。韓非子作為戰國時期韓國的貴族,他選擇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進而極力反對俠。韓非子在其文章《五蠹》中明確表達了對俠的否定:“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可見,在韓非子的眼中,“儒”和“俠”這兩大群體均屬社會的負面力量。“儒”整日寫文章針砭時政、抨擊朝廷;而“俠”則是直接憑借自己力量(以武)將法律取而代之(犯禁),自行主持社會秩序。所以在韓非子看來,“儒”與“俠”這兩大群體均是社會的蠹蟲,應該大力鎮壓。而后世之班固,更是在《漢書·游俠列傳》中,對“俠”做出了“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罪已不容于誅矣”的評價。因此,我們不禁會問,既然“俠”致力于追求完善的人格與高尚的品德,其所維護的乃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如此“義士”、如此“義舉”,為何還會遭到統治者的否定?“以德治國”不正是我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所大力弘揚的嗎?這當然不錯,但問題的根源卻在于:“俠”是民不是官,他們屬于傳統社會中的被統治階級而不是統治階級。因此“俠”絕非“以德治國”的主體,統治者也絕不會允許其成為“以德治國”的主體。事實上,反觀整個中國傳統社會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還有一個群體與“俠”同樣受民間社會的喜愛與尊敬,千百年來也是不斷歌頌稱贊———“清官”。我們常常提到的包青天(包拯),海青天(海瑞),于青天(于成龍)等就屬于這一群體,他們所起到的社會作用與“俠”也看似相同———懲惡揚善,伸張正義。但可見的是,與“俠”相比,統治者對清官的態度卻截然相反———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雖亦有時對清官存在著諸多不滿,但基本都會將其樹立為官吏的榜樣,進而加以褒獎———其原因就在于俠客仗劍行俠屬于個人行為而非政府行為,他們的功名業績只屬于他們自己而不屬于國家;而清官為百姓伸張正義則屬于政府行為,他們的功名業績不僅屬于他們自己更屬于整個國家。清官替百姓伸冤昭雪,百姓們會夸贊政府,夸贊朝廷有道。而俠客行俠仗義替百姓出頭,百姓們會夸贊俠客,指責朝廷無道,這是統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更是統治者所不允許的。所以,在統治者眼里,“伸張正義”的事情只能由政府去做,俠客再有道德,也不許越俎代庖。“其實,俠客不討皇帝喜歡,恰恰就因為他們講道德,有人格。我們知道,道德與人格是有凝聚力的,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懷遠’。但我們要記住,在帝國時代,這種凝聚力只能屬于王朝,屬于皇上,而不能屬于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團”[2]252。正是在種政治考量之下,傳統中國的統治者對“俠”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打擊。有學者認為,西漢時期,被漢武帝殺掉的郭解乃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位真實的“大俠”。郭解之后,“俠”這一群體便成了一股松散且不成氣候的社會力量———自《后漢書》始,正史便不再為“俠”者著述立傳———“俠”也隨之成為了中國文人心中的“千古一夢”[2]254-255。然而,身處現代社會的我們卻不應過分懷念“俠”,因為究其根本,“俠”———無論其“義舉”如何正當———畢竟是一股游走在國家法律秩序之外的社會力量。因此,一個極力呼喚渴望“俠”的時代,一定是社會腐敗黑暗而人民又無能為力的時代。
參考文獻:
[1]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易中天.帝國的惆悵[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3]鮑鵬山.鮑鵬山新說水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87.
[4]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5]姚建宗.法治的生態環境[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113.
[6]茅于軾.通向富裕和公平之路[M].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8.
作者:才圣
擴展閱讀
- 1生態政治與政治生態化
- 2政治處思想政治總結
- 3時事政治在初中政治中的應用
- 4時事政治融入政治課堂
- 5思想政治途徑
- 6思想政治
- 7思想政治
- 8醫院思想政治
- 9生態政治生態化
- 10思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