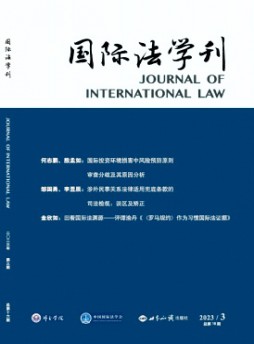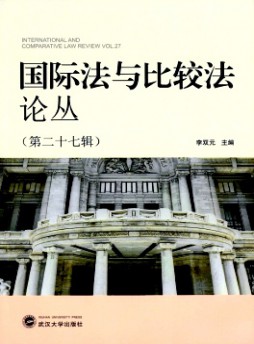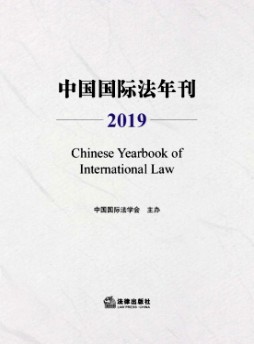論國際法中的單邊貿(mào)易對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論國際法中的單邊貿(mào)易對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單邊行動概述
在國際法學(xué)者看來,單邊主義是經(jīng)常被視為相當于臟話的用語。如果將一個行為定性為“單邊的”,就如同在譴責(zé)該行為。“單邊主義”這個詞語背后所隱含的意思,包括傲慢自大、漠視他人、支配或控制甚至是非法的等。⑦例如,美國2003年繞開聯(lián)合國安理會攻擊伊拉克,以及選擇不參與《國際刑事法院規(guī)約》和《京都議定書》的事例。“單邊主義”一詞通常和其他一些詞如“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雙邊主義”(bilateralism)和“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cooperation)等概念相對立,而后者一般被認為是解決國際問題的較好方式。雖然“單邊主義”被用來象征性地批評不同的實踐活動,但是它本身并沒有法律意義。“單邊主義”的概念寬泛且沒有什么固定的形式,這使得其被作為萬能鑰匙(passpartou)用以概括各種具有國際后果的行動、措施和行為。
但是,有一些單邊主義只是政治意義上的,有一些則具有法律內(nèi)容并產(chǎn)生法律后果。大多數(shù)單邊行為具有一個共同特征,即由一個或者幾個國家聯(lián)合采取、主張或者實施某種行為,并對其他國家產(chǎn)生重要影響。⑧在國內(nèi)層面上,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管轄的范圍一般沒有什么爭議,單邊行動一般不會成為什么問題。問題往往發(fā)生在國際層面上。⑨國家每天都在采取單邊措施,完全依據(jù)國內(nèi)法律或政策單方所采取的某種措施,一般不存在國際法層面的適法性問題。只有一個國家試圖將其價值觀施加于他國,而他國不同意所施加的價值觀時,該單邊行動才會引起爭議。
當一國施加強制性的單邊措施以規(guī)制具有廣泛影響的問題,而否定其他受影響國家在決策過程中的話語權(quán)時,該措施的合法性就很容易受到質(zhì)疑。尤其當一種文化自認為優(yōu)越于其他文化時,隨之而來的就是單向輸出(unilateralexport)而非最有利于追求全球進步的多邊對話。但是,從正面的角度看,由于多邊談判可能因各種原因而失敗,單邊主義有時是保護更重要價值的唯一可行途徑。如果有效的多邊行動顯得不可能,選擇就不在于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而是在單邊主義和“不行為”(inaction)之間。
因此,從利益重要性的視角而言(如保護環(huán)境,或保護個人防備暴行),單邊行動不應(yīng)當必然地受到負面的評價。例如,在外層空間長期缺乏以條約為基礎(chǔ)的劃界,最終可能導(dǎo)致為空間管理目的而通過建立劃界管轄領(lǐng)域的單邊國家立法。再如,國家主張對國際犯罪行使普遍管轄權(quán),因其包含大量國家自由裁量的成分而具有單邊性質(zhì),但由于其旨在實施國際公認的規(guī)則而為國際法所允許。在環(huán)境領(lǐng)域,港口國對于違反國際規(guī)則與標準的海洋環(huán)境污染管轄權(quán),這種做法也得到《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認可。有時,合法性頗具疑問的國家單邊行動會鼓舞其他國家采取類似做法,甚至導(dǎo)致一項新的習(xí)慣國際法規(guī)則的產(chǎn)生。大陸架和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的發(fā)展,就是這個造法過程中作為對國家管轄權(quán)單邊擴張的反應(yīng)。一般說來,國家出于保護環(huán)境等需要所采取的貿(mào)易措施很有可能波及其主權(quán)管轄范圍之外,特別是當強國采取的單邊貿(mào)易措施威脅或未經(jīng)他國同意強加義務(wù)于對方時,該行為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其他國家的質(zhì)疑。由于多邊主義是對于WTO而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概念,單邊貿(mào)易措施不僅會損害到這個理念,還可能催生保護主義和抵消關(guān)稅談判的成果。
二、單邊貿(mào)易措施的適法性分析
判斷單邊貿(mào)易措施在國際法中的合法性,主要是區(qū)分在某一特定法律體系框架內(nèi)該行為是屬于自身授權(quán)(或至少允許)的單邊行為,還是屬于漠視、曲解或違反完全可行規(guī)則的行為。習(xí)慣國際法和條約都是檢驗單邊貿(mào)易措施是否合法的重要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說,習(xí)慣國際法反映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和人類的整體利益,因而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國際法規(guī)范,對各國皆課以普遍的義務(wù);國際條約乃國家之間合意的產(chǎn)物,根據(jù)“條約必須信守”原則也不容許任意違反。在國際貿(mào)易領(lǐng)域,時常發(fā)生國家從多邊協(xié)定中撤銷先前的承諾,或基于環(huán)境保護、勞動標準等理由采取制裁等手段向不遵守相關(guān)標準的國家施加壓力的事例。這些單邊貿(mào)易措施是否具有WTO合規(guī)性呢?
(一)國家是否擁有從習(xí)慣國際法中單邊退出的權(quán)利
國家通常不會公然宣稱違反習(xí)慣國際法,如果它們想以該規(guī)則相反的方式行動,要么必須違反該規(guī)則并希望其他國家默許該違反,要么它們必須說服其他國家加入推翻包含該項習(xí)慣國際法規(guī)則的條約。Bradley和Gulati教授將其稱為習(xí)慣國際法的“必須遵循的觀點”(Man-datoryview),他們對這種支持習(xí)慣國際法拘束所有國家而不考慮個體同意的觀點予以辯駁,認為現(xiàn)代“必須遵循的觀點”使得習(xí)慣國際法過于黏稠(sticky)會造成釘子戶問題(holdoutproblem)和適應(yīng)性不足(in-sufficientlyadaptable),并為國家至少可以從部分習(xí)慣國際法規(guī)則中退出的“不履行的觀點”(defaultview)進行辯護。瑏瑦支持“不履行的觀點”者認為,由于法律的限制以及無數(shù)制度、政治和聲譽方面的成本阻止國家退出條約,如果國家從習(xí)慣國際法中退出必然會付出極大成本,但有更重要的理由來拒絕對“從習(xí)慣國際法中退出”的絕對禁止。例如,一項退出選擇可能為國家提供談判更廣泛的國際承諾或鼓勵更多國家批準條約的安全需要,這有利于促進國家之間的合作從而更好地解決全球問題。
反對者認為,基于習(xí)慣國際法的本質(zhì)和目的,“不履行的觀點”在理論上缺乏說服力,就實踐而言也具有局限性。例如《防止和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14條明確賦予締約方退出的權(quán)利,但從條約中退出的國家仍受到實質(zhì)性禁止滅絕種族的約束,因為這是國際習(xí)慣及其強行法的地位。當然,此時國家再也不受非習(xí)慣國際法義務(wù)的約束,如對國際法院管轄的同意。還有學(xué)者指出,設(shè)想如果在習(xí)慣國際法中“不履行的觀點”得到接受而代替“必須遵循的觀點”,或者當美國面對恐怖主義威脅而決定從“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rules)中退出,由于美國不是《第一附加議定書》的當事國,其一旦退出“比例原則”就不能給條約規(guī)則留下一張安全網(wǎng)。“Bradley和Gulati教授呼吁國際法規(guī)則中應(yīng)當有更大的靈活性,但忽視禮讓原則(comitydoctrines)在歷史上已允許他們所尋求的這種靈活性。”瑐瑡國際法主流觀點認為,一項習(xí)慣國際法規(guī)則一經(jīng)得以確立,國家就不再擁有單邊退出的權(quán)利。如果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3條的規(guī)定可比照適用于單方面行為,凡違反國際法強制規(guī)范的單方面行為均無效,基于相同理由,可得出國家不能從國際習(xí)慣法規(guī)則中單邊退出的結(jié)論。
(二)締約國對于國際條約是否擁有采取單邊行動的余地
不同于習(xí)慣國際法,國家在某種條件下可單邊決定偏離其承擔(dān)的國際條約義務(wù)。有效的條約是由締約方自愿確定權(quán)利與義務(wù),締約方必須按照條約的規(guī)定,善意地解釋條約并忠實地履行條約義務(wù)。為應(yīng)對國際事務(wù)中遍布各種不確定性,包括對未來事件不充分的信息、其他國家的偏好以及國內(nèi)政治的變化等,國際條約中往往存在某些靈活性機制(flexibilitymechanisms)。瑐瑤正式的靈活性工具包括單邊保留、退出條款(withdrawalprovisions)、廢止條款(denunciationclause)和例外條款(escapeclauses)等,非正式的實踐包括自動解釋(auto-interpreta-tion)、不參加(nonparticipation)和不履行(noncompliance)等。國際條約中不同的靈活性工具服務(wù)于不同的功能。當國家明確地協(xié)商創(chuàng)造條約義務(wù),它們通常會在條約中包含退出的權(quán)利,有時以一段時間的通知為條件。即便當它們沒有明確簽訂這樣的協(xié)定,某種主題的條約有時也會自身表明有一項具體的退出權(quán)利。即便當條約中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退出權(quán),國家往往在情勢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時擁有某種退出權(quán)。國家還有能力通過使用保留或借助“損抑條款”(derogationclauses)避免適用條約的特定條款。例如,國際人權(quán)條約賦予成員方的“損抑權(quán)”使得政府有能力面對國內(nèi)危機時爭取時間和法律的呼吸空間,同時向有關(guān)國內(nèi)民眾傳遞中止權(quán)利是暫時性和合法的信息。國際環(huán)境條約也需要權(quán)衡適應(yīng)不能預(yù)見的緊急情勢之靈活性和避免因為條約過于容易被修正而減損其效力與成員的承諾水平。在國際貿(mào)易條約中,同樣包含為國家提供一定程度靈活性的機制,例如允許國家在不超過約束關(guān)稅水平的前提下可單邊調(diào)整關(guān)稅,再如保障措施和反傾銷都是允許國家在滿足某種條件時即可提高超過約束水平關(guān)稅的緊急保護措施。
一般而言,單邊機制通常只在國家為減少國內(nèi)經(jīng)濟或政治不確定性時才援引,締約國的單邊行動是否具有合法性主要根據(jù)國際條約的實體規(guī)定來具體判斷。瑐瑨根據(jù)習(xí)慣國際法或條約法規(guī)則的授權(quán)所采取的單邊行動,無論是國家單獨采取自衛(wèi)行為,還是根據(jù)條約規(guī)定所采取的單邊執(zhí)行或遵守措施等,都屬于國際法允許之列。強權(quán)國家為推行本國政策和法律目標,而采取的違反國際習(xí)慣法或條約法規(guī)則的單邊措施,或根據(jù)違反現(xiàn)有的國際法規(guī)則的國內(nèi)法所采取的單邊措施,則不存在討論其適法性與否的余地。當出現(xiàn)國際條約與國際習(xí)慣相互重疊的情況時,國家是否擁有單邊退出的權(quán)利呢?有關(guān)這類條約如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guān)系公約》、1963年《維也納領(lǐng)事關(guān)系公約》和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退出只字不提;有些條約如1948年《防止和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明確允許退出但并未提及國際習(xí)慣;有些條約允許退出但明確指出國家仍然受其習(xí)慣國際法義務(wù)的約束。但是,無論何種情形,其背景假設(shè)都是國家仍然受到國際習(xí)慣的約束。這既尊重有關(guān)國家加入條約的意愿,也是要求該國遵守其加入條約的前提條件。可見,不能簡單地以特定領(lǐng)域的國際條約允許退出為根據(jù),就得出國家可以從相同的習(xí)慣國際法規(guī)范中退出的結(jié)論,因為該推導(dǎo)沒有考慮到習(xí)慣國際法具有被推定為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網(wǎng)作用。正如國際法院在“北海大陸架”案中所言,“因其性質(zhì),必然對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具同等效力,而不能允許任何成員根據(jù)自己的意志單方排除其效力”。
(三)單邊貿(mào)易措施在WTO體制下是否具有合規(guī)性
國際法法律制度確實存在,但很少有中立裁斷者宣布規(guī)則的內(nèi)容或宣告一國政府已經(jīng)違反法律。恰恰相反,如若可以的話,是由爭端當事方?jīng)Q定違約是否發(fā)生以及采取什么救濟。如果這不難做到,即使國際法院存在,政府也習(xí)慣于抗拒法院的管轄權(quán)或忽視其裁決。國際法的懷疑者會問,鑒于這樣單邊的而非中央執(zhí)行的體系,國際法究竟是否能夠合適地被稱為法律。國際法的支持者通常會向懷疑論者指出一項明顯的例外,即準司法體系的WTO。在該貿(mào)易協(xié)定中,各成員方政府建立起一套程序,具有強制性管轄權(quán)的中立司法小組對成員方政府提起的訴訟擁有決定違約是否發(fā)生和專屬權(quán)力,并能制定出違約的救濟方式。在WTO成立之前,雖然政府可通過GATT體制尋求多邊解決貿(mào)易爭端的方法,但一些政府(特別是美國)常常根據(jù)自身決定選擇出和執(zhí)行另一國家是否已經(jīng)違反一項貿(mào)易協(xié)定。相比之下,由于WTO具有“準司法”特征,貿(mào)易強國可在WTO框架內(nèi)來處理與貿(mào)易弱國的貿(mào)易關(guān)系,而無須尋求單邊的貿(mào)易措施。WTO的制度和規(guī)則亦可為弱方提供更多討價還價機會,因為小國在通過多邊條約的國際會議上通常占據(jù)大多數(shù)的席位,因此這類條約嚴重地否定其根本利益的可能性極小。例如,1995年日本聲稱美國貿(mào)易法301條款的適用違反WTO程序,并將該案起訴到剛剛建立的WTO。雖然日本不能在談判中獲得全面的勝利,但其成功地利用國際法規(guī)則使得美國不得不作出撤回其單邊措施的重要決定。美國政府很清楚如果該案件經(jīng)過WTO評審其將會敗訴。如果日本繼續(xù)進行雙邊談判,而不是利用國際法的規(guī)則,就不可能得到這樣有利的結(jié)果。
WTO體制的主要革新是讓各成員方同意將《關(guān)于爭端解決規(guī)則與程序的諒解》(DSU)作為執(zhí)行貿(mào)易法律的專屬方法。政府決定停止對WTO規(guī)則的單邊執(zhí)行。與此同時,WTO出于靈活性的需要也允許承諾的單邊修改。由于WTO協(xié)議乃國家之間的不完全合同,它們不能為未來所有的意外事件有所預(yù)見或制定條件反射。情況改變和政治現(xiàn)實都要求適時調(diào)整,國內(nèi)政策出于各種原因要求對某些承諾進行修改。“單邊修改”(unilateralmodification)條款允許成員方在不違反義務(wù)的情況下可修改或撤銷其承諾。雖然修改一般是基于再談判,但這些條款的主要方面是即便不能獲得受影響成員的同意,希望偏離其承諾的成員也可能單邊修改或撤銷WTO減讓與承諾。允許單邊修改承諾的最主要和影響深遠的條款是GATT第28條和《服務(wù)貿(mào)易總協(xié)定》(GATS)第21條。根據(jù)這些條款的修改并不以“因任何原因有限時間內(nèi)可能被修改的任何承諾”的實質(zhì)條件為先決條件。GATT第18條還規(guī)定,“特定的處于發(fā)展經(jīng)濟但不符合低生活水平的國家,可以申請許可偏離GATT規(guī)則以保護特定的產(chǎn)業(yè)”。該條款允許發(fā)展中國家采取單邊行動,且最終不需要得到受影響國家的授權(quán)。GATT第27條的規(guī)定表明,如任何締約方確定一政府未成為或不再為締約方,則該締約方有權(quán)隨時單邊停止或撤銷對其所承擔(dān)的關(guān)稅減讓等義務(wù)。GATT第19條和第20條同樣有單邊修改承諾的規(guī)定。此外,GATS第21條第5款授權(quán)服務(wù)貿(mào)易理事會為修改減讓表制定程序。事實上,修正錯誤是伴隨著任何條約的一個程序,其中存在著某些習(xí)慣國際法。通常實踐是修改方單邊調(diào)整承諾,并通知所有受其影響的當事方,如果未受到任何反對,該調(diào)整承諾的行為即生效。可見,WTO協(xié)定中有許多靈活性機制,可有效地協(xié)調(diào)多邊體制的法律約束力與成員方單邊貿(mào)易措施之間的沖突。但是,除非相關(guān)國家存在特殊的法律關(guān)系,一般國際法并不包含一項與其他國家維持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權(quán)利,作為主權(quán)的必然結(jié)果國家在原則上也因此有權(quán)制定單邊貿(mào)易措施。
由于WTO制度設(shè)計本身不能杜絕單邊貿(mào)易措施,有時還需要通過爭端解決機構(gòu)結(jié)合個案進行澄清與判斷其合規(guī)性。例如,美國1974年貿(mào)易法基于單邊主義的301條款即使僅僅作為“威脅”手段,也會給成員方之間造成沖突和不妥;如果這些國家迫于美國壓力而先期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措施,則由此造成的損失屬于“自愿調(diào)整”,無法向WTO尋求救濟。1999年,歐盟就美國301條款至310條款進行磋商未果后提出設(shè)立專家組的申請。專家組報告認為,一部法律若保留采取與DSU規(guī)則和程序相悖之單邊措施權(quán)利,正如本案一樣,可能構(gòu)成一項持續(xù)的威脅,并產(chǎn)生導(dǎo)致各方面嚴重損害的寒蟬效應(yīng)(ChillingEffect)。這在實質(zhì)上是限制美國使用這種典型的單邊貿(mào)易制裁的國內(nèi)法工具,同時表明任何潛在使用單邊貿(mào)易制裁措施的國內(nèi)法律必須服從WTO協(xié)定。
再如,根據(jù)上訴機構(gòu)對“蝦和海龜案”裁決,其措辭表明保護環(huán)境的單邊貿(mào)易措施在關(guān)貿(mào)總協(xié)定下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該案可視為一個主要司法權(quán)威對國家單邊地尋求對發(fā)生在其管轄范圍之外的行為適用自身環(huán)境標準潛在能力的全新表達。然而,該權(quán)利的邊界應(yīng)受到限制,即必須滿足某些條件。其一,采取措施的國家對其意圖保護的資源必須具有合法的利益(例如,其可能是遷移的或共享的資源);其二,有關(guān)措施必須旨在保護迫近瀕危的資源;其三,采取措施的國家首先必須窮盡外交手段與有關(guān)國家達成協(xié)議。在通過談判仍不能解決糾紛的前提下,締約方可采取相應(yīng)的單邊措施,從而為WTO的規(guī)則體系同其他國際環(huán)境公約的銜接提供法律依據(jù)。可見,DSU必須平衡該體制在限制單邊行動方面的成就,與此同時若不是鼓勵也是允許單邊行動。
正如上訴機構(gòu)在“美國汽油標準案”中所強調(diào),只要能履行其在WTO協(xié)議下的義務(wù)和尊重其他成員的權(quán)利,WTO成員即可自由決定其以保護環(huán)境為目標的政策(包括其與貿(mào)易的關(guān)系)。單邊貿(mào)易措施在WTO框架下的適法性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世界貿(mào)易體制的精髓就在于它能在國際貿(mào)易關(guān)系中克服單邊行動。WTO爭端解決機制引進“規(guī)則導(dǎo)向”的新方法解決成員之間爭端,DSU的目標就是限制成員之間的單邊行動。DSU第23條標題為“多邊體制的加強”,其整體設(shè)計旨在通過強制成員遵循DSU的多邊規(guī)則與程序以阻止WTO成員單方面解決它們之間涉及WTO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爭端。另一方面,某些單邊行動在WTO體制中具有合法性,因其已為成員所共同接受并包含在WTO協(xié)定中。例如,DSU第22.2條允許成員方單邊地中止有關(guān)協(xié)議的減讓或其他義務(wù)。鑒于DSU沒有提供任何集體執(zhí)行WTO的方法,個體成員可單邊地執(zhí)行其權(quán)利。但是否實施樣的制裁由爭端解決機構(gòu)授權(quán)決定,而不完全是WTO成員的自主行為。GATT第20條和GATS第14條一般例外條款也允許限制性貿(mào)易措施。再如,在違反條約或其他國際不法行為的情形下,國家可求助于傳統(tǒng)的反措施。就這一點而言,如果滿足各自的前提條件,單邊貿(mào)易措施具有正當性。無論如何,根據(jù)多邊主義和談判原則,成員方在采取單邊貿(mào)易措施之前,應(yīng)當首先進行談判以便獲得相互同意的解決方案。這體現(xiàn)出WTO適應(yīng)國家行使主權(quán)的靈活性,同時也力圖敦促各成員方遵守貿(mào)易規(guī)則的基本特點。
三、單邊貿(mào)易措施的國際法救濟
從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角度講,各國政府在制定決策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國內(nèi)利益群體的影響。當政府決策主要是基于本國選民利益,往往會忽略其對貿(mào)易伙伴的影響,最終可能導(dǎo)致他國的利益受到損害。在主要大國違反國際法的情形時,它們很少真正受到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施加的制裁或者報復(fù),致使其在國際法上享有例外的奢侈(excep-tionalluxury)。瑒瑦WTO的成立和爭端解決機制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抑制可能破壞多邊貿(mào)易體制穩(wěn)定性的單邊貿(mào)易制裁,但國家出于各種需要采取單邊貿(mào)易措施并損害到他國利益的事例仍然層出不窮。誠如歐美法諺所云,“有權(quán)利,必有救濟”。此時,國際法應(yīng)當能就加害國為其單邊主義行動對受害國造成的損失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救濟。
(一)國際法救濟制度的歷史性缺失
就歷史而言,救濟是國際法最不發(fā)達的領(lǐng)域之一。標準的條約和文本對此話題著墨極少。在貿(mào)易和投資法律之外,很少有國際司法或仲裁意見涉及救濟問題,其他權(quán)威的淵源同樣很欠缺。國際法委員會曾起草大量文章討論救濟問題,但國家不可能對其正式地接受。對救濟的關(guān)注不足反映出國際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實施的(self-enfor-cing),因此典型的救濟在歷史一直都是不受到法律監(jiān)督的單邊報復(fù)行動。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以相互不遵守法律的形式抑或其他懲罰,單邊報復(fù)都不是鼓勵遵守國際法的完美機制。報復(fù)本身可能成本過高和消耗資源。一個有單邊報復(fù)的體系可能要冒著報復(fù)過度的風(fēng)險。由于國際法缺乏補償性賠償?shù)捏w系,對違法國家的制裁在國際體系中是負和(negativesum),即這對于當事方而言是增加凈損失。國際法救濟制度的歷史性缺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法領(lǐng)域普遍缺失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而提供的具有程序意義的次級規(guī)則(second-aryrules,又稱二級規(guī)則)。在國際法層面,國家之間通過條約或習(xí)慣國際法承擔(dān)國際義務(wù),而違反這些義務(wù)就會引起國際責(zé)任,這些對國家施加義務(wù)的規(guī)則即為“初級規(guī)則”(primaryrules,又稱第一性規(guī)則或者原初規(guī)則)。與之相對,“那些對行使權(quán)力的方式施加義務(wù)的規(guī)則和標準,以及對違反基礎(chǔ)規(guī)則給予補償和懲罰的規(guī)則都是二級規(guī)則”。換成國際法的語言,“次級規(guī)則”包括國家責(zé)任、反措施、制裁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概念。
“一般國際法不同于國內(nèi)法。與前者不同,國內(nèi)法設(shè)置了具有強制管轄權(quán)的法院,從而在任何非法造成損害的情況下,一個確定的賠償可以由一個公正的機關(guān)來加以決定。建立一個國際法庭,由有關(guān)各國自愿締結(jié)國際條約,是必要的;而締結(jié)一個仲裁條約,授權(quán)法庭決定賠償?shù)囊庵緟s往往是缺乏的。”瑓瑣如果沒有當事方在條約的明示條款,國際法院一般也不會要求實際履行或賠償。而國際司法機構(gòu)諸如WTO法庭和國際法院,這些裁斷者都沒有超過比其裁決更大的能力,無法對不順從的當事方扣押財產(chǎn)或使用武力。如果一方違反國際法應(yīng)受到有意圖的制裁,該制裁必須由他國以反措施的形式來施加。瑓瑤由于國際社會缺乏立法機關(guān)、具有強制司法權(quán)的法庭和組織性的制裁,使其更像是僅僅由科以義務(wù)的初級規(guī)則所構(gòu)成的形式簡單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一般國際法是否真正規(guī)定賠償義務(wù)值得懷疑,因為對于義務(wù)的內(nèi)容、如何履行義務(wù)等問題都是難以確定的。對于國際法而言,“引入次級規(guī)則以補充初級規(guī)則的缺陷,這是前法律世界邁入法律世界的一步”。
(二)國際法救濟制度的新發(fā)展
國際法領(lǐng)域次級規(guī)則的完善正在促進國際法救濟制度的發(fā)展。國際法相對于國內(nèi)法的原始與分散狀態(tài),依賴受制于國際法的當事方自我實施而非由第三方來執(zhí)行的事實,并不能否定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本質(zhì)特征,否則國際社會不會保持如此有序的狀態(tài)。“一個尚未進步到超出自助原則的社會秩序可能會產(chǎn)生很多不能使人滿意的狀態(tài)。然而人們?nèi)钥赡苷J為這一狀態(tài)是一種法律狀態(tài),這種分權(quán)秩序是法律秩序。”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無政府狀態(tài),但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表現(xiàn)常常并不是赤裸裸地遵從權(quán)力利益邏輯,而是受到國際法規(guī)范和規(guī)則的調(diào)節(jié)。更重要的是,國際法由于缺乏“次級規(guī)則”造成的“原始狀態(tài)”正逐步得到改變。
第一,隨著國際社會的日益組織化與國際法法典化程度的提高,國際法關(guān)于促進國家遵守方面的責(zé)任規(guī)則正在不斷完善之中。從17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國際社會正處于自然法的時代。人們對于自然法的內(nèi)容持有不同主張,但很少去懷疑國際法源自普遍適用于國際社會的國際道德。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對于違反戰(zhàn)爭與人道法的追訴與處罰更是體現(xiàn)出自然法的色彩。然而,如果國際法規(guī)范基本上都是習(xí)慣規(guī)范,就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即對于需要精確、具體、系統(tǒng)加以規(guī)范的國際法領(lǐng)域顯得無能為力。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創(chuàng)設(shè)具體權(quán)利義務(wù)的造法性條約開始出現(xiàn),學(xué)者紛紛表達出透過法典化使權(quán)利義務(wù)更加明確的觀點。根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第13條第1項,聯(lián)合國大會的重要職責(zé)之一就是“提倡國際法之逐漸發(fā)展與編纂”,而國際法編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將不成文的習(xí)慣國際法規(guī)范轉(zhuǎn)換為成文的條約法典。條約特別是編纂性條約,已成為現(xiàn)代國際法的首要淵源。根據(jù)該條款,聯(lián)合國大會于1947年成立國際法委員會,旨在促進國際法的逐漸發(fā)展和編纂。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法委員會審議包括國家的單方面行動、外交保護、對條約保留、國際組織的責(zé)任和國家間共有自然資源等議題。尤其是國際法委員會草擬《關(guān)于國際責(zé)任的條文草案》,從而打破傳統(tǒng)國家法律責(zé)任內(nèi)容的局限性。同其他有能力準備編纂法律的機構(gòu)一樣,國際法委員會希望其起草的條約能為國家所接受,并得到善意的解釋與執(zhí)行。
第二,國際法的價值取向正在從國家本位向國際社會本位轉(zhuǎn)變,國際法正從“初級規(guī)則”(即強調(diào)國家承擔(dān)義務(wù)的內(nèi)容)到“次級規(guī)則”(即如何確保國家實現(xiàn)這些義務(wù))轉(zhuǎn)變。“初級規(guī)則”要求國際法主體必須履行的義務(wù),包括國家的單邊行為須符合其承擔(dān)的義務(wù);“次級規(guī)則”旨在規(guī)定違背“初級規(guī)則”所設(shè)定義務(wù)而產(chǎn)生的法律后果。例如,2001年聯(lián)合國大會第56屆會議通過的《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zé)任的條款草案》(簡稱《國家責(zé)任條款草案》)對國際不法行為造成的損害賠償規(guī)定單獨或合并地采取恢復(fù)原狀、補償和抵償?shù)姆绞健!秶邑?zé)任條款草案》不能被認為是有約束力的法律,但卻是該領(lǐng)域規(guī)則和標準發(fā)展演變的指南。關(guān)于國家責(zé)任的國際法表明國際法正在朝著多邊主義的方面發(fā)展。
一般國際法并未禁止使用單邊貿(mào)易措施,但如果國家因使用而導(dǎo)致違反國際法義務(wù),就可能引發(fā)國家責(zé)任。根據(jù)《國家責(zé)任條款草案》第56條,對于沒有明文規(guī)定的國家責(zé)任問題仍應(yīng)遵守可適用的國際法規(guī)則的規(guī)定,沒有理由不將該原則適用范圍擴及WTO法領(lǐng)域。瑔瑡如果國家在WTO等國際貿(mào)易條約體制下承諾通過多邊或雙邊的方式解決爭端,就有義務(wù)善意履行其在條約下所承擔(dān)的各項具體義務(wù)。如果擅自采取單邊貿(mào)易措施,就可能構(gòu)成對國際法的違反而產(chǎn)生國家責(zé)任。
(三)單邊貿(mào)易措施與WTO法律救濟
WTO救濟的真實本質(zhì)反映著該體制自身存在的理由(raisond''''etre)。瑔瑢W(xué)TO體制對違反其規(guī)則的任何貿(mào)易措施提供相對完善的法律救濟機制。眾所周知,國際法一直被批評過于虛弱而無法提供有效的執(zhí)行機制,因此國際條約在保留、執(zhí)行等事項上的剛性規(guī)定是增強各國承諾可靠性的重要保障。在WTO體制內(nèi),任何成員方都無法運用一般條約中的“保留條款”來排除可能有損國家主權(quán)的條款適用,除非該成員方選擇不加入或退出。因此,與加入其他條約或國際組織相比,加入WTO并接受爭端解決機制的約束將意味著各主權(quán)國家將自主讓渡更多的“主權(quán)”由WTO及其爭端解決機構(gòu)來行使。對于傳統(tǒng)國際法缺乏執(zhí)行力的困境,WTO爭端解決機制具有以規(guī)則導(dǎo)向為主的司法模式、強制管轄權(quán)和強制執(zhí)行力等獨特性都是國際法重大的突破和發(fā)展。WTO爭端解決機制本身是違反與賠償?shù)闹贫龋湟?guī)定一套較為完善報復(fù)機制之目的就是督促成員國遵守執(zhí)行WTO協(xié)議。WTO通過《關(guān)于爭端解決規(guī)則與程序的諒解》(DSU)強調(diào)爭端解決程序的解釋與適用的“規(guī)則導(dǎo)向”而非“權(quán)力導(dǎo)向”,對違約的救濟不再是相互“不遵守”,而是根據(jù)WTO規(guī)則的授權(quán)進行懲罰。相比于一般國際法,WTO既為成員方設(shè)定明確的義務(wù),同時為判定成員是否違反初級規(guī)則提供程序,這就極大地彌補了傳統(tǒng)國際法在救濟方面效率不足的缺陷。但是,WTO所提供的賠償和報復(fù)等救濟方式也并非盡如人意。
其一,根據(jù)DSU的措辭,直到WTO認定違約之后,成員方政府才能合法地對違約方進行制裁。因此,WTO只認可“預(yù)期制裁”(prospectivesanctions),即制裁是從認定違法從未來前溯。由違約導(dǎo)致的任何經(jīng)濟損失在WTO認定之前無法得到賠償。如果成員方政府在DSU程序結(jié)束后消除違法措施,則無論已經(jīng)造成多少損失他方政府也不能得到賠償。該法律語境不是具體認可政府能在DSU裁定期間的違約得到豁免,而是設(shè)計一個只要在訴訟結(jié)束前能撤銷措施即可在事實上免責(zé)(defactofreepass)的制度。例如,在2002年3月,布什總統(tǒng)提高鋼鐵進口關(guān)稅。盡管布什聲稱該做法在WTO協(xié)議下合法,但這被廣泛認為違反國際貿(mào)易規(guī)則。但在DSU規(guī)則下,直到WTO爭端解決機構(gòu)宣告該措施違法,其他國家才能被允許采取報復(fù)措施。當WTO在2003年12月份確實正式宣布該高關(guān)稅違法時,布什總統(tǒng)只需簡單地撤銷該措施。布什總統(tǒng)公然地利用“拖延和撤銷”(stallandwithdraw)的漏洞違反WTO協(xié)定,而其他國家并不被允許對美國所造成的損失進行報復(fù)。正因為“拖延和撤銷”的法律漏洞,造成DSU框架之外貿(mào)易報復(fù)行為的需求。
其二,“通過私人化的制裁從而將報復(fù)的權(quán)力留在勝訴方手里,WTO剝奪自身的法治取而代之的是招致國際政治中的叢林法則。”當一個國家違反一項義務(wù),如果授權(quán)受害國通過違反自身的義務(wù)來報復(fù),該權(quán)利能夠減少受害方的損失,并允許受害方對違法者給以制裁。確實,該報復(fù)性違約的權(quán)利甚至比其在國內(nèi)合同法中更加重要,因為這可能是唯一現(xiàn)實的救濟和國家遵守承諾的唯一動機。不可否認,通過震懾未來類似的違反行為,制裁可在促進WTO規(guī)則的遵守方面發(fā)揮一定的作用。但是,貿(mào)易制裁的雙邊主義屬性意味著弱國無法有效地對強國進行制裁,而強國一般來說將擁有比弱國更大的行動自由。美國、歐盟和日本可以通過對GATT/WTO體制置之不顧來破壞它,而其他國家不能。因此,即便窮國獲得授權(quán)對富國進行報復(fù),鑒于兩方經(jīng)濟規(guī)模的巨大差異,該報復(fù)的有效性將大打折扣,甚至得不償失。在2001年,盡管厄瓜多爾和歐盟在香蕉問題上有激烈的爭吵,但因其認識到完全采取法律手段通過WTO起訴歐盟將付出的代價,最終選擇以談判方式解決爭端,力爭避免歐盟對其香蕉出口征收高額關(guān)稅。與之相反,強國僅僅是采取單邊貿(mào)易措施威脅弱國,對后者而言都是一次致命的打擊。
由于嚴格遵守WTO義務(wù)可能會干預(yù)到國家主權(quán),而包括反措施在內(nèi)的現(xiàn)有救濟手段通常涉及對來自敗訴方貨物的貿(mào)易限制而不利于貿(mào)易自由化,最終還有可能對采取報復(fù)措施的國家產(chǎn)生經(jīng)濟上的不利影響。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確立,標志著國際經(jīng)濟事務(wù)從權(quán)力導(dǎo)向型外交向著規(guī)則導(dǎo)向型外交轉(zhuǎn)變,但如果申訴方的經(jīng)濟實力欠佳,就可能導(dǎo)致其無法順利對不執(zhí)行爭端解決機構(gòu)(DSB)裁決的敗訴方進行制裁和報復(fù)。從1995年1月1日到2012年3月底,WTO共收到434件指控,上訴機構(gòu)90份報告。但是,只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巴西、厄瓜多爾、智利、印度、韓國、日本、墨西哥、安提瓜和巴布達等為數(shù)不多的國家提出過請求授權(quán)“中止減讓”(WTO用語的“報復(fù)”)。由于不履行而導(dǎo)致事實上實施報復(fù)的只有美國在香蕉案中對歐盟采取報復(fù)措施、美國和加拿大在荷爾蒙牛肉案中對歐盟實施報復(fù)措施、歐盟在外國銷售公司案中對美國實施報復(fù)措施以及歐盟、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在伯德修正案中對美國實施報復(fù)性措施等屈指可數(shù)的案例。“雖然可靠的國際懲罰機制對于維持在標準‘囚徒困境’描述下貿(mào)易政策的合作很有必要,但在實踐中國家似乎并未違反其貿(mào)易承諾而受到懲罰。”
尤其在發(fā)展中國家勝訴時,貿(mào)易報復(fù)就更難發(fā)揮其作用。例如,鑒于政治和經(jīng)濟方面的實力懸殊,不難設(shè)想安提瓜和巴布達對美國的貿(mào)易報復(fù),不大可能會對美國構(gòu)成實實在在的影響。再如,DSB于2000年5月18日授權(quán)厄瓜多爾對歐盟進行報復(fù),這是發(fā)展中國家第一次在多邊貿(mào)易體制中獲得授權(quán)對發(fā)達國家進行報復(fù),但厄瓜多爾迄今為止仍未對歐盟實施報復(fù)。在發(fā)展中國家中,只有墨西哥2006年9月在伯德修正案中對美國真正地實施過報復(fù)性措施。2008年2月美國法院判決因北美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NAFTA),該法案不適用墨西哥。有觀點認為,WTO規(guī)定違約賠償?shù)臋C制意味著鼓勵“有效違約”(efficientbreach),無須禁止所有違反國際協(xié)定的行為,只要對其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即可。該理論還預(yù)先假設(shè)違約所遭受的損失與金錢賠償或其他形式賠償之間的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即假設(shè)人與人之間(或國家之間)效用比較和所產(chǎn)生問題不僅存在于合同,而且也存在于軍備控制、人權(quán)、國家安全、環(huán)境保護以及其他條約的假設(shè)。
由于條約如同合同一樣,并不解決未來所有的緊急情況。當緊急情況增加履行的成本超過相對方對履行的估價時違約便是有效率的。從本質(zhì)上說,有意違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xié)定,本身具有機會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性質(zhì)。據(jù)此學(xué)說,無論單邊貿(mào)易措施是否符合多邊貿(mào)易體制的要求,只要國家認為對自身有利即可實施。但是,如果每個人都相信富國和大國可簡單地通過賠償或支持暫停義務(wù)的方式“購買”(buyingout)其應(yīng)承擔(dān)的義務(wù),而這些所逃避的義務(wù)又是交易者對可預(yù)見性和安全性所依賴的規(guī)則,那么該體制相當程度的可信性和公允性將會被削弱或消失。長此以往,必將從根本上損害到WTO體制的“安全性和可預(yù)見性”。
四、結(jié)論與啟示
單邊貿(mào)易措施的正當性源于反措施捍衛(wèi)“對國際社會整體的義務(wù)”(obligationsergaomnes)的理論。單邊貿(mào)易措施的概念隨著國家經(jīng)濟和非經(jīng)濟偏好的路線演化。只要國際制度系統(tǒng)仍然被單獨功能和微弱權(quán)力的各種國際組織所分割,國家一直都會依賴單邊經(jīng)濟措施。這也為在經(jīng)濟戰(zhàn)略和非經(jīng)濟價值方面不存在普遍共識的事實所證明。甚至在日益致密的國際義務(wù)構(gòu)架里,主權(quán)國家仍是單邊貿(mào)易措施的法律依據(jù),而國際法規(guī)則也只是在某些場合下對其有所約束。主要風(fēng)險在于國際機構(gòu)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以及其法律會導(dǎo)致有關(guān)單邊貿(mào)易措施合法性的不一致結(jié)論。毋庸置疑,國家有權(quán)單邊決定其國內(nèi)事務(wù),但不能未經(jīng)他國同意而將其意志強加于他國。國家的單邊貿(mào)易措施不得違反其以公約或單方行為的方式承擔(dān)的義務(wù),更不得與習(xí)慣國際法規(guī)則相違背。雖然WTO具有限制單邊措施的潛在能力,但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仍擔(dān)心單邊經(jīng)濟制裁成為“政治和經(jīng)濟脅迫”的手段。為此,聯(lián)合國大會決議“促請國際社會采取緊急和有效的措施,消除對發(fā)展中國家采用既未經(jīng)聯(lián)合國相關(guān)機關(guān)授權(quán)、又不符合《聯(lián)合國憲章》所闡述的國際法原則并且違反多邊貿(mào)易體制基本原則的單方面經(jīng)濟脅迫措施”。正因為歐盟單方面收取航空碳稅,有違背《國際民用航空公約》(TheInternationalCivilA-viationCovenant,即“芝加哥公約”)第1條的領(lǐng)空主權(quán)原則之嫌,且該措施可能會導(dǎo)致與歐盟有航空服務(wù)貿(mào)易往來的大多數(shù)國家利益受損,從而遭到這些國家的聯(lián)合抵制。如果歐盟在這一問題上繼續(xù)一意孤行,多國可能對其實施反制措施,并可能引發(fā)嚴重的貿(mào)易戰(zhàn)。因此,歐盟方面建議“有條件暫停”航空碳稅新法規(guī)部分內(nèi)容,這是對航空碳稅一貫表示強硬態(tài)度的歐盟第一次“松口”。這表明,即便是大國也不能輕易肆意去破壞規(guī)則,采取單邊行動以削弱或規(guī)避國際法的束縛。在某些情況下,即便美國和有限數(shù)量的主要大國無視國際法規(guī)則,其作為國際法之違法者的負面聲譽仍然存在,并經(jīng)常危及其與他國在未來關(guān)系中的領(lǐng)導(dǎo)者地位。大國的決策者還顧慮到來自國內(nèi)反對黨、媒體機構(gòu)和非政府組織對其違反國際法的政府決策的消極反應(yīng)。
綜上所述,包括WTO在內(nèi)的多邊貿(mào)易協(xié)定仍是國家處理對外貿(mào)易事務(wù)不可或缺的工具。當國家之間針對某項貿(mào)易議題進行談判時,通常也是通過締結(jié)條約的方式表達其承諾。國際秩序必須具有靈活性,但國家首先應(yīng)當考慮是否可通過協(xié)商方式解決,而非貿(mào)然地采取單邊措施。從“蝦和海龜案”可知,在首先窮盡國際談判之前,沒有國家可采取單邊措施。瑖瑧由于國際法對于單邊行動尚未形成明確統(tǒng)一的規(guī)則,如何在國家合法運用主權(quán)以追求人權(quán)、環(huán)境等價值目標與不適當?shù)貑芜吰x國際法規(guī)則的貿(mào)易措施之間劃定一條清楚的界限,仍有待國際法的繼續(xù)發(fā)展才能見分曉。
作者:韓逸疇單位:華東政法大學(xué)國際法專業(yè)2010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