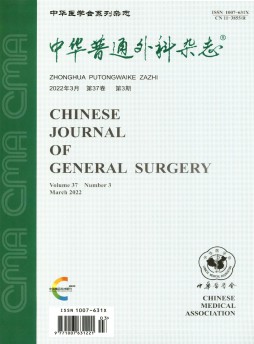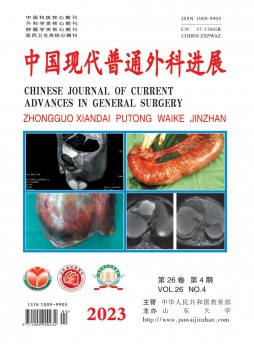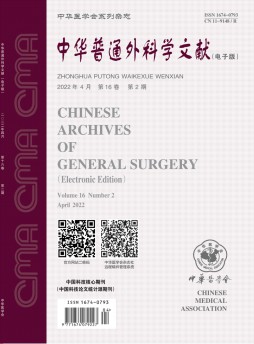普通論文范文
前言:寫(xiě)作是一種表達(dá),也是一種探索。我們?yōu)槟闾峁┝?篇不同風(fēng)格的普通論文參考范文,希望這些范文能給你帶來(lái)寶貴的參考價(jià)值,敬請(qǐng)閱讀。

茶文化考古和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驛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杭州有著極久遠(yuǎn)的茶文化史。代代傳承,源遠(yuǎn)流長(zhǎng),據(jù)一些茶學(xué)研究者認(rèn)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橋人就有飲茶的習(xí)慣。”這段話引起筆者極大的詫異,因?yàn)楣P者所知有關(guān)跨湖橋遺址的報(bào)道里,并沒(méi)有跨湖橋人已知飲茶的內(nèi)容。正如序言所說(shuō),跨湖橋人有飲茶的習(xí)慣,是“一些茶學(xué)研究者認(rèn)定”的,那末這和考古學(xué)界無(wú)關(guān),應(yīng)該到茶學(xué)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尋找。
在《倡導(dǎo)茶為國(guó)飲、打造杭為茶都~高級(jí)論壇論文集》里(2005年)終于找到答案。論文百事通那是該論文集獲得優(yōu)秀論文獎(jiǎng)的作品,題目是“根深流長(zhǎng)的杭州茶文化之開(kāi)發(fā)暢想”(以下簡(jiǎn)稱(chēng)《暢想》)。這篇論文很長(zhǎng),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許為“茶史研究上的一個(gè)突破”和“開(kāi)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領(lǐng)域”。本文是專(zhuān)就《暢想》第一部分展開(kāi)討論,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兩節(jié)敘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較完整發(fā)展環(huán)節(jié)證據(jù)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讓我們看看作者是怎樣在這兩節(jié)里展開(kāi)他的“考古”和“論證”的。
關(guān)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
說(shuō)跨湖橋有茶,是根據(j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跨湖橋》發(fā)掘報(bào)告(2005)附錄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顆炭化的植物種子,附有茶的學(xué)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錄部分附錄表二一(365頁(yè))地層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種實(shí)遺存和數(shù)量統(tǒng)計(jì)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顆茶子,與彩版相呼應(yīng)。此外,《跨湖橋》發(fā)掘報(bào)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態(tài)與經(jīng)濟(jì)》的“植被和氣候”節(jié),詳細(xì)敘述了跨湖橋植被的演變內(nèi)容,分為六部分:1,闊葉、針葉混交林階段;2,干旱、較干旱稀疏林~草叢階段;3,闊葉、針葉混交林發(fā)展階段;4,沼澤植被發(fā)展階段;5,干旱闊葉林混交林~草叢、沼澤發(fā)展階段;6,落葉、常綠混交林~草叢發(fā)展階段。這六節(jié)里敘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獨(dú)沒(méi)有提到茶(不論野生或栽培)。這不是遺漏或疏忽,是因這顆唯一的炭化種子,在制作附錄彩版說(shuō)明時(shí),工作人員覺(jué)得它象茶子,臨時(shí)給它一個(gè)茶的學(xué)名,因并未經(jīng)專(zhuān)家鑒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敘述,就是說(shuō),所謂茶子只供業(yè)內(nèi)人討論鑒定,不供發(fā)表引用的。嚴(yán)格地說(shuō),這也是整理報(bào)告時(shí)不夠慎重,正確的做法應(yīng)該是把炭化種子的定名寫(xiě)作Camellia?表明沒(méi)有最后鑒定,便不致引起誤會(huì)。
聽(tīng)說(shuō)《暢想》一文的作者??訪問(wèn)過(guò)文物考古所,該所同志一再告訴他這是初步鑒定,不可據(jù)為定論引用。但《暢想》的作者堅(jiān)持作為茶子引用,所以這事與考古所無(wú)關(guān),是《暢想》作者個(gè)人的見(jiàn)解。遺憾的是,《暢想》作者不去質(zhì)疑或糾正考古所的鑒定,反而作為肯定依據(jù),并大加發(fā)揮,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現(xiàn)今的茶樹(shù)資源,除栽培種Camelliasinensis外,還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見(jiàn)《浙江林業(yè)自然資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業(yè)廳編,2002)。現(xiàn)在僅憑一顆炭化的種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種,不是其他茶種?另一種可能性是,這顆炭化種子根本不是茶屬種子,這類(lèi)差錯(cuò)在其他出土種子的鑒定失誤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植物種子??誤鑒定為蠶豆、花生、芝麻,后來(lái)糾正)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舉例介紹。不過(guò)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種子鑒定的失誤,是單純的鑒定水平不夠,鑒定人對(duì)被鑒定物沒(méi)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意圖。而“暢想”作者顯然是抱著追溯茶文化源頭,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調(diào)子發(fā)揮的。
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發(fā)現(xiàn)一個(gè)殘破的釜,里面有一塊焦黑的殘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號(hào)的“藥”釜和“藥”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頁(yè))說(shuō)明這份標(biāo)本曾送浙江省藥品檢驗(yàn)所中藥室檢測(cè),定為莖葉類(lèi),沒(méi)有進(jìn)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莖葉。但“暢想”作者根據(jù)茶、藥同源的理論,認(rèn)為“藥”釜應(yīng)即茶釜(見(jiàn)《中國(guó)文物報(bào)》(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藥品檢驗(yàn)所中藥室都沒(méi)有肯定的“藥”釜,一變而成肯定的茶釜,這樣的“考古”能有說(shuō)服力嗎?百事通
期刊特征與被引頻次的關(guān)系
1研究現(xiàn)狀
現(xiàn)有學(xué)者對(duì)期刊特征和被引之間關(guān)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載文量、基金論文比、論文合著者、引文特征、出版時(shí)滯等方面,具體如下:
(1)期刊載文量。Elizee等[1]認(rèn)為,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和讀者數(shù)量增加,用戶(hù)可以更方便地獲取論文,期刊載文量的增加可以提高期刊被引量。陳留院[2]以36家?guī)煼洞髮W(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為例,發(fā)現(xiàn)期刊的學(xué)術(shù)影響力與載文量成正相關(guān)。劉巖等人[3-5]的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結(jié)論。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觀點(diǎn)。譬如,王鐘健等[6]以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類(lèi)期刊為樣本的研究顯示,期刊載文量的增加與期刊學(xué)術(shù)質(zhì)量之間沒(méi)有必然聯(lián)系。
(2)期刊基金論文比。Shen等[7]對(duì)ACMSIGIR、ACMSIGKDD兩個(gè)國(guó)際會(huì)議論文的研究,以及Pqi等[8]對(duì)2010~2012年WOS收錄的自然科學(xué)論文的研究均表明,基金論文的學(xué)術(shù)影響力高于普通論文。戚爾鵬和葉鷹[9]通過(guò)分析WOS數(shù)據(jù)收錄的2010~2012年基礎(chǔ)學(xué)科論文,發(fā)現(xiàn)除邏輯學(xué)以外,所有基礎(chǔ)學(xué)科的基金資助引用優(yōu)勢(shì)為正,這表明基金論文的被引頻次和影響力普遍高于非基金論文。劉睿遠(yuǎn)等人[10-12]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diǎn)。但是,王謙等[13]對(duì)中文醫(yī)學(xué)核心期刊的研究和林麗芳[14]對(duì)高校學(xué)報(bào)的研究卻顯示,基金論文比與期刊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不完全具有相關(guān)性,基金論文與其學(xué)術(shù)影響力之間不存在必然聯(lián)系。而徐晶等[15]分析2007~2011年口腔醫(yī)學(xué)類(lèi)期刊基金論文的引用情況之后,指出基金論文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期刊質(zhì)量,但是不能單純依此評(píng)判期刊的質(zhì)量。
(3)論文合著者。Glänzel和Thijs[16]的研究發(fā)現(xiàn),生物醫(yī)學(xué)、化學(xué)和數(shù)學(xué)領(lǐng)域論文的平均引用率隨著合作者的數(shù)量而增長(zhǎng);Leimu和Koricheva[17]進(jìn)一步指出,4個(gè)共同作者的平均引用率高于3個(gè)、2個(gè)或1個(gè)。鐘鎮(zhèn)[18]以2004~2008年WOS圖情學(xué)科研究型論文為樣本,發(fā)現(xiàn)按照合著人數(shù)進(jìn)行分組,圖情學(xué)科4人合著論文的篇均被引頻次最高,但合著者的數(shù)量與論文被引影響力之間不能劃等號(hào),合著作者數(shù)的提高未必能帶來(lái)論文被引頻次的提高。類(lèi)似的,Glänzel和Schubert[19]的國(guó)際合著研究也發(fā)現(xiàn),相當(dāng)一部分國(guó)際合著論文的被引績(jī)效低于研究樣本的平均水平。Abramo和Ange⁃lo[20]的研究同樣拒絕了作者數(shù)量與期刊影響力之間的正相關(guān)假設(shè)。論文合著研究除了作者之間的合作,還包括機(jī)構(gòu)之間的合作。趙金燕[21]發(fā)現(xiàn),機(jī)構(gòu)分布數(shù)與被引頻次高度相關(guān),對(duì)被引頻次有較強(qiáng)的解釋能力。盛麗娜[22]也認(rèn)為,用作者機(jī)構(gòu)的分布情況評(píng)價(jià)科技期刊影響力優(yōu)于使用影響因子和被引頻次。
(4)引文特征。Biglu[23]以SCI和WOS為數(shù)據(jù)源,發(fā)現(xiàn)期刊的引文量和被引量具有一定的線性關(guān)系。期刊的篇均引文量越大,相應(yīng)的被引量也就越高,期刊引文量和期刊的被引量之間會(huì)形成“馬太效應(yīng)”。Didegah和Thelwall[24]也認(rèn)為適當(dāng)數(shù)量的參考文獻(xiàn)將提高其獲得更多被引用的可能性。在國(guó)內(nèi),程慧平和萬(wàn)莉[12]也持相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平均引文量表明了學(xué)術(shù)論文的研究起點(diǎn)和深度,可以反映論文的學(xué)術(shù)水平,而且周吉光等[25]還提出,期刊引用半衰期衡量了期刊刊載文獻(xiàn)的參考文獻(xiàn)的時(shí)效跨度,期刊引用半衰期短,意味著該刊對(duì)較短期內(nèi)發(fā)表的較新的研究文獻(xiàn)的興趣度。
(5)期刊出版時(shí)滯。Tsay等[26]對(duì)醫(yī)學(xué)期刊2000年JCR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研究發(fā)現(xiàn),出版頻次較高的期刊被引頻次也高。Shen等人[27]以Nature、Science、Cell三種期刊為對(duì)象的研究顯示,期刊發(fā)文時(shí)滯與被引頻次之間存在相關(guān)性。與此類(lèi)似,Pautasso和Schäfer[28]發(fā)現(xiàn),生態(tài)學(xué)期刊平均編輯延遲天數(shù)與影響因子之間存在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但是,韓牧哲等[29]對(duì)圖書(shū)情報(bào)學(xué)中文核心期刊的研究卻表明,雖然論文的影響力與其發(fā)表時(shí)滯的長(zhǎng)短存在相關(guān)關(guān)系,具有能使論文影響力最大化的理想時(shí)滯區(qū)間,但是,發(fā)表時(shí)滯并非越短越好。同樣,劉俊婉等[30]以Scientometrics和《情報(bào)學(xué)報(bào)》為例,發(fā)現(xiàn)期刊論文的發(fā)文時(shí)滯與論文被引頻次之間僅具有相關(guān)性趨勢(shì),但并不顯著。綜上,雖然已有不少研究分析了期刊特征與被引之間的關(guān)系,但是,在許多方面并未達(dá)成共識(shí)。為了準(zhǔn)確地揭示國(guó)內(nèi)期刊特征與被引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有針對(duì)性地指導(dǎo)工作實(shí)踐和管理決策,本研究在系統(tǒng)梳理現(xiàn)有期刊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的基礎(chǔ)上,提煉出11個(gè)期刊特征指標(biāo),分析它們與期刊被引之間的關(guān)系。
2數(shù)據(jù)獲取與主成分回歸分析
喝茶歷史和文化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驛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杭州有著極久遠(yuǎn)的茶文化史。代代傳承,源遠(yuǎn)流長(zhǎng),據(jù)一些茶學(xué)研究者認(rèn)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橋人就有飲茶的習(xí)慣。”這段話引起筆者極大的詫異,因?yàn)楣P者所知有關(guān)跨湖橋遺址的報(bào)道里,并沒(méi)有跨湖橋人已知飲茶的內(nèi)容。正如序言所說(shuō),跨湖橋人有飲茶的習(xí)慣,是“一些茶學(xué)研究者認(rèn)定”的,那末這和考古學(xué)界無(wú)關(guān),應(yīng)該到茶學(xué)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尋找。
在《倡導(dǎo)茶為國(guó)飲、打造杭為茶都~高級(jí)論壇論文集》里(2005年)終于找到答案。那是該論文集獲得優(yōu)秀論文獎(jiǎng)的作品,題目是“根深流長(zhǎng)的杭州茶文化之開(kāi)發(fā)暢想”(以下簡(jiǎn)稱(chēng)《暢想》)。這篇論文很長(zhǎng),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許為“茶史研究上的一個(gè)突破”和“開(kāi)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領(lǐng)域”。本文是專(zhuān)就《暢想》第一部分展開(kāi)討論,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兩節(jié)敘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較完整發(fā)展環(huán)節(jié)證據(jù)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讓我們看看作者是怎樣在這兩節(jié)里展開(kāi)他的“考古”和“論證”的。
關(guān)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
說(shuō)跨湖橋有茶,是根據(j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跨湖橋》發(fā)掘報(bào)告(2005)附錄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顆炭化的植物種子,附有茶的學(xué)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錄部分附錄表二一(365頁(yè))地層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種實(shí)遺存和數(shù)量統(tǒng)計(jì)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顆茶子,與彩版相呼應(yīng)。此外,《跨湖橋》發(fā)掘報(bào)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態(tài)與經(jīng)濟(jì)》的“植被和氣候”節(jié),詳細(xì)敘述了跨湖橋植被的演變內(nèi)容,分為六部分:1,闊葉、針葉混交林階段;2,干旱、較干旱稀疏林~草叢階段;3,闊葉、針葉混交林發(fā)展階段;4,沼澤植被發(fā)展階段;5,干旱闊葉林混交林~草叢、沼澤發(fā)展階段;6,落葉、常綠混交林~草叢發(fā)展階段。這六節(jié)里敘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獨(dú)沒(méi)有提到茶(不論野生或栽培)。這不是遺漏或疏忽,是因這顆唯一的炭化種子,在制作附錄彩版說(shuō)明時(shí),工作人員覺(jué)得它象茶子,臨時(shí)給它一個(gè)茶的學(xué)名,因并未經(jīng)專(zhuān)家鑒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敘述,就是說(shuō),所謂茶子只供業(yè)內(nèi)人討論鑒定,不供發(fā)表引用的。嚴(yán)格地說(shuō),這也是整理報(bào)告時(shí)不夠慎重,正確的做法應(yīng)該是把炭化種子的定名寫(xiě)作Camellia?表明沒(méi)有最后鑒定,便不致引起誤會(huì)。
聽(tīng)說(shuō)《暢想》一文的作者曽訪問(wèn)過(guò)文物考古所,該所同志一再告訴他這是初步鑒定,不可據(jù)為定論引用。但《暢想》的作者堅(jiān)持作為茶子引用,所以這事與考古所無(wú)關(guān),是《暢想》作者個(gè)人的見(jiàn)解。遺憾的是,《暢想》作者不去質(zhì)疑或糾正考古所的鑒定,反而作為肯定依據(jù),并大加發(fā)揮,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現(xiàn)今的茶樹(shù)資源,除栽培種Camelliasinensis外,還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見(jiàn)《浙江林業(yè)自然資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業(yè)廳編,2002)。現(xiàn)在僅憑一顆炭化的種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種,不是其他茶種?另一種可能性是,這顆炭化種子根本不是茶屬種子,這類(lèi)差錯(cuò)在其他出土種子的鑒定失誤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植物種子曽誤鑒定為蠶豆、花生、芝麻,后來(lái)糾正)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舉例介紹。不過(guò)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種子鑒定的失誤,是單純的鑒定水平不夠,鑒定人對(duì)被鑒定物沒(méi)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意圖。而“暢想”作者顯然是抱著追溯茶文化源頭,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調(diào)子發(fā)揮的。
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發(fā)現(xiàn)一個(gè)殘破的釜,里面有一塊焦黑的殘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號(hào)的“藥”釜和“藥”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頁(yè))說(shuō)明這份標(biāo)本曾送浙江省藥品檢驗(yàn)所中藥室檢測(cè),定為莖葉類(lèi),沒(méi)有進(jìn)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莖葉。但“暢想”作者根據(jù)茶、藥同源的理論,認(rèn)為“藥”釜應(yīng)即茶釜(見(jiàn)《中國(guó)文物報(bào)》(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藥品檢驗(yàn)所中藥室都沒(méi)有肯定的“藥”釜,一變而成肯定的茶釜,這樣的“考古”能有說(shuō)服力嗎?
淺談抗戰(zhàn)時(shí)期淪陷區(qū)內(nèi)的大學(xué)教育
[摘要]北平淪陷后,高等教育受到嚴(yán)重破壞,輔仁大學(xué)因其德國(guó)教會(huì)背景得以保持相對(duì)獨(dú)立。通過(guò)輔仁大學(xué)學(xué)生董毅的日記可以看出,在淪陷時(shí)期,輔仁大學(xué)抵制日偽的奴化教育,堅(jiān)持開(kāi)設(shè)傳統(tǒng)文化課程,重視語(yǔ)文、歷史及體育團(tuán)體活動(dòng),而對(duì)不得不開(kāi)設(shè)的日文課程,師生多采取應(yīng)付態(tài)度以消極對(duì)抗。輔仁大學(xué)在北平淪陷時(shí)期的獨(dú)立色彩,成為青年學(xué)生躲避“漢奸教育”尋求民族文化根脈的文化家園,凝聚著師生們的愛(ài)國(guó)情懷及對(duì)日本侵略者的隱性抵抗,而輔仁大學(xué)也通過(guò)堅(jiān)持辦學(xué)自主性,為戰(zhàn)后儲(chǔ)備人才做出了一定貢獻(xiàn)。
[關(guān)鍵詞]輔仁大學(xué);淪陷時(shí)期;戰(zhàn)時(shí)教育;董毅日記
北平淪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遷或停辦。整個(gè)淪陷時(shí)期,一直堅(jiān)持原有辦學(xué)的高校為數(shù)不多[1],其中,輔仁大學(xué)作為淪陷前北平“五大學(xué)”之一,堅(jiān)持傳統(tǒng)的辦學(xué)特色,抵制日偽的奴化政策,被譽(yù)為“抗日大本營(yíng)”[2](p.164)。學(xué)界對(duì)于淪陷時(shí)期的輔仁大學(xué)已有相關(guān)研究,這些研究多聚焦于校長(zhǎng)陳垣及國(guó)民黨政權(quán)對(duì)輔仁大學(xué)的組織等問(wèn)題,而對(duì)輔仁學(xué)生在校的真實(shí)學(xué)習(xí)狀態(tài)少有關(guān)注。本文以1938年9月考入輔仁大學(xué)國(guó)文系的董毅的日記①為主體史料,從一個(gè)普通學(xué)生的角度觀察輔仁大學(xué)在淪陷時(shí)期的辦學(xué)特色,以及淪陷區(qū)青年學(xué)生對(duì)抗戰(zhàn)的感受和認(rèn)知。
一、堅(jiān)守在淪陷區(qū)進(jìn)行戰(zhàn)時(shí)教育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大學(xué)教育受到嚴(yán)重破壞,清華等多所高校陸續(xù)南遷,最初幾年,“碩果僅存,賴(lài)以支撐這半壁江山的,只有燕京、輔仁兩私立大學(xué)。這兩所學(xué)校,因是教會(huì)所立,由外人為靠山,所以尚能茍延殘喘”[3](p.27)。輔仁大學(xué)和燕京大學(xué)在“驚濤巨浪中,屹然未動(dòng)”,一同被視為“魯?shù)铎`光”[4]。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輔大還保持著半獨(dú)立”[5](p.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學(xué)也最終被迫關(guān)閉[6](p.58),僅剩輔仁大學(xué)與其他日偽直接進(jìn)駐的大學(xué)有所不同[7](p.240),故在一般民眾眼中,當(dāng)時(shí)的輔仁大學(xué)成為淪陷區(qū)“站在教育界的先鋒”[8]。淪陷時(shí)期,青年學(xué)生報(bào)考高校會(huì)有所比較和考量,如有人所言:“處在日寇占領(lǐng)時(shí)期,京津地區(qū)比較有名的大學(xué)是北京大學(xué)、燕京大學(xué)和輔仁大學(xué)。北大雖是老字號(hào),但是日偽直接管理的學(xué)校,不甘心報(bào)考。燕京大學(xué)是英、美系統(tǒng)的大學(xué),已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隨時(shí)將面臨被封閉接收的噩運(yùn)。只有輔仁大學(xué),雖校齡很短,但因是德國(guó)教會(huì)主政,而德國(guó)是軸心國(guó)之一,日寇因同盟關(guān)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寬松些。許多著名老師也多齊集輔仁,因此成為大多數(shù)青年學(xué)子報(bào)考的焦點(diǎn)”[9](p.264)。所以,在整個(gè)淪陷時(shí)期,輔仁大學(xué)不僅“仍照常開(kāi)辦”[10](p.697),其規(guī)模還得到進(jìn)一步擴(kuò)大。北平淪陷后,“輔仁在應(yīng)付上,雖較困難,差幸尚能上課”[11]。師生們深切地感受到學(xué)校所處的困難境遇,但“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應(yīng)付困難事件,總抱不屈不撓的態(tài)度……英、美、德使館方面,也能隨時(shí)贊助”,以至在整個(gè)淪陷時(shí)期輔仁大學(xué)能堅(jiān)持原有教學(xué)風(fēng)格[10](p.697)。輔仁大學(xué)借助教會(huì)的力量應(yīng)對(duì)日偽政府管控的同時(shí),一直和國(guó)民政府保持聯(lián)系,接受?chē)?guó)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開(kāi)放狀態(tài),基本延續(xù)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學(xué)設(shè)置,培養(yǎng)了青年的愛(ài)國(guó)精神。輔仁大學(xué)還建議與京津地區(qū)其他國(guó)際教育組織協(xié)力合作,以如下三條原則為指導(dǎo):“(一)獨(dú)立管理(二)學(xué)術(shù)自由(三)不懸偽旗幟;以示正義不屈。”[12](p.7)正因輔仁大學(xué)在抗戰(zhàn)時(shí)期堅(jiān)持原有的辦學(xué)特色,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后,南京國(guó)民政府教育部把輔仁大學(xué)與后方大學(xué)一同對(duì)待,無(wú)條件地承認(rèn)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時(shí)輔仁大學(xué)的學(xué)歷證書(shū)。而淪陷時(shí)期日偽控制的其他高校的畢業(yè)生,則必須參加補(bǔ)習(xí)和考試才能得到國(guó)民政府的學(xué)歷認(rèn)可[13](pp.209-213)。這是國(guó)民政府對(duì)輔仁大學(xué)在淪陷時(shí)期堅(jiān)持原有教學(xué)方針的認(rèn)可,同時(shí)也是國(guó)民政府戰(zhàn)時(shí)教育政策的落實(shí)。戰(zhàn)爭(zhēng)開(kāi)始時(shí),對(duì)于教育是要服務(wù)于戰(zhàn)爭(zhēng),是應(yīng)該保持正常的教育體系,社會(huì)上存在很多爭(zhēng)論。在重慶召開(kāi)的第三次全國(guó)教育會(huì)議上的講話指出,雖然教育不可以獨(dú)立于國(guó)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著眼點(diǎn)不僅在戰(zhàn)時(shí),還應(yīng)該看到戰(zhàn)后,不應(yīng)把所有的青年都無(wú)條件地從課堂、實(shí)驗(yàn)室、研究室趕到戰(zhàn)場(chǎng)上去[14](pp.128-129)。國(guó)民政府戰(zhàn)時(shí)教育政策鼓勵(lì)青年學(xué)生在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堅(jiān)持完成教育。
二、堅(jiān)持開(kāi)設(shè)傳統(tǒng)文化課程
占領(lǐng)北平后,日本“為使中國(guó)人民徹底認(rèn)識(shí)‘東亞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視各種教育,控制了北平原有學(xué)校,開(kāi)設(shè)了各種師資訓(xùn)練學(xué)校和“職業(yè)學(xué)校”,強(qiáng)迫中國(guó)子弟入學(xué)。就大學(xué)教育方面,日本開(kāi)展所謂事業(yè)本位的教育,設(shè)立了偽“北京工商學(xué)校”,以及偽“北京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農(nóng)學(xué)院、工學(xué)院、理學(xué)院、文學(xué)院等。日偽政府除從日本方面聘請(qǐng)教授,設(shè)立日本文學(xué)、日本美術(shù)、日本精神講座等科外,還組織了“臨時(shí)政府教科書(shū)編審科”,將各校課本一律改成奴化色彩濃厚的所謂“漢奸”教科書(shū)[15](p.24)。淪陷時(shí)期,很多過(guò)去的國(guó)立大學(xué),都由日偽組織直接控制,校門(mén)前豎起日本國(guó)旗,派入大批日籍教師和教官,有的學(xué)校師生每天進(jìn)校門(mén)時(shí),要向日本國(guó)旗、日本軍官行禮。學(xué)校強(qiáng)迫學(xué)生讀日文,有的學(xué)校必須用日文課本,或不準(zhǔn)讀中國(guó)歷史,有的大學(xué)則用從東北運(yùn)來(lái)的偽“滿洲國(guó)”編寫(xiě)的歷史教材,進(jìn)行奴化教育。日本在華北的教育政策不似東北那樣強(qiáng)化,重在控制而不是發(fā)展,因此,“也不是無(wú)漏洞可鉆”[13](pp.174-175)。輔仁大學(xué)雖然從外部也不能擺脫日偽統(tǒng)治的管理,如當(dāng)時(shí)日偽政權(quán)各種管理機(jī)構(gòu)不下十幾個(gè)①,但由于德國(guó)人及教會(huì)方面與日偽政府周旋,經(jīng)過(guò)往復(fù)協(xié)商,校內(nèi)教學(xué)體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課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課本,不懸掛日本國(guó)旗,日文不作為必修課程[7](pp.239-240)。與日偽直接控制的大學(xué)不同,輔仁大學(xué)在整個(gè)淪陷時(shí)期的課程設(shè)置仍基本保持原有體系,堅(jiān)持用中國(guó)課本。如學(xué)生在第一學(xué)年一般性的必修課較多,專(zhuān)業(yè)性課程較少。學(xué)校特別要求,無(wú)論何院、何系,在第一學(xué)年必修“國(guó)文”及“英語(yǔ)”等語(yǔ)文課,而“國(guó)文”每?jī)芍苡幸淮巫魑模⑦x優(yōu)者于“以文會(huì)友”玻璃櫥窗公開(kāi)展示。“于此不難想象校方強(qiáng)化語(yǔ)文教育,以乃重視民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p.270)。董毅第一學(xué)年,每周四也選了必修課國(guó)文[17](p.37)。輔仁大學(xué)國(guó)文課的目的是強(qiáng)化語(yǔ)文教育。董毅所上國(guó)文課內(nèi)容有二:一是講授、背誦漢文經(jīng)典。如董毅在國(guó)文課上聽(tīng)授了《洪亮吉與崔瘦生書(shū)》《讓太常博士書(shū)》,背誦了《后漢書(shū)•吳裕傳》等[17](p.12)。二是訓(xùn)練學(xué)生的漢文寫(xiě)作能力,如寫(xiě)作《論文字之功用》《讀書(shū)小記(別記)》《春日紀(jì)游》等題目的文章。有時(shí)教師也會(huì)給學(xué)生講“普通錯(cuò)漢字”[17](p.99)。國(guó)文考試所出題目也以此為宗旨,如標(biāo)點(diǎn)幾段《后漢書(shū)》、寫(xiě)作《一年來(lái)對(duì)國(guó)文作文之興趣》為題的文章等[17](p.106)。對(duì)于國(guó)文系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這些是最基本的訓(xùn)練。董毅顯然比較喜歡國(guó)文,認(rèn)為自己這個(gè)科目學(xué)得不錯(cuò),在考國(guó)文的時(shí)候自認(rèn)“不甚難,答的還滿意”[17](p.21)。輔仁大學(xué)加強(qiáng)漢語(yǔ)教育,以此來(lái)重視傳統(tǒng)民族文化,國(guó)文作為必修課只是其中一個(gè)措施。其他科目輔仁大學(xué)也基本保持了淪陷前的課程設(shè)置,董毅1939年所選課程便可證明這一點(diǎn)。董毅在日記中記載了他選的課程,1939年上半年(即一年級(jí)第二學(xué)期),除了體育、英語(yǔ)、國(guó)文等必修課,專(zhuān)業(yè)課程有目錄學(xué)、聲韻學(xué)、中國(guó)文學(xué)史、邏輯學(xué)、文字學(xué)、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只有日語(yǔ)課是為了應(yīng)付時(shí)局而開(kāi)設(shè)的新課。1939年下半年(即第二學(xué)年第一學(xué)期),除了英語(yǔ)外,其余均為專(zhuān)業(yè)相關(guān)課程,包括唐宋詩(shī)、詞及詞史、文字學(xué)名著、經(jīng)學(xué)通論、各體散文習(xí)作、倫理學(xué)、中國(guó)小說(shuō)史、新文藝習(xí)作。這些專(zhuān)業(yè)課程都是延續(xù)淪陷前國(guó)文系的課程設(shè)置,教師也多是淪陷之前即在國(guó)文系授課,如目錄學(xué)余嘉錫、聲韻學(xué)及文字學(xué)名著沈兼士、邏輯學(xué)英千里、文字學(xué)陸宗達(dá)①、唐宋詩(shī)儲(chǔ)皖峰、詞及詞史孫人和、倫理學(xué)伏開(kāi)鵬、中國(guó)小說(shuō)史孫楷第等。從教師配置與課程設(shè)置來(lái)看,輔仁大學(xué)具有很高的穩(wěn)定性和繼承性,特別是國(guó)文系,依然側(cè)重語(yǔ)文教育,重視民族傳統(tǒng)文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日偽的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延續(xù)了中華民族的文脈與內(nèi)在精神。如儲(chǔ)皖峰開(kāi)設(shè)的唐宋詩(shī)課程,訓(xùn)練學(xué)生作詩(shī)填詞。
1939年10月的一次課,儲(chǔ)先生出的兩道題目,一是《重九登白塔》,一是《晚秋新雨》[17](p.219)。董毅交上了自己所做的詩(shī),一周后,儲(chǔ)先生發(fā)回修改后的詩(shī)。1939年11月的一次課,儲(chǔ)先生又出了兩個(gè)題目,讓學(xué)生寫(xiě)《霧松》和《司馬池》。董毅自稱(chēng)“向來(lái)不會(huì)作詩(shī)”[17](p.219),但經(jīng)過(guò)學(xué)習(xí),能夠按時(shí)完成這些詩(shī)詞作業(yè)。日偽政府為進(jìn)行奴化教育,很多有關(guān)中日關(guān)系及現(xiàn)代中國(guó)的書(shū)籍都被查禁,但對(duì)中國(guó)歷史書(shū)籍的查禁不太嚴(yán)格,對(duì)大學(xué)內(nèi)中國(guó)歷史的課程監(jiān)控也不甚嚴(yán),輔仁大學(xué)校長(zhǎng)陳垣就在校內(nèi)開(kāi)設(shè)了歷史課程。1939年下半年,作為國(guó)文系學(xué)生的董毅選修了陳垣《中國(guó)史學(xué)名著評(píng)論》課程。陳垣對(duì)學(xué)生要求嚴(yán)格,在課堂上講授《史記》《漢書(shū)》等經(jīng)典史書(shū),并留了許多課后作業(yè)。如1939年10月初,陳垣讓學(xué)生整理三國(guó)以前現(xiàn)存書(shū)目錄。董毅為了完成作業(yè),到學(xué)校圖書(shū)館查閱了《四庫(kù)總目提要》,還到國(guó)立北平圖書(shū)館查閱了一些參考書(shū)[17](p.197),花費(fèi)了很多工夫,一個(gè)多星期后的10月16日課上交了作業(yè)[17](p.205)。之后,陳垣又給學(xué)生們陸續(xù)留了兩個(gè)題目,整理“史漢異同目錄”與《玉函山房輯佚書(shū)》引用書(shū)目。董毅和大多數(shù)普通學(xué)生一樣,從心里認(rèn)可校長(zhǎng)的講授,認(rèn)為“很有條理也明白”[17](p.205),認(rèn)真地去完成作業(yè)。以整理《玉函山房輯佚書(shū)》引用書(shū)目為例,董毅共“抄了共有五百六七十種之多”[17](p.242)。陳垣對(duì)學(xué)生的作業(yè)認(rèn)真批改。董毅對(duì)歷史的學(xué)習(xí)是主動(dòng)的,并不是羨于校長(zhǎng)的名望,因此,聽(tīng)課“兩小時(shí)精神專(zhuān)一”[17](p.268)。課余時(shí)間,董毅也會(huì)去圖書(shū)館看歷史書(shū)籍,旁聽(tīng)感興趣的歷史課程[17](p.190)。從董毅的日記還可看出,國(guó)文系各科的考試也多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和歷史方面的題目。如1939年11月的季中考試,詞及詞史的考試題目是作一首詞《浣溪沙》或者“溫韋李三人合論”[17](p.254);文字學(xué)名著的題目是“試述讀段注說(shuō)文之方法”[17](p.256);中國(guó)史學(xué)名著評(píng)論題目是“后漢書(shū)之?dāng)⑹路ㄅc史漢有大不相同之點(diǎn),試詳述之”[17](p.257);經(jīng)學(xué)通論考試題目是“‘經(jīng)學(xué)展史’開(kāi)辟時(shí)代書(shū)后”[17](p.259)。即便是與時(shí)代聯(lián)系比較緊密的新文藝習(xí)作也考的是諸如“如何寫(xiě)一個(gè)劇本”“舞臺(tái)藝術(shù)的重要”“評(píng)父歸”等題目[17](p.255),與日偽政府所進(jìn)行奴化宣傳的內(nèi)容毫無(wú)聯(lián)系。從以上課程設(shè)置和董毅所學(xué)內(nèi)容可以佐證,輔仁學(xué)生“對(duì)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意識(shí)形態(tài)或有關(guān)日本和德國(guó)研究的題目毫無(wú)興趣”[13](p.210),而是仍專(zhuān)注于學(xué)習(xí)中國(guó)傳統(tǒng)歷史與文化。從這個(gè)意義上講,輔仁開(kāi)設(shè)的科目培養(yǎng)了青年的愛(ài)國(guó)精神,延續(xù)了民族教育。
中國(guó)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歷史發(fā)展
摘要:中國(guó)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形成經(jīng)歷一個(gè)長(zhǎng)期的歷史過(guò)程,在萌芽時(shí)期,職業(yè)教育理論進(jìn)行初步的發(fā)展;在依附階段,是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發(fā)展的探索時(shí)期;到了完善階段,基本上形成職業(yè)教育的學(xué)科體系。盡管如此,隨著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變化,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研究進(jìn)入反思和重構(gòu)階段,必須確立職業(yè)教育是一個(gè)研究領(lǐng)域而不只是個(gè)獨(dú)立學(xué)科的觀點(diǎn),建立具有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中國(guó)范式的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模式。
關(guān)鍵詞: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學(xué)科體系;研究范式;反思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探尋我國(guó)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發(fā)展的變遷過(guò)程,以及在變遷過(guò)程中所呈現(xiàn)的研究特點(diǎn),進(jìn)而為我國(guó)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反思和重構(gòu)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萌芽時(shí)期:職業(yè)教育理論的初步發(fā)展
這個(gè)歷史時(shí)期可以限定于1840-1949年,這個(gè)歷史時(shí)期既是中國(guó)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萌芽時(shí)期,也是傳統(tǒng)職業(yè)教育理論的發(fā)展時(shí)期。在這個(gè)歷史時(shí)期,由于我國(guó)當(dāng)時(shí)特殊的國(guó)情與經(jīng)濟(jì)形勢(shì),職業(yè)教育實(shí)踐形態(tài)主要是學(xué)徒制,同時(shí)也伴有部分的學(xué)校制。隨著職業(yè)教育實(shí)踐的發(fā)展,其理論體系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顯然,在這一歷史時(shí)期,職業(yè)教育理論的體系發(fā)展與一大批具有實(shí)干精神的教育家是分不開(kāi)的。他們對(duì)于實(shí)業(yè)救國(guó)、實(shí)業(yè)教育的倡導(dǎo)、論證、指導(dǎo)、實(shí)踐,對(duì)職業(yè)教育理論的發(fā)展起到重要的推動(dòng)作用。1902年,山西大學(xué)堂總督辦姚文棟在“添聘普通教習(xí)文”中對(duì)職業(yè)教育的作用有著精辟的論述,他認(rèn)為:“論教育之形式,與國(guó)民關(guān)系最為密切者,乃是職業(yè)教育……職業(yè)教育與普通教育分屬教育之兩端,缺一不可。”[1]這個(gè)表述應(yīng)當(dāng)是中國(guó)歷史上最早的關(guān)于職業(yè)教育的認(rèn)知。隨著職業(yè)教育的實(shí)踐發(fā)展,人們對(duì)職業(yè)教育的概念開(kāi)始探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陸費(fèi)逵先生,當(dāng)時(shí)他擔(dān)任《教育雜志》總編,在該雜志創(chuàng)刊詞中,他發(fā)表了如下觀點(diǎn),即中國(guó)教育最需要改進(jìn)的是國(guó)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職業(yè)教育,而其中最緊迫的乃是職業(yè)教育,因?yàn)椤奥殬I(yè)教育是教人謀生的教育形式,是教人擁有一技之長(zhǎng)的教育形態(tài)”[2]。從這個(gè)表述可以看出,其對(duì)職業(yè)教育的內(nèi)涵做出一個(gè)基本界定,這個(gè)界定體現(xiàn)了職業(yè)教育的實(shí)踐屬性,即職業(yè)教育是技術(shù)技能教育。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學(xué)者開(kāi)始注意到職業(yè)教育的理論問(wèn)題,但在當(dāng)時(shí),教育研究的主流依然是普通教育,特別是在科舉被廢之后,對(duì)普通教育的形式、實(shí)踐形態(tài)的討論依然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fā),民族資本主義的快速發(fā)展既激發(fā)了社會(huì)對(duì)技術(shù)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從客觀上促進(jìn)了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這一時(shí)期,不少教育先驅(qū)對(duì)職業(yè)教育開(kāi)展深入的理論研究工作,在蔡元培、黃炎培、晏陽(yáng)初等人的引領(lǐng)下,創(chuàng)辦了一批職業(yè)教育的學(xué)校,同時(shí)也開(kāi)展了大量的職業(yè)教育理論研究,涌現(xiàn)出一批學(xué)術(shù)成果,包括引進(jìn)和翻譯的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著作和論文。如1916年出版的,由朱景寬編寫(xiě)的《職業(yè)教育通論》,是我國(guó)近代第一部職業(yè)教育的專(zhuān)著,后來(lái),相繼出現(xiàn)了朱元善翻譯的《職業(yè)教育精義》(1917年)、顧樹(shù)生的《外國(guó)職業(yè)教育學(xué)》(1917年)、潘文安的《職業(yè)教育ABC》(1927年)、陳表的《各國(guó)勞動(dòng)教育概覽》(1930年)、何清儒的《職業(yè)教育學(xué)》(1941年)等;除了這些著作以外,像陶行知、晏陽(yáng)初等人還發(fā)表了多篇論述職業(yè)教育特性方面的論文。顯然,這一時(shí)期的職業(yè)教育理論研究工作,既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職業(yè)教育實(shí)踐的總結(jié),也對(duì)當(dāng)時(shí)職業(yè)教育實(shí)踐發(fā)展起到一定的指導(dǎo)作用,還論證了職業(yè)教育實(shí)踐與理論體系之間的關(guān)系。特別是何清儒的《職業(yè)教育學(xué)》,用今日之眼光看,依然是一部觀點(diǎn)清晰、體系嚴(yán)密的學(xué)術(shù)著作[3]。整體觀之,這一歷史時(shí)期的職業(yè)教育理論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職業(yè)教育的概念、性質(zhì)、作用、地位以及與普通教育的關(guān)系等方面,這些問(wèn)題是職業(yè)教育理論的基本問(wèn)題,因此,在總體上還沒(méi)有形成系統(tǒng)的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盡管如此,這些先驅(qū)的探究對(duì)于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構(gòu)建,還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為我國(guó)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發(fā)展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因此,這個(gè)時(shí)期既可以稱(chēng)為傳統(tǒng)職業(yè)教育理論時(shí)期,也是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萌芽時(shí)期。
二、依附時(shí)期: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探索
1.對(duì)普通教育理論的依附職業(yè)教育從一開(kāi)始引入中國(guó)就未能取得獨(dú)立地位,在理論研究上,也是從普通教育內(nèi)部脫胎而形成的,可以說(shuō)職業(yè)教育理論是借鑒普通教育理論而形成的。換言之,普通教育理論猶如“母體”,而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是由“母體”孕育的“子體”。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初期,我國(guó)深受蘇聯(lián)教育模式的影響,在實(shí)踐及理論研究方面也是完全照抄照搬蘇聯(lián)的,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職業(yè)教育的理論依附性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直到1980年代中期,職業(yè)教育的研究者才開(kāi)始意識(shí)到職業(yè)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區(qū)別以及二者理論體系之間的差異,此時(shí)才開(kāi)始嘗試運(yùn)用普通教育學(xué)的基本理論對(duì)職業(yè)教育的內(nèi)涵、概念、價(jià)值、形態(tài)、地位、規(guī)律等基本問(wèn)題進(jìn)行探究,逐漸建立職業(yè)教育的理論體系[4]。這一時(shí)期的學(xué)術(shù)著作、論文也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華東師范大學(xué)職業(yè)教育研究所編著的《技術(shù)教育概論》、天津師范大學(xué)編著的《職業(yè)教育概論》等,較為系統(tǒng)地以普通教育理論為基準(zhǔn)來(lái)闡釋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
2.對(duì)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依附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改革開(kāi)放后,國(guó)內(nèi)學(xué)界職業(yè)教育理論研究積累嚴(yán)重不足,以及職業(yè)教育實(shí)踐剛從“”中恢復(fù)不久,因此這一時(shí)期我國(guó)職業(yè)教育的研究者開(kāi)始將目光瞄準(zhǔn)國(guó)外,希望通過(guò)翻譯和引介國(guó)外的職業(yè)教育理論來(lái)完善我國(guó)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當(dāng)時(shí),關(guān)于國(guó)外的職業(yè)教育研究成果豐富,呈現(xiàn)以下三個(gè)方面的特點(diǎn):第一,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理論研究的成果形式豐富多樣。既有翻譯國(guó)外學(xué)者關(guān)于職業(yè)教育的著作,如1981年由河北大學(xué)比較教育研究所翻譯的日本倉(cāng)內(nèi)史郎、宮地誠(chéng)哉的《職業(yè)教育》,也有國(guó)內(nèi)學(xué)者研究具體國(guó)家的職業(yè)教育相關(guān)論文,如王曉明發(fā)表在1985年第4期《比較教育研究》上的《談?wù)劼?lián)邦德國(guó)的職業(yè)教育》;陳希蓮發(fā)表在1985年第10期《人民教育》上的《西班牙的勞動(dòng)教育和職業(yè)訓(xùn)練》等。第二,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理論研究的內(nèi)容較為廣泛。既有對(duì)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基本介紹的,也有涉及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管理的,還有涉及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政策方面的,更有涉及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另外,部分學(xué)者探討了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的課程及教法。總之,這些研究涉及領(lǐng)域眾多,理論性較強(qiáng)。第三,國(guó)外職業(yè)教育研究關(guān)注面較廣。
傳播學(xué)學(xué)科教育
傳播學(xué)作為一門(mén)新興的科學(xué)在我國(guó)大陸興起的時(shí)間并不長(zhǎng),直到現(xiàn)在也還沒(méi)有真正獨(dú)立,還是一個(gè)二級(jí)學(xué)科。沒(méi)有獨(dú)立,說(shuō)明它還稚嫩,還有很好的發(fā)展前景。然而,最不湊巧的是,在它還十分稚嫩的時(shí)候,碰上新中國(guó)歷史上尚未出現(xiàn)過(guò)的大學(xué)生就業(yè)難的時(shí)期,因此,對(duì)于它的未來(lái),大家都十分關(guān)心,特別是學(xué)習(xí)傳播學(xué)的同學(xué)特別關(guān)心。為此,我談?wù)勛约旱目捶ǎ┐蠹覅⒖肌N医裉煲v的主題就是:傳播學(xué)的發(fā)展趨勢(shì)、學(xué)科教育與就業(yè)問(wèn)題。
圍繞這個(gè)主題,我講四個(gè)內(nèi)容:1、傳播學(xué)在中國(guó)大陸的現(xiàn)狀;2、未來(lái)的發(fā)展趨勢(shì);3、傳播學(xué)教育的問(wèn)題與發(fā)展方向;4、傳播學(xué)與就業(yè)。
一、傳播學(xué)在中國(guó)大陸的現(xiàn)狀
傳播學(xué)七十年代傳入我國(guó)大陸。那個(gè)時(shí)候,除了少數(shù)學(xué)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傳播學(xué)。進(jìn)入80年代,更多的中國(guó)大陸學(xué)者開(kāi)始對(duì)傳播學(xué)發(fā)生興趣。
1982年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在北京召開(kāi)第一次傳播學(xué)研討會(huì),有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人民大學(xué)、廈門(mén)大學(xué)及《新聞戰(zhàn)線》等單位共20多人參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傳播學(xué)被批評(píng)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為“不講階級(jí)斗爭(zhēng)”,有人說(shuō),中國(guó)只能有宣傳學(xué),不能有傳播學(xué)。
1992年鄧小平南巡,引發(fā)了新一輪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國(guó)大眾傳播媒介的改革,使傳播學(xué)再度受到關(guān)注。從1993年開(kāi)始,由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新聞研究所與相關(guān)新聞院系、研究單位合辦的全國(guó)性傳播學(xué)研討會(huì),成為每?jī)赡暌淮蔚娜珖?guó)會(huì)議,至今已開(kāi)辦了第八次。
從第八次全國(guó)傳播學(xué)研討會(huì)來(lái)看,歷經(jīng)20多年,傳播學(xué)在中國(guó)大陸可以說(shuō)取得了跨越式發(fā)展。八十年代是傳播學(xué)的登陸期,兩次都差點(diǎn)被趕下海。之后,僅十來(lái)年的時(shí)間,就召開(kāi)了多次全國(guó)性會(huì)議,一次比一次規(guī)模大:人越來(lái)越多,研究的問(wèn)題越來(lái)越廣泛深入。第一次研討會(huì)有點(diǎn)像搞地下工作,門(mén)口還要有人“把關(guān)”。現(xiàn)在開(kāi)會(huì)已是大張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國(guó)傳播學(xué)研討會(huì),不僅有大陸的大多數(shù)著名的新聞傳播學(xué)專(zhuān)家,港臺(tái)學(xué)者,還有不少外國(guó)專(zhuān)家,如日、韓、新加坡、美、英等國(guó)的專(zhuān)家蒞臨。不僅參加人數(shù)多,一共220多位,還有不少北京各大學(xué)前來(lái)旁聽(tīng)的碩士、博士生。地點(diǎn)則選擇了最高學(xué)府清華大學(xué),由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院長(zhǎng)范敬宜擔(dān)任會(huì)議主席。
中古聲調(diào)演變
【論文關(guān)鍵詞】聲調(diào)中古語(yǔ)音近代語(yǔ)音現(xiàn)代語(yǔ)音
【論文摘要】聲調(diào)是字音(音節(jié))的要素之一。音節(jié)有聲調(diào)是漢藏語(yǔ)系語(yǔ)言的特點(diǎn),在漢語(yǔ)以及與漢語(yǔ)同系的語(yǔ)言中。聲調(diào)在區(qū)別詞的意義方面的重要性和聲母、韻母相等。本文從古音聲母清濁方面,就漢語(yǔ)的聲調(diào)及其發(fā)展演變,對(duì)中古語(yǔ)音的聲調(diào)、近代語(yǔ)音的聲調(diào)以及現(xiàn)代語(yǔ)音的聲調(diào)做了簡(jiǎn)單的思考與論述。
所謂聲調(diào),是指音節(jié)讀音高低升降的變化。
漢語(yǔ)從何時(shí)起就有了聲調(diào)的存在,現(xiàn)在還無(wú)法斷言。通常認(rèn)為,上古漢語(yǔ)也應(yīng)該有聲調(diào)的區(qū)別,但究竟有多少個(gè)調(diào)類(lèi),它們可能的調(diào)值如何,至今尚無(wú)定論。而中古時(shí)期的漢語(yǔ)語(yǔ)音的聲調(diào)區(qū)別已經(jīng)得到了共識(shí),并且,當(dāng)時(shí)的音韻學(xué)者已開(kāi)始對(duì)這種區(qū)別進(jìn)行了深入的、系統(tǒng)的研究。
一、中古語(yǔ)音的聲調(diào)概述
漢代以前,人們還不知道有四聲,直到齊梁間駢體文盛行,受佛教轉(zhuǎn)讀佛經(jīng)聲調(diào)的影響,逐漸覺(jué)察到自己的語(yǔ)言中也有聲調(diào)存在,開(kāi)始以“宮、商、角、徵、羽”五音對(duì)字音進(jìn)行歸納,隨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稱(chēng)為四聲。《切韻》、《廣韻》、《韻鏡》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聲”分韻的。
四聲的名稱(chēng)起于南北朝齊梁時(shí)代(五世紀(jì)末六世紀(jì)初),據(jù)《南史•陸厥傅》說(shuō):齊永明年間,“時(shí)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x,瑯?e王融,以氣類(lèi)相推轂,汝南周?J善識(shí)聲韻。約等為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永明時(shí)期的這段敘述是平、上、去、入“四聲”名稱(chēng)見(jiàn)于記載的較早的材料。此外,《梁書(shū)•沈約傳》云:“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dú)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wèn)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J傳》記云:“?J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shí)。”
“四聲”只是歸納了中古時(shí)期語(yǔ)音的調(diào)類(lèi),至于各個(gè)聲調(diào)具體的調(diào)值如何,古人沒(méi)有明確的記載,我們只能從古人的形象的描繪中感受到大致的概括:“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yuǎn),入聲急而促。”我們由此可推測(cè),中古時(shí)期四聲中的平聲是平調(diào),入聲是短促調(diào)。因?yàn)槠铰暃](méi)有升降,較長(zhǎng),而其他三聲或有升降或短促,所以“平聲”與“上、去、入”三聲形成了平與仄兩大類(lèi)型。
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起源及其流變演講范文
本文對(duì)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在古代中國(guó)、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國(guó)的產(chǎn)生、發(fā)展及演變的過(guò)程進(jìn)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在中國(guó)古代即已出現(xiàn),但多用為“律學(xué)”,且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有著重大區(qū)別;現(xiàn)代意義上的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原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后伴隨著日本近代化的過(guò)程而產(chǎn)生,并由日本傳入中國(guó)的。在考察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由日本傳入中國(guó)的途徑之后,作者指出,古代意義上的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兩者所依據(jù)的世界觀不同:前者強(qiáng)調(diào)的是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力意識(shí)和臣民的義務(wù)、責(zé)任,將法視為役使臣民的工具;后者強(qiáng)調(diào)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權(quán)威性,將法視為保障公民權(quán)利的手段。最后,作者還指出,多年來(lái),我們對(duì)“法學(xué)”一詞仍抱有一種排斥心理,這與我國(guó)輕視法學(xué)的傳統(tǒng)意識(shí)有一定聯(lián)系。
作者何勤華,1955年生,華東政法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教授。
現(xiàn)在我們所使用的“法學(xué)”一詞,是一個(gè)舶來(lái)品,它的故鄉(xiāng)在古代羅馬,是經(jīng)過(guò)二千余年的發(fā)展、演變,才為西方各個(gè)國(guó)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傳入中國(guó)。那么,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的起源、流變是什么樣的?它反映了古代、近代中國(guó)人怎樣的法律意識(shí)和法律觀念?本文將對(duì)此進(jìn)行探討。
一
在中國(guó)近代以前的辭書(shū)(如《康熙字典》)或現(xiàn)代出版的解釋中國(guó)古典文獻(xiàn)的辭書(shū)(如《甲骨金文字典》、《辭源》、《辭海》等)中,是沒(méi)有“法學(xué)”一詞的。據(jù)高名凱、王立達(dá)和實(shí)藤惠秀等中日學(xué)者的研究,“法學(xué)”一詞是近代中國(guó)人在向日本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從日本傳入中國(guó)的(2)。然而,這個(gè)結(jié)論僅僅在下述意義上才正確,即現(xiàn)代含義的漢語(yǔ)“法學(xué)”一詞是從日本傳入的;“法學(xué)”一詞早在中國(guó)古代即已出現(xiàn)。
在我國(guó),“法”和“學(xué)”字出現(xiàn)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了。在我國(guó)古語(yǔ)中,“法”字寫(xiě)作“灋”。在中國(guó)現(xiàn)存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現(xiàn)了(鹿去“比”加“與”去“一”為灬)字,寫(xiě)作□(讀zhi)(3),相傳是一種善于審判案件的神獸。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該字事實(shí)上就是我國(guó)法的締造者蚩尤部落的圖騰(4)。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現(xiàn)了“灋”字,寫(xiě)作□(克鼎)(5)。至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出現(xiàn)了灋的簡(jiǎn)體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灋字仍被頻繁地使用(這從前幾年考古發(fā)現(xiàn)的云夢(mèng)秦簡(jiǎn)《語(yǔ)書(shū)》中可以得知),有時(shí)也與“法”字一起出現(xiàn)在同一篇文獻(xiàn)中(6)。漢代以后,灋字逐漸消失,為“法”字所取代。
“學(xué)”字比“法”字出現(xiàn)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學(xué)”字,寫(xiě)作“□”。在金文中,“學(xué)”字有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寫(xiě)作“D”(7)。古代教、學(xué)通用,釋義為:
一、教也,《靜簋》:“靜學(xué)(教)無(w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