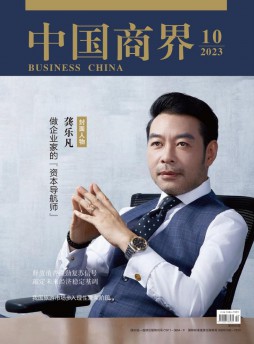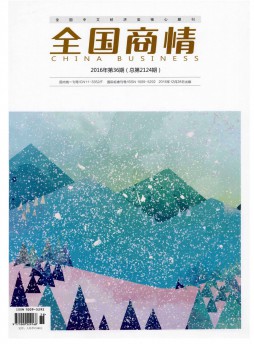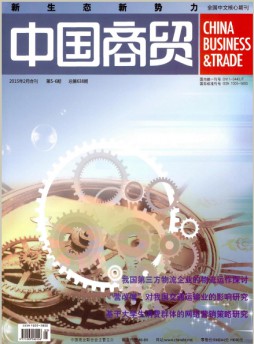中國商文學(xué)研討的興盛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中國商文學(xué)研討的興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現(xiàn)代社會,西方人憑借發(fā)達(dá)的物質(zhì)文明而成為世界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他們已經(jīng)將“物質(zhì)”置換為“精神”,把物質(zhì)文明的相對落后等同于精神上的貧弱枯乏、急需指導(dǎo)和拯救,帝國主義就因而有了堂而皇之推行的理由。抓住物質(zhì)的主導(dǎo)權(quán)成了掌握話語權(quán)力、實現(xiàn)精神自由的前提條件。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恪守清貧、以強化精神來傲視物質(zhì)的生存方式失去了由來已久的贊嘆和仰慕,也難以再獲得心靈的平靜和滿足。以追求物利為直接目的的商人群體就此站到了社會舞臺的中央,以其為描寫對象的商文學(xué)及其研究也日益興盛。
一術(shù)語界定
“商人”指以買賣或經(jīng)營為職業(yè)的人,包括現(xiàn)代企業(yè)的中高層管理者。“商文學(xué)”這一提法則是筆者在綜合已有的相關(guān)術(shù)語的基礎(chǔ)上提出來的,與已有的“經(jīng)濟(jì)小說”、“財經(jīng)文學(xué)”、“儒商文學(xué)”、“商賈小說”等術(shù)語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經(jīng)濟(jì)小說”指一切圍繞經(jīng)濟(jì)題材為中心的小說,不單指商業(yè)。“財經(jīng)文學(xué)”則聚焦于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業(yè)。香港梁鳳儀創(chuàng)作的很多財經(jīng)小說曾引起財經(jīng)文學(xué)熱。“儒商文學(xué)”這一提法主要源自暨南大學(xué)的潘亞暾先生,包括“儒商寫”由儒商作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以及“寫儒商”以儒商為描寫對象的作品。①邱紹雄的《中國商賈小說史》(2004)則確立了“商賈小說”這一提法,指“以商人為主人公、以商人經(jīng)商求利活動為主要表現(xiàn)內(nèi)容的小說”②,本研究的“商文學(xué)”概念基本借鑒于他。在這個全球性的商業(yè)時代,“經(jīng)濟(jì)小說”的提法過于寬泛;“儒商文學(xué)”這一概念帶有濃厚的道德價值評判色彩,況且在當(dāng)代社會什么是“儒商”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商賈小說”中的“商賈”這一術(shù)語的中國古代色彩過于濃厚。綜合以上考慮,筆者提出“商文學(xué)”這一概念,指以描寫商業(yè)或商人為主要內(nèi)容的文學(xué)作品,以往提出的“財經(jīng)文學(xué)”、“商賈小說”都是商文學(xué)的一部分。
二我國傳統(tǒng)商人與商文學(xué)的歷史困境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農(nóng)業(yè)國。逐漸成為社會價值坐標(biāo)的圣人之道與農(nóng)業(yè)文明相適應(yīng),努力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培養(yǎng)出安于土地、不思流動、懂禮知節(jié)、忠君愛人的好臣民。這一導(dǎo)向的一個自然結(jié)果就是有意忽視、壓制容易帶來不穩(wěn)定因素的商業(yè)。歷代統(tǒng)治階級重農(nóng)抑商做法的主要原因多半在于糧食和兵源乃古代強國之根本。對于農(nóng)業(yè)國而言,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可以提供馴順的人民,分散而穩(wěn)定的農(nóng)人及其自足而微薄的愿望不構(gòu)成對整個體制的威脅,其剩余產(chǎn)品總和又大到足以支撐整個體制的運轉(zhuǎn)。相對于能提供大量的糧食和穩(wěn)定的兵源的農(nóng)業(yè)而言,商業(yè)則更容易給封建統(tǒng)治階級制造不穩(wěn)定因素。在科技通信很不發(fā)達(dá)的古代,中央政府要監(jiān)控幅員廣大的疆土顯得力不從心。零星散布、老死不相往來的閉塞農(nóng)村,難以聚眾生事,自然對統(tǒng)治者不構(gòu)成威脅。商業(yè)活動性強,超過一定限度便會破壞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穩(wěn)定性。如果商人形成強大的社會階層,一方面會造成從商者眾而農(nóng)業(yè)人口不斷流失,另一方面也容易促長政治野心,這將對統(tǒng)治階級的集權(quán)統(tǒng)治構(gòu)成嚴(yán)重威脅。所以,重農(nóng)抑商政策是我國歷代封建帝王的必然選擇。
逐漸地,農(nóng)與商不再是兩種簡單的經(jīng)濟(jì)活動的區(qū)分,而是代表了兩種人生道德境界。《呂氏春秋•上農(nóng)》中指出,農(nóng)民樸實而易使喚,天真而不自私,念家而不思游,在國家有難時,他們也從不輕易棄家而逃;而商人則心腸壞,詭計多,很自私,流動性強,一旦國家有難,他們總是逃往國外。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是,不僅在經(jīng)濟(jì)上農(nóng)業(yè)比商業(yè)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農(nóng)也比商高尚。
與這種重農(nóng)輕商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適應(yīng),古代文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輕商賤商的傾向,對商人的輕蔑與對商業(yè)本身的隔膜,使得商人很難成為他們的描寫對象,更別說成為作品中的英雄主角,這是古代商文學(xué)不發(fā)達(dá)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王充《論衡•佚文篇》記述的一個故事:
揚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錢十萬,愿載于書,子云不聽,曰:“夫富賈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
這則故事清楚地展示了古代士商壁壘與商人雖富仍屈的歷史命運。就商人本身而言,由于他們處于文化劣勢,自己沒有掌握話語權(quán)力,也難于進(jìn)行自我創(chuàng)作和自我辯護(hù)。當(dāng)然,古代商文學(xué)中也有不少同情甚至贊頌商人的篇章。但是,其同情與贊頌的基點往往在于道德層面而不是商才層面。從總體上看,由于生產(chǎn)方式的限制,古代商文學(xué)處于仁義道德對求利的疏遠(yuǎn)與壓制這一大環(huán)境中,其進(jìn)步性主要表現(xiàn)在宣揚求利并不害義這一點,還停留在努力為商人贏得道義上的同情、道德上的認(rèn)可這一階段,并且不少作品仍透露出士人的優(yōu)越感,對商人群體進(jìn)行著比較簡單的價值判斷,最終成為農(nóng)業(yè)文化的維護(hù)者而缺乏對現(xiàn)實的批判力度。
三商人的崛起與商文學(xué)的興盛
我們知道,現(xiàn)代化、全球化首先是經(jīng)濟(jì)的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jì)的全球化,“環(huán)顧世局,要提高國力,并不需要槍彈大炮沖鋒陷陣。利用經(jīng)濟(jì)力量,最能夠立竿見影。”③這是著名印尼華商李文正的一段名言。而商人群體正是現(xiàn)代化、全球化進(jìn)程的先鋒隊。綜觀近五六百年間的西方歷史,曾先后崛起的西方大國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都是靠商業(yè)尤其是海外貿(mào)易使國力迅速強盛起來的。新的時代呼喚新的英雄,在今天這個商業(yè)時代,以物質(zhì)成功為直接目的的商人群體就此站到了社會舞臺的中央,成為新的時代英雄。
在我國,直到改革開放之前,商人一直是帶著鐐銬跳舞的一群,在數(shù)千年封建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和重農(nóng)輕商傾向的陰影下,在國力式微的尷尬與屈辱中,他們的奮斗與抗?fàn)幨侨绱似D苦和悲壯。1978年12月,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的工作重心轉(zhuǎn)移到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上來。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指出:“商業(yè)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人民的生活,這個問題在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重要性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地顯示出來。……我們必須在充分了解情況、認(rèn)真總結(jié)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切實改進(jìn)商業(yè)工作,大力疏通、擴(kuò)大和增加流通渠道,做到貨暢其流,物盡其用,充分發(fā)揮商業(yè)在促進(jìn)生產(chǎn)、引導(dǎo)生產(chǎn)、保障供應(yīng)、繁榮經(jīng)濟(jì)中的作用。”④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決定》,使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進(jìn)一步得到發(fā)展和完善。國營商業(yè)的壟斷局面從此打破,形成百家經(jīng)營的局面,出現(xiàn)廣泛的經(jīng)商熱潮。1978年從事個體商業(yè)的人員只有2萬人,到1985年底迅速發(fā)展到1000萬人以上。個體商業(yè)零售額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0.1%上升到14.6%。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商業(yè)教育也蓬勃發(fā)展,為壯大商業(yè)隊伍、提升商人群體的整體素質(zhì)提供了有力保障。1982年,商業(yè)部門直屬高等院校就達(dá)10所,還辦了兩所商業(yè)專科學(xué)校,并在其他部門辦的8所院校內(nèi)設(shè)立了12個對口專業(yè);中等商業(yè)學(xué)校達(dá)到199所。⑥這些學(xué)校共同培養(yǎng)出各種層次的大批商業(yè)人才。政策的扶持、教育的支撐使中國商人獲得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空間,他們逐漸成為時代的風(fēng)云人物受到各方關(guān)注。
商人走上歷史的前臺,商場成為沒有硝煙的廣闊戰(zhàn)場,為現(xiàn)代社會的成就與問題搭建出絕佳的時代展臺。如何揭示、規(guī)避現(xiàn)代性之弊而張揚其利,不僅是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話題,也是現(xiàn)當(dāng)代所有深具人文關(guān)懷意識的作家們時時刻刻思考的問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生活最為敏感的“攝影師”,自然會對商場這個時代展臺以及展臺上的主角進(jìn)行多方位的照攝。于是商文學(xué)相應(yīng)興盛起來,文學(xué)長廊中出現(xiàn)了一批鮮活的商人形象,這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數(shù)千年輕商賤商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大國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視做文化發(fā)展與轉(zhuǎn)型的一個重要風(fēng)向標(biāo)。
香港的梁鳳儀從1989年開始在七八年間創(chuàng)作出版的五十多部“財經(jīng)小說”無論在中國港臺地區(qū)、海外華人社區(qū)還是中國大陸都掀起一陣研讀的熱潮。1991年,她獲得香港市政局和藝術(shù)家聯(lián)盟聯(lián)合頒發(fā)的最高作家年獎,同年底她創(chuàng)辦自己的出版社,次年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系列商文學(xué)作品,小說印數(shù)最低6.5萬冊最高達(dá)10萬冊,到1995年底她的作品在大陸的正版銷量達(dá)到200萬冊。1993年3月3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和中國社科院文研所還聯(lián)合舉辦了梁鳳儀作品的研討會。⑦這種高規(guī)格的待遇足已顯示出她的財經(jīng)文學(xué)對時代之心弦的精準(zhǔn)觸撥。“這些作品不但給我們提供了香港這個發(fā)達(dá)的自由商業(yè)社會一幅幅光怪陸離的生活畫面,而且還向我們呈現(xiàn)著一種文學(xué)的存在方式,提示著這種發(fā)達(dá)商業(yè)社會文學(xué)發(fā)展與創(chuàng)作的某種態(tài)勢。這是很值得我們關(guān)注、思考以至借鑒的。”⑧在我國,文與商之間矛盾對立的一面被歷史性地一再強化,使人們幾乎難以想象如何去實現(xiàn)兩者的和諧統(tǒng)一。而梁鳳儀無論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還是創(chuàng)辦出版社都比較成功地實現(xiàn)了文與商之間的和諧統(tǒng)一、相互促進(jìn)。這對于已經(jīng)感覺到商業(yè)大潮的濃烈氣息而又在忙亂中找不到出路的國人來說無疑有類似福音的效果。
當(dāng)梁鳳儀筆下的香港商業(yè)風(fēng)云逐漸淡去的時候,國內(nèi)的商文學(xué)開始風(fēng)起云涌,而這種興盛是時代使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明顯感覺到,在市場上流行的通俗小說中,商文學(xué)占的比例快速增大,哪怕是言情小說也紛紛以商場為背景。其中的代表作如臺灣作家高陽的《胡雪巖全傳》,這本書無論是在70年代初的臺灣還是在90年代初的大陸的先后出版,都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甚至被人視為“成功商人圣經(jīng)”⑨來加以研讀。近年來更是出現(xiàn)數(shù)量眾多、且頗有收視率的商戰(zhàn)電視劇,如《商界》、《龍票》、《東方商人》、《胡雪巖》、《大清藥王》、《錢王》、《大染房》、《天下第一樓》、《背叛》、《白銀谷》、《昌晉源票號》、《喬家大院》等等。現(xiàn)在,剛出版不久的《圈子圈套》、《青瓷》、《灰商》、《輸贏》等商小說正在熱銷當(dāng)中,每本的銷量基本都在5萬冊以上,有些還超過了10萬冊。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學(xué)術(shù)性著名的大學(xué)出版社介入商文學(xué)的出版,如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圈子圈套》、《圈套玄機(jī)》,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輸贏》、《破冰》等,這說明商文學(xué)的價值在經(jīng)過市場驗證后,進(jìn)一步得到主流文化圈的認(rèn)可。商文學(xué)興盛的背后,是士商之間的歷史界限的消解。在全民經(jīng)商的熱潮中,哪怕是大學(xué)、科研機(jī)構(gòu),也紛紛創(chuàng)辦附屬產(chǎn)業(yè)尋找創(chuàng)收的出路,很多民辦學(xué)校本身就是商業(yè)的產(chǎn)物,以贏利為主要目的。在這個知識經(jīng)濟(jì)時代,士商結(jié)合似乎已成為時代驕子們的康莊大道。
四商文學(xué)的研究現(xiàn)狀
隨著商人作為新的時代英雄站在了社會舞臺的前面,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者開始日益關(guān)注這一群體。商文學(xué)的研究也開始興盛起來。在國內(nèi),其研究對象與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對傳統(tǒng)商文學(xué)資源的挖掘與清理。其代表性成果體現(xiàn)在三部專著上(從嚴(yán)格的意義上講只有兩部)。其中兩部是邵毅平的《傳統(tǒng)中國商人的文學(xué)呈現(xiàn)》(1993)B11和《中國文學(xué)中的商人世界》(2005)B12,前書分十多個主題加以論述,后者則以史的形式按照時代先后來闡述,但每一個時期細(xì)分為多個主題展開,前書的主要內(nèi)容基本融進(jìn)了后一書中。邵毅平的著作把史料梳理和主題研究相結(jié)合,有利于我們從多個角度透視古代商文學(xué)。其遺憾之處在于主題的劃分有些散亂,各主題之間有不少重疊交叉,分類層次上缺乏一種邏輯順序。還有一本是邱紹雄的《中國商賈小說史》(2004)B13,它完全是按傳統(tǒng)文學(xué)史的寫法來編排的,對社會背景、作家、作品內(nèi)容加以一一介紹,有比較高的史料價值,但此書只限于對小說體裁的梳理。在時間分野上,邵毅平的研究限定在古代文學(xué),邱紹雄的梳理止于近代小說。除了上面幾部專著,這方面的成果還包括一些碩士論文以及科研小論文。如《論中晚明通俗小說中的商人形象》(2001)、《汪道昆商人傳記研究》(2002)、《王世貞商人傳記研究》(2004)等碩士論文都入選了“中國優(yōu)秀博碩士學(xué)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關(guān)注“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商人形象的小論文更是為數(shù)眾多,這里不再一一枚舉。
其二,對近代以來的商文學(xué)作品的挖掘與闡釋。因為長期以來的農(nóng)業(yè)文明氛圍,古代商文學(xué)的資源確實比較有限,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把目光轉(zhuǎn)向和當(dāng)下聯(lián)系更為緊密的近代以來的商文學(xué)作品。姬文的《市聲》、吳趼人的《發(fā)財秘訣》、茅盾的《子夜》等商小說受到較多的關(guān)注。而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一批商業(yè)歷史小說與電視劇的走俏,它們以歷史上的名商巨賈為描寫對象,史實加虛構(gòu),描繪出一幅幅精彩悲壯的商業(yè)風(fēng)云畫卷,也引起研究者的濃厚興趣,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楊虹的系列論文《當(dāng)代歷史小說中商人精神的詩性張揚》(2003)、《商人精神的詩情闡釋以成一的〈白銀谷〉、鄧九剛的〈大盛魁商號〉為例》(2003)等,以及大量學(xué)者研究《胡雪巖全傳》的論文。但是,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研究的專著還未出現(xiàn)。
其三,對海外華商及其相關(guān)文學(xué)的關(guān)注。20世紀(jì)90年代興起的儒商研究和儒商文學(xué)研究就是這種關(guān)注的產(chǎn)物。儒商和儒商文學(xué)研究隨著十來次世界性的儒商大會而推動起來。首屆世界儒商大會于1994年7月26日至31日在海口召開,海內(nèi)外有百余位儒商和儒商作家與會,當(dāng)時的會牌是“首屆國際儒商暨儒商文學(xué)研討會”,這是極具開創(chuàng)性的文商結(jié)合的范例,不僅掀起儒商新風(fēng),促使華商學(xué)者化、儒商化,而且推動了海外華人文學(xué)的蓬勃發(fā)展。這次會議還成立了國際儒商學(xué)會,潘亞暾為創(chuàng)會會長。前面提到,“儒商文學(xué)”這一提法主要源自潘亞暾先生。他在研究臺港海外華文文學(xué)時發(fā)現(xiàn)了儒商和儒商文學(xué)這一現(xiàn)象,于1984年在一次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針對海外華商積極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狀況提出“16字訣”“亦商亦文,以商養(yǎng)文,商發(fā)文興,商文并茂”,強調(diào)這是曲線救文振興中華之道。有人譏笑潘先生的“儒商文學(xué)”是“銅臭文學(xué)”,認(rèn)為其“16字訣”“非學(xué)者之論”,但笑罵由人的潘先生經(jīng)過十年探索,寫成《儒商文學(xué)論稿》,于1994年7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儒商座談會上分發(fā)討論。首屆國際儒商暨儒商文學(xué)研討會也正是在潘先生的倡議、策劃下得以勝利召開。大會關(guān)于儒商文學(xué)的論文有云里風(fēng)的《漫談儒商文學(xué)》、汪義生的《儒商文學(xué)新走向》、費勇的《關(guān)于儒商文學(xué)及其評論》、張世君的《淺談西方儒商文學(xué)傳統(tǒng)》和王列耀的《意識的多層與儒商文學(xué)在當(dāng)代的必然》等。B141993年,北京文界為陳瑞獻(xiàn)、吳正、周穎南等儒商作家分別召開座談會和研討會,北大的季羨林先生場場登臺講話,稱贊他們一手拿算盤一手拿筆桿,為弘揚中華文化做出重要貢獻(xiàn)。這在文界真是一個很大的轉(zhuǎn)變。2004年,國際儒商學(xué)會十周年慶典暨首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在廣州舉行。十余年來這種華商與華文結(jié)合的會議方式大大推動了“儒商學(xué)”的發(fā)展。B15作為儒商學(xué)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商文學(xué)研究體現(xiàn)出敏銳的時代意識,順應(yīng)了現(xiàn)代人希望擺脫現(xiàn)代性困境、實現(xiàn)物質(zhì)與精神并舉的時代訴求。不過,儒商文學(xué)的相關(guān)研究還處在漫談、隨感層面,缺乏深層次的、系統(tǒng)的闡述。但是,儒商文學(xué)研究造成的聲勢與影響為商文學(xué)的研究與發(fā)展做了很好的鋪墊。這實在要感謝前輩們敏銳的時代嗅覺與敢于創(chuàng)新的勇氣。相信到現(xiàn)在,至少不會有人再譏笑本研究提出的“商文學(xué)”為“銅臭文學(xué)”了。
五構(gòu)想與展望
從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趨勢、商文學(xué)的蓬勃興盛及其研究現(xiàn)狀來看,商文學(xué)是一個大有可為的研究領(lǐng)域。我們可從以下三個層面來展開進(jìn)一步的研究。首先是對國別商文學(xué)進(jìn)行詳細(xì)的梳理與研究,探討一國商文學(xué)的流變、商人精神的詩情詮釋、商文學(xué)的當(dāng)代解讀等問題。其次,從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視角探討不同國家、不同文明間的商文學(xué)的異同,在文化互照中尋找商文學(xué)與文化模式的深層關(guān)聯(lián)等問題。再次,從族裔散居的角度研究商文學(xué),其關(guān)注的焦點是那些描寫跨越多種文化、率先受到多種文化合力作用的商人群體(如海外華商群體、猶太商人群體)的文學(xué)作品。他們的奮斗軌跡與文化發(fā)展方向?qū)τ谖覀兩羁塘私夂皖A(yù)示現(xiàn)代化、全球化的進(jìn)程極具典型意義。
從總體上看,綜觀世界文學(xué)史,金錢是經(jīng)久不衰的人性“試金石”。而以追求金錢為直接目的的商場,更是成為了人性的煉獄。在現(xiàn)當(dāng)代社會,隨著商業(yè)意識的遍播天下,商文學(xué)在揭示人性、現(xiàn)代性問題方面所具有的典型意義將日益突顯出來。比起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來,商文學(xué)作者們往往多了一層歷史理性,充分肯定物質(zhì)追求的正當(dāng)性。“人有無匱乏之自由”的這一現(xiàn)代人權(quán)理念是他們的歷史理性的支撐點。
但是,比起那些深陷物欲的泥淖、或被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緊緊抓住而失去否定能力的人,以及那些陷入純粹的價值虛無主義的人而言,商文學(xué)作者又多了一層人文關(guān)懷,他們清醒認(rèn)識到物質(zhì)繁華背后人的物化、生活的異化現(xiàn)象,并產(chǎn)生深切的憂慮。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面對這種現(xiàn)代性困境,商文學(xué)作者們往往懷著一種不可為而為的抗?fàn)幘?努力地提出一些拯救之方,給努力掙扎的現(xiàn)代人一抹希望,幾許慰藉。我們期待著商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進(jìn)一步繁榮與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