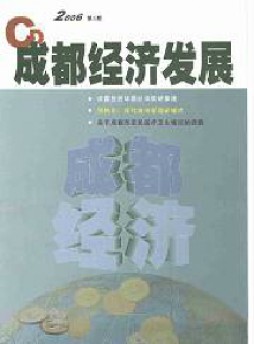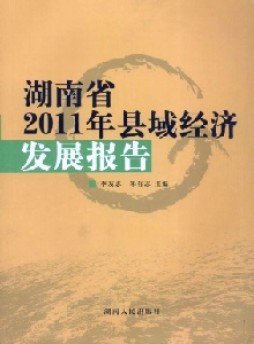經濟發展對文學演變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經濟發展對文學演變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
經濟生活與中國文學發展變遷的關系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文學研究中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但在相當一個長的時期內,我們只注重階級斗爭或者意識形態變化對文學變化發展的影響,而忽略或者貶低社會經濟生活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前幾年《文學評論》編輯部辟專欄討論這一問題,在學界影響很大,促進了學人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開拓了新的學術領域。但當時發表的文章偏重于古代文學,尤其是文體變化與經濟生活的關系,對現代經濟生活與文學發展變化的關系,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本文將探討的視點放在上世紀30年代,因為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者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民族資產主義發展極為艱難,封建王朝以及傳統思想阻礙了它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和經濟侵略,又幾乎摧折了它的生機。連年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中國陷入深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30年代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一次難得的機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在危難中前行。這個時期是中國現代史上社會經濟邁向基本現代化的最好時期,是所謂民族資產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30年代又是一個群星燦爛、流派紛呈的年代,在30年代社會現代性實踐的大背景下,知識分子基于不同政治及文化立場,建構起多元文學景觀。
顯然,對于現代文學研究來說,這是一個重要問題。直到現在,學界以意識形態批評對現代文學研究形成的思維定勢,以左翼政治意識形態文學作為30年代文學主潮的結論,對京派,海派與右翼文學的相對忽略是狹隘的。我們需要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重新回到30年代歷史的客觀語境,考察現代性問題與文學流派之間的深層關聯。對30年代現代文學的考查必須回溯至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現代性發展狀況,唯有對這個時代的現代性問題進行考查,才能對30年代文學進行合理定位。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現代性的肯定,與30年代左翼反現代性的批判視角形成歷史的鮮明對照,而30年代以現代化建設為主導的歷史及這段歷史中的相關問題都需要給予重新的認識與評價。
二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生重大轉折的時期。國家繼續把孫中山發達國家資本、發展國營經濟的理論,作為其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30年代,國家關注經濟建設的舉措,日本侵略的威脅,使原本保持中立立場、不介入政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關注,有的甚至介入到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為政府實施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經濟發展戰略提供有力人才保證。如國防設計委員會即是實例,該會容納了當時方方面面的著名專家,國際關系的王世杰、周覽、徐淑系,文化教育的胡適、楊振聲、張其昀,財經方面的吳鼎昌、陶孟和、劉大均,材料方面的丁文江、翁文灝(地質學家)等。
1927—1937年,中國政府經歷了中原大戰、長江水災、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入侵、3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國內的政治斗爭等多重危機。在如此復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下,國家在發展經濟,實現國家工業現代化為目標的指導思想下,使中國經濟在30年代形成了初步工業化的基礎;30年代的1936—1937年,是現代國民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段。1937年抗戰爆發,打亂了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促使國民經濟轉入戰時狀態。政府適應戰爭需要,改革經濟體制,調整工業政策,逐步建立了以重工業為主導的戰時工業經濟體系。
經濟發展實績:
通過這一時期的經濟數據,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發展的軌跡。1920年GDPl66.5億元(1933年幣值),1936年252.64億元,人均GDP分別是37.2,50.5;國民收入1920年202.37億元,1936年258.01億元。趙德磬《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中認為1895—1937的近40年間,中國現代工業經歷了二次發展浪潮,其中1928—1937年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第三次浪潮,1936年工業發展達到近代時期的高峰,該年現代工業資本比1920年增長兩倍。1936年現代工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23.69%,比1920年提高12.91個百分點,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1.35%,比1920年提高6.32個百分點。且在幾個重要行業里,機械化程度有較大提高。1936年,在棉紡、棉制、煤、鐵礦、鐵五大部門中,機械生產所占比重分別為39%、83%、84.7%、87.0%、82.7%。1936年的農業總產值比1935年增長了5.9%,1936年的工業品總產值比1935年增長11.1%,1936年對外貿易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貿易順差,1937年達到1935年的兩倍左右,貿易赤字迅速縮小;1936年除少數省份受災減產外,全國農業空前豐收(到1936年,耕地面積增加到14.2億畝,比1887年增加25.8%;農業生產在1936年達到歷史最好水平。
在30年代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與經濟危機下,國家不僅在經濟上打下了現代化的基礎;在對外關系領域,也取得重大收獲。經過外交斡旋與斗爭,抗戰前收回了部分外國在華特權。抗戰時期重工業建設初見成效,不平等條約的相繼廢除改變了清末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的半殖民地狀態,大后方地區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后方工業發展排除了外國勢力的干預,是中國現代工業產生以來首次實現工業獨立,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色彩在淡化。但是國民黨政府頑固的反共、剿共政策和連年發動的對紅色根據地的圍剿,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階級的對立,耗費了好不容易積累的經濟發展成果,遲滯和阻斷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使得30年代成為一個機遇和問題共存的年代。
鄉村問題與國民政府的應對措施: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與農民狀況,關系到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關系到國家政權的穩定與社會的穩定。近代以來,西學東漸與西方現代性的挑戰,中國走上“被動現代化”之路,導致了近代中國現代化與鄉村經濟的嚴重錯位。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發展造就了東南沿海城市的發展與繁榮,但整個鄉村被遺忘和遺棄。這種對鄉村控制的遺棄與犧牲為后來的中國社會帶來重大而難以逆轉的問題,造成鄉村社會的失控與無序化。由于社會轉型,連年戰亂人禍,自然災害等影響,農村經濟出現了極度的衰落,鄉村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的破壞,出現了嚴峻的“農民問題”。
“20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的全面危機,成為推動政府和社會去尋求拯救‘危機’,改良和整合農村的內部動力”。20世紀初,西方合作經濟思潮涌入中國,農村形勢極度惡化使越來越多的人士認識到鄉村開展合作運動的必要性與迫切性。20年代初,孫中山、戴季陶、陳果夫等開始關注合作經濟問題。1924年孫中山刊發《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包含合作經濟思想。1928年政府延續了這一施政綱領,把合作制度看作改良社會生產,解決民生問題,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方式。
從1928年—1945年,政府將鄉村合作運動作為一項基本政策,納入整個國家行政計劃中。創辦農民銀行以解決鄉村金融短缺及高利貸問題;設立中央合作人才訓練所(1935年)培訓合作人才;通過信貸合作機構或農業信貸署(1937年成立)向農民提供信貸或發展農業經濟,制定眾多農業經濟發展項目并開始實施,包括開發荒地、植樹造林、興修水利、保持水土、控制蟲害、改良種子、改進工具和牲畜品種,引進美國式大型農場。但鄉村合作運動由于信貸資金發放不足,未能與鄉村實情結合,政府建設資金嚴重不足等諸因素并未取得明顯功效,但政府改造與建設鄉村的努力與實踐確有其實際意義。“合作本質上是一個文化問題,中國缺乏接受西歐式合作經濟制度的社會制度,文化與經濟等背景因素,由此決定了靠國家行政力強制進行的制度變遷,只能是一種缺乏下層機構有效參與的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這也是合作經濟組織在中國陷入發展困境的根本性原因”。農業發展嚴重滯后制約著中國整個現代化的進程,1931—1936年,中國農業年增長率為1.5%(除去東北),而現代工業增長率為6.7%,農業增長率嚴重偏低。
將30年代命名為革命的時代,是對這個時代命名的簡化。革命是3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部分,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這一時期國家對經濟發展的規劃與實施卻也取得了相當的實績。30年代鄉村經濟衰敗與階級矛盾的劇烈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中國現代化發展之路上付出的慘重代價。
三
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社會滋生復雜的社會現象,不同政治立場及審美立場的知識分子對此進行思考,文學成為直接或間接闡釋現實社會與文明的方式。30年代城市經濟興起,農村經濟衰退,城市文明以一種異質于傳統的文明形式出現,兩種經濟背后則是兩種不同意旨的文化沖突——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左翼關注社會急劇變化中底層社會生活惡化的現象,以消除階級壓迫為政治理想,通過革命與文學的雙重實踐介入政治;右翼知識分子以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為目標,試圖以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強化國家意識形態,以民族意識整合不同資源,為政府主導的現代經濟制度建設提供意識形態支持;京派知識分子關注與現代性伴生的城市文明負面現象,試圖以傳統人文精神再造民族性格;而都市文化中新生的一代知識分子則積極擁抱這新的風景,構成立足于上海以描寫都市風景與都市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海派文學。左翼與右翼文學以意識形態闡發為目的,京派強調文學的非功利性、文學的審美獨立性,海派則在現代主義美學與都市消費文學間取得平衡。
“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小說形式與嚴格意義上的經濟結構、與市場生產和交換結構,具有最及時、最直接的聯系”。任何文學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超越現實生活。穆卡洛夫斯基指出:“在文學和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觀察其內在的藝術形式,以及作為結構的發展過程,而且要觀察此結構與其他現象,尤其是與心理性或社會性的現象之間的關系。”因此對文學現象的考察必須與社會政治經濟等密切結合,才能對文學形式與外在社會因素之間互動的狀況給予客觀的闡釋。“文學事實與文學作用之間的關系,關于過去事件的限定性的一般概念,對藝術,對歷史都是適用的。寫下的東西就是限定的”。我們必須回到特定歷史時代的語境,才能給出時代語境“限定”的文學解釋。
左翼文學:
1931年11月左翼作家執行委員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確立了題材范圍:反帝反軍閥地主資本家的題材、蘇維埃運動、土地革命、紅軍及工農群眾英勇斗爭的題材、白色軍隊“剿共”大屠殺題材、農村經濟衰敗、勞資矛盾地主剝削等階級壓迫題材;聲明“將那些‘身邊瑣事’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式的‘革命的興奮和幻滅’,‘戀愛和革命的沖突’之類等等定別的觀念的虛偽的題材拋去”。決議為30年代左翼文學確立了主題、題材、人物、形式等諸要素的寫作規范。茅盾1932年12月完成的《子夜》是左翼文學的奠基之作,其宏大的結構、社會分析的視角,為左翼文學寫作提供了范式。作品建構了左翼的題材、人物、主題。就題材而言,其反殖民、反封建、社會政治批判、城市文明批判等內容皆經過左翼主題的過濾。茅盾以無產階級理論為預設,緊扣吳蓀甫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命運,揭示30年代民族資本家的歷史性遭遇及中國的社會性質。其主題由于左翼政治立場遮蔽和誤釋了許多現代性問題:吳蓀甫振興民族工業夢想的失敗,既有策略失誤(倚重公債投機的冒險行為),也有世界經濟危機導致民族工業受損的影響,更與趙伯韜斗法的失敗,應是公債市場正常的經濟行為;而從鄉村農民到工廠工人,甚至地主、小工廠主、大資本家均遭遇的經濟衰退等寫實描寫顯然與預設的階級斗爭主題構成矛盾,意識形態并不能完全解釋客觀現實。左翼階級立場反現代的政治實踐性與現代性問題構成了矛盾,《子夜》依然有著許多溢出意識形態的寫實性細節描寫。
30年代左翼文學主要由農村題材和城市題材構成。農村題材以豐收成災與階級壓迫為主,城市題材以勞資矛盾的斗爭性題材為主。主題上,兩種題材都以揭示階級壓迫與階級斗爭為核心。敘事邏輯大致是同一種模式:悲慘生活境遇的工農,在革命思想的啟發下,階級意識覺醒。茅盾的“農村三部曲”以豐收成災題材揭示鄉村階級矛盾,奠定了左翼鄉村寫作模式,葉紫的《豐收》,丁玲的《水》、《田家沖》,葉紫《山村一夜》等,皆屬同類作品。
對于這一時期農村經濟的衰退,英國學者萊特《中國與1930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Chinaandthe1930sWorldDepression)一文,認同費孝通考察后得出的農村經濟衰退并非地主對農民壓迫的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世界市場的中國擴展與鄉村經濟的封閉性無法對抗造成的。氣候、地租等其他因素都是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之一,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是首要因素。因此左翼作品的階級壓迫不能完全解釋鄉村經濟衰頹問題,政治意識形態簡化和遮蔽了現代性進程中的鄉村問題。
左翼城市題材是經過左翼政治過濾的題材,城市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其革命性,城市空間與人物行動都經過政治篩選賦予革命意義。上海不是海派筆下的現代性城市空間,而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空間。兩個空間截然不同:《子夜》對城市景觀進行了左翼定性,夜總會、跑馬場等現代城市景觀是罪惡的淵藪;左翼筆下革命的空間恰是現代城市景觀背后的角落:亭子間、工廠、車間、貧民窟等。左翼文學中的都市上海,是典型的階級斗爭敘述,如丁玲的《法網》、夏衍的《包身工》等。
這些作品中,資本主義制度是上海罪惡之源,階級性是人物的主要身份特征,城市底層人物的悲慘境遇起因于經濟壓迫,其本質是政治壓迫,故階級反抗具備了合理性。以《法網》為例,丁玲試圖說明工人顧美泉與于阿小之間的仇恨與兩個家庭的災難非個體性,而是階級性。根本上導致顧美泉失業的原因,并非于阿小借顧美泉請假擠兌對方,而是勞資對立的階級矛盾。左翼文學城市題材將勞資矛盾上升至階級壓迫,階級性定位構成左翼城市文學的合法性特征,甚至階級斗爭被賦予國家革命的政治意義。
京派文學:
京派文學將關注視角投向鄉村,立足于文明視角書寫鄉村文明與鄉村生活。沈從文與師陀可以說是30年代頗具盛名的京派小說家,他們構成了鄉村書寫的兩種方式。沈從文筆下體現優美自然與和諧人性的鄉村社會成為承載作家人文理想的載體;師陀則書寫著鄉村的衰敗、傳統倫理的崩潰,表達對逝去文明的無限感傷。京派以超越思考關注現實背后的文明問題,沈從文以鄉村想象建構的文學湘西試圖改造日益功利化、欲望化的現代都市問題,并將之上升到建構民族性格的高度——以湘西人性重塑民族性格。《邊城》成為這種思考的集中表達。他的小說及散文集《湘行散記》在表現主題上有著高度的集中性,是其文學觀念與文明觀念的載體。沈從文自覺追求文學的獨立審美性,避免文學的商業化與政治化。他說:“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志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做志士,對于文學唯知在它的產生,與產生技術,以及產生以后對它在社會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實分量同價值,不許它把價錢開得太大,也就是不許人家對它希望太大”。表明他堅持文學審美獨立性立場。師陀小說關注鄉村固有文明(風俗)、人情倫理及鄉村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文明結構的衰頹,從審美視角表現作者對傳統文明變遷的復雜情感。
京派對鄉村問題的關注非社會政治層面,其文明視角具有超越的審美意味。京派文學題材除鄉村題材之外,還有城市題材。城市題材以諷刺性為主要表現方式,對城市文明弊病的諷刺(金錢至上的城市人生存邏輯,放縱及墮落的欲望人性),構成了京派鄉村書寫的對照,京派對城市現代化伴生的欲望人性保持著深刻的反省,試圖以傳統倫理救治現代文明之弊。比起小說在文體形式上與社會深層結構問題聯系的密切性,京派的美文更趨向自我性情的書寫,審美的獨立性色彩更為突出。小品文方面,周作人20年代的美文余緒綿延,林語堂頗具個人風格的幽默小品文,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何其芳的《畫夢錄》、郁達夫的《達夫游記》等均是書寫作者個人性情的純粹美文,均是這一時期頗負盛名的作品。而近于京派注重文學人性與文化意蘊的劇作家曹禺,更是30年代話劇的頂峰。
海派文學:
30年代的上海,已經成為世界第五大都市。作為現代都市的上海,消費與文化生活深受西方影響,造就了一批生活歐化的文人,成為30年代海派產生的生活基礎。深受西方現代主義美學影響,加之上海的都市消費性,造就了海派審美與商業的特殊組合。
現代派、新感覺派作家在作品中著力于表現新奇的都市感覺,捕捉都市印象,表達現代都市人的情緒心理。海派文學成就表現在:描摹都市景觀,展示五色雜陳的都市人的生活,揭示現代都市男女新型的兩性關系,書寫現代都市人的價值取向,揭示現代人孤獨寂寞的心理及精神狀態。海派為新文學提供了新的表現空間:現代都市的新奇景觀進入文學表現領域,如跑馬場、賽狗場、夜總會、電影院、大街等,均是伴生現代都市的地理景觀。穆時英《街景》中的城市景觀描寫:去野宴的跑車、街上骯臟的乞丐、經過月臺的火車、時裝店的人群等。更有都市的活動場景,如《上海的狐步舞》動靜結合的城市景觀:貼著廣告的電車,夜總會門前的黃包車,紅綠交通燈,街上涌動的人潮,街上的各色人等(女秘書,冒充貴婦的模特,追逐時髦的姑娘);甚至人物活動都是景觀:深夜林肯路的槍殺事件,工人勞動的慘烈場景,華東飯店有錢人的享樂場景,街邊陰暗角落里拉客的下等妓女;海派也將筆觸伸向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與情感:《上海的狐步舞》描寫錯綜復雜的家庭關系,資本家年輕妻子與繼子的亂倫關系。劉吶鷗小說集《都市風景線》熱衷于書寫男女兩性間的情感——擺脫傳統束縛、放縱情欲的兩性關系。穆時英《被作為消遣品的男子》中男子不再是男權威嚴的象征,卻成為都市摩登女郎的情感消遣品。《夜總會的五個人》書寫現代都市人的孤獨與寂寞。現代化造就的都市文明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使傳統倫理喪失了在現代都市的控制權,現代化及其文化一方面釋放被傳統壓抑的人性,動搖著傳統倫理秩序的根基,另一方面也將現代人推向了精神的虛空。
施蟄存則超越了都市書寫,他關注鄉村經濟現代變遷中的農民命運,關注失去傳統宗族基礎的現代都市人的精神世界,書寫現代性中國社會(鄉村與都市)日常生活的變遷。《扇》、《上元燈》作為傳統文明的象征,所代表的生活及情感方式成為都市人心靈的慰藉。施蟄存著力挖掘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浸染于傳統思維的中國人在城市文明沖擊下的心理應激,關注傳統鄉村經濟在現代性沖擊下的劇烈變化及農民遭遇:《街景》中農民上海夢破碎,來自鄉村卻再也無法回到鄉村。《汽車路》中具有現代文明象征的汽車路在農民關林眼中,成為剝奪他活路的惡魔。關林屢次破壞汽車路的行為成為傳統鄉村經濟與現代化發展之間尖銳矛盾的隱喻,極為真切、客觀地揭示了中國鄉村與現代化進程之間的嚴重問題。《獵虎記》則是對30年代衰敗、混亂的鄉村問題的反思。海派風格奇幻怪誕,但多數海派作家偏重形式,重新奇而未能深入社會生活與人物命運則成為主要缺失。
右翼文學:
30年代具有右翼傾向的文學團體及其創辦的文藝刊物,主要圍繞“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展開,包括上海以前鋒社為中心的文藝運動,南京以中國文藝社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以及杭州以初陽社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
圍繞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建立的文藝社團雖然由國民黨黨員創辦,但成員構成、文學刊物及文學作品卻并非只有黨派性質,其構成復雜多元。前鋒社骨干成員雖有官方身份,如范爭波(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上海警備司令部偵緝處處長),朱應鵬(《申報》資深編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會委員),但有不少人是沒有官方背景的,如傅延長(同濟大學教授),以及葉秋原、陳穆如、陳抱一、李金發等文藝界人士;最活躍的是一群尚在大學讀書或剛出校門富有理想、思想激進的文學青年,如受前鋒社影響的草野社成員。草野社創辦《草野周刊》,鼓動青年為民族而戰的民族意識,頗受青年學生歡迎。南京的中國文藝社的《文藝月刊》、杭州的《黃鐘》均如此,弱化黨派色彩,吸引文藝界名人參與,創作構成復雜多元。
在文學創作上,民族主義文藝以“民族主義意識”為主題;在作品中,通過人物強烈的生命意識,為民族而戰的政治意識傳達民族主義意識。《前鋒月刊》中的文學作品常通過人物強烈的生命意識和意志力表現民族主義意識。李贊華的《變動》與《飄搖》將筆觸伸向動蕩的鄉村社會,描寫因生存所迫鋌而走險的農民命運,對鄉村衰敗、社會動蕩、倫理崩潰等鄉村問題的書寫極有見地;拋開其意識形態暗示的角度,在描寫上有京派的氣息,與京派、海派等類似主題構成互文情境。
小說比較突出的還有黃震遐的《黃人之血》和《隴海線上》,以強化人物生命意識傳達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30年代文壇絕非各派壁壘森嚴,頻繁文藝論爭之外,呈現出各派相互交流與互動的良性狀態。各派雜志之間的寬容尺度,均表明30年代文學發展的多元與繁榮狀態。海派《現代》發表過魯迅具有鮮明意識形態性的紀念左聯五烈士《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右翼《文藝月刊》撰稿作家有新月派沈從文、梁實秋、陳夢家、方瑋德,有巴金、卞之琳、戴望舒、施蟄存等自由作家,還有左翼作家何家槐、聶紺弩、魯彥等。左翼《北斗》發表過京派凌叔華、林徽因、沈從文的作品,及海派戴望舒的詩歌作品。
30年代文學的多元狀態是文學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追求的不同所致:社會現代性以功利性為文學訴求的目的,審美現代性則超越現實功利;從流派而言,左翼因政治影響而產生文學影響,京派因文學審美而確立根基,海派因都市寫作切近現代都市實際;三者各有勢力所及,右翼民族主義影響相對偏弱。從文學總體成就而言,30年代文壇上頗具盛名的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曹禺、林語堂,各派作者各領風騷;曹禺的《日出》、師陀的《谷》以及何其芳的《畫夢錄》獲得1937年《大公報》文藝獎金則表明批評界依舊以文學的審美探索作為衡量文學價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