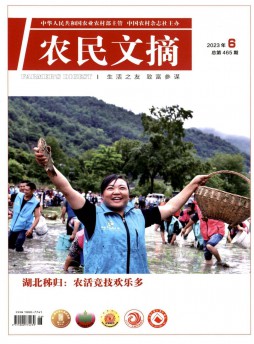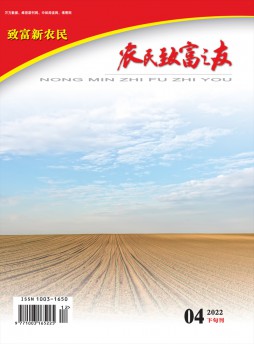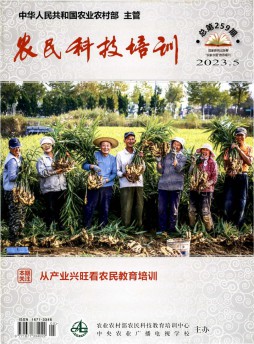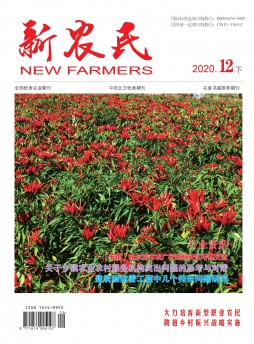農(nóng)民形象主體人格創(chuàng)建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農(nóng)民形象主體人格創(chuàng)建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論文關(guān)鍵詞:《皇天后土》農(nóng)民主體人格
論文摘要:周同賓的鄉(xiāng)土散文多取材于農(nóng)村生活,其系列紀(jì)實(shí)散文《皇天后土》建構(gòu)了時(shí)代浪潮沖擊下的農(nóng)民的主體人格。《皇天后土》中的農(nóng)民主體人格可粗略地分為三類:保守型人格、開(kāi)放型人格和中間型人格。作家對(duì)不同類型主體人格的描繪形象地勾勒出當(dāng)代農(nóng)民鮮明的個(gè)性特征,再現(xiàn)農(nóng)村生活的豐富多彩和當(dāng)代農(nóng)民的奮斗、希望、挫折、困惑以及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農(nóng)民獨(dú)特的人格魅力。
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無(wú)數(shù)作家都對(duì)農(nóng)民的生存狀況、主體人格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關(guān)注。從80年代開(kāi)始,作家們更是一反以前對(duì)農(nóng)民群體一味贊美的做法,冷峻地剖析當(dāng)代農(nóng)民的主體人格。“一個(gè)只對(duì)農(nóng)民階級(jí)哀其不幸,怒其不爭(zhēng),一味美化的時(shí)代過(guò)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定與否定的結(jié)合。”[1](頁(yè)11)
作為首屆魯迅獎(jiǎng)獲獎(jiǎng)作品,周同賓的《皇天后土》在向讀者展現(xiàn)農(nóng)民多彩的生活內(nèi)容、豐富的人生畫(huà)面,為大地母親塑像的同時(shí),也為當(dāng)代農(nóng)民畫(huà)像,建構(gòu)并審視當(dāng)代農(nóng)民的主體人格。
每個(gè)人的行為、心理都有一些特征,這些特征的總和就是主體人格。主體人格的發(fā)展具有穩(wěn)定性,也具有可塑性,它隨著顯示環(huán)境的多變性和多樣性而或多或少地發(fā)生變化。“人格是在遺傳、環(huán)境、成熟、學(xué)習(xí)許多因素影響下形成和發(fā)展起來(lái)的。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對(duì)不同人的影響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這是造成人格差異的原因。”[2](頁(yè)3)“如果我們要對(duì)真實(shí)的自我、人自身或說(shuō)真正的人的最深、最真、最本質(zhì)的各基本方面下定義的話,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我們不僅需要囊括他的各種能力、生理上的特質(zhì)以及他基本的內(nèi)在固有的需要,而且還得囊括存在價(jià)值,這也是他自身的存在價(jià)值。”[3](頁(yè)39)就《皇天后土》中農(nóng)民形象主體人格的建構(gòu)而言,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其分為三類:保守型人格、開(kāi)放型人格和中間型人格。
一、保守型人格
在現(xiàn)代文明這個(gè)大語(yǔ)境中,周同賓以現(xiàn)代文明為背景,把握時(shí)代變遷,觀照鄉(xiāng)土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文明中的滯后性,以知識(shí)分子應(yīng)有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去審視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文明,建構(gòu)出當(dāng)代農(nóng)民的保守型人格,并在《皇天后土》中對(duì)此種主體人格進(jìn)行了鮮明的刻畫(huà)與表現(xiàn)。保守型人格最本質(zhì)的特征表現(xiàn)為:時(shí)代雖然前進(jìn)了,但他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卻沒(méi)有跟上時(shí)代的步伐,依然恪守舊時(shí)代的觀念,而且不能正視現(xiàn)實(shí),自私狹隘、墨守成規(guī)、不思進(jìn)取。這些因素,使得他們不是以積極的態(tài)度應(yīng)對(duì)現(xiàn)實(shí),相反,他們恐懼現(xiàn)實(shí)中的新生事物,所以體現(xiàn)出極端守舊意識(shí)。“悠悠歲月”之《世道》中的耿世臣,懷念當(dāng)年做貧農(nóng)、斗惡霸、當(dāng)干部的情景,慨嘆現(xiàn)在世風(fēng)不正,人心不古。覺(jué)得自己兒子下臺(tái),爆發(fā)戶耿四寶倒風(fēng)光起來(lái),太沒(méi)有天理了。耿四寶在自家門(mén)前演場(chǎng)電影也被他看成是“夸富哩,耍能哩,收買人心哩”。其實(shí)耿世臣的想法一部分是對(duì)過(guò)去光輝歲月的懷念,一部分也是對(duì)社會(huì)發(fā)展,現(xiàn)實(shí)狀況的恐懼。“一般而言,這種恐懼是自衛(wèi)性的。是為了保護(hù)自尊,為了保護(hù)對(duì)自己的愛(ài)和對(duì)自己的尊重。對(duì)于任何足以導(dǎo)使我們輕視自己,或是我們自感卑下、軟弱、不值得、邪惡、可恥等的一切認(rèn)識(shí),我們自然會(huì)感到恐懼。我們借著壓抑和類似的自衛(wèi)方式來(lái)保護(hù)自我、保護(hù)自我理想的影像。”[3](頁(yè)94)《瘋九》里的秦捍東,“毛選”、紅寶書(shū)至今倒背如流,與耿世臣一樣,接受不了任何先進(jìn)事物,讓人直慨嘆他的“迂”!對(duì)適應(yīng)新時(shí)代農(nóng)村發(fā)展的聯(lián)產(chǎn)責(zé)任制,他看不到它的先進(jìn)性、時(shí)代性本質(zhì),反而認(rèn)為:“聯(lián)產(chǎn)責(zé)任制,就是包產(chǎn)到戶嘛。舊社會(huì)就是一家一戶種莊稼,誰(shuí)種誰(shuí)吃,也是聯(lián)產(chǎn)責(zé)任制?這能是新政策?這是閨女穿她奶奶的鞋———老樣!”
保守型人格除卻表現(xiàn)為極端守舊思想的主體人格特征外,還體現(xiàn)出宿命論的人格特點(diǎn)。對(duì)于社會(huì)和時(shí)代的轉(zhuǎn)變,他們不是積極地挑戰(zhàn)自我,把握機(jī)遇,而是寄希望于虛無(wú)的鬼神和所謂的“命運(yùn)”。“行動(dòng)的抑制和責(zé)任的喪失,必定導(dǎo)致宿命論,亦即,‘會(huì)來(lái)的一定會(huì)來(lái),世界本來(lái)就是如此。早就注定了,我實(shí)在無(wú)能為力’。因此喪失了意愿,喪失了自由意志,成為一種最糟糕的宿命論,這當(dāng)然有害于任何人的成長(zhǎng)與自我實(shí)現(xiàn)。”[3](頁(yè)171)《黃蛇》中的閻四也一樣對(duì)這世道不滿:住在他前面的鄰居閻振海發(fā)財(cái)致富蓋起了高樓,自己卻仍住著“滿地雞屎豬糞”的“一方小院”,閻振海家的高樓給自己一家的生活帶來(lái)了種種不便,他到處找人但是最終也未能解決。于是無(wú)知的閻四竟用“善惡到頭終有報(bào)”這樣一種宿命論想法,或者說(shuō)類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來(lái)安慰自己,將心中的怨憤寄希望于鬼神的報(bào)應(yīng),希望鬼神顯靈,以此報(bào)復(fù)閻振海對(duì)自己的鄙視。他不只是憎恨,甚至上升到詛咒對(duì)方的程度了,堅(jiān)信閻振海現(xiàn)在欺負(fù)自己,將來(lái)一定會(huì)遭報(bào)應(yīng):“有初一就有十五。常在橋上過(guò),總會(huì)掉下河。黃衣大仙能饒了他?說(shuō)不定啥時(shí)候拉他娃去償命。”他察覺(jué)不到自己窮、受人鄙視就是因?yàn)楹⒆佣?每年都被罰款,家里缺少經(jīng)濟(jì)來(lái)源。對(duì)此,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恪守著越窮越光榮的“貧民”思想,而不是振作起來(lái)尋找致富門(mén)路,在致富路上與閻振海一比高下。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皇天后土》中的保守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國(guó)民劣根性的主體人格特征,然而應(yīng)該指出的是,保守型人格并不都是具有國(guó)民劣根性的主體,也有不失人性的堅(jiān)韌和農(nóng)民善良、淳樸、敦厚本色的主體人格。他們講述“活著”的艱辛、生活的苦楚,用整個(gè)人生盼望著苦盡甘來(lái)的那一天。《苦菜》中熬寡四十年的無(wú)怨無(wú)悔的屈巧兒:“命苦啊。就像那苦苦菜,從根兒到梢,都苦。”他五歲便沒(méi)有了親娘,后媽狠心歹毒,好不容易出嫁了,生活有盼頭了,十九歲便又守了寡。她吃遍了千般苦,受遍了萬(wàn)般罪,“潑上命掙工分”,將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自己無(wú)怨無(wú)悔地付出,只愿孩子能夠出人頭地,表現(xiàn)出了人性的堅(jiān)韌、頑強(qiáng)。《皇天后土》開(kāi)篇就呈給世人一道《苦菜》讓人慢慢品味,細(xì)細(xì)咀嚼,悠悠回味,理解人生的“苦中作樂(lè)”,生活原本就是苦辣酸甜攪在一起,不同的主體看到的“苦”的意義是不同的。
在《皇天后土》中還有一部分農(nóng)民,一輩子靠天吃飯,靠土地養(yǎng)家,靠牲畜耕田、勞作,對(duì)土地、牲畜、農(nóng)具有著滿腔的熱戀與感激。《牛事》中的李來(lái)成,“一個(gè)憨厚的莊稼人”,“憨厚”突出了其最主要的人格特征。他愛(ài)牛如狂,恨不得“下輩子托生成牛”,“莊稼人,不能沒(méi)有牛,莊稼人更不能對(duì)不起牛。咱那莊稼地,牛犁過(guò)幾千幾萬(wàn)遍,祖宗八代沒(méi)餓死,不都是牛的功?看見(jiàn)牛,我心里美,吃飯香,睡覺(jué)也甜”。《土命》中把土地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傳統(tǒng)農(nóng)民趙得富;《黑土》中的邵金聚,不向往城市的燈紅酒綠,偏偏鐘情于這黑土地,“咱就是這窮命,一輩子離不開(kāi)土……土里生,土里長(zhǎng),土里刨食,死了還睡到土里化到土里”。這應(yīng)該是唱給摯愛(ài)土地的一曲生命的戀歌。
作者清醒地意識(shí)到社會(huì)在發(fā)展、在變革,千百年靠畜力勞作的歷史一去不復(fù)返。但是老輩的農(nóng)民割舍不下這份情,在他們心里,自己和那些出過(guò)力、立過(guò)功的“老功臣”一樣,他們愛(ài)惜那些“老功臣”,其實(shí)也是對(duì)自己一生功績(jī)的肯定與系念,還有一分不舍與不忍。這正是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各種復(fù)雜因素綜合作用在農(nóng)民主體人格方面既矛盾又統(tǒng)一的集中體現(xiàn)。“比較而言,農(nóng)村比城市更貧窮、更落后,農(nóng)村人比城市人更苦、更累、更少文化而多愚昧;農(nóng)民的苦、甜、酸、辣,農(nóng)民的喜、怒、哀、樂(lè),便更有歷史的沉重感。正由于歷史的原因,農(nóng)民的命運(yùn)便總有一種濃濃的悲劇色彩。雖然他們往往想不到這點(diǎn)。世事滄桑,新舊代謝。新事物出現(xiàn),舊事物消失,這無(wú)疑是進(jìn)步。但是,失去的有的該失去,有的不該失去。不該失去的,竟失去了,難再回復(fù);該失去的卻依然存在,且還要往下發(fā)展。這是無(wú)可奈何的,總使人感慨不已。”[4](頁(yè)270)農(nóng)民的主體人格“既有那么好的前途,又有那么多的羈絆,既有那么美的憧憬,又有那么多的遺憾……實(shí)在是一個(gè)一言難盡的話題”[4](頁(yè)271)。作者之所以建構(gòu)這種保守型主體人格,大概也是基于此吧。
二、開(kāi)放型人格
較之保守型人格,開(kāi)放型人格則具有更多的自主意識(shí)和進(jìn)取精神,能順應(yīng)時(shí)代的發(fā)展,體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歷史主動(dòng)性。他們是當(dāng)代新型的農(nóng)民主體,“追索著時(shí)代的主潮,回蕩著生活的基調(diào),承載著認(rèn)識(shí)的價(jià)值,高揚(yáng)著社會(huì)主義的思想光耀和進(jìn)取精神”[3](頁(yè)63)。
《皇天后土》中開(kāi)放型的主體人格是作者熱情贊揚(yáng)的,也是寄托著作者殷殷期望的主體人格類型。他們有著不同的愛(ài)情觀、人生觀、價(jià)值觀。不管是《入贅》的白玉棟、做《木匠》的姜長(zhǎng)水;還是從事著受人鄙視的低賤職業(yè),仍努力追求自我價(jià)值的《閹豬》的葉貴,《駒場(chǎng)》的單福祥;抑或是《烘爐》中那心胸寬廣,“多大的鐵疙瘩都能化成水兒”,有情有義的大男人姚中義,還有帶領(lǐng)全家人科學(xué)致富、《治家》有方的徐興順,都是《皇天后土》中能夠把握自我命運(yùn)的主體。“開(kāi)放型人格拋棄過(guò)去與未來(lái),不使自己遠(yuǎn)離當(dāng)下的情景……完全著眼于當(dāng)下,有足夠的勇氣與自信,當(dāng)新問(wèn)題來(lái)臨時(shí)亦能平靜地面對(duì),相信自己有能力應(yīng)付。這就是健康的自尊與自信,免于不安與恐懼的情緒。換句話說(shuō),他們對(duì)世界、現(xiàn)實(shí)或環(huán)境的評(píng)價(jià),使他們信任這世界,不認(rèn)為它是危險(xiǎn)而強(qiáng)勢(shì)的。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應(yīng)付,他并不會(huì)感到害怕。它看起來(lái)一點(diǎn)也不恐怖。擁有自尊代表個(gè)人視自己為初始的行動(dòng)者,對(duì)自己的命運(yùn)負(fù)有責(zé)任,是自我命運(yùn)的決定者。”[5](頁(yè)373)
《入贅》里為求真愛(ài)而甘愿入贅到妻子家賣豆腐的白玉棟,“想結(jié)婚,就得‘倒插門(mén)兒’……為小改嘛,也就是為愛(ài)情嘛”。白玉棟在愛(ài)情的態(tài)度和行為上都體現(xiàn)出鮮明的自主意識(shí),把握自己的幸福,決定自己的命運(yùn)。《改嫁》里的丁小艾失去丈夫后,開(kāi)明的婆婆不想耽誤兒媳的幸福,毅然摒棄了千百年來(lái)在世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留根”的傳統(tǒng)觀念,主動(dòng)勸兒媳改嫁,并親自出面為她挑選人家。于是丁小艾帶著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一起改嫁,到了李成栓家。李成栓也完全接納了他們,絲毫不介意自己娶的是個(gè)寡婦,撫養(yǎng)的是別人的孩子,他很寵愛(ài)孩子,就像對(duì)待自己親生的孩子一樣:“見(jiàn)到人家吃魚(yú),(孩子)也想吃,想得直哭。成栓說(shuō):‘娃,別哭,我去給你逮魚(yú)。’就掂個(gè)小桶去了。”另外他也很尊重孩子的生父,清明節(jié)帶孩子去給生父上墳,“燒了紙,他給墳添土,添多大”。他們的幸福完全是自己把握和爭(zhēng)取來(lái)的,因?yàn)樗麄兏矣谔魬?zhàn)世俗的傳統(tǒng)觀念,追求自我幸福;還有不顧世俗禮教的約束為仙逝的老母親辦喜喪的快活三,他對(duì)鼓手們說(shuō):“我媽是喜喪死后要升天,成仙哩。吹那哭哭啼啼的調(diào)調(diào)兒,啥意思!”他一說(shuō),就都吹喜調(diào)了。一下子喪事變成了喜事,“鬧成鍋滾一樣,都像瘋了”。《圓魚(yú)》里靠養(yǎng)殖元魚(yú)發(fā)家致富的吳柱子,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干出了點(diǎn)成績(jī),一場(chǎng)大雨讓他的事業(yè)化為烏有,但他不氣餒,“有人就有東西,有人就有錢(qián)……全當(dāng)十萬(wàn)元買個(gè)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重打鑼,另開(kāi)張,又干……”
在這里,我們看到這些主體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是沉著冷靜的堅(jiān)定與正直,因?yàn)樗麄兪执_知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并能專心一意全力以赴,毫無(wú)懷疑、猶豫、三心二意或退卻。因此能夠朝目標(biāo)全力以擊,而不是隨意瀏覽、不痛不癢地輕飄而過(guò)。周同賓說(shuō):“我對(duì)農(nóng)村,對(duì)農(nóng)民,便有一種復(fù)雜的情愫,既愛(ài)又憂,既喜又悲。執(zhí)筆為文,便一邊眷戀,一邊嘆惋;眷戀和嘆惋里尚有真切的希望。我的散文,便是唱給農(nóng)村生活的一曲綿綿的歌,也唱情歌,也唱挽歌;不論唱得好壞,自信歌里尚有一顆真心。”[4](頁(yè)271)這種開(kāi)放型的主體人格便是作者“真切的希望”、“自信歌里……一顆真心”。在社會(huì)進(jìn)一步發(fā)展,思想日漸開(kāi)放的今天,他們“主宰自己的內(nèi)在本性,掌握自己的潛在力、自己的才干與才能,操控自己創(chuàng)造的沖動(dòng)。他認(rèn)識(shí)自己的需求,日益變得更為整合、更具統(tǒng)一性;他日益覺(jué)察到自己的本來(lái)面貌,覺(jué)察到自己真正的所需,并覺(jué)察到自己的召叫、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命運(yùn)”[3](頁(yè)67)。
三、中間型人格
在周同賓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理想人格的創(chuàng)造與建構(gòu)是始終處于某種矛盾與沖突的困擾之中的。這種矛盾與沖突,主要體現(xiàn)在社會(huì)對(duì)創(chuàng)作主體的制約與創(chuàng)作主體對(duì)理想生活的渴求與探尋的不協(xié)調(diào)方面,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延續(xù)。這種矛盾沖突在《皇天后土》中也有所體現(xiàn):即作品中所呈現(xiàn)出的一種中間型人格,這是介于保守型人格和開(kāi)放型人格之間的一種交叉型人格。其性格有多個(gè)側(cè)面,每一個(gè)側(cè)面反映其主體人格的某一特點(diǎn):有時(shí)他們自私,有時(shí)也開(kāi)明;有時(shí)膽小懦弱,有時(shí)也堅(jiān)強(qiáng)勇敢;有時(shí)開(kāi)放,有時(shí)也保守;但他們有自己的追求、目標(biāo)、理想。
最典型的是《留根》中的毛栓,政府號(hào)召發(fā)家致富,聰明的他辦起了養(yǎng)雞廠,很快便成了養(yǎng)雞專業(yè)戶,體現(xiàn)出開(kāi)放型人格勇于開(kāi)拓創(chuàng)新的一面。但傳統(tǒng)的子嗣觀念卻時(shí)刻困擾著他,因?yàn)樗麤](méi)有生育能力,但又一心想為自己留個(gè)根:“只要有了娃,留條根,也算沒(méi)白活一場(chǎng)。”為了達(dá)到“留根”的目的,他甚至放棄了作為男人的尊嚴(yán)和作為丈夫的底線,竟讓妻子和自己的“光屁股”好友私通,妻子懷孕并生下一個(gè)兒子,他便把這個(gè)孩子算做是自己的兒子。但是他心知肚明:“我的娃,明明不是我的娃,是野種。這個(gè)根,不是我的根。把他養(yǎng)大,還是野種。”所以雖然圓了“留根”夢(mèng)卻又時(shí)時(shí)為此感到臉慚,即使事業(yè)有成也絲毫不能彌補(bǔ)內(nèi)心的挫敗感:“我是專業(yè)戶咧,有錢(qián)咧。我窩囊。我不算個(gè)男人。錢(qián)算啥?錢(qián)能給你笑?錢(qián)能給你睡?錢(qián)能給你生個(gè)親生兒子?”事業(yè)上他吃苦耐勞、精明能干,順應(yīng)社會(huì)發(fā)展,積極接受新事物并不斷開(kāi)拓進(jìn)取,但是思想上卻有保守型人格愚昧守舊的一面,固守封建傳統(tǒng)的子嗣觀念,為達(dá)目的,甚至棄社會(huì)綱常倫理于不顧。新舊思想在他身上合而為一:既聯(lián)合又不停地斗爭(zhēng),這正是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農(nóng)民身上新舊思想雜糅的典型表現(xiàn)。
《時(shí)運(yùn)》中的主人公靳春陽(yáng),熱愛(ài)文學(xué),曾模仿《少年維特之煩惱》寫(xiě)了一本散文詩(shī),還“整天鉆屋里寫(xiě)詩(shī),寫(xiě)小說(shuō),寫(xiě)了就往外寄,最高寄到《人民日?qǐng)?bào)》”,畢業(yè)后迫于生計(jì)停止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高中畢業(yè)的他很迷信,特別信“命運(yùn)”,認(rèn)為“命是不可以改變的,人一出生就定了;運(yùn)是可以改變的,或者說(shuō),是可以利用的。命是一生的,運(yùn)是一時(shí)的。這就是時(shí)運(yùn),一時(shí)一時(shí)不同”。用作者的話說(shuō),他是一個(gè)“睿智”的青年,曾瘋狂地追求著自己的文學(xué)夢(mèng),但他迷信地認(rèn)為一個(gè)人如果“時(shí)運(yùn)不好,就是有危機(jī)……甚至還會(huì)把命送掉”。就連哪天出門(mén)也要算算是否吉利。他搞文學(xué)創(chuàng)作,到了“沒(méi)稿紙了,也買不起郵票”的地步,他沒(méi)錢(qián)、沒(méi)房子,也沒(méi)人給他介紹對(duì)象,他相信這是自己的命運(yùn),于是狠狠心,開(kāi)始跑生意。他做買賣,也投機(jī)取巧,將石子塞進(jìn)所賣雞、鴨、鵝的嘴里以增加其重量。怎樣評(píng)價(jià)他?好人?壞人?僅僅那么簡(jiǎn)單嗎?新舊思想在他身上也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沖突:他身上有著保守型人格迷信落后的一面,那些關(guān)于“時(shí)運(yùn)”的看法也有一些宿命論的味道,但他又是受過(guò)先進(jìn)思想教育的新時(shí)代青年,有著自己的夢(mèng)想與追求,因此不能用一個(gè)干巴巴的詞來(lái)定義他的人格特征,更何況他還沒(méi)有放棄他的追求呢:“我還想搞創(chuàng)作——我看報(bào)上、雜志上登的那些東西,我也能寫(xiě)出來(lái)。到時(shí)候你給我引薦。我真愛(ài)文學(xué)。不知道是誰(shuí)說(shuō)的,文學(xué)像個(gè)浪女人,一旦被她纏住,會(huì)和她勾搭一輩子,一有空閑,就和她偷情。”
中間型人格主體,每個(gè)人身上都有兩股拉力,這兩股拉力始終相互作用,可以說(shuō)是個(gè)人心理的一種內(nèi)戰(zhàn),是個(gè)人在某一部分與另一部分彼此之間的對(duì)立。這是社會(huì)和時(shí)展所產(chǎn)生的新觀念與傳統(tǒng)農(nóng)民的舊思想激烈斗爭(zhēng)的結(jié)果和表現(xiàn)。正如作者所說(shuō):“新的與舊的,傳統(tǒng)的與現(xiàn)代的,在他們身上既矛盾又統(tǒng)一,他們是這個(gè)時(shí)期的標(biāo)本和證明”。[4](頁(yè)67)總的來(lái)說(shuō),周同賓的《皇天后土》通過(guò)構(gòu)建當(dāng)代農(nóng)民主體的保守型人格、開(kāi)放型人格和中間型人格全方位、大容量描寫(xiě)一個(gè)地域的農(nóng)民,并以獨(dú)特的視角來(lái)審視農(nóng)民、喚醒農(nóng)民,表現(xiàn)他們的愛(ài)與恨,展現(xiàn)他們真實(shí)的生活。讓農(nóng)民自己走上前臺(tái),去宣講他們的追求與渴望。周同賓的愿望是:“把形形色色的農(nóng)民一個(gè)個(gè)寫(xiě)下來(lái),為當(dāng)代做個(gè)記錄,為后世留下檔案。”[4](頁(yè)268)
參考文獻(xiàn):
[1]曹文軒.中國(guó)八十年代文學(xué)現(xiàn)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8.
[2]高玉祥.健全人格及其塑造[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
[3][美]馬斯洛.馬斯洛成功人格學(xué)[M].長(zhǎng)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04.
[4]周同賓.周同賓散文(四)文心春秋[M].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
[5]艾斐.時(shí)代精神與文學(xué)的價(jià)值導(dǎo)向[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