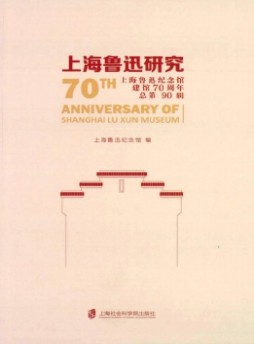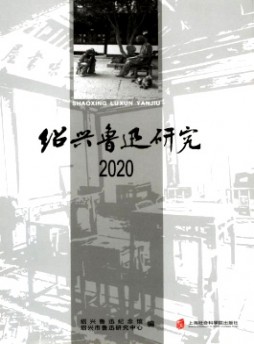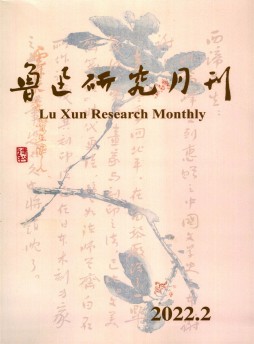魯迅作品和合學思想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魯迅作品和合學思想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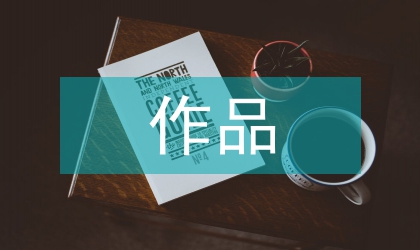
和合學是張立文先生1988年提出的一種哲學和文化理論。所謂和合的“和”是和諧、和平、祥和,“合”是結合、融合、合作。和合是指自然、社會、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沖突、融合,與在沖突、融合的動態過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為新結構、新生命、新事物的總和[1]。張立文在《和合哲學論》中提到困擾社會持續發展的五大沖突和五大危機:人與自然的價值沖突及其生態危機;人與社會的價值沖突及其人文危機;人與人的價值沖突及其道德危機;人與心靈的價值沖突及其信仰危機;人與文明的價值沖突及其智能危機[2]43-44。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在魯迅看來,只有引進外國文化,才能拯救民族危亡,因此魯迅的翻譯動機、譯本選擇無不滲透著“啟國救民”這一“和合學”思想。
一、魯迅文學翻譯作品化解人文危機
摩爾根指出:人類發展的“每一階段都包括一種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3]”。魯迅經歷了清末和民國時期,正是中國社會激烈動蕩和變革時期,魯迅作為時代先進的知識分子,思想自然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發展。許壽裳曾說過,“正惟其愛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觀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癥結也越加詳盡,毫不留情。魯迅的舍棄醫學,改習文藝,不做成一位診治肉體諸病的醫師,卻做成了一位針砭民族性的國手[4]”。“國名性”問題一直是魯迅思想中一個揮之不去的命題,并對其所處時代的“國名性”有所覺悟。魯迅曾提到,“廚川白村所狙擊的要害,我覺得往往也就是中國的病痛的要害,這是我們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5]。“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6]。而和合的追求是和合自己敞開自己,迫使自己置身于對和合的懷疑狀態之中2[61]。魯迅認為,“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6]47。”并且他認為中國的“國名性”是劣質帶有貶義色彩的,并在其文中提到,“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于我們有用……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于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7]242。”“無論什么時候,總是生活在自己的種族所有的傳統的范疇里。于是他們也就毫不進步了。……現在的支那的衰運,也就是中華民國的自負心的結果呵[8]369。”因此,中國應該改造和提升自身的“國名性”,可是,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6]349,魯迅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人只能靠自身的力量去爭取新的社會,當前的社會不可能也不會為國人出謀劃策,當時政府也曾派遣許多文人志士去國外學習西方的先進的技術與知識,但是政府所做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當時新的形式、新的環境、新的學問刺激和吸引著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去探究西方新知。當時中國社會急劇變革,加上西方也希望憑借炮艦的神威對中國進行文化的滲透,各種思想、文化激烈地碰撞,于是一場富國強民的“洋務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不過想利用他(小說)的力量,來改良社會[7]525”。魯迅期望當時的政府能改良政治體制。在這個過渡的時代,并不僅僅是單純的符號之爭與史實之爭,它從一開始就超越了紀年的范疇,演變成政治體制和文化觀念的爭執。不同的紀年方式隱含著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在其背后,則是不同的政治訴求[9]。其反映了中國近代化的內在要求,即中國走向世界的內在要求。自16世紀以來的中西歷史紀年的“中西文化沖撞”也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碰撞和融合后歸于“和合”。魯迅認為,我們應該抱了謙虛淵淡的心,將世界的文化毫無顧慮地攝取。從這里面,才能生出新的東西來[8]373。魯迅于1903年初剪掉了象征滿族統治的辮子,并拍了一張“斷發照”送予同鄉好友許壽裳,并在相片后面題了一首詩,其中著名的一句為“我以我血薦軒轅”,反映了他這種迫切希望改良國家的決心。出于政治的功用,魯迅翻譯了大量的國外文學作品到中國,如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記中提到,“我譯這書,……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們的參考或服用,也如金雞納霜既能醫日本人的瘧疾,即也能醫治中國人的一般[8]285”。同樣在《文藝政策》的后記中,魯迅提到,“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較不枉費了身軀……然而,我也愿意于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10]”。和合精神家園可賦予人人安身立命之所……和合精神家園可為人提供一種和諧、友愛、平等、互助、自由的溫馨家園。這個家園……更主要的是人的靈魂的溫馨的家[11]4。腐朽沒落的政府讓當時的知識分子深刻地感受到“無國”的危機,迫切地想尋找一種新的國家認同。魯迅關注人的思想覺醒和社會、民族的解放,大膽實踐和推動中國文學的意義和文體形式的變革,并有選擇地吸取了世界先進的文化,反思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惰性,并積極扶植文藝戰線的革命新生力量,看到問題,就剖析給國民看,號召國民去抗爭;看到希望,就鼓勵國民去戰斗,希望借此能營造一個美好的家園。通過譯介國外的文學作品,魯迅希望能呼喚中華民族趕快從這種愚昧的狀態中走出來,走出象牙塔,正視社會現象,尋找自己的創造性和救國救民的良策,擺脫舊文化和舊社會的束縛,早日實現社會的改造,真正地融入這個世界。
二、魯迅文學翻譯作品化解道德危機
《說文解字》把“和合”釋為兩義:一曰“相應也”,即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諧一致;二曰“調也”,即多種不同的事物、成分、因素,按照一定的規則與關系和諧地組合在一起,有著和諧、和順、諧和、調和、和睦、中和等多種相異又相同的涵義[12]。當時中國人民正處于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中國人如果要成為獨立的人或要重新當人,就要奮起抗爭。而當時在愚民政策的熏陶下,忍讓和謙慎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何啟蒙勞苦大眾和開發民智也是魯迅一生所最為關注的一大問題。他說,“因為中國的工農,被壓榨到死尚且不暇,怎能談到教育;……不過人的向著光明,是沒有兩樣的,無祖國的文學也并無彼此之分,我們當然可以先來借看一些輸入的先進的范本。……從此脫出文人的書齋,開始與大眾相見,此后所啟發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讀者,它將要生出不同的結果來[13]。”在魯迅的翻譯專論中,并沒有詳盡地闡釋這些寶貴的思想和觀點,但他的只字片言卻體現了魯迅希望通過譯介國外的文藝作品和文學作品來改變人們的精神,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14]439。”中國舊社會充滿了血腥的欺騙和剝削,不可能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美。通過與西方科學文化的對比參照,魯迅對舊中國的封建教育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反對舊社會對人性的壓迫和壓榨,希望國人能通過對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的吸收來改變其思想,能實現國人思想的健全與解放。和合生存世界的和合,就是人對人所生存的對象世界的思考的自我觀念、自我創造的活動。2[63]同時,和合生生道體是創造性的人文化成,其邏輯前提是人的自我覺醒、主體的精神獨立和人道的差分運行……人類才有了和合生生的可能性、迫切性、主體性和創造性[11]2。”于是獨立的人是一個國家進行改革,步入繁榮昌盛的前提。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寫道,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14]58。但中國長期的文化專制制度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愚昧了大眾,于是人的個性缺失,如果要把人從無所不在的等級制度、家族制度的框架中拯救出來,從一代代沉淀而成的歷史負擔之中解救出來,就只有靠引入新的思想和文化。于是,魯迅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到中國。作為譯者,在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時,應“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占有”之后必須要“挑選”,然后再決定“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15]40-41”。如果不這樣,“人不能成為新人[15]41。”這種人就是自己能當家做主,不再是皇帝或者別人的奴隸,是真正的人道主義所關懷的“人”,只有這種真正意義上的人才能創造出和諧美好的社會。魯迅對傳統文化作出了大膽的批判,勇敢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挑戰,并用大量的譯文來證明其方向。通過翻譯,借助外國的文藝和文學來救治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毒瘤,開闊國人的眼界,化解了人的道德危機,最終能夠對中國的思想界有所影響。
三、魯迅文學翻譯作品化解精神危機
在當時內外交困時期,深受國學熏陶的文人志士們,身處中西學之間,對譯介西學其實矛盾重重。其一,“西學”、“新學”逐漸取代了“夷船”、“夷炮”等話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深入人心,甲午戰爭后,日本作為戰勝國令中國有識之士刮目相看。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提倡借鑒日本的經驗,向西方學習強國之術的呼聲越演越烈。其二,這些文人志士們又無法放棄中國數千年來的圣典禮法,常常又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復古的傾向。于是這兩種思想在這些人心中不斷地沖突、升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作為人類精神兩大部類,……科學滿足了我們的理智,人文滿足了我們的情感。只有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視野交叉在一起,我們才能看到一個“合情合理”的世界[16]74-75。在魯迅最初的翻譯生涯里,他曾提到“因為向學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17]”。魯迅是“五四”之前中國最早介紹科學小說到中國的譯者之一。在日本留學期間(1903-1909年),他從日語轉譯了幾部科學小說,有把法國儒勒•凡爾納當作美國培倫著的《月界旅行》,有把凡爾納當作英國威男寫的《地底旅行》,還有美國作家路易斯•托倫的《造人術》、《北極探險記》、《世界史》、《物理新詮》等。魯迅前幾部譯作中有明顯的改譯和編譯等多種譯法的跡象,如魯迅自己所說“凡二十八章,例若雜記。今截長補短,得十四回[18]4”,明顯是受當時譯界風氣的影響。但魯迅翻譯科學小說自有他的用意,如在《月界旅行辯言》提到,是為了讓讀者“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故荀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18]4”,他是要把以西方新的小說形式表達出來的科學精神引進國內。進入近代以來,我國的愛國進步人士對舊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新舊文化的交替之爭讓許多人迷茫、困惑。在《隱憂篇》、《大哀篇》中,魯迅在《仿惶》中都真切地流露過這種情感:一方面傳統倫理秩序已經失范,另一方面又尚未形成新的人際關系和道德規范;一方面老權威已喪失了信仰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找不到足以替代的新的信仰權威[16]232。毫無疑問,當時的他們也與不少的新青年都曾陷入虛無、幻滅的認同喪失的痛苦之中。但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們能在這種迷茫失落中,尋找自己的新的信仰。魯迅的翻譯具有強烈的時代性,主要是為了填補當時中國落后的科學和語言文化空缺,滿足中國讀者真實地了解外國科學和語言文化的需求,體現了他借鑒外國文法來改造中國文法的精神,帶有明顯的政治索求和語言文化改良目標[19]。由于國民大革命的失敗和社會主義思潮在世界及中國的流行,魯迅在他人生的最后階段,蘇聯吸引了他的目光,并將他引向了馬克思主義。魯迅選擇作品時,注重作品是否對讀者有益,對社會有用。其譯介作品關注文學與革命的關系。這些作品的翻譯與魯迅對于中國革命和革命文學的思考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也促進了魯迅對于中國的革命與文學的思考,使之在中國革命與革命文學運動中做出清醒地選擇,魯迅對于托洛茨基的關注是這一階段中明顯的特點。參見魯迅翻譯板塊圖[20]:從上圖可得知,俄蘇文學和文藝理論的翻譯在魯迅文學譯作中占很大的比重,大約有140萬字以上,他在促進俄蘇文學及其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開拓作用。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提到,那時候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然而從文學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里,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斗,建設的辛苦和成功[7]473-475。
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了》中提到,我所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7]525。魯迅翻譯了《毀滅》等大量前蘇聯革命文藝作品,旨在介紹“鐵的人物和血的戰斗”給國人,希望通過介紹安德列夫的小說來讓國人們看清自己內心的痛苦和壓抑,能勇敢地站起來與現實社會抗爭,還有譯介了安特萊夫的《謾》、《默》和迦爾洵的《四日》、阿爾志跋妥夫的《幸福》、《醫生》等作品來提升和超越人的精神。還譯介了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希望能把國外的文學理論和作品真實地展現在國人面前,以此鼓勵中國人民投身于革命斗爭,并為中國革命作家提供文學創作的新材料和新契機。魯迅積極為中國讀者提供了有用之識,滿足了讀者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渴求,提高了國人的文學素質與思想覺悟,并為國人的思想指明了方向。魯迅的文學翻譯作品將人們的精神從長期的愚昧狀態和腐朽的道德枷鎖中解放了出來,化解了人們的精神危機。
四、魯迅文學翻譯作品化解價值危機
“和實生物、和生萬物”則認為多種因素和要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動造就了世界事物,如果事物要生存下去,或者新的事物要產生,就需要有“和合”。近世的“中西之爭”,實質上是東亞農排生存方式與西歐工商生存方式、儒教倫理道德傳統與新教倫理道德傳統在中國疆域里的短兵相接……向歐美學習工業技術和商務管理,去西洋請教民主理念和科學精神,已成為新文化運動以來華語世界無可奈何的共識[11]3。國內先進的學者們認為,只有通過翻譯,新的思潮才能被引入中國,才能拓寬國人的視野。但是翻譯不是一味地迎合讀者的口味。不同文化的交流就會產生碰撞,碰撞之后就會有靈感。—切藝術、哲學作品及其精神世界,都是借助符號手段與感性質料虛擬出來的……虛擬的東西具有相對穩定的邏輯結構,能在文化、哲學舞臺上賦義呈現,充實成為文化、哲學存有[2]9-10。他國的文學作品其表達方式、思維方式等異于中國,于是就需要把這種靠語言文字虛擬的世界介紹到國內。勒費弗爾曾提到,文學翻譯對一國的文學進化起著舉足輕重的推進作用[21]。具有憂患意識的魯迅提到,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達到表達自己想要說的意思[7]527。魯迅在1903年開始他的翻譯生涯,后來受翻譯的啟發創作了許多傳世之作,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費在這艱苦的翻譯工作之上,尤其是他生命的晚期。魯迅翻譯的文學種類有多種,有科學小說,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戲劇,童話故事,雜文,詩歌,文藝理論等,如下圖[22]:“五四”時代啟蒙者的真正的深刻性就在于他們以極大的勇氣強忍著文化沖突的悲劇性,大膽地追求現代文明價值,而不惜付出舊文明失落的代價[16]253。當然,魯迅也曾迷茫過,在《域外小說集》的序言中說,“半年過去了……計第一冊賣出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沒有人買了……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18]582”,但他們偉大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譯本卻在國內受到了冷遇,“這事使我到現在,還感到一種空虛的苦痛[18]583。”而且在序中還提到文化之間的差異,“……所描寫的事物,在中國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爾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幾于極無,所以更不容易理會。同是人類,本來決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時代國土習慣成見,都能夠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鏡一般明,照見別人的心了[18]583。”但是,這并不能挫敗魯迅,反而為魯迅文學翻譯提供了新的契機和視角,他認識到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匯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行著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語言的斗爭,那對于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7]380-381。為了豐富國人的表達方式和創建新的中國文化體系,在魯迅的直譯文本中,可生動形象地看到一些引進的創新詞匯和詞組,如“超人”與“末人”,心跳如“一只籠子里的鵪鶉”,“魚膏”“發沸”“用了撒野的速率在往前跑”“一生就像是一個大謊在那里逛蕩著”“出色的馬匹”“透空鑄鐵的大門”等等。魯迅說,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并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23]。他還提到,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語言。……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余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7]380”。魯迅翻譯文學作品,是想通過虛擬的語言文學化解國人的價值危機。五四時期,有志之士包括魯迅大量閱讀和翻譯了外國的文學著作。同時在鴉片戰爭之后,西方也同樣非常重視和吸收東方文化的和諧觀念及各種人文理念。無疑這種有效的結合能讓我們身心受益,使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更加全面和透徹。正是以中西文化碰撞為基礎,以先覺者們的“個性覺醒”為突破口,魯迅試圖喚醒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和個人意識,揚棄其自身的缺點,大膽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魄,促使傳統的中國人蛻變成現代的中國人,再由單個中國人的轉變從而達到新中國的崛起。
五、結語
“和合”自身內有之意義包含著沖突與融合,這是一對相對應的因素。魯迅和合文學思想是在新文學運動時期中與西、古與今文學思想強烈沖突的基礎上得出的。在20世紀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在面對中國前所未有的危機之時,魯迅,這位盜火者以文學為途徑,將國外的文學作品引入中國文化這口染缸,把自己反思的結晶傳達給國人,以啟悟人們為改造自身和本民族的精神,化解了當時困惑年輕一代的人與社會的價值沖突,人與人的價值沖突,人與心靈的價值沖突及不同文明的價值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