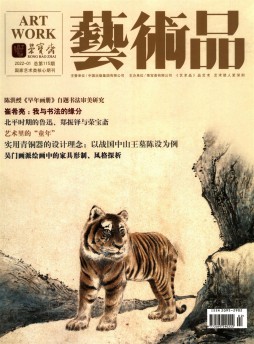藝術品保護論文:民間藝術品的法律保護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藝術品保護論文:民間藝術品的法律保護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九瑪草
一、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涵義
學界認為,民間文學藝術包括民間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創作以及傳統工藝三個主要分類,這個概念可以擴展到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中體現生產生活審美情趣且具有極高藝術和商業價值的作品,例如民間傳說、民歌、民間舞蹈、戲劇等通過各種不同的表達形式來展現其藝術魅力的作品,在我國的著作權法中應當給予應有的版權保護。
以上規定雖然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概念作出了有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它們都對其特征有著相同的認識,即民族性、區域性、延續性,因此,筆者認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可以被認為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創作出來的世代相傳的表現其審美觀念和意識情趣的作品,如我國的民間傳說《阿凡提的故事》、歌曲《在那遙遠的地方》,又比如吉卜賽人的舞蹈等。
二、關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的問題
(一)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的確定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應當如何進行界定?發生在2002年底的“《烏蘇里船歌》案”曾引起了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廣泛探討。2002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以赫哲族人民名義對訴郭頌、中央電視臺及南寧市人民政府提起訴訟,告其侵犯赫哲族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益一案進行了一審判決。法院認為,《烏蘇里船歌》是郭頌等被告人在赫哲族民歌《想情郎》的曲調之上經過改編而成的,郭頌等人的行為僅屬于再創作,作品《烏蘇里船歌》的著作權應當屬于赫哲族人民,因此法院在經審理之后,作出以下判決:(1)郭頌和中央電視臺在以任何形式使用《烏蘇里船歌》時,應當注明“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的字樣;(2)判決郭頌和中央電視臺在判決生效二十日內于《法制日報》上發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系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而成”的聲明;(3)駁回原告的其他賠償請求。被告郭頌及中央電視臺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這起案件中,原告赫哲族鄉人民政府是否有權代表赫哲族人民提起對赫哲族民間藝術作品的保護訴訟,成為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從法院的判決結果來看,法院對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的思考不再拘泥于過去的說法,開創了法院承認鄉政府作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權利主體地位的先河,對于類似案件中涉及權利主體的判定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的意義。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版權原則上應當屬于創作它的群體,而人民政府則有權以該區域民族群體的名義提起訴訟、主張權利。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不同于一般的文學創作,它的創作是一個集創作、傳播、提高于一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很多的人或民間組織都為之付出了勞動和努力,因此,其權利主體應是一個多層次的問題,不同層次的人在作品中所分享的利益也有所不同,除非主體無法層次化,則此時應被看做是抽象的主體,可以委托或委派相關代表來行使權利。
(二)權利主體層次化的問題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其最初有可能是一個或者幾個人創作的,但是隨著時間和歷史的推移,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被越來越多的人或組織予以不斷地再加工和完善,從而凝聚了更多人的智慧結晶,這時的作品已不再是某一個人的創作了,而是逐漸成為了這一地區的某個民族的群體作品,具備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區特點,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藏族地區廣為流傳的《格薩爾王傳》,就目前的搜集和整理情況來看,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一部史詩,共有120多部,100多萬詩行,2000多萬字,在此之前,人們認為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是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格薩爾王傳》這一偉大的英雄史詩僅僅依靠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它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結晶,其內容極其豐富多彩,是主要以民間說唱的形式來歌頌英雄的詩歌。這部史詩大約產生于公元三世紀至公元六世紀之間;在公元十一世紀左右隨著藏傳佛教的在藏區的復興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這期間主要是藏族寧瑪派僧侶在藏族古代詩歌、諺語以及神話傳說的基礎上進行豐富和完善,形成基本框架,并編纂成了最初的手抄版本。在此之后主要是通過傳唱的形式,由無數的吟游歌手世代承襲著有關它的吟唱和表演,歷經了藏族人民一代代的口述流傳,在不斷地演進和完善中,成為藏民族歷史文化最高成就的象征,在藏民族的文化遺產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其所有權和著作權應該屬于這些群體而不是某一個人。
當然,在這一群體中,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層次,不同層次的人在作品中能分享到的利益也會有所不同。首先是真正的作者,這一群體在作品中除了享有著作權法規定的權利之外,還要考慮到作品的特殊性,除署名、發表等基本人身權之外,還應當包括:一是保真權,即保持作品的真實性和原生面貌,如作品出處和創作群體,禁止歪曲、篡改、貶低、褻瀆作品;二是繼承與再創作權,這一權利的規定是考慮到了作品的特殊性,因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很可能被群體中的任何成員創新;三是回歸權,即有關群體對于歷史上流落于群體之外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享有將其追回的權利,以上三項精神權利僅僅是學界中一些觀點,而財產權則包括了很多,基本沒有什么改變。
其次是傳承人,在集體享有版權的前提下,傳承人也應當享有部分版權,主要是側重于財產權,在人身權方面,應該適當地享有署名權。
第三類是記錄人和收集人,這類群體在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的勞動屬于客觀、真實地記錄原貌,不再是創造性勞動,而是一般性勞動,所以不可能將這類群體置于“類似于作者”的地位,而是以適當的方式注明其為記錄人或收集人,此外,在作品的開發、利用中,如果獲得了一定的利益,則可以適當地支付報酬給記錄、收集人,即記錄人或收集人享有一定的獲酬權。
第四類是整理人,這類群體在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的勞動是加工、整理,使作品初步成型,其中也包括一些創造性勞動,因此這類群體也應當獲得相應的版權與財產權。
第五類是改編與創作人,這類群體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付出了創造性勞動,所以應對這些作品享有版權,在行駛著作權的時候不能脫離原作品的著作權,可視為演繹作品,這類作品的使用過程實行雙重許可、授權和雙重報酬,取得演藝人的版權地位,既要顧及作品的原始主體的地位,還需尊重原始主體的保真權。
第六類是傳播人,這類群體包括出版者、表演者、錄制者和廣播電視組織,在我國這類群體中還包括出版者。這一群體在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也要付出創造性勞動,可以按照“鄰接權人”的制度來設計其權利。
在具體的行使過程中,集體版權該如何行使呢?理論界普遍認為,可以委派代表人行使,這類人可以是有威望的人,也可以選代表,甚至吸納群體之外的人參與進來,組成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或者通過立法,來規定建立這些民間組織,從而行使權利,另外,當群體無法進行界定時,也可以由國家來作為版權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