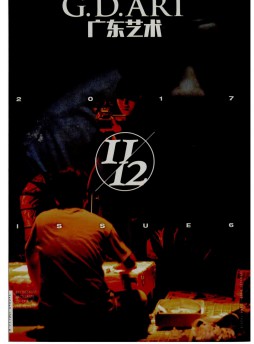藝術評論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藝術評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論文關鍵詞:莊子,劉辰翁,評點
劉辰翁(1231—1297),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曾大量評點過詩文,所著《南華真經點校》[①]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莊子散文評點,開后世《莊子》散文評點之先河。與林希逸“條分而縷析”的批評方法不同,劉辰翁的評點較為靈活,主要是以直觀感悟、隨手批點的方法,運用生動形象而富有個性化的語言,向讀者揭示出《莊子》散文的藝術魅力。他說:“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齊物論》)[②]其評點文字長短不齊,多則幾句,少則三言兩語,甚至一字,但語短情長,耐人尋味,很有啟發意義。正因為劉氏的評點表現為即興隨感式的,所以就顯得較為散亂,缺少系統性和理論性。再加上劉氏曾評點過大量詩文,又評點過小說《世說新語》文學藝術論文,因此其《莊子》評點受詩歌和小說評點的影響較大,在概念的使用上顯得豐富多彩,使人較難把握。如他在評點中常使用像“痛快”、“奇俊”、“灑脫”、“清麗”、“氣象”、“潔靜”等一類的詞,如果讀者缺乏一定的審美鑒賞經驗,就很難體會這些詞所蘊含的真正涵義。但劉氏畢竟長期涵容于評點鑒賞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趣味和審美標準,因此在評點《莊子》的過程中,這些特點又時時反映出來。仔細推敲其評點,可以發現劉氏主要抓住了《莊子》散文的以下幾個特點來進行鑒賞的。
第一,莊子善于描摹人物,敘述故事,體察物情,能畫出“不盡之意”。《莊子》一文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既有作者理想世界中的人物,也有現實中的人物;既有帝王將相,也有普通百姓;既有儒家圣人,也有江湖大盜;既有神人、美人,也有畸人、丑夫,各行各業、各種身份的人融匯在一起,儼然一幅形態各異的群生圖。他們各有性格,各有口氣,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充分展現了作者嫻熟的藝術技巧和表現能力。林希逸在《口義》中已注意到《莊子》散文這一特色,每一“畫筆”來稱之。劉辰翁繼承了林氏的說法,常以“畫意”來評論《莊子》。如《大宗師》篇謂駝背人子輿閑適得很,蹣跚地走到井邊照著自己的影子,他認為這“極是畫意”。《天運》篇謂“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他認為這是在“畫馀意”。但劉辰翁又在林氏基礎上作了較大的發揮,他每每抓住莊子人物形象中最傳神的東西,將人物的性格特點及精神面貌傳達給讀者,以達到“若點眼睛便活”(《齊物論》)的效果。如在評點《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時說:“語其游,語其神,亦猶儒者氣象,可以想見。”便抓住了神人“游”和“神”的特征,從而將“猶儒者氣象”的神人形象揭示了出來,讓讀者去領會、體悟。在評點《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幾而坐”一段時說:“三句畫子綦已盡,并與形骸之外者著之矣。”認為這幾句話不但將子綦的形象完整地勾畫了出來,更重要的是將他身體之外的東西也“畫”了出來。評點《養生主》“庖丁解牛”說:“寫得提刀四顧躊躇,亦覺此老神氣獨王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林希逸最早對其藝術特征進行闡述說“畫出一個宰牛底人”。而劉氏的評點,更將莊子筆下的“庖丁”形象活靈活現地還原給了讀者,讓人覺得此人就在面前,言行舉動神氣活現,可謂傳神寫照、畫龍點睛之筆。劉辰翁還發現莊子善于運用符合人物性格的語言、動作和心理活動等描寫來刻畫人物形象。如在評點《人間世》“顏回見仲尼請行”一段時說:“看他寫出回口中語,不過二三十字,別是諄至貌惻。”認為顏回雖然只說了幾句話,不過二三十字文學藝術論文,但其敦厚的性格、憂戚的神態和內心活動已顯現出來。評點《德充符》篇“申徒嘉與子產”一段對話時說:“其為子產語,雖等閑杜撰,亦古意雅甚。”認為子產的話雖杜撰出來,卻有其時代特點,并與其地位身份相符合。當子產被批評得“蹴然改容”時,他評點說:“筆下寫出子產惝怳自失之狀”,子產的神態、心理活動躍然紙上,讀之不覺使人失笑。可見,劉辰翁是以評點小說的手法來評點莊子的。因此他在評點過程中經常將《莊子》與小說聯系起來。他批評人們說“從淺至深,句句是道,今人作小說看了,喜其文而已。”(《山木》)其實,劉辰翁也未嘗不這么做。他在《馬蹄》篇就一會兒說:“起語突兀,本是小說家。”一會兒又說:“小說家時時有之。”在《徐無鬼》篇更直截了當地說:“雖小小說,亦必有情致。”劉氏以小說評點的方式來評析《莊子》,無疑能揭示出莊子散文的獨到之處。
劉辰翁進一步認為作文如同畫畫,只將畫面畫出還不行,還要留有馀地,留出想象的空間,讓人讀之有不盡之意。他認為莊子在敘述故事、體物狀情時,常常能畫出“不盡之意”。他在評點《山木》篇“莊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雀”一段時說:“作文如畫,畫者當留不盡之意,如執彈而留是也,此間妙意在捐彈而走。” 劉辰翁在這里指出,《山木》篇先寫“莊周”執彈而留守于栗樹之下,接著又寫他“捐彈而走”,終于沒有將彈發出,這正是《莊子》像畫家那樣“留不盡之意”。在評點《天地》篇“子貢南游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一段時說:“眼前事物,外意第雜,說亦不可及。抱甕之狀與橰之為物,曲折備具于其往復、俯仰、緩急,如忿然作色?Γ允巧猓諮醞狻!比銜鈾櫳吹惱庖還適攏嫦拭鰨次锎瘢宋鐠蜩蛉縞搖巴庖獾印保芏嗖瘓≈猓災痢八狄嗖豢杉啊薄S惺彼紙庵只安瘓≈狻背浦盎乓狻保紜短煸恕菲幸歡巍翱鬃蛹像跤鍶室濉保峁鬃穎煥像蹀陜浣萄盜艘歡伲崳燦小翱鬃蛹像豕椋詹惶浮繃驕浠拔難б帳趼畚模賴闥嫡饈恰盎乓狻保蛭蒜乓饣觶允刮惱賂右馕渡畛ぁS肓窒R菀謊乇鶼不丁鍍胛锫邸貳按罌猷嫫幣歡問榛獾奈淖鄭?
翏翏一語,便有描摸,其下不過山林二物,舉其概甚疏,雜以七八者字,而形與聲若不可勝數,妙在于喁一語,映帶前后皆活,重出愈奇,調調刁刁又畫中之遠景,形容之所不盡也。
很明顯,劉辰翁的欣賞視角與林希逸有所不同,林希逸認為此段文字是有聲詩,莊子居然能將“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畫得出來!而劉辰翁雖然也欣賞莊子“形與聲若不可勝數”的奇妙,但他卻以“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為更妙,認為此句語映帶前后,不僅使風之形象、情狀再度活靈活現地出現在人們面前,更重要的是帶出了后面“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一句,而此句是畫中的遠景,給人以朦朧縹緲之感,實是畫畫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這是用語言所無法表達的,所以“形容之所不盡”。劉辰翁抓住“畫不盡之意”這一點來分析此段,無疑更具有藝術魅力。
第二,莊子的散文極有“味”。劉辰翁是以藝術鑒賞家的眼光對《莊子》進行審美觀照的,因此在他看來莊子的散文極具詩情畫意,含蓄蘊藉、富有意味,故劉辰翁每以與“畫”緊密聯系的“味”這個傳統的詩歌審美范疇來評價《莊子》。梁劉勰早在《文心雕龍》中就已使用“味”、“馀味”、“滋味”等概念來進行文學批評了。如他在《隱秀》中說:“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深文隱蔚,馀味曲包。”在《聲律》篇中說:“聲畫妍蚩,寄在吟詠,滋味流于下句,風力窮于和韻。”在《體性》篇中說:“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鐘嶸在《詩品·序》中正式提出了“滋味”說:“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批評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強調詩歌要達到“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藝術效果。唐司空圖則在《詩品》中進一步提出了“味外之味”、“韻外之致”的審美理論。此后批評家每以“有味”、“無味”來品評詩歌,認為這是詩歌應達到的藝術境界。南宋以來,人們經常把詩歌中的一些批評概念引用到散文中,以此來豐富散文的鑒賞理論。林希逸開始使用“味”這個概念來品評《莊子》了。雖然用得不多,但很有啟發性。如他說:“筆勢如此起伏文學藝術論文,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認為從形式上說,莊子的文章技巧性很強,很有意味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此數句極有味”、“此語尤有味”又認為莊子的語言韻味無窮,很值得人們細細品味。“味”更是劉辰翁在評點詩文時一個很重要的審美范疇。他每以“味”來品評詩歌:“絕句難作,要一句一絕,短語長事,愈讀愈有味為正。”(《唐詩品匯·歷代敘錄》)他更在林希逸的基礎上大量使用“味”來評點《莊子》。如他在《逍遙游》“堯讓天下于許由”一段下評點說:“設客以見主人,語有味。”《人間世》孔子教訓葉公子高時有“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一段話,劉辰翁評點說:“此意人人曉得,只不似他能言,有許多馀味。”這里的“味”、“馀味”即語有不盡之意,也就是劉勰說的“馀味曲包”、鐘嶸說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意思。劉辰翁又以“味”來評價莊子的“譬喻”。在《口義》中林希逸每以“奇特”來贊賞莊子的譬喻,而劉辰翁更多的是品味莊子的譬喻,如《在宥》篇“云將東游過扶搖之枝”一段,他評點說:“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言物有不同而以類相感,人事皆若此,比為狐兔、松柏之喻,又有味。”認為以“狐兔、松柏”之類的比喻來說明治人的危害性,值得人深思,意味無窮。評點《外物》篇“胞有重閬”一段時說:“胞有重閬,直指空闕處也。室無虛則塞其竇矣。婦姑勃磎,狹路博則不得也。大山、大林見者畏其陰森,眩其廣莫,皆神者不勝耳。譬喻切近有味。”認為這些譬喻貼切自然而有意味。又在《則陽》篇“觸蠻之爭”的寓言后評點說:“以為實固無理,以為虛亦或可厭,最是以意實之,而其理確,然無不實。但見有味,愈廣而愈不厭也,讀者超然,愈有所醒。”認為此譬喻虛虛實實,很有味道,雖然作無限夸張,卻能使讀者超然醒悟。除了使用“味”、“馀味”外,劉辰翁還使用像“滋味”、“諷味”、“風味”之類的詞來評點《莊子》。如在《山木》篇“莊子行于山中”首段評點說:“極浮世薄惡之滋味。”在《徐無鬼》篇“吳王浮于江”一段說:“但譬已警,添董先生又高,未有無風味者。”這里“滋味”、“風味”是與“味”同一意義的審美范疇。在《田子方》“溫伯雪子適于齊”一段說:“規矩龍虎體狀得似,所謂嵬岸抑揚者,兩語深中人心,時時諷味不絕。得于人者,可以無怪,施于人者,可以戒之又戒也。”是說莊子刻畫得很具有諷味意味,能使人引以為戒。“諷味”一詞無疑很好地?得髁俗印柏獍迥鋇奶氐恪?
第三文學藝術論文,莊子散文又具有“奇”的藝術特征。林希逸在《口義》中曾多次以“奇”來評析《莊子》。劉辰翁繼承了林氏這一說法,也每以“奇”這個審美范疇來評點《莊子》。如《德充符》篇有語云:“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他評之曰:“語奇。”是贊其用語之奇。《駢拇》篇有語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他評之曰:“其所謂性,即所謂德也。其言扶疏,其字錯落重出,初非有意,亦非無謂者,故其所以為奇也。”是贊其用字之奇。《德充符》中有“王駘”一人,他評之曰:“‘王’字林作王天下之王固奇,只作王駘之王更奇。”是贊其起名之奇。評《列御寇》篇“鄭人緩也”一句曰:“個般起語,便是莊子撰得奇。”是贊其起語之奇。然而劉辰翁絕不認為莊文之“奇”僅限于這些細微的地方,他更認為《莊子》具有“意奇,文奇,事又奇”的多重審美特征。他在《齊物論》中評點“罔兩問景”的寓言故事時說:“影已無形之物,罔兩又非影之比也,寓又寓者也。意奇,文奇,事又奇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達生》篇有“祝宗人說彘”的寓言故事,是莊子讓祭祀官與豬對話,他評之曰:“玄冠說彘,皆奇事也。”在《大宗師》“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一段后又評曰:“兩‘藏’字已怪,又夜半又負走,何其奇也。”在劉辰翁看來,莊子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寓言故事,無不具有奇特的藝術魅力。而且他更以為像《齊物論》篇“莊周夢為胡蝶”、《徐無鬼》篇“郢人運斤成風”之類的寓言故事,更有出人意料的“奇又奇也”的美學特征。“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死,齊盡在是矣,奇又奇也。”(《齊物論》)莊周夢蝶的一個小故事,居然無所不“齊”,真可謂“奇又奇”。然而,劉辰翁又認為,莊文之“奇”并不只是單一意義上的“奇特”,它具有豐富的內容和因素,因此他又以“神奇”、“怪奇”、“奇俊”、“奇詭”等具體意義的審美范疇來評論《莊子》。如《德充符》篇有語云:“刖者之屨,無為愛之。……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他評之曰:“娶妻不使,本非以形不全,故經他變化,無不神奇。”意思是說娶妻者免除服役,與前文形不全沒有關系,但經他變化,前后意思聯系了起來,可謂“神奇”。《至樂》篇有語云:“支離叔與滑介叔觀于冥伯之丘,昆侖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文學藝術論文,其意蹶蹶然惡之。”他說此事實在可稱“怪奇”。《天運》篇有語云:“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他說這里所表述的意思,實可謂“參差奇詭而近于物情”。《馬蹄》篇末謂馬因受到人為的約束而學會了盜智,他就指出這番話真可謂“奇俊”。劉辰翁將“神”、“怪”、“詭”、“俊”等因素引入到“奇”中,大大豐富了莊文“奇特”的思想內涵,也使《莊子》散文“恢詭譎怪”的特征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另外,劉氏還認為,莊子在行文中能將平凡轉化為奇特,善于化“腐朽為神奇”。《徐無鬼》篇有“子綦有八子”的寓言故事,他評述說:“前所言,未奇也。雖鶉、牂語,亦未奇也。至盜刖之鬻之,則奇矣。”《徐無鬼》篇先謂子綦的兒子梱沒有任何功勞而有“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的征兆,這未足為奇;繼謂子綦父子“未嘗為牧而牂生于奧,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宎”,這也未足為奇;及謂使梱去燕國,途中為盜賊所擄獲,“刖而鬻之于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則奇矣。可見,莊文能從平淡無奇中轉出奇,劉氏的這一說法對于后人的文藝創作,無疑具有指導意義。
劉辰翁將詩論與小說理論的審美范疇引入了莊子散文評點,開啟了莊子文學研究的新紀元,對明清莊子散文評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今人重視。
[參考文獻]
[1]劉辰翁.南華真經校注.臺灣:嚴靈峰《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本.
第2篇
關鍵詞:生態女權主義;文學評論;《我的安東尼亞》
中圖分類號:i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11)02—0194—02中國
一、生態女權主義概述
生態女權主義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之中,20世紀90年代達到。生態女權主義首先出現于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發表于20世紀70年代的兩部作品:《女權主義或死亡》和《生態女權主義:革命或變化》。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號召女性發動一場生態革命來拯救地球,這種生態革命將使兩性之間以及人類與非人類的自然之間建立起新型的關系。
生態女權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西方文化中在貶低自然和貶低女性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關系”。生態女權主義者s.格里芬等人強調女性身體功能和自然接近,認為女性比男性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國學者伊內斯特拉·金把生態女權主義定義為一場女性認同運動,她聲稱:“我們為了忠于未來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這個地球而向父權挑戰。我們通過自己的性別特征和我們作為女性的經歷對此有著深刻和獨特的見解。”
生態女權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生態女權主義的首要內容是女性與自然的認同,是價值觀念與實踐活動緊密結合的社會運動。生態女權主義不僅涉及意識形態,也是一場為實現社會變革而興起的實踐活動,是女性為維護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區,反對由于父權社會、跨國公司和全球資本化主義而引起的惡性發展和環境惡化所進行的不懈斗爭,是理論與實踐的相互統一。第二,生態女權主義的重要論點還包括對西方現代科學的批判,多樣化和統一性,對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沉重代價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等。西方現代科學、生活多樣化、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等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均是在父權社會觀念主導下,人類社會為了滿足物質豐盈或者追求國際地位所做的掠奪自然、破壞生態平衡的活動,這種掠奪和破壞的意識同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第三,尋求建立聯系的原則是生態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生態女權主義尋求建立一個平等、和諧、友好共處的關系,這種關系涵蓋了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女權主義與文學評論
近年來,隨著生態問題研究的不斷推廣和深入,其思想已經深入歷史、政治、哲學、文化等各個領域,生態女權主義也隨之而起,生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以生態女權主義批評理論解讀含有生態和女性內涵的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新動向。
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原則”和“生態原則”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新標準,凡是體現了對整體、相互關系和穩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著關懷、同情和“慈育意識”的文學作品會受到極力頌揚,相反,彌散著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擴張、功利性的破壞性話語,則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包括以下內涵:(1)對文學文本中將女性作自然或者將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態寫作的理論概括,及其與男性自然寫作的比較;(3)女性文學作家在其文學作品或者文藝理論中表露的自然觀的整理與歸納,批判男性偏頗的自然觀;(4)結合相關時代背景,分析解讀文學文本中生態女權主義的回歸與叛離,由此文學經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闡釋并賦以意義和價值。
有不少評論者運用生態女權主義的視角和方法,對文學作品進行解讀,如有研究者對威拉·凱瑟的小說《啊,拓荒者!》進行了生態女權主義解讀,并認為“生態女權主義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和諧社會……女性、自然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系不再是貶低性的概念時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還有不少學位論文也以生態女權主義為研究視角,對相關文學作品進行分析解讀。這些從生態女權主義解讀文學作品涌現出的優秀評論文章從不同的側面分析了生態女權主義在刻畫女性的文學作品中體現的女性與生態之間深刻的淵源,使女性主義與生態整體有了共識——構建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融洽共處的和諧畫面。
三、從生態女權主義角度解讀《我的安東尼亞》
生態女權主義著眼于未來社會的建設,旨在建立一種人類與自然和睦共處、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態女權主義者呼吁建立一種不是基于統治原則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則的生態道德倫理觀,因此也賦予了文學評論新的視角和研究價值。
美國現代女作家威拉·凱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紀美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東尼亞》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現“拓荒時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純樸,藝術風格舒暢清雅。該作品以美國西部大草原為背景,講述了一位波希米亞姑娘安東尼亞在困境中的成長歷程,塑造了這位女拓荒者的生動形象,體現了美國早期開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為尋求自我建構和實踐身份認同而不屈不撓地抗爭,為超越自身情感實現自我價值而苦苦掙扎,為擺脫性別所帶來的不公正命運而不懈努力。
轉貼于中國
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解讀威拉·凱瑟的作品《我的安東尼亞》,可以使我們跳出常規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男性中心論,探索自然與女性之間密切的精神內涵,看到世界的真諦和價值在于人類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與友愛相處,從而加深對文本的核心內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對草原的認同,對土地的依戀,和自然環境的結合,與父權制主導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這種差異,生態女權主義者認為,“如果人類決心變革他們的性別關系,摧毀父權制,就能隨之改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種觀點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間存在著某種質的關聯,她們都是父權制思想主導下受壓迫和被征服的對象,只有意識到這種關聯,意識到父權制在整個統治體制中的獨霸地位,才能將愛惜自然與珍愛女性聯系起來,也就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人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中國
《我的安東尼亞》這部作品體現了生態女權主義的觀點,因為作品給我們展示出了內布拉斯加這片土地上繁衍的萬物都相得益彰:安東尼亞通過自己的成長和經歷贏得了“一種無法用世俗的價值觀來測度,無法用財富、名譽或者肉體上的吸引力之類的標準來衡量的成功”。這部小說在人與自然和諧融洽的氣氛中結束,達到了自然界萬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東尼亞》中的人物描寫蘊含了生態女權主義觀點。在吉姆看來,安東尼亞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親,“只要是女人可以成為的身份均可”,可見他們的關系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男女關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義的蹤跡,而是男性與女性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構成人類社會的兩大重要群體。安東尼亞等草原上長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幫工,雇主,特別是女主人,欣賞她們干活的本領,將她們也當做是家庭中的成員,這里也看不到傳統意義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贊揚人作為個體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國本地居民,而安東尼亞·雪摩爾達家卻是從波希米亞遷至美國,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懸殊,但是伯登家卻沒有因為這些懸殊而鄙視或者欺詐雪摩爾達家,相反他們互相幫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現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和諧相處的優美畫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對人類(特別的婦女)與動物的描寫——動物和人類同樣具有生存權是生態女權主義的另一重要觀點。吉姆的奶奶,這個常年在農田忙碌的婦女,總有各種小動物如土撥鼠、獾和菜花蛇等與她為伴,“我喜歡那些土撥鼠跳出洞來看活”,這使她不覺得孤單和疲倦。安東尼亞將受傷了的小昆蟲放進自己的頭發里——“為它搭了一個溫暖安全的窩”,即便是吉姆想幫她把昆蟲放進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從我當上了母親,我就不再殺任何動物了”,中年的安東尼亞更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般愛護著動物。在這部作品中,動物不僅與人類同樣具有靈性,并且關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更體現了生態女權主義者對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望。有學者認為,并非有描寫景物的作品就是對自然的關愛,若是描寫大自然是為了服務人類的感情表達,那便不是生態意義上的寫作。而若是設身處地地將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與人類同樣具有喜怒哀樂的生物,才是生態女權主義所秉持的人與自然的觀點。文中安東尼亞會在半夜冒雨為她的樹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園子,秋日里一望無垠的草垛,夜幕即將降臨時緋紅的天邊,備受人們愛護的路邊的向日葵,都是人類的伙伴,都讓吉姆這個“風光”的城里人眷戀不舍。
轉貼于中國
中國 四、結語
生態女權主義者強調女性擁有一種男性所沒有的本性、一種與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在《我的安東尼亞》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權利、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同時,與大自然結下了不解的情誼,這正是生態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人與自然的回歸。這種回歸不像環境保護者那樣雖然倡導的保護環境,但卻以自然為人類服務為目的;也不像女權主義者那樣雖然爭取與男性擁有同等社會權利,但卻仍然將男性、女性視為對立的兩種群體;這種回歸是女性運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實現自己的價值同時也在實現自然的價值,實現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此,生態女權主義者倡導女性用自己保護自然、珍愛自然的實踐行為構建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處的生態模式。因此通過生態女權主義解讀《我的安東尼亞》,不僅加深了對作品中的生態女權價值觀的理解,也對生態女權主義文學評論的基本觀點有了更深的認識。中國
參考文獻:
[1] 孫宏.《我的安東尼亞》中的生態境界[j].外國文學評論,2005,(1).
[2]王諾.歐美生態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willa cather.my antonia [m].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5.
第3篇
[論文關鍵詞]方衛平;兒童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藝術化
批評和藝術,是兩個很難讓人聯系到一起的詞。前者指對文學理論的探討和對作家作品及相關文學現象的闡釋評價,它容易引起讀者深奧,甚至艱澀的感覺,是偏于理性的詞語;而藝術則往往為欣賞者帶來形象感,相較于批評,是一個帶有感性色彩的詞。不過,在讀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后,我不由得將這兩個詞聯系到了一起,原來,批評也可以很藝術。
其實,方衛平教授對批評方式的藝術化的傾心可以從他對“藝術”一詞的鐘愛中見出,在《文集》中,藝術一詞所用的頻率非常高,諸如藝術狀態…、藝術內容、藝術思維、藝術對象、藝術敏感、藝術召喚、藝術蹤跡、藝術秩序、藝術偏態、藝術回歸等詞語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頻繁地使用了藝術一詞,不管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我看來,《文集》所達到的兒童文學批評的藝術化效果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兒童文學理論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匯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別是作者的專著《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以下簡稱《批評史》)和《法國兒童文學導論》(以下簡稱《導論》),卷二是作者的單篇評論性文章和專著《兒童文學接受之維》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對中外兒童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進行的闡述,也是單篇評論性文章的結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論、評三部分,我以為,作者的批評的藝術化這一風格在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批評的藝術化,通常是指批評主體批評思維的藝術化和批評呈現形式(批評文本)的藝術化。于《文集》,作者無論是對文學理論批評史和文學發展史的探究,對文學現象的思考,還是對作家作品的體味和闡發,總是能以自己的學術激情和智慧對當時的文化語境進行獨到的研讀和體悟,進而以自己個性化的學術語言,為我們提供了既具理論深度又不失批評活力的學術文本。
文學史的書寫,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對史料進行藝術化處理顯得極為重要,這就需要書寫者對歷史的獨特悟性和對歷史尺度的準確把握,這種悟性和把握主要見諸書寫者以個人的史觀對史料進行篩選,并以此為基礎,完成文學史的文本敘事形態。
閱讀《文集》第一卷《批評史》和第四卷《導論》,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觀而辨證的史觀。作為文學史的書寫者,作者往往能對具體的文學批評作出客觀的評價,不管是肯定還是指出不足,他都不會以現今的標準去苛責前人。如在談到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對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影響時,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說,“雖然前蘇聯的理論模式在今天看來帶有許多消極因素和歷史局限,但它曾經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起到過促進的作用,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的”,從中,作者對歷史把握的態度可窺一斑。此外,“歷史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因果決定論所能決定得了的”、“理論的自信與理論的寬容同樣重要”、“當然,現代早期兒童文學研究中存在這些不足是難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評述在書中也時而出現。不僅是文學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滲透著作者的這一史觀,如“歷史的發展充滿了辯證法”,“歷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客觀現實,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學史觀決定著文學史書寫者親近歷史的方式,方衛平先生以自己對文學史持有的激情體悟著文學史。“作者一反傳統的史論述著中多見的述著者冷靜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場,以及隱蔽的‘幕后論理者’的角色慣例,頻頻在史論闡述的前臺‘亮相”,這既是作者對文學史懷有激情的一個注腳,也是作者親近文學史的具體方法——述評,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貫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評史》和《導論》都是對歷史的描述和對史實的理論闡發的結合,歷史描述顯得客觀而冷靜,理論闡發則透出作者的激情。兩者的結合可以為文本帶來活力和跳動感,而不見了文學史敘事中易于出現的沉悶之感。
文學史觀還決定著書寫者對史料進行收集、篩選和布局的方式。翔實、準確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這無疑得益于作者嚴謹的治史態度。作者在《批評史》的“后記”中提到,“由于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更由于這一研究領域(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蕪,人們常常在有意無意之中忽視了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存在過的那些理論批評現實”,可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記中提到,為確定中國現代第一部《兒童文學概論》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還是“周侯于”,而翻閱了大量資料。正是作者治學的嚴謹,為讀者帶來了閱讀上的放心。雖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諸般努力,但,作者并沒有為此將自己收集的史料進行全盤羅列,而是以自己敏銳的眼光對史料進行解讀、篩選,這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導論》的工作即是“宏觀描述與微觀分析、總體把握和個案研究”的相互體認。《導論》主要是依照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脈絡展開敘述的,這即是“宏觀描述”、“總體把握”的一側。具體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對法國兒童文學進行了整體的把握,闡述了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主要特點,不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體論述部分述評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沿革。就“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時間為緯對法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分期,且他對每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紀被概括為“法國的自覺”,18世紀被概括為“盧梭的世紀”,19世紀被概括為“黃金時代”,作者將法國兒童文學發展中的這一時期特征闡明為世紀特征,對此,他在前言中做了這樣的闡述:“法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節奏與世紀更迭的自然時序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它確實構成了一個獨特而有趣的歷史發展事實——對于本書來說,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歷史敘述線索和邏輯框架”;不僅僅限于“世紀特征”,“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還體現在作者對各個歷史時期內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準確把握上,如19世紀的塞居爾夫人、喬治·桑、儒勒·凡爾納、埃克托·馬洛等,20世紀的圣·埃克蘇佩利、保爾·阿扎爾、馬塞爾·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當時一個時代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水平的作家。史料與理論支撐的緊密融合,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層次特色。人類學、文化學、闡釋學等中外文藝理論在作者的論評說時有涌現,但作者并不是為了搬用理論而用理論,他通常在這些理論的挪移中,與文學史料貼切結合,從而為自己的理論建構而用。
如果說史觀和親近文學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觀上的努力方向的話,那么對史料進行收藏、篩選和布局的方式則是讀者所見到的文本呈現方式,也是讀者借以對作者藝術化書寫文學史的風格進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觀上的內蘊同時也決定著他親近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論評中呈現出來的又是怎樣的藝術化方式呢?
理論探求是對思想深度展開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書名《思想的邊界》極富哲理性,但相信讀者讀后的強烈感覺是思想無邊界。“邊界”和“無邊界”看似矛盾,其實正是作者藝術化批評處理的結果。邊界是文本觸角延伸的限域,無邊界則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達到的空曠遨游狀態。在有邊界的文本格局里,飛翔著的思想卻沒有邊界。從有邊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論格局為“理論探索”、“批評縱橫”和《兒童文學接受之維》三個版塊。雖然,三個版塊各有側重點,“理論探索”是對兒童文學中一個個具體理論點的探究,“批評縱橫”主要是對兒童文學現象的考察,包括對一些理論批評者和批評著作的考察,《兒童文學接受之維》是對兒童文學中的“接受”課題進行的闡發,但是,不同的豐富性正突現著作者的批評個性,他總是選取能觸動他的理論感動的批評點,這些批評點或者是在當時的兒童文學理論中尚且處于模糊狀態、有待探討的,或者是雖引起了諸多的理論關注,但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的話題,如“理論探索”中的“兒童文學理論邏輯起點”話題、“兒童本體觀”話題、“經典”話題、“兒童文學的民族性與現代性”話題、“兒童文學的深度”話題和“少年讀者”話題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論儲備,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對這些話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將童年作為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等觀點都給予了當時的探討以推動作用。“批評縱橫”中“對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體系建設”的考察、對“浙江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近代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重要評論者的評論等。在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銳的理論眼光,通過對當時復雜的現實的透視,發出了自己的批評聲音;《兒童文學接受之維》選取的是兒童文學理論中受到普遍關注、并被加以諸多探討的“接受”問題展開的思考。作者在對中外文藝理論,如接受美學、解釋學、新批評等理論的信手拈來中,在對相鄰學科,如心理學、教育學甚至生物遺傳等學科知識的熟稔運用中,在將“接受”與現實兒童文學發展的聯系拷問中,將“接受”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次。在作者營造的思想空間中,讀者體驗到的是思想上沒有邊界的展開和漫游。
作為一位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方衛平教授既親身投入這一領域中出現的許多重大探索,也為其中某些固守的觀念而焦慮;既有對探索精神的積極肯定,也有對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問題進行的思考;既主動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見解,也樂意甚或期盼聽到其他批評者不同的理論聲音。
對文本的闡釋集中體現了闡釋者以自身的理論功底對文本進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與闡釋》,一則日文本,一則日闡釋,此卷正是對文本進行的闡釋,包括了“創作尋蹤”、“年度論評”、“作品解讀”、“域外偶拾”和“夢尋小記”五個模塊。文本在這里獲得了廣義上的涵義,它既是指記載了兒童文學創作者創作足跡的具體作品,如《灰顏色白影子》、《彭懿童話文集》、《六年級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兒童文學整體創作軌跡的文學記事,如1990年少年小說的發展,9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兒童文學的發展等。進入作者理論批評視野的往往是當時兒童文學領域中的焦點文本,這顯示了他的學術敏感性,如“創作尋蹤”中對《中國少年文學書系》、對少年文學、對新的藝術常態及對《兒童文學選刊》等進行的思考,“作品解讀”中對常新港、梅子涵、張之路、班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關注,“域外偶拾”中對拉丁美洲的兒童小說、日本的“晴天下豬”等現象給予的注視。
作者在文本闡釋的批評角度的切人、批評尺度的拿捏、批評過程的推演、結論的得出及希望的表達等方面都具個性。盡管具體的評論文章不盡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評擅長由描述切人論題,如《一份刊物和一個文學時代——論》、《青春的萌動——當代青少年文藝現象的描述和思考》、《論當代兒童文學形象塑造的演變過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論和材料的支撐下,他將批評層層推演、不斷深入,這種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將結論拋給讀者,而是使讀者在閱讀的帶動下完成自我意識中的推理過程,進而順應地獲得和接受結論的過程,藝術化的批評實現的是藝術化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