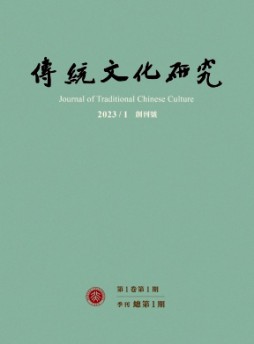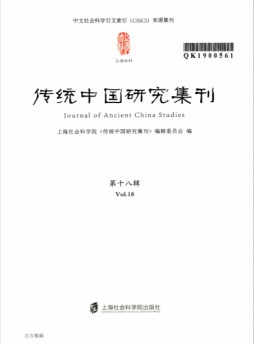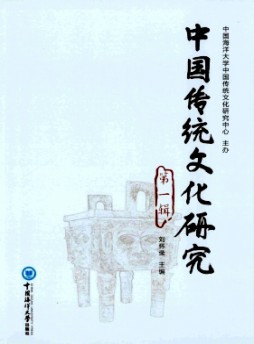傳統(tǒng)村落的保護(hù)與進(jìn)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傳統(tǒng)村落的保護(hù)與進(jìn)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落水村分為落水上村、落水下村,上村靠山而建,下村傍湖而居,[1]下村發(fā)展旅游較為完善,其主要經(jīng)營者為摩梭人,但目前經(jīng)營模式效仿外來商業(yè)模式,缺少民族特色且品質(zhì)還不及里格村;里格村坐落于獅子山下,是瀘沽湖北緣灣內(nèi)一個(gè)美麗的半島,三面環(huán)水,一條小路與湖堤相通,環(huán)境十分幽靜,[2]其主要經(jīng)營者為外來商人,商業(yè)化比落水村嚴(yán)重,摩梭文化幾乎蕩然。
(一)落水村現(xiàn)狀
民俗文化,民俗活動展現(xiàn)形式單一,目前落水村僅三種民俗活動展示,即拉馬、劃船、歌舞篝火晚會,活動對外展現(xiàn)略顯簡單,無法讓人深層次了解民俗;缺乏摩梭文化對外展示的平臺,整個(gè)落水村基本無文化展示場所,來此的人,是對其民俗文化深感興趣的,但現(xiàn)在只剩下滿目琳瑯的店鋪,讓懷著好奇心來探尋摩梭文化的游客倍感失落。景觀營造,建筑大體保持木楞結(jié)構(gòu),但建筑密度較大,丟失了原本建筑與建筑之間保持距離的格局形態(tài),使之既不利于木結(jié)構(gòu)的防火也給人壓迫感;沿街造景單調(diào)、乏味,缺失民族景觀塑造,目前為兩種處理方式,沿街設(shè)休息坐凳、懸空親水平臺;景觀用材過于現(xiàn)代化,道路與駁岸采取規(guī)則的青石板,使景觀質(zhì)感失去了淳樸感。植物景觀,缺乏整體規(guī)劃,植物造景整體性雜亂、局部缺乏美感;停水植物造景效果不明顯,岸邊景觀較生硬;濫用耕地改造為建筑用地,導(dǎo)致村民經(jīng)濟(jì)林木的減少,減少村民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環(huán)境也遭到破壞。建筑構(gòu)造,建筑外觀屬摩梭居住的木楞結(jié)構(gòu),但局部形式已發(fā)生改變,傳統(tǒng)的摩梭建筑樓層為二層式,但為滿足游客人流量,如今三層、四層房屋也拔地而起,破壞了瀘沽湖的天際線;建筑內(nèi)部格局也與傳統(tǒng)也背道而馳了,原來的祖母房、經(jīng)堂、花樓、草樓圍合而成的三合或四合院改成了賓館標(biāo)間的形式,內(nèi)部裝飾隨即也變得毫無摩梭特色;材料在細(xì)部上,抄襲外來商人房屋處理方式,融入現(xiàn)代材料,破壞了建筑的原汁原味感,失去了原有的價(jià)值。
(二)里格村現(xiàn)狀
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活動表現(xiàn)較為簡單,目前此地有一家藝術(shù)劇院,每晚上映著風(fēng)情、人俗的表演,用商業(yè)的形式來表現(xiàn)瀘沽湖的內(nèi)涵,除此之外,無其它民俗文化展現(xiàn)。景觀營造,建筑景觀形式繁、雜,民族特色丟失,出現(xiàn)多種形式外來建筑樣式;商業(yè)景觀形態(tài)無摩梭特色,多種外來商業(yè)形態(tài)出現(xiàn),如西洋酒吧、咖啡廳、家庭旅館布滿整街道;交通組織混亂,人車無分流,缺少安全考慮并降低景觀品質(zhì);景觀細(xì)部民族特色缺乏,小品、欄桿、臺階等設(shè)計(jì)與選材過于現(xiàn)代都市化,與環(huán)境不相符合。植物景觀,植物整體規(guī)劃性欠缺,植物景觀呈現(xiàn)散落狀,植物栽種隨意性強(qiáng),造成植物景觀從空間上看顯得小氣、雜亂;植物景觀藝術(shù)性、美感性不夠,現(xiàn)有植物群落營造景觀方式略顯單一,缺乏植物造景藝術(shù)與美感的構(gòu)造,并且植物組合層次少、品種少、顏色少。建筑構(gòu)造,摩梭建筑的本質(zhì)遭到破壞,建筑形態(tài)已變樣,由傳統(tǒng)的四合院形式,正面可觀的為三面屋頂,而現(xiàn)在卻出現(xiàn)多個(gè)屋頂,改成“小洋樓”的樣式;建筑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也并非四合院或三合院形態(tài),樓房樣式的小木樓是里格村建筑樣式最為突出的變化,但這種形式的變化與傳統(tǒng)不相符;建筑材質(zhì)上的質(zhì)感消失,玻璃材質(zhì)大面積地用于門、窗等,失去了木頭門、窗的純粹感。
如此下去,落水村、里格村都將失去傳統(tǒng)民俗、文化,他們將失去人類寶貴的歷史財(cái)富——母系氏族的活標(biāo)本,他們將失去旅游發(fā)展的大好前途。瀘沽湖發(fā)展旅游業(yè)優(yōu)勢點(diǎn)就是民族文化特色,而民族文化旅游是以人文事象和自然風(fēng)光為旅游吸引物,以體現(xiàn)異質(zhì)文化,追求純樸潔凈,滿足“求新、求異、求樂、求知”心理動機(jī)的旅游活動。[3]只有如定義所貫徹,景區(qū)才能可持續(xù)發(fā)展而且母系文化也可得以保存。由此可見保護(hù)傳統(tǒng)文化將首當(dāng)其沖,并以此為前提,發(fā)展落水村與里格村為不同性質(zhì)定位的旅游村落,即落水村——展現(xiàn)摩梭人民俗風(fēng)情的村落;里格村——文化藝術(shù)與創(chuàng)作的村落。使兩村落在即保護(hù)摩梭民俗的前提下,又具不同旅游價(jià)值點(diǎn),讓保護(hù)與進(jìn)步同步發(fā)展。
(一)落水村的保護(hù)與發(fā)展
民俗文化,豐富民俗活動展示,保留原有的傳統(tǒng)項(xiàng)目拉馬、劃船、歌舞篝火晚會,并將此與飲食、手工飾品、民族服飾等串聯(lián)一起,組成活動一條龍的形式,使原有單薄的活動表現(xiàn)形式變得豐富;增加文化展示平臺,讓來于此的游客不會是走馬觀花,而是能了解摩梭民俗、文化,并能體驗(yàn)?zāi)λ笤鷳B(tài)的生活方式。主要通過兩種方式表現(xiàn):一是修建民間藝術(shù)展覽體驗(yàn)館。一方面展出摩梭人文化、生活、娛樂等各方面,如年滿13歲的男孩與女孩需參加的成人禮,至此之后便可以社交等。“走婚”并非亂倫,他們有較好的道德約束。另一方面提供游客體驗(yàn)?zāi)λ笕松顮顟B(tài)的設(shè)施,如走婚體驗(yàn),這樣才能切實(shí)地讓游客感受歷史博物館并不枯燥。二是在落水村經(jīng)營旅店的摩梭人,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所在,熟知摩梭生活的各方面,因此要讓下榻旅店的游客吃上本土飲食、住上摩梭最純正的民居、玩上當(dāng)?shù)靥厣珚蕵贩绞健_@樣不僅有利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hù)與發(fā)展,而且也能與外來經(jīng)營模式的里格村形成有利的競爭。景觀營造,保持建筑之間一定的距離感,嚴(yán)禁在建筑與建筑之間見縫插針,破壞原有的植被,修建建筑體,使整個(gè)建筑節(jié)奏過于緊密,且摩梭建筑主要材料為木材,狹窄的建筑間距對于火災(zāi)防范也不利,將會給摩梭人帶來財(cái)產(chǎn)與生命的安全性更大,另外過于緊湊的布局使摩梭人失去了原有的山水構(gòu)架——有山、有水、植物環(huán)抱人家的美好畫面,舒適性遭到破壞;豐富沿街布景,增加園林景觀小品與雕塑組合在其中,營造摩梭人生活場景畫面,做到處處有景,使游客真正能做到在沿街中能賞建筑、看風(fēng)景、品民俗的三重感受;景觀材質(zhì)上應(yīng)選用本土用材與原生態(tài)的材料,道路以及沿湖駁岸還原生態(tài)狀態(tài),勿用規(guī)整的青石板等,使環(huán)境貼近原本摩梭人的生活。植物景觀,應(yīng)將落水村整體、組團(tuán)規(guī)劃考慮,運(yùn)用當(dāng)?shù)氐牟荼局参餅橹鳌⒈就翗浞N為輔的植物配置,打造成花香四溢、綠樹成蔭的植物景觀,營造出鳥語花香,環(huán)境優(yōu)美的湖畔村落;加強(qiáng)停水植物的配置,選用本土停水植物種植于岸邊,弱化硬質(zhì)駁岸,豐富湖畔邊的造景,使湖水更加生態(tài)、靈動;嚴(yán)禁將耕地變?yōu)榻ㄖ玫兀?dāng)?shù)鼐用穹从常瑸榘l(fā)展旅游業(yè),將自家的耕地變成了商業(yè)用地,但經(jīng)濟(jì)效益卻不是好,耕地也失去了。因此在發(fā)展過程中,當(dāng)?shù)卣杓訌?qiáng)力度管制,采取村民合作的方式,保留耕地,栽種經(jīng)濟(jì)林、果樹等,不僅能增加當(dāng)?shù)厝宿r(nóng)業(yè)收入,也有利于形成景觀的錯(cuò)落、層次感,最終能保護(hù)周邊的山水構(gòu)架。建筑構(gòu)造,保留木楞構(gòu)造,整條村落的建筑外觀大體形式需保持一致,具體形式,每家可有區(qū)別,但在風(fēng)格上應(yīng)屬于當(dāng)?shù)靥厣问剑庥^保持傳統(tǒng)的木楞結(jié)構(gòu),限制樓層高度,不能超出4層,二層為最佳,需保持建筑在不打破原有的瀘沽湖的天際線,使之大體發(fā)展維持在一定的基準(zhǔn)中;落水村建筑內(nèi)部空間,需恢復(fù)與保留原有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圍合方式,在滿足游客居住所需的現(xiàn)代化設(shè)施前提下,內(nèi)部空間結(jié)構(gòu),正房、廂房的組成盡可能保留,內(nèi)部房間陳設(shè)按照摩梭當(dāng)?shù)丶彝サ牟季中问剑绮煌块g的也能為游客提供不同感受與規(guī)格、檔次,使之不僅保留了傳統(tǒng)建筑、室內(nèi)而且也能為當(dāng)?shù)鼐用駧硎袌龈偁幜Α⒃黾邮杖耄徊牧线x用本地特色材料,避免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材料,如玻璃、鋼鐵等運(yùn)用于門、窗,使建筑失去摩梭建筑的淳樸感。
(二)里格村的保護(hù)與發(fā)展
民俗文化,豐富里格村的民俗文化,使其展現(xiàn)出來的既有具有摩梭特色又與落水村展現(xiàn)的有區(qū)別,根據(jù)里格村經(jīng)營對象為外來商人,他們對當(dāng)?shù)仫L(fēng)俗、文化相對于陌生,但他們具有較好的商業(yè)經(jīng)營模式與理念,熟知如何包裝,將廉價(jià)的物品具有較好的價(jià)值,因此這部分人應(yīng)與當(dāng)?shù)啬λ笕瞬扇『献鳌⒒ダ姆绞綄ΜF(xiàn)有的摩梭的娛樂、服飾、飾品、手工藝品,進(jìn)行再次加工與創(chuàng)作,將其特色民俗文化在修飾后的具有較高的美感、藝術(shù)性,能具有對外展示、宣傳的良好功能。這樣不僅繼承發(fā)揚(yáng)了傳統(tǒng),而且與落水村發(fā)展形成不同。景觀營造,杜絕將外來樣式帶入里格村,建筑風(fēng)格整體上需是摩梭建筑樣式,細(xì)部上可突出特色,但特色也需屬當(dāng)?shù)靥厣桓淖冊型鈦砩虡I(yè)形態(tài),咖啡廳、西餐廳等,將傳統(tǒng)手工藝、服飾、飾品等加工再創(chuàng)作,西餐廳、咖啡廳改成當(dāng)?shù)氐娘嬍巢蛷d,使之具有一定適當(dāng)性,與大背景相吻合,還區(qū)別于傳統(tǒng)模式——落水村的景觀商業(yè)形態(tài);景觀細(xì)部需遵循當(dāng)?shù)靥厣∑贰跅U、臺階等設(shè)計(jì)與選材都因是本土風(fēng)格與材料,在此基礎(chǔ)上,可以再加工、設(shè)計(jì),使之具有一定的美感與藝術(shù)性。也只有這樣,才能與大環(huán)境相合。植物景觀,在植物搭配上,以本土植物為基準(zhǔn),規(guī)劃要整體考慮,避免植物景觀出現(xiàn)散、亂、碎的情況;設(shè)計(jì)植物更具藝術(shù)與美感性,增加植物組合層次、品種、顏色,選擇本土植物無需修剪并有一定的觀賞效果,目的是,營造一種野趣感,最后注重色感、美感、質(zhì)感的搭配,需考慮植物季相變化,游人在其中能感受春、夏、秋、冬四季植物的姿態(tài),使游客在其中能感受到富有藝術(shù)氣息的植物配置。
建筑構(gòu)造,在整體風(fēng)格上,里格村應(yīng)保持木楞房的基礎(chǔ)樣式,結(jié)構(gòu)應(yīng)屬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形態(tài),所有的樣式需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發(fā)揮創(chuàng)作,使里格村能做到雖內(nèi)部格局可能與傳統(tǒng)不同,但大體形式是相同的;統(tǒng)一材質(zhì),盡量需用本土材料,少運(yùn)用玻璃、鋼鐵構(gòu)筑建筑體,木材因最大限度采取本土木材資源,保持木材本身的質(zhì)感、顏色,使之能在大體形式符合摩梭建筑樣式,讓建筑的整體感更具本土性。四、結(jié)語綜上所述,只有將落水村與里格村通過民俗文化、景觀營造、植物景觀、建筑構(gòu)造四個(gè)方面統(tǒng)一保護(hù),在母性文化總領(lǐng)下發(fā)展旅游,將落水村發(fā)展成展現(xiàn)摩梭人民俗風(fēng)情的村落,里格村發(fā)展成文化藝術(shù)與創(chuàng)作的村落,在保護(hù)之中求發(fā)展進(jìn)步。否則,這種表面、膚淺的旅游開發(fā)就將把重要的母系文明所吞噬,最終旅游業(yè)也會窮途末路。就目前來說,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村落就相當(dāng)于一副祖?zhèn)鞯拿嫞S多建設(shè)行卻把它變成一張毫無價(jià)值的印刷品。[4-5]傳統(tǒng)村落的保護(hù)不是只保護(hù)那些歷史建筑的軀殼,更為核心的是保存它承載的文化。[6]母系氏族這塊人類文明的活化石它是瀘沽湖摩梭人最為寶貴的財(cái)富,它也是這個(gè)地區(qū)走出家門、國門的必要條件;而發(fā)掘傳統(tǒng)村落文化的存異性,是瀘沽湖與瀘沽湖的旅游業(yè)雙贏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本文作者:金鑫、樊國盛、陳堅(jiān)單位:西南林業(yè)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