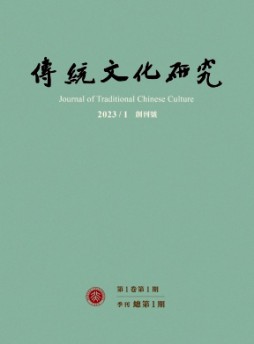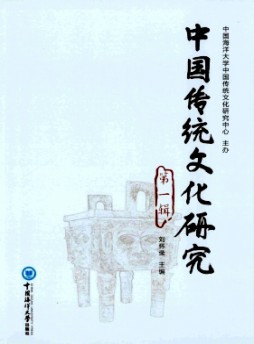傳統文化資源價值重組解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傳統文化資源價值重組解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悠久豐富的傳統文化并不是文化力量的直接對等物,它就像蘊藏在地下的豐富礦藏,如果不經過人工的開采、加工它永遠都不可能轉化成推進歷史列車的動力,不可能“兌現”它的內在能量。因此,特定的文化資源只有經過創造性轉化,才能夠實現它的現代價值。像傳統戲曲《趙氏孤兒》的原作中所貫穿的“血親至上”的傳統道德,這曾經是推進全劇情節發展的重要敘事動力。與此相一致的還有一種“冤冤相報”的復仇倫理。論文百事通在元雜劇《趙氏孤兒》中屠岸賈開始是要把趙盾全家滿門抄斬;而最后在趙孤得勢以后屠岸賈卻遭全家滅門(“全家盡滅亡”)。現在,如果我們在電影中也沿襲這種“你殺了我全家,我也要殺你全家”的殺戮邏輯,就等于把我們置于古代封建社會,在以一種豺狼的方式對待豺狼。人類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是不是也要像納粹法西斯對待猶太人的屠殺方式,把所有的日耳曼人都送進集中營呢?記得美國電影《惡魔軍官》在片頭曾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話:“要想戰勝惡魔的人,當心不要變成惡魔”。就連“娛樂至上”的好萊塢電影也知道不要采用以惡制惡的方式誤導觀眾,我們今天的電影當然不能再去重復過去的殺戮邏輯。現在盡管我們還是在影片《趙氏孤兒》中看到趙孤最后拿起了刀劍,可是,他的行為動機并不是建立在“世襲的仇恨”上,而是建立在他對父親的至愛上。他是為了去完成父親(程嬰)的心愿才要殺死屠岸賈。趙孤對屠岸賈說:“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命,為我爹報仇。”這個“爹”其實并不是在指趙朔而是指程嬰,因為程嬰還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屠岸賈殘忍地殺害了。這就是說,推動趙孤復仇的敘事動力不僅僅是他內心的殺父之仇,還包括了一種替天行道替程嬰報親子被害之仇。可見,同樣是舉刀相向,現代電影中人物的行為動機與傳統戲曲中的動機顯然已經不盡一致了。另外,程嬰在原作中本是趙家的門客,與趙家有利益關系,所以,即便就是獻子救孤,這種身份也會“矮化”程嬰的義舉。因為真正的俠士往往都是在“事不關己”的情況下挺身而出,去完成原來并不屬于自身的道義使命。在電影中根據“利益回避”原則設計的這些人物最容易引起觀眾的普遍認同。陳凱歌說影片中的程嬰是“民做了士該做的事”,我想就是這個意思。程嬰在完全變成一個草澤醫生情況下,他的所作所為與趙家沒有了功利的牽涉,使他的行為相對獨立,也相對崇高,這樣便提升了程嬰這個人物的精神境界,進而也校正了傳統戲曲的價值取向。
與此相關的是影片《孔子》,作者在力圖還原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形象的時候,表現了孔子所向往的社會理想所具有的正向的歷史價值。客觀地講,孔子期望諸流和鳴的大同世界,向往大道暢通、眾芳獻瑞的和諧時代,追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淳樸民風,贊賞尊老愛幼的人倫勝境——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夠實現的。尤其是在電影這種以敘事為核心的傳播媒介中,關鍵的不在于人物在說什么,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去做什么。在影片開始我們就看到一個少女被巨大的石門封閉在墓穴里面,驚恐的尖叫與隆隆落下的地宮大門展示出慘無人道的殉葬制度,而此時的孔子站在了這種野蠻的殉葬制度對立面。他堅決主張廢黜殘酷的殉葬制度,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在當時無疑是一種與整個體制相對抗的進步力量。其實,孔子所向往的“天下歸仁”的社會理想就是再美好,也是在向一個古代的理想社會致敬。我們今天沒有人會愿意與孔子一起回到那個時代。可是我們為什么還會對孔子這個人物產生由衷的敬意、為什么還會對他所倡導的道德理想表示贊譽呢?這表明孔子的某些思想可以跨越時間的屏障,沖破空間的壁壘,贏得人們的普遍認同。其實,我們真正被影片中的孔子所感動是從他踏上風雪交加的周游列國之路開始的。孔子的這種行為代表的是他對自我人生價值的一種抉擇,也是其社會責任的一種歷史擔當。盡管孔子的思想至今還存在著許多爭論乃至非議,可是一個在風雪中懷才不遇的孔子,比一個在官場上春風得意的孔子更讓人們感動;一個在逆境中迎風冒雪的孔子比一個在順境中自鳴得意的孔子更令人敬佩。所以,影片《孔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是從歷史主義的維度上確立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弘揚是從人格精神的建構意義上展開的。
盡管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對于傳統文化資源的開采和利用方式并不一致,但是在文化取向上應當恪守相同的價值觀。我們的有些影片把傳統文化中尊老、敬老的節日,表現成一個殺戮之日。在這個節日里滿城刀光,遍地鮮血,所有的鮮花都被踐踏,人像螻蟻一樣被殘殺。還有些影片把傳統的中醫演變成為最為殘忍的酷刑,它比任何刑具都有效,能夠在頃刻間摧毀人鋼鐵般的意志,這種在商業邏輯主導下對我們傳統的文化資源的“破壞性開采”顯然都是不值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