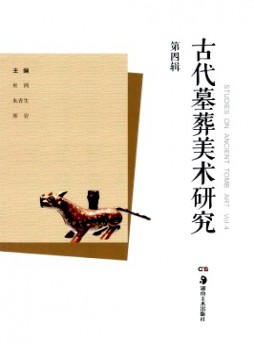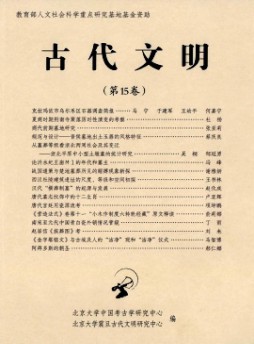古代辭書中的建筑文化信息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古代辭書中的建筑文化信息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我國(guó)古代辭書中,《說(shuō)文解字》(簡(jiǎn)稱《說(shuō)文》)是比較著名的。該書中收錄了眾多的宀部字,宀部字與古代建筑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建筑是文化的上部結(jié)構(gòu),建筑的每一現(xiàn)象都有文化的根基。”這些漢字一方面展示了從穴居野處到地面建筑的悠久建筑文化,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人與建筑、社會(huì)乃至天地萬(wàn)物的關(guān)系。
1宀部字對(duì)上古建筑及五行思想的反映
房屋建筑既保障了人身財(cái)物的安全,又為社會(huì)生活的改善奠定了基礎(chǔ),《說(shuō)文》中的宀部字從文字構(gòu)造、文化意蘊(yùn)的獨(dú)特角度反映了古代建筑和上古先民生活的實(shí)際情況,較全面展示了房屋建筑從上古時(shí)期一直到漢代的發(fā)展演進(jìn)過(guò)程。上古先民最初是“穴居而野處”,利用天然洞穴居住,其后又掘地為穴、上立草木以遮風(fēng)雨,最終木骨泥墻,形成了壯麗繁復(fù)之宮室。在《說(shuō)文》中,對(duì)房屋建筑基本形制進(jìn)行描述的有“宕、宋、宅、家”等字。遠(yuǎn)古時(shí)期,先民多以石洞為居,反映在宀部字上有如“宕”字,《說(shuō)文》曰:“過(guò)也。一曰:洞屋。”朱駿聲《通訓(xùn)定聲》:“洞屋當(dāng)為本訓(xùn)。”林義光《文源》:“洞屋,石洞如屋者,從石宀。洞屋前后通,故引申為過(guò)。”“宕”的甲骨文義據(jù)谷衍奎《漢字源流字典》釋為“會(huì)如屋山洞之意”[2]。石料在中國(guó)傳統(tǒng)建筑樣式中運(yùn)用較少,多在柱子的底部使用墊石,稱為礎(chǔ)。傳統(tǒng)上以為中國(guó)地上建筑缺乏石料運(yùn)用,實(shí)則不然,傳統(tǒng)建筑中廣泛使用的磚瓦與石料性質(zhì)相近,據(jù)考證,周代可能就已經(jīng)開(kāi)始使用磚瓦,如《詩(shī)經(jīng)•陳風(fēng)•防有鵲巢》“中唐有甓”,甓即建筑所用的磚瓦。磚瓦以水、土為原料,以火為輔,其性近石,金石相通,火以木生,所以磚瓦可謂是涵括了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因磚石在后世五行觀念中以為屬金,氣有陰殺,因而多應(yīng)用于墓室陵園之建筑,這屬于五行思想對(duì)建筑材料選擇的影響。氏族時(shí)代,先民離開(kāi)了洞穴,開(kāi)始構(gòu)建以草木為主材的房屋,掘地為淺穴,四周樹以木樁,上覆茅草屋頂,室內(nèi)以木柱支撐,四周墻體表面涂泥以擋風(fēng)寒,其形制即《說(shuō)文》“宋”字,“居也。從宀,從木。”徐鉉以為:“木者所以成室以居人也。”
林義光《文源》:“木者,床幾之屬,人所依以居也。”上古時(shí)期我國(guó)木材豐富,易于采運(yùn)加工,因而成為主要的建筑材料,“宋”字就是與建筑材料木材有關(guān)的宀部字,反映了先民的建筑材料意識(shí)。中國(guó)傳統(tǒng)建筑觀視建筑為自然的一部分,房屋應(yīng)居者的需求而建,居住者“視建筑且如被服輿馬,時(shí)得而更換之”[3],因而多選擇木材為建筑材料。自然界的樹木是生命源泉的象征,在五行中,木又被視為吉象,以木為材的房屋包括建筑內(nèi)的眾多木柱、家具自然暗喻著居住者欣欣向榮、家業(yè)興旺。土是傳統(tǒng)建筑最重要的材料,這主要緣于其來(lái)源方便、廣泛,先民對(duì)黃土的特性也有深入的了解,因而使用起來(lái)得心應(yīng)手。《孟子•告子下》:“傳說(shuō)舉于版筑之間。”版筑即用木板夾持,中間夯筑黃土以建墻,后世的建筑大多因循此道以土為主材修造,土木所建造的墻壁也是古老洞穴的延續(xù)。土木這兩種建材在性質(zhì)上天然接近,因而表現(xiàn)在五行理論中就是它們相輔相成。土木所建即為家宅,“宅”字,《說(shuō)文》以為:“所托也。”《玉篇•宀部》:“宅,人之居舍曰宅。”《正字通•宀部》:“宅,今謂屋為宅。”宅為居住休息的地方,是一般性的住宅。《急就篇•卷三》顏師古注:“宅,總言院宇之中也。”引申為院落。家,《說(shuō)文》:“居也。”《段注》:“此篆本義乃豕之居也,引申假借以為人之居。”《玉篇•宀部》:“家,人所居,通曰家。”《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扆,其內(nèi)謂之家。”“家”的本義即為人的基本居室。綜上所述,中國(guó)古代建筑所使用的材料相當(dāng)豐富,有泥土、草木、磚石、金屬等,在不同地域、不同時(shí)代也有所側(cè)重和變化,上古時(shí)代和北方地區(qū)多使用泥土草木,建筑手段以木骨泥墻、夯土等為主,近世和南方地區(qū)多以磚混、純木建筑為主。建筑與民族文化息息相關(guān),因?yàn)橄让褚苑课菹笳魈斓兀蚨@些建筑材料也被認(rèn)同為構(gòu)造天地的基本元素,這對(duì)傳統(tǒng)五行思想的形成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2宀部字中蘊(yùn)含的宗教文化意義
建筑還蘊(yùn)涵著審美趣味、宗教態(tài)度、社會(huì)風(fēng)尚等文化意識(shí),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在“室、宗、宔”等字上就描述了宗教建筑與物品,體現(xiàn)著宗教祭祀功能。古代中國(guó)為尊崇祖先的宗法社會(huì),對(duì)祖先、神靈的崇拜源于上古時(shí)代,先民囿于自身力量,對(duì)風(fēng)雨雷電、洪澇干旱、生老病死、福禍人事等自然和社會(huì)現(xiàn)象缺乏客觀與正確的認(rèn)識(shí),以為天地之間存在著超異力量在主宰、控制著這一切,于是便有了神鬼的觀念。在這種信念的驅(qū)動(dòng)之下,先民們逐漸樹立了祖先信仰和天神地祇信仰,并創(chuàng)立崇拜偶像、修造神廟,舉行各種規(guī)模的祭祀活動(dòng)。對(duì)祖先的崇拜是先民對(duì)血親祖輩的敬仰,膜拜的目的是為了保佑家族的延續(xù)、福祉以及在對(duì)外爭(zhēng)斗中獲得勝利。古代宮室的內(nèi)部空間分為堂、室、房。堂為舉行祭祀禮儀的地方;室是堂后面居住人的房子,即為建筑內(nèi)部的居室,人和物充實(shí)在室中;室之兩側(cè)為東、西房。其“室”字,《說(shuō)文》:“實(shí)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許慎認(rèn)為是人到這里而止息。《釋名》:“室,實(shí)也。人物實(shí)滿其中也。”唐•玄應(yīng)《一切經(jīng)音義》卷六:“戶外為堂,戶內(nèi)為室。”《段注》:“以疊韻為訓(xùn),古者前堂后室。”《禮記•問(wèn)喪》:“入門而弗見(jiàn)也,上堂又弗見(jiàn)也,入室又弗見(jiàn)也。”《急就篇•卷三》顏師古注:“室,止。謂一室耳。”陳夢(mèng)家認(rèn)為:“《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是室為廟中之一部分,處于兩夾之中間。”[4]即“室”多為祭祀天地祖先之宗廟的內(nèi)設(shè)房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祭祀天地祖先之宗廟的“宗”字,《說(shuō)文》曰:“尊、祖廟也。從宀,從示。”《段注》:“當(dāng)云:‘尊也,祖廟也。’示謂神也,宀謂屋也。”按照傳統(tǒng)的說(shuō)法,示字上面兩橫代表上天,下面三豎代表日、月、星。《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無(wú)寧以為宗羞。”杜預(yù)注:“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甲骨文中有“祖丁宗”“武乙宗”等卜辭,“宗”當(dāng)是古代紀(jì)念、祭祀祖先的祖廟,如《左傳•成公三年》:“使嗣宗職”,是宀部字中區(qū)別于其他表示居住建筑的專門性符號(hào)。通常認(rèn)為,示字是先民以石擬神膜拜的反映,在我國(guó)民間社神信仰中,人們通常用一大一小兩塊石頭作為“社公”“社母”的象征。據(jù)考證,其金文字形在石頭兩側(cè)各有一點(diǎn),即示字的兩點(diǎn),表示祭奠時(shí)灑落的酒水。另?yè)?jù)董來(lái)運(yùn)考證,其“示”字的甲、金文字形均像樹干之上掛系紙條、布條等物,也就是說(shuō),是用樹干來(lái)祭祀土地神的。如《廣韻》:“祇,地祇,神也。示,上同。”示即地祇之本字。《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釋曰:“示,音祇,本或作祇。”在“宗”字里,上為房屋,下為代表祖先神靈的樹干或木牌,因而宗字就具有了祖先的意義。宗廟這種建筑出現(xiàn)得很早,《詩(shī)經(jīng)•大雅•綿》“作廟翼翼……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描述的便是周文王修建祭祖的宗廟。我國(guó)先民以為,人死后的魂靈都要到另外一個(gè)世界去,即祖先靈魂聚集的地方,所以祭祀祖先是一件神圣莊嚴(yán)的事情,因?yàn)檫@也意味著鑄造自身未來(lái)回歸之路。作為祭祀儀式成熟的表現(xiàn),宗廟中的神主牌有專門的收藏器具,稱之為“宔”。《說(shuō)文》曰:“宗廟宔祏。”徐鍇《系傳》:“以石為藏主之櫝也。”即宗廟之中藏神主的石盒。
在《說(shuō)文》中,“寍、安、宓、宜、宄”等字反映了祭祀祖先、鬼神的相關(guān)程式和內(nèi)容。如“寍”,《說(shuō)文》:“安也。從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由宀(室)、由“心”在“皿”上會(huì)意“安寧”之意。甲骨文字形中有宀有皿有丁,至金文時(shí)則增加了“心”,其中“丁”字形符即“示”的簡(jiǎn)化,表示與祭神有關(guān)。“皿”是先民的飲食物品,也是古人獻(xiàn)祭常用的禮器,“心”可能表示祭祀神靈之后心神穩(wěn)定,也可能是用來(lái)獻(xiàn)祭的血食,古人觀念中以為神靈都是嗜血的,而心臟是血液之源,用它祭祀可以使神靈安寧、安定。安,《說(shuō)文》:“靜也。從女在宀下。”《段注》:“安,竫也。竫各本作靜。今正。立部曰竫者亭安也。與此為轉(zhuǎn)注。青部靜者,審也。非其義。”《方言》曰:“安,靜也。”桂馥《義證》引《六書故》:“室家之內(nèi),女所安也。”“安”為會(huì)意字,甲骨文、金文和篆文皆從女坐在宀(房子)下之狀,表示靜如處女之意,隸變后楷書寫作安。“女”字在甲、金文中的字形多為跪姿,且雙手亦有交叉于身后之形,疑似捆綁之姿,聯(lián)系上古社會(huì),可能是對(duì)戰(zhàn)爭(zhēng)中擄掠的女奴的反映。也有人認(rèn)為,殷商之際女字即有奴仆之意。古漢語(yǔ)詞匯中的人稱代詞“汝”的本字即為女,此人稱代詞含有蔑視、輕視的意味,這大概和當(dāng)初最早用來(lái)稱呼奴仆有關(guān)。商周之時(shí),古人以為向神靈、祖先獻(xiàn)祭物品可以保佑自身,所以祭祀活動(dòng)頻繁而又盛大。祭品除了牛羊之外,還包括人牲,通常由戰(zhàn)俘、奴仆充任,所以“安”字也有可能反映了在宗廟用人牲獻(xiàn)祭的祭祀場(chǎng)景,獻(xiàn)祭之后,奴隸主貴族就自以為獲得了神靈庇護(hù),在心理上就獲得了安全、安定之感。這種獻(xiàn)祭風(fēng)俗在日本甚至一直延續(xù)到明治維新時(shí)期才被廢除。
“宓”字與祭祀也具有一定的聯(lián)系。《說(shuō)文》:“安也。”《淮南子•覽冥訓(xùn)》:“宓穆休于太祖之下。”高誘注:“宓,寧也。”宜,《說(shuō)文》:“所安也。從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徐鍇《系傳》:“一,地也。既得其地,上蔭深屋為宜也。”只是這并非宜的本義,其本義如《詩(shī)•鄭風(fēng)•女曰雞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傳》曰:“宜,肴也。”《鄭箋》:“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shí),與君子共肴之。”其甲、金文字形均為放置肉食祭品的禮器或俎案,本義為獻(xiàn)祭之法,后來(lái)引申為祭祀之名,如《尚書•泰誓》:“祭社曰宜。”至《說(shuō)文》古文時(shí)才加上了宀字形。宗廟祭祀中有了肉食,神靈才會(huì)高興,所以“宜”有“安定”義。宄,《說(shuō)文》:“奸也。外為盜,內(nèi)為宄。”《段注》:“奸宄者通稱,內(nèi)外者析言之也。凡盜起外為奸,中出為宄。”從其甲骨文字形來(lái)看,為商代祓除室內(nèi)不祥的祭名。
3宀部字所反映的宇宙天地文化觀念
廣泛運(yùn)用的大屋頂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建筑的重要特征,自商代以來(lái)頗受人們重視,除了遮陽(yáng)避雨的實(shí)際功效之外,它還具有濃厚的文化意味和強(qiáng)烈的民族精神。《淮南子•覽冥訓(xùn)》記載的上古神話“女媧補(bǔ)天”中,就以“五色石補(bǔ)天”“鰲足所立四極”等事象隱喻先民修繕建筑的屋頂?shù)然顒?dòng)和支撐房屋的大木柱等物象。最早用來(lái)表述大屋頂?shù)氖恰板病弊帧!墩f(shuō)文》曰:“交覆深屋也。象形。”《段注》:“古者屋四注(屋檐滴水處),東西與南北,皆交覆也。有堂有室,是為深屋”。“宀”描繪的是最原始的茅草房屋建筑形態(tài),隨著陶瓦的運(yùn)用,屋頂形態(tài)也出現(xiàn)了諸多變化,形成了雄壯美麗的外觀。在《說(shuō)文》中,有多個(gè)漢字被用來(lái)指稱這最為顯赫的建筑形態(tài),如“宸”字,《說(shuō)文》:“屋宇也。”《段注》:“屋者以宮室上覆言之,宸謂屋邊。”朱駿聲《通訓(xùn)定聲》:“宸,謂屋檐。”又如“察”字,《說(shuō)文》:“覆也。”鄭知同《商義》:“乃屋宇下覆之名。”漢代儒家思想逐漸神化,著力宣稱“以類合之,天人合一”,屋宇的文化意義逐漸加重。屋宇被認(rèn)為取法自然宇宙,建筑成為時(shí)空的象征,如《淮南子•齊俗訓(xùn)》所云“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lái)為宙”。對(duì)于“宇”字本義,《說(shuō)文》以為:“屋邊也。從宀,于聲。《易》曰:‘上棟下宇。’”《詩(shī)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陸德明釋:“宇,屋四垂為宇。”《釋名•釋宮室》更進(jìn)一步形象化:“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郝懿行《爾雅義疏•釋詁》解釋說(shuō):“蓋屋檐四垂,為屋之四邊,天形象屋四垂,故曰‘天宇’,亦曰‘大宇’。”《段注》:“宇者,言其邊。凡于聲字多訓(xùn)大。”也就是說(shuō),“宇”為廣闊的空間,乃至于無(wú)所限度,如《莊子》所言:“有實(shí)而無(wú)乎處者,宇也。”至于“宙”字,《說(shuō)文》:“舟輿所極、覆也。”桂馥《義證》:“舟輿所極也;覆也。”王筠《句讀》:“舟輿所極,即舟車所至。覆也者,猶言天之所覆也。”《釋例》:“以宀為天也。”《淮南子•覽冥訓(xùn)》:“不能爭(zhēng)于宇宙之間。”高誘注:“宇,屋檐也;宙,棟梁也。”《廣雅•釋詁》:“宙,居也。”《段注》:“宙之本義謂棟,一演之為舟輿所極覆,再演之為往古來(lái)今。”“宙”字,久也,本義為房屋建筑內(nèi)的棟梁,進(jìn)而泛指車船所達(dá)之處,“宇宙”也就由具體事物轉(zhuǎn)化到了抽象的時(shí)空概念,如《莊子•庚桑楚》:“有實(shí)而無(wú)乎處者宇也,有長(zhǎng)而無(wú)本剽者宙也。”郭象注:“宇者,有上下四方,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宙者,有古今之長(zhǎng),則古今之長(zhǎng)無(wú)極。”“從建筑理念看,建筑體象宇宙;從宇宙觀念看,宇宙體象建筑,建筑與宇宙是同構(gòu)的”。也就是說(shuō),“宇”和“宙”字深刻反映了先民樸素的空間概念和時(shí)間概念。中國(guó)傳統(tǒng)建筑的大屋頂氣象莊嚴(yán),雍容華貴,其人文意義在于效仿天宇,傳達(dá)的是對(duì)自然的崇拜與模仿。“漢朝人的宇宙觀,可以簡(jiǎn)化為外圓內(nèi)方相疊的圖形上。”人們普遍認(rèn)為,屋頂?shù)乃膫€(gè)突兀的檐角即象征著天地四象,也就是所謂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屋頂加上地基和居住者,這三者成為后世“天、地、人”三才思想的具體來(lái)源與象征。漢代以后,屋檐逐漸向上出現(xiàn)了挑勢(shì),如班固《西都賦》所說(shuō)“上反宇以蓋載,激日景而納光”,宛若鳳凰向天空扇動(dòng)的雙翼,如“寪”字,《說(shuō)文》釋“屋皃”,徐灝《段注箋》曰“此云屋皃,亦謂屋宇開(kāi)張之皃耳”,描述的便是其呈現(xiàn)出的變化。
隨著統(tǒng)一國(guó)家的強(qiáng)盛,秦漢時(shí)代的恢弘文化氣度在建筑上表現(xiàn)為對(duì)高度、規(guī)模的追求,出現(xiàn)了氣吞山河、嵯峨宏大的建筑,如秦代的阿房宮,漢代的長(zhǎng)樂(lè)、未央、明光、長(zhǎng)信、建章諸宮,這些偉岸的建筑以前所未有的尺度和力度充分展示了時(shí)代精神。漢未央宮之正殿為宣室殿,乃皇帝正寢,其名稱中的“宣”字,據(jù)《說(shuō)文》曰:“天子宣室也。”《段注》:“蓋謂大室也。”徐鍇《系傳》引《漢書音義》:“未央前正室也。”除此之外,還有諸多宀部字展現(xiàn)了對(duì)高大建筑的企求,如“寷”,《說(shuō)文》:“大屋也。從宀,豐聲。《易》曰:‘寷其屋。’”孔穎達(dá)《周易正義》:“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cái)多德大,故謂之豐。”《段注》:“宀,屋也。豐,大也。故寷之訓(xùn)曰大屋。”建筑的高大除了展示政治權(quán)力的威嚴(yán)之外,也體現(xiàn)了神仙方術(shù)、道家思想對(duì)現(xiàn)世享樂(lè)的追求。先秦神仙方術(shù)、漢代黃老思想廣泛流布,無(wú)不宣揚(yáng)長(zhǎng)生、養(yǎng)生之樂(lè),以為海上、天上有仙人,皆住巍峨之宮殿,熱衷于現(xiàn)世人生歡愉的人們,自然致力于自身房屋的高大,反映在文字上便是以眾多的漢字來(lái)描述建筑的宏大。如“寬”,《說(shuō)文》曰“屋寬大也”。“宥”,《說(shuō)文》曰“寬也”,朱駿聲《通訓(xùn)定聲》曰“廣廈容人曰宥”,徐灝《段注箋》曰“引申為凡寬宥之稱”。另如“宛”字,《說(shuō)文》曰“屈草自覆也”,徐灝注箋“夗者,屈曲之義,宛從宀,蓋謂宮室窈然深曲”。房屋深廣則有回音,如“宖”,《說(shuō)文》:“屋響也。”“宏”,《說(shuō)文》:“屋深響也。”朱駿聲《通訓(xùn)定聲》:“深大之屋,凡聲如有應(yīng)響。”只有房屋空間寬大才能產(chǎn)生回音,所以用“宏”指示能產(chǎn)生回音的大房屋。“宖”“宏”則用來(lái)形容房屋室內(nèi)空間的廣大。以土木結(jié)構(gòu)為主體的大房子,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重要外在特征,所謂“夏”即為“廣居也”。
4結(jié)語(yǔ)
“以中國(guó)的古代建筑而論,……它們的個(gè)體和群體形象都是一個(gè)時(shí)期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技術(shù)諸方面條件的綜合產(chǎn)物。”[8]通過(guò)對(duì)以上漢字的分析,可以看出,傳統(tǒng)建筑文化審美意義在于雄偉、壯麗,以“方正為尚”,以屋宇廣大為榮,高大的建筑更容易接近上天,鮮明地體現(xiàn)出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道德價(jià)值的影響。
作者:邢怒海 單位: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