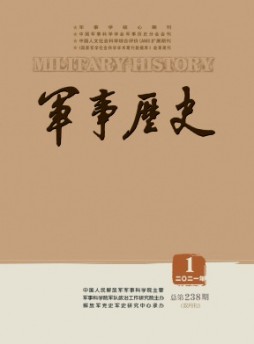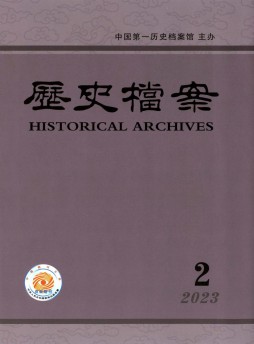歷史文學中封建帝王評價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歷史文學中封建帝王評價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作者們在寫古代帝工生活的時候,也要有主體意識的介入,即對帝王及其生活進行評價。把某帝王的所謂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羅列,堆砌各種資料,拼湊各種細節,虛構具體的場景,東拉西扯,萬般鋪陳,這都是無濟于事的,或沒有意義的。作為的劇作者還應該運用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這個“最現代的思想”去掌握和選擇歷史資料、去歷史事實、去評價歷史人物、去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并最終讓人對于今人的有所“感悟”和聯想。評價帝王應該有三要點:我們的作者不要把這些帝王看成是人生的,離開他們歷史就不能前進;我們的作者們應當把帝王置于歷史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順應歷史潮流呢,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要寫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復雜性,定量分析沒有意義,需要的是寫出他們的悖論式悲劇。
[關鍵詞]主體意識;最現代思想;評價帝王原則
一帝王形象創造需要“主體意識”的參與
有的學者說,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是“雙聲話語”,既要歷史的真,又要的美。這樣說是對的,但還不夠。實際上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是“三聲話語”,除歷史的真和藝術的美之外,還必須有作家或編導的主體意識。所謂主體意識,差不多就是胡風所說的“主觀戰斗精神”。我還認為這第三種聲音,并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劇本的內在的靈魂。誠然,我們看重歷史的真(可信),藝術的美(好看),但是歷史的真和藝術的美如何才能達到呢?這就有賴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與參與。歷史的真,不是現成的東西,盡管有各種歷史著作作為依據,但那是后代的歷史學家追憶的東西,其中的偏見幾乎到處可見,有意的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學者把原本原貌歷史的叫做“歷史1”,而把歷史著作中所展現的歷史叫做“歷史2”。作家不可能面對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的“歷史1”。在我看來,就是大家一致稱贊的司馬遷的《史記》,其中也有不少的虛構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選擇與擯棄,增添和忽略,隱藏與突顯,否則那些人物對話他是從何得來的?難道他司馬遷真的聽到了幾百年前他筆下人物的對談了嗎?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盡可能(我只說盡可能)接近歷史的本真原貌呢?這就要靠作家主觀思想情感的介入與參與,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選擇那些應該選擇的,擯棄那些應該摒棄的,補充那些必須補充,刪改那些必須刪改的……,這樣,也許更能接近歷史本真。藝術的美更要作家主觀思想感情雨露的澆灌,如果沒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澆灌,如實地描寫,或巧妙地描寫,不論描法如何創新,都不可能把讀者需要的藝術的美展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的“主體意識”力量重于歷史的真與藝術的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歷史文學中的另一重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們在寫古代帝王生活的時候,也要有主體意識的介入,即對帝王及其生活進行評價。把某帝王的所謂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羅列,堆砌各種資料,拼湊各種細節,虛構具體的場景,東拉西扯,萬般鋪陳,這都是無濟于事的,或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主體意識的灌注,給帝王一個中肯的評價。把某帝王的真實還給歷史。這種經過作家主體意識參入的歷史,我們似乎可以叫作“歷史3”。帝王的真實不在歷史1,因為這樣的歷史本真無從追尋;也不在歷史2,這僅是歷史家的歷史。唯有具有作家主體意識參予的歷史3,才是歷史文學所需要的歷史真實。
二帝王形象需要“最現代的思想”的評價
馬克思1859年在給拉薩爾的信中,談到他的歷史題材的劇本《弗朗茨?馮?濟金根》創作的得失。馬克思認為拉薩爾對于濟金根貴族們隱藏著的舊的帝國和強權的夢想,描寫得太多,“占去了全部注意力”,而“農民和城市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你就能夠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樸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1](p554)。馬克思這段話對我們是有啟發的。特別他要求歷史劇“用樸素的形式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尤其精辟。如何來理解歷史劇表現“最現代的思想”呢?是不是像正在熱播電視劇《漢武大帝》那樣,漢代的古裝的人們說者現代的白話,加上諸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類清代才有的警句,就表現出“最現代的思想”呢?當然不是。讓古人嘴里充滿了如今才流行的話語,這是作家或編導無能的表現。讓古人做現代的事情,講現代的革命道理,以現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向現代人說教,把一切現代的都強加到古人身上,這是反歷史主義。馬克思要歷史劇表現“最現代的思想”肯定不是指這些反歷史主義的種種做法。
馬克思的意思顯然是作為現代的劇作者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這個“最現代的思想”去掌握和選擇歷史資料、去分析歷史事實、去評價歷史人物、去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并最終讓人對于今天的社會有所“感悟”和聯想。例如在拉薩爾的《濟金根》的劇本中,馬克思認為以“最現代的思想”,分析當時的社會發展趨勢和社會發展力量,不應該把全部的興趣放在濟金根們這些貴族的身上,“農民和城市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特別要有農民的參與,這才更具有歷史真實。
大家都知道曾針對過歷史電影《武訓傳》說過的話:“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留舊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統治階級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過去的歷史中壓迫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0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理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2](p136-137)我認為在這里表述的歷史唯物史觀應該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應該用階級論觀點和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作者們筆下歷史生活,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是以“最現代的思想”來看待歷史的一個典范。按照唯物史觀,封建帝王的本質什么?封建帝王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他們雖然生活于不同的歷史時期,所遭遇的社會各不相同,所具有的個性也各異,但都號稱天子,所謂“君權神授”,個人擁有至高的權威和權力,并以此實行嚴酷的專制統治,有生死予奪之權,用今天“最現代的思想”看,帝王無不是反民主的、反法治的,他們代表著舊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代表著舊的政治和文化,這是他們的共性。盡管歷代帝王中有實行“王道”和“霸道”的區分,似乎“王道”更講人情和道德,更順應民情,所實行的是“善政”,而“霸道”則不顧人情和道德,逆民情而動,一味依靠權勢,頤指氣使,橫行天下,實行惡政,但對于歷代帝王而言,完全實行“王道”的很少,完全實行“霸道”也不多,大多是“王道”中有“霸道”,“霸道”中有“王道”,即所謂的“常道”,而其結果可能會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建立了偉大的功業,有的則庸庸碌碌,潦倒一生。并不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必須要承認的。
與此相聯系,人們可能會問,歷史上是不是有開明皇帝?帝王中是不是有偉大的人物?如果有的話,他們對社會發展問題的解決做出貢獻是否應該得到肯定的評價?我想這些問題都是需要也是可以回答的。馬克思說:“每一個社會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3](p113)的確是這樣,歷史總是給歷史人物(包括帝王)提供了機遇。現實也總是給現實的人提供機遇。不論是什么時代,都可能面臨一些必須解決的問題,如在漢代,北方的匈奴不斷如侵,殺虜邊民,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漢高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所謂的“文景之治”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漢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在衛青、霍去病等將領和無數士兵和廣大人民的支持下,平息了匈奴之亂,同時打通了河西走廊,開辟了絲綢之路,是一大功績。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肯定和頌揚了打擊匈奴所取得的功績,是大體不錯的。所以我們應當承認帝王中有開明的或睿智的或有氣魄的或有才干的,有為歷史過程中重大問題的解決獲得成就的人物,有為民族國家的形成作出貢獻的偉大人物,不承認這一點區別,統統簡單地歸結為罪不可赦的剝削者壓迫者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就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在肯定漢武帝的功績的同時,對于漢武帝的贊頌,也過分“拔高”,特別在開篇的歌詞中竟然唱漢武帝“你燃燒自己,溫暖大地,任自己成為灰燼……”,這樣的鼓吹和贊頌,對封建帝王的漢武帝是合適的嗎?特別是當人們看到他晚年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煉仙丹,喜方士,那種吹噓諂媚之詞,是漢武帝能夠承受得起嗎?漢武帝的偉大,仍然是作為封建帝王的偉大,帝王的本性在他身上并沒有改變,過分的鼓吹乃是臣民的奴性思想在作怪,離馬克思所說的“最現代的思想”很遠很遠。這種過分夸大帝王作用的描寫是一種帝王崇拜,與辛亥革命反帝制和“五四”時間批判“國民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在當代文學創作中,帝王常常是人物描寫的中心,成為作者們極為熱衷的事情。《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成吉思汗》、《漢武大帝》等等很大的小說和電視連續劇,都以帝王作為主角來展開描寫。這里當然不應設什么禁區。在于怎樣寫才是成功的。我認為,在寫帝王的時候,不但要看他們所寫的歷史是否可信,不但要看藝術表現是否栩栩如生,更重要還要看它們對于作為作品的主角的封建帝王的評價是否準確和正確。
那么,我們在描寫那些有作為的帝王的時候,應該注意那些問題呢?
第一,我們的作者們不要把這些帝王看成是天生的,離開他們歷史就不能前進。要知道,在封建中,誰成為帝王,是封建內部斗爭的結果,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恩格斯曾經說過:“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侖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這一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凱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1](p733)同樣的道理,像漢代的漢武帝出現,是歷史需要的結果,因為在那個時期,匈奴的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需要有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帝王出來平定匈奴之亂。如果沒有劉徹,“他的角色會由另一個人來充當的”。那種在小說或影視作品中故意渲染某個帝王出生時就不同凡響,有什么天人感應的現象發生,連孩子哭聲都不同凡人,似乎他真是上天派下來專為解決某個歷史難題的人物。這樣一些描寫,都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偽藝術伎倆。
第二,我們的作者們應當把帝王置于歷史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順應歷史潮流呢,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帝王總生活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的現實是否是必然的合理的呢?即是否合符歷史潮流?如果現實是必然的合理的,你肯定這個現實,擁抱這個現實,那么你是對的。但是如果歷史潮流已經向前發展了,那么就顯示出原有的現實的不合理,必須加以調整或推翻。我們的作者不應該總是守住黑格爾的那句話:“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而應該聽一聽馬克思的話:“一切發展,不管其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發展階段,它們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系著。比方說,人民在自己的發展中從君王專制過渡到君主立憲,就是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4](p169)我們還可以更具體地聽一聽恩格斯的話:“法國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里,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替代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1](p215-216)如果我們聽懂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那么他們的思想是清楚的:一定階段的社會現實不一定是必然的合理的,應該加以贊揚的,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原有的現實可能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那就要用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現實加以取代。對于帝王及其行為的評價,就應該用這樣的觀點加以衡量。
例如同樣是生活于封建社會的帝王,也有一個是生活于封建社會上升時期還是衰落時期的問題,我們對于他們作為的評價,就不能不考慮這種區分。
還是以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為例。這部電視劇的主要人物漢景帝和漢武帝,都處于封建社會上升時期。電視劇的主要內容寫了漢景帝平定內部的七國之亂,建立漢代中央集權,漢武帝討伐匈奴的勝利,擴充了疆土,就應該放到這個歷史背景中去加以考量。漢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戰勝項籍,做了皇帝,建立了西漢王朝。但是漢高祖在立國以后,留下了兩大問題沒有解決。一個諸侯王割據,漢朝廷直接統轄僅有十五郡,其他地方由諸侯王統轄。當時這樣做,對于漢高祖來說實在是出于無奈,因為不分封,大家不能齊心合擊項籍,不能齊心推他為皇帝。但分封之后的局面與戰國的割據局面十分相似,國家未能統一起來,也時時威脅漢王朝的穩定。另一個是對于匈奴的和親政策。漢高祖也曾率三十二萬軍隊進駐平城(今山西大同縣東),準備襲擊匈奴。被匈奴冒頓率40萬騎兵圍困平城七日,漢高祖不戰自退。從此匈奴更加強大,經常入寇西漢王朝西北部邊境,漢朝只能忍辱退讓,以和親政策求得暫時的和平。但歷史問題總是要解決的。漢景帝時期,諸侯王割據問題進一步激化,公元前154年發生了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諸侯王聯合反叛,形成了七國之亂。漢景帝奮起應戰,運籌帷幄,派智謀過人的周亞夫擊敗七國叛軍,滅了諸國。此后皇子受封為侯,只征收稅租,不再管理政事,在中國歷史上真正結束了諸侯割據制度,符合歷史潮流,也加強了西漢王朝的中央集權,這應該說是歷史的功績,作為這場削藩戰爭的最高代表漢景帝有歷史貢獻,應予以積極評價。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對于漢景帝的評價應該說是大體不錯的。漢高祖留下的第二個問題,即對匈奴的戰爭問題則由在位54年的漢武帝解決了。漢武帝從公元前133年-公元前89年開始對匈奴的戰爭,耗費了“文景之治”所留下的大量的經費和各種資源,重用衛青和霍去病等將領,動用了無數的人力資源,征戰44年,打了幾大戰役,最終把匈奴趕往漠北,結束了匈奴對漢朝地域的侵擾。《漢武大帝》贊揚了漢武帝的“雄才大略”,特別是他對匈奴作戰的勝利,這也是符合歷史潮流的,評價應該說也大體不錯。歷史提供了順應歷史潮流的機會,漢景帝、漢武帝雖然是封建時代的帝王,但他們抓住了這個機會,有所作為,建功立業,是應該得到適當的積極評價的。
但是對于處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來說,就不能與漢景帝、漢武帝同日而語了。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所寫的“康雍乾盛世”處于18世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4年,乾隆禪位于嘉慶那年離標志著中國衰落的1848年鴉片戰爭只有44年,離1911年辛亥革命只有116年。對于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古代中國來說,封建社會不但處于衰落的后期,甚至可以說已經進入末世。“康雍乾盛世”不過是封建社會這個衰老的軀體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對于二月河創作的‘帝王系列’長篇小說,以及其后所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明知“康雍乾盛世”不過是末世的‘繁榮’,是即將開敗的花,是即將枯萎的樹,是黃昏時刻的落日,是遠去的帆影,但作者還是不能按照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去真實地把握它,而用眾多的藝術手段去歌頌“康、雍、乾”諸大帝,如稱頌康熙的溢美之詞是:“面對冰刀血劍風雨”,“踏遍萬里山河”,“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夜旋轉”,“愿煙火人間,安得太平美滿”,說他“還想再活五百年”。吹噓雍正則是什么“千秋功罪任評說,海雨天風獨往來,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作者們真的把他們的統治描寫成“盛世”,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推銷最腐敗的專制帝王文化。這不能不說是令人費解的。其實,中國的歷史發展到明代,中國社會自身已經生長出了資本主義的幼芽,特別是到了晚明時期,資本的流通和市民社會也初步形成,特別是出現了泰州學派,出現了李贄等一群思想解放的學者,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加上農民起義風起云涌,使中國到了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頭,如果不遇到障礙,資本主義有可能破土而出。這就是當時社會發展的走向。清朝建立后是順應這個歷史潮流呢,還是逆這個歷史潮流而動呢?這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康雍乾三朝長達134年的統治,雖然社會是基本安定了,生產也得到恢復,但他們把封建主義的專制制度發展到極端,朝庭的全部政務,包括行政、任免、立法、審判、刑罰等一切,事無巨細,都要皇帝欽定。特別是以儒家思想僵硬地鉗制著人們,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盛行的文字獄,一朝比一朝嚴厲。乾隆朝文字獄竟多達一百三十余起,因文字獄被斬首、棄市、凌遲、門誅甚至滅九族等,層出不窮。整個知識文化思想界噤若寒蟬、萬馬齊喑。這一扼殺思想自由的行為,最為嚴重,他直接導致了國民奴性的形成,也直接導致朝庭眼光狹隘、閉關鎖國、蔑視、重農輕商等。可以說在康雍乾三朝已經埋下了晚請社會落后、國力孱弱、內憂外患、亡國滅種的危機。不幸得很,正當我們為17、18世紀康雍乾盛世而自滿自驕自傲的時候,歐洲的主要國家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開始并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科學技術發明接連不斷,轟轟烈烈的革命創造了人類空前的財富,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把東方各國甩在后面。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已經開始向東方的中國虎視眈眈。中國離遭受別人宰割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這就是歷史大趨勢和總趨勢坐標中的所謂“康雍乾盛世”,他們的統治并非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顯然,帝王系列小說并沒有從這種宏闊的眼光來認識這段歷史,雖然二月河也把它稱為“落霞三部曲”,但寫康雍乾的缺陷只是一種點綴,而歌頌他們殫思竭慮為百姓謀利益,不畏艱險為中國謀富強,千方百計為國家除腐敗等則成為主調。這是在歌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最腐朽的東西,我不認為這樣的評價是可以接受的。[5]
第三,要寫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復雜性,定量沒有意義,需要的是寫出他們的悖論式悲劇。現在描寫帝王形象的歷史小說和電視連續劇,總是按所謂的“三七開”、“四六開”來評價,這種量化的評價必然會把帝王形象簡單化,不可能把帝王思想和心理的復雜性充分展現出來。有的作者總是把全部興趣放在這些帝王所謂的建功立業上面,農民和其他階級的不滿和他們的斗爭,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沒有成為對照的背景。
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也存在這個問題。編導者只關心表現他的“雄才大略”這一面,而沒有展現他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一面,當時的農民起義也沒有進入到他們的視野;作者們只關注他性格中堅強的一面,沒有強調他性格中殘酷的一面;只強調他大敗匈奴的戰功,而窮兵黷武的一面則完全被忽略了……。
歷史就是歷史,表現漢武帝,要尊重歷史。一定要把漢武帝的復雜性表現出來。漢武帝不完全是他本人,他就是那個歷史時代的產物。他的一生,無論個人命運,還是政治生涯,都是復雜的。早年的漢武帝意氣風發,雄心不已;晚年他權力獨攬,但他的悲哀是連個親人都沒有。最后寧可把監國大權交給大臣,也不交給親屬。當他權力達到頂峰時,他實際也成了孤家寡人。漢武帝還夢想長生不老,導致各種迷信的騙子出入朝廷,攪擾朝政。晚年更是剛愎自用,性情古怪,朝令夕改,深不可測,太子被迫自殺,衛夫人也被迫自殺,后來誰被他任命為丞相,誰就會感到大禍臨頭,甚至有人哭著不肯做丞相。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漢武帝下“罪己詔”時,罪惡已經鑄成,已經無法挽回。他為了支持對匈奴的戰爭,需要經費,不能不巧取豪奪。于是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田三十畝按一百畝征收稅租,口錢二十改為二十三,七歲起算改為三歲起算,結果,貧民生子多殺死,農民貧困破產。在漢武帝統治下,“海內虛耗,人口減半”。這是漢武帝自己沒有想到的。
漢武帝完全是個悖論式的悲劇人物,可以說,他是一個普通人,有人性人情,但又是一個政治家,擅權專斷,不講道理;他是一個明君,深知自己的責任,但又是一個暴君,殺人如麻;他權力大無邊,臣民們都圍著她轉,但他又是孤家寡人;他是一個情種,他鐘情于女人,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可他又是一個無情的人,頃刻之間,見異思遷,移情別戀,而且說殺就殺;他是一個硬漢子,殺發決斷,敢作敢為,但又是一個軟弱的人,他害怕他做的事情有可能失敗……這樣的復雜的人物性格,不是“三七開”、“四六開”的定量分析可以表現出來的。應該充分展現他的多面性格,展現他內心的痛苦,展現他最后的又勝利又失敗的悲劇悖論……可惜得很,我們所見到電視連續劇恰恰停留在這種“三七開”的定量分析中,因而無法展示特定時期帝王性格的復雜性和悲劇命運。
擴展閱讀
- 1歷史形象歷史題材
- 2歷史
- 3少先隊歷史
- 4憲政歷史
- 5東歐演變歷史
- 6歐洲擴張歷史思索
- 7文化歷史論文:古代的音樂文化歷史
- 8唯物史觀歷史命運
- 9音樂史料歷史
- 10鄉土歷史資源在歷史教學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