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式散曲家的個人境遇與心態(tài)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家庭式散曲家的個人境遇與心態(tài)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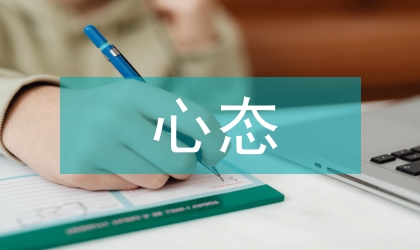
《西華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四期
摘要:
楊廷和、楊慎、黃娥是明代中期特點鮮明的三位家庭式散曲家。個人境遇與心態(tài)的變化使楊廷和的閑適曲背后蘊有一種不安、郁悶的心緒;長期謫戍云南的痛苦經(jīng)歷使楊慎的離思曲表達出了痛切、感人的真情;三十多年的獨守生活與女性獨有的心思使黃娥的離思曲中舒泄出了悲苦、幽恨的情懷。
關(guān)鍵詞:
楊廷和;楊慎;黃娥;散曲;心態(tài)解析
生活境遇的變化會影響到作家思想、心理的轉(zhuǎn)變,特別是在遇到一些重大變故時,這一影響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與深刻。具體到文學創(chuàng)作,這些影響與變化會程度不同地波及到題材內(nèi)容的選取、藝術(shù)形式的選用與復雜、微妙情感的表達。明中期的散曲家楊廷和、楊慎、黃娥分別為父子、為夫婦,嘉靖年間的“大禮議”事件對這一顯赫家庭,尤其是對這三人的境遇與命運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沉痛的打擊影響到他們各自心態(tài)的變化,也影響到了他們的散曲創(chuàng)作。這里,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與個人境遇,我們從解析散曲文本入手來探尋他們曲作中蘊載的個體心態(tài),以助于對三人當時困苦心態(tài)的了解與體察,也助于透視震驚朝野的歷史事件———大禮議———對一個官宦家庭成員命運的影響。
一、閑適、淡泊背后的不安與郁悶———楊廷和閑適曲中的心態(tài)解析
楊廷和(1459—1529)官至內(nèi)閣首輔,是明代歷史上的一位重臣。據(jù)《全明散曲》計,楊廷和現(xiàn)存散曲作品117首/套,涉及9種題材類型。其中,僅詠懷、閑適類題材就有98首/套,占現(xiàn)存曲作總量的83.7%,表現(xiàn)出題材狹窄、思想單一的特點,與同時代關(guān)中曲家康海散曲題材的24類、王九思的17類比,有著明顯差距,這也是楊廷和在明代散曲史上地位不夠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楊廷和的曲作中沒有涉及當時多數(shù)曲家關(guān)注的言情曲,而是以表達隱閑、自適情感的閑適曲為主,表現(xiàn)出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特點。如[北雙調(diào)•殿前歡]《閱耕亭寫懷》十首之三:閱耕亭,茆亭小小蓋初成,旋移新竹開三徑。水墨圍屏,鶯啼不住聲,蟬噪相呼應,鳥下無爭競。閑情稱我,我稱閑情。[1]745又如[北中呂•紅繡鞋]《竹亭寫懷》四首之四:谷雨深含雨意,名花正是花時。田園幽興兩相宜。布谷尋高樹,提壺揀嫩枝。引詩情多賴此。[1]763—764
再如[北雙調(diào)•清江引]《竹亭漫興》十二首之二:虛亭坐來天欲雨,閑看云生處。行蟻上階除,飛雁穿簾廡。芳辰幾何春又暮。[1]764由上面的曲作,我們不難體悟到楊廷和閑適、恬淡的心緒,也領(lǐng)略到了其曲作“詞俊而妥,調(diào)殊而諧”[1]770《樂府余音•小序》的風格特點。可是,通過對楊廷和全部散曲細加研讀、體悟之后,卻讓人感受到了一種不安、憂憤的情緒,如曲句“惠在農(nóng)桑,威在豺狼”中以“豺狼”為喻表達對言官的痛斥;“急流中扁舟歸去難”“盼歸期不知是何日也”“上竿時不知竿上難”對仕途中身不由己的感嘆;“利名途禍患端”“常記三緘口”“怕人情翻覆波瀾”對京師兒子安危的掛念;“消閑只用這些兒,此外別無事”“相當初年少時”“費盡了千般力”,“做少師,兼太師,都未宜”的無奈喟嘆等。顯然,楊廷和這些曲句中所表達出的思想情感與他多數(shù)散曲中顯現(xiàn)出的平靜、閑淡的情懷不相協(xié)調(diào)。于是,我們就產(chǎn)生了疑問,楊廷和的多數(shù)曲作中流露出的恬淡情懷是其真實的內(nèi)心書寫嗎?結(jié)合楊廷和的生平經(jīng)歷、致仕緣由、家庭變故等因素,我們認為楊廷和大量曲作中表現(xiàn)出的閑適情懷具有一定的表面性,選取抒發(fā)閑適情懷的題材進行創(chuàng)作,應是他借以舒泄內(nèi)心苦衷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大家知道,在明朝嘉靖初年的“大禮議”事件中,楊廷和因與明世宗意見相左,于嘉靖三年(1524)初被迫退出官場———致仕歸田。在楊志仁為楊廷和撰寫的《行狀》中說他歸田后:“絕口不及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端虹司馬(楊廷儀)兄弟,倡和為樂,泊如也。”①
結(jié)合楊廷和致仕前顯赫的宦途,以及面對強大皇權(quán)被迫辭官歸里的事實,我們有理由認為他歸田后不問時事、及時行樂的表現(xiàn)并不是其內(nèi)心的真實外顯,而是委曲求全的一種表現(xiàn),是“治療”其內(nèi)傷的安全方式,也是做給朝廷看的一種自保式的“表演”。美學家魯•阿恩海姆說:“將藝術(shù)作為一種治病救人的實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藝術(shù)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2]345這種認識,有助于我們了解楊廷和創(chuàng)作此類曲作的深層次原因和目的。像楊廷和曲作中“消閑只用這些兒,此外別無事”“有詩能自遣”“自吟自和,誰人閑似我,瀟灑,快活”等直言式訴說,除了在現(xiàn)實中確實能起到充實自我、消磨時光的作用外,以此轉(zhuǎn)移痛苦的內(nèi)心需求恐怕是他大量創(chuàng)作此類散曲的主要原因。如果僅言“石齋之曲,多為晚年歸休后自娛之作,非以曲應歌或以曲泄憤之篇”,[3]175恐未能體悟到楊廷和內(nèi)心的真正苦衷,未認識到他創(chuàng)作此類散曲的真實動機。我們試想嘉靖三年(1524)二月,因“大禮議”事件,楊廷和被迫致仕歸田,其長子楊慎也因此事在當年的七八月份間便踏上了流放云南永昌衛(wèi)所的征程,這對他的打擊能小嗎?由楊廷和的曲作《八月十六有懷寄京師兩兒》中對兩位在京為官兒子的擔憂看②,楊廷和當時的心情恐怕并不象他的曲中所展示的那樣悠閑自得。事實上,表面悠游的閑適生活并沒有真正緩解楊廷和長時間的壓抑、擔驚與煩悶,嘉靖五年(1526)五六月間他終于扛不住了,身染重病。后來,雖經(jīng)治愈,但緊接著嘉靖六年次子楊惇被“褫職為民”,對楊廷和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不久,他內(nèi)心預感“大禮議”之事對楊家的打擊遠沒結(jié)束的事情終于發(fā)生了:“(嘉靖)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為民。”[4]5039
應該說這對他更是致命的打擊。楊廷和為大明江山辛勞大半生,作為首輔大臣,還為迎立嘉靖即位穩(wěn)定大局,然而,最后卻被嘉靖帝定格在恥辱柱上,這讓他能心平如水嗎?嘉靖八年(1529)五月因幼子楊恒去世,慟悼過傷,臥床不起,終于是年六月二十一日撒手人寰。綜上,面對接二連三的家庭變故,對于久經(jīng)宦途、圓熟而執(zhí)著的楊廷和而言,他能真正保持著像曲作中所以表現(xiàn)出來的那樣灑脫與自適嗎?我們認為他越是在曲作中大寫閑適之趣,越是暗示出了他內(nèi)心無法解脫的苦悶與不安,他把散曲創(chuàng)作作為療傷的一種手段,可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最后,在打擊、擔憂、郁悶、恐懼中,楊廷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至于隆慶朝為他所作的“平反”也只能算是對死者在天之靈的一個告慰罷了,更是統(tǒng)治者收買人心所慣用的一種伎倆。由此,這也為我們說明了一個道理:作家內(nèi)心的真實情感與文學作品中所表達出的情感之間是存有一定距離的。與同時代的關(guān)中散曲家康海比,楊廷和之所以沒有像康海那樣把自己的憤懣與不滿通過散曲毫無遮攔地發(fā)泄出來,而是采取較為委婉的形式抒寫憂悶,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楊廷和曾官居一品已經(jīng)歷過仕途的輝煌,迫于皇權(quán)的壓力自己主動提出致仕請求,其心中的怨憤相對而言不是那么強烈,而康海正值壯年有為之時,卻被冠以“閹黨”之名罷官歸田,內(nèi)心有著強烈的冤屈、憤慨之情;二是,楊廷和所面對的是一位不惜殺生通過“正名”來確立其統(tǒng)治地位的新君———嘉靖帝,而康海罷官時的正德帝并無心思對付大臣的一些不敬行為,故楊廷和以謹小慎微的心態(tài)度過其致仕后的生活,康海則采取了狂放不羈的方式來度過自己的家居生活,現(xiàn)實、心態(tài)的不同影響到了他們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與風格;三是,楊廷和性格中有“柔順”的一面,而康海具有西北高原上的“粗豪”性情,個性差異使兩人的散曲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了一隱一顯的方式來消解內(nèi)心的郁悶。
二、流放“路上”的悲歌———楊慎離思曲中的心態(tài)解析
自幼警敏、聰穎的楊慎,以其廣博的才學一舉奪得正德六年(1511)殿試第一的好成績,被授予翰林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因諫阻武宗微行,不稱己意,隨以養(yǎng)疾告歸。世宗即位,充當經(jīng)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大禮議”事起,楊慎“偕學士豐熙等疏諫”,“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又“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糾眾伏哭”等舉動,使得嘉靖帝大為震怒。在遭受兩次廷杖之后,“(楊)慎、(王)元正、(劉)濟并謫戍……慎得云南永昌衛(wèi)。”[4]5082時年三十七歲。因“大禮議”事件被謫戍云南的重大變故,使楊慎“男子志四方,焉能守一丘。壯游輕萬里,逸跡凌九州”③的宏大志向瞬間化為了泡影,留給他的是屈辱、恐懼、孤獨、悲憤等無盡的肉體與精神折磨。然而,客觀上的人生悲劇在他主觀的堅毅斗爭中變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動力,他把“胸中實不知有幾斗熱血,眼中實不知有幾升熱淚”④化作篇篇佳作,時時沉吟著“久戍勞行惻,天高奈若何”“飛蓬無根株,飄飄隨風起。游子辭家鄉(xiāng),流落在萬里”⑤的傷感,吶喊出“他鄉(xiāng)雖好不如家”“故鄉(xiāng)咫尺是天涯”“千里有家歸未得,可憐長作滇南客”⑥的悲情。從歷史史實看,楊慎和他的內(nèi)心一直走在流放的路上,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終老戍地才得以安頓。正是基于這種流放的生活,在楊慎現(xiàn)存的242首(套)曲作中,有116首(套)曲作書寫了自己懷思、孤寂、愁怨的情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表達他對家鄉(xiāng)、親人思念之情的離思曲。長期流放“蠻荒之地,瘴癘之鄉(xiāng)”的悲慘遭際使他始終存有一種漂泊他鄉(xiāng)的客者心態(tài),朋友的接濟使他免受物質(zhì)上的困苦,與朋友酬唱、游賞也一時沖淡了他孤寂的情懷,可這些都難以消除其內(nèi)心的苦痛,多數(shù)時間還需他面對影單、燈孤的情景,忍受錐心、裂肺的思念之痛。當他把思痛化為文字時,便為我們譜寫出了真切動人的悲歌。如[南南呂•羅江怨]四首之一:空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guān)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jié),鴛鴦被冷雕鞍熱。[1]1397又[北雙調(diào)•對玉環(huán)帶過清江引]:長夜如年,孤燈相伴曉。海角飄零,風塵何日了。春夢不曾成,枕上聞啼鳥。青鏡慵看,朱顏容易老。東風寂寥南望杳,望斷星關(guān)道。心搖似旆旌,愁亂如煙草。百般不如歸去好。[1]1420長久的別離,使他不得不思念,而一年年的盼望變失望,又使他肝腸寸斷;長期的孤寂生活、飛蓬心態(tài)使他心緒難平,“百般不如歸去好”的呼喊是他內(nèi)心真實的表白。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謫戍者的悲苦心態(tài),體悟到了他真切的愿望———與家人的團圓。像這樣的曲句還有:“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xiāng)”“萬里客衣單”“可憐寒食清明,長是他鄉(xiāng)外井”“百般歸都歸到家居”“思鄉(xiāng)淚,遠戍人”“有信書難寄,無言淚暗流”等。這種對親情、家人的渴盼,表面看是對物質(zhì)的家和充滿倫理親情的家的渴求,從深層次講則是作者心中的一種精神需求,“是陷入困境下的個人對歸宿的詢問”[5]58。楊慎之所以在他的這類曲作中能表達出如此真切、動人的真情,除了謫戍離家的現(xiàn)實因素外,應與他歌謠“出自肺腑”、詩歌“質(zhì)任自然”⑦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有著一定的關(guān)系。在為楊慎這類作品中的真情感動的同時,我們覺得他的這類作品多停留在對具體情感的抒寫上,未能像蘇軾的此類作品上升到哲理層面達到對人生思考的目的。對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謫戍云南之后,楊慎愛讀老莊之作,也曾有“丹心炯炯,一寸成灰……儒術(shù)于吾何有哉?”[6]37《[沁園春]己丑新正》的感嘆,可總體看來儒家用世思想仍是他思想的主導,從而束縛了其曲作在思想上的超越;又有,楊慎“不善談,對人言甚謇澀。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貴公子”[7]159的儒雅個性,與蘇軾的達觀、自放有所不同;還有,北宋相對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文化繁榮與理學興盛的社會氛圍以及廣泛的興趣與愛好,使宋朝的士夫文人即使被貶官謫居,也樂于尋找超越苦悶、獲得適意的精神旨趣,已為明代士夫文人生活的社會環(huán)境和精神追求所不能比。當然,散曲文體的特點與作者的文學觀也應是影響這一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重要因素。
三、獨守者的思怨———黃娥相思曲中的心態(tài)解析
作為楊慎繼室,黃娥自幼聰慧,“博通經(jīng)史,能詩文,善書札”,[6]439被譽為蜀中才女。嫁于狀元楊慎,一時成為美談,由黃娥“萬點落霞明照眼,彩衣金屋正相宜”[6]431《庭榴》高興情愫的流露可見其婚后生活的幸福美滿。可惜這一幸福的時光太過短暫,自正德十四年(1519)黃娥嫁入楊門,⑧至嘉靖三年(1524)楊慎因“大禮議”事件被流放滇南,兩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僅有六個年頭。在楊慎流放云南的三十多年里,嘉靖五年(1526)楊慎回鄉(xiāng)看望病重的父親,黃娥曾與楊慎一同前往云南(嘉靖五年七月),嘉靖八年(1529)六月楊廷和去世,她便隨楊慎返回新都,主持家務,自此二人再也沒有長時間團聚過,即使楊慎偶爾回到新都,也只是短暫的相聚。這種分多聚少、天各一方的境況,加之女性相對狹窄的視野、細膩的心思,使黃娥散曲中更多地表現(xiàn)出的是一種痛苦、細婉的寄思情懷。據(jù)《全明散曲》計,在黃娥現(xiàn)存的63首小令、6套套曲中,有66首(套)是書寫寄思、幽怨情懷的。其中,或直抒會少離多的現(xiàn)實,或直繪影只形單、獨枕孤眠的情形,或抒發(fā)恨滿懷、寸腸斷的心情等。與男性曲家借女性口吻代言的曲作相比,黃娥的這類曲作取消了作者與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距離,使作品中抒發(fā)的情感更為真切,更具穿透力。如[北雙調(diào)•卷簾雁兒落]:難離別,情萬千。眠孤枕,愁人伴。閑庭小院深,關(guān)河傳信遠。魚和雁天南,看明月中腸斷。[1]1757又[南中呂•駐云飛]《足古詩四首》之三:暗想嬌羞,往事牽情不自由。帳薄燈光透,寒峭花枝瘦。休,一日比三秋,人在心頭。兩字相思,鎖定雙眉皺。殘夢關(guān)心懶下樓。[1]1747在這里,黃娥把長期的孤獨、苦悶、渴盼與次次的失望、不斷的哀嘆化作粒粒文字,直寫自己的離思、孤寂之苦。人常言:人生最苦是離別。大凡有過長期離別經(jīng)歷的人,讀到此類曲作都會為之動容心傷的,更何況黃娥與丈夫離別長達三十多年之久!這些看似平常的話語,卻是他悲苦情懷的一種具體外化,是用血淚凝成的不幸的人生悲歌。又如“分散西東,會少離多,天也將人弄”;“無福也難消,淚染紅桃。欲寄多情,魚雁何時到”;“萬水千山夢,三更半夜心。獨枕孤眠分,這愁懷那人爭信”;“夢峽啼湘,千古多情兩斷腸。眼穿心碎,影只形單,意慘神傷”等曲句,無不是她血淚的訴說。再有,一些書寫黃娥幽怨、恨愁情懷的相思曲,頗能睹見其愛之深、恨之痛的情愫,如[北雙調(diào)•折桂令]二首之一:寄與他三負心那個喬人,不念我病榻連宵,不念我瘴海愁春。不念我剩枕閑衾,不念我亂山空館,不念我寡宿孤辰。茶不茶飯不飯全無風韻,死不死活不活有甚精神。阻隔音塵,那個緣因?好事多磨,天也生嗔。[1]1754又如[南仙呂•皂羅袍]:為相思瘦損卿卿,守空房細數(shù)長更。梧桐金井葉兒零,愁人又遇凄涼景。錦衾獨旦,銀燈半明,紗窗人靜。羅幃夢驚,你成雙丟得咱孤另。[1]1756—1757
長期的渴盼是黃娥的精神支柱,可一次次的失望使她的內(nèi)心倍受折磨,如果說這還可以在忍耐、期盼中承受的話,那么丈夫?qū)矍榈谋撑褎t是任何一位女性都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即使在允許擁有三妻四妾的封建社會也是如此。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們可以用各種制度、學說、手段構(gòu)建、維護一個男權(quán)社會,進而把女性變?yōu)槟袡?quán)社會的附屬,但它沒有辦法改變女性要求男性從一而終的心里訴求。雖然這種渴求對于古代女性來說簡直是一種“奢望”,更多的是在忍受中喪失自己的權(quán)利和尊嚴,可不同歷史時期總會有一些女子做出或激烈、或委曲的反抗舉動。上面所舉兩曲,則是黃娥聞知楊慎納妾后,用自己的筆對楊慎這種“背叛”行為的控訴⑨。楊慎的兩次納妾對黃娥刺激強烈,是對其尊嚴的一種冒犯,也是對其長年苦守的兩次否定。因此,她在[折桂令]中連用五個排比句喊出了自己內(nèi)心的壓抑、凄苦與痛恨,[皂羅袍]中也發(fā)出了“你成雙丟得咱孤另”的牢騷,表現(xiàn)出了與她的其他相思曲不同的味道,由此可以感受黃娥的激憤情懷。楊慎、黃娥離思曲中表達出的情感深、痛、切,可謂是真實感人、令人動容。不過,楊慎以罪人的身份流放云南,是一位身在異鄉(xiāng)的客者,加之他特殊的家世、才學,使他交結(jié)了許多朋友,因此也就使他離思曲中的思念對象相對寬泛,除了對家園、親人的思念外,也含有對朋友的別思。相較于楊慎,黃娥長時間生活于四川新都家中,交往范圍相對狹窄,離家、思家的情愫較弱,思念的對象也較為單一,因此在她的這類曲作中不存在對家鄉(xiāng)、對朋友的思念,僅是表達了對丈夫楊慎強烈的渴盼、思念之情,以及得知楊慎納妾后由思轉(zhuǎn)怨的情感。綜之,楊廷和以創(chuàng)作閑適曲為主的特點代表了致仕曲家的一種創(chuàng)作傾向,但在這類曲作背后蘊有一種苦悶、無奈、不安的心緒卻不同于他人;獨特的生活經(jīng)歷使楊慎在離思曲中表達出了真切、感人的效果,黃娥以女性獨有的個性與筆法表達出的思念與幽怨之情也頗具“杜鵑啼血”之效,為明代其他散曲家所不及,都值得進一步研讀。
參考文獻:
[1]謝伯陽.全明散曲[M].濟南:齊魯書社,1994.
[2][美]魯•阿恩海姆.作為治療手段的藝術(shù)[M].郭小平,翟燦,譯.藝術(shù)心理學新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3]趙義山.明清散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清]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6]王文才.楊慎詞曲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7][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M].北京:中華書局,1959.
作者:劉英波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