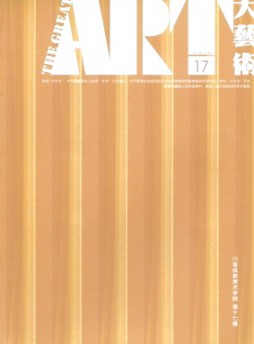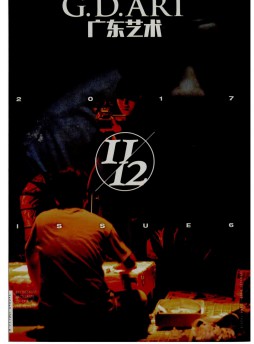藝術視角下文學作品的價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藝術視角下文學作品的價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20世紀50年代全國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早已是年長一代遙遠的記憶。同樣,在我們談論它的當下,這一運動也已成了幾十年前的歷史。然而,在作家寫作《山鄉巨變》、《三里灣》和《創業史》這三部小說的當時,它卻是明明白白的社會“現實”。周立波、趙樹理和柳青并不是在寫歷史題材的小說,而是在反映當時的現實生活。這三部長篇小說和文學史上別的歷史小說迥然有別,這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的十分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以“現實”的尺度來要求它們,來觀察作家的藝術視角,審察他們當時的藝術眼光,即他們審察生活和表現生活的角度。具體說來,這眼光和審察角度即藝術視角,在這三部作品的生活形態和人物情態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一)生活形態:政治形態、日常生活形態、文化形態《山鄉巨變》描寫的是湖南清溪鄉從1955年冬建立初級社到1956年高級社成立的歷程。小說一開始,寫縣團委副書記鄧秀梅在進清溪鄉的半路上,遇見了老倌子亭面糊,他一聽到辦社的風聲,害怕自己的財產要歸公,便馬上砍下自家的楠竹到街上去賣。之后,隨著合作社運動的開展和深入,那位勤勤懇懇、一心為公的貧農黨員劉雨生,因為無暇顧及家務,他的妻子受到富裕中農哥哥的挑唆,便以離婚來要挾他,以圖打擊他辦社的積極性。但他寧可離婚,仍然積極工作。之后,貧農陳先晉家里“先進和落后,擺了一個插花的陣勢”,時的貧農亭面糊也產生了不安和苦惱。而破壞分子龔子元則勾結富裕中農張桂秋,進行騷擾和搗亂。當然,在鄧秀梅、劉雨生等人的努力下,農業合作化運動最終獲得了勝利。在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完全展現了農村各個階級的本性:貧下中農雖有不安,但還支持;富裕中農搖擺不定;地主富農破壞反抗。這完全符合當時的階級分析。各個階級都是在按各自的階級本性行事。亭面糊、陳先晉等人的自私雖然有文化的意味,但都歸向于階級性。因為作為個體勞動者的貧農,自私也是其階級性的體現。作品中的生活就是階級生活,生活里只有政治,呈現的只是政治的形態。這是以階級的政治眼光審察出來的政治化的生活,也是作品中表現出來的生活面貌和情態,并不是生活中原有的復雜多樣的形態。《三里灣》反映的是山西的一個“模范村”三里灣的生活。對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描寫,作品注重從農民的日常生活著筆,它寫了村里四個不同的家庭:合作化帶頭人、支書王金生一家;熱衷于個人發家致富的村長、黨員范登高一家;政治上十分保守、糊涂,但在為自己謀取私利時卻十分精明的富裕中農“糊涂涂”馬多壽一家;“兩只腳踏在兩條路上”的黨員袁天成一家。看看這些人物的品德、行為以及他們的身份,我們就可以感受到,趙樹理不是以政治的眼光來審察生活和判定生活中的階級陣線的。特別是因為“富農在農村中的壞作用”,他“自己見到的不具體”,在作品中也就“根本沒有提”①,這是不完全符合當時的階級分析的。有論者稱:“任何一個作家,包括那些光照千秋的大師和巨匠,都不可能超離他所生存的那個具體的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局限。”②但他面對生活,以生活的眼光來審察生活,就發現了當時和別人眼中、作品中不一樣的生活情態。生活中有政治,但不全是政治,政治之外還有別的。他是以日常生活的眼光,即生活的視角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的。《創業史》描寫的是20世紀50年代關中地區蛤蟆灘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它一開始并沒有進入合作化的“正題”,而是在“題敘”中介紹梁三老漢一家三代創家立業的悲慘歷史。這既表明“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走黨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農民才會有自己的光明前途”③,同時也顯示出,并且強調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個人發家致富觀念。之后,作品圍繞著梁生寶互助組的鞏固和發展,直至燈塔社的建立,寫出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艱難歷程。其間,寫出富農姚世杰反對合作社,富裕中農郭世富、郭二老漢一家、梁大老漢和他的兒子梁生祿一家對入社都不樂意,農會主任郭振山也不愿入社,而梁三老漢最初同樣是一千個一萬個不情愿。這些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從個人發家致富的觀念出發,來決定自己對合作社的態度。最后,梁生寶互助組在黨的領導下,依靠、團結、教育農民群眾,取得了最后的勝利。整個故事就是中國農民如何克服個人發家致富觀念的故事。作品中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勝利”,既是政治上的“勝利”,同時也是共同富裕文化觀念的“勝利”,即文化上的“勝利”。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勝利顯然是極“左”路線所為,雖然柳青在當時沒有看清這一點,但他卻是超越了政治,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勝利”。由此可見,他并不是以單純的政治眼光來審察農業合作化運動,而是從文化的視角來審察和表現這一運動的。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現出文化觀念上的角力。因而,作品中的生活形態,是包含著政治內容的文化形態。
(二)人物情態:政治人物、生活人物、文化人物《山鄉巨變》中的女主人公鄧秀梅,有人說是作家“從實際生活出發”①去描寫的人物。但其實,她并不是實際生活中的人物,因為在她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熱愛勞動,熱愛群眾,政治上很敏銳,政策觀念強”以及青年人的“朝氣蓬勃,熱情樂觀”和作為女性的“綿密細致、溫柔和氣”。②這些都是完全正面的品質,是從政治上去評判的。劉雨生被說成是“描繪得成功的”“生動形象”,但他身上所表現出來的也只是“任勞任怨、大公無私、自奉儉約”,以及“樸實謙遜、公道能干”等政治品質。③作品中被認為“寫得很出色”的人物亭面糊和陳先晉,前者作為貧農,卻又怕別人瞧不起,中翻了身,擁護黨和,但謠言一來,就昏頭轉向,聽到合作化的號召,連忙要二崽寫入社申請,但又在破壞分子龔子元家貪杯誤事”④;后者“沉默寡言,思想保守,恪守祖傳的生活道路和處世哲學”⑤。應該說,這兩個人物是有些文化色調的,但作品只從政治角度即從他對合作社的態度去表現,把文化色調融入政治色彩,濃重的政治色彩把文化色調掩蓋了。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指出,一些作品“把個別的人只看成階級的代表”,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比如“工人不獨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單位,有其本階級的印記,而且還是一個人”⑥。而《山鄉巨變》基本上就是把人當成“階級的代表”來寫的。所以,總觀《山鄉巨變》的人物,便會覺得他們基本上還是政治人物,或者說是政治色彩濃厚的人物。《三里灣》中把黨員、村長范登高寫成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代表人物,這是來自生活的,因為“合作化運動中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⑦來。“糊涂涂”馬多壽政治上十分保守、糊涂,但在為自己謀取私利時卻十分精明,他利用范登高的錯誤頑固地阻撓合作社的擴建,利用互助組的勞力為自己種田。同時,他明明是一家之主,但卻愿意背負“怕老婆”的名聲,為的是不愿在外擔當責任,這里足見他不但自私而且奸狡。作品中的人物是有個性的人物,其性格之中,既有政治又不全是政治,是中國那段生活的原生態。這是生活化的人物,是生活中的人。《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這個老貧農,經歷了三起三落創家立業的辛酸史,“他善良,好心眼,又有些倔強。他樸實,熱愛土地,愿意通過自己誠實的勞作,使自己的家道興旺起來,有自己的耕地,自己的耕畜,自己的瓦房院。他古板、正直、愛自己的家,疼孩子。但他也有農民的源于小農經濟的狹隘眼界”⑧,他是一個文化化的中國老一代農民的形象。另一個人物郭振山也是個貧農,他因在中有突出的表現,所以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他本來是帶梁生寶進黨的,但后來卻不被重用而受到冷落,他不服,所以和梁生寶產生了矛盾。在合作化問題上他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這個人物既有狹隘本性,又有妒忌心理,他“有能耐、有魄力、有智慧、會算計,是莊稼人家里的能人。他是共產黨政權的獲利者,入黨、當干部、分田地,屬于以后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⑨。這個人物既是政治人物,又是文化人物。至于梁生寶卻只是政治人物,作品突出的是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和熱愛,他“覺得只有這樣做,才活得帶勁兒”,認為“照黨的指示,給群眾辦事,受苦就是享樂”,這些都屬于政治思想品質,全是從政治著眼的。但從主要人物梁三老漢、郭振山看,《創業史》采用的主要還是文化視角。這三位作家都有長期創作小說的經歷,也有以創作配合政治運動的積極表現。結合這三部作品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周立波寫《山鄉巨變》時,和建國前寫《暴風驟雨》時一樣,采用的主要是政治視角;趙樹理寫《三里灣》時,和20世紀40年代初寫《小二黑結婚》等作品時一樣,采用的主要是生活視角;而柳青寫《創業史》時,卻和他1947年寫《種谷記》、1951年寫《銅墻鐵壁》時不同,不再采用政治視角而主要采用文化視角。這是他們小說創作的藝術視角的變化軌跡。
二、不同藝術視角產生的不同文學意義和價值
西方一位學者說,藝術(這里所說的“藝術”包括文學———筆者)身上的“藝術特質必須……從內容方面加以探討”⑩。而我國著名的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對此也十分認可。他說:“詩所寫的行動和思想感情可以美,即內容意義可以美。”①這就是說,無論從文學還是從美學上看,作品的思想內容都是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極為重要的方面。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主要也在思想內容上面。考察中外文學史可以發現,那些有成就的作家都是首先從思想內容著眼的。但是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思想內容又由什么來決定呢?這就是作家的藝術視角。藝術視角雖然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家個人。藝術視角是作家個人獨特的文化觀念、政治意識、審美理想、文學素養的體現,所以由他的藝術視角所觀察和所表現出來的生活,會有它獨特的模樣,作品也會因之而具有不同的意蘊。《山鄉巨變》由于基本上采用政治視角,所以它的內容基本上是政治內涵,雖然有亭面糊等人的某種文化意義,但突出的還是政治,所以作品還是顯出生活的平面化,缺乏深度和廣度。有人說它“反映出這場社會變革的廣泛性和深刻性”②,這只能是就政治而言,作品最大的意義也就在于對農業合作化作政治上的宣傳,即贊揚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偉大勝利。我們姑且撇開這一贊揚在政治上是否正確的問題不說,只就文學而言,這其實并非是文學的價值和意義。《三里灣》從生活出發,主要呈現的是生活化的情態,其中也有某些文化內涵,其思想意蘊要比《山鄉巨變》深厚。
有論者說它“顯示了趙樹理高漲的政治熱情與忠于現實生活的創作態度”③,這是事實,但說它“還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重要問題,如在合作化運動中應該重視技術革命,培養農業技術骨干;應該重視知識青年的作用,引導他們走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道路等,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顯示了作者思想的深邃”④,卻是牽強附會的。因為即使作品提出了這些問題,也與“思想意義”關系不大,這些問題還只屬于工作和技術層面,并不能顯示出“思想的深邃”,與文學的意義和價值關系不大。《創業史》則主要從文化著眼,展現的是文化心理,作品中的合作化運動發展史就是中國農民的心理變化史,它是20世紀50年代我國農民,甚至是全國人民的思想、文化面貌的寫照。當然,從今天的角度看,這種思想、文化面貌明顯的具有“左”的色彩,并不科學和客觀,但畢竟是那段歷史的縮影。可以說,《創業史》有歷史的深度,也有文化的廣度,其文化意義和價值比政治層面的《山鄉巨變》要厚重得多,也明顯地優于停留在生活層面的《三里灣》。
過去一些評論者在評述《創業史》的成就時,往往與政治掛鉤,比如說它“思想內容的深刻性,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首先,它在廣闊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生活的藝術畫面中,展示了中國農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的必然趨勢;其次,作者在對于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特點認識的基點上牢牢掌握了實現農業合作化的中心環節———‘多打糧食’;第三,作者在把握革命的不同性質和矛盾沖突的不同特點的基礎上,正確地反映和處理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民內部錯綜復雜的矛盾”⑤。這里所說的“深刻”,是政治認識上的深刻,不是文化意義上的深刻,而且還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之前帶有“左”的思想傾向的認識上的“深刻”。而在新世紀的2006年,一位論者說:“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國出現了成千上億的農民進城務工的歷史潮流。這股潮流不僅改變著農村的面貌,促進著農民社會身份的變化,而且成為國家發展的動力。當年的郭振山是最早感受到這一歷史趨勢必將出現的為數不多的農民智者之一。如果他生活在今天,就會成為一個出色的農民企業家”⑥。這就是說,《創業史》不但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過程,而且還預示了我國今后政治的發展方向。這就又拔高了作品的意義和價值,并不切合作品的實際。因為評論者只從政治著眼,對柳青作了誤認,即把作為作家的柳青看成了政治家,而且是難得的、十分高明的政治家。實際上,柳青并不一定有或者說十之八九都不會有這樣的政治預見。更重要的,是他并沒有想作什么政治預見。從作品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柳青雖然也看重政治,但更看重文化,否則他就不會一反常規采用文化視角了。筆者認為,作為評論者,也要從文化著眼看待《創業史》這部文化視角的作品,這樣,對它的認識和評價才會比較客觀。同時,筆者還認為,《創業史》的最大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它顯示出包括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內的任何政治變革,都不只是一場政治變革,而更是一場文化變革,即文化觀念的變革。不管這種變革科學與否,也不管這種變革是否具有進步意義,其深度都落實在文化上,而不是在政治上。
三、關于藝術視角的思考
(一)藝術視角與作品題材上面談到藝術視角對于作品思想意蘊的重要性,這表明題材雖然是重要的,但藝術視角更為重要。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題材相同的作品,但它們的意蘊和成就大相徑庭,這都是藝術視角不同的原因。反之,如果視角相同,則作品的面貌和水平則大體相同,比如同是以政治視角審察生活的《不能走那條路》就和《山鄉巨變》大同小異。這就提示創作者在創作時既要注重題材的選擇,更要有文化的眼光,不能以找到較新的題材為滿足。真正決定作品水平的,還是藝術的眼光,即視角的文化性。因為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即使寫政治也要以文化的眼光來看待它。馬爾庫塞說的“藝術的政治潛能在藝術本身之中”①,就是從文化著眼,把政治變為藝術,變為文化之意。世界上許多名著都寫政治,但都以文化眼光來看待政治,比如《水滸傳》、《三國演義》、《戰爭與和平》等等,它們給予人的感受不是政治上的誰勝誰負,而是文化的感悟和色彩。
(二)文化視角的個人性上面說到政治視角、生活視角的差別,同時也談到文化視角對文學創作來說是最為完美的視角。但這是否意味著文化視角就千篇一律呢?否。實際上,藝術視角也是千差萬別的。同樣是文化視角,還有個人不同的認識,不同的愿望、理想和追求。比如同是從文化的角度看待封建社會,《水滸傳》把目光對準封建統治者對農民政治和文化上的壓迫,看出了農民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反抗的必然性;《紅樓夢》則把目光對準封建禮教對人的摧殘,看出了封建社會包括政治和文化在內的沒落和必然崩毀的趨勢;《三國演義》則把目光對準封建軍閥之間的政治、文化混戰,看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文化發展趨勢。西方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把目光對準資產階級的發家途徑,通過老葛朗臺對女兒的態度,看出資產階級的殘忍和刻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則把目光對準資產階級的家庭生活,看出資產階級“不允許”女人“在家庭生活中有任何發言權”的文化觀念上的不平等關系”②。這些都能說明,文化視角具有鮮明的個人性。正是視角的個人性,造就了文學作品的獨特性。
(三)藝術視角的時代性與作家的“反叛”上面說過,藝術視角是由個人的思想意識和藝術素養所決定的,但同時也與時代的集體意識相關。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現代派,既是創作方法和創作流派,同時也是藝術視角的體現。同是這一“主義”的作家、藝術家,大都以同一或者相近的藝術視角(指視角的某一方向的共同性,實際上其中還有個人性)來看社會生活,這就是由時代的集體意識所操縱的結果。但是,每一時代又都有違反集體意識的人,這是對集體意識的反抗或者說是反叛。當然,這樣的人畢竟少而又少,藝術視角的時代性是一條基本的規律。比如:不但周立波會采用政治視角,趙樹理的視角中也缺少不了政治的成分,即使是柳青,雖然他整體上是采用文化視角,但其中同樣也有政治的因素。他們同是生活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同是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政治漩渦之中,特別是在工農兵文學的創作規范之下,如果不以政治的眼光看待農業合作化運動,不持贊頌的態度,是不被允許的。這是時代的局限,政治的局限。然而,像柳青,其作品總體的文化視角,實際上又是一種對時代的“反叛”。趙樹理也是如此,他的生活視角,就超出了政治的范圍。甚至周立波也有某種“反叛”的成分,因為《山鄉巨變》中到底還是有某些不完全屬于政治的因素。加拿大學者琳達•哈欽說過:“歷史指涉是當前的事”③,而加拿大的另一位學者萊思•芬得利,把這話解釋為“現時構成問題與歷史指涉造成的問題緊密相關”④。我們探討《山鄉巨變》、《三里灣》和《創業史》的藝術視角問題,是針對當今一些文學作品不是采用文化視角的情況來說的。應該說,當今單純采用政治視角的文學作品已經很少了,但也還是有。而所謂“純文學”并不是文化視角,而是“語言視角”。這既是對政治視角的反叛,也是對藝術視角的反叛。
作者:劉江單位: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科研處
- 上一篇:農村高中生文學閱讀水平思考范文
- 下一篇:古代文學作品中家長形象的評價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