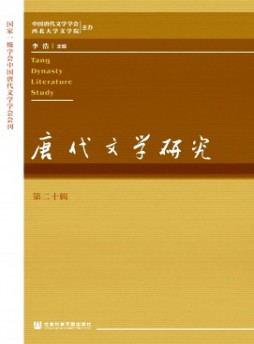唐代牧監(jiān)基層勞動者身份芻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唐代牧監(jiān)基層勞動者身份芻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農史雜志》2015年第四期
在唐前期的諸牧監(jiān)和馬坊里,有大量的畜群,包括馬、牛、駝、騾、驢、羊等,唐朝政府詳細設置了一系列的職務,從事它們的飼養(yǎng)工作。其中,最基層的職務就是牧長和牧子。對于這兩個職務,前輩學者的論著多有涉及。專著如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1,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2,乜小紅《唐五代畜牧經(jīng)濟研究》3等,單篇論文如陸離《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的官府牧人》4等。這些論著有的對牧長與牧子一筆帶過,有的論述較詳,但是均沒有從法令制度的角度對這些職務的內涵進行嚴格的辨析。同時還遺留了不少問題,如牧長與群頭的關系、牧子的身份特征等。有的研究結論尚待商榷,如牧子的服役形式、牧子的待遇等。因而筆者不揣淺陋,依據(jù)《天圣令》中的新資料,對以上問題進行重新的梳理,以期廓清學界論著中一些習而不察的說法,供方家批評指正。
一、牧長與群頭的關系
對于牧長的設置,《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諸牧監(jiān)”條云:凡馬、牛之群以百二十,駝、騾、驢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長、牧尉。1《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太仆寺諸牧監(jiān)”條云:凡馬之群,有牧長、尉。2《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太仆寺諸牧監(jiān)”條云:《新唐書》卷五十《兵志》云:根據(jù)前三條史料可知,牧監(jiān)中一群的長官為牧長,十五長置一尉。但《新唐書•兵志》中除了“牧長”以外,還有“群頭”一職。顧名思義“,群頭”應是“一群之頭”,但這樣一來它就與牧長的管轄范圍重復,《新唐書》將其與牧長并舉,實在令人費解。故唐長孺在《唐書兵志箋正》中說“:《兵志》之群頭疑即牧長,又所云‘群置長一人’即牧長也‘,十五長置尉一人’即牧尉也。《新書》以省字自詡,而重復如此,可怪。”5唐先生的觀點很有啟發(fā)性,但《新唐書》明言“牧尉、排馬、牧長、群頭”云云,可見牧長、群頭應非同一職務,懷疑群頭即牧長似乎理由不足。又,乜小紅在《唐五代畜牧經(jīng)濟研究》中,一則認為唐代的“牧長即是群頭,群頭直接管理畜群,其下還有牧子”6;二則說,敦煌文書中有“駝官”、“知駝官”、“知馬官”、“牧牛人”、“牧羊人”等稱謂,這些人“均可稱為‘牧子’……他們都屬于群頭,是監(jiān)牧系統(tǒng)下屬最基層管理牲畜的‘官’員”7。也就是說,牧子是一個總稱“,屬于群頭”。所以她總結道,在唐末五代歸義軍時期“,牧子即是群頭,也就是牧長……似乎牧子與牧長這兩種稱號便合二為一了”8。
對于這樣的分歧,筆者認為,唐代的群頭既不是牧長,也不是牧子。首先,群頭不可能是牧子,即便在宋代人的其他表述中,二者也是分開的。《天圣令•廄牧令》宋1條云可見直到北宋時期,牧子與群頭仍是兩個不同的身份,且群頭是牧子的上級。其次,充當群頭之人的身份與牧長有很大區(qū)別。筆者在此作一點考察。《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一》“都官郎中員外郎”條云:據(jù)此,唐代的樂工、獸醫(yī)、騙馬、調馬、群頭和栽接之人皆是從官戶奴中選拔的。其中與畜牧業(yè)相關的,有獸醫(yī)、騙馬、調馬和群頭,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人。那么,如果要想知道群頭的身份地位,只要先了解與其處于同一等級的獸醫(yī)、調馬等人的相關情況就行了。《天圣令•廄牧令》唐3條云:根據(jù)令文,系飼中的獸醫(yī),是從普通百姓和軍人中選拔的,他們要“分番上下”。但是對于監(jiān)牧而言,并沒有專業(yè)獸醫(yī)前去服役,而是指派系飼中的獸醫(yī)輪番到牧所,把相關知識教授給監(jiān)牧中的戶、奴中男,然后由這些人負責監(jiān)牧中的牲畜就醫(yī)事務。換言之,監(jiān)牧中做獸醫(yī)的人出身非常低,是從官戶奴中選拔的。那么群頭的身份地位亦可想其仿佛。又,《唐律疏議》引《太仆式》云:按,唐代諸牧中的馬以一百二十匹為一群,設牧長一人,十五群設一牧尉。以每尉配調習馬人十名計算,每人負責調習的馬數(shù)是一百八十匹。但他們分為五番上下,每次共同調習的人數(shù)就是兩人。由此可知,從官戶、奴中選拔出來的群頭也應是分番上下的。而牧長則不會分番上任。另外,《天圣令•廄牧令》唐1條云:群頭既然也是從戶奴中選出的,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兩個充當牧子的戶奴中的一個,選拔出來后作為牧長的副手4。而牧長是由什么樣的人充任的呢,《天圣令•廄牧令》唐2條云:可見,充當牧長之人的身份地位遠高于群頭。所以除了《新唐書》外,其他唐代文獻中均未提及群頭,可能正是因為群頭的地位不高而將其忽略。隨著時間的推移,該職位發(fā)生了變化,宋代則以群頭代替牧長。
二、牧子的服役形式與待遇
馬俊民、王世平認為“:《六典》中把飼丁和牧人并列,除了表明二者有相同點,即身份地位一樣外,也表明二者有不同點,即勞役形式不同。《六典》對上番者稱丁,不上番者不稱丁,表明‘丁’這一稱謂同番上制、也就是征發(fā)制的聯(lián)系。牧人們‘長上專當’,并且是通過雇傭而不是征發(fā)進入牧場,所以就不稱丁了。”1他們從力役征發(fā)形式的角度比較了系飼中的飼丁與牧監(jiān)中牧子的區(qū)別,同時認為,牧子(包括丁和官戶、奴)與監(jiān)牧之間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這種觀點被乜小紅承襲,說“:牧子受雇于官府,給以傭值……關于雇價,由于文書中無明確記載,不敢臆測。至于傭食,即口糧一項,一般按月供給。”2但是筆者認為,唐代牧監(jiān)中的“牧子”也就是馬、王二先生所說的“牧人”,并不是通過雇傭形式進入牧場的。其實,牧子對于監(jiān)牧來說,屬于力役征發(fā)的范疇。在《天圣令》發(fā)現(xiàn)以前,研究監(jiān)牧中勞動者身份的依據(jù)主要是《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諸牧監(jiān)”條:但其中并無《天圣令•廄牧令》唐1條中“別配牧子四人(二以丁充,二以戶奴充)”的規(guī)定,故此,前賢并未辨析牧子的來源問題。根據(jù)前文的論述可知,充當牧子的人一共有丁、官戶、官奴三種身份,這就需要區(qū)別對待。《天圣令•廄牧令》唐8條說:對于牧子而言,既有“長上專當者”,那么就會有非“長上專當”者。對照牧子的身份來源,可知“長上專當”者只有官奴。前揭書所說“牧人們長上專當”是不確切的,因為并非所有的牧人都長役無番,有的人比如丁、官戶就是分番服役的。這樣一來“,牧子受雇于官府,給以傭值”的觀點也就不攻自破了。對于牧子在牧監(jiān)中的生活情況,只能從一些殘存的文書中窺探只鱗片爪。陸離認為,歸義軍時期的“牧子身份自由,為官府從事辛苦的勞作,可以從主管部門領取相應的報酬”。
由上文可知,這個結論并不適合唐代的情況,同時,即便是歸義軍時期,牧子的生活待遇情況仍值得繼續(xù)考察。與陸先生相似,乜小紅在《唐五代畜牧經(jīng)濟研究》中,也引用P.4525(8)號文書《壬申年(972或912)官布籍》第7至15行,認為牧子擁有土地,且不用繳納官布,從而得出結論云:“牧子的身份不僅是自由的,而且在享有少量土地耕作的同時,還享受著政府的免稅優(yōu)待。”5為此,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她所引的這份文書。按,這份“官布籍”是記錄敦煌鄉(xiāng)課戶向政府繳納布匹的籍帳,其中的“布”與P.3236號《敦煌鄉(xiāng)官布籍》2及ДХ1405、1406號《官布籍》3中的“布”一樣,都是政府向丁男征收的稅。但是,在繳納布匹時,由于各戶所有的土地大小不一,有的所需繳納量不足一匹布,所以就由多戶人家湊在一起,共同繳納整數(shù)的布匹。這就是文書中所說的“計地貳頃五十畝,共布壹疋”及“計地貳頃五十二畝半,共布壹疋”的用意。在合在一起時,有的戶主的名字要被寫在布匹的兩頭上,稱為“布頭”。李錦繡復原唐《賦役令》第2條云:這就是上引文書中書寫“布頭某某”的由來。但是,有的戶主并不需要與他人一起湊成一匹布,其自身應繳的數(shù)量就可能遠遠超過了一匹之數(shù)。如ДХ1405、1406號文書第三行中說:“承宗郎君地叁頃,造布壹匹。”承宗郎君一人有地三頃,他獨自就須造布一匹,無須與他人合成。由此可知,記錄官布的格式并不是整齊劃一的:一是擁有土地的數(shù)量與繳納布匹的比例有所變動,出現(xiàn)2.5∶1和3∶1兩種情況,這可能與不同時期的政令變化有關;二是根據(jù)土地所有者土地數(shù)量的不同,該與他人合成的則合成,不須合成的則均獨自承擔。茍明于此,我們再來審視P.4525(8)號文書的第11-15行:表面上看,這幾行文書只是羅列了土地的數(shù)量,并未表露出這些“都頭及音聲、牧子、打窟、吹角”等人所需繳納布匹的數(shù)量。但既然這些記錄出現(xiàn)于《官布籍》中,他們必定都是要繳納布匹的,此處絕對不會只記錄他們的土地數(shù)目,好像是專門為了給他們分配土地一樣。另一方面,15行后所缺的文字估計是“共布若干匹”,這批人的土地總數(shù)雖然超過了通常的“貳頃伍拾畝”或者“叁頃”,但必定會繳納更多的布匹,就像承宗郎君一人就須繳納一匹布一樣。所以,從這件文書得不出牧子不用繳納地稅的結論。雖然這份文書是五代歸義軍時期的籍帳,不能直接拿來解釋《天圣令》的相關規(guī)定。但是,如果唐代牧子是有土地的,那么他們依然要向政府繳納租調。另外,根據(jù)《廄牧令》的規(guī)定,唐代的牧子分為兩類,一是由丁男充當?shù)哪磷樱皇怯蓱簟⑴洚數(shù)哪磷印τ谇罢叨裕鸵凑斩∧械臉藴适谑芡恋兀U納租課。另外,乜小紅論述牧子口糧的史料依據(jù)亦值得商榷。她認為,在敦煌文書中,有關于支給牧人糧食的記載。如S.6185號文書《公元十世紀歸義軍衙內破用粗面歷》云:其中第2行出現(xiàn)了“牧牛人”,第6行出現(xiàn)了“牧羊廝兒”,大概因此乜先生就將其作為牧子口糧的史料依據(jù)。但這份文書中,還出現(xiàn)了“拽鋸人”、“拔草渠頭”“、薅園人夫”“、托壁匠”等各色雜役,他們均應是所謂“歸義軍衙內”的服役人員。那么,“牧牛人”、“牧羊廝兒”就不是專職在監(jiān)牧上服役的牧子。所以,不能用這份文書來討論監(jiān)牧中牧子的待遇問題,此其一。其二,文書中所說給各色人等支取粗面,實際上是給他們的口糧。在歸義軍時期,這些人可能是受雇傭而來從事勞動的,但即便如此,口糧以外估計還會有其他補償,這些粗面也不會是整個雇價。我們不能就此認為整個唐代監(jiān)牧中的牧子都是被雇傭而進入牧場的。其實,在監(jiān)牧中服役的官戶、官奴是要享受一定的待遇的,具體情況可以從《天圣令》中窺見一斑。《天圣令•田令》唐29條云:由本條可知,官戶、官奴雖無永業(yè)田,但普通的官戶基本上能受四十畝口分田,在牧的官戶、官奴可受十畝口分田。這就是他們在牧場上勞動時口糧的來源。《倉庫令》唐8條云:諸官奴婢皆給公糧。其官戶上番充役者亦如之。并季別一給,有剩隨季折。除了口分田,官戶在上番之日,是要給公糧的,而官奴婢由于長役無番,則要長期給公糧。又《廄牧令》唐16條云:諸官戶、奴充牧子,在牧十年,頻得賞者,放免為良,仍充牧戶。這條令文規(guī)定了官戶、官奴擺脫賤民身份、轉換為良人的途徑,即在監(jiān)牧十年,多次得到賞賜的,就可以跨越雜戶這一等級,直接變?yōu)榱既恕5既司褪恰岸 保麄円廊灰粼诒O(jiān)牧中,即所謂“仍充牧戶”。而要“得賞”,是與監(jiān)牧中牲畜繁殖數(shù)量增長的情況緊密相連的。《天圣令•廄牧令》唐8條即是關于這種賞罰的詳細規(guī)定:另外,在牧的牧子可能還會得到一些胡餅、酒的賞賜1。但唐10條云:可見,如果在牧場上走失牲畜,還要懲罰牧子,而無財?shù)墓賾簟⑴珓t要受到杖罰,這說明他們的地位依然是很低的。
三、牧子的身份及賤民問題
唐代監(jiān)牧中牲畜的飼養(yǎng),是由牧子來具體執(zhí)行的。由前引《天圣令•廄牧令》唐1條可知,每群共有牧子四人,由兩個丁、兩個戶奴充當,這是《天圣令》給我們的新的啟示。其中,丁即丁男,易于理解。戶奴,則指官戶、官奴2,屬于唐代的賤民階層。《廄牧令》中有五條令文涉及到戶奴,但在其中的唐1、3、10、19條中,均是直接稱“戶、奴”,唯獨唐16條作“官戶、奴”。筆者認為,令文中的戶奴乃是官戶奴的簡稱。《新唐書》稱:這里的“官戶奴婢”實際上就是“官戶”與“官奴婢”,其中“官奴婢”又包括“官奴”和“官婢”兩個群體。換言之,在說“官奴婢”的同時,其實已經(jīng)包括了“官奴”在內。那么,上面引文中的“官戶奴婢”在后文中即被直接稱為“戶奴婢”,可證戶奴是官戶奴的簡稱。同樣的例子還見《天圣令•雜令》,該令唐22條云:令文先說“官戶、奴婢”,后說“戶奴婢”,點校者黃正建認為后者缺了一個“官”字5,其實這里應是一種省稱。唐代的官戶奴婢受刑部的都官曹管轄,而主要放遣于司農寺1。《唐六典》云“:凡諸行宮與監(jiān)、牧及諸王、公主應給者,則割司農之戶以配。”2司農寺所轄的官戶奴婢,出路之一就是被分配到監(jiān)牧之中,亦可與《天圣令•廄牧令》相互印證3。牧子的出身,與唐代的賤民制度有關,對此問題,學術界雖已基本達成共識,但仍有遺留問題。比如日本學者榎本淳一提出了一則說法,涉及到唐代賤民的轉化問題,筆者認為此說值得商榷。如果搞清了唐代賤民的階層狀況,這樣就更利于了解牧子這類人的真實一面了。唐代的賤民,基本上都是由犯重罪之人的后代或家屬沒官之后形成的。關于這一階層,前賢已做過很多研究4。這里不再贅述。所可論者,是諸史料之間尚存矛盾之處,影響了對相關制度以及法令的認識,需要將其進一步廓清。
《唐六典》云:按,武英殿本《唐會要》卷八六《奴婢》6及《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志二》“刑部都官郎中員外郎”條7與《唐六典》之說法完全一致。這三則資料表明了官奴婢、番戶、雜戶與良人之間的關系,從低到高是官奴婢→番戶→雜戶→良人。一般認為,番戶又稱官戶。《新唐書》則是另一種說法:“凡反逆相坐,沒其家配官曹,長役為官奴婢。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為雜戶,亦曰官戶,二歲五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為良人。”8其將雜戶稱為官戶,與前三種史料不同9,但與南宋費袞《梁溪漫志》卷九“官戶雜戶”條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此,官戶就是番戶與雜戶的合稱,而不再僅僅是番戶的代稱。榎本淳一對《梁溪漫志》這條史料進行研究,認為它與靜嘉堂文庫所藏抄本《唐會要》卷八六《奴婢》的說法一致,所以在官戶、番戶與雜戶的關系上,應以它們的說法為準,官戶是番戶和雜戶的總稱。但同時,他并沒有因此認為其他史書的記載就是錯誤的,而是認為上引《唐六典》中的說法自成體例,即便《梁溪漫志》等書中的記載如彼,亦不影響《唐六典》和《舊唐書》文字的正確性。這樣一來,《唐六典》、《舊唐書》所記載的制度與其他諸書出現(xiàn)差異的根本原因就體現(xiàn)為唐代不同時期的國家制度存在差異。他從而認為《新唐書》和《唐會要》中的記錄很可能是基于貞觀令,《唐六典》則是“基于開元七年令之物”。
筆者認為榎本淳一的論證和結論值得商榷。首先看一下《梁溪漫志》的這段材料。這是費袞為了解釋“官戶、雜戶、良人”三個名詞的含義而寫的。其中“按唐制”之后至“蓋本于此”之前,顯系其抄撮唐代文獻而進行的引證。這就不能排除書寫錯誤的可能性。另外,既然他明言“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那么也就是說,至南宋時仍存在這三種叫法,只是人們“罕知其故”,但官戶、雜戶、良人這三個人群的排列次序還是盡人皆知的。所以,即便真如費袞所寫的那樣,官戶包括番戶和雜戶,當時也不可能再有官戶與雜戶、良人并列之說了。故《梁溪漫志》的這段材料是自相矛盾的。茍明于此,這段材料就不足以推翻通行本《唐六典》、《唐會要》及《舊唐書》的說法了。其次,榎本淳一認為“官戶=番戶”(《唐六典》說)是開元年間的制度,而永徽年間的規(guī)定亦是如此,故只有把“官戶=番戶+雜戶”的規(guī)定提前到貞觀年間。這實際上是一種臆測,是一種排除法,沒有正面的證據(jù)。因為并無明確的資料證明貞觀年間有此制度。所以,如果筆者上面的反駁意見成立的話,那么他的這一推論的前提就是子虛烏有,遑論其考證其存在的時間。總之,把“官戶包含番戶和雜戶”的規(guī)定追溯到永徽以前,將其定為是貞觀年間的制度,十分欠妥。關于唐代賤民等級的轉化問題,還有一樁公案。《舊唐書》卷一八八《裴子余傳》云:從裴子余口中可知,在景龍年間,官戶的級別很低,需要“承恩”才能變?yōu)榉瑧簟5徽摴賾舻降资菍V阜瑧暨€是包括番戶和雜戶,都與此條記載相矛盾。對于這一矛盾,張澤咸解釋說:“此事發(fā)生在《唐六典》編撰前20多年,大概是玄宗開元以前,官戶地位比番戶低,由番戶轉為官戶乃是抑之為賤。”
另外,可能還有兩種原因,一是文獻中所謂“隋代蕃戶”其實質即是唐代的“雜戶”,所以比官戶的等級要高;二是趙履溫奏沒隋代蕃戶為官戶奴婢這一事件,在《新唐書》或《唐會要》中均被記載成沒為“奴婢”或“官奴婢”,那么“子余以為官戶承恩”很可能應為“子余以為官奴承恩”之誤。這樣一來,裴子余的說法就順理成章了。或少加銅、鋅等重金屬元素的飼料,探討各種妨礙牲畜糞便肥料利用的添加劑替代物等。另外,勞動強度大是制約牲畜糞便肥料利用的又一障礙因素,要研究各種有機糞肥施用的配套農業(yè)機械和技術,包括相應的政府政策扶持措施等。只要重建種植業(yè)和養(yǎng)殖業(yè)的新型互動關系,就有望實現(xiàn)農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除了觀念性的啟發(fā)作用之外,我國傳統(tǒng)的一些知識和經(jīng)驗還是可以直接借鑒利用的。如壟作的知識和經(jīng)驗,包括“上田棄畝,下田棄畎”等具體經(jīng)驗等。壟作技術在如今內蒙古敖漢旗旱作農業(yè)系統(tǒng)中的普遍應用,就表現(xiàn)了這一技術的生命力和現(xiàn)代價值。又如,桑田中桑間不能種谷(粟),也不能種蜀黍,但能種綠豆、黑豆、芝麻、黍等的經(jīng)驗,在當今的農業(yè)生產(chǎn)中也具有直接的利用價值。這方面的具體例子很多,不贅述。
作者:侯振兵 單位:西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