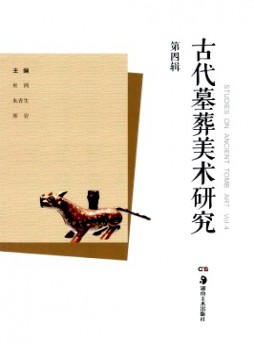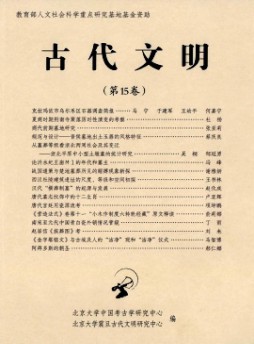古代水利工程的改建與特征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古代水利工程的改建與特征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文中稱發(fā)卒數(shù)十萬(wàn),費(fèi)用以百億計(jì),這次調(diào)動(dòng)民役,耗費(fèi)資財(cái)?shù)臄?shù)量只有西漢武帝時(shí)期對(duì)漕運(yùn)的治理可與之比堪,據(jù)《史記•平準(zhǔn)書(shū)》:“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shù)萬(wàn)人;鄭當(dāng)時(shí)為渭漕渠回遠(yuǎn),鑿直渠自長(zhǎng)安至華陰,作者數(shù)萬(wàn)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shù)萬(wàn)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fèi)亦各巨萬(wàn)十?dāng)?shù)。”不過(guò),若就西漢武帝和東漢明帝時(shí)期國(guó)力對(duì)比而言,王景治理黃河花費(fèi)了東漢中央政權(quán)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也說(shuō)明了這種規(guī)模的水利工程只能以中央政權(quán)的力量來(lái)實(shí)施。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汴渠所在是河南尹轄境,為東漢京畿地區(qū)的核心,漢明帝花大氣力治理久已成災(zāi)的這條河渠,或許也有加強(qiáng)對(duì)京師腹地統(tǒng)治的目的。
事實(shí)上,這種大型治理工程,不僅花費(fèi)巨大,而且因?yàn)榧夹g(shù)等方面的原因,也未必能夠達(dá)到預(yù)定的效果。據(jù)《后漢書(shū)•鄧禹傳》:“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cāng),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wú)成,轉(zhuǎn)運(yùn)所經(jīng)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沒(méi)溺死者不可勝算。”按,都慮,史書(shū)無(wú)載。石臼河是虖沱河的一條支流,在冀州常山國(guó)境內(nèi),羊腸倉(cāng)即汾陽(yáng)故城,屬并州太原郡。仔細(xì)揣摩文義,都慮似為這條漕運(yùn)路線的另一個(gè)端點(diǎn),應(yīng)該在常山國(guó)。溝通這條水路的目的是連接兩郡之間漕轉(zhuǎn),但所經(jīng)過(guò)之處,地形復(fù)雜,最終勞而無(wú)功。這一問(wèn)題最終還是以陸路運(yùn)輸?shù)姆绞絹?lái)解決。建初三年,章帝聽(tīng)從鄧訓(xùn)的建議:“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fèi)億萬(wàn)計(jì),全活徒士數(shù)千人。”正因?yàn)槿绱耍芍醒虢M織修建的水利工程在史籍中的記載并不多見(jiàn)。當(dāng)然,這也與和帝以后皇權(quán)衰微,中央很難集中社會(huì)資源,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水利建設(shè)有關(guān)。在東漢后期,甚至一些舊有的水利工程也被毀棄。《水經(jīng)注》卷二十九《湍水》:“漢孝元之世,南陽(yáng)太守召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開(kāi)三門(mén)為六石門(mén),故號(hào)六門(mén)堨也。溉穰、新野、昆陽(yáng)三縣五千余頃,漢末毀廢,遂不修理。”南陽(yáng)為東漢帝鄉(xiāng),素為東漢統(tǒng)治者所重視,即便如此,曾經(jīng)在農(nóng)業(yè)灌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水利工程,東漢末年亦被毀棄。
因此,中央政權(quán)對(duì)水利工程的關(guān)注更多地表現(xiàn)在對(duì)水利工程的管理方面。首先,通過(guò)詔令等法律形式對(duì)水利工程的修建提出要求。《后漢書(shū)•和帝紀(jì)》記載,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堤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不以為負(fù)。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dǎo)。勿因緣妄發(fā),以為煩擾,將顯行其罰。”和帝的這道詔書(shū),就是對(duì)地方刺史、郡國(guó)守相等地方長(zhǎng)吏修理水利工程提出的政策要求:既要注意修葺,又不能勞民傷財(cái),這也反映出修建水利工程的迫切和所耗役費(fèi)繁多之間的矛盾。在出現(xiàn)水災(zāi)以后,中央對(duì)地方官吏的懲罰也切實(shí)執(zhí)行著。如黃香在魏郡太守任上,雖然治績(jī)突出,但“后坐水潦事免”。其次,設(shè)置專門(mén)職官也是重要的一面。除在郡縣等地方政權(quán)設(shè)置專門(mén)的主管水利官員如水曹及都水、監(jiān)渠諸掾外,中央任命的專司其職的職官主要是河堤謁者。東漢的河堤謁者一般由三府掾?qū)偌嫒危瑢O星衍輯應(yīng)劭《漢官儀》:“又舊河堤謁者,世祖改以三府掾?qū)贋橹]者領(lǐng)之,遷超御史中丞、刺史,或?yàn)樾】ぁ!蓖蹙耙驗(yàn)橹卫磴旰佑泄Γ瑤捉?jīng)擢遷作為謁者,“(永平)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wú)鹽。帝美其功績(jī),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能夠被選任為謁者,有治水方面的專門(mén)經(jīng)驗(yàn)或許是其中的必然要素。并且,由這兩條材料亦反映出河堤謁者為國(guó)家所重視,多有超遷或額外賞賜的機(jī)會(huì)。又《水經(jīng)注》卷七《濟(jì)水》:“《漢官儀》曰:舊河堤謁者居之(酸棗)城西,有韓王望氣臺(tái)。”可以看出,他們的治所在其所負(fù)責(zé)區(qū)域,并不在京師。
河堤謁者之所以治于酸棗城,根據(jù)《風(fēng)俗通義•山澤》所言:“河堤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岳同。”酸棗所在的濟(jì)水就是古代四瀆之一。這段話也揭示出河堤謁者員額很可能為四人。
地方行政官員對(duì)水利工程的整治
總體說(shuō)來(lái),除了對(duì)個(gè)別大型水利工程進(jìn)行修建,中央政權(quán)對(duì)水利工程的關(guān)注重心主要體現(xiàn)在政策方面。東漢時(shí)期對(duì)水利工程的維護(hù)和修葺,更多表現(xiàn)為地方官員的個(gè)體行為。地方長(zhǎng)吏修建水利工程的記載,頻見(jiàn)史籍。《水經(jīng)注》卷二十八《沔水》:“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huì),楚時(shí)于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溉田,謂之木里溝。”在南郡太守的任上,王寵以先秦舊有渠道為基礎(chǔ),又作了進(jìn)一步的修建,形成新的水利工程。作為地方行政的一部分,地方官員對(duì)水利工程的修葺行為,遍布于東漢統(tǒng)治區(qū)域內(nèi)。不僅有深耕熟耨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區(qū)。如鄧晨在汝南太守任上,為了有效利用舊有的鴻?quán)S陂,“署(許)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shì),起塘四百余里,數(shù)年乃立”;王梁任“河南尹,穿渠引谷水,以注洛陽(yáng)城下”。而且在一些邊遠(yuǎn)地區(qū),水利工程的修建也見(jiàn)于記載。如:西北涼州地區(qū),任延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在西南巴蜀地區(qū),“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kāi)通溉灌,墾田二千余頃”。此外,在南陽(yáng)、廣陵、下邳、廬江、隴西等地也有地方官員建設(shè)水利工程的記載。地方長(zhǎng)吏能夠熱衷于水利工程的建設(shè),這和兩漢對(duì)地方官員的考績(jī)制度內(nèi)容有著密切關(guān)系。
根據(jù)西漢晚期材料尹灣漢簡(jiǎn)《集簿》的記載,地方官員向中央上計(jì)的內(nèi)容就有“提封”、“獲流”,即墾田和吸收流民數(shù)量的統(tǒng)計(jì),這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jī)的重要指標(biāo)。而這兩項(xiàng)和水利工程建設(shè)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元和三年,張禹任下邳相,“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kāi)水門(mén),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shù)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谷實(shí)。鄰郡貧者歸之千余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他通過(guò)修繕?biāo)T(mén),開(kāi)渠灌溉,輔之以勸耕假貸等措施,不僅增加了田地面積,而且還吸納了鄰郡的貧困人口。這些自然是由地方官員的考績(jī)制度所促成的。
地方官員重視水利工程建設(shè),還與當(dāng)時(shí)農(nóng)作技術(shù)的發(fā)展,特別是稻作技術(shù)的進(jìn)步與種植面積的拓展有一定關(guān)系。據(jù)西嶋定生先生的研究,西漢武帝時(shí)期,將東越等東南地方的稻作民遷移到江淮地區(qū),后又遷移到華北,使得南方的水稻栽培技術(shù)對(duì)華北產(chǎn)生了影響。因此,東漢時(shí)期關(guān)于北方種植水稻的記載逐漸增多,如:張堪擔(dān)任漁陽(yáng)太守時(shí),“乃于狐奴開(kāi)稻田八千余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崔瑗任汲令時(shí),“為人開(kāi)稻田數(shù)百頃”。這也就意味著,水利工程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旱田的灌溉問(wèn)題,還需要為稻田提供更多的水源。《水經(jīng)注》卷二《河水》:“昔馬援為隴西太守六年,為狄道開(kāi)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lè)業(yè)。”所謂秔稻,即粳稻,馬援在西北地區(qū)開(kāi)挖水渠,就是以種植秔稻為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地方水利灌溉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樗痉N植范圍擴(kuò)大所導(dǎo)致的。如上所述,地方官員對(duì)水利工程修建的現(xiàn)象在全國(guó)各地都能看到,但對(duì)此也不宜估計(jì)過(guò)高。因?yàn)樵诟鞯厮拗蔚乃こ蹋嗍菍?duì)舊有的工程進(jìn)行改造而成,新建的工程則十分鮮見(jiàn)。傅筑夫先生、馬新先生都曾經(jīng)指出這一點(diǎn)。
《后漢書(shū)•循吏王景傳》載,王景遷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qū)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辟倍多,境內(nèi)豐給”。所謂“修起蕪廢”就是將郡界內(nèi)先秦時(shí)期已有的芍陂重新整理。又《后漢書(shū)•馬援傳》載,馬棱遷廣陵太守,“興復(fù)陂湖,溉田二萬(wàn)余頃,吏民刻石頌之”。“興復(fù)陂湖”說(shuō)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已有的陂池等。在農(nóng)業(yè)發(fā)展比較早的地區(qū)這一現(xiàn)象尤為明顯。如汝南在明帝時(shí)期,鮑昱“后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fèi)常三千余萬(wàn)。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的開(kāi)發(fā),才會(huì)出現(xiàn)“郡多陂池”,這也就成為地方官員進(jìn)行重建的基礎(chǔ)。據(jù)《北堂書(shū)鈔》卷七六引華嶠《后漢書(shū)》,在章帝時(shí)期,“何敞為汝南太守,修治鲖陽(yáng)之舊陂,溉田萬(wàn)頃,墾田三萬(wàn)余,咸賴其利,吏民刻石,頌敞功德”。何敞所利用的也是汝南境內(nèi)的鲖陽(yáng)舊陂。
還值得注意的是,史籍明確提到地方官員對(duì)水利工程的修建都集中在光武、明帝、章帝三朝。此時(shí)皇權(quán)集中,皇帝能夠掌控地方官員,對(duì)地方官員的治績(jī)也能進(jìn)行有效的考核。但從和帝開(kāi)始政局紊亂,皇權(quán)不僅不能對(duì)地方官員實(shí)行有效的控制,并且,地方長(zhǎng)吏的選任也常由外戚和宦官控制。政績(jī)的優(yōu)劣并不能決定仕途通暢與否。因此,水利工程的修治因?yàn)楹馁M(fèi)巨大,被擱置起來(lái)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安帝時(shí)期也有兩次地方興修水利的記載:元初二年,“修理西門(mén)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元初)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對(duì)舊有溝渠的修理行為,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時(shí)重要事件,反映了各地修建水利工程已經(jīng)十分罕見(jiàn),這反過(guò)來(lái)也說(shuō)明地方水利工程逐漸廢蕪的事實(shí)。三、豪強(qiáng)控制的水利工程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東漢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水利工程雖然曾促進(jìn)了轄境內(nèi)農(nóng)業(yè)灌溉的發(fā)展,為當(dāng)?shù)刈∶駧?lái)切實(shí)的益處。但因?yàn)樾陆ǖ乃こ毯苌伲⑶視r(shí)間也非常集中,所以從整體上說(shuō),這一層次的水利建設(shè)還存在很大的局限。
與此相對(duì)應(yīng)的是,民間自發(fā)修建的小型水利工程卻比較常見(jiàn)。如《后漢書(shū)•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jié)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顯然,這類水利工程并不是一般小農(nóng)家庭所修建的。它為西漢中后期逐漸發(fā)展起來(lái)的豪強(qiáng)所修建和控制。劉秀外家樊氏“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yú)牧畜,有求必給”。《水經(jīng)注》卷二九《比水》引司馬彪《續(xù)漢書(shū)》對(duì)此有更詳盡的記載:“能治田殖,至三百頃。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yú)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mén)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wàn)。其興工造作,為無(wú)窮之功,巧不可言,富擬封君。”從土地規(guī)模和家貲數(shù)目,以及田莊內(nèi)高度的自給性看,顯然是勢(shì)力很大的地方豪強(qiáng),并且,對(duì)水利工程的日常維護(hù),也是豪強(qiáng)組織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必要工作之一。《四民月令》有:“三月……農(nóng)事尚閑,可利溝瀆。”《四民月令》所反映的是豪強(qiáng)田莊內(nèi)一年中每月的生產(chǎn)生活日程,修溝瀆都是在農(nóng)閑時(shí)節(jié)完成的,也是豪強(qiáng)田莊內(nèi)生產(chǎn)活動(dòng)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地方官員對(duì)水利工程的修治是出于對(duì)本地區(qū)多數(shù)人的利益考慮。而豪強(qiáng)的水利工程只關(guān)注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二者無(wú)論是在規(guī)模,還是在功能上均有著很大的差異。各地出土的陂塘模型提供了許多直觀的例證。劉文杰先生和余德章先生在《四川漢代陂塘水田模型考述》一文中提供幾個(gè)四川地區(qū)的樣本:“新津縣寶子山出土陶水田……田中橫著一道溝渠,在渠中刻畫(huà)著幾條游魚(yú)和田螺,渠水可由通道流入兩邊的田中”;“綿陽(yáng)新皂鄉(xiāng)東漢墓出土一長(zhǎng)方形陶水田模型,此水田深似水塘,分左右兩部分。右塘中有泥鰍、田螺和荷花,當(dāng)為藕田;左田應(yīng)是秧田”;“峨嵋縣雙福公社東漢磚墓中出土了一件浮雕石水塘水田模型……右邊似一深水塘,塘中水鴨爭(zhēng)食,蝦蟆、螃蟹、田螺和游魚(yú)點(diǎn)綴其中,又有一小船泊于塘中。
左邊是農(nóng)田兩塊”。從這幾個(gè)例子可以看出,除了利用陂渠進(jìn)行稻作灌溉,同時(shí)其中也養(yǎng)殖了田螺、魚(yú)、蓮藕、水鴨等副產(chǎn)品,發(fā)展多種經(jīng)營(yíng)。這固然具有四川地區(qū)的地方特色,但也是東漢豪族莊園內(nèi)部經(jīng)濟(jì)自給性質(zhì)的真實(shí)反映。此外,豪強(qiáng)家族水利工程的功能似乎也不僅限于此。平陸地區(qū)有一件“池中望樓”模型,在養(yǎng)有水鴨的池塘中央有一望樓,分三層,其中第二層“四阿頂,四周有圍欄,四角有弓箭手站守”。池塘中央的望樓中設(shè)置弓箭手,使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這個(gè)池塘還兼具自衛(wèi)的功能。豪強(qiáng)勢(shì)力的不斷膨脹,使他們不僅僅滿足于控制單個(gè)家族內(nèi)的小型水利工程,甚至還要染指政府所修治的地方公共水利工程。如明帝任用王景等修治汴渠后,特別以詔書(shū)的形式強(qiáng)調(diào):“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wú)令豪右得固其利。”
在中央集權(quán)還很強(qiáng)大的時(shí)候,明帝還有這種憂慮,更遑論和帝以后情形了。而和帝以后政府修建水利工程數(shù)量的減少,或許同強(qiáng)宗豪右對(duì)地方公共水利工程的侵蝕有一定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豪強(qiáng)不僅試圖控制水利工程,有時(shí)他們還要干預(yù)地方水利工程的修建。《后漢書(shū)•方術(shù)•許楊傳》:“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jìng)欲辜較在所,楊一無(wú)聽(tīng),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辜較”即“辜榷”,《漢書(shū)•王莽傳下》顏師古注:“謂獨(dú)專其利,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東漢前期,地方大族為了獲得在水利工程修建中的利益,竟不惜排擠地方官員。四、豪強(qiáng)勢(shì)力的擴(kuò)張與東漢水利工程格局的形成由上所述,國(guó)家政權(quán)和地方豪強(qiáng)對(duì)水利工程的控制范圍、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從中央到地方,東漢政權(quán)對(duì)水利工程的修建雖然作出了種種努力,但從全國(guó)范圍來(lái)看,更多地體現(xiàn)為個(gè)體行為。
并且官方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集中在東漢前期中央權(quán)力相對(duì)強(qiáng)大階段。與此相對(duì)應(yīng),豪強(qiáng)所控制的小型水利工程自西漢后期開(kāi)始,就有廣泛的分布。并且,他們還試圖進(jìn)一步蠶食歷史遺留下來(lái)和國(guó)家控制的水利工程帶來(lái)的利益。為什么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呢?自西漢后期開(kāi)始社會(huì)秩序的變動(dòng)是其中的一個(gè)重要推動(dòng)因素。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豪強(qiáng)勢(shì)力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是導(dǎo)致水利工程的控制權(quán)由政府逐漸轉(zhuǎn)移到地方豪強(qiáng)手中的重要原因。豪強(qiáng)勢(shì)力的增強(qiáng)首先表現(xiàn)在政治領(lǐng)域中的地位逐漸加重。西漢前期,出于保護(hù)自耕農(nóng)階層的利益,并進(jìn)而穩(wěn)定帝國(guó)統(tǒng)治的需要,對(duì)工商業(yè)主階層予以限制和打擊,對(duì)其采取身份歧視政策。如《史記•平準(zhǔn)書(shū)》載:“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shí),為天下初定,復(fù)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
很自然,對(duì)商人的禁錮,使他們?cè)谡紊蠜](méi)有任何地位。而在小農(nóng)分化尚不明顯的時(shí)代里,這個(gè)階層是豪強(qiáng)階層最主要的來(lái)源。不過(guò),隨著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政策的調(diào)整,以及豪強(qiáng)階層的不斷發(fā)展壯大,在西漢中期以后,他們逐漸取得鄉(xiāng)里的支配權(quán)。如《后漢書(shū)•王丹傳》記載王丹在兩漢之際的情況:“家累千金,隱居養(yǎng)志,好施周急。每歲農(nóng)時(shí),輒載酒肴于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孏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yè)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zé)之。沒(méi)者則賻給,親自將護(hù)。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xiāng)鄰以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風(fēng)俗以篤。”這是地方民豪強(qiáng)在鄉(xiāng)里發(fā)生影響的一個(gè)典型實(shí)態(tài):他們依靠自身的財(cái)富,周濟(jì)鄉(xiāng)里,并在道德上率先垂范,躬行教化,以此取得在基層社會(huì)的實(shí)際控制權(quán)。
漢代社會(huì)階層的這種變動(dòng),使豪強(qiáng)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內(nèi),利用規(guī)則和程序,開(kāi)始逐漸步入政壇,參與到各級(jí)政權(quán)組織當(dāng)中。漢代地方政府的屬吏選任,都是由本籍人士擔(dān)任。長(zhǎng)吏的籍貫則都來(lái)源于其轄地以外,并且這種限制,在東漢時(shí)期愈加嚴(yán)格。地方長(zhǎng)吏為了能夠更好地對(duì)地方進(jìn)行管理,選拔已經(jīng)在本地取得支配地位的豪強(qiáng)來(lái)?yè)?dān)任屬吏便是很自然的事情。這樣,就使得豪強(qiáng)參與到地方政治當(dāng)中。事情并不止于此。漢代仕進(jìn)的一個(gè)主要通道為察舉制度,即由長(zhǎng)吏推舉屬吏到中央出任郎官,并進(jìn)而成為長(zhǎng)吏。這樣豪強(qiáng)就成可以利用這一規(guī)則進(jìn)入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級(jí)政權(quán)當(dāng)中。除了政治、經(jīng)濟(jì)方面的自然發(fā)育而使豪強(qiáng)在政治舞臺(tái)的地位逐漸重要以外。這一階層在東漢立國(guó)過(gu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可忽視。兩漢之際,相對(duì)于其他割據(jù)勢(shì)力而言,劉秀所怙恃的力量主要是豪強(qiáng),一部分是南陽(yáng)地區(qū)的元從,如李通、彭寵、鄧禹等。除此以外,在統(tǒng)一進(jìn)程中,歸附劉秀的一些割據(jù)勢(shì)力亦為豪強(qiáng)出身,如河西地區(qū)的竇融,自其高祖始,累世仕宦河西。正因?yàn)槿绱耍缽?qiáng)在國(guó)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很強(qiáng)的話語(yǔ)權(quán)力。因而可以想見(jiàn),在東漢各種政策的制訂過(guò)程中一定會(huì)有維護(hù)本階層利益的傾向,對(duì)關(guān)系他們存在基礎(chǔ)的水利工程也莫能例外。
此外,在制度方面促使東漢的豪強(qiáng)更加關(guān)注水利工程的建設(shè)還在于,東漢致仕或去官的高級(jí)官員,一般都要回到原籍居住,這和西漢政權(quán)將這批人留在京畿地區(qū)是截然不同的。這一點(diǎn)已為何茲全先生所指出:“東漢的政策,和西漢相反,除外戚家族和特許者外,一般大臣去官就要回歸鄉(xiāng)里原籍,而且還不得私歸京師。”從前面分析東漢官員的出身看,他們多來(lái)源于地方豪強(qiáng),因?yàn)樗麄兪嘶轮蟮臍w宿依然是本籍,所以他們?cè)谒呱舷蛩郊宜こ虄A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豪強(qiáng)對(duì)水利工程的重視,除了政治方面所提供的必要條件和必然的需求外,豪強(qiáng)自身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改變,則為豪強(qiáng)修繕?biāo)こ烫岢隽艘蠛捅U稀N鳚h中期以后,因?yàn)閲?guó)家政策的調(diào)整,同時(shí)古典的商品交換經(jīng)濟(jì)逐漸讓渡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jì),從西漢中期以后,豪強(qiáng)的經(jīng)營(yíng)形式由工商業(yè)領(lǐng)域逐漸減轉(zhuǎn)向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通過(guò)兼并土地,逐漸形成田莊內(nèi)的多種經(jīng)營(yíng)。有學(xué)者曾強(qiáng)調(diào)武帝推行統(tǒng)制經(jīng)濟(jì)政策以后,特別是“告緡令”的實(shí)施,使豪民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逆轉(zhuǎn),促使社會(huì)資金大量回流農(nóng)業(yè),使土地兼并、豪民役使等問(wèn)題日益嚴(yán)重,田莊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土地迅速集中,規(guī)模擴(kuò)大,迫切需要豪強(qiáng)組織修建水利工程,以抵御水旱災(zāi)害,提高產(chǎn)量,增加收入。同時(shí),因?yàn)樽晕鳚h后期開(kāi)始,伴隨著土地兼并嚴(yán)重而發(fā)展起來(lái)的依附關(guān)系,也為水利工程的修建提供了必要保證。豪強(qiáng)可以組織和協(xié)調(diào)自己所控制的包括宗族、賓客在內(nèi)的各種依附人口,完成先前一般單個(gè)小農(nóng)家庭所無(wú)力擔(dān)負(fù)的水利工程,也就變相地承擔(dān)起先前國(guó)家所擔(dān)負(fù)的修建水利工程的職能。盡管這種規(guī)模比起后者要小得多。從政府角度看,東漢政府特別是和帝以后,國(guó)力的衰微、政局的混亂使其無(wú)力新建水利工程。
但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方面,東漢國(guó)家似乎對(duì)水利工程的修葺也措意不多。從設(shè)立與水利相涉的職官方面就可以反映出來(lái)。如河堤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岳同”。所謂四瀆,“江、河、淮、濟(jì)為四瀆”。對(duì)主要江河的祭祀是這一職官的重要的職能。一般的水官設(shè)置的著眼點(diǎn)也不在于水利工程維修。《續(xù)漢書(shū)•百官志五》:“有水池及魚(yú)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這就是說(shuō)他們同鹽鐵官一樣,其重心是放在對(duì)稅收的斂取方面,并且也不是在全國(guó)普遍設(shè)置的。國(guó)家對(duì)水利工程職官的設(shè)置,是從直接關(guān)系其自身利益的經(jīng)濟(jì)和政治角度考慮的。水利工程所具有的保障生產(chǎn)的功能并不是他們首先要注意的。
但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離不開(kāi)水利灌溉,政府力量的衰微又不能提供有力的幫助,需要?jiǎng)趧?dòng)力極多的水利灌溉工程的維護(hù)與修繕工作,便被已勢(shì)力日彰的豪強(qiáng)所把持。豪強(qiáng)加強(qiáng)對(duì)水利工程的壟斷,在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小農(nóng)從事生產(chǎn)的必要手段,加大了小農(nóng)對(duì)豪強(qiáng)依賴,加深了小農(nóng)對(duì)豪強(qiáng)的依附,加速了小農(nóng)破產(chǎn)的進(jìn)程。在此之后的劉宋時(shí)人的話也能反映出這點(diǎn):“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采掇存命……此郡(晉陵)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并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谷,皆有巨萬(wàn),旱之所弊,實(shí)鐘貧民。”
這就說(shuō)明在大旱之年,富室豪強(qiáng)憑借自己的水利工程,損失并不明顯,而只有那些貧民之家才會(huì)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此雖是劉宋時(shí)期的情況,但東漢時(shí)期的情況也可以此為參照。因此,水利工程主導(dǎo)權(quán)在東漢時(shí)期從政府手中轉(zhuǎn)移到豪強(qiáng)手中,對(duì)社會(huì)階層的變動(dòng)產(chǎn)生了一定作用,是影響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封建化進(jìn)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沈剛單位:吉林大學(xué)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