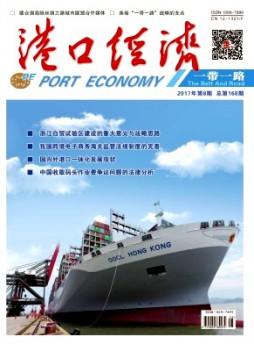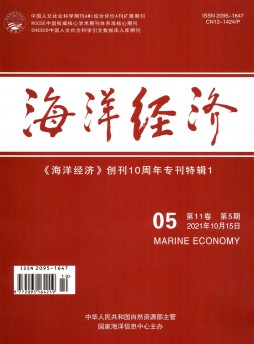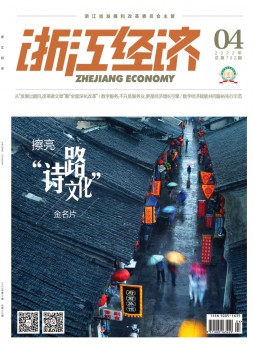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Kuznets曲線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Kuznets曲線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關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很多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1992年,美國經濟學家G•Grossman和A•Kureger對此提出了一個環境kuznets曲線(EnvironmentKuznetsCurve,EKC)的假設[1]。該假設試圖說明如果沒有一定的環境政策干預,一個國家的整體環境質量或污染水平是隨著經濟增長和經濟實力的積累呈先惡化后改善的趨勢。他們采用跨國數據說明了EKC的存在,即最初環境惡化程度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達到一個轉折點后,將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并把這種現象歸因于以下幾點:(1)當人們越富有時,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高;(2)人們越富有,越有能力降低環境惡化程度;(3)經濟增長有利于經濟結構向低污染型生產轉化;(4)經濟增長有利于加速降低環境污染強度的技術的進步。Beckerman(1992)甚至認為,“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環境惡化程度的下降可以由經濟增長來解決。”國外學者對這項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在認為存在EKC的基礎上,采用橫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通過擬合二次多項式或三次多項式模型進行估計,在此基礎上再來計算出拐點而進行的;另一種是利用一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來進行分析的。但是,前一種研究方法目前受到了許多嚴厲的批評。批評者們認為,只有使用單一國家數據才能判別不同污染的真實EKC是否存在(如RobertsGrimes1997)。截面數據僅僅能反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所具有的負向關系,它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是呈正向關系的,因而,它不是一個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單一關系。這一結論同樣也適用于一個國家內不同地區的截面數據。因為,采用截面數據等于暗含了所有國家(或地區)都有相同的發展路徑,而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
ListGallet(1999)就曾用美國1929~1994年的數據對不同州的EKC進行了分析,他發現不同州的轉折點并不相同,即美國各州的污染路徑是不一致的,從而也印證了上面的結論。至于第二種方法,目前國外對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結論也并不相同。一種認為存在EKC,如Carson等人(1997)利用美國1988~1994數據發現七種空氣污染物與經濟增長存在負向關系,并且轉折點明顯在用截面數據計算出來的轉折點之上,從而印證存在EKC。但是,大部分利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的研究卻表明EKC并不存在,如HannesEgli(2001)利用德國數據所作的研究就證明EKC并不存在[2]。KathleenM.day(2001)利用加拿大數據也正證明EKC并不存在[3]。國內對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是否符合EKC的研究始于20世紀末,在方法上雖然大都是采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的,所不同的是有的是以我國不同年份作為樣本來進行研究的,如朱智(2004)就是利用我國1991~2001年的數據,采用指數回歸模型進行研究的,并認為我國水環境與水利經濟發展的關系位于EKC的上升階段[4]。有的則以省市數據作為樣本來進行研究的,如吳玉萍等(2002)利用北京市1985~1999數據[5]、高振寧等(2004)選取江蘇1988~2002數據[6]、陳華文等(2004)利用上海市1990~2001年數據[7]、劉耀彬等(2003)利用武漢市1985~2000年數據所作的研究[8]。但這些研究有一個共同點,首先,都是先假定EKC存在,然后,再通過直接運用時間序列數據擬合二次多項式或三次多項式,并據此再求出拐點來進行的。綜觀這些實證研究,他們存在一個共同的弊端,那就是對于時間序列數據,并沒有進行平穩性和協整性檢驗,因此,所得到的結論就有可能因為是虛假回歸而不能令人信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國是地球上經濟變化最快的地方,也許在歷史上絕無僅有,英國用了差不多整個19世紀才使人均收入增長了2•5倍,美國在1870~1930年的60年間收入增加3•5倍,日本在1950~1970年增長了6倍,而中國卻比它們都快。自從1979年擺脫了經濟孤立后,中國的收入增長了7倍,如果中國經濟還將騰飛,這樣的轉變引起的全球效應將是戲劇化的”(JimRohwer,2001)。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的環境污染情況不容樂觀: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1998)提供的資料,我國1995年單位美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國的5•5倍,日本的13•8倍,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7•9倍,世界平均水平的4•6倍。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1998)提供的資料計算,我國1993年日水污染量是美國的2•2倍,日本的3•4倍,英國的7•8倍。由此可見,我國經濟發展付出了十分昂貴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這樣的發展是難以持續的。因此,對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到底是否符合EKC進行深入細致研究,這對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避免和減少環境污染具有重要意義。
二、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間關系的簡化模型
(一)簡化模型的設計
本文用來研究經濟增長和環境關系的指標是這樣設計的:用來反映經濟增長的指標是人均實際GDP(通過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反映環境污染程度的指標是用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廢物排放量三個指標,即通常所說的“三廢”指標。對環境污染程度之所以采用這三個指標,一是因為目前在我國普遍采用的都是以它們作為環境污染程度指標的;二是因為這三個指標具有長期值,便于進行統計分析,這三個指標中的任何一個上升都將意味著環境污染程度的加大。關于環境污染程度指標和人均GDP關系的EKC研究國際上常用如下兩種形式的簡化模型來進行:一是二次多項式;再一個是三次多項式,可以包括常數項或時間項。也有一些專家學者在此簡化模型中加入了其他一些變量,如貿易強度(Grossman和krueqer1995)、能源價格(deBrugn,vandenBergh和Opschoor1998)、經濟結構(surichapman1998)、經濟活動的空間密度(kaufmannetal1998)和收入的不平等性等(TorrasBoyce1998)。但是,添加這些附加的變量,由于其中一些隨著時間變化很少,因此,用在只有一個國家的利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估計的簡化模型中作為回歸量并不合適。此外,使用僅包含人均GDP作為變量的簡化模型有利于進行國際比較。因此,我們所采用的簡化模型中將不包含這些附加變量。本文采用的三次多項式簡化模型來進行的,模型表達式為:lnEi=α1+α2lnYi+α3lnY2i+α4lnY3+ui(1)其中,lnEi為環境污染指標的對數,lnYi為真實人均GDP的對數。
在上述模型中,如果α2>0,α3>0,且α4=0,則環境污染程度曲線將呈倒U型曲線;如果α2<0,α3=0,且α4=0,則環境污染程度曲線將直線下降;如果α2>0,α3<0,α4>0,則環境污染程度曲線將呈N型;如果α2<0,α3>0,且α4<0,并以人均GDP為橫坐標,環境污染程度指標為縱坐標,則環境污染程度也將呈現倒N型,這意味著一個令人滿意的人均GDP和環境污染的長期關系將存在。利用上述簡化模型,我們分別對我國的工業廢水(E1)、工業廢氣(E2)和工業廢物(E3)的EKC進行了估計,樣本數據區間為1986~2003年,資料來源為1987~2004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估計結果如下:對工業廢水EKC的估計,采用三次多項式簡化模型,經檢驗lnY3的系數不顯著,采用二次多項式進行估計,結果如下:lnE1=4•368lnYi(18•21)-0•3253lnY2i(-9•80)R2=0•108DW=2•1F=0•85(Prob(F-statistic))=0•448769)(2)該估計方程雖然兩個系數顯著,但由于F檢驗的P值為0•448769,故回歸方程總體上并不顯著。對工業廢氣EKC的估計結果如下:lnE2=-328(-2•51)+142•746lnYi(2•64)-20•039(-2•69)lnY2i+0•94(2•75)α4lnY3(3)R2=0•98DW=2•28F=180•99(Prob(F-statistic)=0•000000)該估計方程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回歸方程總體上也是顯著的(F檢驗的P值為0),模型擬合很好,且不存在序列相關,這說明模型的解釋力很強。對工業廢物EKC的估計結果如下:lnE3=2283•95(3•436)-936•3lnYi(-3•373)+128•21lnY2i(3•324)-5•84lnY3(-3•277)(4)R2=0•741DW=2•13F=13•364(Prob(F-statistic)=0•000215)該回歸方程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回歸方程總體上也是顯著的(F檢驗的P值為0•000215),模型擬合很好,且不存在序列相關,模型的解釋力較強。
從工業廢水的EKC估計方程看,由于α2>0,α3<0,且α4=0可知,這似乎符合倒U形曲線存在的條件,但由于該回歸方程在總體上并不顯著,所以這種關系等于不存在;對于工業廢氣EKC估計方程,由于α2>0,α3<0,α4>0,故表明廢氣污染程度曲線是呈N型的,即最初廢氣污染程度是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的,當達到一個轉折點后,將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再達到一個轉折點,又隨國民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對于工業固體廢物EKC估計方程,由于α2>0,α3<0,α4<0,故固體廢物污染程度曲線是呈N型的,它表明對于工業固體廢物而言,它是人均GDP與工業固體廢物環境污染之間有一個令人滿意的長期關系。上述分析結果表明:就中國而言,除了工業固體廢物以外,對環境質量有益的人均GDP與環境污染程度指標的EKC關系并不存在。上述分析過程雖然采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但由于并沒有進行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因此還很難肯定結論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數據非平穩,上述估計結果有可能是虛假回歸,所以還需要對數據作進一步統計分析。
(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
在對EKC簡化模型估計過程中,為了避免可能出現虛假回歸,因此,首先需要對上述簡化模型中所涉及的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而后再對時間序列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首先檢驗H0∶μ=β=δ=0,檢驗統計量為:F=(RSSR-RSSU)/JRSSU/(T-k)~F(j,T-k)(5)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為約束個數,T為用于估計的觀察值的個數,k為無約束的回歸因子的個數。當計算出來的F統計量的值大于臨界值時,則拒絕原假設,說明數據至少含有截距或時間趨勢。然后檢驗H0∶β=δ=0,仍然使用上面的F統計量。如果接受原假設,則說明數據不存在時間趨勢,類似的還可檢驗是否存在截距項。在上述檢驗過程中,滯后階數的選取,一般是采用AIC標準或SC標準,我們是選用AIC標準進行。按照上述檢驗方法,我們首先進行的是ADF檢驗,然后是PP檢驗。
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對于估計方程1、2,由于被解釋變量lnE1和lnE2前者為平穩后者為二階單整,而解釋變量lnY、lnY2、lnY3卻皆是一階單整的,這表明,這兩個估計方程的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前述關于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所作的估計是“偽回歸”。而對于工業廢物估計方程,由于被解釋變量lnE3與解釋變量lnY、lnY2、lnY3皆是一階單整的,表明此方程的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前述由該估計方程所得出的結論可信。2•變量協整關系的檢驗。為了進一步驗證工業廢物估計方程工業廢物污染與人均GDP增長變量間的協整關系成立,對此我們又對模型中變量間的協整關系作了檢驗。對變量間協整關系的檢驗方法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單方程的最小二乘估計法,以E-G兩步法為代表;另一類是最大似然估計法。相對而言,最大似然估計檢驗的勢較E-G兩步法高。不論采用哪一種方法,都必須在大樣本下來進行才行。然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卻是樣本容量過少,當樣本較小時,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將缺乏一定的可信性,因為漸近臨界值只有在大樣本下才比較精確。Maddalaandkim(1998)甚至認為樣本容量應超過100才行。為了克服樣本較小的問題,我們采用了類似單位根檢驗過程,分別采用了基于E-G兩步估計法下殘差的單位根檢驗和DW檢驗,基于最大似然估計法下的hohansen檢驗等三種不同方法進行協整檢驗,以彌補因樣本容量較小的不足,增加檢驗的可信性。
E-G兩步估計法是指第一步進行協整回歸,第二步對協整回歸的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殘差是平穩的,則說明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否則協整關系不成立,所以,E-G兩步估計法下的協整檢驗實質上就是對殘差的單整檢驗。但由于是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故它的檢驗的臨界值和一般序列單位根檢驗的不同,它的臨界值更靠左。Engle-Yoo給出了這個檢驗的臨界值,稱為EG和AEG檢驗臨界值。由于在第二部分我們已經進行了協整回歸,所以可以直接對它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經計算AEG臨界值(無截距、無時間趨勢、無滯后)為-4•2763,EG臨界值為4•11,這說明殘差是平穩的,存在協整關系。另一基于最小二乘估計的協整檢驗是對殘差作DW檢驗,由Sargan-Bhargava(1983)提出,稱為協整DW統計量,記為CRDW。其計算公式和通常用于序列相關檢驗的DW統計量的計算公式相同,即CRDW=∑Tt=2(^ut-^ut-1)2∑Tt=1u^2t(6)對于工業廢物估計方程,經計算CRDW=2•13,臨界值為0•89,說明殘差是平穩的,故表明上述工業廢物污染與人均GDP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是成立的。最大似然估計法下的hohansen協整檢驗是基于VAR來進行的。根據AIC準則,選擇滯后期為2。為了說明工業廢物是否隨人均GDP的增長而趨于減少,在檢驗時采用數據存在線性趨勢,并且協整方程存在截距項和趨勢項來進行。無論是1%的顯著性水平,還是5%的顯著性水平,其統計量的值都大于臨界值,故也表明上述工業廢物污染與人均GDP增長協整關系成立。綜合上述三種檢驗方法表明,工業固定廢物和人均GDP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個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所以,關于工業固體廢物的估計方程可信。
三、結論
綜合上述關于我國人均GDP與環境污染指標之間關系所進行的實證分析標明,我國只有一個工業固體廢物污染程度指標是隨人均GDP的增長而下降的;其他兩個環境污染程度指標(工業廢水、廢氣)與人均GDP之間并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沒有證據表明我國的人均GDP的增加有助于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如果要阻止環境進一步惡化,只能通過一定的政策和激勵措施,減少企業的每單位產出的污染強度,或通過產業轉型,從多污染型向少污染型產業轉移來解決。而這一切只有通過界定產權才能實現。環境污染并不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而是缺乏所有權造成的。環境污染是由于負的外部性造成的,諾斯關于外部性的定義為:當某個人的行動所引起的個人成本不等于社會成本,個人收益不等于社會收益時,就存在外部性。傳統的辦法和標準福利經濟學是按照庇古原則采取罰款或征稅的措施來解決的。由于該方案由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加以闡述的,故又稱為“庇古稅”方案。對環境有污染行為的企業收稅或收費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在采用的一種方法,但是不能從根本上使環境負外部性內在化,收稅是收稅,污染還是污染,簡單的收稅并不是解決外部性的好辦法。世界各國環境保護的實踐已證明,僅僅通過政府來保護環境,不僅政府承擔不了,而且效率也低下。要提高環境保護的效率,只有實行環境保護市場化,環境保護市場化的實質就是要通過市場使外部性內在化,而外部性內在化的關鍵是產權制度。因為明確產權可以解決責任問題,并有利于經濟主體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的建立。如授予公眾有不被污染的權利,則可以約束污染企業排污,并激勵污染企業改進技術或進行產業轉型。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不清會導致一個國家陷入“貧困陷阱”,而在貧困陷阱中的國家,則永遠不可能達到高收入的穩定狀態。同樣,產權不清會導致一個國家陷入“污染陷阱”,而在污染陷阱中的國家,則永遠不可能得到清潔的空氣和河流。
通過產權明晰來解決污染問題,需要有三個前提:一是產權界定清楚,二是產權的有效轉讓,三是產權的法律保護。產權界定清楚是基礎,產權界定不清,就沒有交換的主體,產權就不能轉讓,而產權的有效轉讓取決于法律的保護程度。法律保護是解決環境污染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其中有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軟政權”問題。軟政權的根本含義是,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被遵守、不易實施的權力。這主要表現為包括環境保護人員在內的各級公務人員在環境保護中所普遍存在的“尋租”現象。我國雖然也頻布了一系列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但環境問題依然嚴重,除產權(污染權或被污染權)不明外,各級部門執法不利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通過對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EKC研究表明,我國的環境污染是不會隨經濟增長而自動改善的;僅僅靠國家干預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環境問題的;只有界定產權,通過一定的政策和激勵措施減少企業的單位產出的污染強度,或者產業轉型,從重污染型向輕污染或無污染型產業轉移,并輔之以嚴格執法,才能阻止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使我國環境問題得到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