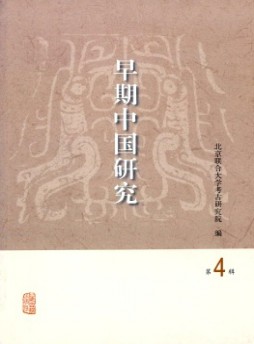早期樂戶問題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早期樂戶問題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戲劇藝術(shù)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樂戶淵源之探討
北魏雜戶制度固然直接影響了樂戶制度,但在此以前,一些民戶在功能和結(jié)構(gòu)方面已經(jīng)與后世的樂戶趨于接近了,特別是漢魏以來(lái)的樂家、音家和倡家,這為尋找樂戶的淵源提供了重要線索,可惜學(xué)界對(duì)此關(guān)注得不夠,以下稍作申述。據(jù)《太平御覽•樂部七》引《漢書》云:“惠帝葬安陵,徙關(guān)東倡優(yōu)、樂人五千戶以為陵邑。”從這條史料看,當(dāng)時(shí)掌握著表演伎藝的倡優(yōu)、樂人群體一般就以“戶”作為結(jié)構(gòu)單位。這種“戶”的內(nèi)部組織又是怎樣的呢?一些史料為此提供了信息,如《史記•佞幸列傳》及《漢書•外戚傳》分別記載: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6](P.3195)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jìn)。初,夫人兄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平陽(yáng)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shí)妙麗善舞。[7](P.3951)自上引可知,李延年一戶之內(nèi)無(wú)論男女老少人人皆以歌舞表演為業(yè),而且這些伎藝明顯帶有世代傳承的性質(zhì)。和其他史料比對(duì)又可知,這些“戶”的特點(diǎn)與后世的雜戶、樂戶存在不少相似之處,如《魏書•世祖紀(jì)》載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庚戌“詔”云:其百工伎巧,騶卒子自成,當(dāng)習(xí)其父兄所業(yè),不聽私立學(xué)校。這是北魏雜戶制度推行以后發(fā)生的事情,由此可見當(dāng)時(shí)樂雜戶的伎藝是父兄子弟之間世代相傳的。另?yè)?jù)劉肅《唐新語(yǔ)》卷二《極諫》引李綱諫曰:“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yè)。”[8](P.297)這條史料再次表明,即使樂戶制度出現(xiàn)以后,戶內(nèi)世代傳承技藝的特點(diǎn)仍然牢不可破。所以說(shuō),漢魏以來(lái)一些民戶在功能和結(jié)構(gòu)上與后世的雜戶、樂戶確實(shí)存在相似之處。另外,漢魏這批民戶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稱謂,如“樂家、音家、倡家”等,也近似于后世“樂戶”之有專稱,這些稱謂在歷史典籍中出現(xiàn)的頻率還是比較高的,茲舉數(shù)例如次:《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為太樂官。《太平御覽•樂部二十一》引《風(fēng)俗通》:琵琶,近代樂家所作,不知所起。《漢書•外戚傳》: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宋書•律歷上》: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wú)施于樂。《三國(guó)志•后妃傳》:武宣卞皇后,瑯玡開陽(yáng)人,文帝母也。本倡家。《三國(guó)志•許慈傳》:(劉備)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效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皆可為證,其中“樂家有制氏世世為太樂官”一條,亦反映出這種音樂伎藝在家族內(nèi)的傳承性,而且“家”與“戶”在意義上也相當(dāng)接近。直至隋唐時(shí)期,人們?nèi)匀挥杏谩皹芳摇币辉~稱呼樂戶的習(xí)慣,舉例如:《隋書•裴蘊(yùn)傳》:蘊(yùn)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yōu)百戲者,皆直太常。《新唐書•王虔休傳》: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圣樂》,因帝誕日以獻(xiàn)。
以上例子又一次證明,樂戶與漢魏以來(lái)大量出現(xiàn)的樂家、音家、倡家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在樂戶制度正式出現(xiàn)以后,仍有人用“樂家”這種舊有稱謂來(lái)稱呼樂戶。而在近代學(xué)者的論文中,則有使用“樂戶”一詞稱呼兩漢魏晉時(shí)期伎樂人的做法,也不能說(shuō)完全沒有道理。但嚴(yán)格來(lái)講,那個(gè)時(shí)候樂戶制度尚未正式出現(xiàn),還是把他們稱為“樂家、音家、倡家”更準(zhǔn)確一些。樂家、音家、倡家不但與樂戶存在相似之處,而且也逐步成為后世樂雜戶、樂戶的骨干組成部分,這與外交、戰(zhàn)爭(zhēng)和掠奪有很大關(guān)系,舉《魏書•樂志》所載的幾條史料為證:永嘉已下,海內(nèi)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于關(guān)右。苻堅(jiān)既敗,長(zhǎng)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zhǎng)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內(nèi)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jìn)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弦管具矣。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jīng)鲋荩闷淞嫒恕⑵鞣穸嬷3酰咦嬗懟础h,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可以肯定,漢魏以來(lái)的樂家、音家、倡家由于掌握著世代傳承的特殊技能,所以成了政治外交中的饋贈(zèng)佳品,更是戰(zhàn)勝國(guó)爭(zhēng)相掠奪、羅致的對(duì)象。當(dāng)北方政權(quán)普遍推行雜戶制度以后,他們很自然會(huì)被進(jìn)一步編入雜戶民中。而當(dāng)樂戶制度正式出現(xiàn)以后,憑藉其世代掌握的表演伎藝,樂家、音家、倡家也必然會(huì)成為樂戶中的骨干組成部分。因此,若要追溯樂戶更早淵源的話,這確實(shí)是一條頗為重要的線索。當(dāng)然,這些戶民雖可視為東魏以來(lái)樂戶的淵源之一,但二者的區(qū)別也十分明顯,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第一,當(dāng)時(shí)的政府尚未將樂家等列入專門的樂籍,對(duì)此前文已有闡述,毋庸多敘;第二,樂家、音家、倡家的社會(huì)地位與樂戶也有所不同,可舉以下史料為證:《漢書•外戚傳》:孝武衛(wèi)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hào)曰衛(wèi)氏,出平陽(yáng)侯邑。子夫?yàn)槠疥?yáng)主謳者。《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本長(zhǎng)安宮人。初生時(shí),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yǎng)之。及壯,屬陽(yáng)阿主家,學(xué)歌舞,號(hào)曰飛燕。《三國(guó)志•后妃傳》:武宣卞皇后,瑯玡開陽(yáng)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從上引來(lái)看,漢魏的“倡家”可以嫁入王室,甚至有成為皇后者,這就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倡家的社會(huì)身份并不太低,而且在戶籍上似乎也沒有嚴(yán)格的限制。而據(jù)《唐會(huì)要》所載武德四年(621)九月二十九日“詔”云:太常樂人,本因罪譴,沒入官者,藝比伶官。前代以來(lái),轉(zhuǎn)相承襲,或有衣冠繼緒,公卿子孫,一沾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絕于士庶,名籍異于編氓。大恥深疵,良可矜愍。這篇詔書說(shuō)明,樂戶職業(yè)不但世代不能變改,而且社會(huì)地位極低,故為士庶所深恥,連婚姻也必須是同類戶民自相為配。在這種條件下,要嫁入王室甚至成為皇后幾乎不太可能。即使要嫁給一般的平民或士人,也須先行脫籍,難度也相當(dāng)大。由此可見,樂戶的地位明顯要低于漢魏以來(lái)的樂家、音家、倡家,所以二者雖存在一定的源流關(guān)系,卻千萬(wàn)不要混為一談。最后還有一點(diǎn)須要澄清,即早期樂戶的社會(huì)地位雖然比較低,但仍不能等同于奴隸。據(jù)《大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記載:“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隋唐時(shí)期,一部分樂戶是番上服役的“番戶”,一部分樂戶則是太常“雜戶”,但無(wú)論如何都屬“戶民”身份,雖比良人即一般平民百姓地位要低,卻比“官奴婢”要高出一等或兩等,所以才有奴婢豁免為番戶、雜戶之說(shuō)。近世某些著述直接將樂戶等同于奴隸,這是欠妥的,特此提請(qǐng)注意。
二、樂戶中心的轉(zhuǎn)移
早期樂戶研究中尚有一個(gè)問題頗為值得關(guān)注,亦即樂戶中心的形成、發(fā)展與轉(zhuǎn)移。現(xiàn)今研究樂戶的著述,往往只論及近古(宋金以來(lái))樂戶最為集中的山西一地,這是不夠全面的,也不足以反映樂戶發(fā)展的完整歷史,以下接著探討。如前所述,樂戶制度是北魏政權(quán)遷鄴以后才正式出現(xiàn)的,“配為樂戶”的法令最初乃針對(duì)京畿群盜而制定。由于鄴都一帶盜賊頗多,稍涉末罪就有配為樂戶的可能,遂為樂戶人口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亦復(fù)因此,鄴都很自然地成為了樂戶繁聚的中心,前引《通典》提到“相州多樂戶”,便是一個(gè)很好的證明。當(dāng)然,還有其他一些促成因素,比如陳寅恪先生就曾指出:蓋北魏洛陽(yáng)既有萬(wàn)余家之歸化西域胡人居住,其后東魏遷鄴,此類胡人當(dāng)亦隨之移徙,故北齊鄴都西域胡化尤其胡樂之盛必與此有關(guān)。否則齊周東西隔絕,若以與西域交通論,北周領(lǐng)土更為便利,不應(yīng)北齊宮廷胡小兒如是之多,為政治上一大勢(shì)力,而西域文化如音樂之類北齊如是之盛,遂至隋代猶承其遺風(fēng)也。故隋之胡樂大半受之北齊,而北齊鄴都之胡人胡樂又從北魏洛陽(yáng)轉(zhuǎn)徙而來(lái),此為隋代胡樂大部分之系統(tǒng)淵源。陳先生的論述表明,鄴都樂戶的繁盛與“隨之轉(zhuǎn)徙”的“胡人胡樂”有密切關(guān)系,這些胡人胡樂也為這一“中心”的形成提供了人員和技術(shù)上的支持。直至隋唐時(shí)期,太常樂工中仍有不少是這些胡樂人的后裔,可見其勢(shì)力之龐大。由于南朝并未實(shí)施配沒為樂戶的制度,北周初年國(guó)力不及北齊,正致力于軍國(guó)建設(shè),也無(wú)暇專注樂戶的問題,所以北齊的鄴都實(shí)際上就是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樂戶繁聚之所。鄴都雖是樂戶制度正式出現(xiàn)以后的第一個(gè)樂戶中心,但隨著北周滅齊、隋并天下,它卻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那么這些樂戶將何去何從呢?據(jù)《隋書•音樂志》《隋書•裴蘊(yùn)傳》《新唐書•禮樂志》等分別記載:自漢至陳樂工,其大數(shù)不相踰越。及周并陳,各得其樂工,多為編戶。至(大業(yè))六年,(煬)帝乃大括魏、齊、周、陳樂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關(guān)中為坊置之,其數(shù)益多前代。
蘊(yùn)揣知(煬)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yōu)百戲者,皆直太常。唐之盛時(shí),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樂]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hào)“音聲人”,至數(shù)萬(wàn)人。從上引史料中的前兩條不難看出,這些樂戶及其子弟被隋煬帝所搜括,并集中在“關(guān)中”,“為坊”以“置之”,被搜括者還包括南朝和北周的“樂家子弟”,關(guān)中的樂戶中心毫無(wú)疑問就是長(zhǎng)安。這一點(diǎn)從第三條史料中也足以看出來(lái),因?yàn)樗逄茣r(shí)期的樂戶主要隸于太常的太樂署或鼓吹署,人數(shù)以萬(wàn)計(jì)。而作為中央禮樂機(jī)構(gòu)的太常寺,很明顯是設(shè)置在長(zhǎng)安城內(nèi)的。由此可知,到了隋唐時(shí)期長(zhǎng)安已經(jīng)取代鄴城而成為新的全國(guó)性樂戶繁聚之中心。這里有一點(diǎn)須要稍作補(bǔ)充。前文引《唐六典•都官郎中》時(shí)提到了“番戶”和“雜戶”這兩個(gè)概念,并指出它們均屬樂戶民,但在社會(huì)等級(jí)上略有區(qū)別,這一點(diǎn)還有《唐律疏議》所載可作補(bǔ)充說(shuō)明:議曰:工、樂者,工屬少府,樂屬太常,并不貫州縣。雜戶者,散屬諸司上下,前已釋訖。太常音聲人,謂在太常作樂者,元與工、樂不殊,俱是配隸之色,不屬州縣,唯屬太常,義寧以來(lái),得于州縣附貫,依舊太常上下,別名“太常音聲人”。⑥這則史料說(shuō)明,工戶統(tǒng)屬于少府,樂戶統(tǒng)屬于太常;⑦太常樂戶之中有一種是“雜戶”,“散屬”太常“諸司”,而且戶籍置于太常而不置于州縣,所以身份要稍高一些。另一部分太常樂戶的戶籍則置于州縣,采取番上服役的方式,亦即“依舊太常上下”。他們就是“番戶”,別名“太常音聲人”,比雜戶的身份要略低一些。但勿論如何,太常樂戶均為特殊的戶民而非奴隸,且均以長(zhǎng)安的太常寺為聚集之中心。到了唐玄宗時(shí)期,長(zhǎng)安依然是樂戶中心,而另一個(gè)中心也悄然誕生了,這與開元二年(714)玄宗設(shè)立教坊以“典俗樂”有極大關(guān)系。據(jù)史料記載,當(dāng)時(shí)一度出現(xiàn)了五個(gè)教坊,其中宮內(nèi)的教坊稱為“內(nèi)教坊”,地點(diǎn)設(shè)在蓬萊宮側(cè)。⑧宮外的教坊則稱為“外教坊”,共有四個(gè),其地點(diǎn)在《教坊記》中有明確記載: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成習(xí)。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
可見,當(dāng)時(shí)西京除內(nèi)教坊外,新置了左右二教坊,分別位于長(zhǎng)安的光宅、延政二坊。東京即洛陽(yáng),也新置了左、右二教坊,它們?nèi)课挥诼尻?yáng)的明義坊。教坊所典的俗樂,原本屬于太常,當(dāng)教坊分立以后,原本表演俗樂的太常樂戶遂改而隸于教坊。⑨復(fù)由于五教坊中有兩個(gè)設(shè)在東京,所以洛陽(yáng)也聚集了大批的樂戶,從而成為與西京并峙的又一個(gè)樂戶中心。那么唐皇朝為什么要在首都長(zhǎng)安以外的地方另設(shè)教坊呢?原來(lái),出于政治、經(jīng)濟(jì)等方面的原因,唐代帝王頻往東都,⑩而玄宗本人更曾五幸洛陽(yáng)。如果每次出行都帶上大批樂人、樂器會(huì)很不方便,于是干脆就在東都另置一套樂官、樂人以供娛樂,這恐怕就是洛陽(yáng)也置教坊的主要原因。輯訛輥如此一來(lái),也產(chǎn)生了樂戶制度出現(xiàn)以后的第三個(gè)樂戶繁聚中心。現(xiàn)在學(xué)界一提起樂戶,首先就會(huì)想到山西,但在早期樂戶發(fā)展史上,山西的地位根本無(wú)法和鄴都、長(zhǎng)安、洛陽(yáng)這三個(gè)中心相比。即使到了北宋初期,山西樂戶的地位也并不算突出,據(jù)《宋史•樂志》記載: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荊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zhí)藝之精者皆在籍中。可見,北宋初年為了設(shè)立教坊,朝廷曾廣泛羅致全國(guó)各地高水平的藝人,山西太原雖亦有“執(zhí)藝之精者”進(jìn)入教坊,但只有“十九人”,遠(yuǎn)較西川、荊南等地為少。這就足以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性的樂戶中心肯定還輪不到山西。不過,一些歷史的原因卻為山西日后成為樂戶中心奠定了基礎(chǔ),其中起到關(guān)鍵性作用的當(dāng)是后唐莊宗的出現(xiàn)。據(jù)歷史記載,山西是后唐立國(guó)的主要根據(jù)地,后唐莊宗最初稱王的地點(diǎn)即在太原;輰訛輥同光元年(923),莊宗于魏州即皇帝位,遂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zhèn)州為北都。輱訛輥更為重要的是,這位莊宗最喜歡俳優(yōu),據(jù)《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稱:(后唐)莊宗既好俳優(yōu),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制”者皆是也。……是時(shí),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倖,四方藩鎮(zhèn),貨賂交行。引文提及的俳優(yōu)、伶人,都是教坊中典俗樂的樂戶民。由于皇帝的喜好,當(dāng)時(shí)伶人的勢(shì)力非常之大,縉紳、群臣亦“莫敢出氣”,其影響自然也非常之大,以至于“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后唐莊宗還因此而成為了傳說(shuō)中戲劇的祖師爺。可以說(shuō),山西日后之所以能成為樂戶中心,就是以此為開端的。但研究早期樂戶發(fā)展歷史則必須承認(rèn),北宋以前其地位還不足以和鄴都、長(zhǎng)安、洛陽(yáng)相提并論,有學(xué)者將山西視為“樂戶的主要發(fā)源地”,恐怕是不夠客觀的。
三、小結(jié)
以上對(duì)早期樂戶發(fā)展史上的若干問題作了一些考析。概而言之,樂戶制度的正式出現(xiàn)是在東魏而非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的北魏,它是從北魏雜戶制度中發(fā)展出來(lái)的。而在北魏之前,一直有大量樂家、音家、倡家的存在,他們無(wú)論在功能抑或戶民結(jié)構(gòu)上都與后來(lái)的樂戶有相似之處,可視為樂戶產(chǎn)生的淵源之一。當(dāng)然,他們與樂戶的區(qū)別也相當(dāng)明顯,特別是在社會(huì)地位方面。此外,北宋以前曾出現(xiàn)過幾個(gè)全國(guó)性的樂戶中心,東魏、北齊時(shí)期的鄴都是第一個(gè),隋唐時(shí)期的長(zhǎng)安是第二個(gè),唐玄宗以來(lái)的洛陽(yáng)是第三個(gè),出現(xiàn)的原因雖各有不同,但均為樂戶的集中、繁聚之所。至于目前樂戶研究界最重視的山西,從五代開始就有不少的樂戶存在,但在當(dāng)時(shí)其地位尚無(wú)法與上述的三個(gè)中心相提并論。總之,樂戶制度正式出現(xiàn)的時(shí)間、樂戶與漢魏以來(lái)樂家、音家、倡家的關(guān)系、樂戶中心的產(chǎn)生和轉(zhuǎn)移等問題,是早期樂戶發(fā)展史上較為重要但又較少獲得學(xué)界關(guān)注的幾個(gè)問題,若能將其考析清楚,對(duì)于宋金以后樂戶發(fā)展歷史的研究也有較高參考價(jià)值,因?yàn)樵慈舨磺澹淞饕搽y于考究。只是筆者學(xué)識(shí)有限,所述未必確當(dāng),還望方家教正。
作者:黎國(guó)韜單位:中山大學(xué)中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研究中心教授
- 上一篇:模糊控制工程論文范文
- 下一篇:元明清戲曲的審美取向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