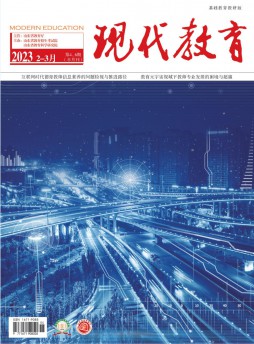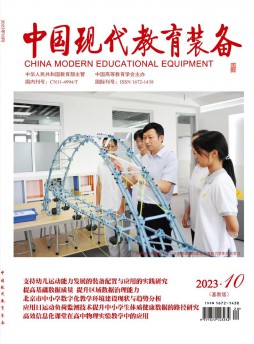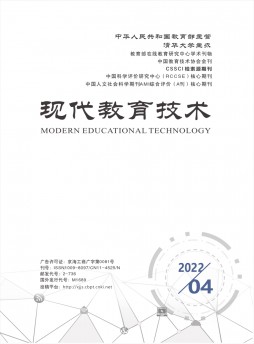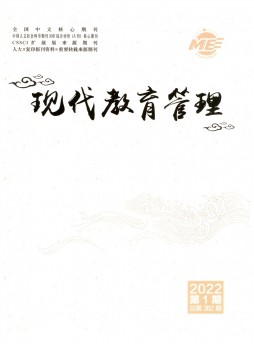現(xiàn)代教育思想的哲學(xué)意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現(xiàn)代教育思想的哲學(xué)意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認(rèn)識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因此簡單地說,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關(guān)系實際上就是改造與被改造的關(guān)系,即以主體在實踐中所獲得的規(guī)律性知識為基礎(chǔ),按照主體自身的需要和要求對客體進(jìn)行加工和改造。人類之所以能夠認(rèn)識世界,是因為人類具有理性,人類運用自身的理性去認(rèn)識對象化的客觀世界并能發(fā)現(xiàn)隱含于其中的客觀規(guī)律,從而形成對客觀世界即客體的相對確定性和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由此可以看出,在這種二元對立的哲學(xué)中,人與自然彼此對立,人們把自然當(dāng)作物質(zhì)實體加以改造,因而作為世界本源的自然被實體的自然物所取代,哲學(xué)研究的對象就不再指向自然界,而是指向物質(zhì)實體。這樣,主客二元論哲學(xué)的目標(biāo)就不再是探討人類的存在意義,也不再討論人類的道德善惡問題,更不以建構(gòu)人類理想的精神家園為宗旨,在這一哲學(xué)語境中,人們不再追問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等人性問題,而以研究外在的、經(jīng)驗的、客觀的、機械的物質(zhì)世界為己任,人的工具理性作用受到極度重視,當(dāng)人的工具理性發(fā)揮到極致時,必將物極必反地導(dǎo)致人類價值理性的喪失和主體性沉淪,結(jié)果人被異化了。第一,價值理性的喪失。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理性逐步代替愚昧,整個近代西方社會展現(xiàn)出了普遍的理性精神和人文關(guān)懷,這既包括現(xiàn)階段仍然流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形而上學(xué)的理想觀念,也包括人們對實證主義科學(xué)的向往。而且,隨著主客二元論思想成為人們認(rèn)識事物的指導(dǎo)思想,人們對認(rèn)識主體能力的關(guān)注使人的工具理性作用受到盲目推崇,人們越來越感受到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是人們改造世界和獲取真理的唯一方法,他們對自然科學(xué)充滿幻想,相信唯有自然科學(xué)才能給人類帶來美好幸福的現(xiàn)實生活。而事實上,自近代以來,科學(xué)技術(shù)已確實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并顯示出極其巨大的作用。這主要體現(xiàn)在:首先,人類能夠利用科學(xué)技術(shù)開發(fā)、改造和征服自然并向自然無限地攫取人類所需要的一切生產(chǎn)和生活資料,為人類創(chuàng)造出高度發(fā)達(dá)的物質(zhì)文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在自然面前是自由的。其次,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勞動工具的更新,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chǎn)力,改變了社會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導(dǎo)致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變革和整個社會的全面進(jìn)步,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給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已是有目共睹。再次,科學(xué)技術(shù)的迅速發(fā)展促進(jìn)了社會分工,使腦力勞動從體力勞動中分離出來,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在進(jìn)行知識生產(chǎn)過程中推動了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發(fā)展。總之,科學(xué)技術(shù)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領(lǐng)域的方方面面,使社會日益走向科學(xué)化,在這一過程中,科學(xué)也被日益社會化了。
然而,科學(xué)技術(shù)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推動人類社會進(jìn)步的同時,也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界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在社會生產(chǎn)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機械化、自動化、系統(tǒng)化的工作流程,在這種工作流程中,不是人控制和支配機器,而是機器大生產(chǎn)在無形地支配和控制人,人越來越變得機械和被動。在自動化生產(chǎn)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被扼殺,人的各種潛能被埋沒,人的完善性被肢解,人日益成為片面性和“單向度”的人,這容易造成人的精神性危機。如是觀之,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已經(jīng)不再是一種使人獲得解放和身心自由的手段和力量,相反地,它卻成了現(xiàn)代人在高科技條件下被奴役、被壓迫的根源。高科技條件下產(chǎn)生的一個社會后果是人的心態(tài)失衡和精神分裂,于是我們可以這樣斷定:后現(xiàn)代是人生意義和人生價值處于迷茫的時代。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軌跡告訴我們,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在增強人們對自然的控制力、提升人們的自由度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的自由,變成了統(tǒng)治人、支配人的超人的異己力量。第二,主體性的沉淪。從古希臘哲學(xué)家巴門尼德開創(chuàng)本體論之后,西方哲學(xué)一直延續(xù)著本體論研究傳統(tǒng),而笛卡爾的二元論哲學(xué)體系使西方哲學(xué)的研究發(fā)生了轉(zhuǎn)向,即由本體論轉(zhuǎn)入認(rèn)識論,從而揭開了高揚人的主體性的序幕。但是,如前所述,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礎(chǔ)上的主體性強調(diào)的是主體對客體的認(rèn)識、征服和占有,其實質(zhì)是把主體自身的意志、愿望和目的強加給客體,使客體轉(zhuǎn)化為主體并為自身所利用。這種認(rèn)識論上的主客二分造成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身的對立和分離,從而導(dǎo)致人對自然的無限掠奪和生態(tài)危機的出現(xiàn),導(dǎo)致民族主義、強權(quán)政治的發(fā)生以及世界范圍內(nèi)的歧視和戰(zhàn)爭,導(dǎo)致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和信任危機。
在主客二分論者看來,認(rèn)識論上主體和客體的分立以及二者在認(rèn)識關(guān)系上的發(fā)展,是有目的、有意識、有理性的人發(fā)揮其主體能動作用的產(chǎn)物,與客觀物質(zhì)世界的自然發(fā)展毫無關(guān)系。所以,主客體關(guān)系的確立,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因為人首先把自己看作主體,把與之對立的自然看作客體,這本身就是對自我價值的優(yōu)先肯定,是典型的“人本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通過這種對自我的優(yōu)先肯定,人把自己作為主體。表現(xiàn)在對自然的關(guān)系上,人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人變成了能改造自然的技術(shù)化的人。所謂“技術(shù)化”,是指人類有能力利用自然科學(xué)征服和改造自然,有能力發(fā)明各種勞動工具克服自然,使人能充分利用自然,人的最大作用就是不停地改進(jìn)科學(xué)技術(shù),達(dá)到控制自然和地球上一切生命體的目的。這種強化個人主體性所帶來的社會后果已在上文所提及。表現(xiàn)在社會制度方面,人不是現(xiàn)實的人,而變成了抽象的人。人的技術(shù)化表現(xiàn)在社會領(lǐng)域,就是社會制度的理性化,即以科學(xué)技術(shù)為手段管理社會,把人當(dāng)作一個可供計算的單元,以實現(xiàn)社會的“可計算性”管理。對此,我們可以作一個形象的比喻,隨著科技的社會化,整個社會就像一臺機器,而人只不過是這臺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在機器轉(zhuǎn)動過程中人沒有了自由,人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在這種理性化的過程中,人被理性化為毫無個性和自由的抽象的人。因此,無論是在自然層面上的技術(shù)化還是在社會層面上的抽象化,其根源都是由社會分工所致。社會分工的專業(yè)化使人變成了片面化的個體,人不再被認(rèn)為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因此,笛卡爾二元論哲學(xué)對主體性的弘揚,其最終結(jié)果必然走向反面,導(dǎo)致主體性的沉淪,人的自由反而受到限制。在二元論哲學(xué)模式下,人不是被看作全面發(fā)展的人,而是被看作具有某種工具性質(zhì)的人,即人能夠做什么、有什么用處,從而按實際用途和工具理性對人進(jìn)行分門別類。這種對人的畸形理解,必然導(dǎo)致人最終走向異化。這正如曼弗雷德•弗蘭克所言:“自啟蒙運動始,人的主體性便被精神科學(xué)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啟蒙運動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主體性的發(fā)揚和弘揚。然而,二百多年來的社會狀況和人的實踐日益證明……事實上真正的主體性并不存在,主體始終處在被統(tǒng)治、被禁錮的狀態(tài)。”
懷特海指出,隨著人的自由的喪失,現(xiàn)代教育活動也呈現(xiàn)出主體和客體二元劃分的趨勢。這種二元論思想在教育過程中的體現(xiàn),即是認(rèn)為教育只有一個主體即教育者,教育對象即受教育者是客體,教育活動就是一個對象化和客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育的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養(yǎng)成為對社會和國家有用的人才,使教育客體具有工具性質(zhì)。這種對教育的價值定位,拒斥了教育的本體價值,導(dǎo)致了教育的異化。直接地說,這種異化了的教育,其目的不是把受教育者培養(yǎng)成全面發(fā)展的人,而是把人培養(yǎng)成為專業(yè)化的、片面性的、具有某種工具性的單向度的人。第一,教育的主客體關(guān)系異化。在二元論哲學(xué)思維模式下,教育過程被看作是一個“主體—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這一過程只承認(rèn)一個主體即教育者。教育是教育者作用于受教育者的過程,或者說,教育是一個以一定的內(nèi)容為中介,由教育者對受教育者施加影響的過程。在這一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變成了教育的對象即客體,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就成了一種“對象化關(guān)系”或“客體化”的關(guān)系。在對象化活動中,主體用自己的目的、意識等人的本質(zhì)力量作用于客體,以便塑造和改變客體。這種對象化活動的目的在于把主體的意志強加給客體并改造客體,客體被認(rèn)為是滿足主體需求的對象,因此,教育活動中的主客體關(guān)系就演變成了一種“目的—對象”的關(guān)系。這樣一來,教育過程實質(zhì)上就是一種教育主體訓(xùn)練和控制教育客體的過程,教育主體和客體之間形成了一種控制與被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中,教育活動就表現(xiàn)為規(guī)范化、規(guī)律化、科學(xué)化的模式,于是學(xué)校不再是塑造和培養(yǎng)健全人格的搖籃。相反,它變成了一個政治性機關(guān)、經(jīng)濟(jì)式組織,追求的是效益,注重的是科學(xué)化甚至是行政化管理,嚴(yán)重窒息了教育對象的主體性,扼殺了受教育者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懷特海認(rèn)為,教育培養(yǎng)人是一個極為復(fù)雜的題目,對此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了解。在懷特海看來,由于受教育者是“活”的,所以必須把激發(fā)和引導(dǎo)學(xué)生的自我發(fā)展貫穿于教育過程的始終。對教師的決定性要求也必須是:他們是思想活躍的“活”人,而不允許是照搬書本的被考試牽著走的機器。他尖銳地批判當(dāng)時的學(xué)校“被無活力的概念沉沉地壓住了”,而這種教育不僅無用,而且有害,它把“人類束縛住了”。懷特海強調(diào),“我們是在處理人的心智,而不是處理死的物質(zhì)”,心智絕非被動的,把人當(dāng)做工具是教育理論中“最致命、最錯誤、最危險的概念之一”。而利用幾本書或種種輔導(dǎo)材料,幫助學(xué)生把校外考試中可能出現(xiàn)的題目背熟,借以達(dá)到獲取學(xué)歷或某種資格的目的,則代表了一條“罪惡道路”。懷特海認(rèn)為,教育的本質(zhì)是一種教人們掌握如何運用知識的藝術(shù),教育的核心問題正是如何“使知識充滿活力和防止知識僵化”。
第二,教育的專業(yè)化。在教育的主客體關(guān)系異化之影響下,受教育者為了實現(xiàn)自身的利益,比如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愿望和物質(zhì)利益的滿足,他們都自覺地認(rèn)可異化了的教育模式并被動地接受教育。受教育者這種自身利益的驅(qū)動是教育專業(yè)化的內(nèi)在動力。無可否認(rèn),近代以來教育的專業(yè)化促使人類分工更趨完善化和細(xì)化,社會眾多專業(yè)領(lǐng)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基因工程、太空飛行、火箭上天等,這種由教育專業(yè)化而引起的36社會分工,在很長一段時期內(nèi)推動社會取得了革命性的進(jìn)步,因此教育專業(yè)化一度受到人們的贊賞。今天,人們依然采取填鴨般的教學(xué)方式,將那些形而下之“器”的東西灌輸給學(xué)生,學(xué)生成了記憶的機器。面對這種情況,懷特海極力主張的解決方法是:“要根除各科目之間那種致命的分離狀況,因為它扼殺了現(xiàn)代課程的生命力。教育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五彩繽紛的生活。”在教育專業(yè)化的影響下,文藝復(fù)興以來所提倡的人文主義精神日益被消解,教育對人的本真存在之“道”一再冷落,這無疑阻擋了學(xué)生通向自由精神的道路。可以說,當(dāng)代教育忽視了這樣一個問題———人的自身價值與存在。在教育過程中,人成為推動社會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工具,教育成了把人塑造成工具的活動,從而忽視了人自身的發(fā)展。然而,個人并不是工具,他除了有專門才能貢獻(xiàn)人類外,他還必須首先是一個健全的人,即對世界、社會有他自己的認(rèn)識、看法,對已有的人類精神文化成果———文學(xué)、美學(xué)、音樂都能欣賞的身心和諧健康的人。教育專業(yè)化的致命弱點是過分偏重于對知識進(jìn)行理智性、要領(lǐng)性、公式化的理解,而沒有對現(xiàn)實世界中人的價值理性作全面透徹的思考。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人出現(xiàn)了畸形化發(fā)展態(tài)勢。這種人性的異化,潛伏著人類未來發(fā)展的致命危機。面對這種越演越烈的專業(yè)化趨勢,懷特海指出:“這種情形埋伏著一個危機。它將產(chǎn)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個專業(yè)都將進(jìn)步,但它卻只能在自己那一個角落里進(jìn)步。在思想上限于一隅,在一生中便只會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這個角落將成為人們跨過原野的障礙,而抽象概念所概括的東西,是沒有人再加以注意的了。但任何抽象角落都是不足以包括人生的。”
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我們不但要教給學(xué)生基本知識、基本技能,還要把學(xué)生培養(yǎng)成為具有清醒頭腦、精神高尚、能辨別是非并具有一定審美判斷的人。“教育所要傳授的是對思想的力量、思想的美、思想的條理的一種深刻的認(rèn)識,以及一種特殊的知識,這種知識與知識掌握者的生活有著特別的關(guān)系。”懷特海說:“培養(yǎng)一個兒童如何思維,最重要的是必須注意我所說的那種‘呆滯的思想’———這種思想僅為大腦所接受卻不加以利用、或不進(jìn)行檢驗,或沒有與其他新穎的思想有機地融為一體。……在教育發(fā)展史上,最引人注意的現(xiàn)象是,一些學(xué)校在某個時期充滿天才創(chuàng)造的活力,后來卻迂腐而墨守成規(guī)。其原因就在于,這些學(xué)校深受這種呆滯思想的束縛和影響。囿于這種思想的教育不僅毫無價值,還極其有害。……使人類走向偉大崇高的每一次知識革命無不是對這種呆滯思想的激烈反抗。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對人類的心理特點茫然無知,于是某種教育體制自身形成的僵化思想重又束縛了人類。”可見,在懷特海看來,教育的真正價值在于不斷引導(dǎo)人類從無知、愚昧和盲從中解放出來,在于不斷地超越人類各種當(dāng)下的、特殊的生存狀態(tài),達(dá)到人的完善。第三,教育的功利化。教育的功利化主要表現(xiàn)為國家功利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注重人的有用性和教育的工具性。那么,究竟什么是國家功利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簡單地說,國家功利主義就是國家在制定教育方針和政策時,優(yōu)先考慮教育的經(jīng)濟(jì)和政治功能,追求教育對社會物質(zhì)利益、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和政治需要的滿足,強調(diào)按照社會對人才的標(biāo)準(zhǔn)化、規(guī)范化和職業(yè)化的要求來培養(yǎng)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個人功利主義則把教育作為謀求個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把教育視為個人工作流動、職位升遷的學(xué)歷資本,接受教育不再被看作學(xué)業(yè)理想、陶冶性情、追求人生價值和意義、提升善性和道德的內(nèi)在人性要求,教育成為追求實實在在的名利的手段。由此,無論是國家功利主義教育觀還是個人功利主義教育觀,其教育的價值取向都是使教育實現(xiàn)工具性,而摒棄教育本體價值及人的全面發(fā)展,這是對教育作用的本末倒置。
正如有學(xué)者所指出的:今日,大學(xué)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務(wù)站”了。社會要什么,大學(xué)就給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學(xué)就給什么;市場要什么,大學(xué)就給什么。大學(xué)不知不覺中社會化了,政治化了,市場化了。大學(xué)與外界之間的一道有形或無形的圍墻已被拆除了。在這種情況下,大學(xué)已非獨立研究學(xué)問之地,而成了即產(chǎn)即用的知識工廠,大學(xué)與社會之間一個保持清凈思維的距離也消失了。我們在這里并不否認(rèn)教育應(yīng)該為社會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服務(wù),但是為社會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服務(wù)并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換言之,教育并不是完全地直接為社會服務(wù),而是通過培養(yǎng)受過良好教育的全面發(fā)展的人來實現(xiàn)教育的社會功能,推動社會發(fā)展。因此,如果直接地把教育與政治或經(jīng)濟(jì)目的掛鉤,肯定是錯誤的。因為教育的真正價值在于使人成為全面發(fā)展的自由的人,而不是成為某種工具性的人。就人的發(fā)展趨向來說,人首先必須是人,其次才是具有某方面技能的人。
換言之,人之為人在于其善性、道德和精神,而不在于其知識、技術(shù)和專長的多寡。一句話,教育絕不僅僅是教師傳授知識,學(xué)生記憶知識,而應(yīng)當(dāng)把啟發(fā)學(xué)生的視野和激發(fā)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力置于重要的位置。要想開發(fā)學(xué)生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首先就應(yīng)當(dāng)擺脫眼前的狹隘的功利目的的束縛,提供給學(xué)生自由的學(xué)術(shù)空氣和足夠的休閑時間。教育應(yīng)當(dāng)關(guān)心國家、社會以及人類的長遠(yuǎn)利益,以實現(xiàn)人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為目標(biāo)。懷特海說:“理想的逐漸消失可悲地證明了人類的努力遭受了挫折。在古代的學(xué)園中,哲學(xué)家們渴望傳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學(xué)里,我們卑微的目的卻是教授各種科目。從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現(xiàn)代人獲得各個科目的書本知識,這標(biāo)志著在漫長的時間里教育的失敗。我并不堅持認(rèn)為,在教育實踐中古人比我們更成功。……我只想說明,當(dāng)歐洲文明的曙光初露時,人類最初是懷著種種完美的理想,這些理想本該促進(jìn)教育;但漸漸地,我們的理想為了與實踐保持一致而變得淡漠了。”“文化是思想的活動,是對美和高尚情感的接受。支離破碎的信息或知識與文化毫不相干。一個人僅僅見多識廣,他不過是這個世界上最無用而令人討厭的人。我們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專門知識的人才。專業(yè)知識為他們奠定起步的基礎(chǔ),而文化則像哲學(xué)和藝術(shù)一樣將他們引向深奧高遠(yuǎn)之境。”
懷特海生活在19世紀(jì)至20世紀(jì)上半葉的英國與美國,此時的歐美國家早已駛?cè)肓爽F(xiàn)代化的軌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別是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必定對懷特海的思想產(chǎn)生重大而持久的影響。著名英國歷史學(xué)家霍布斯姆曾對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作了這樣的描述:“這是信仰經(jīng)濟(jì)發(fā)展依靠私營企業(yè)競爭、從最便宜的市場上采購一切(包括勞動力),并以最高價格出售一切的社會的勝利。建立在這個原則基礎(chǔ)上的經(jīng)濟(jì),自然是要依靠資產(chǎn)階級來主宰沉浮,資產(chǎn)階級的活力、價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與其地位相當(dāng)?shù)某潭取⒉⒗卫伪3制鋬?yōu)勢。依此為基礎(chǔ)的經(jīng)濟(jì),據(jù)信不僅能夠創(chuàng)造豐富而且分配適當(dāng)?shù)奈镔|(zhì)財富,還能創(chuàng)造日新月異的人類機遇,擺脫迷信偏見,講究理性,促進(jìn)科學(xué)和藝術(shù)發(fā)展。總之,創(chuàng)造一個物質(zhì)和倫理道德不斷進(jìn)步、加速前進(jìn)的世界。在私有企業(yè)任意發(fā)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無幾的障礙均將一掃而光。……不過關(guān)于這點有個限度:得保證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秩序,排斥資產(chǎn)階級被推翻的危險。”
對此,懷特海深有同感,他說:“19世紀(jì)是一個文明的進(jìn)步時代———它是人道主義的、科學(xué)的、工業(yè)的、文學(xué)的、政治的。但是最終,它把自己耗盡了。大戰(zhàn)(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轟隆聲標(biāo)志著它的結(jié)束,而且標(biāo)志著人類生活決定性地轉(zhuǎn)入某種迄今尚未充分了解的新的方向。”因此,這個表面看來十分合理的時代實際上卻并不那么合理。狄更斯在《雙城記》一開始那段著名的描述是這個時代最好的寫照:“那是最昌明的時代,那是最衰微的時代;那是理智開化的歲月,那是混沌蒙昧的歲月;那是信仰篤誠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陽光燦爛的季節(jié),那是徹夜晦暗的季節(jié);那是欣欣向榮的春天,那是死氣沉沉的冬天;我們眼前無所不有,我們眼前一無所有,我們都徑直奔向天堂,我們都徑直奔向另一條路。”極端相反的東西,在這個時代同時并存。例如,在工具理性日益控制一切的同時,社會的非理性也日益明顯。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并沒有導(dǎo)致民主的同步發(fā)展,相反,市場的專橫已經(jīng)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人被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系統(tǒng)所支配,日益淪為無足輕重的齒輪和螺絲釘。幸福只是個人物質(zhì)欲望的滿足,而自由只是這種滿足的不受干擾。虛無主義成了現(xiàn)代文化的標(biāo)志性特征。正是在現(xiàn)代,西方文化的前提發(fā)生了根本動搖,西方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而反思危機和解決危機則成了不少現(xiàn)代思想家的工作目的和動力。
絕大多數(shù)思想家都把現(xiàn)代性危機理解為精神危機和文化危機,因而試圖在西方文化的前提和基礎(chǔ)上找到危機的根源,然而,懷特海卻從分析西方近代哲學(xué)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和問題出發(fā),對現(xiàn)代社會的種種弊端特別是現(xiàn)代人自由的喪失和教育異化進(jìn)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懷特海看來,現(xiàn)代人自由的喪失和教育異化都與笛卡爾開創(chuàng)的近代西方哲學(xué)主客二元的思維方式密不可分。懷特海對現(xiàn)代教育的內(nèi)涵與本質(zhì)屬性有著深刻的理解,他的上述見解對于今天泛濫成災(zāi)的應(yīng)試教育,對于忽視人文思想的過分技術(shù)化的教育,對于浮淺的急功近利的物質(zhì)生產(chǎn)至上觀念,都是有效的清醒劑。
作者:楊芳陽黔花單位:貴州師范大學(xué)歷史與政治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