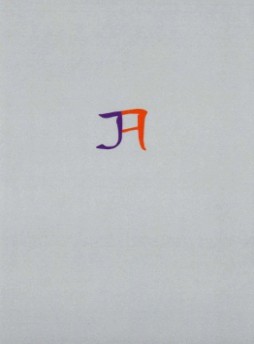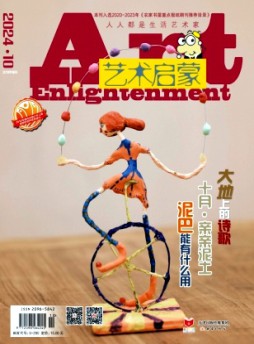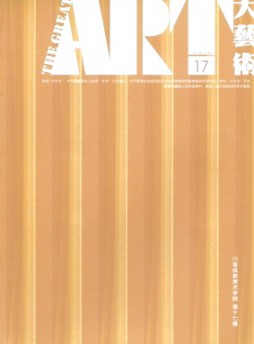藝術(shù)的跨文化研究史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藝術(shù)的跨文化研究史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民族藝術(shù)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1900年左右的德國藝術(shù)學(xué)以及相關(guān)研究
當(dāng)代某些對全球藝術(shù)研究方法感興趣的學(xué)者,已開始致力于表明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是多么富有前景。馬利特•哈爾伯特斯瑪(MarliteHalbertsma)和普菲斯特爾(UlrichPfisterer)對19世紀(jì)80年代到20世紀(jì)30年代德語世界藝術(shù)研究的世界性發(fā)展進(jìn)行了分析。普菲斯特爾指出,整個(gè)世界藝術(shù)的開放性尤其被初期的藝術(shù)學(xué)者所提升,這使其區(qū)別于更為傳統(tǒng)的歐洲藝術(shù)學(xué)。他指出兩個(gè)領(lǐng)域的知識論辯是以19世紀(jì)末期藝術(shù)研究在學(xué)術(shù)體制中爭得一席之地為背景的。他還指出,將藝術(shù)作為一種世界現(xiàn)象加以研究,得益于當(dāng)代兩門學(xué)科的發(fā)展。心理學(xué)尤其是民族心理學(xué),其研究者假定人類心理的一致性,而人類學(xué)的學(xué)生堅(jiān)持同樣的原則,即“人類心理的一致性”,人類學(xué)的跨文化比較研究,使其認(rèn)識到人類普遍存在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現(xiàn)象。從全球性角度研究藝術(shù)的觀念,盡管催生了些許有趣的著作,引發(fā)了相當(dāng)?shù)墓娕d趣,然而它在德國學(xué)界卻最終沒有開花結(jié)果。普菲斯特爾提到了諸多相關(guān)原因來解釋這種失敗,包括學(xué)術(shù)興趣的轉(zhuǎn)移,德國民族主義的興起,1933年納粹的上臺(tái),他們對雅利安人種的觀念,及其文化優(yōu)越感。他觀察到,二戰(zhàn)以后“,德國藝術(shù)史家逃避曾經(jīng)的研究。因之,世界藝術(shù)的話題從藝術(shù)史的課題中刪掉了”。更糟的是,從全球視角對藝術(shù)的探討“在今天已被徹底遺忘,因此有必要重拾話題”③。德語學(xué)界對世界藝術(shù)的遺忘,以及對此前所做的藝術(shù)的跨文化研究的集體漠視,當(dāng)然令人遺憾。不過與此同時(shí),這種遺忘在學(xué)術(shù)史上具有合法化的特點(diǎn),值得引起注意。
1900年代前后,德語學(xué)界并非首次在藝術(shù)研究中應(yīng)用跨文化方法。例如,19世紀(jì)末期的一位德國學(xué)者就已致力于提升不同時(shí)間和不同地域的藝術(shù)知識。恩斯特•格羅塞在1894年出版了《藝術(shù)的起源》,在該書前兩章,他試圖建立一種以全球藝術(shù)為基礎(chǔ)的藝術(shù)學(xué)。他對藝術(shù)的跨文化研究進(jìn)行了溯源,將其歷史追蹤到了在他之前的兩個(gè)世紀(jì)。格羅塞明確指出,杜博斯(JeanBaptisteDubos)的著作中已經(jīng)明確用到了跨文化視角,在他1719年出版的《詩與畫的批判性反思》一書中就參考了中國、印度、墨西哥和秘魯?shù)奈墨I(xiàn)。18世紀(jì)末期,赫爾德(JohannGottfriedHerder)又提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他認(rèn)為應(yīng)該關(guān)注歐洲之外的小型的無文字社會(huì)的藝術(shù),盡管他強(qiáng)調(diào)的是詩歌。④然而,這些前景不錯(cuò)的提議并沒有被后繼學(xué)者所踐行,格羅塞對此感到十分訝異和沮喪,他感到必須在19世紀(jì)末期的藝術(shù)研究中重拾全球性的視角。例如,他看到他的同時(shí)代人,藝術(shù)理論家兼比較文學(xué)家丹納(HippolyteTaine)“獲得的材料要比他的同時(shí)代人遠(yuǎn)為豐富,然而卻只關(guān)注歐洲文明民族的藝術(shù),好像其他地方?jīng)]有藝術(shù)似的。他的批評者痕涅昆(Hennequin),在這點(diǎn)上和他如出一轍”。正如格羅塞以更為概述性的術(shù)語所說:“杜博斯和赫爾德提出了人類學(xué)(即跨文化比較)方法,并沒有付諸實(shí)施,此事情有可原,因?yàn)樵谒麄兊臅r(shí)代并無這些材料。不過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如果一個(gè)藝術(shù)研究者不知道歐洲藝術(shù)并非唯一存在的藝術(shù),實(shí)在不可原諒。幾乎每座大城市都建立了人類學(xué)博物館,越來越多的文獻(xiàn)描寫和圖畫著國外蠻荒部落的藝術(shù)知識,而藝術(shù)科學(xué)卻對此視而不見。除非它自甘愚蒙,否則再也不能無視人類學(xué)材料了。”
此處引用格羅塞,亦能說明一些學(xué)者對歐洲之外的小型社會(huì)的視覺藝術(shù)發(fā)生興趣,要早于20世紀(jì)早期的歐洲先鋒藝術(shù)家發(fā)現(xiàn)“原始藝術(shù)”好多年。事實(shí)上,格羅塞不僅用了“藝術(shù)”這一標(biāo)簽指示“部落文化”中的特定物品,他還認(rèn)識到這些物品乃是審美情感的表達(dá)(這一觀點(diǎn)是幾位同代歐洲學(xué)者的共識)。這闡明了一個(gè)更大卻更明顯的觀點(diǎn):對藝術(shù)的跨文化研究學(xué)術(shù)史的探尋,或許會(huì)質(zhì)疑某些被通常接受的觀點(diǎn),甚至揭露一些學(xué)術(shù)神話。它需要考察原始文獻(xiàn),從而避免人們依賴二手文獻(xiàn),或似乎具有權(quán)威性,卻由于種種原因而被歪曲的觀點(diǎn)。格羅塞主要關(guān)注藝術(shù)理論,尤其是如何解釋世界范圍內(nèi)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多樣性,杜博斯和赫爾德明確提出了這一問題。格羅塞對藝術(shù)理論的關(guān)注,解釋了他何以沒有看到諸如弗朗茲•庫格勒(FranzKugler)的《藝術(shù)史手冊》(HandbuchderKunstgeschichte)。該書首版于1842年,一般認(rèn)為該書提供了首次針對視覺藝術(shù)的近乎全球性的調(diào)查。盡管該書是描述性的,庫格勒的全球視角還是值得在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史的框架內(nèi)進(jìn)行深入解讀。
二、基歇爾對建筑的跨文化比較
格羅塞所追溯的學(xué)術(shù)史強(qiáng)調(diào)跨文化藝術(shù)研究的理論性和分析性的方法,這使他本該關(guān)注杜博斯之前一位非常活躍的學(xué)者,即17世紀(jì)的博學(xué)家亞塔那修•基歇爾(AthanasiusKircher),一位在羅馬就職的耶穌會(huì)學(xué)者。①的確,基歇爾研究的是格羅塞并不關(guān)心的建筑。再者,基歇爾的比較研究分散于他的幾部著作之中,這些著作深具推測性,與杜博斯、赫爾德、格羅塞所強(qiáng)調(diào)的一樣,致力于解釋文化的一致性而非差異性。邁克爾•格林哈爾希(MichaelGreenhalgh)考察了基歇爾對建筑的比較研究。他指出,在1650至1675年間,基歇爾分析了諸多世界知名的建筑物,稱為“全球建筑理論”②。基歇爾似乎對在世界各地發(fā)現(xiàn)的金字塔式建筑情有獨(dú)鐘。基歇爾完全遵循一種圣經(jīng)的歷史框架,從大洪水時(shí)代之后,巴別塔是世界上第一座紀(jì)念性建筑物。他還認(rèn)為,巴別塔乃是世界上所有金字塔結(jié)構(gòu)的建筑物的源頭。基歇爾重建了自己的巴別塔,他認(rèn)為埃及人修筑金字塔是為了追隨巴比倫人。他不僅看到了風(fēng)格的類似,即錐形結(jié)構(gòu),還提到了功能的相同。他特別指出,巴別塔和埃及金字塔都是祭壇,都建在高高的平臺(tái)上。基歇爾認(rèn)為埃及的影響巨大而深入,中國的寶塔就是源出于此。這些多層建筑物具有同樣的宗教功能。基歇爾還比較了墨西哥的金字塔,亦將其看作高聳的圣壇。格林哈爾希沒有解釋基歇爾為什么沒有考慮到原初的巴比倫/埃及模式何以沒有散播到美洲。實(shí)際上,在基歇爾的時(shí)代,人們猜想美洲居民是從亞洲遷徙而來。格林哈爾希以一條學(xué)術(shù)史的注解結(jié)束了對基歇爾的建筑理論的探討。他提出,“他所采取的比較方法,盡管非常隨意,卻為凱呂斯(ComtedeCaylus)和昆西(QuatremèredeQuincy)的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學(xué)研究方法鋪了一條路”。這兩位生于18世紀(jì)和19世紀(jì)的學(xué)者,分別在著作中對歐洲之外的建筑進(jìn)行了比較研究。不過,格林哈爾希承認(rèn),基歇爾是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這兩位學(xué)者還有待證明。至今依然如此。
三、知識譜系學(xué)?
與此同時(shí),托馬斯•考夫曼(ThomasDaCostaKaufmann)讓我們注意到一位更早也更直接地受到基歇爾影響的人,即桑德拉特(JoachimvonSandrart)和他在1675—1679年間出版的《德意志學(xué)院》(TeutscheAcademie)。考夫曼將此研究描述為“以德語寫成的探討藝術(shù)史的首部重要著作”③。和經(jīng)常拿來與他作比的著名傳記作家瓦薩里與曼德爾不同,桑德拉特“在地理上拓展了他的關(guān)注對象”,以一定篇幅討論了中國藝術(shù),盡管懷有某些偏見,還對印度藝術(shù)作了簡短評論。除了對亞洲藝術(shù)的關(guān)注,桑德拉特還考察了埃及的象征主義,分析了古代近東的其他藝術(shù),就此引用了基歇爾的研究。就歐洲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的知識譜系而言,有人可能補(bǔ)充說考夫曼追溯了一條線索,這條線索從桑德拉特到他所謂的“關(guān)于建筑史的第一部著作”①,即費(fèi)舍(JohannBernhardFischervonEhrlach)1721年出版的《建筑簡史》(EntwurffeinerhistorischenAr-chitektur)。該書第三卷考察了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中國和暹羅的建筑,盡管主要是帶有解說的插圖。這些成果所依據(jù)的學(xué)術(shù)資源,引發(fā)我們更深入地探究其學(xué)術(shù)史。四、服裝之書:領(lǐng)略世界服飾前面兩節(jié)提到的著作盡管非常有限,并且具有選擇性,卻表明歐洲在1500年以后的地理文化視野愈見拓展。在16世紀(jì),歐洲人不僅發(fā)現(xiàn)了美洲,而且加強(qiáng)了與亞洲的貿(mào)易與交往,對亞洲視覺藝術(shù)的知識也大為增加。在基歇爾之前的100年,歐洲人心中已有一個(gè)開放的世界,這一世界在服裝之書中留下了蹤跡。這類出版物提供了一種跨越空間甚至?xí)r間的比較視野,很可能影響了基歇爾對世界上紀(jì)念性建筑物的分析。從當(dāng)代藝術(shù)研究的全球視野來看,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服裝書因其“世界藝術(shù)”的標(biāo)題而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例如,安特衛(wèi)普人布魯恩(AbrahamdeBruyn)的《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幾乎所有民族的服裝》(‘[ThedressofalmostallpeoplesofEurope,Asia,Africa,andAmerica’)(1581),威尼斯人維切里歐(CesareVecellio)的《全世界古今服飾》(Ancientandmoderncostumesofthewholeworld)。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服飾之書使我們提出了一個(gè)在當(dāng)前的學(xué)術(shù)語境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問題:在我們反思過去的研究時(shí),我們所關(guān)注的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史應(yīng)該搜羅哪些內(nèi)容?特別是,怎樣的藝術(shù)觀念指導(dǎo)我們梳理以往針對其他文化世界的特定的現(xiàn)象的研究?人類學(xué)視野下更為開闊的藝術(shù)觀,以及當(dāng)代的視覺文化研究,皆使我們不能將注意力僅限于繪畫、雕塑和建筑等傳統(tǒng)的藝術(shù)類型。我們應(yīng)該關(guān)注其他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視覺產(chǎn)品,如紡織品、個(gè)人飾物和服飾。我們應(yīng)該考察可能被忽視掉的某些有趣的學(xué)術(shù)進(jìn)展,其中包括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服飾之書,盡管大多數(shù)相關(guān)書籍,尤其是早年間的,更多是繪畫,而非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文字。
16世紀(jì)的后半葉,法國、意大利、德國和低地國家出版了超過12本服飾之書。這些書不斷再版,有了其他語種的譯本,或者改頭換面重新出版,市場反響良好。如其標(biāo)題所示,這些服飾書提供了一幅“全球服飾地圖”或“世界各地的服裝地圖”,描繪的是來自在亞洲、北非和美洲等各地區(qū)穿著本民族服裝的人們。當(dāng)然,這些出版物中的大多數(shù)木版畫和蝕刻畫表現(xiàn)的還是歐洲各地區(qū)的獨(dú)特服飾,有些書籍還同時(shí)展現(xiàn)了現(xiàn)在和過去的服飾。書中所涉及的每個(gè)時(shí)代或地區(qū)中,男性服飾和女性服飾數(shù)量大體持平,所有的圖畫配有文字解說,隨著時(shí)代進(jìn)步,制作更為精良。這些插圖所附的文字是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服飾書的諸多特點(diǎn)之一,值得深入研究,其他特點(diǎn)還包括描寫的來源,所表現(xiàn)的著裝人物的準(zhǔn)確度及模式,書籍的讀者身份以及各種后繼者。此處我們僅關(guān)注服飾書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②我們將以伊爾格(UlrikeIlg)最近的研究(2004)為基礎(chǔ),他力圖將這些書置于16世紀(jì)后半葉的人文主義文化之中。伊爾格的“現(xiàn)象論者”的分析,關(guān)注服飾書的知識背景,使人們認(rèn)識到考察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所發(fā)生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的重要性。伊爾格將服飾書視為16世紀(jì)力圖“以百科全書的方式組織知識”的一部分。她指出,服飾書與那一時(shí)代的百科全書同樣具有“對世俗世界的世俗方法”以及“綜合處理其主題的觀念”。由此,服飾書同樣可以被看成試圖覆蓋全球的地圖。首部世界地圖集是由安特衛(wèi)普的亞伯拉罕•奧特留斯(AbrahamOrtelius)于1570年出版的。事實(shí)上,在至少一本服飾書的序言中表明,它是對這些新地圖集所提供的地理信息的一個(gè)補(bǔ)充。③伊爾格認(rèn)為,服飾之書嘗試提供一個(gè)全球性的民族服飾概貌,其與歷史學(xué)的當(dāng)展亦有關(guān)聯(lián)。她特別提到了一個(gè)“書寫全球史而非以某個(gè)民族的眼光看待歷史的趨勢”。當(dāng)然,此前已經(jīng)寫過“世界編年史”,這些新全球史與人文主義者不僅描述歐洲文明的過去與現(xiàn)在,而且探討非歐民族的起源的旨趣是一致的。伊爾格認(rèn)為,路易斯•雷羅伊(LouisLeRoy)于1575年出版的《變遷》(DeLaVicissitude)即是歷史書寫的全球化趨勢的一個(gè)案例。該書被視為第一部世界文化史,25年間重印七次,并出版了意大利文和英文譯本。雷羅伊不僅論述了古希臘和古羅馬,還涉及了伊斯蘭和亞洲世界的文化。服飾之書與這種寬闊的歷史建構(gòu)法,可謂異曲同工。
16世紀(jì)的人文主義學(xué)者的研究在空間和時(shí)間上都有廣泛提升,覆蓋了所知的整個(gè)世界。然而,除了服飾的研究,這種世界或全球的方法并沒有拓展到其他視覺藝術(shù)的研究之中,并沒有擴(kuò)大到任何類似研究都使用此方法的程度。也就是說,此類研究已相當(dāng)普遍。不過人們應(yīng)該記著,那是瓦薩里的《藝苑名人傳》刊行的時(shí)期,考夫曼稱這一研究為“Tusco-centric”。①結(jié)語世界藝術(shù)研究正處于發(fā)展期,藝術(shù)研究史的學(xué)者應(yīng)該調(diào)整他們的學(xué)術(shù)史雷達(dá)的參量,以與這一視覺藝術(shù)研究的綜合性框架所體現(xiàn)出的全球性和多學(xué)科原則相適應(yīng)。就全球性原則而言,學(xué)者們需要考察歐洲和其他地區(qū)的歷史,用一種跨文化和全球性的視角去研究藝術(shù)。這種學(xué)術(shù)史的探尋不可避免地要吸取一些現(xiàn)代主義的形式,如果跨學(xué)科意味著從興趣、假設(shè)和當(dāng)代范疇去研究過去,或某種程度上的謬誤。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一種目的論的或輝格式的方法,其與現(xiàn)代主義時(shí)有關(guān)聯(lián)。事實(shí)上,這種方法在我們的案例中似乎不太可能。無論如何,歐洲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史似乎極其間斷,至少是斷斷續(xù)續(xù),而建立穩(wěn)定的知識積累乃當(dāng)前首要之事。逐漸消失并漸被遺忘的總體方案被一個(gè)世紀(jì)之前的德語藝術(shù)界所發(fā)展,便是一個(gè)恰當(dāng)?shù)陌咐N覀儜?yīng)對的似乎是廣泛而整體的文化方法的不斷革新,盡管這種革新會(huì)重新發(fā)現(xiàn)先前從事的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不過每種方法都與其時(shí)代相調(diào)和。實(shí)際上,對這種研究的消長,以及它們的(暫時(shí)的)遺忘和再發(fā)現(xiàn)的考察,應(yīng)該是任何綜合性研究的一部分。像所有的學(xué)術(shù)史研究一樣,從前的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或許得到了細(xì)致的考察。這些考察結(jié)合了兩種歷史主義的視角:一是內(nèi)在論的方法,突出個(gè)體及其觀念,追蹤其歷史傳承;二是外在論的方法,重在知識、社會(huì)文化和制度語境中考察其發(fā)展。觀念史學(xué)者傾向于用現(xiàn)代主義的方法對比這兩種歷史主義的視角,他們所用的“現(xiàn)代主義”這一概念與人們提到的有所差異。也就是說,人們時(shí)常隱藏歷史主義研究的純學(xué)術(shù)趣味,以反對現(xiàn)代主義研究的工具價(jià)值:我們今天能從過去學(xué)到什么?思想史對當(dāng)代有什么用?盡管有些思想史家對歷史主義研究的任何即時(shí)的實(shí)用價(jià)值保持警惕,不過談到當(dāng)代的人們會(huì)從過去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獲得實(shí)在的好處,這種觀念還是不無誘惑的。對有些人來說,已經(jīng)認(rèn)識到過去的假設(shè)乃是偏見,過去的問題乃是誤解,過去的分析框架不夠完善,他們學(xué)到了這些教訓(xùn),在當(dāng)下的研究中會(huì)盡量避免。
這些撤退在當(dāng)代通常被視為有效的,事實(shí)上在未來也會(huì)被視為有效的。除了觀點(diǎn)會(huì)發(fā)生變化,人們應(yīng)該想到,對過去的這種輕視性評價(jià)可能會(huì)掩蓋某些質(zhì)疑、話題和方法,現(xiàn)在認(rèn)為它們?nèi)毕莺苌伲⑶腋挥袉l(fā)性。因此,一些思想史研究者積極看待以往的學(xué)術(shù)成果以及能從中學(xué)到什么。這使一些被后來的成見所遮蔽的研究的潛在價(jià)值得到重視認(rèn)識。正如拉里•夏納(LarryShiner)所說,思想史的一個(gè)任務(wù)就是“讓那些落敗的、邊緣的或被遺忘的事物發(fā)出聲音”。更為普遍的是,追尋或記錄學(xué)術(shù)史,尤其是在人文學(xué)科中,有助于人們更好地認(rèn)識知識和觀念建構(gòu)的偶然性,以及它們的傳播或中斷。通過鼓勵(lì)心理距離、語境化,思考替代性的研究方法,對觀念史的認(rèn)知也能對當(dāng)代的學(xué)術(shù)研究提供新的視角。這些研究更容易被視為在其范式之內(nèi)的實(shí)踐,意即在可能的和受約束的知識框架之內(nèi)。所有這些同樣適用于本文的主題。對知識史的視角的思考有助于洞察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xiàn)在的,甚或未來的。不管能從中獲得何種學(xué)術(shù)益處和知識嘉獎(jiǎng),跨文化的藝術(shù)研究史,如法國人類學(xué)家列維-斯特勞斯所說,“值得思考”。
作者:范丹姆 李修建單位:荷蘭萊頓大學(xué)藝術(shù)史論系教授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