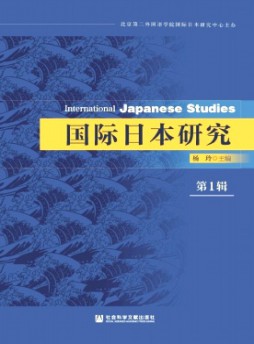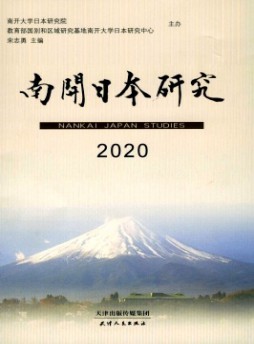日本建筑文化重生的啟示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日本建筑文化重生的啟示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古代
從遠古到飛鳥時代之前,日本建筑在本土文化根基上發展,該時期的日本建筑所展現的是一種自然、質素、簡單、清透的審美,也確立了長期以來日本建筑所保持的民族性特征,這段時期的建筑代表,即是由日本原始的神道教主導形成頗具本土代表性的神社建筑——鳥居。至六朝—隋唐時期,隨著中日文化的密切交流,佛教如流水傾瀉一般傳入日本,伴隨佛教一起傳入的,還有中國佛教的建寺制度。之后,在圣德太子執政期間大興佛教,盛行建造佛寺,而佛寺的建造模式,正是典型地復制了中國佛寺的建筑形式——伽藍布局法。到了奈良前期,“伽藍布局法”也從中國六朝式向唐式典雅清麗過渡。初期的佛寺建筑完全模仿了中國寺院建筑物,在結構式也是沿著中軸線對稱分布,柱梁系統的結構以及瓦葺屋頂。所不同的是,本土所盛產的檜柏和杉樹等木材使得日本佛塔更多地采用方形木造而唐式非多角形磚石結構。這是因為,相對于火山地震頻發自然地理條件,充足的森林資源算得上是上天給該民族為數不多的饋贈,而在塔的層數上也有微妙差異。除了寺院建筑,唐式豪華宮殿建筑和住宅建筑風格也傳入日本。然而,在經過半個世紀之后,唐文化和日本文化發生并存折衷,包括神道教和佛教也發生神佛融合,寺院建筑打破一貫恪守的對稱格局,而是出現靈活自然的變形。他們不再一味崇尚“漢風化”,而是更多民族性感悟。平安時期,漢風建筑真正脫離唐代建筑的模子而實現了日本化的質變再造。日本本民族性所追求的是自然質樸的審美情趣,如法隆寺、唐招提寺、東大寺等大尺度、豪華、平整對稱的“平地伽藍”的模式早已消融,取而代之的則是小尺度、素簡、靈活自由地“山地伽藍”式;在結構上,也不是中國古建筑承重梁系統,而是用長短不同的木柱支撐輕便的屋頂;在建造過程中,也不再強求飛檐和華麗的裝飾,而是繼承了史前神社建筑的傳統,使用扁柏樹皮葺屋頂,以水平拉伸的輕盈線條、素凈的造型以及因地制宜的空間布局帶出和風化的日本建筑文化風采。
2中世
到了日本中世鐮倉和室町時代,皇權貴族統治被削弱,而是武家和公家政權共存的形式。在文化方面,由明庵榮西禪師所引導的中國禪宗文化傳入日本,同時,又掀起一波南宋建筑和南亞印度天竺建筑式樣的模仿狂熱。“禪宗樣”和“天竺樣”建筑流傳開來。禪宗是佛教的延伸,但它的思想核心更加深入日本人心中。日本對于中國禪也發生吸收變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觀念思想。四季分明、峻山美水的自然環境以及頃刻覆滅的自然災難,人們內心畏懼自然,恐慌美好的消失,而禪宗的“空”、“寂”取出了人們心中的“畏”,并逐漸成為支持他們靈魂思想的有力武器。“我心即山林大地”、“我心即佛”禪宗思想被剝離出,從而衍生出日本文化中“物哀”“空寂”“幽玄”的核心審美理念。這一時期外來建筑文化發生成熟質變再造的應該就是日本古代庭園。日本庭園建筑的濫觴,可以追溯到蘇我馬子邸筑池,與古代中國一樣,作為宮室府邸的附屬。在平安時期同樣繼承了飛鳥時代那種純粹烘托自然風景的構建方式,實現了中和并存。禪宗思想的日本化,也帶動了日本庭園的質變,“立石僧”夢窗疏石創造了“凈土庭園”樣式,對于庭園的思想觀念,他是這么說的“相信山河大地,草木瓦石,都有各自的本分者,一旦愛上山水,就宛如世間人情,就有人很快將這種人情作為道心,潛心鉆研涉及泉、石、草、木之四種靈氣的神態,倘若鉆研好的話,就自然會形成道人之山水。”有夢窗疏石的造庭觀念為鋪墊,“枯山水”這種日本象征性庭園形式順勢而生。所謂“枯山水”,就是在沒有水的池子中,以砂代水,并且設立石頭來塑造宇宙自然的微縮景觀,這種建筑藝術正是禪宗中“無中萬般有”的思想表達。中國園林被皇權和貴族所擁有,更多是作為賞玩的場所,而日本的石庭枯山水更多的是給修道者提供一個信仰空間,將人們從紛亂的世道中帶入一個可以暫時安撫內心與精神的幽玄之境。從造園的方法和思想,已經徹底與中國發生分離而有了自身的內涵,日本建筑文化又再一次成功地對外來建筑文化進行吸納并給予新生。
3近世
桃山和江戶時代日本建筑開始接觸西方建筑文化,到了1868年明治維新,日本政治社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西方文化強烈沖擊日本文明,在本土掀起“歐化”風潮。建筑發生革命性變化,比如大浦天教堂、東京赤坂離宮、筑地本愿寺、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等,在它們身上幾乎找不到民族性的影子,建筑接受鋼筋水泥結構,瓦石建造等西方建筑形式,而西方文化幾乎侵蝕了從神佛建筑、公共建筑甚至是住宅的所有建筑類型。可是日本建筑并沒有在歐化風潮中迷失太久,很快,純粹西方建筑的形式逐漸被消化,而產生了“和洋折衷”的共存方式,建筑仍然效仿洋式的空間布局,廣泛地運用鋼筋混凝土,外形上也采用西方的元素符號,但是傳統的木構建造、內部空間組成,依然堅持了日本傳統的形制。經歷了“洋式”以及“和洋折衷”的模式后,近代日本建筑文化也迎來了它的再造。人們認識到和式建筑受到的強烈沖擊,在思索日本未來建筑的發展時,有意識地將“和式”主導性進行了一個強調,在日本建筑由近代向現代過度時期,出現了批量地創新傳統建筑模式——采用西方建筑結構、材料、建造技術,而在形式上繼承和延續了民族性的基調,而不再是仿造西方古典建筑的樣式。
二、日本建筑文化于時代的重生
重生:即是再一次獲得新生的意思,日本建筑文化的重生,是日本在歷史長河中所形成沉淀底蘊,在時代面前以全新的姿態展現,猶如破繭成蝶,令人驚艷。二戰以后的日本建筑,正是以這樣驚人的態勢,走向世界建筑舞臺。丹下健三是將日本現代建筑推向世界舞臺。他所設計的代代木國立綜合體育館,成為日本現代建筑的一個標志。從他的設計中,可以窺見他是如何把握現今時代下日本建筑的奧義:他大膽地破壞了傳統的形制和固有性表達,這種破壞并非對民族性的毀滅,從某一層面看,破壞和保持處于相反的兩極是能夠發生辯證互換的,就如日本傳統禪宗思想中“無中見有”“靜中見動”的意思一樣,他用現代主義的思維,新型的懸索結構,在破壞傳統形制的同時又將日本民族性文化很好地保存在現代建筑軀殼內,首次實現了對日本傳統在現代的成功質變。20世紀70年代后現代主義廣泛流行,日本處于一個具有不廣泛確定性和尋求城市特征的時期,石井和纮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對借鑒西方建筑文化的實踐產生疑問,他開始全神貫注地關注日本自身的歷史文化價值,并發展出一套日本式的后現代主義。在他看來,盲目地機械性地照搬建筑佳作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是處于“和洋共存”文化的時代完全性地體現日本地方性也是很困難的,所以他用了“等價并存”的觀念,把日本藝術中色彩轉換原則轉換到建筑中,并創造出一種萬花筒式的抽象派藝術,他感性地運用具有意義的數字“54”設計了“54”系列作品。在54窗建筑中,遵循“形式隨從功能”的原則,用等跨框架柱和板圃形成54扇窗,但他用“54”窗來表達靈活多樣化內部生活,從而打破自密斯以來西方建筑所遵循的單調。真正地占有后現代主義并賦予日本建筑重生的意蘊。伊東豐雄的仙臺媒體中心,是一個信息時代下的建筑產物。伊東豐雄創造了一種不穩定的流體式建筑,靈活自由的樓層空間給使用者帶來信息化的前衛感受,并且他用不同程度透明度的房間來表達信息時代下虛擬和現實的主題。輕盈單純的鐵骨承重結構,這種建筑思想與以“柱”來建的傳統日本住屋相同,整面玻璃能從外面直接看到支柱的骨架結構,從中環視中滿櫸樹定禪寺大街之際,里外也充滿了一體感。此外,靈活自由的空間體驗,這和日本建筑歷史中的“數寄屋”中自由平面和不拘泥于照舊的觀念一致。在伊東豐雄的建筑,你很難看到傳統建筑的影子,但是屬于日本民族性的精神意識卻早已被根深蒂固地種植在建筑師心中,不斷地開花結果,締造一次又一次地建筑重生。
三、日本建筑重生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日本現代建筑在世界舞臺上碩果累累,且不論在普利策獎已有6名建筑師上榜,它們在世界的影響力也是不容小覷的。從東京都俯瞰,可以明顯辨識出民族本土性——輕盈通透的結構、執著的細節表達、“無有”空間的禪意辯證、質素簡潔的審美意趣,它沒有歐洲那種傳統,也沒有北美洲那種現代高速的城市景象,形形色色建筑以一種隨機的方式密集堆積,更多展現的卻是東方的民族表達。在這座都市中,并不是凝固僵直的,而是有機流動的,在東京它所流露的對傳統的延續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交相輝映。現今中國也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高速前進,我們不缺國際化大都市,城市里不缺摩天大樓,不缺地標建筑,但我們卻只能在城市建筑中看到現代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的發達,中國本土的東西消弭無蹤,我們用西方建筑的思維思考,也許會被形式所震撼,但真正丟失了民族內核。中日建筑從某種意義層次上擁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在近現代也同樣受過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沖擊,如何不在各種風潮迷失,捍衛住民族性的精髓,而在時代變換中獲得破繭成蝶的重生。筆者認為有三點可以借鑒:
1拿來主義。對于外來建筑文化風潮,首先,我們不需要瞻前顧后地考慮太多,也不要被動地接受,主動大膽地占有。若不占有,而是唯唯諾諾摘個樣式,抄個元素,那永遠成為不了新的主人。若是義憤填膺地說捍衛傳統而堅決不接受,那只是重蹈“閉關鎖國”的悲劇,也沒有半點對本民族的自信。若是因為崇拜和羨慕接受這一切,無論良藥還是毒藥都胡亂消化,是堅決不行的。我們要沉著,有辨別。拿來的東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總的而言,外來建筑文化,只是我們實現本土現代化目標的手段之一,它是隨時可拿來也可放棄的工具,我們也無需嚴格地恪守外來文化圈子里的規矩。比如:日本在接受中國古代建筑文化時,就靈活放棄了中軸對稱的布局,柱梁結構系統、華麗的藻飾;再比如在“歐化”風潮中,也只是保留了實用主義原則和磚構技術而丟掉了其他。
2破而后立。也許是歷史上日本經受太多文化風潮的沖擊,他們對于民族傳統,沒有太多教條式的標準,而是把它作為意識留在創作思維中。這種意識不會讓他們簡單地去形似傳統,而是解讀傳統,甚至敢破壞傳統,而是他們敢于將傳統進行抽絲剝繭,而將民族意蘊溶于現代化的軀殼中,暈染出來。而正是這種大膽勇敢的決斷,使得日本建筑獲得新的生命,毀滅和重生,一線之隔。這和中國對待傳統的方式些許不同,傳統不是古董,它們不需要呆在玻璃盒里被保護被觀摩,屬于歷史建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更多地不是去打這保護歷史建筑的招牌去謀取商業利益,而是真正解讀歷史建筑所要傳達的民族性意識,讓它們賦予新時代使命重生。
3自由的發散。在日本,建筑師的創造空間極為廣闊,建筑形式的表達是豐富而多變的,安藤忠雄的“清水混凝土”、伊東豐雄的“流體建筑”、畏研吾的“負建筑”、妹島和世的“極簡主義”,坂茂的“無限制空間結構”等等先鋒建筑在島國爭相迸發。這種發散是有條件的,傳統的民族性意蘊確實始終存在的內核,無論何者,都被深沉的民族意識牢牢牽絆,如同宇宙中圍繞恒星運轉星系,軌跡不同,卻共同在這股引力下運轉,生生不息。
本文作者:白宇泓單位:華中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