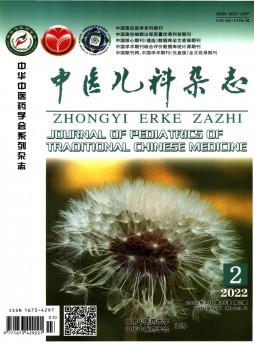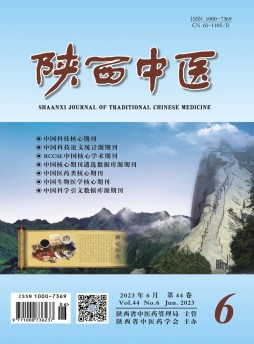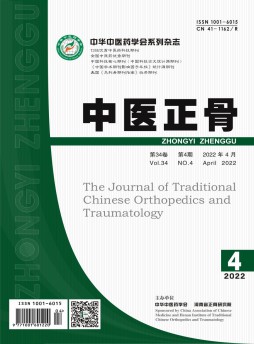中醫學基本特征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中醫學基本特征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摘要:在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中,不僅富有獨特的民族審美命題與范疇,而且也貫穿著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在這種美學思想影響下的文藝創作,無不充滿了對人的關注、對人之生命價值意義的關切與肯定。
縱觀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傳統。無論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莊子的“大道為美”說,還是鐘嶸《詩品》中的“詩唯性情”論、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以及后來的“妙悟”說、“意境”說等,都是圍繞著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進行的。其中的“意境”說、“神韻”說、“風骨”說、“妙悟”說等,都屬于我國民族傳統的美學范疇,體現了我國古典美學中自然主義與人格主義的兩大品格。在這種美學思想引導下的文藝創作,充滿了對人的情感精神的關注和人之生命價值的肯定。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的作用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發人的情緒,體察民情民意,抒發其怨憤之情。其詩論始終圍繞著人的情緒,所以他編定的《詩三百》將人的感情的抒發放在了首位,這種情感也構成了該詩集的精華部分,充分體現了其藝術價值。此外,孔子的“盡善盡美”說、孟子的“沖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說等范疇和命題對中華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具有深遠影響,并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重視文藝審美教化作用的審美原則。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審美思維方式和審美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和命題,為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齊物我”等思想在我國美學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為例,他高度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莊子論美也是以人為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影響下的美學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莊子把“道”視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樂”的美論主張,即美是從“道”的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因而“道”與美密切相關。在莊子看來“道”是一種絕對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應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勝物而不傷”、“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祿所累,不應為物所奴役,而應成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貴*、窮達、禍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對的東西,從而追求一種心靈精神的絕對無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美”。
在《逍遙游》中莊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神人”的形象:在形體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著絕對的自由和廣大無邊的神力,而這種“神人”其實就是人的本質的一種人格化。同時,在莊子的審美思想中也論及了審美主體的自由心態。在《田方子》中,莊子描繪了一個“真畫者”在畫圖時的獨特的自由行動和神態:“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在這里旨在說明真正的畫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創作,敢于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特個性。莊子的這種審美態度使其美學思想帶有了鮮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學思想中,真與美密切相關,提出了“法天貴真”的審美命題。此“真”乃一種出于主體心靈的純真之情,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天然感性的東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作用。在莊子的“法天貴真”思想中強調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莊子對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了其對人之生命的熱切關注.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而且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六朝鐘嶸的《詩品》發展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莫定了“詩唯性情”的理論。《詩品》以詩人個人的風格為品評對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詩為一品,“為建安之杰”。在藝術手法上.進一步解釋了“興”為言已盡而意無窮,把審美范疇擴展到詩文以外。用詩的風格立品,是自覺的美學追求的開始。(詩品)所體現出的美學觀的核心便是“詩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影響,使人的性情發生波動,便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正如《詩品·序》所寫:“嘉匯寄詩以親,離群托時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踐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詩歌的創作無不與社會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關。
唐代.禪宗興盛.形成一種新的美學思想。禪宗是從印度佛學發展起來而又能充分表現中華民族思想與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脫人世煩惱、達到心靈絕對自由的境界。但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生命價值,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過個體心靈、直覺、頓悟,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禪宗重視主體的內心體驗.尊重其內心思考的權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條的束縛.開拓了個性解放的天地。這種思想理論圍繞著人、人的生活.讓人看到生命的本質.且將主體心靈的體驗放在首位.強調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靈的實在性.從人的某種人生境界的體驗中去追求美、尋找美,在一種心靈自由的境界中去獲得審美滿足。這種思想無意中激發了當時的詩人及理論家們的思維方式,促使禪思轉化為藝術思維、藝術機趣,禪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詩歌美學理論的研究和創作之中。特別是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后社會由盛轉衰.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時的士大夫們的審美興趣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創作理論上.皎然獨標性情,引發哲理思考。他在詩論專著《詩式》中說道:“級者嘗與諸公論康樂(謝靈運號)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又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與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可見其仍不脫離性情說。所謂“性情”指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他強調詩人在構思時要善于引發人性的率直真情,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顧詞彩,從而達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這種詩學觀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禪宗“離言”的發揮。司空圖則綜合儒釋道三家學說,撰《二十四詩品),論述詩歌的風格美.分為雄渾、沖淡、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韻語形象地描述了每種風格的特征.從而表達了中國人獨有的民族審美觀,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確,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是獨有的一種民族審美風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礎上還提出了詩之“韻味”說。這種“韻味美”的營構.不僅需要創作主體的“妙造”,還需通過作品審美主體—鑒賞者的閱讀、接受、想象和認同。從這時候的詩歌創作來看,士大夫們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使其審美情趣趨向清幽、平淡、寧靜。其中自然適宜、渾然天成乃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們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領略著人生的哲理.并把這些融化在心靈深處。其中王維的詩歌創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人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舊(《鳥鳴澗))詩很短,但禪意充盈。王維深得禪意、禪趣,故營造了獨特的淡遠含蓄、玲瓏澄澈之意蘊。他說:“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辨覺寺》),這便是其禪悟心態的表現。“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粵。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芙蓉花自開自落,物態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亂”使許多士大夫都經歷了一段慘痛的生活,對王維的心靈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從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門”。“獨坐悲雙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秋夜獨坐)》“無生”.在這里指代佛門“真諦”。涅架境界無生無滅,簡稱“無生”。可見,由于社會的變動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滲透,使文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審美個體心靈的寧靜曠達與超然適意上,使其逐漸悟得在短暫的生命中獲得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途徑。
宋代是文字禪的時代。由于時局的動蕩.禪與文人的關系更加密切.禪宗那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自然適宜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內向封閉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禪的廣泛滲透,改變了文人們的價值觀和審美心態.促進了文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禪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使宋代文人產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態.使宋代詞風多以冷清、平淡為美.追求空靈、疏淡的意境。如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靜初。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又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鴻、人互見,語語相關,營造了一種幽緲、清冷、安謐的意境。蘇軾吸收莊子齊物論的哲學觀而形成曠達的人生態度.反映在其文藝創作中是一種通達不執的審美理想。而且,由于蘇軾一生中的坎坷經歷,使其在創作中,在思維方式上常常融進禪思佛理,形成一種清幽空靈的藝術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賦》中,由個體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時空的無極之壯,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暗含著佛禪思想,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闡明事物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重性,表達了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忘懷得失、處之坦然的人生態度,啟迪人們要在體悟人與宇宙冥合的境界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樂趣。其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浸透著禪思理趣,暗含著人生哲理、人生的價值意義,融會著人本主義的思想。
在文藝創作理論中,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論詩,其見解更豐富,更有啟發性,創立了“妙悟”說、“興趣”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古典詩歌的含蓄之美。
以禪論詩,包藏了無限的機趣,使詩話進人到更高的審美價值境界,體現了一種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禪宗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人類性靈的自由抒發,將其引人到詩話當中,就充分表現了人的靈感與活躍的情慷,從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義的精神。以禪心點化詩心,通過神思,領悟詩的意境美,使主體內心體驗與宇宙生命脈動相連,從而達到物我兩忘,自身獲得徹底解脫。
第2篇
〔論文摘要]在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中,不僅富有獨特的民族審美命題與范疇,而且也貫穿著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在這種美學思想影響下的文藝創作,無不充滿了對人的關注、對人之生命價值意義的關切與肯定。
縱觀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傳統。無論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莊子的“大道為美”說,還是鐘嶸《詩品》中的“詩唯性情”論、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以及后來的“妙悟”說、“意境”說等,都是圍繞著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進行的。其中的“意境”說、“神韻”說、“風骨”說、“妙悟”說等,都屬于我國民族傳統的美學范疇,體現了我國古典美學中自然主義與人格主義的兩大品格。在這種美學思想引導下的文藝創作,充滿了對人的情感精神的關注和人之生命價值的肯定。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的作用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發人的情緒,體察民情民意,抒發其怨憤之情。其詩論始終圍繞著人的情緒,所以他編定的《詩三百》將人的感情的抒發放在了首位,這種情感也構成了該詩集的精華部分,充分體現了其藝術價值。此外,孔子的“盡善盡美”說、孟子的“沖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說等范疇和命題對中華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具有深遠影響,并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重視文藝審美教化作用的審美原則。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審美思維方式和審美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和命題,為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齊物我”等思想在我國美學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為例,他高度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莊子論美也是以人為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影響下的美學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莊子把“道”視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樂”的美論主張,即美是從“道”的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因而“道”與美密切相關。在莊子看來“道”是一種絕對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應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勝物而不傷”、“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祿所累,不應為物所奴役,而應成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貴賤、窮達、禍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對的東西,從而追求一種心靈精神的絕對無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美”。
在《逍遙游》中莊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神人”的形象:在形體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著絕對的自由和廣大無邊的神力,而這種“神人”其實就是人的本質的一種人格化。同時,在莊子的審美思想中也論及了審美主體的自由心態。在《田方子》中,莊子描繪了一個“真畫者”在畫圖時的獨特的自由行動和神態:“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在這里旨在說明真正的畫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創作,敢于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特個性。莊子的這種審美態度使其美學思想帶有了鮮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學思想中,真與美密切相關,提出了“法天貴真”的審美命題。此“真”乃一種出于主體心靈的純真之情,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天然感性的東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作用。在莊子的“法天貴真”思想中強調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莊子對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了其對人之生命的熱切關注.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而且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六朝鐘嶸的《詩品》發展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莫定了“詩唯性情”的理論。《詩品》以詩人個人的風格為品評對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詩為一品,“為建安之杰”。在藝術手法上.進一步解釋了“興”為言已盡而意無窮,把審美范疇擴展到詩文以外。用詩的風格立品,是自覺的美學追求的開始。(詩品)所體現出的美學觀的核心便是“詩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影響,使人的性情發生波動,便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正如《詩品·序》所寫:“嘉匯寄詩以親,離群托時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踐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詩歌的創作無不與社會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關。
唐代.禪宗興盛.形成一種新的美學思想。禪宗是從印度佛學發展起來而又能充分表現中華民族思想與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脫人世煩惱、達到心靈絕對自由的境界。但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生命價值,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過個體心靈、直覺、頓悟,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禪宗重視主體的內心體驗.尊重其內心思考的權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條的束縛.開拓了個性解放的天地。這種思想理論圍繞著人、人的生活.讓人看到生命的本質.且將主體心靈的體驗放在首位.強調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靈的實在性.從人的某種人生境界的體驗中去追求美、尋找美,在一種心靈自由的境界中去獲得審美滿足。這種思想無意中激發了當時的詩人及理論家們的思維方式,促使禪思轉化為藝術思維、藝術機趣,禪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詩歌美學理論的研究和創作之中。特別是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后社會由盛轉衰.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時的士大夫們的審美興趣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創作理論上.皎然獨標性情,引發哲理思考。他在詩論專著《詩式》中說道:“級者嘗與諸公論康樂(謝靈運號)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又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與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可見其仍不脫離性情說。所謂“性情”指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他強調詩人在構思時要善于引發人性的率直真情,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顧詞彩,從而達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這種詩學觀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禪宗“離言”的發揮。司空圖則綜合儒釋道三家學說,撰《二十四詩品),論述詩歌的風格美.分為雄渾、沖淡、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韻語形象地描述了每種風格的特征.從而表達了中國人獨有的民族審美觀,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確,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是獨有的一種民族審美風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礎上還提出了詩之“韻味”說。這種“韻味美”的營構.不僅需要創作主體的“妙造”,還需通過作品審美主體—鑒賞者的閱讀、接受、想象和認同。從這時候的詩歌創作來看,士大夫們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使其審美情趣趨向清幽、平淡、寧靜。其中自然適宜、渾然天成乃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們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領略著人生的哲理.并把這些融化在心靈深處。其中王維的詩歌創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人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舊(《鳥鳴澗))詩很短,但禪意充盈。王維深得禪意、禪趣,故營造了獨特的淡遠含蓄、玲瓏澄澈之意蘊。他說:“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辨覺寺》),這便是其禪悟心態的表現。“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粵。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芙蓉花自開自落,物態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亂”使許多士大夫都經歷了一段慘痛的生活,對王維的心靈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從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門”。“獨坐悲雙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秋夜獨坐)》“無生”.在這里指代佛門“真諦”。涅架境界無生無滅,簡稱“無生”。可見,由于社會的變動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滲透,使文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審美個體心靈的寧靜曠達與超然適意上,使其逐漸悟得在短暫的生命中獲得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途徑。
宋代是文字禪的時代。由于時局的動蕩.禪與文人的關系更加密切.禪宗那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自然適宜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內向封閉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禪的廣泛滲透,改變了文人們的價值觀和審美心態.促進了文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禪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使宋代文人產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態.使宋代詞風多以冷清、平淡為美.追求空靈、疏淡的意境。如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靜初。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又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鴻、人互見,語語相關,營造了一種幽緲、清冷、安謐的意境。蘇軾吸收莊子齊物論的哲學觀而形成曠達的人生態度.反映在其文藝創作中是一種通達不執的審美理想。而且,由于蘇軾一生中的坎坷經歷,使其在創作中,在思維方式上常常融進禪思佛理,形成一種清幽空靈的藝術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賦》中,由個體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時空的無極之壯,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暗含著佛禪思想,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闡明事物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重性,表達了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忘懷得失、處之坦然的人生態度,啟迪人們要在體悟人與宇宙冥合的境界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樂趣。其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浸透著禪思理趣,暗含著人生哲理、人生的價值意義,融會著人本主義的思想。
在文藝創作理論中,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論詩,其見解更豐富,更有啟發性,創立了“妙悟”說、“興趣”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古典詩歌的含蓄之美。
以禪論詩,包藏了無限的機趣,使詩話進人到更高的審美價值境界,體現了一種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禪宗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人類性靈的自由抒發,將其引人到詩話當中,就充分表現了人的靈感與活躍的情慷,從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義的精神。以禪心點化詩心,通過神思,領悟詩的意境美,使主體內心體驗與宇宙生命脈動相連,從而達到物我兩忘,自身獲得徹底解脫。
第3篇
關鍵詞:中醫脈診;現代化研究;對策
中圖分類號:R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1
一、中醫脈診的基本特征
中醫脈診具有微觀性、辯證性、多維性、個體差異性、時間性和整體性等基本特征。中醫脈象的主要內涵在于,在一個多維空間內,同時具備勢、形、數、位等基本脈搏要素,具體來看,中醫脈診涉及脈搏的時間因素、波動范圍、脈形、走勢、節律、頻率、力度和脈位等多方面的概念。所以,對中醫脈診進行研究分析,應結合其多維空間特征,對脈象進行綜合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因為患者病情通常存在較大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不同的患者在邪正盛衰、病性、病因、病位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因而脈象較為復雜。在進行中醫脈診時,應從其脈象的產生機制和表現等出發進行綜合分析[1]。
二、中醫脈診現代化研究的困境
所有脈象的產生均具有勢、形、數、位等幾個方面的屬性,以及流利度、硬度、強弱、長短、粗細、節律、至數和深淺等幾個方面的特性,各類特性之間相互組合,即成為各式各樣、形形的脈象形態。各種脈象的特性和屬性均可作為中醫脈診的依據。現階段,臨床上尚未出現一種能夠同時反映兩種屬性的傳感器。因為不同屬性和特征所使用的設備性能與結構存在一定的差異,且其描記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中醫脈診所繪制出的各種脈象圖測量指標參數和波形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因而尚未形成統一的脈象圖診斷標準,這就對中醫脈診的臨床應用價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相關中醫學研究結果證實,很多中醫學臨床醫師都以西醫血流動力學和心電圖檢查方法和原理出發進行研究,并從外周血管壓力、血管周圍組織結構、血液黏稠度、血液成分、血管彈性等角度出發進行論事,這一研究手段的基礎在于生物學信息所導致的人體病理改變,因而并不屬于常規的中醫學研究范圍。中醫理論的主要特點在于天人相應的辨證思維,在中醫脈診方面,十分重視空間狀態的特征和變化,這與中醫學體系的相關規定具有一致性,而其他血液流變學和心血管系統方法無法完全替代[3]。
三、中醫脈診現代化研究對策
第一,建立和完善科學、系統、符合實際的中醫脈診臨床研究體系。中醫脈診的現代化研究一方面要符合科學性、方法論和思維方式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還應通過優化整理等方法,實現中醫脈診的規范化發展,并與其他相關學科相互配合、協調發展,切實形成符合臨床實際的中醫脈診體系。僅僅依靠患者的脈搏圖儀檢查結果無法實現全方位的中醫脈診現代化。就現階段的臨床實際情況來看,中醫脈診現代化研究不僅與中西醫相關的理論和方法有關,還涉及電子工程學、流體力學、物理學、數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因而有必要建立起一套多學科相互協調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中醫脈診現代化研究體系[4]。
第二,增強中醫脈診研究的規范性。中醫脈診研究的規范性是逐漸減少中醫臨床脈診主觀性影響的主要方法,能夠與其他客觀化、計量化的脈診數字技術相互協同,從而相互促進共同進步。中醫脈診規范化研究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相關中醫學臨床醫師和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系統,且科學化和規范化水平較高的脈診方法,這還需要相關政府中醫藥管理部門的協同努力[5]。
第三,優化整理中醫脈學相關理論知識。中醫脈學理論中存在較為豐富的常規形式理論和方法,其常見形式為“如果A那么B”,然而,這一理論形式中,僅有一少部分屬于完全的普遍規律,而大部分均屬于以概率形式存在的規律,也就是“如果A那么B的幾率為百分之幾”,另有一部分形式屬于偶然的概括,也就是“如果A那么可能是B也可能不是B”。由于規律可以用于為與事實相反的條件提供依據,則上述的相關理論無法成立。若全部醫學研究人員都將常規的中醫脈學理論當做普遍形式的陳述,就會造成理論與實踐不相符的現象。中醫脈學普遍形式的全部論述,都應以實際為基礎,加以最終的檢驗,并用于解決實際問題。所以,醫學研究人員應從科學性的角度出發,在臨床實踐中重鑄和錘煉中醫脈診的相關知識和方法。
四、結語
按照現階段的中醫學研究結果,臨床上尚未形成統一規范化的中醫脈診傳感器或是物理量,且對于患者脈象檢查的兩種屬性資料的采集仍然缺乏統一的標準,由此可知,中醫學研究人員和臨床醫師在進行中醫脈診研究時,應從多物理量、多角度出發,通過中醫脈診傳感器采集患者的脈象信息。中醫學研究人員應從中醫學辯證思維模式出發,對中醫脈診的機制和方法進行針對性分析,最終形成靈敏實用、多方面反映脈象信息、特色規范的中醫脈象診斷設備,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符合中醫本質的脈圖診斷方法,以充分彰顯中醫學脈診的精髓。筆者認為,我國中醫藥管理部門應在繼續增加中醫學科研力量和資金投入的基礎上,從根本上轉變中醫脈診現代化研究思路,由現有的中醫基礎理論出發,結合相關學科知識,形成多層次、多方位、多學科的現代化中醫脈診體系,從而真正有效地為臨床醫療服務。
參考文獻:
[1]閃增郁.中醫脈診信號采集與分析研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9,15(1):77-78.
[2]葛麗娜.中醫脈診的客觀化研究之我見[J].現代中醫藥,2012,32(2):9-10.
[3]徐剛,魏紅,劉明林.關于中醫脈診客觀化研究的思考[J].遼寧中醫雜志,2007,34(1):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