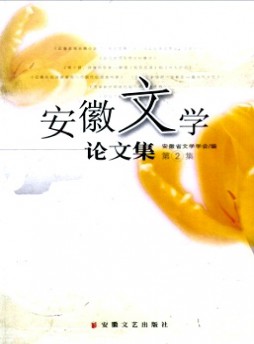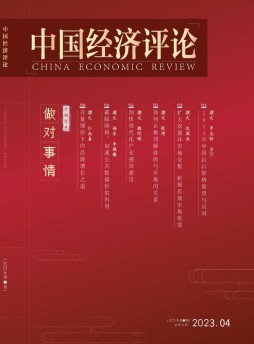思考哲學(xué)基本問題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思考哲學(xué)基本問題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guān)鍵詞]哲學(xué) 基本問題 辯證關(guān)系 社會發(fā)展
一、恩格斯“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認識
恩格斯在1886年初寫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終結(jié)》中指出:“全部哲學(xué),特別是近代哲學(xué)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他進一步指出:“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 思維和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著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chuàng)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近代哲學(xué)家依照如何回答世界的本原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來說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以某種方式承認創(chuàng)始說的人,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于唯物主義的各種學(xué)派。”
二、“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發(fā)展
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基本上是用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評定所有哲學(xué)或“全部哲學(xué)”。 既然是“全部哲學(xué)”,就應(yīng)該包括古希臘哲學(xué)、恩格斯以后的西方現(xiàn)代各哲學(xué)流派,還應(yīng)該包括全部中國哲學(xué)史。由于時代的原因,恩格斯對他之后的西方哲學(xué)不可能知道,中國哲學(xué)恩格斯基本不了解,又怎能把“思維和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來硬套在“全部哲學(xué)”頭上呢?把唯物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來劃分所有哲學(xué)家呢?
哲學(xué)產(chǎn)生以前,人們是用神話和,通過感性的、表象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哲學(xué)的產(chǎn)生意味著人們主要是通過思維、概念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世界觀。古希臘哲學(xué)是從神話和的束縛下誕生的,其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普遍與特殊、一與多的關(guān)系問題。古希臘哲學(xué)是整個西方哲學(xué)的誕生地,西方哲學(xué)史上各種流派幾乎都可以從古希臘哲學(xué)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和萌芽。
最初的古希臘自然哲學(xué)家很重視自然的研究,開始不用神秘的、非自然的東西而用經(jīng)驗的物質(zhì)性的東西來解釋萬物的本原,他們的思想中包含著一個如何用不變的東西來解釋變的東西的問題。如赫拉克利特強調(diào)變,認為只有變才是真實的,沒有永久不變的東西;巴門尼德認為存在的東西既不能產(chǎn)生,也不能消滅,變意味著“多”,不變意味著“一”,只有“一”才是真實的,“多”不過是幻想。
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xué)的興趣由關(guān)注自然轉(zhuǎn)向關(guān)注人。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他認為一切都同樣的真,是非善惡都是相對于人的感覺而言的。蘇格拉底認為真理不在個人,而在人類一般,不在感覺,而在思維,真正的知識就是從具體的道德行為中尋找道德的普遍性定義,而尋找定義的方法就是論辯詰難。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哲學(xué)進入了一種系統(tǒng)化的時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理念”是各類具體事物的普遍概念,他把“理念”看成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個別之外,認為“理念”是最真實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實的。亞里士多德雖然也重視“理念”,他稱之為“形式”,但他不同意把“理念”看成是和個別事物分離的、獨立存在的實體,而認為“理念”或“形式”不能離開感官事物而獨立存在,普遍的東西不能離開個別而東西而獨立存在。
在哲學(xué)形成和發(fā)展的同時,西方許多國家也逐漸產(chǎn)生了其他各種哲學(xué)流派。科學(xué)主義與人文主義基本上代表了19世紀下半葉以來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對待世界萬物的態(tài)度。在英美主要形成了以科學(xué)主義為特征的分析哲學(xué),基本上把人和世界看成是互相外在的,人不過是自然界的旁觀者、觀察者和反映者,人站在事物的旁邊而不參與其中;在歐洲大陸主要形成了以人文主義為特征的現(xiàn)象學(xué)和存在主義,基本上認為人心具有融合人與世界萬物巨大力量,它們關(guān)心人的存在,關(guān)心個人的東西、反對非人性化,反對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學(xué)院氣和遠離生活。
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點:第一,不再像近代哲學(xué)那樣一心關(guān)注自然、關(guān)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對世界的認識,而是專心致志于語言問題、符號意義問題和交往問題,第二,都從不同角度批判傳統(tǒng)哲學(xué)那種崇尚超感性的抽象概念王國的舊形而上學(xué),反對超驗的領(lǐng)域,強調(diào)現(xiàn)實生活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第三,不再像傳統(tǒng)哲學(xué)那樣崇奉確定的、普遍有效的準則或規(guī)范,強調(diào)一切都可以發(fā)生變化,多元主義和分歧在哲學(xué)界占統(tǒng)治地位。
中國哲學(xué)史從商代開始萌芽,到春秋時期形成,截止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先秦哲學(xué);二是秦漢至明清之際的哲學(xué);三是明清之際至?xí)r期的哲學(xué)。中國哲學(xué)探討的問題主要有以下特點:
明清以前的天人合一思想包括:一是儒家的有道德意義的“天”與人合一,如以朱熹為代表的人受命于天、“與理為一”,以王陽明為代表的“人心即天理”的天人相通,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相類;二是道家無道德意義的“道”與人合一。天人合一實際上就是不注重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的區(qū)分,而是把二者看成渾然一體。明末清初開始興起了一種反對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轉(zhuǎn)向類似西方的主客關(guān)系和主體性思想。典型人物是王夫之,他認為“氣者理之依”,強調(diào)“即事以窮理”,反對“立理以限事”。這是中國哲學(xué)史的一個轉(zhuǎn)折點。
由此可見,從哲學(xué)史的現(xiàn)實內(nèi)容來說,硬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來套整個古希臘哲學(xué)以及西方現(xiàn)代哲學(xué)的一切思想流派,來套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顯然不合適。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不能只限于西方近代哲學(xué)所突出的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從哲學(xué)史的現(xiàn)實內(nèi)容看,同樣說明了貫穿全部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應(yīng)該是如何認識和處理人與周圍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關(guān)系。
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理論相對性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還是物質(zhì),它們何者為第一性、何者為第二性的問題?也就是歸根到底誰先誰后,誰依賴誰、誰決定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唯物主義是正確的,唯心主義是荒謬的。恩格斯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里也不能在別的意義上被用。”
1. 唯物主義的局限性
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往往只從一種或幾種常見的物質(zhì)形態(tài)上去尋找世界的本原。近代機械唯物主義,恩格斯指出它的第一個局限在于“僅僅用力學(xué)的尺度來衡量化學(xué)過程和有機過程”,第二個局限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fā)展中的物質(zhì)。”也就是說,機械唯物主義把不同質(zhì)的事物和現(xiàn)象都用機械運動的原理加以說明,用孤立、靜止和片面的觀點來觀察世界,在社會歷史領(lǐng)域則無法用唯物論進行說明,因而陷于唯心史觀。由此可見,恩格斯要創(chuàng)立和堅持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樸素唯物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
其實,從邏輯角度分析,唯物主義認為世界的本原是物質(zhì)的,這只是歸納的結(jié)果,事實上世界上所有的歸納都是一種不完全的歸納,因為在人的經(jīng)驗所不能觸及的地方就不包括在人類的歸納之中。因此,通過歸納而獲得的結(jié)論是不確定的,需要反思。
2. 唯心主義的合理性
唯心主義有兩個分支。一支是主觀唯心主義,把個人的精神(心靈、意識、觀念、意志、感覺等)當(dāng)作世界的本原,認為世界上的一切其他事物都只存在于“我”的感覺、意識之中。如宋代的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代的王陽明的“心外無物”,英國的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奧地利的馬赫的“物是觀念的復(fù)合”等。另一分支是客觀唯心主義,認為不依賴物質(zhì)、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著的“客觀精神”是唯一真實的存在,在這種絕對的客觀精神的發(fā)展過程中,才產(chǎn)生了物質(zhì)世界。如柏拉圖認為“理念”世界是高于一切的惟一真實的存在,黑格爾認為現(xiàn)實世界是“絕對精神”的外化或表現(xiàn),宋學(xué)認為“理”是世界的本原,主張“理在氣先”等。
唯心主義在探究精神生活的獨立性方面有其積極意義。就主觀唯心主義來看,它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客觀世界的存在,只是強調(diào)沒有人的參與,這些存在都是沒有意義的。就客觀唯心主義來看,認為上帝、神是造物主,肯定了人的意識、精神的價值高于身體存在的價值,從而使人獲得了一種價值和道德上的至善的標準,提升了人存在的價值。成為人們辨別是非,科學(xué)實踐,從而成為改造自然的理論工具。
參考文獻:
[1]《古希臘羅馬哲學(xué)》,商務(wù)印書館2002年版
第2篇
關(guān)鍵詞:人的本質(zhì);方法論;形而上學(xué);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B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1-0213-02
一、人的本質(zhì)問題的再次提出
正是歷史上對人的忽視、現(xiàn)實中對人的本質(zhì)的訴求以及理論研究的迫切需要,時時催促我們?nèi)シ此?人是什么、人的本質(zhì)是什么。正如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家卡西爾在他的《人論》中說:“認識自我乃是哲學(xué)研究的最高目標”[1]。可是以往的人們對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的研究多集中在對人的本質(zhì)內(nèi)容的規(guī)定上,而對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的研究方法缺乏探討,結(jié)果使這種研究難以把握問題的真諦。對人的本質(zhì)的追問,離不開對西方人學(xué)思想和中國傳統(tǒng)人學(xué)思想的重點考察。
縱觀整個西方哲學(xué)史,從古代到現(xiàn)代,人類一直不停地轉(zhuǎn)換視角,執(zhí)著而頑強地思考著人的本質(zhì)問題,旨在揭開困擾人類的人性之謎。當(dāng)然由于時展和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各個時代的哲學(xué)家的答案自然各不相同。有的哲學(xué)家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上,從自然界那里尤其是從動物那里,從人與動物的比較中尋找人類的身世;有的哲學(xué)家站在德行主義的立場上,從社會歷史上,尤其是從人類的理性中去探索人類的本性;有的哲學(xué)家站在宗教神學(xué)的立場上,從上帝神靈身上尤其從人類的原罪中探索人類的起源。面對人性問題,西方哲學(xué)家們苦苦求索了幾千年,至今還沒有一個完滿的答案。
在中國哲學(xué)史上,人的本質(zhì)問題也得到了一定的關(guān)注,把人看做是先天基因生成和后天環(huán)境塑造的綜合生成性存在物。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最引人注目。
應(yīng)該說,近三十年來,中國的人學(xué)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就人的本質(zhì)問題上,中國理論界也呈現(xiàn)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歸納起來,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第一,人的本質(zhì)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第二,人的本質(zhì)是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或?qū)嵺`活動或勞動);第三,人的本質(zhì)就是人的需要。上述幾種觀點都有自己的道理和理論依據(jù),從不同的角度看,他們都是合理的。若只承認其中一種,難免會陷入片面性。實際上這幾種看法具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可以綜合統(tǒng)一起來。人的本質(zhì)絕不等于某個單個的因素,它是由現(xiàn)實的人的多方面因素組成的有機系統(tǒng)。“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人是一種在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中通過自己的能動活動特別是生產(chǎn)實踐活動作用于對象而不斷實現(xiàn)和滿足自己發(fā)展著的需要的存在物,這就是人的本質(zhì)。”[2]
二、對人的本質(zhì)問題研究困境之因的反思
中西哲學(xué)史上及當(dāng)代中國人學(xué)研究的相關(guān)成果,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的本質(zhì)問題的再認識,推動了中國人學(xué)的發(fā)展。但是這只是萬里走完了第一步,任重而道遠,特別是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問題及其研究方法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們認為,人性之謎之所以難以解開,人的本質(zhì)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哲學(xué)難題,關(guān)鍵在于很難達到客觀的和全面的自我認識,我們無法跳出自身來認識自己。“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自己的感覺和經(jīng)驗,其他人只能推測。”[3]以往的哲學(xué)家對人的認識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當(dāng)然存在著客觀的原因(主要是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但更為根本的原因卻在于:他們思考和理解人的方式不同,即哲學(xué)思維方式不同,或更具體一點說是人的本質(zhì)問題研究方法出了問題。
三、對人的本質(zhì)問題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中國哲學(xué)史上,孟子以人的后天為善行為而推定人性善的研究方法,這只具有或然性,不具有必然性。況且,人的后天行為中也有作惡之舉。 荀子把人的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nèi),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否定人的自然欲求,本著為國家統(tǒng)治有利的實用主義傾向而界定人性,把社會的特性強加于人。此種研究方法得出的并非人的本質(zhì)。即使在西方哲學(xué)史上,這些研究理路的影子依然存在。
將人與動物作比較的研究方法,是人性認識論中的常見思維定式,從中找出一些人類的特性,并由此來界定人的本質(zhì)所在。但是僅靠這種比較是不夠的。因為人除了具有動物性的一面外,還具有超越動物性的另一面。更何況運用人與動物相比較的方法,只能將人與動物區(qū)別開來,并不能將人與人區(qū)分開來。
即使綜合全面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考察的。它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缺乏必要的論證性過渡環(huán)節(jié)。邏輯學(xué)告訴我們:“種屬關(guān)系的詞項的內(nèi)涵和外延具有一種反變關(guān)系,即一個詞項的內(nèi)涵越多,外延就越少。通過增加內(nèi)涵使一個外延較大的屬詞項過渡到外延較小的種詞項。如果通過限制和概括所得的詞項之間不是屬種關(guān)系,那么這種限制和概括就是錯誤的。”[4] 我們不能隨意擴大“人”的外延,也不能縮小人的外延,更不能將原來不屬于人的本質(zhì)的特性強加給人。否則就會犯“定義過寬”或“定義過窄”的邏輯錯誤。
種加屬差的定義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這是一個由亞里士多德開創(chuàng)的相當(dāng)管用的方法,它隨著亞里士多德的其他思想統(tǒng)治了西方人的頭腦達千年之久。運用這一方法,哲人們提出了“人是兩足無毛的動物”、“人是政治動物”、“人是締造國家的動物”、“人是理性動物”、“人是類存在物”、“人是會制造工具的動物”等等。舉不勝舉,不一而足。在這些提法中都以動物為“種”,是屬差的不同形成了對人的不同看法。這就說明“亞里士多德的方法用來認識簡單的事物是非常有用的,但“人”是這個世界上最特殊、最復(fù)雜的,我們不能再用認識“物”的方法來認識“人”。這種“種加屬差的方法”把人的屬性直接等同于人的本質(zhì),“沒有認識到人的屬性與人的本質(zhì)屬性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概念,由前者到后者沒有一番思想的提煉和升華是不可能的。”[5] 況且邏輯學(xué)專家何向東教授也指出:“用種加屬差的方法可以給絕大多數(shù)詞項下定義。”[4] 這說明該方法不能給所有詞項下定義,它的局限性使之可能對人的本質(zhì)問題無能為力。
一般而論,人的本質(zhì)就是人所特有的、人之為人的特有屬性。但人的成長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是由具有人的形體的自然人逐步轉(zhuǎn)變?yōu)橐粋€體現(xiàn)人的本質(zhì)的社會人的過程,是由非人轉(zhuǎn)化為真人的過程。“人的自我產(chǎn)生有一個從潛在的人到現(xiàn)實的人的過程,其結(jié)果便是使人成其為人。”[6] 可見,人之初只是“行尸走肉”并不體現(xiàn)人的本質(zhì),只是在社會化過程中成熟以后才體現(xiàn)人的本質(zhì)。但是認識論告訴我們:現(xiàn)象是體現(xiàn)本質(zhì)的現(xiàn)象,本質(zhì)是隱藏在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zhì),任何事物都是現(xiàn)象和本質(zhì)的統(tǒng)一,從現(xiàn)象入手來透過現(xiàn)象把握本質(zhì)。顯然前二者相悖。然而,人的本質(zhì)是在人的成長的社會化過程中逐漸淡出顯現(xiàn)的漸進過程,這似乎與西方哲學(xué)史上的“存在先于本質(zhì)”的觀點不謀而合,但也只是貌似神合。既然這兩種理論都不能解釋說明人的本質(zhì)問題,那么我們只有另辟蹊徑才能前進。由于人在實踐中呈現(xiàn)的是現(xiàn)實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它是在現(xiàn)實中存在于歷史中不斷生成的,是在繼承既定社會生產(chǎn)力和人類文化文明的空氣中生存的。這樣任何單方面的概括都將是片面的,任何支離破碎的行為模式的推測及其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商榷和質(zhì)疑的。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對中、西方哲學(xué)史上的人的本質(zhì)問題及其研究方法的考察,覺察出了它們的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性,又對當(dāng)今流行的比較的研究方法,綜合全面的研究方法、種加屬差的定義方法給予或然性的意見,并不是要否定一切,更不是持不可知論的觀點。只是想說明,哲學(xué)的主題已經(jīng)由古代的本體論轉(zhuǎn)變?yōu)榻恼J識論,又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的語言學(xué)、人學(xué),以及后現(xiàn)代的實踐哲學(xué),哲學(xué)也要與時俱進,應(yīng)聚焦當(dāng)今世界的社會、自然與人。 “哲學(xué)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7] 問題不僅在于人的本質(zhì)是什么,而且在于人是如何存在的,人怎樣在實踐中改變自己。
參考文獻:
[1][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2]龔振黔.人的活動研究[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25-27.
[3]夏基松.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新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何向東.邏輯學(xué)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倪志安,侯繼迎.實踐思維方式與馬克思人的本質(zhì)理論[J].西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4,(1).
[6]韓慶祥.馬克思人學(xué)思想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9.
Philosophically Think Deeply Again to Human Nature And It’s Research Way in Human Activities Research
CHEN Jiu-shuang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Kaifeng475004,China)
第3篇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終--結(jié)》中首次明確提出“全部哲學(xué),特別是近代哲學(xué)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1]以此為依據(jù),我國現(xiàn)行教科書將恩格斯關(guān)于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具體內(nèi)容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zhì)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哲學(xué)派別的根本標準;另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有無同一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標準。可見,在哲學(xué)的理論體系中,哲學(xué)基本問題具有硬性的規(guī)范性作用,它是劃分哲學(xué)派別的重要標準,影響著哲學(xué)其他問題的解決方向和方法。鑒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學(xué)基本問題一直是我國哲學(xué)界爭論的重要問題。
一、關(guān)于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爭論及其理由
哲學(xué)不是教條,需要不斷的豐富和完善,所以對哲學(xué)要采取既堅持又發(fā)展的態(tài)度。但是。改革和發(fā)展哲學(xué)絕不是將其正確的、本質(zhì)的東西拋棄,而是在結(jié)合實踐的基礎(chǔ)上辨明是非、修正錯誤、不斷完善。
近年來,我國關(guān)于哲學(xué)基本問題出現(xiàn)了不少爭論,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關(guān)于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內(nèi)容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傳統(tǒng)觀點認為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內(nèi)容包含兩個方面,即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問題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哲學(xué)界對傳統(tǒng)僵化的教科書體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學(xué)者認為原有哲學(xué)基本問題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沒有充分的反映哲學(xué)能動性和革命性特點。因此。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這兩個方面不夠全面,還應(yīng)包含其他方面的內(nèi)容。例如有學(xué)者提出“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問題”是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學(xué)基本問題中不加上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只堅持存在對思維的制約作用,不承認人在客觀世界面前的能動作用,也就是只堅持人能認識客觀世界,而不承認人在認識的指導(dǎo)下,通過實踐能動的改造世界,這就使哲學(xué)基本問題無法體現(xiàn)辯證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學(xué)唯物主義;其二,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本體論、認識論講的都是怎樣認識世界的問題,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因此,原有的兩個方面沒有強調(diào)改造世界,突出實踐的作用;其三,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即實踐論方面,作為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能為認識提供手段,從而提高主體的認識能力和思維能力,使我們能更好的認識世界。在此基礎(chǔ)上,有人提出辯證法與形而上學(xué)的關(guān)系問題是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內(nèi)容之一。
第二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是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但其具體形式會不斷變化。面對恩格斯哲學(xué)基本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質(zhì)疑,有學(xué)者提出“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是全部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3]因為,哲學(xué)作為一門學(xué)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對象決定的,哲學(xué)是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世界觀。哲學(xué)存在于多種多樣的具體理論中,但這些具體的哲學(xué)理論是在“統(tǒng)一性”基礎(chǔ)上表現(xiàn)出“多樣性”。哲學(xué)的對象決定了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是全部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哲學(xué)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學(xué)基本問題,而是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也有學(xué)者提出,要用“歷史的觀點”[4]對待恩格斯哲學(xué)基本問題,即在總體上肯定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是“全部哲學(xué)史的基本問題”,但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即在遠古時代表現(xiàn)為靈魂與肉體的關(guān)系問題、在古代哲學(xué)中表現(xiàn)為一般和個別的關(guān)系問題、在中世紀表現(xiàn)為神與世界的關(guān)系問題、在近代哲學(xué)中表現(xiàn)為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
第三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不是永恒的哲學(xué)基本問題,只是近代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因為哲學(xué)從屬于現(xiàn)代哲學(xué),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不是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例如,有學(xué)者提出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是“實踐問題”。[5]認為我們必須把哲學(xué)與哲學(xué)的具體類型區(qū)分開來,哲學(xué)是唯一的,與它對應(yīng)的問題是哲學(xué)的元問題,即什么是哲學(xué)的問題。哲學(xué)有許許多多的具體類型,所謂“哲學(xué)基本問題”不是對應(yīng)哲學(xué)而言的,而是對應(yīng)于具體的哲學(xué)類型而言,有一種哲學(xué)類型,就有一個哲學(xué)基本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只是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黑格爾等為代表的知識論哲學(xué)類型的基本問題,現(xiàn)代哲學(xué)從根本上超越了知識論哲學(xué)傳統(tǒng),馬克思哲學(xué)從屬于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xué),所以它的哲學(xué)基本問題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此外,也有些學(xué)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將“實踐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主體與客體的關(guān)系問題”、“合規(guī)律性與和目的性的關(guān)系問題”、“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問題”和“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問題”作為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
第四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作為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已經(jīng)過時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隨著馬克思實現(xiàn)哲學(xué)的偉大變革和哲學(xué)的產(chǎn)生,哲學(xué)基本問題被終結(jié)了或被超越了,馬克思哲學(xué)不再是什么思維存在何為第一性,有無同一性、主客體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的關(guān)系。例如有學(xué)者提出“人的實踐和人道評價的關(guān)系問題或?qū)嵺`和人道的雙向批判的關(guān)系問題”是馬克思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6]
可見,上述關(guān)于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這些觀點大多是針對恩格斯哲學(xué)基本問題、針對教科書中傳統(tǒng)的解釋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筆者認為對待哲學(xué)基本問題,不僅要結(jié)合新的實踐不斷發(fā)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那里,去挖掘馬克思本人關(guān)于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一些思想,特別是其思考哲學(xué)基本問題時的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繼承和發(fā)展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思想。
二、我國哲學(xué)界在解決哲學(xué)基本問題時思維方式的缺失
哲學(xué)是從總體上研究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而人與世界最本質(zhì)的關(guān)系是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作為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時代的哲學(xué)之中。因為,人作為實踐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對的是外在客觀的世界,這就促使人從自己的需要出發(fā),按照某種思維方式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guī)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屬性賦予客觀世界以改變世界,這就必然發(fā)生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所以正確的回答兩者的關(guān)系是人在處理人與世界的實踐活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它不是任何哲學(xué)家臆造出來的,也不是任何哲學(xué)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是貫穿全部哲學(xué)史的一條線,它規(guī)定和制約著解決其他一切哲學(xué)問題的基本方向。雖然,有人認為哲學(xué)研究不能采取帖標簽的方式,不能把對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回答即哲學(xué)陣營的劃分問題作為哲學(xué)研究的唯一活動內(nèi)容,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面對如此繁雜的古今中外的哲學(xué)思想,抓住哲學(xué)基本問題這條線索有利于考察其發(fā)展軌跡和脈絡(luò)。
馬克思能夠?qū)崿F(xiàn)哲學(xué)的偉大變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終結(jié)了哲學(xué)基本問題.而是從實踐出發(fā)科學(xué)的、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傳統(tǒng)觀點看來,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思維與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問題,二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但僅有這兩個方面還不足于體現(xiàn)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哲學(xué)的特性。因為馬克思的哲學(xué)不是要去引導(dǎo)人們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哲學(xué)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7]因此,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應(yīng)該成為哲學(xué)基本問題內(nèi)容的第三個方面。此外,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作為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還能夠揭示思維與存在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guān)系,即它們的辯證關(guān)系,這就科學(xué)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樣存在的問題。因此,辯證法與形而上學(xué)的關(guān)系問題也是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內(nèi)容之一。但是,哲學(xué)基本問題要體現(xiàn)馬克思哲學(xué)的實踐本性,就不能將視野僅僅局限在抽象的層面來探討思維與存在的一般關(guān)系及其所包含的內(nèi)容。因為,馬克思哲學(xué)的出發(fā)點是現(xiàn)實的人類實踐活動,隨著人類實踐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fā)展及哲學(xué)研究的深入,我們還可以在抽象的層面上揭示出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內(nèi)容,會出現(xiàn)哲學(xué)基本問題內(nèi)容的第四個方面,第五個方面甚至更多,這就會使我們在抽象層面上就哲學(xué)基本問題一般的關(guān)系及其內(nèi)容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導(dǎo)人們改變世界。因此,我們不應(yīng)該將視野局限在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的一般層面上來探討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內(nèi)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應(yīng)該由抽象上升到具體,返回到馬克思哲學(xué)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去,依據(jù)馬克思哲學(xué)的內(nèi)在規(guī)定,去尋找哲學(xué)基本問題在馬克思哲學(xué)中的具體的存在形式或表現(xiàn)形態(tài)。
隨著近年來我國哲學(xué)界對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從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的視角來重新闡釋哲學(xué)基本問題,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只是近代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不再是馬克思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似乎這樣哲學(xué)基本問題就不會“過時”或“落伍”。實質(zhì)上,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是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是恩格斯在總結(jié)全部哲學(xué)史的基礎(chǔ)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結(jié)果。這也就是說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作為哲學(xué)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xiàn)為不同的形態(tài)或形式。在這不同的具體形態(tài)或形式下面。思維與存在關(guān)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著。在當(dāng)前的一些學(xué)者看來,恩格斯或傳統(tǒng)教科書體系中的哲學(xué)基本問題不能夠體現(xiàn)馬克思哲學(xué)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視現(xiàn)實的、具體的人,進而從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的視角出發(fā),在早期的馬克思哲學(xué)著作中尋找理論支撐來建立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新形態(tài)或形式。我認為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為,馬克思能夠?qū)崿F(xiàn)哲學(xué)的偉大變革。在于科學(xué)合理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實現(xiàn)了哲學(xué)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革。因此,把握馬克思的哲學(xué)思維方式是我們?nèi)婧侠淼睦斫庹軐W(xué)基本問題的重要前提。
三、馬克思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哲學(xué)基本問題
首先應(yīng)當(dāng)明確,馬克思在論哲學(xué)基本問題時,是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人思的。馬克思在《關(guān)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的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xiàn)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dāng)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dāng)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fā)展了,當(dāng)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xiàn)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8]
從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學(xué)家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解決思維與存在關(guān)系問題上的不同缺點。黑格爾強調(diào)思維對存在的能動性、主觀對客觀的改造。以此強調(diào)思維與存在的辨證關(guān)系。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xiàn)實世界的創(chuàng)造主,而現(xiàn)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xiàn)。”[9]從對思維內(nèi)容的理解上看,馬克思和黑格爾正好相反,在馬克思看來思維內(nèi)容是移人人的頭腦而被改造過的感性的東西,即物質(zhì)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他只是“抽象的發(fā)展了”思維的能動性。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觀,反映在哲學(xué)基本問題中也就是強調(diào)思維要通過“直觀”的方式認識存在,但是“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其原因就在于費爾巴哈僅將理論活動看作實踐活動,將真正的人的活動,即物質(zhì)實踐活動,看作是“卑污的猶太人活動”,所以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yè)和社會狀況的產(chǎn)物,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jié)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因此,單純的通過依靠感覺的直觀方式雖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觀現(xiàn)實性,但卻抹煞了思維的能動性。可見,以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德國哲學(xué)的問題在于思維與存在的能動性與感性基礎(chǔ)統(tǒng)一不起來。在此問題根源在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處理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時所采取的思維方式就是從思維和存在的兩極對立出發(fā),用一極去統(tǒng)一另一極的思維方式,沒能很好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