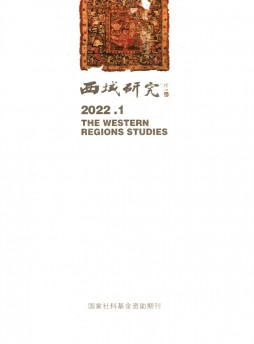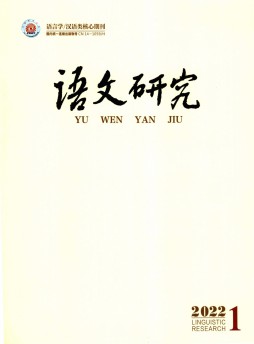西方哲學(xué)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西方哲學(xué)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xi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guān)鍵詞】“西方”/馬克思哲學(xué)/
【正文】
一、對(duì)馬克思哲學(xué)的走近
“西方”具有的理論來(lái)源,并且在理解馬克思的哲學(xué)時(shí)具有新的視野。他們更注重資本主義的當(dāng)展、科學(xué)技術(shù)的當(dāng)展、社會(huì)主義的當(dāng)代實(shí)踐,重視對(duì)馬克思著作的研究,重視對(duì)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在新的理解視野中,他們看到了、看清了傳統(tǒng)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馬克思的一些思想。
(一)社會(huì)歷史或人的問(wèn)題是哲學(xué)的主題
在傳統(tǒng)理解中,社會(huì)歷史或人的問(wèn)題至多只是哲學(xué)的主題之一,哲學(xué)的真正主題是整個(gè)世界的一般本質(zhì),本體論(一般世界觀)被看作是哲學(xué)的核心、靈魂。
“西方”者在理解馬克思的哲學(xué)時(shí)普遍強(qiáng)調(diào),馬克思哲學(xué)的主題不是自然,不是整個(gè)世界,而是社會(huì)歷史問(wèn)題或人的問(wèn)題。盧卡奇把馬克思的哲學(xué)理解為“總體性哲學(xué)”,在他看來(lái),“總體性”不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人類(lèi)歷史有“總體性”,因此他理解的馬克思哲學(xué)是一種社會(huì)歷史理論,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認(rèn)識(shí)到這種方法(馬克思的辯證法——引者注)被限定在歷史的和社會(huì)的范圍內(nèi),這是特別重要的。”(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柯?tīng)柺┮舱J(rèn)為,馬克思的哲學(xué)“它是一種把社會(huì)發(fā)展作為活的整體來(lái)理解和把握的理論;或者更確切地說(shuō),它是一種把社會(huì)革命作為活動(dòng)的整體來(lái)把握和實(shí)踐的理論。”(注:柯?tīng)柺骸逗驼軐W(xué)》,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頁(yè)。)施密特說(shu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并不理會(huì)關(guān)于心靈的精神或物質(zhì)的本性問(wèn)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首先關(guān)心從這個(gè)世界上消除饑餓和痛苦的可能性問(wèn)題。”(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薩特認(rèn)為,“如果存在某種像辯證唯物主義那樣的東西,那它一定是歷史唯物主義,……如果這種唯物主義存在的話,也只能在我們的社會(huì)世界有限范圍內(nèi)才是真理。”(注:薩特:《辯證理性批判》,陳學(xué)明主編《二十世紀(jì)哲學(xué)經(jīng)典文本》,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頁(yè)。)馬爾科維奇在介紹“實(shí)踐派”的觀點(diǎn)時(shí)說(shuō):“在馬克思看來(lái),根本的問(wèn)題是創(chuàng)造一個(gè)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時(shí)如何實(shí)現(xiàn)人的本質(zhì)……哲學(xué)的基本任務(wù)就是對(duì)異化現(xiàn)象進(jìn)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實(shí)現(xiàn)、走向?qū)嵺`的實(shí)際步驟。”(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西方”思潮在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歷史問(wèn)題、人的問(wèn)題是哲學(xué)的主題時(shí),其“主題”的含義并不是很清晰和確定的,但是確實(shí)有啟發(fā)意義。至少在以下幾個(gè)意義上,可以說(shuō)馬克思哲學(xué)的主題是人的問(wèn)題、社會(huì)歷史問(wèn)題:馬克思哲學(xué)所關(guān)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的歷史發(fā)展,馬克思哲學(xué)的根本目的是實(shí)現(xiàn)人的解放,首先是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解放;馬克思哲學(xué)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是人的歷史活動(dòng);馬克思哲學(xué)的基本任務(wù),是揭示歷史運(yùn)動(dòng)的規(guī)律;馬克思哲學(xué)活動(dòng)的重點(diǎn)是唯物史觀,馬克思的哲學(xué)不是本體論哲學(xué)。
(二)不能把哲學(xué)僅僅理解為是對(duì)唯心主義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顛倒”
在傳統(tǒng)的理解中,哲學(xué)被理解為是對(duì)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xué)的顛倒,即把唯心主義辯證法顛倒為唯物主義辯證法。一些“西方”者對(duì)“顛倒”說(shuō)提出質(zhì)疑,他們強(qiáng)調(diào)這種顛倒不能僅僅理解為把唯心主義辯證法轉(zhuǎn)變?yōu)槲ㄎ镏髁x辯證法,而是在于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shí)歷史運(yùn)動(dòng)的辯證法。柯?tīng)柺┱f(shuō):“列寧把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轉(zhuǎn)變僅僅看作一種轉(zhuǎn)變:由不再是‘唯心主義的’而是‘唯物主義的’新的哲學(xué)世界觀取代植根于黑格爾辯證法的唯心主義世界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duì)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的唯物主義顛倒只不過(guò)在于把這種辯證法從它的最后的神秘外殼中解放出來(lái),在‘觀念’辯證法的‘自我運(yùn)動(dòng)’下面發(fā)現(xiàn)了歷史的現(xiàn)實(shí)運(yùn)動(dòng),并把這一歷史的革命運(yùn)動(dòng)宣布為唯一的‘絕對(duì)的’存在。”(注:柯?tīng)柺骸逗驼軐W(xué)》,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頁(yè)。)施密特說(shuō):“在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僅僅解釋成是與任何唯心主義相對(duì)立的、僅僅是哲學(xué)內(nèi)部的甚至是世界觀上的二者擇一時(shí),是不能理解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柯?tīng)柺┖褪┟芴卦谶@里透露出一種深刻的理解:僅僅從與唯心主義對(duì)立的意義上來(lái)理解馬克思的哲學(xué),還不能深刻理解馬克思哲學(xué)變革的實(shí)質(zhì);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新哲學(xué)不能簡(jiǎn)單地理解為是對(duì)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顛倒,“辯證法+唯物主義”這一公式不能深刻揭示哲學(xué)變革的實(shí)質(zhì)。實(shí)際上,對(duì)黑格爾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顛倒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費(fèi)爾巴哈首先完成的,費(fèi)爾巴哈在《哲學(xué)改造的臨時(shí)綱要》中說(shuō):“只要將思辨哲學(xué)顛倒過(guò)來(lái),就能得到毫無(wú)掩飾的、純粹的顯明的真理。”(注:《費(fèi)爾巴哈哲學(xué)著作選集》上卷,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4年,第102頁(yè)。)這里所說(shuō)的“思辨哲學(xué)”指的就是黑格爾哲學(xué)。作為對(duì)黑格爾哲學(xué)的顛倒的費(fèi)爾巴哈唯物主義也不是機(jī)械的或形而上學(xué)的唯物主義,而是辯證的唯物主義。因此,如果僅僅把馬克思的哲學(xué)理解為是對(duì)黑格爾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顛倒,僅僅把馬克思的哲學(xué)理解為辯證的唯物主義,我們可能還是停留在費(fèi)爾巴哈唯物主義的水平上。馬克思哲學(xué)對(duì)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xué)的顛倒的真實(shí)意義在于,馬克思發(fā)現(xiàn)了人的真正現(xiàn)實(shí)的感性活動(dòng)即實(shí)踐的全部意義,用實(shí)踐出發(fā)點(diǎn)代替黑格爾哲學(xué)的理念出發(fā)點(diǎn)。馬克思對(duì)黑格爾哲學(xué)的這一顛倒,不僅超越了唯心主義,同時(shí)也超越了舊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推進(jìn)到實(shí)踐的或歷史的唯物主義形態(tài)。
(三)實(shí)踐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人是什么?一些“西方”者認(rèn)為人是實(shí)踐的存在物,實(shí)踐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對(duì)這一點(diǎn)表達(dá)得最明確的是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馬爾科維奇說(shuō):“人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實(shí)踐的存在。”(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彼德洛維奇說(shuō):“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存在是因?yàn)槿耸且环N實(shí)踐的存在。”(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提出“人是實(shí)踐的存在物”是對(duì)馬克思哲學(xué)的走近。在傳統(tǒng)的理解中,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主要強(qiáng)調(diào)人是各種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這一理解不能說(shuō)錯(cuò),但沒(méi)有揭示人區(qū)別于動(dòng)物的本質(zhì)是什么。馬克思的論斷并不是講人的共同本質(zhì)是什么,而是講要理解一個(gè)人或一些人區(qū)別于其他人的具體本質(zhì),必須看他或他們所處的具體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那么,在馬克思看來(lái),人區(qū)別于動(dòng)物的共同本質(zhì)是什么呢?是勞動(dòng),或更一般地說(shuō),是實(shí)踐。馬克思說(shuō):“一當(dāng)人們自己開(kāi)始生產(chǎn)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shí)候,他們就開(kāi)始把自己和動(dòng)物區(qū)別開(kāi)來(lái)。”(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5頁(yè)。)“實(shí)踐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論斷,是符合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只有理解實(shí)踐是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人的本質(zhì)在現(xiàn)實(shí)性上是各種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因?yàn)檎窃趯?shí)踐中,人們存在著具體的社會(huì)關(guān)系。
(四)實(shí)踐范疇是哲學(xué)的總體的、基本的范疇,是哲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范疇
在傳統(tǒng)的理解中,哲學(xué)的總體的基本范疇是物質(zhì),實(shí)踐范疇只是認(rèn)識(shí)論的基本范疇。“西方”者們則普遍提出,實(shí)踐是哲學(xué)的總體的基本的范疇,是哲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范疇。盧卡奇在談到他的《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一書(shū)時(shí)說(shuō),實(shí)踐概念是“這本書(shū)的中心概念”。(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施密特說(shuō):“不是所謂物質(zhì)這抽象體,而是社會(huì)實(shí)踐的具體性才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的真正對(duì)象和出發(fā)點(diǎn)。”(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馬爾科維奇在介紹南斯拉夫的哲學(xué)爭(zhēng)論時(shí)說(shuō):“在這場(chǎng)辯論中,主張馬克思哲學(xué)的核心范疇是自由的人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dòng)——實(shí)踐——的觀點(diǎn)占了優(yōu)勢(shì)。”(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他自己認(rèn)為,馬克思的哲學(xué)是“建立在實(shí)踐概念的基礎(chǔ)上的哲學(xué)”。(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弗蘭尼茨認(rèn)為,“歷史實(shí)踐的范疇是馬克思對(duì)人和歷史的哲學(xué)解釋的根本范疇。”(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盡管許多“西方”者在肯定實(shí)踐范疇是哲學(xué)的基本范疇時(shí)常常否定物質(zhì)范疇在哲學(xué)中的意義,而且對(duì)實(shí)踐的物質(zhì)本性缺乏正確的認(rèn)識(shí),但是,在肯定實(shí)踐范疇是哲學(xué)的基本范疇、是哲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范疇這一點(diǎn)上,他們是比傳統(tǒng)的者更接近馬克思的。實(shí)踐范疇確實(shí)是哲學(xué)的總體的、基本的范疇。馬克思自覺(jué)意識(shí)到的自己的新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區(qū)別,不是對(duì)物質(zhì)的理解,而是對(duì)“‘革命的’、‘實(shí)踐批判的’活動(dòng)的意義”的理解。
(五)把意識(shí)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當(dāng)作人的感性活動(dòng)、當(dāng)作實(shí)踐去理解
馬克思對(duì)“‘革命的’、‘實(shí)踐批判的’活動(dòng)的意義”的理解,首先在于他把實(shí)踐理解為意識(shí)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傳統(tǒng)理解始終沒(méi)有能理解馬克思的意識(shí)對(duì)象觀,仍然把意識(shí)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理解為某種既成的、非主體存在的東西,而不是把人自身的物質(zhì)活動(dòng)即實(shí)踐理解為意識(shí)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把對(duì)象理解為歷史地生成的東西。“西方”者們則大多十分重視馬克思的《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特別是其第一條的思想,馬克思在此清晰地表達(dá)了新唯物主義的意識(shí)對(duì)象觀。盧卡奇在講到意識(shí)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時(shí),直接表述了馬克思《提綱》第一條的思想:“馬克思強(qiáng)烈地要求我們要把‘感性世界’、客體、現(xiàn)實(shí)理解為人的感性活動(dòng)。”(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他認(rèn)為馬克思在意識(shí)對(duì)象觀上堅(jiān)持“創(chuàng)造的原則”,(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作為意識(shí)對(duì)象的“現(xiàn)實(shí)……無(wú)論如何它要高于那種產(chǎn)生于經(jīng)驗(yàn)世界的僵硬、物化了的事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這種現(xiàn)實(shí)決不同于經(jīng)驗(yàn)的存在,它不是固有的,而是變異的。”(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霍克海默也理解到了意識(shí)對(duì)象的歷史生成性,他說(shuō):“被判斷的對(duì)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種活動(dòng)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194頁(yè)。)施密特說(shuō):“在《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中,他曾批判了以往所有唯物主義把現(xiàn)實(shí)片面地理解為在直觀上給予的客體,‘而不是把它們當(dāng)作人的感性活動(dòng),當(dāng)作實(shí)踐去理解的,不是主觀地去理解的。’”(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從認(rèn)識(shí)論來(lái)說(shuō),自然與其是作為逐步地純粹‘給予的東西’,不如說(shuō)越來(lái)越作為‘被創(chuàng)造的東西’出現(xiàn)的。”(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能被認(rèn)識(shí)的東西,在嚴(yán)格要求意義上只是主體‘所創(chuàng)造的東西’。”(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實(shí)踐派”波什尼亞克說(shuō):“存在并非某種在(主體)以外的東西;人就是存在的組成部分。人意識(shí)到了存在,即在人自身之內(nèi),存在意識(shí)到了它自身。”(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
二、對(duì)馬克思哲學(xué)的遠(yuǎn)離
“西方”哲學(xué)除了的源頭外,還有西方哲學(xué)的源頭,“西方”者們往往站在某一西方哲學(xué)的立場(chǎng)上來(lái)解讀馬克思的哲學(xué),這一視野限制了他們對(duì)馬克思哲學(xué)的另一些方面的正確理解,在這些方面遠(yuǎn)離了馬克思,看不到或看不清在傳統(tǒng)理解中已經(jīng)看到和看清了的馬克思的思想。“西方”哲學(xué)對(duì)馬克思哲學(xué)的遠(yuǎn)離,最主要的表現(xiàn)是這樣那樣否定馬克思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性質(zhì)。其中,少數(shù)人明確提出馬克思的哲學(xué)是超越了唯物、唯心對(duì)立的“實(shí)踐哲學(xué)”,而大多數(shù)“西方”者雖然在口頭上還承認(rèn)馬克思的哲學(xué)是唯物主義哲學(xué),但是在一系列哲學(xué)問(wèn)題上又背離了唯物主義。
(一)馬克思的哲學(xué)是超越唯物、唯心對(duì)立的“實(shí)踐哲學(xué)”
葛蘭西明確否定馬克思的哲學(xué)是唯物主義,他說(shuō):“大家知道,實(shí)踐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從來(lái)不曾把他自己的概念叫作唯物主義的,當(dāng)他寫(xiě)到法國(guó)唯物主義的時(shí)候,他總是批判它,并斷言這個(gè)批判要更加徹底和窮盡無(wú)遺。所以,他從來(lái)沒(méi)有使用過(guò)‘唯物辯證法’的公式,而是稱之為同‘神秘的’相對(duì)立的‘合理的’,這就給了‘合理的’此詞以十分精確的意義。”(注:葛蘭西:《實(shí)踐哲學(xué)》,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頁(yè)。)葛蘭西把所有哲學(xué)分為三類(lèi):“感受的哲學(xué)”、“整理的哲學(xué)”和“創(chuàng)造的哲學(xué)”,唯物主義屬于第一二類(lèi)哲學(xué),唯心主義和哲學(xué)屬于第三類(lèi)哲學(xué),馬克思的“創(chuàng)造的哲學(xué)”“它肯定不是唯心主義的一元論,也不是唯物主義的一元論”。(注:葛蘭西:《實(shí)踐哲學(xué)》,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頁(yè)。)葛蘭西在講到對(duì)“歷史唯物主義”這個(gè)術(shù)語(yǔ)的理解時(shí)說(shuō):“人們忘記了在一個(gè)非常普通的用語(yǔ)[歷史唯物主義]的場(chǎng)合,人們應(yīng)當(dāng)把重點(diǎn)放在第一個(gè)名詞——‘歷史的’——而不是把重點(diǎn)放在具有形而上學(xué)的根源的第二個(gè)名詞上面。”(注:葛蘭西:《實(shí)踐哲學(xué)》,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頁(yè)。)葛蘭西的“超越論”對(duì)整個(gè)“西”思潮產(chǎn)了重要的影響,其他許多“西方”者雖然沒(méi)有像葛蘭西那樣明確否定馬克思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性質(zhì),但在許多哲學(xué)問(wèn)題上,實(shí)際上是沿著葛蘭西的“超越”路線走的。
(二)否定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反對(duì)“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反對(duì)所謂“二元論”思維
許多“西方”者或明或暗地批評(píng)恩格斯關(guān)于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的論斷,把堅(jiān)持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看作是一種“二元思維”而加以否定。柯?tīng)柺┰谂u(píng)“庸俗社會(huì)主義”時(shí)說(shuō):“用的術(shù)語(yǔ)來(lái)說(shuō),庸俗社會(huì)主義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相當(dāng)‘不科學(xué)地’堅(jiān)持著一種樸素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在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中,所謂的常識(shí)(即‘最壞的形而上學(xué)’)和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的標(biāo)準(zhǔn)的實(shí)證主義科學(xué)二者,都在意識(shí)和它的對(duì)象之間劃了一條明顯的分界線。……我們將證明,事實(shí)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決沒(méi)有任何這樣的關(guān)于意識(shí)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的二元論的形而上學(xué)觀”。(注:柯?tīng)柺骸逗驼軐W(xué)》,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頁(yè)。)“然而,列寧回到了‘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zhì)’的絕對(duì)對(duì)立,而這種對(duì)立曾經(jīng)構(gòu)成了劃分17世紀(jì)和18世紀(jì)啟蒙運(yùn)動(dòng)兩大流派的那種哲學(xué)爭(zhēng)論甚至某種宗教爭(zhēng)論的基礎(chǔ)。”(注:柯?tīng)柺骸逗驼軐W(xué)》,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頁(yè)。)薩特在批評(píng)“自然辯證法”思想時(shí)說(shuō):“這一教條主義的源頭來(lái)自‘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問(wèn)題。”(注:薩特:《辯證理性批判》,陳學(xué)明主編《二十世紀(jì)哲學(xué)經(jīng)典文本》,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頁(yè)。)馬爾科維奇在總結(jié)“實(shí)踐派”的觀點(diǎn)時(shí)說(shuō):“正統(tǒng)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diǎn),即認(rèn)為哲學(xué)的基本問(wèn)題是物質(zhì)和精神的關(guān)系問(wèn)題,一般被認(rèn)為是抽象的、與歷史無(wú)關(guān)的二元論的觀點(diǎn)而受到擯棄。”(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在這聲辯論中,……物質(zhì)和精神、客體和主體的二元論被這些范疇是如何可能從實(shí)踐概念中推演出來(lái)的觀點(diǎn)所取代了。”(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以及由對(duì)這一問(wèn)題的回答而區(qū)分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gè)哲學(xué)派別,都是以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zhì)、主觀和客觀的區(qū)分為前提的,沒(méi)有這種區(qū)分,就不能提出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就不會(huì)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誰(shuí)接受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誰(shuí)就必須承認(rèn)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誰(shuí)就必須接受“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反過(guò)來(lái),誰(shuí)反對(duì)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反對(duì)“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誰(shuí)就不可能堅(jiān)持唯物主義。“西方”者一方面承認(rèn)馬克思的哲學(xué)是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又否定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反對(duì)“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這不能不是自相矛盾的。實(shí)際上,他們的真正傾向在于否定、弱化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性質(zhì),而對(duì)馬克思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性質(zhì)的承認(rèn)往往是口頭的和字面的。
(三)借口反對(duì)思維和存在關(guān)系的“二元論”,堅(jiān)持非唯物主義的“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概念
不少“西方”者在反對(duì)思維和存在關(guān)系的“二元論”時(shí),形成了他們的一種非唯物主義的“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概念,把精神活動(dòng)也看作是一種現(xiàn)實(shí),或是現(xiàn)實(shí)的一個(gè)要素。盧卡奇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包括精神和物質(zhì)兩個(gè)基本因素:“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它們是同一個(gè)而且同樣真實(shí)的、歷史的、辯證過(guò)程的諸多方面。”(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柯?tīng)柺┱f(shuō):“對(duì)現(xiàn)代辯證唯物主義來(lái)說(shuō),重要的是,在理論上要把哲學(xué)和其它意識(shí)形態(tài)體系當(dāng)作現(xiàn)實(shí)來(lái)把握,并且在實(shí)踐上這樣對(duì)它們……他們總是把意識(shí)形態(tài)——包括哲學(xué)——當(dāng)作具體的現(xiàn)實(shí)而不是空洞的幻想來(lái)對(duì)待的。”(注:柯?tīng)柺骸逗驼軐W(xué)》,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頁(yè)。)各種科學(xué)意識(shí),“如果它們也是作為世界的一個(gè)‘觀念的’組成部分的話,那么它們就作為世界的真實(shí)的和客觀的組成部分而存在于這個(gè)世界之中。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和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之間的第一個(gè)明顯區(qū)別。”(注:柯?tīng)柺骸逗驼軐W(xué)》,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頁(yè)。)馬爾科維奇更明確地說(shuō):“無(wú)論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還是自然現(xiàn)象問(wèn)題,‘現(xiàn)實(shí)的本質(zhì)’都包含了主觀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會(huì)事件所以是主觀的,乃是意識(shí)存在——作為活動(dòng)者的人——的參與使然。”(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西方”者很少去談實(shí)踐的構(gòu)成因素,但是從他們反對(duì)“二元論”思維方式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理解來(lái)看,他們不是把實(shí)踐看作是人們的客觀物質(zhì)活動(dòng),而是把意識(shí)、理論看作是實(shí)踐的一個(gè)有機(jī)構(gòu)成因素。更有少數(shù)“西方”者把理論活動(dòng)直接看作是實(shí)踐的一種方式,阿爾都塞就是這樣,他認(rèn)為:“除了生產(chǎn)外,社會(huì)實(shí)踐還包括其他的基本實(shí)踐。這里有政治實(shí)踐……意識(shí)形態(tài)實(shí)踐;還有理論實(shí)踐……”(注:阿爾都塞:《保衛(wèi)馬克思》,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4年,第139、140頁(yè)。)還說(shuō):“關(guān)于理論,我們指的是實(shí)踐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也屬于一定的人類(lèi)社會(huì)中的‘社會(huì)實(shí)踐’的復(fù)雜統(tǒng)一體。”(注:阿爾都塞:《保衛(wèi)馬克思》,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4年,第139、140頁(yè)。)阿爾都塞甚至認(rèn)為馬克思的理論是馬克思的“理論實(shí)踐”的反映,檢驗(yàn)馬克思理論正確與否的實(shí)踐標(biāo)準(zhǔn)也不是社會(huì)歷史實(shí)踐而是馬克思的理論實(shí)踐本身。(注:參見(jiàn)阿爾都塞《閱讀(資本論)》;陳學(xué)明主編《二十世紀(jì)哲學(xué)經(jīng)典文本》,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706-707頁(yè)。)
無(wú)論是把理論活動(dòng)看作是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的一個(gè)要素還是把理論活動(dòng)看作是現(xiàn)實(shí)或?qū)嵺`活動(dòng)的一種方式,都遠(yuǎn)離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概念。馬克思?xì)v史唯物主義中的“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是相對(duì)于意識(shí)、理論的范疇,是指人們的“客觀的活動(dòng)”、“人的感性活動(dòng)”,人們的“實(shí)際生活”、“人們的存在”或“社會(huì)存在”。把理論看作是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或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的一個(gè)要素,馬克思的“從物質(zhì)實(shí)踐出發(fā)來(lái)解釋觀念的東西”、“生活決定意識(shí)”、“理論反映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存在決定社會(huì)意識(shí)”等命題就失去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
(四)“拒斥形而上學(xué)”,否定物質(zhì)本體論,反對(duì)“自然辯證法”
許多“西方”者受西方哲學(xué)思潮的影響,把尋求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zhì)的思維叫作“形而上學(xué)”而加以否定,在他們看來(lái),唯物主義的“物質(zhì)本體論”就是一種形而上學(xué)的思維,是馬克思的哲學(xué)所沒(méi)有的。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具有本體論的意義,所以也在他們的反對(duì)之列。盧卡奇批評(píng)“恩格斯錯(cuò)誤地追隨黑格爾,把這種方法(指辯證法——引者注)擴(kuò)大到自然界。”(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施密特說(shuō):“和蘇聯(lián)的所有解釋相反,真正的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爾主義,不是竭力用另一個(gè)本體論的始基即物質(zhì),去簡(jiǎn)單地替換所謂精神這個(gè)本體論的始基。”(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而在恩格斯那里,“辯證法成為在馬克思那里所決沒(méi)有的東西,即世界觀、解釋世界的積極原則。”(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恩格斯的自然概念歸根結(jié)蒂仍然是本體論的。”(注: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頁(yè)。)薩特說(shuō):“自然辯證法,它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是由一種形而上學(xué)假設(shè)的客體。”(注:薩特:《辯證理性批判》,陳學(xué)明主編《二十世紀(jì)哲學(xué)經(jīng)典文本》,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頁(yè)。)“拒斥形而上學(xué)”、否定物質(zhì)本體論和自然辯證法,必然會(huì)否定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性質(zhì),至少會(huì)弱化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路線。否定物質(zhì)本體論,否定自然辯證法,從形式來(lái)看,并不完全否定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性質(zhì),他們至少在口頭上還承認(rèn)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但是,從實(shí)際來(lái)看,這種否定就是放棄唯物主義的一個(gè)重要陣地,并最終會(huì)導(dǎo)致放棄唯物主義的所有陣地。放棄了物質(zhì)本體論這個(gè)重要陣地,也就不能堅(jiān)守其他陣地。不肯定世界的物質(zhì)性,當(dāng)然也就不能真正承認(rèn)社會(huì)歷史歸根到底是一種特殊的物質(zhì)運(yùn)動(dòng)形式,就不可能有歷史唯物主義。
不能以馬克思哲學(xué)的主題是人的問(wèn)題、社會(huì)歷史問(wèn)題為根據(jù)否定物質(zhì)本體論。理解人的本質(zhì)、社會(huì)歷史的本質(zhì),最重要的當(dāng)然是要認(rèn)識(shí)人和社會(huì)歷史區(qū)別于自然運(yùn)動(dòng)的特殊本質(zhì),但也要認(rèn)識(shí)人、社會(huì)歷史與自然運(yùn)動(dòng)共同的本質(zhì),對(duì)這種共同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就是物質(zhì)本體論。因此,物質(zhì)本體論是馬克思哲學(xué)主題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并不是與解決人的問(wèn)題、社會(huì)歷史問(wèn)題不相關(guān)的理論。也不能因?yàn)轳R克思談?wù)撐镔|(zhì)本體論不多就認(rèn)為馬克思的哲學(xué)沒(méi)有物質(zhì)本體論。馬克思對(duì)物質(zhì)本體論談得不多,這是可以理解的,因?yàn)檫@些問(wèn)題基本上已經(jīng)由先前的唯物主義特別是費(fèi)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解決了,馬克思的任務(wù)主要不是重復(fù)前人已經(jīng)基本解決了的理論,而是把唯物主義推向前進(jìn),超越直觀唯物主義而走向?qū)嵺`唯物主義,超越自然唯物主義而走向歷史唯物主義,所以其理論重點(diǎn)是制定科學(xué)的實(shí)踐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談得不多不等于沒(méi)有,馬克思是談到世界的物質(zhì)性、自然的先在性和自然的辯證運(yùn)動(dòng)的,馬克思是繼承了唯物主義的物質(zhì)本體論思想的。物質(zhì)本體論是馬克思?xì)v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
(五)否定反映論,否定客觀真理
在認(rèn)識(shí)論上,“西方”者普遍否定反映論,否定客觀真理。盧卡奇借口思維對(duì)象的變易性否定反映論,他說(shuō):“如果變易的真理是將要被創(chuàng)造出來(lái)而尚未產(chǎn)生出來(lái)的未來(lái),如果它是種新的東西,存在于各種傾向之中,但這些傾向(借助于我們的意識(shí))將會(huì)變成現(xiàn)實(shí),那么,思維是為一種反映這個(gè)問(wèn)題就顯得毫無(wú)意義了。”(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如果事物不存在,思維何以‘反映’?……在‘反映’論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思維和存在、意識(shí)和現(xiàn)實(shí)的理論上的具體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對(duì)物化意識(shí)來(lái)說(shuō)很難統(tǒng)一。從這樣的觀點(diǎn)來(lái)看,無(wú)論是事物被認(rèn)為是概念的反映,還是概念反映了事物,這都無(wú)足輕重。在這兩種情況下,兩重性都依然如故。”(注:盧卡奇:《歷史和階級(jí)意識(shí)》,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頁(yè),“新版序言”第22頁(yè),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頁(yè)。)盧卡奇這里所說(shuō)的“兩重性”,指的就是“二元論”。馬爾科維奇在介紹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觀點(diǎn)時(shí)說(shuō):“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被當(dāng)作對(duì)藝術(shù)研究方法的一種諷刺普遍地受到拋棄。”“在這場(chǎng)生動(dòng)的、時(shí)而是戲劇性的辯論中,正統(tǒng)的者試圖拯救‘反映論’這一由蘇聯(lián)辯證唯物主義者和保加利亞哲學(xué)家T.巴甫洛夫發(fā)展起來(lái)的認(rèn)識(shí)論基石。針對(duì)這種理論提出的三個(gè)主要的反對(duì)理由是:首先,它忽視了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的全部經(jīng)驗(yàn),又回到了一種18世紀(jì)自在的物質(zhì)客體和精神主體的二元論;其次,在反映是一切意識(shí)的根本特征這一觀點(diǎn)中,內(nèi)含了明顯的教條主義;第三,這種理論的錯(cuò)誤還在于,意識(shí)實(shí)際上遠(yuǎn)不是消極地伴隨并復(fù)制物質(zhì)的過(guò)程,它常常預(yù)見(jiàn)和設(shè)計(jì)尚不存在的物質(zhì)客體,試圖通過(guò)說(shuō)明我們?cè)谶@些情況中討論的是‘創(chuàng)造性的反映’來(lái)重新定義反映論,給人一種專門(mén)為此約定的印象,根據(jù)這種約定,反映的概念便以這種方式被夸大到使人完全不知其所云的地步。”(注:馬爾科維奇等主編《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導(dǎo)論”第23、23、13、23、13、13頁(yè);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頁(yè)。)
第2篇
關(guān)鍵詞:分析哲學(xué)代表人物特點(diǎn)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特征
一、分析哲學(xu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分析哲學(xué)產(chǎn)生于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的歐洲國(guó)家,并為北美國(guó)家所熟知。它作為20世紀(jì)西方哲學(xué)的重要思潮之一,曾在世界哲學(xué)流派中占據(jù)制高點(diǎn)。德國(guó)哲學(xué)家和數(shù)學(xué)家弗雷格在19世紀(jì)末在語(yǔ)言哲學(xué)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diǎn),成為分析哲學(xué)的直接思想先驅(qū)。不過(guò),西方哲學(xué)界一般說(shuō)來(lái)仍把20世紀(jì)初的英國(guó)看作分析哲學(xué)的發(fā)源地,并把羅素于1905年發(fā)表的《論指示》一文視為分析哲學(xué)形成的象征,它頭一次比較詳細(xì)地闡述分析哲學(xué)某些基本觀點(diǎn)。維特根斯坦等人又對(duì)其作出了更深入的發(fā)展。美國(guó)哲學(xué)家卡普蘭曾對(duì)這個(gè)流派在西方世界中的影響作出評(píng)價(jià):“我現(xiàn)在稱之為‘分析哲學(xué)’的這種廣泛的哲學(xué)思潮,是目前英語(yǔ)國(guó)家中影響最大的哲學(xué)思潮。幾乎在美國(guó)各大學(xué)中,以及在英國(guó)各個(gè)大學(xué)中,人們所說(shuō)的哲學(xué)實(shí)際上就是指這種思潮。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印度和日本,情況也變得與此相似。這種分析思潮在南美也有某種影響。最后,在歐洲大陸的國(guó)家中,它也并不是完全沒(méi)有地位的。”[1]可見(jiàn),分析哲學(xué)在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上獨(dú)樹(shù)一幟不斷發(fā)展。
二、分析哲學(xué)的主要代表人物
從狹義的分析哲學(xué)上來(lái)看,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羅素、摩爾、維特根斯坦等,他們?cè)诓煌慕嵌葘?duì)分析哲學(xué)進(jìn)行了概括和發(fā)展。
(一)弗洛布弗雷格(1848—1925)
弗雷格是分析哲學(xué)的直接思想先驅(qū)。1848年他出生于德國(guó)魏瑪,并從1879年起在耶拿大學(xué)執(zhí)教。波蘭哲學(xué)家沙夫稱他為“偉大的數(shù)學(xué)家和邏輯學(xué)家,現(xiàn)在人們相信他是從亞里士多德以來(lái)邏輯學(xué)中最偉大的革新者”。[2]其著作有《論概念與對(duì)象》《概念語(yǔ)言》等。弗雷格首先反對(duì)心理主義,批判心理主義者“把一切歸結(jié)為主觀的東西,這種觀點(diǎn)貫徹到底,就等于取消了真理”。[3]即認(rèn)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shí)的基礎(chǔ)不是人的心理過(guò)程而是邏輯。其次,他通過(guò)研究知識(shí)表達(dá)的形式研究知識(shí)本質(zhì)。他認(rèn)為知識(shí)與表達(dá)是哲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重要問(wèn)題,認(rèn)為自然語(yǔ)言不夠嚴(yán)密,必須構(gòu)造一個(gè)形式語(yǔ)言以確保知識(shí)的客觀性和確定性。隨后,弗雷格由提出“函項(xiàng)學(xué)說(shuō)”,即把語(yǔ)句的邏輯結(jié)構(gòu)分解為函項(xiàng)和自變項(xiàng)。只有通過(guò)函項(xiàng)分析,區(qū)分語(yǔ)言的邏輯層次,我們才能避免無(wú)意義的陳述。對(duì)象與概念的區(qū)別既是弗雷格的邏輯,也是他的本體論。最后,弗雷格提出涵義是語(yǔ)言意義的內(nèi)容,指稱是語(yǔ)言有意義性的標(biāo)準(zhǔn),用于科學(xué)目的的語(yǔ)言必須有指稱,語(yǔ)詞的涵義和指稱有嚴(yán)格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涵義和指稱的學(xué)說(shuō)形成他的語(yǔ)言哲學(xué)的基本觀念。總之,弗雷格把研究意義理論看作哲學(xué)研究的首要任務(wù),并把意義理論看作哲學(xué)中唯一的一部分,為語(yǔ)言哲學(xué)的發(fā)展開(kāi)辟了新紀(jì)元。但應(yīng)當(dāng)指出,他的觀點(diǎn)也導(dǎo)致一部分人把哲學(xué)的任務(wù)歸結(jié)為語(yǔ)言分析,解決探討物質(zhì)和意識(shí)的關(guān)系等哲學(xué)基本問(wèn)題。
(二)貝特蘭羅素(1872—1970)
羅素是分析哲學(xué)的主要?jiǎng)?chuàng)始人,出生于英國(guó)貴族家庭,開(kāi)創(chuàng)用現(xiàn)代邏輯進(jìn)行哲學(xué)分析的新局面。其著作有《我的哲學(xué)發(fā)展》《意義與真理的探究》等。他的主要哲學(xué)思想是外在關(guān)系論與多元論,即在認(rèn)為命題都是主—賓詞關(guān)系的命題,內(nèi)在聯(lián)系不能用于反映對(duì)象和關(guān)系的命題;摹狀詞理論和親知理論,即分析名稱和摹狀詞的差別并把知識(shí)分成兩類(lèi),我們通過(guò)感官直接認(rèn)知的親知的知識(shí)是必不可少的;邏輯原子主義與邏輯構(gòu)造論,邏輯原子就是經(jīng)過(guò)邏輯分析后所達(dá)到的最基本的單元,并提出“只要有可能,就用有已經(jīng)實(shí)體的構(gòu)造替代對(duì)未知實(shí)體的推論”;日常語(yǔ)言與邏輯理想語(yǔ)言學(xué)說(shuō),即邏輯的分析工作正是通過(guò)發(fā)現(xiàn)語(yǔ)言真正的邏輯形式來(lái)消除哲學(xué)問(wèn)題的,因此,應(yīng)當(dāng)建立一種邏輯上的理想語(yǔ)言。總之,羅素的一生中哲學(xué)思想發(fā)生多次變化,但都對(duì)世界哲學(xué)思想產(chǎn)生巨大影響。
(三)喬治愛(ài)德華摩爾(1873—1953)
摩爾是分析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出生于倫敦近郊,在1911年回到劍橋擔(dān)任講師。其著作有《駁斥唯心主義》《保衛(wèi)常識(shí)》等。摩爾對(duì)分析哲學(xué)的貢獻(xiàn)主要在于他一方面領(lǐng)導(dǎo)了反對(duì)唯心主義,建立一種常識(shí)哲學(xué);另一方面,他創(chuàng)造了概念分析方法,即對(duì)日常語(yǔ)言的分析,這使他成為分析哲學(xué)的奠基人。
(四)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1889—1951)
維特根斯坦是羅素之后影響最大的分析哲學(xué)家,其主要著作有《邏輯哲學(xué)論》《哲學(xué)研究》。維特根斯坦在哲學(xué)觀點(diǎn)上經(jīng)歷過(guò)重大轉(zhuǎn)折。前期他追隨羅素,創(chuàng)造了邏輯原子主義哲學(xué)。而后期,他卻與前期哲學(xué)大相徑庭,提出語(yǔ)言意義的用法理論。不過(guò)他兩種相異的哲學(xué)思想對(duì)整個(gè)哲學(xué)界都產(chǎn)生過(guò)重大影響。維特根斯坦的前期代表著邏輯實(shí)證主義,而后期則回歸日常語(yǔ)言學(xué)。
三、分析哲學(xué)的特點(diǎn)
分析哲學(xué)理論復(fù)雜繁多,它不僅在不同支派之間產(chǎn)生許多分歧,更在同一支派內(nèi)部產(chǎn)生許多的矛盾。盡管如此,他們的觀點(diǎn)粗略說(shuō)來(lái)仍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一)把語(yǔ)言分析當(dāng)作哲學(xué)的首要任務(wù)
分析哲學(xué)家將大部分哲學(xué)問(wèn)題歸結(jié)為語(yǔ)言問(wèn)題,并將哲學(xué)的任務(wù)歸結(jié)為是對(duì)科學(xué)語(yǔ)言進(jìn)行邏輯分析抑或?qū)θ粘UZ(yǔ)言進(jìn)行語(yǔ)言分析。維特根斯坦曾指出:“全部哲學(xué)就是語(yǔ)言批判。”[4]他認(rèn)為,哲學(xué)上的迷惘混亂產(chǎn)生于濫用語(yǔ)言或誤用語(yǔ)言,強(qiáng)調(diào)概念的清晰性和推理的嚴(yán)謹(jǐn)性。卡爾納普也道,“哲學(xué)應(yīng)當(dāng)被關(guān)于科學(xué)的邏輯所代替,那就是說(shuō),應(yīng)當(dāng)被對(duì)于哥們科學(xué)的概念和語(yǔ)句的邏輯分析所代替,因?yàn)殛P(guān)于科學(xué)的邏輯不是別的,正是科學(xué)語(yǔ)言的邏輯句法。”[5]他們認(rèn)為語(yǔ)言是哲學(xué)的唯一研究對(duì)象,哲學(xué)的任務(wù)不是發(fā)現(xiàn)新的命題,而是將已存在的命題變得清晰,探求解釋科學(xué)語(yǔ)言或日常語(yǔ)言的意義。因此,一切超出這個(gè)范圍的問(wèn)題都是毫無(wú)認(rèn)識(shí)意義的形而上學(xué)命題。
(二)把分析方法看作哲學(xué)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理解和使用分析方法中,羅素、前期維特根斯坦和邏輯實(shí)證主義者基本上都強(qiáng)調(diào)形式分析或邏輯分析,而摩爾、后期維特根斯坦以及日常語(yǔ)言學(xué)派則強(qiáng)調(diào)概念分析或語(yǔ)言分析。盡管分析哲學(xué)家對(duì)分析方法的理解不盡相同,但他們都一致重視這種方法的應(yīng)用。分析方法可以發(fā)揮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作用。而且,在隨后處理哲學(xué)問(wèn)題的過(guò)程中,他們通過(guò)利用這種方法在語(yǔ)言哲學(xué)和科學(xué)哲學(xu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積極成果。
(三)高度強(qiáng)調(diào)理論具有科學(xué)性,并把他們的哲學(xué)稱為“科學(xué)哲學(xué)”
一方面,他們強(qiáng)調(diào)有必要在自然科學(xué)中建立自己的理論,特別是以數(shù)學(xué)和物理學(xué)為榜樣,使自己的論證達(dá)到自然科學(xué)那樣的精確程度。許多分析哲學(xué)家既研究哲學(xué),又研究科學(xué),他們或者是具有科學(xué)修養(yǎng)的哲學(xué)家,或者是具有哲學(xué)修養(yǎng)的科學(xué)家。如弗雷格、羅素等人既是分析哲學(xué)的主要代表,又對(duì)數(shù)學(xué)或物理做過(guò)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他們?cè)诮鉀Q哲學(xué)問(wèn)題時(shí),都強(qiáng)調(diào)要從細(xì)處著手,從小到大地逐個(gè)解決,以得出精確答案。卡爾納普對(duì)研究的科學(xué)性曾這樣描述道,“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科學(xué)的哲學(xué)并不導(dǎo)向宏偉的思辨體系,而毋寧導(dǎo)向一點(diǎn)一滴的澄清。只有當(dāng)眾多的思想家辛苦工作,解決了一系列細(xì)小問(wèn)題之后,才能?chē)L試構(gòu)造這樣的體系。”[6]
第3篇
關(guān)鍵詞:理性;信仰;人學(xué);生存論
一
二十世紀(jì)以來(lái),西方哲學(xué)、神學(xué)由近代轉(zhuǎn)向現(xiàn)代,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這個(gè)概念當(dāng)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計(jì)時(shí)來(lái)區(qū)分的,在哲學(xué)、神學(xué)上不像在現(xiàn)實(shí)中有一條明確的時(shí)限可劃。哲學(xué)、神學(xué)之所以能劃分為近代和現(xiàn)代,是因?yàn)樵谶@兩個(gè)時(shí)期中,哲學(xué)和神學(xué)有各自不同的特點(diǎn)和不同的問(wèn)題。需要指出的是,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神學(xué)中的問(wèn)題同近代哲學(xué)、神學(xué)問(wèn)題之間盡管有著質(zhì)地差別,但仍然存在著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它一方面是對(duì)近代問(wèn)題的繼承與接續(xù),另一方面也是對(duì)近代問(wèn)題做出的現(xiàn)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討現(xiàn)代哲學(xué)、神學(xué)中的生存本體論,就必須回溯近代哲學(xué)、神學(xué)對(duì)相關(guān)問(wèn)題所做的說(shuō)明,只有察源觀流,才能真正把握這一問(wèn)題的脈絡(luò)和精神實(shí)質(zhì)。在對(duì)諸多近代哲學(xué)、神學(xué)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筆者既沒(méi)有選擇近代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者笛卡爾、培根,也沒(méi)有選擇近代哲學(xué)的終結(jié)者黑格爾,而是選擇了康德作為重點(diǎn)分析對(duì)象。做出這一選擇的理論依據(jù)是什么?以探討知識(shí)論問(wèn)題而著稱的康德學(xué)說(shuō)與生存本體論有何關(guān)聯(lián)?康德的相關(guān)見(jiàn)解對(duì)現(xiàn)代哲學(xué)、神學(xué)話語(yǔ)的生存論轉(zhuǎn)向有何種?對(duì)上述問(wèn)題的回答構(gòu)成了本論文的主要。
俄羅斯文藝?yán)碚摷腋曷逅鞣蚩藸栐谄洹锻铀纪滓蛩够c康德》一書(shū)中指出:“在哲學(xué)這條道路上,一個(gè)思想家不管他是來(lái)自何方和走向何處,他都必須通過(guò)一座橋,這座橋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國(guó)的康德專家貝克曾引述哲學(xué)家中流傳的一句格言:“在哲學(xué)問(wèn)題上,你可以贊同康德,也可以反對(duì)康德,但不能沒(méi)有康德。”2)人們之所以給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評(píng)價(jià),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學(xué)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個(gè)人類(lèi)在日益豐富的生活實(shí)踐中所取得的優(yōu)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臘發(fā)軔而來(lái)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結(jié)晶,在康德這里既有蓬勃發(fā)展的科學(xué)及其方法的影響,又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啟迪,還有文藝復(fù)興運(yùn)動(dòng)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論者和經(jīng)驗(yàn)論者的理論碰撞,又有法國(guó)早期啟蒙學(xué)者和人文學(xué)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頓、盧梭和休謨等這些時(shí)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層積淀。正是在上述綜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國(guó)自身的萊布尼茲——伏爾夫?qū)W派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學(xué)”,奠定了近代德國(guó)哲學(xué)和神學(xué)的基礎(chǔ),而這種哲學(xué)和神學(xué)的影響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國(guó)的范圍。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學(xué)史、神學(xué)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duì)現(xiàn)代生存本體論的影響,僅看到上述因素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更主要的是要從康德所提問(wèn)題的深度和廣度上來(lái)理解康德思想的歷史意義。康德哲學(xué)和神學(xué)思想的根基是其《純粹理性批判》,特別是其中的“分析篇”,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神學(xué)的主要思潮大都從這里出發(fā)來(lái)尋找自己的立足點(diǎn)。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類(lèi)先天認(rèn)識(shí)能力為出發(fā)點(diǎn),以闡釋理性與信仰的矛盾沖突為目的,其主要任務(wù)就是要確定人類(lèi)認(rèn)識(shí)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這些先天要素的來(lái)源、功能、條件、范圍和界限,最終為信仰留下足夠的地盤(pán)。康德把人類(lèi)的認(rèn)識(shí)能力首先區(qū)分為:作為低級(jí)認(rèn)識(shí)能力的感性和作為高能認(rèn)識(shí)能力的理性。感性通過(guò)先天的直觀形式——空間和時(shí)間去接受由于物自體對(duì)感官的刺激而產(chǎn)生的感覺(jué),從而為高級(jí)的認(rèn)識(shí)能力提供對(duì)象和質(zhì)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級(jí)認(rèn)識(shí)能力區(qū)分為知性、判斷力和理性三種。他認(rèn)為知性的先天思維形式是所謂純粹知性概念(即范疇:如質(zhì)、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運(yùn)用范疇綜合統(tǒng)一感性材料才產(chǎn)生了經(jīng)驗(yàn)或知識(shí),而范疇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從范疇規(guī)定時(shí)間圖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這種形式進(jìn)行的,知性的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構(gòu)性,作為認(rèn)識(shí)對(duì)象的自然界的各種,正是知性通過(guò)其范疇或原理而頒定給它的,亦即人為自然立法,這就是康德自稱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斷力的作用則在于運(yùn)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統(tǒng)攝、規(guī)定特殊的感性現(xiàn)象,以形成關(guān)于對(duì)象的具體的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而理性的作用則在于通過(guò)其主觀產(chǎn)生的關(guān)于無(wú)條件者的理念(諸如:靈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導(dǎo)知性的活動(dòng),使認(rèn)識(shí)達(dá)到最大可能的繼續(xù)、擴(kuò)大和系統(tǒng)化。然而理性在認(rèn)識(shí)中的迷誤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與之對(duì)應(yīng)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這些無(wú)條件的、超感性的現(xiàn)象界以外的對(duì)象,即物自體或本體。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疇只有同感性材料結(jié)合才能產(chǎn)生關(guān)于對(duì)象的知識(shí),因而把本來(lái)僅適用于感性現(xiàn)象的范疇,用來(lái)規(guī)定超感性、超經(jīng)驗(yàn)的物自體。其結(jié)果必然產(chǎn)生關(guān)于靈魂不朽之類(lèi)的謬誤推論、世界有限與無(wú)限之類(lèi)彼此沖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觀存在的虛假證明等。所有這一切都是舊形而上學(xué)所必然產(chǎn)生的假知識(shí)和偽科學(xué)。這說(shuō)明只有現(xiàn)象可知,本體不可知,從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認(rèn)識(shí)的范圍。而這不可知的本體的存在也就為人擺脫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對(duì)來(lái)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認(rèn)為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為未來(lái)科學(xué)的形而上學(xué)的出現(xiàn)提供了理論前提和基礎(chǔ)。3)
如果我們僅從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討論知識(shí)形成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問(wèn)題,但這僅是康德哲學(xué)的核心之點(diǎn),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發(fā)來(lái)構(gòu)建其更為恢宏磅礴的理論大廈。換言之,康德建構(gòu)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遠(yuǎn)非僅僅要指明知識(shí)形成的可能性問(wèn)題,而是要以人類(lèi)知識(shí)形成的可能性問(wèn)題為基點(diǎn),探討與人類(lèi)自身的生存密切相關(guān)的各種問(wèn)題。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時(shí)期的馳騖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內(nèi)在宇宙,由前批判時(shí)期向世人呈現(xiàn)出的壯觀的自然之圖轉(zhuǎn)而再向世人貢獻(xiàn)一幀人類(lèi)深遂的心靈之畫(huà)。在康德看來(lái),知識(shí)與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yàn)槿祟?lèi)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兩大目標(biāo),即不僅包含自然法則,而且還包含道德法則;最初是在兩種不同體系中表現(xiàn)它們,最終將在惟一的哲學(xué)體系中表現(xiàn)它們。基于這種考慮,康德在研究了人類(lèi)心靈的認(rèn)知能力后,又進(jìn)一步研究人類(lèi)心靈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這三種能力指向的三種對(duì)象——真、善、美。他認(rèn)為其《純粹理性批判》論述了知識(shí)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實(shí)踐理性批判》論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終極目的;《判斷力批判》論述了審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斷力中綜合統(tǒng)一起來(lái),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識(shí)和道德的分離。康德晚年對(duì)自己一生的哲學(xué)研究進(jìn)行了認(rèn)真,他認(rèn)為他一生中哲學(xué)研究的所有問(wèn)題都是圍繞與人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guān)的四個(gè)問(wèn)題展開(kāi)的,當(dāng)他完成《單純理性范圍內(nèi)的宗教》一書(shū)后,給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說(shuō):“很久以來(lái),在純粹哲學(xué)的領(lǐng)域里,我給自己提出的研究計(jì)劃,就是要解決以下三個(gè)問(wèn)題:一、我能夠知道什么(形而上學(xué))?二、我應(yīng)該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著是第四個(gè)、也就是最后一個(gè)問(wèn)題:人是什么(人類(lèi)學(xué))?”4)與上述四大問(wèn)題相對(duì)應(yīng),從而產(chǎn)生了四門(mén)學(xué)問(wèn):認(rèn)識(shí)論,倫,宗教學(xué),文化人類(lèi)學(xué)。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類(lèi)精神文化的全部學(xué)科,它在體系上博大恢宏,內(nèi)涵上豐富深厚,幾乎各個(gè)部分都閃爍著智慧的真知灼見(jiàn),從任何一個(gè)角度看它都呈現(xiàn)一種面貌,以致對(duì)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難。它不像黑格爾哲學(xué)那樣在體系上易于領(lǐng)會(huì),在環(huán)節(jié)上含混難懂,而相反在環(huán)節(jié)上清晰易懂,在體系上卻難以把握。所以,國(guó)內(nèi)外歷來(lái)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點(diǎn)和傾向性的差別,常常各執(zhí)一端、各據(jù)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個(gè)知識(shí)學(xué)家、倫理學(xué)家、美學(xué)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個(gè)科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宗教學(xué)家、法學(xué)家、人類(lèi)學(xué)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離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時(shí),也被專門(mén)化了,仿佛任何一門(mén)科學(xué)都可以從康德這個(gè)百科全書(shū)式的坩鍋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餾、發(fā)酵、膨脹而形成一種新的體系和學(xué)問(wèn)。5)
上述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向我們提出了重新認(rèn)識(shí)和理解康德的任務(wù),即在對(duì)康德進(jìn)行分析研究的同時(shí)還要進(jìn)行綜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則寓于綜合之中,把康德學(xué)說(shuō)看成一個(gè)完整的有機(jī)體:它有著自身的宗旨、基本問(wèn)題和邏輯線索,有著自身的風(fēng)格和特質(zhì),它的各個(gè)部分和環(huán)節(jié)表現(xiàn)出一種有機(jī)的遞演關(guān)系,并服務(wù)于一種終極的目標(biāo)和理想。基于此種認(rèn)知,筆者認(rèn)為康德在東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強(qiáng)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學(xué)術(shù)思想的深層所包含的濃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氣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與人類(lèi)生活緊密相關(guān)的一切實(shí)踐領(lǐng)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問(wèn)題,度量了人類(lèi)心靈的各種功能、條件和界限,它不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攝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無(wú)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現(xiàn)了人的價(jià)值、人格的尊嚴(yán)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從人學(xué)的視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實(shí)質(zhì)。但本論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討康德的人學(xué)思想(筆者對(duì)此另有專論),而是要以此認(rèn)識(shí)為基礎(chǔ),探討康德之后受其人學(xué)思想影響而發(fā)展起來(lái)的各種哲學(xué)、神學(xué)思潮及其這些思潮的生存論轉(zhuǎn)向問(wèn)題。由之,一方面使我們從中尋覓出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神學(xué)話語(yǔ)生存論轉(zhuǎn)向的歷史軌跡,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更為清晰地透視現(xiàn)代哲學(xué)、神學(xué)與康德人學(xué)思想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下面筆者分四條路線展開(kāi)這種考察,這四條路線分別是:費(fèi)希特、謝林、黑格爾的傳統(tǒng)哲學(xué)路線;科學(xué)主義的語(yǔ)言分析路線;人本主義的現(xiàn)象學(xué)路線和現(xiàn)代神學(xué)路線。
二
康德以知識(shí)論為基礎(chǔ),以人為中心的,是近代歐洲哲學(xué)的分水嶺,但誰(shuí)也不能在分水嶺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識(shí)論顯然留下了許多難以解決的。既然知識(shí)以主體和客體的分離為前提,那么這種知識(shí)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識(shí),就活生生的現(xiàn)實(shí)過(guò)程而言,是一種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這種知識(shí)不是真知識(shí)。在康德看來(lái)主體與客體之間固然可以得到相對(duì)的結(jié)合,但卻永遠(yuǎn)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于是這種知識(shí)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
:
1.何爾森.古留加,《康德傳》,賈澤林等譯,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1年版,第121頁(yè)。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參閱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頁(yè)相關(guān)論述。
4.康德著《單純理性范圍內(nèi)的宗教》,李秋零譯,香港漢語(yǔ)基督教文化所,1997年版,第216頁(yè)。
5.范進(jìn),《康德的文化》,文獻(xiàn)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頁(yè)。
6.張世英,《自我實(shí)現(xiàn)的歷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頁(yè)。
7.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0年1月版,第326頁(yè)。
8.葉秀山,《思.史.詩(shī)》,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頁(yè)。
9.陳俊輝,《海德格爾論存有與死亡》,學(xué)生書(shū)局印行,民國(guó)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頁(yè)。
10.鄒詩(shī)鵬,生存論轉(zhuǎn)向與當(dāng)代生存哲學(xué)研究,求是學(xué)刊,2001年第5期,第33頁(yè)。
11.張政文,關(guān)于上帝之在的對(duì)話,求是學(xué)刊,1996年第4期,第20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