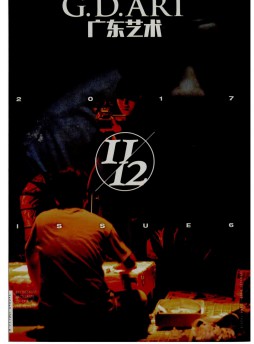藝術領域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藝術領域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論文摘要]考察近幾年高等學校藝術教育的迅猛發展,我們會發現其中存在的大量問題都根源于我們關于藝術教育價值目標缺乏應有的深入思考,以人文教育統領技藝教學,以大眾教育取代精英教育,以審芙教育超越功利教育是高等學校藝術教育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近幾年來,全國高等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呈現出巨大的表里反差。在表層次看來,藝術教育的發展是令人樂觀的.從生源基礎來說,中小學基礎音樂的教育的積極廣泛開展,為高校藝術教育提供了雄厚的招生來源;從高等學校藝術類專業教育來看,各大音樂(師范)院系的持續擴招,各大綜合高校乃至于理工科院校普遍新增藝術院(系或者專業)I從高校藝術教育的推廣普及來講,各級各類高校文藝活動如“藝術節”等節慶如火如荼。以2006—2008年全國的藝術類高考報名人數的增長為例,自2006年全國藝術類高考報名人數過百萬以后,藝術類高考熱潮迭起,全國每年以約20%的水平遞增。高考大省河南2007年更是藝術類高考報名人數創紀錄的四成增長,2008年繼續遞增19.4%。同期,全國2000多所高校中已有逾700所高校新設或則新增藝術類專業。但是,從深層面來看,對于高等學校藝術教育進行全面深入分析和調查的人士都能夠體味到,我們時下的藝術教育教學存在著巨大的隱憂。首先是高校藝術類教學水平在擴招形勢下出現下滑;在就業形勢壓力下,許多高校(尤其是新增藝術類專業學校)的藝術專業辦學出現萎縮局面,更為危險的是許多藝術類專業教師乃至于教學主管領導,沒有把藝術教學的目標確立為開發學生自我創造潛力的獨特活動,視藝術教學為校園中令人愉悅的裝飾品,把藝術教學的存在看做可有可無;在各種藝術具體教學活動中,藝術類教學的發展為技巧技能的強化訓練所左右,教學效果服從和服務于少數人(精英)的成功,教學創造力的培育受困于教學主體——學生缺乏人文精神的理念和對于藝術作品和生活審美感知的淡漠。這些問題最終必將導致我們藝術教育作為美育和素質教育支柱的功能缺位,作為高等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在自己酌教育教學實踐活動中對這一課題加以思考,并尋求應對之策。
一、我國現行的高等學校藝術教育體制分為專業和非專業(公共藝術類教育)兩個層次,分別針對于藝術專業學生和廣大非專業學生。但是無論專業和非專業教學中,我們都有意無意地把技能訓練,技法技巧的強化作為重點。因此無論在教學內容安排、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時數的安排,還是大學生廣泛參與的社團文學藝術活動中,只講求專業忽視技巧背后對于藝術美、人性豐滿的追求。這必將導致藝術教育教學陷入對于技能技巧的無限崇尚,對于時尚藝術的跟風模仿(這對于感知敏銳而又缺乏相應的理論和實踐修養的高校學生是具有自身合理性的)。高校學生藝術設計表現出來的無生機的雷同,音樂創作演奏演唱中呈現出來的刻板的“神似”,這可以在如火如茶的高等學校校園各級各類文藝活動中屢見不鮮。在這種教育教學氛圍內發展的藝術及其作品必然缺乏對于思想的表達,無力于情感信息的表現,更加無法成為透射大學生人生的信仰、理想、情感、人格追求、審美趨向的強力音符。在這種技能技巧教育主導取向指導下的藝術教育,必然導致“習藝愈勤,修養愈淺”。這種所謂的藝術教育在許多教育學者必然是看來是非人文的,非人性的。
由此,以人文精神統領技藝技巧教育就成為藝術類教育教學的必然選擇。當代科學史奠基者薩拉將科學、宗教和藝術視為人類對自身的真、善、美探究的結晶體,將之喻為一個三棱錐體的三個面.從錐體底部的各個側面看去,它們之間似乎相距甚遠,但愈往錐體頂端攀登,它們的距離愈靠近,及至頂端,達到了完整的統一。這就要求我們的技能技巧教學要緊密結合學生對于自我的生活中“真”和“善”的理解,以自我獨特視角的審視、統領和構造自己的技能技巧。這些技能技巧也只有在融入自己對于特定對象和作品的創造性理解之中時,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因為只有這樣,藝術才具有創造者個體的屬性,才具有內在于人自身生命的人文意義,這就是現代意義的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的統一。所以,有必要加強藝術史、藝術欣賞、藝術批評、特別是美學的教育,打破以往技能技巧訓練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局面,通過廣泛而深人的人文學識修養教育和引導,實現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塑造,這是走出‘‘藝術創造一技藝訓練”這一教育教學困境,培育具有創造力的藝術人才的必然選擇.
二、高等學校藝術教育的宗旨在于培養和造就“我國21世紀的一代高素質新人”。因此我們的藝術教育應該是大眾教育,即面向每一個受教育者,以提升整個受教育群體的藝術素養和藝術創造力為最終目標標,這就是藝術教育在高校內的大眾化。但是基于我們傳統的藝術教育的目標取向,藝術只能是一部分人的高雅享受,藝術是一部分人天才的創造,藝術教育只能為一部分人服務,無論是閑暇階層,抑或是天賦異稟者。這種藝術教育的“精英化”實際上否認了高等學校藝術教育的大眾化。鑒于此,美國音樂教育學家貝內特·雷默(BennettReier)曾經基于傳統音樂教育中五線譜的教學作過這樣的論述:“五線譜是非常復雜的,哪怕是單行譜表.如果我們想要普通音樂課上所有的在校孩子們都培養起實際使用它的能力,即使只用于學生們在這樣的課上唱歌和演奏比較簡單的音樂,那我們也必須花上過量的時間來教讀譜技能。事實上,我們已經這樣做了大約兩個世紀了,結果卻是令人羞愧.只有極少比例的學習者的樂譜讀寫能力真正超出了入門階段……,這不是我們現有藝術教育教學活動的真實寫照嗎?特別是面臨時下商等學校持續擴招,我們將面對著越來越多技能水平參差不齊,興趣愛好豐富多樣的大學生,我們的藝術教育的對象受到越來越多的置疑。許多藝術教學工作者對于自己的教育教學的工作目標也越發模糊了。高等學校文化藝術活動,無論專業還是非專業領域,總是只有一部分人,而目總是一少部分人愿意和能、夠參與的活動。這必然導致高等學校藝術教育教學實踐活動與宗旨的錯位。
以上問題的解決的關鍵在于我們轉變對于藝術教育的“精英化”觀念,實現藝術教育的大眾化,更需要我們對于藝術教育的內涵上作更深層次的理解。首先在藝術教育教學的對象上,我們的專業教學和公共藝術類教學應該注重發掘大多數人的藝術潛能,善于激發少數優秀者的才智,以多向度的發掘代替單一的技能技巧評比,最終實現藝術教育對于大多數人的本來意義——學會發現美、欣賞美、創造美。其次,在教學內容的豐富化,我們要特別注意將具有表現力的,能夠激發起學生活力的各種作品,無論其風格特色抑或是來源地域,都應該引入我們的藝術教育教學。而不是與此相反,以在我們現有許多學校的專業音樂教學中,一味排斥所有的流行音樂和“非主流音樂學習外國音樂的興趣僅僅局限在歐洲文化圈之內;更沒有能夠充分尊重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許多優秀的本土音樂文化,近年來高校專業音樂教學對于青歌賽中原生態唱法的“失語癥”的根源就在于此。所以,高等學校應該將藝術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相結合,尤其是重視普及,加強公共藝術類教學的師資,改革教學體系和內容,為最廣大的高校學生創造良好的藝術潛能發掘展示和培養的環境。
三、高等學校的藝術教育,尤其是專業藝術教育,存在著強大的社會功利性慣性。由于傳統社會中的藝術教育是少數人享有,藝術教育強調技能技巧的專業要求,許多人把藝術等同于一種奢侈的享受品。在市場化經濟的作用下,人們思考藝術教育的功能時往往與經濟利益掛鉤。對于許多考生而言,藝術類高考錄取分數較低,以后能夠獲得高薪的期盼,往往是他們涌人藝術類高考群體的重要原因。同樣,許多高等院校在藝術專業設置和教學中,片面強調的是投入產出效益比,追求的是藝術類教學的模式化流水線式教學,無不是功利化在藝術教育中的體現。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許多綜合性、理工類院校中,包括大多數藝術教育工作者乃至于高校的教育主管領導在思考藝術教育的基礎性地位時,仍然把藝術教育功能的基礎建立在以藝修德,以藝開智,以藝促體之上,簡而言之,藝術的功能只能夠依賴依附于德育、智育和體育,這何嘗不是一種更深層次更具慣性的功利化取向呢?這些取向的存在對于許多高等院校的辦學理念、行為發揮著強大的導向作用。由此,我們在高等院校看到的藝術教育教學和校園文藝活動的違背藝術發展規律種種表現就不足為奇了。:
第2篇
關鍵詞:術語,性靈說,文化內涵
中圖分類號:NO4;HO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578(2011)03-0028-04
引言
“性靈”一詞很早就出現于我國文學批評領域,至明清形成一種比較完備的詩文理論――“性靈說”,可見“性靈”和“性靈說”當屬中國文論術語。文論術語的翻譯涉及許多因素,如文化內的語義求證和文化策略、文學傳統、跨語言和跨文化語境的話語分析以及文學意向等。也就是說文論術語除具備術語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深厚的語言和文化內涵;“不僅有語內因素需要考慮,還有語外因素需要考慮,即所謂文化因素等”,其翻譯本質上是文化的翻譯。“性靈”一詞的譯法很多,筆者通過網絡查到的譯法包括soul、spirit、tempera-ment、disposition、personality、intelligence等,這些詞的指稱意義顯然是有差別的。在此筆者通過對“性靈”及“性靈說”文化內涵的分析,結合相關翻譯理論和觀點,對“性靈說”這一術語的翻譯作些探討。
一、“性靈”的含義及翻譯
百度百科對“性靈”含義的注釋如下:
(1)內心世界,泛指精神、思想、情感等
《晉書?樂志上》中有:“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于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于手足。”唐朝孟郊在《怨別》詩中說:“沉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瑾的《精衛石》彈詞第一回:“只有英雄忠義輩,肉身雖死性靈存。”楊朔在《望南山》中提到:“在人們眼里,大南山似乎不是沒有性靈的石頭,倒像最知心知意的親人,有什么酸甜苦辣的話,都可以對他說。”
(2)性情
唐朝元稹《有鳥》詩之二:“有鳥有鳥毛似鶴,行步雖遲性靈惡。”宋朝徐鉉《病題》詩:“性靈慵懶百無能,唯被朝參遣夙興。”
(3)智慧,聰明
唐朝段安節的《樂府雜錄-琵琶》有云:“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也。”《紅樓夢》第九十一回:“你的性靈,比我競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話,我實在對不上來。”
根據第一種含義應譯為soul或spirit,第二種應譯為natural disposition或者temperament,第三種應譯為intelligence。
由此可見,對“性靈”一詞的不同譯文從不同的角度對“性靈”進行了詮釋,傳遞“性靈”不同的含義,沒有一種譯文可以掩蓋其他譯文的存在。雖然“單義”是術語翻譯的重要原則之一,但是許多術語,尤其是文論術語,其含義隨著語境的變化而變化,很難找到可以完全適用的譯文,所以不妨允許多種譯文的存在,它們的關系是平等互補的。
二、“性靈說”的文化內涵及翻譯
基于“性靈”一詞的不同譯文,“性靈說”的翻譯也是莫衷一是,比如theory of disposition、theory oftemperament、soul theory、spirit theory、personality the-ory,等等。“性靈”在不同的語境中傳遞不同的含義,從而有與之相呼應的譯文;而“性靈說”作為一個比較系統的詩文理論,含義單一,其翻譯也應當遵從術語翻譯的單義原則。
為使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轉換減少差異,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根據翻譯的本質,提出了著名的“動態對等”,即“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功能對等是建立在譯文讓讀者產生的反應與源文讓讀者產生的反應對比之上的對等;不僅包括詞匯意義上的對等,還包括語義、風格和文體的對等。奈達認為,在功能對等的各個方面中,“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因為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語的文化意義,并阻礙文化交流。根據奈達的理論,在文學翻譯中,譯者應以功能對等的各個方面作為翻譯的原則,準確地在目的語中再現源語的文化內涵。因此,對“性靈說”一詞,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比較貼切和準確的譯文,首先有必要對其文化內涵進行分析。
1.“性靈說”的文化內涵
“性靈說”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審美理論,其代表人物包括明代“公安三袁”中的中郎袁宏道和清代的袁枚。他們都主張獨抒心靈,強調真情個性,但后者進一步對各種藝術表現手法進行了總結和探索,內涵更加完善,體系愈發完整,是“性靈說”發展的成熟期。許多學者對袁枚的“性靈說”做了分析和歸納,認為其詩藝追求主要體現在真情、個性和詩才三方面。
(1)“性靈說”的真情論
袁枚論詩,“性情”一詞用得最多,他認為性情的真實自然表露才是“詩之本旨”。他說:“詩者,人之性情也。”又說:“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其《續詩品》中說:“惟我詩人,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學。”這些都可以充分說明袁枚把“性情”視為其“性靈說”的主要內涵。
“性情”二字于中國古代哲學著作中,原是分為性與情的。孟子主“性善論”,荀子主“性惡論”,董仲舒則根據的多寡與能否為善分人性為“三品”。韓愈繼承“三品說”,并把情與性相對而論,認為性為情的基礎,三品之性分別決定三品之情。李翱《復性書》又進一步提出“性善情惡說”,主張“復性黜情”;所謂“性”指“仁義禮智信”等先天道德概念,所謂“情”指人之“喜怒哀懼愛惡欲”等感情。宋明理學更鼓吹“存天理,滅人欲”,“天理”即性,“人欲”即情,主張存性滅情。袁枚反對“復性黜情”,并認為“須知性無可求,總求之于情耳”川,所以他所謂的“性情”實指具體可求的“情”,而不抽象空洞的“性”。這也決定了他所說的性靈中的“性情”的含義與理學家“性情”分道揚鑣,而僅落在“情”上。
(2)“性靈說”的個性論
“性靈說”的提出,也是針對當時文藝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一復古主義的風氣而發的。袁枚認為古人創作也要學習,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靈為基本出發點:“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所以,袁枚主張詩人必須具有鮮明的個性和藝術表現上的獨創性,即詩人要具有獨自的思想和生活藝術方面的積累,有其自己的審美感受,并采取別出心裁的藝術構思、藝術手段反映其抒情對象的特征,從而形成獨具一格的作品。袁枚筆下的“性情”一般指情,前已詳述,但“性情”有的指個性,其《仿元遺山論詩》日:“從古風人各性情,不須一例拜先生。曹剛左手興奴右,同撥琵琶第一聲。”“曹剛左手興奴右”是“從古風人各性情”的例證,這里強調的是他們各自的思想氣質、藝術修養等方面的個性特征。
(3)“性靈說”的詩才論
袁枚的“性靈說”不僅指“性情”,還包括“靈
機”。“靈機”是指是人在靈感來臨之際,所表現出的強烈敏銳的感受、新穎獨特的構思和準確完美的藝術表現。這既取決于天資稟賦,也取決于藝術修養,天分和學力共同構成了作家的藝術才能。袁枚首先強調的是作家的天分:“詩文自需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他認為情的表現有借于“才”,“才”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聰穎之人一指便悟,靈心敏慧故能見景物而成詩,運技巧而傳性情。當然,袁枚同樣也重視學力,認為只有具備豐富的學識積累,才能有旺盛的藝術創造力,才能有靈活的創作思維。但學問不是第一位的,而是從屬的,這也正是清代“性靈說”的特色。
2.“性靈說”的翻譯
了解了“性靈說”豐富的文化內涵,筆者參考《美國傳統詞典》(1994),試圖對“性靈說”的翻譯做些探討。顯然,現有的各種“性靈”一詞的譯文似乎都無法全面地詮釋“性靈說”。比如“soul the-ory”和“spirit theory”沒有體現出“性靈說”中“性情”的實質。soul和spirit主要指“人類所具備的有生命力以及充滿生機的本性,具有思考、行動以及感情等能力”,而非袁枚所強調的真情。另外這兩種譯文也沒有涵蓋“性靈說”的個性論和詩才論。“theory of disposition”中的“disposition”在中的解釋為一個人“一貫的性情和脾氣”,沒有體現其個性和才能。“personality theory”中“personality”一詞倒是強調了個性――個人聚集的品質、行為、脾氣、情緒和精神的性格模式,但未體現“情”和“才”。另外,心理學中已有“personality theory”,譯作“人格理論”。“temperament”常常被譯為性情,“tern-perament”可以“廣泛地用于指影響或決定一個人的行動或反應的身體的、情感的和智力特征的總和”,既可以表示“某一特定人的思維、舉止或反應的特征和方式”,又可以表示其“與眾不同的精神和肉體的特征”,即“氣質”。所以相對來說,“tern.perament”一詞還是比較全面地涵蓋了袁枚“性靈說”的三大內容,但是,中國傳統哲學“心性論”常常譯作“theory of temperament”,另外也很容易與波蘭心理學家斯特里勞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氣質調節理論(regulative theory of tempera-ment)相混淆,還是無法滿足奈達的功能對等標準。
同時,“性靈說”作為中國傳統文論術語,其悠久的歷史文化代表了一種特定的詩藝風格――“詩文貴曲,獨出靈機”,是中國歷史上反理學、反復古模擬在文學理論上的具體表現。王東風教授曾撰文論及作用于翻譯過程的四類跨文化因素,其中之一為詞語的文化身份,即詞語的附加意義和語用意義。兩種語言中語義對應的一組詞,其附加意義和語用意義不一定相同。如漢語的“月”所包含的豐富的附加意義和語用意義,如“團圓”及引發思古之幽情,思鄉之愁緒等功能是英語“moon”無法對等的。“性靈說”一詞的翻譯亦需考慮這一跨文化因素:雖然在目的語中能找到與“性情”和“靈性”指稱意義相對應的詞,卻無法表現這一術語所蘊含的極具中國歷史文化特色的詩歌藝術。
權衡之下,筆者認為還是用音譯法來翻譯“性靈說”,即“xingling theory”,既滿足了術語翻譯簡潔的標準,又最貼切地表達了其作為中國傳統文論術語的獨特性,避免文化誤讀。目的語讀者開始可能只知道它是一種中國傳統的詩藝主張,但是通過接觸“性靈”一詞在不同語境中的含義及對中國詩藝文化和變革的了解,必然對“性靈說”的音譯名逐漸熟悉。
第3篇
論文摘要:商周時期,中國藝術結構與王文化及史官文化發生分離,其標志是美飾象征結構意識呈現于藝術的深層執創,并通過與你性瓏念的相互協合,捉成藝術觀念的“實用化”,使中國藝術結構之文化體征有了十分關健竹推進和提升。
美飾象征結構是表還是本,這是認識理解早期中國藝術德性觀念形式觀念演化的根本。本文將著重從如下立論給予闡述:藝術結構是藝術生長乃至文化生長的根本。藝術結構作為一個歷史性概念,在早期藝術蛻變時期,其特殊的表現是“美飾象征”的構成,呈現與轉化。這種“美飾象征”意識在其功能不斷發生變化時也促生了藝術審美底蘊與整個結構機制的轉換。因此,從美飾象征角度探討這種早期藝術結構機制的轉化特點,應具有理論上重要的拓新意義。
一、巫文化美飾變奏
巫文化以自然為對象施行溝通人、鬼、神的功效。自然物之于巫術,啟發人從中獲得某種神靈啟示的憑借,因此巫文化以對自然物的能動美飾為最多。在這種巫文化的能動美飾結構與自然物固有的美飾結構之間,神靈充當著協調者的角色。由于神靈本身是觀念化的,從而它能從與自然物形相不相符方面提供某種意念、憧憬、夢幻和臉想,來使民眾感覺到物化的神靈。對于民眾而言,則是對物的敏銳感受與對神靈的覺知呈正比結合,愈是感性鮮明的自然物。愈韶強化人對神靈的某種敬畏感。于是,內在的矛盾漸漸從這里產生,當不具鮮明感性之物給人的生存以或福或患的影響時,人們雖崇拜也愿其如己之所盼;而習見的色彩鮮艷之物.當它們并不能對人的生活產生有力影響時,人們就動用自己的意志對它的“表象”進行分解,結果就產生了由初民創造的、受神靈統御的美飾之物。這種新創的美飾之物自然把美飾功效看做根本的東西:愈是符合心愿的創造。當然也愈是能激發他們對神靈的特殊體驗與感受。
神靈統馭的美飾結構實質上包含三個方面的構成要素:一是自然實相;二是美化飾相;三是顯德虛相。這三種相,越在古樸階段越合抱為一;越到巫文化晚期越趨向分離。而其中之“實相”,即自然固有之相,會漸漸因附著在神靈(虛化的或粘實的)身上而具有可漂移功能,如光、形、色,怪狀、奇特之野力等。《山海經》有個神名叫昆吾,他的形飾為虎身、九尾、人臉、虎爪。過去多視此為圖騰標識,其實圖騰標識正是自然美飾的綜合之物。從美飾角度對神之昆吾加以分解,虎身之威風,九尾之瀟灑,人臉之平易與虎爪之有力……這些表相無不實現其隱喻功能,使得所飾之神真真切切成為超自然的奇異之神。
具備可漂移功能的美飾受神靈統馭,于是,當神靈在民眾觀念中變得越來越具有實體性時,便使神靈的超異能力外化為對象,“美飾”之相則隨神靈之變與人呈若即若離態勢。神靈的演化依循這樣的程序:1.萬物有靈—自然物依自身之形相而產生相應之神靈觀念。“萬物有靈論”表明諸神靈無明顯尊卑區分,此可稱為自然固有之“神”德;2.萬物擇神有靈—民眾漸漸發現自然禍福施于人并不相同,有的恩澤,有的造害,變幻無常難以捉摸。為此,他們選擇并推重某些天神,如“太陽”、“天”、“山”等等,認為萬物惟其具備天神屬性才有靈性,這又可稱為“天”德。“天神”是天德的美飾,如“昆吾”相傳就主管著天上的九個部落和一個苑圃。與“萬物有靈論”的“神”德相比,“天”德更顯得至高無上。說:“天之本質為道德,而其見于事物也,為秩序。故天神之下,有地抵;又有日月星辰山川林澤之神,降而至于貓虎之屬。皆統轄于上帝。據天神觀念所造的天人之靈。最初是萬物皆靈,而后是萬物因天而靈,現在則是人因秉有了“天德”而成為人間的天神,“天子”即是這種人間“天神”的美稱。此可稱為“天人”之德。史家以我國商代為主“天人”之德的時期,意味著德性觀念由天上正向人間過渡。如果前面對天神的美飾表明對萬物的一種希冀,現在則美飾轉化為象征。所謂“天”不外是人間某種觀念本體的外化。4.依照人的方式創造出的神靈。到了巫術晚期,初民在大量的祭祀活動中發現被外化的神靈只是某種僵硬的象征,毫無鮮活生命氣息,于是人們在天神之外盡量用人的方式來美飾、創造神:商代后期人神的祭祀占據重要位置,表明人的感性呈現借助舊式巫術典儀,被移置到天神身上而使之降為人神。同時鬼神亦為人神的變形。由畏天轉而畏人畏鬼,自然災害變故比之祖先功德不過“小巫”而已。先祖神靈若發怒縫怨則人間會降臨莫大的災難!對此則可稱為“人天”之德。雖然至此美飾人性成份的比例加重,但人類仍腳躇在陰履的暗夜,以異化的人性統馭著人的現實生存。人本意識覺醒的“神靈”。商周之際,雖然祭祀仍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重大內容,但根本性質已發生了轉化,人本意識開始走向覺醒!《尚書?舜典》記述一則舞蹈:人們狂放縱情,邀神同歡:
帝曰:夔!名汝典樂。教宵子:直而溫,寬而果,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予擊石扮石,百獸率舞。
這則巫事的“巫師”是一個管理音樂、舞蹈的“小官”,他“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體驗人與神相溝通的樂趣。“商人了媚神,真可謂彈精竭慮,無所不用其極”“商人尊神事鬼并非只是一種外在的形式,而是發自于內心,來自于民族最深厚、最熾熱的宗教情感”’,4_。固然尊神事鬼有其宗教感覺發展的局限,但宗教形式可以通過信仰讓渡人性蘊含二青銅藝術從商代的純祭祀功效到周代融合審美寄托,就反映了審美意識的覺醒。如紋飾圖騰方面,“在西周早期的青銅器紋飾中,出現了一種為殷商所未見的長垂角獸面紋。最具西周特征的紋飾是蝸體獸紋,形狀怪詭,想象奇特。殷商本是以玄鳥為圖騰的,但殷商的青銅器紋飾中,鳳凰的紋飾不算很多,最多的倒是西周初期。審美意識最集中地體現著人本意識,特別是在中國禮樂相通,樂教就是禮教,結果德性的審美象征就不時回復到其原位,在強化審美效力的同時,把更現實、深刻的人倫觀念浸潤到人的意識深處;《周禮?春宮?宗伯下》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著宗。樂德教國子,中、和、抵、庸、孝、友”這是一種向人開放樂教的觀念表達,它說明從事巫祭者,以后不一定為至尊王族,凡“有德”“有道”者都可以做巫師,而且只要做得好,死了一樣像神靈可受祭拜(樂祖)。這里人本意識的凸顯似乎借助著宗傳達出來,但“中、和、抵、庸、孝、友”這些熔鑄社會、個人意識于血緣情結的觀念,卻體現了把人的自在生命、情感,與人的現實位置聯系起來看待的意識,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與自我人本非常切近的觀念。在東方社會,一旦形成這樣的觀念,我們說它的倫理歸宿與審美境界就達到某種價值坐標的諧和。那崇高的祭樂,表達的不正是一種對崇高人德的向往嗎?
上述有關神靈、德性的演化,表明美飾在文化內涵的整個演變過程,始終都扮演一個基本角色:“飾相顯德”。無論這“德”為“神”德,抑或“天”德、“人”德,都要通過“美飾”助人悟解以獲得人倫境界的提升。而作為顯德之“飾”,它的符號特性,又略顯復雜,或為具實體性媒介的顯示(實相),或為游離實體的“物相”呈示(飾相),亦可成為純粹觀念喻說之象(虛相)……幾種復雜情形表明:符號功能的不單一,特別是符碼的呈相可漂移這一特點,為美飾的效用發揮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語義符號學對此也稱贊不已,有的強調它的能指表象性,有的則認為表象的轉換其實正是“意指”的轉換,里面暗含著由文化規約賦予的結構效用。“它們系有限狀態的因素集合而成,這些因素又是以偶對方式構造并受某些組合規則制約,這些組合規則能夠生成這些成分的有定串和無定串,或有定鏈和無定鏈。這種觀點對說明美飾的藝術結構意味頗有益處,我們可據此理解:飾相顯德,表明既可作為獨立的能指成分充分施現其審美效用,又可在轉換中不斷移置所指,兩相結合則得以始終維系藝術之固有結構規律。從而,審美結構規律成為最基礎性的限定,它限定必然呈示的“有限的因素集合”,以審美規律的“偶對方式構造”、“顯相”,服務于“有定鏈和無定鏈”的崇“德”職能。
二、“風和夷樂”的功能性標識
商代父權、男權對人本意識的重視,還只是社會性的結構。藝術的美飾象征結構也與此相應,側重于以粗獷獰厲之美體現某種社會化的抽象觀念、因此,總體而言,商代的藝術結構水平是被動性的,不像周代以自主性的審美意識完成藝術結構之協調與整合。
但任何東西的生成都不是在“是其所是”時才得到生長的權利,相反,更多的情況是在“非其所是”時孕育了它的雛形。此即黑格爾所說“自為”乃通過“他在”向“自在”的返歸“本質的東西直接轉化為非本質的東西,反之亦然……力的交互作用就是發展了的否定。因此,透過商代的審美現象,我們就可以看到反映審美自覺的主體性端倪。以甲骨文為例,在占卜中凝聚了非常多的主體意愿_如《甲骨文合集》所收之14294版和14295版系兩種類同的風向記錄,其中涉及“西風”的用詞兩版相“顛倒”:一為“西方曰豐風曰彝”,一為“西方曰彝風曰豐”考古學家認為應以“西方日彝風曰豐”為準,另一種可能系誤刻,因為彝風即夷風,是和風之意它與“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語序及“修飾”之意相通—和風送“泰”,萬物豐成、但筆者以為所謂筆誤說也不過后人的揣測,難免以今斷古的隔膜因為甲骨文這類卜測事皆依當時的祭拜心意而定。甲骨文是根據灼烤龜甲的紋理進行推測的,它帶有濃重的心理機動性,故不能全然如今天的筆記那樣來看心理、觀念的轉換很難有什么標準版本可言,所以無論龜甲所“顯”為何,當不存在“筆誤”一說。依此而論,則“西方曰豐風曰彝”大可考究。李圃《甲骨文選注》說:本段文字“為前期武丁時期刻辭。…記錄了古代東西南北四方神名和四方風神名,是我國四方的順序、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稱的最早的文獻資料”初民對方位及風名如此稱謂,顯然是把主體的體驗、渴望熔鑄其中的緣故、“西風”曰“豐風”,說明秋季豐收的景況;“彝風”則是“相就命名”或“反向述辭”,把由西方或西風之“豐”所帶來的內在贊嘆轉化為歌詠式表述、語言學家馮?洪堡特這樣理解:“所謂的野蠻人可能比較接近這樣一種自然狀態,他們的語言恰恰處處顯示了大量超出需要、豐富多樣的表達詞并不是迫于需要和出于一定目的而萌生,而是自由自在地、自動地從胸中涌出的…語言結構的規律與自然界的規律相似,語言通過其結構激發人的最高級,最合乎人性的(menschlichste)力量投人活動,從而幫助了人深人認識自然界的形式特征”從西風的秋季豐收‘到萬物彝和、平泰的詠唱,不正反映了一種樸素而能動的主體審美意識嗎?在這種描述中,融合著判斷和價值,把本屬自然的東西,經過人的感知滲透又還給了自然,真可謂最純樸的“主體意識”的呈露!
西周初年,所謂主體意識由巫術典儀所涉之對象、物件而逐漸過度到一種“藝術化”美飾表達,即力使主體之能動性成為一種“功能性標識”。“藝術化處理”是指一切祭祀之事,不再只是純粹典儀,也是樂制禮制的有機組成。《周禮?春宮?宗伯下》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變”,《說文》指“更也”,意思是隨著音調節律的變化,起到對祭祀各種神、抵、人鬼轉換的功效,這里顯然“樂變”在前,“鬼神”現后,而“樂變”又因何而變,雖然沒有直接說明是因人的內在情緒、心意之變而變,但也指出“以樂德教國子,中、和、抵、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語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罄》大夏》、《大鑊》、《大武》,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詣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說明在“樂變”的前面,有更重要的制約性存在,即’‘道”與“德”,能行“教”之“所本”這樣,“樂變”的職能就真正體現為可作為以自在功效服務于“教”的功能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