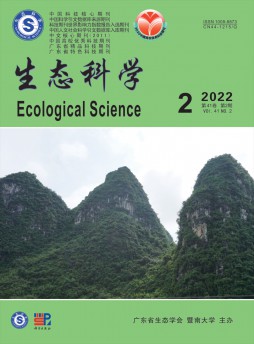生態(tài)哲學(xué)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生態(tài)哲學(xué)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在以人為中心的主體性思想的演進(jìn)中,我們發(fā)現(xiàn):在中世紀(jì)之前,人確立了對(duì)除神以外的其他存在者的主體性地位;到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人的主體性地位有所擴(kuò)展,人已確立了對(duì)包括神在內(nèi)的所有存在者的主體性地位。然而在這一漫長(zhǎng)的歷史過程中,這種主體性思想并不占統(tǒng)治地位,其統(tǒng)治性地位的確立,是從笛卡爾開始的。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由于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地位,標(biāo)志著近代哲學(xué)的開端。這種哲學(xué)以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看待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把自然界人為地分為主體和客體:人是絕對(duì)的主體,是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統(tǒng)治者;自然界是客體,是為人的存在,是人所支配、處置的對(duì)象,它除了具有“消費(fèi)性價(jià)值”之外,在人的眼中不具有諸如“生態(tài)價(jià)值”、“系統(tǒng)價(jià)值”等任何其他價(jià)值。也就是說(shuō),自然界整體及其自然物如果不是為了人而存在的,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存在著的無(wú),它只有依賴于人才能獲得存在的理由和價(jià)值。這樣,在自然界面前,人就成了不需要任何約束的高高在上、狂妄自大、為所欲為的主體,自然成了可以任人統(tǒng)治、踐踏、宰割的對(duì)象。正是在這種對(duì)象性思維的統(tǒng)治下,自然不斷地被征服、被掠奪并正在逐漸地走向終結(jié)。
二、以主體性哲學(xué)為基礎(chǔ)的西方管理是反生態(tài)管理
以西方近代主體性哲學(xué)為指導(dǎo),在西方管理理論和實(shí)踐中,管理的研究者和實(shí)踐者都只看到了自然物的“消費(fèi)性價(jià)值”,都片面地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的最大化,忽視了人與自然的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縱觀西方管理思想史,各種管理理論幾乎概莫能外地聚焦同一中心———片面追求經(jīng)濟(jì)效益。泰羅的科學(xué)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謀求最高工作效率,而達(dá)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學(xué)的管理方法代替舊的經(jīng)驗(yàn)管理,因此科學(xué)管理理論重點(diǎn)解決的是如何用科學(xué)的方法提高生產(chǎn)現(xiàn)場(chǎng)的生產(chǎn)效率問題;法約爾的組織管理理論所研究的中心問題是組織結(jié)構(gòu)和管理原則的合理化,管理人員職責(zé)分工的合理化問題,以確保效率的提高;行為科學(xué)學(xué)派試圖通過行為科學(xué)的研究,掌握人們行為的規(guī)律,找出對(duì)待工人、職員的新手法和提高生產(chǎn)效率的新途徑;管理科學(xué)學(xué)派的主導(dǎo)思想是使用先進(jìn)的數(shù)學(xué)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生產(chǎn)力得到最為合理的組織,以獲得最佳的經(jīng)濟(jì)效益;決策理論學(xué)派以統(tǒng)計(jì)學(xué)和行為科學(xué)作為基礎(chǔ),力圖在管理領(lǐng)域?qū)ふ乙惶卓茖W(xué)決策方法,以尋找到實(shí)現(xiàn)最佳效益的最佳方案;社會(huì)—技術(shù)系統(tǒng)學(xué)派認(rèn)為,組織不僅是一個(gè)社會(huì)系統(tǒng),而且也是一個(gè)技術(shù)系統(tǒng),只有把二者協(xié)調(diào)起來(lái),才能解決組織矛盾從而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可見,西方管理思想的終極旨趣都是為了追求本單位經(jīng)濟(jì)效益、利潤(rùn)的最大化,而沒有考慮或很少考慮企業(yè)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過程中對(duì)自然的破壞和影響,沒有考慮到自然的生態(tài)價(jià)值和生態(tài)平衡問題。這種片面追求效益而忽視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的管理是當(dāng)前迫切需要反思的。在現(xiàn)代管理實(shí)踐中,人們皆自覺不自覺地在行為上忽視人與自然的生態(tài)關(guān)系。管理學(xué)家指出各行業(yè)中管理工作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本單位的既定目標(biāo),通過決策、組織、領(lǐng)導(dǎo)、控制和創(chuàng)新等職能進(jìn)行著任務(wù)、資源、職責(zé)、權(quán)力和利益的分配,協(xié)調(diào)著人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現(xiàn)代管理實(shí)踐僅僅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目標(biāo),在社會(huì)系統(tǒng)內(nèi)部協(xié)調(diào)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而排除了人和自然之間的生態(tài)關(guān)系。在西方近代主體性哲學(xué)的指導(dǎo)下,西方管理理論和管理實(shí)踐在一定程度上對(duì)組織和組織賴以生存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以及其應(yīng)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之間的關(guān)系關(guān)注不夠,這就使組織形成了以片面追求效率為核心的功利的、反生態(tài)的管理觀。這樣,西方管理理論對(duì)人掠奪自然的事實(shí)視而不見,在客觀上放任和加速了這種掠奪的進(jìn)程,從而造成了資源危機(jī)、能源危機(jī)、人類生存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危機(jī),這種危機(jī)本質(zhì)上就是人的生存危機(jī)。因此,為了人類的永續(xù)生存,用一種新的哲學(xué)和管理理論來(lái)指導(dǎo)管理實(shí)踐,已經(jīng)成為大勢(shì)所趨。這種新的哲學(xué)就是生態(tài)哲學(xué),新的管理理論就是生態(tài)管理理論。
三、生態(tài)危機(jī)時(shí)代需要生態(tài)哲學(xué)指導(dǎo)下的生態(tài)管理
哲學(xué)具有時(shí)代性,任何哲學(xué)都是其時(shí)代的產(chǎn)物。生態(tài)哲學(xué)是以生態(tài)世界觀為基礎(chǔ)而構(gòu)建的新哲學(xué),是一種不同于西方主體性哲學(xué)所尊崇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的新哲學(xué),是以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與穩(wěn)定為基礎(chǔ)的整體論哲學(xué)。生態(tài)哲學(xué)是一種整體論的生態(tài)世界觀。一般認(rèn)為,世界由自然界、人類社會(huì)和思維所構(gòu)成。而社會(huì)是人的社會(huì),思維也是人的思維,因此世界就是由自然界和人所構(gòu)成的世界,世界觀就是關(guān)于自然和人的總的看法和態(tài)度。生態(tài)哲學(xué)所堅(jiān)持的生態(tài)世界觀在對(duì)人、自然的態(tài)度上堅(jiān)持整體論、系統(tǒng)論的觀點(diǎn)。人作為地球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員,是自然界高度發(fā)展的產(chǎn)物,但人無(wú)論怎樣特殊,都與自然具有同一性,其生存須臾離不開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整體平衡所提供的清新的空氣、溫暖的陽(yáng)光、充足的食物、清潔的飲用水等。目前,地球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已經(jīng)遭到了嚴(yán)重的破壞,其終極原因就在于西方近代主體性哲學(xué)沒有把包括人在內(nèi)的自然界視為一個(gè)整體,而是把統(tǒng)一的自然界人為地割裂開來(lái)。生態(tài)管理就是在生態(tài)哲學(xué)的指導(dǎo)下,合理吸收生態(tài)學(xué)、系統(tǒng)論、經(jīng)濟(jì)學(xué)、管理學(xué)、現(xiàn)代技術(shù)科學(xué)等學(xué)科知識(shí),反思現(xiàn)代管理理論和實(shí)踐,在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標(biāo)上,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在維護(hù)整個(gè)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和平衡的前提下,實(shí)現(xiàn)人的可持續(xù)生存。生態(tài)管理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龐雜,涉及人類生產(chǎn)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個(gè)領(lǐng)域。從不同的視閾進(jìn)行研究,可以構(gòu)建出不同的生態(tài)管理理論體系。從國(guó)內(nèi)的研究狀況來(lái)看,以“生態(tài)管理”為關(guān)鍵詞的學(xué)術(shù)專著和論文都很少。筆者才疏學(xué)淺,暫無(wú)力構(gòu)建系統(tǒng)的生態(tài)管理理論。這里,提出幾點(diǎn)有關(guān)生態(tài)管理的基本原則:
第一,實(shí)行生態(tài)管理,要堅(jiān)持整體論的管理觀。
由于地球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是人類可持續(xù)生存的基礎(chǔ),因此為了人類的生存,必須更新管理理念,重新審視現(xiàn)代的片面追求利潤(rùn)、片面追求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管理目標(biāo),把維護(hù)地球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作為當(dāng)代乃至未來(lái)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標(biāo),作為管理的出發(fā)點(diǎn)和歸宿。一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都必須服從、服務(wù)于這個(gè)理念和目標(biāo)。今天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層管理者、領(lǐng)導(dǎo)者,必須從忽視人與自然和諧關(guān)系的現(xiàn)代管理理論中“超拔”出來(lái),充分認(rèn)識(shí)到現(xiàn)代管理理論及其指導(dǎo)的管理實(shí)踐給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造成的危害,認(rèn)識(shí)到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fā)展下去,人類就將走向不歸路。
第二,實(shí)行生態(tài)管理,關(guān)鍵是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
整個(gè)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個(gè)有機(jī)聯(lián)系的整體。在這個(gè)整體中,不同的自然物不僅具有供人消費(fèi)的“消費(fèi)價(jià)值”,而且具有維護(hù)整個(gè)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的“生態(tài)價(jià)值”,這兩種價(jià)值都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然而,這兩種為人類生存所必須的價(jià)值卻是正相反對(duì)的:對(duì)于同一自然物來(lái)說(shuō),實(shí)現(xiàn)它的“消費(fèi)性價(jià)值”,就必須犧牲它的“生態(tài)價(jià)值”;而實(shí)現(xiàn)其生態(tài)價(jià)值,又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其消費(fèi)性價(jià)值。面對(duì)這種窘境,人類只能有一種選擇,即必須對(duì)人類改造自然的管理實(shí)踐進(jìn)行必要的規(guī)約和限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從而保證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與穩(wěn)定。人類生存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平衡的保持,是人類管理實(shí)踐活動(dòng)的底線。
第三,實(shí)行生態(tài)管理,各國(guó)應(yīng)“各行其是”,并且積極進(jìn)行國(guó)際合作。
第2篇
一
講“天人之際”首先必須講“天”,但“天”究竟是什么?歷來(lái)有爭(zhēng)議。在《易傳》中,明顯涉及到兩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從《易傳》各篇的論述來(lái)看,答案似乎是明確的。
《易傳》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對(duì)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個(gè)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體上又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當(dāng)時(shí)人們所能觀察到的宇宙空間,似與天文學(xué)、宇宙學(xué)有關(guān);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氣層,似與氣象學(xué)有關(guān)。這兩方面的內(nèi)容在《易傳》中都有論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風(fēng)、雷、雨、露,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易傳》在談到“天”之諸象時(shí),都與生命現(xiàn)象有關(guān),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傳》)、“天地變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則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個(gè)自然界。在《易傳》看來(lái),天地間的萬(wàn)物皆“統(tǒng)”之于天,地與天相輔相成,不可缺一,但地畢竟“順承天”,因此,天能夠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傳》中已經(jīng)基本上沒有了。
地與天相對(duì)而言,指人類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類賴以存在的家園。沒有任何一種生命是能夠離開大地的,天空中飛鳥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傳》稱之為“易之門”,“易之蘊(yùn)”,從這個(gè)意義上講,“周易”就是講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蘊(yùn)涵,這是一個(gè)分析的命題。正如《系辭上》所說(shuō):“乾坤毀,則無(wú)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傳》不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稱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義,這才是《易傳》“自然觀”的特點(diǎn)。它是從人的生命存在出發(fā)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傳》說(shuō):“大哉乾元,萬(wàn)物資始,乃統(tǒng)天。”坤卦之《象傳》說(shuō):“至哉坤元,萬(wàn)物資生,乃順承天。”萬(wàn)物的生命來(lái)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yàn)槿绱耍墩f(shuō)卦傳》將乾、坤二卦視為父母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這所謂“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這個(gè)大父母,不是指人類家庭中的父母,是講人與自然界的關(guān)系,不是講人類自身的血緣關(guān)系。當(dāng)然,這里的父、母二字是從人類引伸而來(lái)的,因此有人說(shuō)《易傳》對(duì)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種“擬人化”、“移情說(shuō)”,并進(jìn)而歸結(jié)為原始神秘主義。
我們說(shuō),這種比擬確實(shí)具有某種“原始性”,因?yàn)樗菑娜祟惿淖钤肌⒆畛跏嫉母炊缘模侨绻堰@說(shuō)成是人與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義,則是有問題的。因?yàn)椤兑讉鳌凡粌H明確區(qū)分了人與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學(xué)說(shuō)(下面還要討論),而且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易傳》講天人關(guān)系,常常用比擬的方法,(“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類”、“擬議”等等),這里有深刻的哲學(xué)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學(xué)語(yǔ)言或認(rèn)識(shí)淪的邏輯語(yǔ)言所能說(shuō)明。因?yàn)樗幪幎缄P(guān)心生命問題,關(guān)心人的問題,講自然界也是從人與自然界的生命關(guān)系立論的,不是將自然界單純地看作一個(gè)“對(duì)象”。
在《易傳》看來(lái),人與自然界本來(lái)是統(tǒng)一的,不能分離。人類離了自然界,還有什么生命?自然界離了人類,還有什么意義?乾、坤二卦是代表天、地的,天地本是以發(fā)育生長(zhǎng)萬(wàn)物為功能。天之大,具有無(wú)限性、永恒性,所謂“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就是形容其無(wú)限永恒之意義的。在現(xiàn)代宇宙學(xué)的發(fā)展中,有些學(xué)者提出宇宙是“有限”的,這種學(xué)說(shuō)如果成立,那也是自然科學(xué)的問題,并不妨礙天對(duì)人而言具有無(wú)限性意義。所謂“萬(wàn)物資始”,是說(shuō)明萬(wàn)物生命是由天而來(lái)的,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夠“生物”,也能夠“載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礎(chǔ)。所謂“萬(wàn)物資生”,就是說(shuō)明萬(wàn)物的生命是由地而生成的。在這個(gè)意:上,并且僅僅在這個(gè)意義上《易傳》將天地比之為父母,并沒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義。所謂“稱乎父”、“稱乎母”,只是說(shuō)在發(fā)育生長(zhǎng)萬(wàn)物的意義上,天可“稱”之為父,地可“稱”之為母,父母只是個(gè)“稱呼”,并不是說(shuō)天地是真父母。人們說(shuō),“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這不只是文學(xué)語(yǔ)言,也是真正的哲學(xué)語(yǔ)言。可見,稱天地為父母,是有哲學(xué)意義的,人類生命確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經(jīng)予的,人對(duì)自然界有一種崇敬之心,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類從自然界獲得生命,反而傲視自然?暈約毫瞬黃稹?nbsp;
二
這樣看來(lái),人作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過是自然界的一個(gè)組成部分,但這一部分,確實(shí)與其他萬(wàn)物不同,因?yàn)槿耸怯欣硇缘模谧匀唤缬衅涮厥獾牡匚慌c作用。這正是《易傳》所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也是《易傳》哲學(xué)的特殊意義之所在。《系辭傳》與《說(shuō)卦傳》都講到“三材之道”,將天、地、人并立起來(lái),視為“三材”,并將人放在中心地位,這足以說(shuō)明人的地位之重要。所謂“材”,不只是材質(zhì)、材料,而且指才能。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沒有人之道?天之道在“始萬(wàn)物”,地之道在“生萬(wàn)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所有這些,都是《易傳》所要講座的問題。其結(jié)論就是,人不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萬(wàn)物”。
《系辭下》說(shuō)“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周易”是由卦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jī)蓚€(gè)爻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對(duì)“易”卦的這種解釋,意在說(shuō)明,“周易”就是講天、地、人三材之道的,進(jìn)而言之,是講人與天地自然界的關(guān)系問題的。這反映了《系辭》作者對(duì)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之極端重視,三材并列而人居其一,說(shuō)明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系辭傳》雖提出了“三材”,卻沒有說(shuō)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說(shuō)卦傳》回答了這個(gè)問題。(由此或可說(shuō)明《系辭下》與《說(shuō)卦傳》的先后問題,即先有《系辭下》而后有《說(shuō)卦傳》;當(dāng)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即先有《說(shuō)卦傳》說(shuō)明“三材之道”,后來(lái)的《系辭下》不必再說(shuō)了。這類問題只是順便說(shuō)說(shuō),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說(shuō)卦傳》說(shuō):“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yáng),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說(shuō)卦傳》指明“三材之道”的實(shí)際內(nèi)容,不僅發(fā)揮了《易經(jīng)》思想,而且概括了《易傳》各篇的基本精神。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對(duì)應(yīng)、相互聯(lián)系的,這不僅是一種“同”關(guān)系,而且是一種內(nèi)在的生成關(guān)系和實(shí)現(xiàn)原則,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則,人之道則是實(shí)現(xiàn)原則,二者缺一不可,在這一點(diǎn)上,天、地、人真正統(tǒng)一起來(lái)了。
陰陽(yáng)作為天之道,是兩種普遍的要素或成分,同時(shí)又是兩種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正是這兩種要素及其作用推動(dòng)了自然界的一切變化,產(chǎn)生了一切生命。《莊子·天下篇》說(shuō),“易以道陰陽(yáng)”,就是對(duì)陰陽(yáng)普遍性意義的認(rèn)識(shí)。在中國(guó)哲學(xué)中,陰陽(yáng)可用來(lái)解釋一切現(xiàn)象,因此有人稱之為“陰陽(yáng)模式”。但陰陽(yáng)的根本意義是說(shuō)明生命的,不是說(shuō)明無(wú)生命的自然界的,是生成論的,不是機(jī)械論的,因此它和一般所說(shuō)的正負(fù)還不完全一樣。柔剛顯然是同陰陽(yáng)對(duì)應(yīng)的,但陰陽(yáng)是無(wú)形的,多以氣言之,故為天之道,柔剛則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為地之道。大地上的萬(wàn)物多是有形的,可以感覺到,觸摸到,故以柔剛概括之,有些則是就其性能而言的,即具有剛?cè)嶂浴F(xiàn)代科學(xué)與哲學(xué)所說(shuō)的“剛性材料”與之也有相近的意思。石是剛的,土是柔的,火是剛的,水是柔的,但這些東西及其性能與生命并不是毫無(wú)關(guān)系,在《易傳》看來(lái),它們恰恰是生命存在的條件或基礎(chǔ)。
仁義則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義,也只有人才能盡其仁義而“成物”。所謂“順性命之理”,就是指人而言的,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又是與陰陽(yáng)、剛?cè)嵊新?lián)系的,這種聯(lián)系正是從生命的意義上說(shuō)的。天地能生物,所生之物便有性命,便足以與天地并立而為三,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里有一種“進(jìn)化”的無(wú)窮過程,這種過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義,就是說(shuō),自然界的生成變化是向著一個(gè)有秩化的目的進(jìn)行的,人的仁義之性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產(chǎn)生的。對(duì)此《序卦傳》進(jìn)行了系統(tǒng)說(shuō)明。“有天地,然后萬(wàn)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wàn)物。”很清楚,自然界的萬(wàn)物是由天地“生”出來(lái)的,這種生成是由低向高發(fā)展的,《序卦傳》還描述了這一過程的順序,即:“有天地然后有萬(wàn)物,有萬(wàn)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這可說(shuō)是萬(wàn)物生成與人類進(jìn)化的一幅自然歷史圖畫。“萬(wàn)物”是指一切存在物,包括有生命與無(wú)生命之物,而以無(wú)生命之物為主。“男女”則是指有生命之物,不只是指人類,雌雄、牝牡皆用“男女”代表。“男女”也就是“陰陽(yáng)”。由此往后,才有夫婦、父子、君臣等家庭、社會(huì)關(guān)系,由此便有仁義之性,禮義之措。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義與天地之陰陽(yáng)、柔剛是一種生命的“進(jìn)化”關(guān)系,而不是簡(jiǎn)單的橫向關(guān)系,它說(shuō)明,人性是不能離開“自然性”的。這所謂“自然性”,不是純粹生物學(xué)上所說(shuō)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義和道德意義,也就是說(shuō),對(duì)人而言,自然界不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義和價(jià)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夠與天地并立而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種特殊地位,但這種特殊地位追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給予的,而且同時(shí)便負(fù)有一種使命。
古人顯然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天文”、“地理”和“人文”進(jìn)行了仔細(xì)觀察,并從生命活動(dòng)中體會(huì)到人與天地即自然的生命關(guān)系,而不是將自然界僅僅作為人之外的對(duì)象去觀察而已。《系辭下》說(shuō):“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yuǎn)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究竟是不是伏羲所作,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之“圣人”作八卦,是在“仰觀俯察”與“近取諸身,選取諸物”的過程中作成的。這里所說(shuō)的“近取諸身”,不僅僅是純觀察的觀察問題,而與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動(dòng)密切相關(guān),不僅是客觀的觀察,而且是主觀的體驗(yàn),觀察和體驗(yàn)是不能分開的,也就是說(shuō),在觀察中有生命體驗(yàn),在體驗(yàn)中有客觀觀察。這樣作的結(jié)果,當(dāng)然不只是創(chuàng)造出純客觀的“自然哲學(xué)”,而是人與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學(xué)。
這一點(diǎn)被某些人稱之為原始落后性與末開化性,即沒有將人從自然界真正分離出來(lái),建立起人的獨(dú)立意識(shí)或人的主體性。但是,如前所說(shuō)《易傳》并沒有將人與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視人的地位與作用。那么,問題在哪里呢?問題在于,《易傳》己經(jīng)自覺地意識(shí)到,人與自然之間,有一種內(nèi)在的生命聯(lián)系,而不只是認(rèn)識(shí)主體與認(rèn)識(shí)對(duì)象之間的關(guān)系。當(dāng)《乾·象傳》說(shu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坤·象傳》說(shuō),“地勢(shì)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時(shí),就不僅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義,而是變成了人的內(nèi)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當(dāng)《乾·彖傳》說(shuō),“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說(shuō),“利貞者,性情也”時(shí),這個(gè)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內(nèi)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體而言,就是仁義。這就是《易傳》講“三材之道”的義蘊(yùn)所在。
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經(jīng)過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歷來(lái)說(shuō)“易”者,都認(rèn)為“易”有三義,三個(gè)方面的意義合起來(lái),就能代表“易”的全部精神。所謂三義就是,一者“變易”,即認(rèn)為“易”是講變化之道的,也就是講“辯證法”的;這方面的內(nèi)容確實(shí)很豐富,不必多舉。二者“簡(jiǎn)易”,即認(rèn)為“易”雖然包羅萬(wàn)象,但有一個(gè)最簡(jiǎn)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稱之為“套子”,一切事物和現(xiàn)象都可以裝迸這個(gè)套子,都可以用這個(gè)“模式”來(lái)說(shuō)明,甚至可以數(shù)字化、符號(hào)化。這方面確實(shí)也有很多例子。三者“不易”,即認(rèn)為“易”雖講變化,但這變化之“道”卻是永恒不變的,這也可以說(shuō)是“以不變應(yīng)萬(wàn)變”。這方面的內(nèi)容《易傳》也講過。總而言之,這些說(shuō)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易傳》的精神。但是,除此之外,“易”有沒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精神?這正是今日研究易學(xué)者應(yīng)當(dāng)進(jìn)一步追問的。其實(shí),《易傳》早已作出了回答,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義。講“變易”也好,“簡(jiǎn)易”也好,其核心是“生”即生命問題,這就是“易”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說(shuō),“周易”不是一般的講世界的辯證法,也不是一般的講宇宙“模式”,而是落在生命上,所謂乾坤、陰陽(yáng)、變化等等,都要落在“萬(wàn)物化生”(《系辭下》)上,最終落在人的“性情”、“性命”上。用《易傳》的話說(shuō),“生生之渭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辭上》),這才是“易”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系辭下》的“生生之謂易”,是對(duì)“易是什么”這一問題的最直接最明確的回答,也是對(duì)“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徹的說(shuō)明,也可以說(shuō)是對(duì)“易”之何以為“易”的一個(gè)最明確的定義。“易”就是“生”,這也是一個(gè)分析命題。“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上常被人們所引用的這些話,正是從“周易”而來(lái)的,也是最能反映中國(guó)哲學(xué)精神的。“生生”是連續(xù)不斷的生成過程,沒有一刻停息,它不是有一個(gè)“主宰者”創(chuàng)造生命,而是自然界本身不斷地生成,不斷地創(chuàng)造,天地本身就是這個(gè)樣子,以“生生”為基本的存在方式。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就在于“生”,所謂“變化”之理,“易簡(jiǎn)”之理,說(shuō)到底就是“生生”之理。
《易傳》進(jìn)而提出天地以“生”為“德”,這就不只是講生成問題,而是賦予天地以某種道德意義。馮友蘭先生所說(shuō)“天”之諸義中之一義,就有義理之天、道德之天,《易傳》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但是仔細(xì)說(shuō)來(lái),天地雖以“生”為“大德”,但天還是那個(gè)自然之天,地還是那個(gè)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沒有某種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識(shí),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樣,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創(chuàng)造世界,創(chuàng)造人類,也不是如同斯賓諾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絕對(duì)命令”那樣,按照某種“必然性”或“先驗(yàn)法則”創(chuàng)造秩序和人類道德。這些都是實(shí)體論的說(shuō)法,無(wú)論“上帝”還是“物自身”,都是絕對(duì)實(shí)體,而《易傳》所說(shuō)“天”(或“天地”),并不是實(shí)體,而是“大化流行”的過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體”。
那么,天地以“生”為“德”又有什么意義呢?它說(shuō)明了自然目的性這一意義,即自然界本身在其變化生成中有一種有序化的秩序,這種有序性包涵著生命的目的性,我們稱之為自然目的性。
所說(shuō)“意義”,當(dāng)然是對(duì)人而言的,離開人,便無(wú)“意義”,但這種對(duì)人而言的“意義”,卻又是自然界所具有的,不是人給它安上去的。何以能知道?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體驗(yàn)而知。《易傳》論“天人之際”,其奧妙就在這里。這不僅是一個(gè)價(jià)值推論,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實(shí)。“意義”雖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但是如果進(jìn)一步追問,人的創(chuàng)造,人的目的,又是從何而來(lái)?答案只能有三種:一是由上帝或神給予的(自然神論包括在內(nèi)),或精神實(shí)體給予的,這是宗教神學(xué)或理性化的神學(xué)所主張的;二是由人自己創(chuàng)造的,這是人類中心論所主張的;三是由自然界給予的,這就是《易傳》哲學(xué)所主張的。《易傳》之所以崇尚自然,談到“天地”時(shí)總有一種崇敬感與使命感,原因就在這里。
自然界的生命意義在于“生生之德”,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乾·文言》:“元者,善之長(zhǎng)也。”),“德”與“善”都是說(shuō)明生命價(jià)值的,也是對(duì)人而言的,其實(shí)現(xiàn)則在于人。《易傳》言天必言人,言人則必言天,其用意也在于此。人之德性與目的,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條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給予的,但要真正變成人的“德性”,則只能靠人自己去實(shí)現(xiàn)。后來(lái)的中國(guó)哲學(xué)如玄學(xué)、佛學(xué)與宋明理學(xué),有“本體論”之說(shuō),特別是宋明理學(xué),提出一個(gè)道理本體與宇宙本體,作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價(jià)值的最后根源,但這所謂“本體”,同西方哲學(xué)所說(shuō)的本體(即實(shí)體)是不同的,這種不同與《易傳》哲學(xué)是直接有關(guān)的(理學(xué)家們都以《易傳》為其理論來(lái)源與基礎(chǔ)),而《易傳》哲學(xué)雖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謂之道”以及“太極生兩儀”之說(shuō),但就其理論意義而言,則是講生命過程的,是講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過程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應(yīng)起何種作用。所以,人的問題始終是它所關(guān)注的。《系辭上》說(shuō):“一陰一陽(yáng)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是《易傳》講天人之學(xué)的真正目的。
四
按照《易傳》的天人觀,人作為天地之所“生”,只是萬(wàn)物中的一個(gè)成員,如果以“類”言之,人只是萬(wàn)物中的“一類”成員。但人畢竟不同于萬(wàn)物,人不僅有特殊地位,而且有特殊作用,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仁義”之性,有“性命”之理,這就決定了,人在天地萬(wàn)物之中,負(fù)有一種神圣的使命。
所謂“天人之際”,不是只從“天”一方面來(lái)說(shuō)的,也不是只從“人”一方面來(lái)說(shuō)的,而是從天、人兩方面來(lái)說(shuō)的,只有從人與自然兩方面著眼,才能說(shuō)明二者的關(guān)系。從“天”方面說(shuō),“天地氤氳,萬(wàn)物化醇;男女構(gòu)精,萬(wàn)物化生”(《系辭下》),這是一個(gè)自然的過程,但是這并沒有完結(jié),“萬(wàn)物化生”之后,便有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問題。就這一層說(shuō),又有兩方面。一是天對(duì)人而言,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一是人對(duì)天而言,便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實(shí)現(xiàn)自然界賦予人的目的,完成人之所以為人之性。
《易經(jīng)》乾卦卦辭有“元、亨、利、貞”四字,《文言傳》解釋說(shuō),元、亨、利、貞是天之“四德”,又稱之為仁、禮、義、正四德,這就真正變成人的德性了。天之“四德”之中,“元者,善之長(zhǎng)也”,是說(shuō)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長(zhǎng)點(diǎn),但這還只是一種“向善”的自然過程,真正“繼”此而生者便是人,人繼此而為善,這才是自然目的的實(shí)現(xiàn)。人雖然“繼”之而有善,但能不能成為人之“性”,還有待人自身去完成,這卻是人自身的事,不是“繼”之而為善就算完事了。這說(shuō)明“善”只是一種目的,并沒有完全實(shí)現(xiàn)出來(lái),真正實(shí)現(xiàn)出來(lái)還要“成性”。
事實(shí)上〈易傳》所說(shuō)的“元”,就是儒家所說(shuō)的“仁”,“仁”即是愛,是一種道德情感。《系辭上》說(shuō):“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有敦厚的仁德,便能愛萬(wàn)物。這應(yīng)是人性的真正實(shí)現(xiàn),也是仁的目的的實(shí)現(xiàn)。《坤·象辭》說(shuō):“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厚德”也就是“敦仁”,“載物”也就是“愛物”。不愛,能有負(fù)載萬(wàn)物的責(zé)任與氣量嗎?
“成性”是人自身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人自身的事,它關(guān)系到如何對(duì)待自然界的萬(wàn)物這樣一個(gè)問題。對(duì)待自然界萬(wàn)物的態(tài)度問題能不能解決,又關(guān)系到人能不能“成性”的問題。所謂“成性”,便蘊(yùn)涵著對(duì)萬(wàn)物的愛,對(duì)萬(wàn)物有一種義務(wù)。“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系
辭上》)“存存”即存其所存,所存之“存”,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其所存,就像出人門戶一樣,是人人應(yīng)當(dāng)實(shí)行的,這個(gè)“道義”就是道德義務(wù),有沒有“道義”,就是能不能盡道德義務(wù)。可見《易傳》講“存在”哲學(xué),是有道德意義的,是要追究存在的價(jià)值和意義的。這個(gè)價(jià)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與道德理性。
《易傳》雖講普遍的道德理性,但也不能歸結(jié)為泛道德主義。在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的問題上,它既講仁,同時(shí)也講知,是仁知并重、德業(yè)并進(jìn)的。“知周乎萬(wàn)物,而道濟(jì)天下,故不過。……樂天知命,故不憂。”(《系辭上》)既要以知“周”天下,又要以道義“濟(jì)”天下。它還主張“窮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變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類的生活。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自然界,取之于自然界,這是人類共同的需要,《易傳》也不例外,它對(duì)歷史上的技術(shù)與工具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是很尊重的,所謂“進(jìn)德修業(yè)”(《乾·文言》)、“崇德廣業(yè)”、“盛德大業(yè)”(《系辭上》)之學(xué),不僅從道德上樹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處理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原則,而且從智性上確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認(rèn)識(shí)自然的必要性,“周易”之所以“廣大悉備”,由此亦可以得到說(shuō)明。
“知周乎萬(wàn)物”之知,無(wú)疑具有客觀認(rèn)識(shí)的性質(zhì),“極深研幾”、“當(dāng)名辨物”(《系辭上》)等等,都有認(rèn)識(shí)論、邏輯學(xué)的意義。至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乾·文言》),則包涵著古代協(xié)同學(xué)的原則。觀察、推類等認(rèn)識(shí)方法也都受到極大的重視。知對(duì)于德、業(yè)都很重要,尤其與功業(yè)、事業(yè)有直接聯(lián)系,而“業(yè)”是以“致用”為目的的。治理天下是業(yè),創(chuàng)造發(fā)明也是業(yè),安排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活動(dòng)更是業(yè),其中當(dāng)然包涵著對(duì)自然界的認(rèn)識(shí)與研發(fā)。這些都是毫無(wú)疑問的。
但是,《易傳》的“崇德廣業(yè)”之學(xué),將德性與知性結(jié)合起來(lái),統(tǒng)一起來(lái),形成整體互動(dòng)的聯(lián)系,而不是只朝著一個(gè)方向發(fā)展,更不是向知性一面發(fā)展。這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德”不僅是個(gè)人的德性,而且要施之于萬(wàn)物,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樣,使萬(wàn)物得到它的潤(rùn)澤。只有這樣,才能稱之為“盛德”,也只有這樣,才能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易傳》的人文主義精神就是表現(xiàn)在這里。
“人文”一詞是《易傳》首先提出的,泛指人類文明。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類所從事的實(shí)踐活動(dòng),都屬于“人文”。但是《易傳》認(rèn)為,所有這一切都不能離開自然界,且只能在處理好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過程中去創(chuàng)造,去完成。這就是“人文化成”。《賁·彖
傳》說(shuō):“剛?cè)峤诲e(cuò),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shí)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包括“地文”)代表自然界的變化生生之道。按照《系辭》、《說(shuō)卦》所說(shuō),天之道為陰陽(yáng),地之道為柔剛,但《賁·彖傳》卻以剛?cè)嵴f(shuō)明天文,可見,剛?cè)峒词顷庩?yáng)。剛?cè)峤诲e(cuò)而生變化,變化而生生不已,如上所說(shuō),我們不能將《易傳》所說(shuō)的“變化”簡(jiǎn)單地理解為機(jī)械的物理變化(盡管它是最基本的),也不能僅僅理解為生物學(xué)的自然進(jìn)化,而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與人類活動(dòng)密切相連的生命流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進(jìn)化論的意義。這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元者善之長(zhǎng),……”以及“復(fù)其見天地之心”(《復(fù)·彖傳》)的意義所在。萬(wàn)物變化是在時(shí)間中進(jìn)行的,生命流行是在時(shí)間中展開的,所以“時(shí)”的觀念非常重要。春生、夏長(zhǎng)、秋收、冬藏,就是“時(shí)變”,這種變化直接關(guān)系到人類的活動(dòng),因此,要“觀天文”而“察時(shí)變”,便人類活動(dòng)與自然界的“時(shí)變”相適應(yīng)、相諧調(diào)。只有在人與自然相適應(yīng)、相諧調(diào)的情況下,才能創(chuàng)造出人類文明,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從而出現(xiàn)“天下文明”的景象。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化成”固屬于“人文”,卻不離“天文”,不僅如此,“化成”本身即包涵著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這一目的,即不僅要行之于“天下”(指社會(huì)),而且要行之于“天地”(指自然)。這是人的責(zé)任與使命,用《易傳》的話說(shuō),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象傳》)。“裁成”決不是對(duì)自然界實(shí)行制裁、控制或任意改造,以滿足人的欲望,以顯示人的成功,而是裁度以成之,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輔相”即是輔佐天地以完成其生長(zhǎng)之“宜”。大要生存,當(dāng)然需要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提供了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問題的關(guān)鍵是,人不能只“索取”而不“回報(bào)”,只享受其“權(quán)利”而不盡其“義務(wù)”。正好相反,人在獲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條件的同時(shí),更要“裁成”、“輔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義,從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易傳》所說(shuō)的“裁成”“輔相”與《中庸》所說(shuō)的“參贊”“化育”具有相同的意義,都是指通過人的活動(dòng),實(shí)現(xiàn)自然界的生生之道。這既是人的責(zé)任和義務(wù),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人類的知性活動(dòng)應(yīng)當(dāng)在這一前提下進(jìn)行。
五
《易傳》的最高理想,是實(shí)現(xiàn)“天人合一”境界。這里所說(shuō)的“天”,具有超越義,但并不是實(shí)體,它無(wú)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稱,是一種哲學(xué)的概括。所謂“天人合一”境界,就是與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狀態(tài),也可以說(shuō)是一種“自由”。《易傳》所說(shuō)的“大人”、“圣人”,就是實(shí)現(xiàn)了這種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為“大”,“圣人”之所以為“圣”,就在于他們能與“天德”合一,充分實(shí)現(xiàn)生命的意義與價(jià)值。
《乾·文言》說(shuō):“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shí)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shí)。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這是對(duì)“天人合一”境界的一個(gè)全面的描述,它不僅包括“大人”的道德人格,而且包括“大人”的種種功業(yè)。“與天地合其德”之“德”,從天的方面說(shuō),就是“生生之德”,“元亨利貞”之德;從人的方面說(shuō),就是“性命”之德,“仁義禮正”之德。“生”始終是天德之根本義,由“生”而有仁義等等德性。既然如此,所謂“合德”,就是完成生命的意義,實(shí)現(xiàn)生命的目的,其中當(dāng)然包涵著“裁成”“輔相”之功。
《易傳》還提出理、性、命三個(gè)范疇,成為后儒特別是宋明儒家建立其理學(xué)體系的重要來(lái)源。周敦頤在其《通書》中,專門設(shè)立“理性命”一章,進(jìn)行了發(fā)揮,其他理學(xué)家也都視之為重要范疇。后來(lái),理成為理學(xué)的最高范疇,性成為理學(xué)的核心范疇,命則成為溝通天人的關(guān)鍵范疇。這三個(gè)范疇就其關(guān)系而言是講“天人合一”的,其基本思路在《易傳》中已經(jīng)形成了。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shuō)卦傳》)就是這一思想的比較完整的表述。
第3篇
關(guān)鍵詞:生態(tài)危機(jī);欲望;科技理性;和諧生態(tài)觀
在人類發(fā)展史上,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出現(xiàn),人類將自身設(shè)定為主體的同時(shí)自然界的存在成為“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使得作為主體的人對(duì)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過度盤剝和壓榨,導(dǎo)致了生態(tài)危機(jī)的產(chǎn)生。從根源上探究,人類追求財(cái)富的欲望是這一問題的邏輯起點(diǎn)。因此,探究生態(tài)危機(jī)的根源,需要將人類的財(cái)富欲望納入歷史通道進(jìn)行反思。財(cái)富欲望的張力隨著世俗社會(huì)商業(yè)精神的發(fā)育而開啟,在利潤(rùn)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帶來(lái)財(cái)富的自然界。發(fā)達(dá)的科技是對(duì)自然界進(jìn)行深度開發(fā)的關(guān)鍵力量,技術(shù)在人類財(cái)富欲望的驅(qū)使下,“促逼”著自然界,使其被過度開發(fā)而遭到破壞,深層次里破壞著“人—自然命運(yùn)共同體”。
一、生態(tài)危機(jī)產(chǎn)生的根源:人類追求財(cái)富的欲望
現(xiàn)代社會(huì)是以資本為軸心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在馬克思看來(lái),資本的存在在于價(jià)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價(jià)值的運(yùn)動(dòng)就是它自身的運(yùn)動(dòng),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獲得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奇能,是因?yàn)樗莾r(jià)值。它會(huì)產(chǎn)仔,或者說(shuō),它至少會(huì)生金蛋。”[1]因此資本家的目的不是獲得使用價(jià)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rùn),而只是謀取利潤(rùn)的無(wú)休止的運(yùn)動(dòng),這種絕對(duì)的致富欲,這種價(jià)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儲(chǔ)藏者所共有的。”[2]這種財(cái)富欲望具有一種擴(kuò)張自身的內(nèi)在張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義定位,它乃是指社會(huì)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產(chǎn)生對(duì)一定的物質(zhì)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識(shí)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動(dòng)傾向,也可以說(shuō)是趨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類欲望的閘門被打開以后,欲望的張力使得人類對(duì)貨幣、資本的追求日益強(qiáng)烈。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當(dāng)貨幣越來(lái)越集中于少數(shù)人的手中,這導(dǎo)致了貨幣持有者與無(wú)產(chǎn)者之間的極大的不平等。貨幣持有者極力將貨幣繼續(xù)投入再生產(chǎn)過程中,以生產(chǎn)出更多的剩余價(jià)值。無(wú)產(chǎn)者則對(duì)貨幣持有者掌握的生產(chǎn)資料日益依賴,越來(lái)越多的勞動(dòng)力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剩余價(jià)值的工具。貨幣持有者日益成為勞動(dòng)者、生產(chǎn)資料的主宰者,貨幣力量由此轉(zhuǎn)化為能夠在生產(chǎn)過程中帶來(lái)增殖的資本力量。資本的擴(kuò)張邏輯不斷生產(chǎn)出剩余價(jià)值并將其投入擴(kuò)大再生產(chǎn)。“資本擴(kuò)張過程是資本向自然界的擴(kuò)張,向自然資源的擴(kuò)張。資本自誕生以來(lái)進(jìn)行的數(shù)百年的擴(kuò)張過程,就是將從地表到地下,從表層到深層的自然資源不斷貨幣化、資本化,吸收到不斷運(yùn)轉(zhuǎn)的資本機(jī)器內(nèi)部的過程,也即吞噬自然資源的過程。”[4]因此,資本的擴(kuò)張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對(duì)自然界無(wú)休止的掠奪為前提。“作為一種生產(chǎn)要素的資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資源,“作為一種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資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資源,才能表現(xiàn)為資本的現(xiàn)實(shí)存在。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guān)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jī)是紡棉花的機(jī)器。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guān)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jià)格一樣。”[7]因而“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huì)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huì)形態(tài)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它體現(xiàn)在一個(gè)物上,并賦予這個(gè)物以特有的社會(huì)性質(zhì)。”[8]世界上越來(lái)越多的自然資源被納入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中,納入資本擴(kuò)張的邏輯體系中,由此進(jìn)一步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kuò)張的欲望。人類不斷開拓著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資本追求擴(kuò)張的本性具有使這些資源進(jìn)入擴(kuò)張?bào)w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在人類欲望的驅(qū)動(dòng)下與貨幣相結(jié)合,進(jìn)入生產(chǎn)領(lǐng)域中,便被賦予了人的主觀意志,被資本化后便獲得了不可遏制的擴(kuò)張本能。我們亟需對(duì)人類瘋狂行為背后的原因進(jìn)行深層次追問。人類企圖將一切資源都資本化,納入資本擴(kuò)張的邏輯體系,刺激著人類追求財(cái)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種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為它的武器,支配了勞動(dòng),鼓起了勇氣,激發(fā)了遠(yuǎn)見,使人類的一切能力日益發(fā)達(dá)。每一種欲望獲得滿足時(shí)的享受或愉快,對(duì)于那些克服了障礙和完成了自然的計(jì)劃的人,是一種無(wú)窮盡的報(bào)酬的源泉。”[9]追求財(cái)富的欲望是資本擴(kuò)張的推動(dòng)力。人類把勞動(dòng)價(jià)值注入到自然資源中時(shí),資源被資本化了,人類追求財(cái)富的欲望這種心理因素就通過物質(zhì)得以顯現(xiàn)出來(lái)。這種獲得物質(zhì)資源的力量承載著人類追求資本擴(kuò)張的意志,使得人類進(jìn)入了瘋狂追求物質(zhì)力量———資源。當(dāng)人類對(duì)尚未資本化的資源進(jìn)行開發(fā),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預(yù)付金,因此必須獲得利潤(rùn),否則就將血本無(wú)歸,因此人類陷入資本邏輯體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動(dòng)著人類的行為動(dòng)機(jī),人類的行為由于這一欲望的滿足而終止。這一欲望的滿足又激發(fā)了新的欲望的產(chǎn)生,一種物欲造波著另一種物欲,由此導(dǎo)致欲望動(dòng)力機(jī)的馬達(dá)強(qiáng)勁,不斷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kuò)張的觸角。亞當(dāng)•斯密指出:“每一個(gè)人對(duì)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對(duì)于住宅、衣服、車馬、家具等舒適品和裝飾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沒有限制和確定界限的。”[10]滿足這類沒有限制的欲望的資本擴(kuò)張也就處于無(wú)止境狀態(tài)。鮑德里亞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一書中也深刻指出了,這種資本擴(kuò)張的欲望邏輯,“物品都徹底地與某種明確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聯(lián)系。確切地說(shuō)這是因?yàn)樗鼈儗?duì)應(yīng)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是社會(huì)邏輯,也可以是欲望邏輯———那些邏輯把它們當(dāng)成了既無(wú)意識(shí)且變幻莫測(cè)的含義范疇。”[11]這是深度資本擴(kuò)張的欲望帶來(lái)的消費(fèi)社會(huì)的圖景。尚未開發(fā)的資源被資本化后獲得了一種價(jià)值通約的社會(huì)性,這種經(jīng)濟(jì)性符號(hào)通兌著對(duì)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價(jià)值通約有著一種將五彩斑斕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過貨幣把異質(zhì)性的社會(huì)變成一種可量度、可計(jì)算、可兌換的存在,使得人類的生活世界被貨幣和資本的增殖體系宰制。人類在這個(gè)體系下追求資本的不斷擴(kuò)張,并在資本力量的驅(qū)動(dòng)下研發(fā)出越來(lái)越多的高尖端的先進(jìn)科技,進(jìn)一步武裝著人類進(jìn)行資本擴(kuò)張的欲望。人類的資本擴(kuò)張欲望在吞噬著自然資源的可再生能力。當(dāng)愈來(lái)愈多的自然資源消耗在資本體系中時(shí),資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斷衰減,最終導(dǎo)致資源枯竭、環(huán)境破壞。“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把追求利潤(rùn)增長(zhǎng)作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價(jià)追求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zhǎng)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shí)向環(huán)境傾倒越來(lái)越多廢物,導(dǎo)致環(huán)境急劇惡化。”[12]人類破壞著與自己的身體發(fā)膚密切相關(guān)的自然機(jī)體而不自知。資本擴(kuò)張欲望無(wú)資源可尋而無(wú)法得到滿足時(shí),或許人類真的會(huì)將觸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將世代詩(shī)意的棲居破壞,人類被瘋狂追求資本擴(kuò)張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與生態(tài)危機(jī)的勾連
發(fā)達(dá)的科學(xué)技術(shù)對(duì)生態(tài)危機(jī)負(fù)有不可推卸的責(zé)任,科學(xué)技術(shù)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lái)快捷、便利、現(xiàn)代化的同時(shí),也給人類帶來(lái)了資源破壞與生態(tài)危機(jī)。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人類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證的同時(shí),人類對(duì)科技的依賴性愈加強(qiáng)烈,對(duì)科技的盲目樂觀的態(tài)度實(shí)際上帶來(lái)的是人的主體地位的缺失,人類的深度異化并日益成為機(jī)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說(shuō)“科學(xué)進(jìn)展是一種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導(dǎo)致生態(tài)危機(jī)的技術(shù)力量。在古希臘和中國(guó)的先秦時(shí)期,將對(duì)德性的追求視為“至善”,柏拉圖、老子等哲學(xué)家都提出技術(shù)是“奇技巧”會(huì)敗壞人的心智,反對(duì)技術(shù)的應(yīng)用。近代以來(lái),隨著“科技樂觀主義鼻祖”培根提出“知識(shí)就是力量”,科學(xué)知識(shí)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迅速發(fā)展為人類戰(zhàn)勝自然的武器。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進(jìn)一步確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這種反思哲學(xué)中成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著,自然是敵人,是一種被規(guī)約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東西都被歸為人的勞動(dòng)而非自然的饋贈(zèng),自然只不過是提供了毫無(wú)價(jià)值的物質(zhì)材料。”[14]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證使得自然越來(lái)越被淪為人類征服的對(duì)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體論變成一種實(shí)證的技術(shù)手段,這種技術(shù)手段追求對(duì)自然的深度開發(fā),以達(dá)到人類自身的財(cái)富欲望,將自然定義為為人的利益而服務(wù)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內(nèi)在價(jià)值的利益驅(qū)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類的價(jià)值判斷,如對(duì)真、善、美的價(jià)值追求等。科技的發(fā)展使科學(xué)的理念成為現(xiàn)實(shí),帶來(lái)便捷與舒適的同時(shí),也越來(lái)越拋棄了對(duì)人文意義的追求。科技的發(fā)展不斷助推著人類財(cái)富欲望的擴(kuò)張,也使人類面臨越來(lái)越多的生存困境與自然困境。比如,農(nóng)藥、化肥、催熟劑等化學(xué)藥劑的超標(biāo)使用,在提高產(chǎn)量的同時(shí)卻破壞了土壤,同時(shí)產(chǎn)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藥物殘留,直接危害人類自身。人類開始意識(shí)到科技理性所導(dǎo)致的人的發(fā)展悖論。人類開始將科技理性作為批判與討伐的對(duì)象加以審視。首先對(duì)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盧梭,他認(rèn)為科學(xué)每往前推進(jìn)一步,人就隨之往后墮落一尺,因此他將科學(xué)定義為人類的禍患和敵人。在《論科學(xué)與藝術(shù)》中,他指出:“科學(xué)的創(chuàng)造神是一個(gè)與人類安寧為敵的神。”[15]胡塞爾也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觀念被實(shí)證地簡(jiǎn)化為純粹事實(shí)的科學(xué)。科學(xué)的‘危機(jī)’表現(xiàn)為科學(xué)喪失生活意義。”[16]科學(xué)家在實(shí)驗(yàn)室里喪失了主觀性,拼命追求物的邏輯而缺失了對(duì)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動(dòng)力因,不斷求解著X而忽視了科技對(duì)人類應(yīng)用領(lǐng)域的后果。實(shí)證科學(xué)導(dǎo)致了現(xiàn)代人漫不經(jīng)心地丟掉了那些對(duì)真正的人來(lái)說(shuō)至關(guān)重要的問題的思考,使人類陷于不幸的困境。貝爾納在《科學(xué)的社會(huì)功能》中指出:“把科學(xué)應(yīng)用于實(shí)際所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武器使戰(zhàn)爭(zhēng)變得更為迫近而可怕,使個(gè)人的安全幾乎降低到毫無(wú)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認(rèn),假如不是由于科學(xué),這些禍害不至于象現(xiàn)在這個(gè)樣子。正是由于這個(gè)原因,科學(xué)對(duì)文明的價(jià)值一直受到了懷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學(xué)必須接受審查。海德格爾認(rèn)為技術(shù)作為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促逼”著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與此同時(shí),人類自身也成為被“促逼”的對(duì)象。對(duì)自然和對(duì)人類自身的“促逼”達(dá)到了“座架”,“座架占統(tǒng)治地位之處,便有最高意義上的危險(xiǎn)。”[18]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認(rèn)為,工具的價(jià)值在于它被主體運(yùn)用在實(shí)現(xiàn)主體目的時(shí)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種效用邏輯。科學(xué)技術(shù)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邏輯下發(fā)展起來(lái)并成為對(duì)人類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馬爾庫(kù)塞延續(xù)了對(duì)科學(xué)技術(shù)批判的思路,認(rèn)為科學(xué)技術(shù)在發(fā)展的過程中缺失了對(duì)事物的人文意義的考量,只追求技術(shù)手段的實(shí)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學(xué)發(fā)展成為一種奴役人類的異化形態(tài),社會(huì)發(fā)展成為一種人性扭曲的病態(tài)社會(huì),導(dǎo)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嚴(yán)的喪失。以科學(xué)技術(shù)為載體的高度發(fā)達(dá)的工具理性剪斷了人與自然的臍帶關(guān)系,同時(shí)工具理性的體制化運(yùn)轉(zhuǎn)也侵占著人類的生活世界,導(dǎo)致人與人之間被各自分離的意見的機(jī)械組合的量化計(jì)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圖以對(duì)世界的操縱為目標(biāo),在影片的情節(jié)推進(jìn)中體現(xiàn)的非常明顯。工具理性實(shí)質(zhì)上是科技發(fā)展進(jìn)程中產(chǎn)生的異化現(xiàn)象,工具的發(fā)展正從帶給人類的裨益走向反面,越來(lái)越缺失對(duì)人類自身的存在論境域的思考,成為危害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自身發(fā)展的“罪惡之源”。科學(xué)技術(shù)強(qiáng)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給人類帶來(lái)的便捷與舒適是不容質(zhì)疑的,但是科學(xué)的發(fā)展和運(yùn)用離不開人類的導(dǎo)控。人類之所與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類自身價(jià)值理性的畸形、正確價(jià)值觀的缺失。科學(xué)技術(shù)從屬于資本的邏輯體系時(shí),逐利的秉性操控著科技,瘋狂的資本擴(kuò)張欲望帶來(lái)科技的飛速發(fā)展,這種科技的發(fā)展當(dāng)然是一種人類僅僅為滿足自身利益的異化的發(fā)展?fàn)顟B(tài)。這種異化狀態(tài)可以深層次追溯到主體性哲學(xué)的痼疾,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來(lái),發(fā)現(xiàn)了自身的主體性力量,“人是萬(wàn)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人的主體性得到了無(wú)與倫比的彰顯。然而人類在將自身設(shè)定為主體的同時(shí)也就意味著其他的存在對(duì)人類來(lái)說(shuō)都是“他者”(Theothers),這就導(dǎo)致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人類在自然科學(xué)與工業(yè)革命的迅猛發(fā)展中感到歡欣鼓舞,主體性力量達(dá)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盲目自信,科技與工業(yè)在主體性力量下發(fā)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帶來(lái)了物質(zhì)生活的日益豐盈。但是人類卻沉迷于機(jī)器與技術(shù)的世界中,技術(shù)越來(lái)越高端、機(jī)器越來(lái)越精密,人類對(duì)工具理性越來(lái)越著迷,將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視為客體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對(duì)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的考量之下畸形發(fā)展,由此破壞著與人類發(fā)展休戚相關(guān)的自然界機(jī)體。
三、基于對(duì)象性關(guān)系的和諧生態(tài)觀
人類的財(cái)富欲望在科學(xué)技術(shù)的助推下不斷擴(kuò)張,最終帶來(lái)了生產(chǎn)危機(jī)。那么能否像一些學(xué)者所提出的那樣,消滅資本也就消滅了人類的財(cái)富欲望,生態(tài)危機(jī)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馬克思指出,“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類社會(huì)的發(fā)展需要資本,只有通過資本才能創(chuàng)造出資產(chǎn)階級(jí)這一最發(fā)達(dá)和最多樣的生產(chǎn)組織。資本作為人類剩余勞動(dòng)的結(jié)晶,本無(wú)善惡是非可言,其性質(zhì)主要取決于它運(yùn)用于何種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下以及人類運(yùn)用資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說(shuō)對(duì)資本擴(kuò)張的考察也就是對(duì)人自身的反省。人類在世界資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尋找到一個(gè)與自然之間的合理距離。馬克思指出,“人們需要合理地調(diào)節(jié)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lái)統(tǒng)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wú)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lái)進(jìn)行這種物質(zhì)交換。”[20]人類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類無(wú)機(jī)的身體,人與自然不是簡(jiǎn)單的主體與客體的關(guān)系。生態(tài)倫理學(xué)基于舊唯物主義的理論,將人與自然主客二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jià)值觀念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人類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將只對(duì)人類有意義的倫理觀、價(jià)值觀賦予自然,自然就淪為了人類利用征服和掠奪的對(duì)象。人類的主體地位導(dǎo)致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始終將與自身生存休戚相關(guān)的自然視作“他者”,自然成為滿足人類利益的奴隸。人類無(wú)限膨脹的欲望導(dǎo)致對(duì)自然的無(wú)限制開發(fā)掠奪,產(chǎn)生了一系列生態(tài)災(zāi)難。生態(tài)倫理學(xué)把自然當(dāng)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觀事物而不是與人產(chǎn)生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人類學(xué)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對(duì)人類的意義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將自己視為主體的人類竭盡所能去掠奪自然,以滿足自身的需求與欲望。埃里希•弗羅姆指出“我們奴役自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來(lái)改造自然,結(jié)果是自然界越來(lái)越多地遭到破壞。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們對(duì)它的敵視態(tài)度使我們?nèi)祟愖兊妹つ科饋?lái),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自然界的財(cái)富是有限的,終有枯竭的一天,人對(duì)自然界的這種掠奪欲望將會(huì)受到自然界的懲罰。”[21]人類錯(cuò)誤的生態(tài)觀導(dǎo)致無(wú)節(jié)制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而忘記了自然與人的生命休戚相關(guān)的對(duì)象性關(guān)系。人類在資本的驅(qū)動(dòng)下瘋狂破壞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時(shí)也是在破壞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環(huán)境,即人類在進(jìn)行著自我毀滅。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并不是單純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生態(tài)倫理學(xué),同樣也不能簡(jiǎn)單地回溯到“生態(tài)中心主義”。生態(tài)中心主義認(rèn)為“自然物的多樣性具有它自身的內(nèi)在價(jià)值”[22],所有自然物因?yàn)樽陨砉逃械膬?nèi)在價(jià)值應(yīng)當(dāng)?shù)玫奖Wo(hù),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受到保護(hù)。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tài)中心主義“僅僅是對(duì)諸如人類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間的對(duì)立這樣古老的二元論的重新闡述。”[23]“這里永遠(yuǎn)存在的二元論觀念往往妨礙了知識(shí)和有意義的實(shí)踐的真正發(fā)展。實(shí)際上,這種觀念中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duì)立’的觀念長(zhǎng)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與自然二分法的生態(tài)學(xué)理論導(dǎo)致的生態(tài)學(xué)困境。人類錯(cuò)誤地將自然視為外在于人的獨(dú)立存在物,這種自然被誤以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義只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也正是錯(cuò)誤地將人與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價(jià)值為中心,導(dǎo)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態(tài)中心主義”。幸運(yùn)的是,人類已經(jīng)意識(shí)到上述兩種基于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確的生態(tài)觀的問題所在,并已經(jīng)開始采取行動(dòng),為建構(gòu)和諧生態(tài)觀而努力,和諧的生態(tài)有賴于人與自然的對(duì)象性關(guān)系。馬克思將自然劃分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與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馬克思認(rèn)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lái)的自然界,對(duì)人來(lái)說(shuō)也是無(wú)。”[26]“非對(duì)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脫離自然界這一對(duì)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duì)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對(duì)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xiàn)實(shí)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lái)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28]事實(shí)上,現(xiàn)實(shí)的、有意義的自然是對(duì)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獨(dú)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樣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duì)象的自然界。對(duì)象性關(guān)系意味著“別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個(gè)‘我’,就成為我的對(duì)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內(nèi)隱,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個(gè)眼睛。只有在別人身上,我才具有對(duì)類的意識(shí)。”[29]“也只有在社會(huì)中,自然界對(duì)人來(lái)說(shuō)才是人與人聯(lián)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它的存在。”[30]這就意味著人與自然是作為對(duì)象性關(guān)系而存在的并通過對(duì)象性活動(dòng)而相互內(nèi)在聯(lián)系。這種對(duì)象性活動(dòng)即人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人類通過實(shí)踐活動(dòng)創(chuàng)造對(duì)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現(xiàn)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xiàn)實(shí)……從而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31]通過實(shí)踐活動(dòng)建構(gòu)“人—自然命運(yùn)共同體”的和諧生態(tài)觀,人在與自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隨著實(shí)踐活動(dòng)而不斷深化,自然成為人的“無(wú)機(jī)身體”。通過實(shí)踐活動(dòng)人類建構(gòu)起與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對(duì)象性關(guān)系以及實(shí)踐活動(dòng)來(lái)研究人與自然休戚相關(guān)的“命運(yùn)共同體”。這種“命運(yùn)共同體”不能屈從于資本力量和人類的財(cái)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犧牲自然為代價(jià)換取人類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相反人的財(cái)富欲望應(yīng)該服從“人—自然命運(yùn)共同體”的和諧生態(tài)觀,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應(yīng)立足于“人—自然命運(yùn)共同體”的和諧生態(tài)觀。這才是滿足人與自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正確的生態(tài)觀。
作者:鄭柏茹 單位: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參考文獻(xiàn):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0、179.
[3][9]張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非理性世界[M].上海:立信會(huì)計(jì)出版社,1995:96、103.
[4]魯品越:資本邏輯與當(dāng)代現(xiàn)實(shí)[M].上海: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6:111.
[5][6]伊特韋爾、米爾蓋特、紐曼:新帕爾格雷夫經(jīng)濟(jì)學(xué)大辭典(第1卷)[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1996:356、362.
[7][26][27][28][30][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3、220、210、211、187、162-163.
[8][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2、928.
[10]亞當(dāng)•斯密:國(guó)富論(上卷)[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3:158.
[11]讓•鮑德里亞:消費(fèi)社會(huì)[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1.
[12]福斯特:生態(tài)危機(jī)與資本主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3.
[13]波普爾:科學(xué)革命的理性[J].世界科學(xué),1979(8).
[14]施特勞斯:現(xiàn)代性的三次浪潮,現(xiàn)代性基本讀本(上)[C].汪民安,陳永國(guó),張?jiān)迄i主編,開封: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5:161.
[15]盧梭:論科學(xué)與藝術(shù)[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9:16.
[16]胡塞爾:歐洲科學(xué)危機(jī)和超驗(yàn)現(xiàn)象學(xu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6.
[17]貝爾納:科學(xué)的社會(huì)功能[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33.
[18]海德格爾選集(下卷)[M].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946.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21]埃里希•弗羅姆:占有還是生存———一個(gè)新社會(huì)的精神基礎(chǔ)[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10.
[22]ArneNaess,IdentificationasASourceofDeepEcologicalAtti-tudes[J].RadicalEnvironmentalism,PhilosophyandTactices,EditedbyPeterC.list,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1993:25.
[23][24]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tài)學(xué)———唯物主義與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