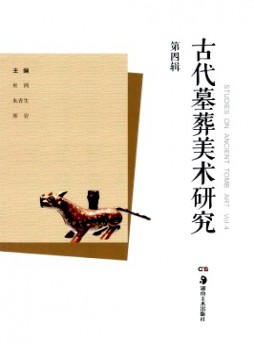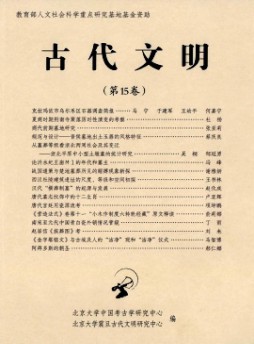古代藝術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古代藝術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作者:胡江平 陳勇建 劉超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武漢體育學院
一處就是周密在《武林舊事》記載中“瓦子勾欄”共有23處[9],本論者根據有關記載可能周密記載比較準確。瓦舍在兩宋時期的繁榮昌盛絕非偶然,它是當時商業和休閑娛樂業興旺發達的時代產物。由于宋朝工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發展,因此人民的娛樂閑暇時間比以往逐步增多。與之相應娛樂場所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并且成為市民休閑娛的社會生活的中心。因此,一種大眾休閑娛樂演出的場所——瓦舍,便迅速發展和壯大起來。
改變武術表演的場所當時市民在瓦舍里進行多種類型的演出,日夜不斷,非常的熱鬧每個大型的瓦舍都是一個綜合性的休閑娛樂文化場所,是市民休閑文化娛樂生活的中心,各種組織和團體在瓦舍里進行多種類型的演出,日夜不斷,非常的熱鬧。在瓦子中,由不同的藝人用欄桿等物分隔而成的一些小的演出場所,稱之為勾欄,又作勾闌、鉤欄,是指曲折彎曲的欄桿,“勾”有曲折、勾連之意。勾欄中設有戲臺、戲房(后臺)、腰棚(觀眾席)。勾欄中戲臺相當我們現代的舞臺,戲臺的出現會提高觀眾的視覺效果和環境氛圍。然而,表演者也會受到戲臺大小的限制。瓦舍出現之前,街頭賣藝的武師們,一般都是就地表演武術,對于場地沒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不會考慮場地的大小,更用考慮是否偏臺。瓦舍的形成卻發改變武術表演的場所,武術表演者不得不受到場地的限制,因此無論是個人演練,還是集體演練,對練在編排上都必須考慮場地大小的因素,改變原來的技術風格。然而,凡事總是一分為二的,表演者受到戲臺限制的同時,瓦舍卻為武術表演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表演平臺和環境氛圍。原先在街頭以賣藝為生的武師們可以去瓦舍這個固定的休閑娛樂場所表演,帶來固定的經濟來源。增加觀賞武術的群體《東京夢華錄•卷二》里記載北宋京都開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多座”。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此可以說明勾欄之多、瓦舍之繁華。而瓦舍的形成主要從以下兩面方影響武術觀賞者:瓦舍的形成增加了武術觀賞者隨著宋朝經濟發展和工商業的繁榮,在宋代都市中“,瓦舍”之類的娛樂場所相當盛行,大型的瓦子可容數千人。一些從事專門武術的藝人在瓦舍中表演“使棒”、“舞斫刀”、“舞蠻牌”、“舞劍”、“射弓”、“射弩”等,這些表演精彩無比,驚人、奇妙、刺激,緊扣觀眾心弦,觀賞者的眼球無不被這些武術表演深深的吸引住。大型的瓦子可容數千人,武術藝人在可容數千人的瓦子表演武術,是對武術的一次很好的宣傳,對民間武術發展起到一定促進作用。與街頭買藝相比,瓦舍的形成使武術表演者擁有了更多的觀眾。瓦舍的形成增加觀賞武術的群體一直以來,體育活動一直都是皇室、貴族、官僚、地主及富有的大商豪們娛樂消遣的工具,但由于瓦舍是一個綜合性的休閑體育娛樂場所,是市民休閑娛樂生活的中心,不限制于家庭出生背景,無論是有士大夫、達官貴員、俠士、還是地痞流氓、普通農民,只要買票就可以前去觀賞武術表演等節目。
因此,宋代體育活動不再囿禁于皇室、官僚、軍隊與貴族豪門,而是通過瓦舍這個表演平臺逐步走進了廣大的人民的生活中。武術表演也因如此,得到更多人的觀賞和喜愛。因此瓦舍的形成增加了觀賞武術的群體,為武術發展帶來了更多的愛好者。增加武術娛樂的功能武術源于古代人們的生產、生活,是古代人類早期與大自然的生存斗爭中自覺或不自覺掌握的一些防衛和攻擊技能。然而,為了滿足大眾娛樂的需要,宋代瓦舍中的表演活動主要表現為社會娛樂性,因此武術的表演色彩加濃,技擊性相對減弱,使武術形成了多樣化、大眾化、娛樂化等特點。軍事武藝注重的是一招致命,講究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將敵人殺死,而民間武師們比武時,同樣也追求在最短的時間將對手制服。在瓦舍表演武術,不論是單練,對練,集體演練,還是表演“使棒”、“舞斫刀”、“舞蠻牌”、“舞劍”、“射弓”、“射弩”等都要注重觀賞性,必然使武術的技擊性在一定程度會得到相適的削弱,從而使得帶有表演性的動作組合和武術套路相應產生。據《夢粱錄•卷二十》中記載“:先以女數對打套子,令人觀睹,然后以膂力者爭交。”其中“女”,指的是女藝人“;對”指的是一對一“;套子”就是動作組合。據史料證明,武術的套路組合也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的。因此,瓦舍的形成使武術增加了更多的娛樂功能,從而弱化了武術部分的搏擊技能,使武術慢慢的偏離了以前的格斗本質,使宋代武術形成了多樣化、大眾化、娛樂化等特點。促進武術組織的發展瓦舍表演是名目繁多的雜樂百戲,滿足了市民日常生活和節日休閑時出游觀賞的需求。同時,在瓦舍中出現大量的武術專業表演人員,他們以賣藝為生,成為瓦舍表演活動中的一支主力軍。正是由于宋代瓦舍中出現大批的武術表演專業人員,因此帶有武術性組織———“社”就在宋代社會應運而生。如以“弓、弩”為主的“踏弩社”這是當時人數最多的社,還有打拳使棒的“英略社、“錦標社”等[4]。宋代瓦舍的興起,為體育表演和體育觀賞活動的發展提供了良好表演場所和營造了良好的環境,同時標志著我國古代休閑體育娛樂性活動邁進了一個新的里程,不僅促進了民間武術組織的發展,還對我國民間武術的發展起到深遠的影響。
第2篇
本體“心源”說認為繪畫藝術源于畫家之“心”,那么,自然就會得出這樣的邏輯結論:畫家之“心”當然也就構成了繪畫藝術之本,繪畫藝術之本體只能是繪畫藝術家之“心”。所以,“寫形”是古代書畫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顧愷之的“以形寫神”說、張彥遠的“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說、荊浩的“畫者,畫也”說、王履的“舍形何所求意”[3]說、莫是龍的“傳神者必以形”[4]說等等,都包含著對“寫形”的肯定。顧愷之的“以形寫神”說,以“神”為本,寫形為手段,“寫神”才是目的。顧愷之是論人物畫,人物畫就是要畫出人物之“神”,并通過人物之“神”來體現畫家之“心”。山水景物畫也同樣如此。中國古代書畫的山水景物畫以“傳神”“寫意”為本,特別是宋元文人畫派,畫山水景物向來不以“寫形”為重,而強調對山水景物之“神”之“意”的傳達。南宋鄧椿《畫繼》云: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眾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元代倪贊《清閟閣全集》卷九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之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鄧椿把“傳神”看做曲盡萬物之態的“一法”,即根本方法。并指出,不但“人之有神”,而且“物之有神”,萬物皆有其神。畫出萬物之“神”,才是佳作。倪贊畫竹之目的,在于“寫胸中之逸氣”。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論氣韻非師》中把缺乏“氣韻”的畫看做“雖曰畫而非畫”。所謂“氣韻”“傳神”“胸中之逸氣”,皆本于畫家之“心”,或者說是畫家之“心”的體現。“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戴熙《習苦齋畫絮》云:“以目入心,以手出心,專寫胸中靈和之氣。”所謂“從于心”“心畫”“胸中靈和之氣”等,都是畫家的心靈精神,是畫之本體所在。
以“心”為本的繪畫本體論,又往往把繪畫看做性情的抒發表現。如《宣和畫譜》卷七載北宋李公麟之語曰:吾為畫,如騷人賦詩,吟詠性情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李公麟把自己的畫作看做類似抒情的詩歌,畫是自己感情精神的表現。而對世人不解其情,只把其畫當做“供玩好”的消閑品,非常不滿。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氣韻非師》云:“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畫。”畫是畫家“高雅之情”的寄托,“高雅之情”是畫之本體。石濤說:“筆墨乃性情之事,于依稀仿佛中,有非筆墨所能傳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卷二云:“畫與詩皆士人陶寫性情之事。”繪畫是“性情之事”,“性情”是繪畫之本。“性情”即畫家之“心”。與以“心”為本的繪畫本體論相關,古代書畫論家又提出了“意在筆先”與“畫盡意在”等畫學命題。如張彥遠認為:“意在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郭若虛說:“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象應神全,然后神閑意定;神閑意定,則思竭而筆不困也。”他們都強調了畫家在執筆作畫之前,應先創立自己的意境。唐岱曾具體地指出:“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縱橫萬里之勢。立身畫外,存心畫中。潑墨揮毫,皆成天趣。”布顏圖的體驗最為深刻與透徹,他說:“意之為用大矣哉!……故善畫者,必意在筆先。寧可意到而筆到,不可筆到而意不到。意到而筆不到,不到即到也;筆到而意不到,到猶未到也。”他們從不同的層次與角度,指出了“意”在繪畫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他們所說的“意”,或指藝術家創作構思時醞釀于胸中的審美意象,或指藝術家受客觀對象的啟發,在一定審美理想的觀照下,浮現在眼前的意境,或指藝術家自己的情意、意趣。藝術家創作時必須率先“立意”,因為此“意”為創作之本。
二、“心源”說與書法藝術
本體書與畫是最為接近的藝術。“畫者,畫也”,繪畫藝術以“形”的描繪為基本形式。書法則是一種點線筆畫藝術、結構藝術,書法家運用一定的筆畫、點線和結構布局,通過書寫漢字而成,也以“形”的描寫為基本形式。書與畫不但在形式上具有“寫形”的共同特點,而且在創作上也有共同特點,清代張庚《浦山論畫》云:“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書與畫有共同根源,二者的共同根源就是“心源”,二者都是寫心藝術。所以,“心”是繪畫之本體,也是書法之本體。清代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從語義學角度闡釋了以“心”為本的書法本體觀,云:后人不曰畫字,而曰寫字。寫有二義:《說文》,“寫,置物也”;《韻書》,“寫,輸也”。置者,置物之形;輸者,輸我之心。兩義并不相悖,所以字為心畫。若僅能置物之形,而不能輸我之心,則畫字、寫字之義兩失矣。無怪書道不成也。此番議論顯然是這位大書法家創作經驗的肺腑之言,體現了書法創作的抒情本質。《佩文齋書畫譜》卷五《記白云先生書訣》載書圣王羲之語云:“書法創作是‘把筆抵鋒,肇乎本性。’”這種以書寫心、借書“理性情”的藝術特征,同繪畫“從于心”“得心源”“陶寫性情”的藝術特征,在本質精神上是相通一致的。所以,張庚說“畫與書一源”,皆以心為源,以心為本。由于書法是人心的表現,書家之心不同,書法作品也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面貌。因此,通過書法可窺探人心。
第3篇
中國人自古講究忠、義、孝的所謂“氣節”,追求的是人的精神品格在現實社會中的實現,而不是脫離了社會倫常追求個人的永生。這種思想上追求,使得中國人注重對人物內在感受的特征描寫。作為人內心物化表現形式的雕塑,在這一方面的表現與繪畫有共同特點———不求形似,注重以型寫神,以達到神形兼備。中國畫無論工筆還是寫意,都不象西方油畫那樣精準的刻畫對象,而是主要依據體驗所得印象,再加上夸張的想像,經過主觀加工美化而成的藝術形象,和客觀對象保有相當距離,所以很多中國雕塑大師都講過中國繪畫妙再似與不似之間的話。就以西漢霍去病墓石雕來說,雕刻設計者并沒有直接表現霍去病本人,而是運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現作品的思想內容。巧妙的運用“因勢象形”的表現手法,霍去病墓石雕的創作者充分發揮了藝術的想像力,利用巨大石塊的自然形態進行創作,許多地方不加雕琢,而是利用巖石原有的塊面體積,使其保持自然趣味,在關鍵部位運用淺浮雕的形式塑造對象,而且這關鍵的幾筆也只是為了傳神,其他部位則十分寫意,顯示了意象性的特點。它們和中國畫一樣,追求神韻,注重表現事物內在,不以形似為滿足。
二、從外形看:注重輪廓線,追求韻律
線條,在中國繪畫中最常用、最簡潔的表現手段之一,中國畫十分注重線的力道和墨色的變化及組合韻律。線恰恰也是雕塑中最主要的表現手段之一。可見中國的雕塑藝術與中國的繪畫藝術一樣注重表現線條的藝術,中國古代優秀的雕塑作品,都十分注重表現輪廓線與身體衣紋線條的節奏和韻律,這些線條都像繪畫的線條一樣,經過高度概括提煉加工而成,每根線條都有用處,多一條則繁瑣,有畫蛇添足之嫌,少一根則殘缺,給人以未完成之感,并且粗細長短各有講究,在佛教造像中,常用粗且短、力道堅硬、顏色重的線條達到外形上的夸張,刻畫出面部猙獰身材威猛的天王形象,多以細柔的陰刻線刻畫菩薩頸下橫紋,表現其肌理豐腴細膩。在人物衣紋的處理方面更見出線條的功夫與魅力,線條的表現常常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更絕妙的是在人物的五官乎上近似與工筆畫的描摹。值得一提的唐代杰出雕塑家楊惠之,由他創造的“山水塑壁”的形式。中國寺院中常見的以連綿山水樹木為背景安排人物或故事的一種塑壁,便是從楊惠之首創的山水塑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表現形式顯然飾受到山水畫的影響,與寫意山水畫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從色彩看:三分塑,七分繪
中國古代雕塑講究“妝鑾”并把這一特色一直保留下來。從原始時代起,以及此后歷代雕塑多是“塑容繪質”,在雕塑上加彩(專業術語稱做“妝鑾”)以提高雕塑的表現能力。現存的歷代雕塑,有許多就是妝鑾過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三彩及佛像。而真正彩塑的出現還是于佛教藝術大量塑像有關。這里面有一個關鍵人物,是東晉的戴逵。作為一個文士和丹青高手,戴逵第一次對傳入中土的佛教雕塑進行改造。他的改造可以簡單的用“藻繪雕刻”四個字來概括。他不滿意傳入的佛像的簡陋樸拙,遂應用中國繪畫的手段和色彩進行彩繪和裝飾,以此創立了中國特色的佛教造像樣式。他這一樣式被后齊曹仲達、南梁張僧繇、唐代吳道子和周昉幾位大師繼承發揚,形成了中國曹、張、吳、周、四大佛畫體系,澤被后世。就泥塑而言,彩繪主要是兩大風格,一是用色工細濃艷,一是用色疏朗清淡。這兩種風格正好就是曹家樣和吳家樣的畫風特色。故北宋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愿者中指出:“雕塑鑄像,亦本曹、吳。”現在的美術學院里雕塑藝術學習西方,注重體積結構,光影對物體對影響,不再加彩,使得中國古代雕塑對這一優良技法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值得慶幸的是民間雕塑仍保持妝鑾傳統,民間彩塑以“三分塑,七分繪”為主,多以概括簡練的造型,飾以大紅大綠等各種鮮艷色彩,簡單的造型,明亮歡快的色彩,寄以美好愿望和祝福,彰顯勞動人民的智慧。
四、結語